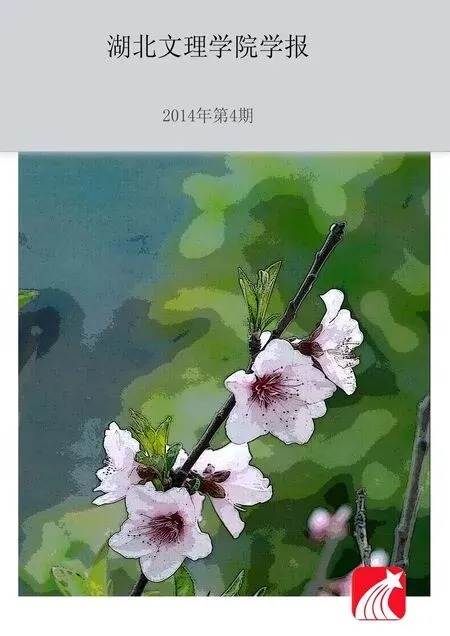创造社诗人写作的“个人性”与“公共性”
——以穆木天为例
易亚云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北碚 400715)
随着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学界对于文学“公共性”展开了系列讨论,并明确提出了中国新诗的“公共性”问题。
以郭沫若、穆木天为代表的创造社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大都经历了诗风转换的过程,由重表现自我到书写社会现实,实现了“个人自我”向“民族国家自我”的转化,在凸显鲜明的个人性的同时,又充分体现了时代社会的公共性特征。
一、“公共性”与“个人性”关系的简要阐释
谈及“公共性”问题首先必须了解“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这个词,在他看来,“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共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1]陶东风在此基础上认为“公共领域是自主自律的个体通过主体间的理性、平等、公开的交往形成公共意见的领域。”[2]文学公共领域虽然区别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公共领域,却为资产阶级政治公共领域准备了具有自律性和批判性的公众。
对于“公共性”,汪晖在《文化与公共性》中认为,“尽管公共世界乃是一切人的共同聚会之地,但那些在场的人却是处在不同的位置上的……事物必须能够被许多人从不同的方面看见,与此同时又并不因此改变其同一性,这样才能使所有集合在它们周围的人明白,它们从绝对的多样性中看见了同一性,也只有这样,世俗的现实才能真实地、可靠地出现。”[3]即注重文学公共领域的多样性。因而,在本文中,我们便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语境下,共在的具有差异的个人性达到了同一,就形成了“公共性”,就代表着公共领域的一个整体的价值取向。
就“公共性”和“个人性”的关系而言,普遍认为二者是对立的存在。而陶东风认为“私人经验的描写丰富了读者对于人性的认识,培育了他们的主体性,因此也为这些人进入公共领域准备了条件”[2],看到了二者相辅相成的一面。
在本文中,我们认为,“公共性”与“个人性”是对立统一的。首先是二者的对立一面,“公共性”是大众的,普遍的,与公众息息相关的,而“个人性”则是个体的,特殊的,更多的是与自身相关。另外,也应看到二者的统一的一面。“公共性”的形成离不开“个人性”,每种共同的社会观念或价值的倾向中都必然包括了无数的具有差异个体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具有一种普世价值的个体性观念,如人文关怀、独立自由等等,同时,“个人性”也离不开“公共性”,公共事件的发生会触发和刺激到个体的生命体验,当无数的个体性生命体验在公共领域经过理性的、平等的、民主的对话达成共识,普遍化,便成为了当时公共领域的共同的价值取向,具备了公共性,“公共性”表现和反映出社会的大多的“个人性”的整体的价值需求。
具体到诗歌领域,诗歌的公共性则是强调诗歌书写和表现人文关怀、民族苦难、独立自由等等,而对个体的生存际遇、生命体验等的观照则有助于公共性的建构和表现。
二、穆木天诗歌“个人性”的表现:生命体验
创造社崛起于“五四”时期,“五四”是狂飙突进的时代,大胆的破坏,彻底的毁灭,破旧立新的时代,人的主体性得到空前的张扬,个性解放、独立自主成为时代的主潮流,这便要求在诗歌中表现自我,凸显人的个性和生命意识的觉醒。
穆木天,创造社后期的代表人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走出国门,前往日本求学的的青年留学生,在求学的岁月中,他摆脱了家庭、社会和固有的封建落后的思想文化的束缚,在异域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受,具体表现在“美化人生,情化自然”和“异国情肠”两个方面。
(一)“美化人生,情化自然”
穆木天曾说,“诗是内生活的真实的象征……诗是内生命的反射,一般人找不着不可知的远的世界,深的大的最高生命”[4]261,强调诗歌书写个体的真实的生命体验。五四的浪潮使他意识到了自我存在于世界上的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他在诗歌中呈现出一个对人生充满美好向往的生命形象,他在歌颂自然,歌颂爱情,歌颂生命。
穆木天的第一部诗集《旅心》主要是他在日本留学时候的创作,这时候的他较多地保留着孩子似的“童心”,如《心欲》其一:“我愿作一个小孩子/濯足江边的沙汀/用一片欢愉的高笑/消尽胸中的幽情……”[5]5,诗人如同孩子般稚气纯真,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好,向往着自由,这是一个有了自我意识的生命体对自然,对世界,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诗人在诗歌中常把对美好人生的向往和对大自然的喜爱结合在一起表现,如《雨后》,细雨濛濛的雨后到湿润的田里去,去听自然的声音,感受生命复苏的喜悦。诗人笔下的自然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是他“内生命”孕育的大自然,诗歌的韵律便是自然的旋律,生命的节奏,人生和自然相结合,美化了人生,情化了自然。
在诗歌中,穆木天呼唤新生,呼唤个性,呼唤自由,此外,破除了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的束缚,在追求个性解放的同时也呼唤爱情。
诗人在诗歌中多次出现“妹妹”这个词,这个“妹妹”也许是他自己暗恋又失恋的那个少女,也许是不具名的,仅仅是他爱情投射的对象,是他倾注了情感与心血塑造的一个形象,“妹妹”的泪滴是珍珠的泪滴,是水晶的泪滴,是白露的泪滴,是最美的新酒,是世上最美的泪滴,“妹妹”就是一切美好的代名词,是爱情的象征。“我不愿做炫耀的太阳/我不愿做银白的月亮/我愿做照在伊人的头上/一点小小的微光”[5]7。诗人在《我愿做一点小小的微光》中坦陈自己的爱的真诚,执着,甚至是卑微,只因我爱你,所以甘心做你头上的小小的微光,不奢求其他,只愿照着你的孤独与悲伤。这与诗人徐志摩的诗歌《偏见》有异曲同工之妙:“一生至少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有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
诗人或许真是将情感投注在某个具体的对象身上,但更大的可能是因为在那个崇尚解放一切的年代中,诗人是以坦率地告白爱情追求而表现出对封建礼教的挑战和反叛,是对自由爱情的赞颂。
穆木天的“美化人生,情化自然”的诗歌创作,正是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受日本的自然山水、民俗文化等的浸染和陶醉而形成的,是他的真实的生命体验,是独具人性的情感表达。
(二)“异国情肠”
留学日本期间,穆木天对日本的山水、风俗、文化等都有强烈的心灵感应,他深吸着“异国的熏香”,想象着“民族的色彩”,看着异国的风景和人事便生出了“异国情肠”。
诗人自己在《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中写道:“那是异国的熏香,同时又是自我的反映,要给中国人无限启示的世界。”[4]265诗人笔下的日本都沾染了故国的气息和色彩,如在《薄暮的乡村》、《山村》两首诗中描绘着村庄、草舍、院墙、余烟、白杨、牧童等物象和具体的生活场景,虽然是他在日本乡间的生活和感受,但显然这些都是诗人十分熟悉的故乡农村人的生活,都具有本民族的生活气息和色彩,触景生情抑或是移情于景,异国之景便是故国之景的直接呈现。
诗人经常会想起故乡,在“江雪”时节,会想起故国那座“肃慎的古城”;在“落花”时节,会想起“人生的故家”;在“北山坡上”时,会想起“甜蜜的家乡”、“心欲的家乡”;在“苍白的钟声”里,会想起“永远的故乡之钟声”……还有水声、歌声,无一不唤起诗人浓烈的“异国情肠”。
除却借景抒情,诗人更是直抒胸臆,直陈自己满腔的思国怀乡,希望祖国强大之情。如《心响》:“几时能看见九曲黄河/盘旋天际/滚滚白浪/几时能看见万里浮沙/无边荒凉/满目苍凉 ∥ 啊 广大的故国/人格的殿堂/啊 憧憬的故乡呀/我对你/为什么出现了异国的情肠……”[5]41,诗人在诗中展现了一个异域漂泊的学子对祖国的深切的怀念,并热切希望祖国强大的民族情感。同为创造社成员的郁达夫,也曾留学日本,对于留学期间的生活和心境,在他的文章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兼具了怀念祖国和对祖国的不认同,希望祖国强大的思想情感,如《沉沦》。“异国情肠”表现出诗人对祖国的怀念和不认同,希望祖国强大的矛盾的心态。
究其创造社整体而言,创造社在早期以浪漫主义崛起于诗坛,他们的大胆创造、个性解放、表现自我等的精神和风格正好适应了那个狂飙突进的时代的创作需求与社会审美心理,因而能迅速展开并发展,这是其“个人性”与“公共性”统一的一面,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创造社区别于当时时代主流的一个具有“个体性”的特点是感伤主义,这是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悲观颓废的情绪,与当时时代主潮格格不入。如穆木天也在诗歌中表现出了这种虚无和颓废的生命体验,如《鸡鸣声》:“鸡鸣声/唤不起/真的/哀悲/我不知/哪里是家/哪里是国/哪里是爱人/应向哪里归/啊 残灯/颓废……”[5]62,这是理想和现实的极大的反差带来的,是看不到希望的绝望,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控诉,在哀叹中带着反抗。
三、穆木天诗歌“公共性”的表现:革命情怀
五卅运动之后,严峻的国内形势促使新文学开始向左翼文学转变和发展,“文学革命”演变为“革命文学”。在中国知识分子陷入极端苦闷和悲观颓废的时候,“革命”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可能,新文学作家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生活和时代现实,其创作也慢慢地趋于革命化和意识形态化。在这种大的时代环境和社会背景下,创造社诗人也顺应整个时代的公共性潮流,转变自身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的个体性特征,鲜明地体现出“公共性”的特点,对革命现实的关注,强烈的政治热忱,拥抱革命现实,弱化文学性,强化政治性、社会性和革命性,如郭沫若,从《女神》到《恢复》,诗歌创作实现了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
穆木天,早年留学日本,随后回国,大学任教,参加左联,投身到左翼文学运动,组织中国诗歌会等等,这些人生经历都和其诗歌创作息息相关。早先诗人醉心于象征主义的诗歌创作,但是这种风格逐渐不适应于当时的社会革命现实,诗人认为自己以往的诗歌创作都是“一场幻灭”,并在《我的文艺生活》中写道,“诗我是再也不作了,因为那种诗,无论形式怎么好,是如何有音乐性,有艺术性,在这个时代,结果,不过是把青年的光阴给浪费些”[4]200,于是,在“目睹着东北农村之破产,又经验着“九·一八”的亡国的痛恨,感到了诗人的社会的任务……在此国难期间,诗人是应当用他的声音,号召民众,走向民族解放之路。诗人要用歌谣,用叙事诗,去唤起民众之反对帝国主义的热情的”[4]242,诗人转而关注社会现实,“为民族生存和革命需要而提供新内容”,以成为“全民族的代言人,感情的传达者”[4]356为目标,其诗歌极具革命情怀,具体表现在“苦难的抒写”和“胜利的喜悦”两个方面。
(一)苦难的抒写
改变了着重抒写个人生命体验的创作倾向,诗人注重“国民生命”和“个人生命”的交响,着力描写国民的生存现状和生命体验。穆木天在《我的诗歌创作之回顾——诗集<流亡者之歌>代序》中写:“我总是热望着,像杜甫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似的,把东北这几年来的民间的艰难困苦的情形,在诗里,高唱出来”[4]214,同时,诗集命名为《流亡者之歌》也主要是突显其为“帝国主义压迫下的血泪的产物”。因而,诗人在描绘“国民生命”时就主要刻画内忧外患中国人民的苦难生存,注重苦难的抒写。如诗集《流亡者之歌》,其基本主题就是揭露并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屠杀,同情东北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呼唤并赞扬人们的反抗精神。就诗集中的《扫射》诗而言,诗人用带恨、带泪的笔触真实地记录了那件令人震惊的血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以照相为名欺骗手无寸铁的民众,将其枪杀,并谎称为“皇军大败义勇军,毙匪五六千人”,但谎言是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的;无独有偶,《守堤者》一诗中,人们“狂叫着:守堤!守堤!哀呼着!狂叫着!在鞭一般的枪声中,一个一个的倒下”[5]112,又是一场血淋淋的屠杀……诗人用大量的笔墨来抒写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恶,和谐宁静的土地变成了饿殍遍野,民不聊生,这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深重的苦难。
面对苦难,面对侵略,诗人将个人情绪和民族情绪相结合,热忱地呼唤革命,呼唤反抗,如在《写给东北的青年朋友们》、《又到了这灰白的黎明》等诗作中,诗人以“朋友”为倾诉对象,让“朋友”认清这血的事实,呼唤着“朋友”起来反抗,“朋友/低下头看这被压迫的民众/朋友/培养革命的意识/写尽他们的悲哀”,“朋友/只要我们努力/我们抗争/朋友/那时我们要造成为人类的永远的劳动”。[5]72
(二)胜利的喜悦
诗人在诗歌中忠实地记录革命实况,表现出自己“客观的真实性的崇高强烈的感情”,也真实地传达了那个时代的人们普遍的情绪体验。
在革命如火如荼地向前发展的时候,穆木天不惜笔墨地对于革命予以极大的礼赞,如《全民族的生命展开了——黄浦江空军抗战礼赞》、《武汉礼赞》,诗人大力称颂全民族抗战,热情地期待着胜利;在革命陷入僵局,进入最压抑的阶段,穆木天对于“祖国的光明的前途,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他在《我并不悲观》中写道:“我永远不会悲观,我也永远不会消极,我感到了空前的烦躁,也许正是因为我怀着热烈的憧憬”[5]280;在革命终于取得胜利的时候,诗人不禁狂喜,在《在自由的天地中欢呼吧!》更是热情地展现自己及公众对于革命胜利的喜悦,“我们在自由的天地中走来走去/我们自由地呼吸/新中国的远景在我们的眼前/伟大的世纪已经开始/全中国/全世界/劳动人民/所期待的日子/终于到来”[5]310。
国难这种公共性事件触发了诗人的生命体验和感受,让诗人一改象征主义的诗歌创作风格,提出要做“我们的诗”,要抛弃形式主义的空虚,诗歌应该是“民族的乐府,大众的歌谣”,有“奔放的民族热情”,是“自由的民族史诗”。[5]124于是,诗人抒写苦难,诅咒侵略,呼唤反抗,并对革命抱有必胜的信心,这正是当时革命形势下,人们所具有的公共性的反帝爱国的心理。
时代和社会对诗人及诗歌所要求的是社会责任、集体认同等,要求诗人成为时代或民族的“代言人”,但在诗人的创作表现社会关怀一面的时候,也应看到诗人对个人自由的追求。穆木天的诗歌创作在后期主要是表现革命和抗战的主题,以适应时代的主潮,但诗人在回到西南地区时期进行的创作,如诗集《新的旅途》,是他在西南地区生活和情感的写照,是极具个人性的创作,诗歌立足于自我创作,增强了自我的人生感触,如诗歌《月夜渡湘江》、《寄慧》,反映的时代背景仍然是抗战,但此时的诗人更多的是在这种环境下对自己心灵的观照,是面对战争自然而然生发的,不再是对历史现象的简单阐述或摹写,诗歌在这个时候就是他的生活,是他这个人本身,这是他的诗歌创作中“个人性”的表现,或者说是区别于“社会性”的一面。
诗人公木曾在悼念穆木天的文章中说:“诗人木天的一生,笑对坎坷,勤奋写作,以生命为诗,并以诗为生命。从早期醉心象征主义……发展到二十年代后期有意识地向现实主义转化,‘显出作者与人民的联系’,直到三十年代初,更承担了左翼文学运动中诗歌方面的任务,成为中国诗歌会的带头人……从起点到迈步前进,一直与历史主线相结合”[6]。公木在文章中直接述说了穆木天的诗歌创作的个人风格的前后转变。前期的象征主义,主要突显其独具个人性的真实的生命体验,后期则在革命大潮的影响下,走向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正符合了当时社会的主潮,是公共性的具体体现,这前后期的风格的变化,是“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对立的表现,同时,其创作转变与“历史主线”的相辅相成,则又表现出了穆木天诗歌创作的“公共性”与“个人性”的统一的一面。
同样,以穆木天为代表的创造社诗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面对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的时代潮流,他们大都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渡,由注重表现生命体验到革命情怀的抒写,虽然这个转换是顺应时代潮流,也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创造社的思维和创作的转换过于殷切、急迫,就必然出现主观思想的实际水平与主观要求之间的矛盾差距,创作的审美习惯定势与现实功利取向之间的矛盾差距”[7],所以,对于创造社诗人的诗歌创作我们还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1]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2] 陶东风.论文学公共领域与文学的公共性[J].文艺争鸣,2009(5):28-34.
[3] 汪 晖,等.文化与公共性[M].上海:三联书店,1998:88.
[4] 蔡清富,穆立立.穆木天诗文集[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5.
[5] 穆立立.穆木天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6] 公 木.穆木天研究论文集[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0:1.
[7] 龙泉明.对于一种社会成规的革命——创造社诗歌创作综论[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4):7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