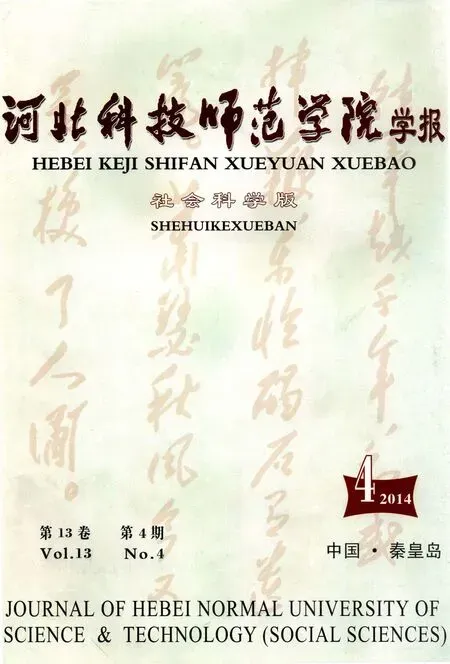无名的“他”——凯瑟琳·安·波特短篇小说《他》中的身份焦虑解读
魏 懿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442)
美国著名作家罗伯特·佩恩·沃伦曾高度称赞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的短篇小说,认为它们在“现代文学中是无与伦比的”[1],并把波特与其他以短篇小说而闻名的作家如詹姆斯·乔伊斯、海明威以及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等相提并论。波特已被公认为美国现代文学史中最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她和尤朵拉·威尔蒂及弗兰纳里·欧康纳被认为是美国南方现代文学中的三位重量级女作家。但目前国内对于凯瑟琳·安·波特及其小说创作的关注度不高,相关的研究也较为薄弱和浅显,尤其对于波特作为一名南方女性作家对于南方人身份意识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本文通过分析凯瑟琳·安·波特的短篇小说《他》来探讨这篇小说中所隐含的作者对于美国南方人身份缺失的焦虑,以期推进国内凯瑟琳·安·波特的相关研究。
一、一场打败了的战争的孙女
凯瑟琳·安·波特1890年5月15日出生于美国南方德克萨斯州印第安河市,其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波特的母亲玛丽·阿莉斯·波特在波特两岁时因病去世,在此之前这个美国南方大家族便已家道中落。在妻子阿莉斯去世之后不久,波特的父亲哈里森·波特便带着小波特和另外四个孩子前往路易斯安那州自己母亲的家中。也正是在祖母卡特的照料和养育下,波特听说了有关南北战争前的“老南方”的故事以及南北战争后整个“老南方”的失落。祖母关于“老南方”的讲述使得波特对于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南方社会有着深深的眷恋。尽管她本人并未亲身感受过“老南方”的魅力,但通过家族中长辈对于“老南方”生活的讲述,她从小便对于“老南方”充满了好奇。波特曾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说到:“我是一场打败了的战争的孙女儿,我对于在一个战败的国度上所经历的生活有着血淋淋的了解。我家族中的长者常常会向我讲述相关的小故事。”[2]美国南北战争中北方美利坚联邦的胜利彻底摧毁了建立在奴隶种植园经济之上的“老南方”,昔日恬静、优雅的“老南方”生活成为了波特家族中长辈们的回忆。历史学家埃德沃德·埃尔和布莱德勒·米顿道夫认为:“在南方历史上,内战是最为重要的事件。无论自由人还是奴隶,黑人还是白人,男人还是女人,富人还是穷人,战争都改变了人们生活的全貌。”[3]美国南方人对于自我南方人身份的自信与骄傲在南方联盟军的节节败退中变得分崩离析。战后尽管重农主义曾让美国南方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随着美国北方资本主义的日益侵蚀,南方的种植园经济进一步凋敝,南方原有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也面临着被北方同化的处境。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南方诗人约翰·克罗·兰瑟姆在《我要表明我的立场》一文中就说到:“我们(指南方人)都支持南方的生活方式,反对所谓的美国式或流行的方式;我们都同意能形容这种分歧的最好字眼就是农业化对工业化。”[4]面对昔日辉煌的农业化的“老南方”以及今日日益被同化的工业化的“新南方”;面对一个北方话语权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美国,南方人对于曾经优越于北方的南方文化以及自己作为南方人的身份价值出现了质疑和困惑。这也使得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南方文学充满了对于南方人命运的焦虑和危机感,正如美国文学评论家路易斯·辛普森所说:“美国白人作家更愿意把他们在一个机械的金钱的文化中感受到的异化与南方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5]威廉姆·福克纳、托马斯·沃尔夫、艾伦·泰特等南方作家的作品无不透露出作者本人对于南方社会命运的思考以及对于南方人身份的焦虑。作为一位生于19世纪末期的南方作家,凯瑟琳·安·波特的童年岁月便是在重农主义思想抬头和新南方的喧嚣骚动中度过的。波特从小耳闻目睹“老南方”的故事,对南方的故土有着深深的眷恋。一方面,她认为老南方已经不复存在,“老南方”的往事就“如同好莱坞构想出来的已经颓败的后罗马帝国时代”[6],一样虚无而遥远;另一方面,波特对于新一代南方人被北方文明同化的大趋势感到痛心疾首,她曾在自己的文章里对南方人在北方工业和消费文明中逐步堕落感到十分失望和痛心,“你如今到德克萨斯州去,即使是中产阶级,他们(指南方人)除了从电视里知道的东西之外,其他一概全都不知。”[7]处在这样一个“老南方”一去不返、南方文化面临着被北方同化的新南方社会中,波特自然会关注南方人的命运与身份问题。同时作为一名以精雕细刻闻名的女性作家,波特更是以女性特有的曲折含蓄的笔触有意无意将自己对于南方人身份的思考与焦虑融入小说的创作中。她的短篇小说《他》就是这样一篇短小精悍,但却又暗藏深意的作品。
二、无名的孩子:身份缺失的焦虑
写于1927年收录在波特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开花的犹大树与其他故事》中的《他》描写了一个缺少家庭温暖,并且最后失去身份的南方小男孩的故事❶小说没有明确指明故事发生的地点,但根据小说中周围邻居对于‘他’血统纯正性的质疑以及惠普尔太太对于家族血统的重视都带有较为鲜明的美国南方社会的特点。此外,小说中的艾德纳和埃姆莉并没有采用Adner和Emily的拼写形式,而是使用了Adna和Emly,这是模仿这两个名字在南方方言中的发音。这些都说明小说《他》的故事地点应在美国南方。。
惠普尔一家是一户普通的南方家庭。他们生活得十分拮据。惠普尔先生是一个务实主义者,他常抱怨生活的艰辛,并有时会向邻居吐苦水,而惠普尔太太则秉承南方好面子的传统,不愿让周围人看出自己窘迫的生活。“千万别让哪一个人听到咱们在抱怨”[8]282,她一直跟她的丈夫这么说。她受不了让别人觉得可怜。“不,哪怕咱们落到不得不住在大车里,在这一带地里摘棉花,也不能让人觉得可怜”,她说,“没有人会有可能瞧不起咱们。”[8]282好面子以及虚荣的幻想使她渴望着自己的家庭能变得富有,但阻碍他们发家致富的障碍便是他们那个似乎智障的儿子“他”。尽管惠普尔太太表面上极力表现出对于“他”的关爱和表扬,“‘他’是这么结实,欢蹦乱跳,‘他’什么事情都要插上一手;打‘他’会走路起,‘他’就是这个样”[8]283,但在内心里,她对这些虚伪的关爱非常憎恶。“要是‘他’死了的话,那倒是老天爷做了一件大好事了。”[8]283为了摆脱“他”这个发家致富的累赘,惠普尔太太允许“他”爬很高的树、要求他做许多超出“他”年龄所能承受的重活、让“他”去对付蜜蜂因为他似乎不怕被蛰、叫“他”去牵凶狠的公牛,并让“他”从一头凶残的母猪身边去偷一头小猪仔。总之,想尽了各种办法想要“除掉”这个智障的儿子。为了能让另外两个孩子艾德纳和埃姆莉在冬天穿着得体,睡得暖和,不会感冒,他们竟然将“他”床上的被子抽去一条给埃姆莉,因为他们觉得“‘他’似乎从来不在乎冷”[8]284。对于一个孩子而言,这样的家庭环境可以说是极度缺少关爱。父母兄弟姐妹只把“他”当作一个不说话的劳工和碍事的累赘来对待。南方家庭原本十分注重的家庭亲情纽带在惠普尔一家已经荡然无存。
20世纪初随着重农主义思想在南方抬头,重建庄园、变得富有的想法在南方开始流行开来。“老南方”原本温情脉脉的家庭人际关系开始被功利主义和金钱关系所替代。随着北方价值观的不断渗透,对于财富的渴望在许多南方人的心中变得根深蒂固。小说中的惠普尔夫妇,尤其是惠普尔太太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他们渴望摆脱窘迫的生活处境,渴望获得财富,过上好日子。“老南方”曾经所崇尚的荣誉、仁慈、博爱等优秀品质,在他们的头脑中已经像虚幻的“老南方”一样随着战争的远去而消失了。他们所想的只有实实在在的财富,对于财富的渴求迷失了他们为人父母的心智。不过,在惠普尔太太以及周围人的身上有一点继承了“老南方”的传统,那便是对于血统纯正的讲究。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邻居们背着惠普尔两口子谈论这件事的时候,这两口子就没法不让他们说心里话。‘要是“他”死了的话,那倒是老天爷做了一件大好事,’他们说。‘那是他们祖上作的孽,’他们背地里这么说。‘准是祖上做人缺德,干了坏事,包管你错不了。’背着惠普尔两口子,他们说的就是这一套。”[8]283在邻居们看来,“他”的弱智状态并非是因为生理的缺陷,而是因为祖上的关系,或更确切地说,是因为血统的关系。由于不纯的血统玷污了南方所强调的纯正血统观,惠普尔一家遭到了鄙视。凯文·雷瑞在《天生的贵族:历史理想和威廉姆福克纳的作品》一书中认为,在南方社会“种族纯洁或是血统纯正是判断是否属于上流阶层的决定性特点。”[9]血统的纯正往往又和家庭的名誉联系在一起。惠普尔太太是极其要面子、十分看重家庭名誉的一个人。这在小说中有多次的表现,例如,她不愿让别人可怜自己,即使是自己的弟弟,惠普尔太太也不愿放低姿态,“我家的亲戚偶然来看咱们一回,咱们竟然拿不出一餐象样的饭菜来,那才叫丢人现眼哪,多寒碜啊”,“我不愿让他的妻子回去说,在我家没有一点儿吃的。”[8]286作为一名不愿让别人觉得可怜的南方女性,周围人对于“他”的血统不纯的质疑恰恰是惠普尔太太最难忍受的事情。惠普尔一家尤其是惠普尔太太似乎也赞同邻居们的看法,认为‘他’是惠普尔家族祖上做的孽,尽管她极力表示:“这个天真的孩子在老天爷的保护下活动——所以‘他’不会受伤。”[8]284但在她内心深处,她仍然觉得“他”玷污了家庭的名誉。“她总是觉得胸口有一个暖乎乎的池塘在漫出水来,眼眶里会全是眼泪;接下来,她就能谈别的事情了。”[8]284惠普尔太太和周围邻居们的态度实质上反映出来了新老南方交替之际南方人复杂的心理变化。一方面,对于财富的追求等功利主义思想已经深入南方人的心里,原本“老南方”温馨的家族血缘关系开始逐步瓦解;另一方面,“老南方”的某些观念,例如对于纯正血统的讲究和家庭名誉的重视,仍然残存在许多南方人的意识中。
当新老南方交替的冲突集中在一个弱智的孩子身上时,“他”受到创伤也就变得不可避免了。在小说中,“他”的创伤来自两个方面:身体上的和心理上的创伤。外在身体上的创伤显而易见,文中有多次描写道“他”的身体上的创伤,例如:养鸡室的木板给风吹下来,砸在“他”的脑袋上;被蜜蜂蛰;被惠普尔太太恨恨地掴耳刮子等。但隐藏在这些身体创伤之下的是“他”心理上的创伤——对于自我身份缺失的焦虑。在整篇作品中“他”始终都没有自己的姓名,邻居、父母以及兄弟姐妹都一直以“他”这个人称代词来称呼“他”。米兰昆·德拉认为:“一个名字意味着过去的延续,没有过去的人们是没有名字的人。”[10]名字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和符号,名字的缺失意味着“他”失去了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名字使一个人从小能从语言和家庭的角度认识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及自己的身份。但在惠普尔家庭中,“他”名字的缺失意味着“他”和整个家庭关系的割裂。“他”不属于父母亲任何一方的家族血统,而是一个被放逐的“他者”。生活在这样一个老南方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新南方的财富价值观念并存的家庭中,“他”的身份显得极为尴尬,名字的缺失意味着自我身份的缺失,意味着过去历史的缺失。“他”既不属于“老南方”,因为“他”是祖上造下的孽,“他”没有老南方所看重的纯正血统,玷污了家庭的名誉;“他”也不属于新南方,因为“他”的弱智状态是南方家庭摆脱贫困追求财富的一大障碍。“他”这个无名的孩子卡在了新老南方的夹缝中。这种尴尬的处境折射出的是作者本人对于迷失于新老南方交替中的南方人的身份焦虑。一方面,“旧南方随着战争‘死去’了,但同时又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顽固地‘存活’着。‘死去’的是社会的、经济的南方,‘存活’的是文化的、心理的南方。”[11]老南方的“幽灵”仍然存活于新南方之中,就像惠普尔太太和周围人所看重的血统与家庭名誉等老南方传统观念仍然影响着新一代南方人。另一方面,随着北方的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经济越过迪克西线,南方人在感叹北方物质生活优越于南方的同时,又不得不面临着南方日益北方化的现实处境。传统在现实中的残留与日益被北方同化的现实使得南方人处于观念和身份的焦虑之中。处在新老南方夹缝中被剥夺了名字的“他”正是这种焦虑人物化的体现。
三、家庭与社会的抛弃——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抛弃
如果说“他”的无名状态意味着个体与南方的家庭纽带之间的断裂,意味着由于自己不纯正的血统受到了历史即老南方的抛弃。那么,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他”被母亲送去县救济院则意味着个体被南方家庭彻底抛弃,意味着个体与整个新南方社会的彻底隔离。
尽管在父母和周围人眼中“他”是个傻子,但“他”已经察觉到自己在惠普尔家庭中失去位置这一现实。“他”极力地想挽回家人尤其是母亲对自己的爱。于是“他”有意无意地承担起惠普尔一家的大部分体力活,终于在一个大冬天,“他”病倒了,生病的原因竟是因为“他”冬天没有暖和的衣服穿:“他们削减一切开支,可是惠普尔太太一直说,有些开支你是没法削减的,他们得花钱……‘他’几乎老待在炉火旁,用不着穿那么多’。”[8]290即使在生病期间,“他”仍被打发出去放牛。直到“他”的病变得越来越重,惠普尔两口子才没有办法,决定只有将“他”送去县救济院里治疗。如果说失去名字意味着“他”失去了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成为了一个家庭中的“他者”,那么被送去县救济院意味着“他”彻底被家庭乃至整个社会所抛弃,失去了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对于自己的无名状态所造成的家庭地位的缺失,“他”还能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来挽回——通过付出自己的劳动力来维系个体与家庭的联系。但面对自己将被送去县救济院的命运,面对将彻底与外部世界隔离的前景,“他”则显得无能为力。
这个在惠普尔一家人的眼中看起来不知冷暖、没有感情、“会把一头猪一股脑儿吃下去”[8]287的傻子竟然落下了眼泪:“‘他’坐在那儿,眼睛一眨一眨。‘他’好不容易才把双手从被窝里挪出来,用指关节擦着鼻子,后来用被子的一头擦起来。惠普尔太太简直没法相信她看到的东西;‘他’在擦掉从眼角里涌出来的大颗大颗泪珠。‘他’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发出一阵抑制的哭声。”[8]196从他的哭泣的行为举止中,可以看到“他”对于被剥夺了家庭中的位置并被强行割断家庭纽带的恐惧。被送去县救济院代表着被母亲拒绝、代表着被家庭和现实世界拒绝、代表着陷于一个既没有过去又没有未来的状态。这种状态其实正是当时新旧交替时南方人的心理写照。“他”的身份缺失是新一代南方人对于自我南方身份焦虑的体现。在美国历史上南北战争割断了南方的历史进程,从而也割断了战后南方与战前的历史联系。此外,战后北方文明的不断“入侵”使得南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变得更加混乱。小说中“他”的妹妹埃姆莉在镇上的一个铁路食堂里当起了女侍者,而“他”的弟弟艾德纳也离开家另谋生路。埃姆莉和艾德纳相继离开土地前往城镇寻找机遇,这意味着新一代南方人对于以土地为根基的老南方价值观念的抛弃,同时也是南北战争后北方文明对新一代南方人思想和价值观念上同化的结果,而与此同时老南方残留的某些观念继续在现实中“阴魂不散”。从象征角度而言,“他”的母亲——惠普尔太太——正是南北战争之后老南方文明与北方文明纠结状态的集中体现。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惠普尔太太这一人物身上同时存在着南方纯正血统观念和北方功利主义观念,即她是老南方意象与新南方意象的混合体。作为惠普尔太太的儿子同时也是家里唯一留在土地上帮助种地的孩子,“他”的缄默、名字的缺失以及被送去县救济院时的痛哭都象征着新一代南方人在面对新老南方交替时对于自身身份的不知所措,同时也折射出美国新一代南方人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集中究竟该何去何从的焦虑感。
惠普尔太太从本质上来说仍属于“老南方”,除了她看重名誉和血统的纯正外,她对于家庭的意识形态也属于“老南方”。小说中有一段惠普尔太太憧憬未来美好生活的心理活动描写:“她一下子又看到盛夏光景了,园子里景色迷人,房子上尽是崭新的遮阳光的包窗帘,艾德纳和埃姆莉都在家里,处处是兴旺的气派,他们都快活地生活在一起。啊,这可能会成为事实,他们的光景会好起来的。”[8]296惠普尔太太畅想着的未来家庭的美好前景:明媚的阳光、崭新的窗帘、兴旺的花园、父母与子女其乐融融生活在一起。惠普尔太太所憧憬的是一派典型的南方家庭的宁静与和谐。但是可以发现,在这个家庭氛围中有惠普尔太太的另外两个孩子——艾德纳和埃姆莉,但却唯独没有“他”的存在。“他”与南方家庭的意象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他”血统不纯正,所以“他”不属于过去和历史,并且在现实生活中被剥夺了身份。如今,“他”又将被送去县救济院,意味着“他”被家庭和社会都抛弃了,在县救济院里“他”将完全与现实的南方社会隔绝。从这一意义上而言,“他”遭到了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抛弃即“老南方”与“新南方”的双重抛弃,这也正是波特这一代南北战争后出生的新南方人面对父辈们的历史和新南方现实时所处的身份困境——既不属于过去的老南方,也不属于现实的新南方。正如安德尔·布雷凯斯顿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指南方人)坠入历史的同时也被排挤出了历史,使他们多年来生活在一种震惊、困惑、麻木,和消亡的过去对峙的状态。”[12]对于新一代南方人而言,过去虽已死去,但其痕迹仍在影响着现在,现实并未真正摆脱过去的纠缠,一个既不属于历史、又不被现实所接受的“他”代表着每一个新南方人对于自身身份的焦虑。
关于南方历史的回顾以及对于南方人身份的思索一直是美国南方文学的大课题。福克纳、沃尔夫、沃伦等美国南方作家在其作品中反复书写自己对于南方历史的反思和对于南方人身份的探寻。作为一位与上述作家同时期的南方作家,凯瑟琳·安·波特也必然会对这一大课题有所思考,并将自己的思考付诸笔端。但与福克纳等男性作家笔下史诗般的南方家族宏大叙事不同,波特作为一名女性作家以细腻委婉的笔触从一个贫困家庭的弱智男孩入手,以极为短小的篇幅向读者揭示了一个处于新旧交替的南方社会。新老南方的对立冲突集中在惠普尔一家,这户人家中的那个无名的“他”折射出的是困于新老南方对立中的新一代南方人对于自我身份的迷茫与焦虑。
[1]ROBERT PENNWARREN.Irony with a Center:Katherine Anne Porter[M].New York:Random House,1958:24.
[2]KATHERINE ANNE PORTER.Collected Stories and Other Writings[M].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2008:745.
[3]EDWARD L.AYER,BRADLEY C.MITTENDORF.The Oxford Book of The American South:Testimony,Memory,and Fiction[M].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111.
[4]JOHN CROWE RANSON.“A Statement of Principles”,The Twelve Southerners,I’ll Take My Stand[M].New York:Harper&Row,1962.
[5]LEWISP.SIMPSON.The Brazen Face of History[M].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3:110-111.
[6]KATHERINE ANNE PORTER.The Days Before[M].New York:Harcourt,Brac and Co.,1926:157.
[7]KATHERINE ANNE PORTER.Collected Stories and OtherWritings[M].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2008:741.
[8]凯·安·波特.波特中短篇小说集[M].鹿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282.
[9]KEVIN RAILEY.Natural Aristocracy:History Ideology and the Production of William Faulkner[M].Tuscaloosa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99:56.
[10]MILAN KUNDERA.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M].trans.,Micheal Henry Heim.New York:Knopf,1980:3.
[11]虞建华.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化思潮和文学表达[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463.
[12]ANDRE BLEIKASTEN.A Furious Beating of Hollow Drums toward Nowhere[C]//FAULKNER.Time and History in Faulkner and History.Salamanca:Ediciones Universidad de Salamanca,198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