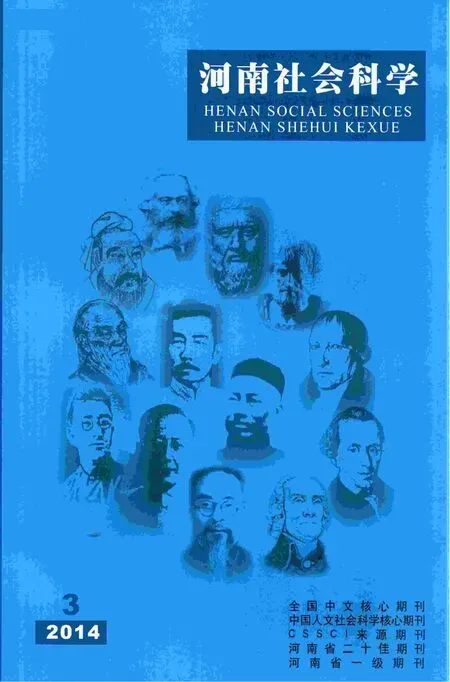从海派文学视角看安妮宝贝的城乡经验书写
姜 欣
(河南城建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36)
英国哲学家洛克曾说:“我们底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而且最后是导源于经验的。我们因为能观察所知觉到的外面的可感物,能观察所知觉、所反省到的内面的心理活动,所以我们底理解才能得到思想底一切材料。”[1]也就是说,经验是我们直接感受世界的方式和结果,同时也构成了我们思考世界的直接知识来源,并且为我们二次感受和思考世界提供了个性化的视角。可以说,文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也面临着如何处理个人经验和时代经验的问题。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城市”和“乡村”这两种当代经验,不仅是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的重要对象,而且这两种经验能否处理得当,还决定着一个作家能否寻找到真正的精神家园。
安妮宝贝,是一位凭借网络走红的作家,其作品多集中书写都市白领的孤独、爱、死亡、漂泊等主题,并受到大众追捧。在她的身上,城市的印记如此明显,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将之命名为新世纪都市文学的代表作家。然而,安妮宝贝的小说创作虽然得益于对城市生活资源的占有和享用,但是城市经验并不构成她的全部精神归宿。乡村经验不仅构成了她小说中身心无定的人物形象的温暖记忆,还迫使着这些人物不断漂泊、踏足一片片陌生的土地。
如果将安妮宝贝的写作分为前后期的话,那么前期作品《告别薇安》《八月未央》《彼岸花》,多以“城市”为背景,充满颓废唯美的末世情绪,我们可以将之看作堕落的现代人面对纷乱世界时的慌不择路。此后,从城市到村镇,随着作者真实的野外行走以及不断增加的人生阅历,后期代表作品《蔷薇岛屿》《二三事》《清醒纪》《素年锦时》等作品,则呈现出空灵清绝、笃定明朗的特色。而到了《莲花》这一小说时,她的小说主人公则赶赴宗教圣地——墨脱,阶段性地完成了精神家园的寻找和重塑。
本文从海派文学的视角,关照和比较海派作家传统与安妮宝贝作品中的城市和乡土经验,力图展现安妮宝贝作品中“城市”“村镇”以及“村镇”的信仰变体——“圣地”三种经验书写的独特性,并对叙述者自我反思、自我拯救和最终寻找到精神家园的心路历程做出深幽的探析。
一、城市经验:纯粹个人的生存空间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因此无论城市生活多么不完美,它依然是人们向往的一种生存方式。但是在文学领域,长期以来,城市得到的关注和热爱远远不及乡土。因此乡土经验书写或者美好田园想象就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学经久不衰的主题,而一直作为重要生活环境存在的城市,却始终不是中国文人乐此不疲的文学关照对象。
按照吴福辉在《都市旋流中的海派小说》中的说法:“五四”是西方文明对“乡土中国”的全面的、势不可挡的一次冲击。但是,现代文学第一个10年占主要地位的仍然是“乡土文学”。只有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文化中心南移并与经济中心合一,现代都会上海和对现代化都会的文学表现,几乎同时升起,我们方才有了全新意义的都市文学。海派小说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2]。
以刘呐鸥和穆时英为主的“新感觉派”,成功地将现代都市感受带入现代文学写作中来。在强调速度和快感的印象式书写中,他们把握了都市消费语境中的刺激和热情,也记录了都市享乐者的失落和倦怠。但是对于新感觉派来说,上海这样的大都会,是纯粹享乐和消费的十里洋场。穆时英在《上海的狐步舞》中的开头和结尾重复描述:“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但实际上,他费尽笔墨描述的主要是天堂,流连忘返的更是天堂。所以他在《黑牡丹》中才会表白心迹:我是在奢侈里生活着的,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3]。
相较于新感觉派,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的深刻之处在于,她成功地将“都市”的范围从下半身上升到上半身,从舞厅酒吧转移到弄堂亭子间,从一部分市民扩大至新老全体市民,从欢愉热闹的快感瞬间拉长到了悲欢离合的庸常生活。张爱玲是苍凉的,连同她笔下的城市书写都带着苍凉的底色,“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的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4]。但她的悲情城市中那些人生悲剧和闹剧,更像是为新时代中的没落旧家庭所做的一场挽歌。悲情的现代个人的心灵,并不追求现代社会珍惜的个人价值,而往往被一个浓厚、浓黑的“家庭”的阴影所遮蔽。
在这样的语境下,安妮宝贝不仅作为一个城市书写者,而且作为一个纯粹的城市书写者出现。她的前三本书《蔷薇岛屿》《八月未央》《彼岸花》背景便多发生在城市,且发生地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北京的酒吧、地铁、咖啡屋、百货公司。正如她自己所说:“我的作品核心,基本上是工业化大城市中有自省意识的人的状态。”[5]对于她和她笔下的人物来说,首先,城市不只是她们的消费娱乐场所,而且是她们赖以生存、不可逃离的生活空间和不可选择的生活方式。城市要么是生来即在的生活场所,个人生命记忆和城市经验已经高度吻合;要么是奋斗打拼的工作场所,理想人生和城市经验高度吻合。
城市是资源集中、高效配置的场所,人口和物质的极大丰富是其重要特征,酒吧、咖啡厅、地铁站、步行商业街,汹涌人潮一再出现,这些恰恰构成了安妮宝贝本人及其笔下人物重要的须臾不能离开的生存环境。在安妮宝贝前期作品中,显示着城市物质的极大丰富和消费欲望的极大膨胀。
在《告别薇安》中,一个男人的夜店感受:“夜色沉寂而迷乱,是他最喜欢的时段。漂亮女孩独自坐在吧台的一角抽烟。咖啡的浓香与烟草和香水交织。唱片放着谋杀人思想的帕格尼尼,无止境的感觉,可以深陷。”[6]
在《瞬间空白》中,安妮宝贝如此描述女性逛街的感受:“以后,我独自去南京路伊势丹,我在那里看漂亮的裙子、鞋、化妆品、项链和香水。我喜欢物质。有时候它能安慰人,很懒散,今天给自己买了一条暗玫瑰红的裙子,简单的式样,上面绣着花朵,不是太贵。我已经很久没有穿新衣服了。”[7]
在《蔷薇岛屿》这本书中,我们无时无刻不被作者反复提及的“物”所吸引:伊都锦的棉布、哈根达斯冰激凌、纪梵希香水、蓝色鸢尾、Espresso咖啡、Kenzo新款香水……
这些貌似不精心实则大费心思的描写,为我们勾勒了一个繁华富有的社会图景,也标榜了都市白领的“趣味”和“个性”,但同时也反映了物对人性的挤压和扭曲。在消费社会中,物质消费和人的内心需求已经高度联系在了一起。物质的购买和占有,本身建立在一定的心理欲求之上,它却可以使人心获得暂时性的满足。但是,在商品极度丰盛、购物随时可能的情况下,主体获得内心欢愉的持续时间越来越短。当主体已经丧失了欢愉心灵的自我构建能力时,它只能不断地通过游逛、挑选、试穿(用)、支付、打包、炫耀等动作,来刺激自己已经疲倦不堪的灵魂。主体和物质之间的关系已经颠倒。正如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所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8]安妮宝贝许多作品中的人物总是感觉自己是欲罢不能的一架商业机器,被物质追求的欲望驱使,无休止地重复物的消费、占有和抛弃。
同时,城市的体验者们被割断了所有与宏达历史追求、复杂家庭关系的羁绊,以孤独个人的身份飘零在城市时空。安妮宝贝笔下的人物,常常是些都市白领,或者夜间工作者,或者无业游民,他们大都背离正常人的作息、交往方式和生活轨道。在《一个人的夜晚》中,自由写作者乔,每天从晚上7点忙碌到次日凌晨5点,白天的时候全都用来睡眠,“与世隔绝,像寄生在巢穴里的幽灵一样”。
他们的灵魂也处在绝对孤独的境遇之中。《告别薇安》的男主人公是个冷漠自私的白领,同居女友只是性伴侣而无法心灵相通,而唯一能够相互交流的只是一个从未谋面的叫作“薇安”的网友。
这些精神孤立的都市个体,并非没有强烈的情感,但是这情感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并不重视他人的存在和关切。《彼岸花》中,女孩南生将同父异母的哥哥林和平看作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依恋和信赖。可林和平却选择了离开。南生前去找他,林和平说:“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南生,我们有各自的路要走,我已经累了,我的生活不需要阴影,你不要进来。”其实在安妮宝贝看来,“南生和和平其实都是自私的人,都习惯了为自己而活”。
他们也习惯了爱情中利己主义,并呈现为一个多发性的爱情模式:女主人公的好朋友爱上了自己的男人。《七月与安生》中,安生爱上了七月的男友家明;《二三事》中,莲安爱上好朋友良生的男友沿见,并为之生下一子;《八月未央》中未央因为爱着乔而想尽一切办法来拆散乔与朝颜。
这种几乎不可改变的绝对“个人”的存在方式,使得小说人物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求得个体的“理想存在状态”是她们自觉的生命主题;另一方面,他们对外在世界的怀疑与拒绝在根本上否定了“理想存在状态”转化为现实的可能[9]。在《彼岸花》中,乔因为单调的写作生活,开始幻想家庭生活:“这种写作生活什么时候才能到头。但不可能有一个男人突然冒出来对你说,我带你走,给你一个家……”但是,卓扬向乔求婚时,乔却拒绝了。她并非不渴求幸福,但是她更愿意沉浸在“孤独自我”的充分自恋感中,她的理由如下:“我要为这个男人改变自己吗?就因为他给了我哈密瓜、香水、新衣服和求婚的诺言?”[10]
弗洛姆曾说:“当我们‘陷入’恋爱时,正如这个富于变现性的动词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周围的世界便不仅在表面上,而且在我们的经验中发生摇晃和改变。”[11]然而,《彼岸花》中的“乔”却道出了都市自私爱情观的“真谛”:“我漠视除我自己关注和重视之外的一切感觉和现象,不太容易付出,有享受孤单的需求,我不知道人与人之间是否需要紧密的联系,像那些有事没事就碰到一起的人。”
二、村镇经验:温馨静止的回忆乐园
在处理城市经验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大多数写作者都形成了一套褒贬并置、辩证而刻板的话语系统。那就是一方面认为城市是罪恶的渊薮,是欲望满足的温柔乡、名利场,另一方面将乡土视为美好的起点,是健康、自然、完整人性的伊甸园。海派小说在描绘欲望得到极大满足的城市经验时,也常常会书写都市人的失落、焦虑和变态。如刘呐鸥曾突然感慨:“我觉得这个都市的一切都死掉了。……我的眼前有的只是一片大沙漠,像太古一样地沉默。”[12]穆时英创作过《父亲》《旧宅》《竹林的惆怅》等怀乡、怀旧之作,施蛰存的《春阳》《雾》中的都市也总抹不掉松江、苏州乡镇的阴影。“海派一心营造的都市形象,归根结蒂离不开大陆的本土,摩天大楼立得再奇再高,仍被笼罩在乡土文化、家族文化的大投影之下。”[13]
当目击城市的不完美时,安妮宝贝早期的作品同样表达了都市边缘人的颓废尴尬和无能为力。但正如郜元宝教授所说:“她刻画城市也并非流俗于对声色犬马的沉迷和炫耀,并没有被这些所辖制,始终执拗地剥离出偶然之后沉默的真相。”[14]当都市经验不但没有解决反而不断加剧我们的精神困境时,作为都市经验的对立物——乡村经验帮助我们寻找到了自我治疗虚无灵魂的道路。当然,安妮宝贝的乡村经验并不是纯粹的农村耕作和生活记忆,而是带有乡土气息并混杂着小镇风情的村镇经验。
相较黑暗的、绝望的、冷漠的现代都市社会,作品主人公回忆里的村镇清晰、明快、宁静、温情。这种村镇经验的书写非常符合张柠对“静止的乡土经验”的描述:“摆脱现代性视野,而对乡土经验进行静态的描述,诗化它,将它假想为一个整体,变成抒情性的对象。”[15]
在《最后约期》中,父母离异的安被寄宿在枫溪镇的奶奶家中。枫溪小镇,常常出现在主人公的梦魇里面:“那个凌晨,他又开始做梦。还是她十岁的时候,深夜背着她送她回家。她的奶奶提着灯笼走在前面,枫溪的碎石子小路是湿漉漉的。”[16]
在《七年》中,他和她“仿佛回到了童年很小的时候,走在迂回的山路上,想到达顶峰。天空是鲜红的颜色,大朵大朵的白云在上空迅速移动。她仰着脸看,心里安宁。觉得自己可以回家”[16]。
在《小镇生活》中,“他们走在小镇街道上,闻到植物和泥土的气息,还有匆匆跑过去的狗的影子。……他们去爬山,他们站在山腰的一块岩石上,俯视着幽静苍绿的山谷,他们坐在裸露的岩石上迎着山峰抽烟”[16]。
记忆中的家乡回望,还出现在安妮宝贝篇幅小巧的纪实散文里。在《素年锦时》一书的《村庄》篇中,她提到了自己童年的家乡——海边村庄。“六岁时,与外祖父一起去山上挖兰花。带着竹箩筐、短锄、水壶,走过村子里鹅卵石铺就的小路,走过哗哗流淌大溪涧旁边的机耕路……临近冬天的早晨,外祖母早起格外忙碌。厨房里的火灶,干柴塞进去,火苗闪耀,松枝和灌木发出噼啪脆裂的声音。碗盘的声音,忙碌而迅疾的脚步声……种种声响,惊动一个寻常早晨……酷暑过后,从院子里走出来,来到大溪涧边上。踩着清凉溪水地下的鹅卵石,小鱼小虾盲目地撞到脚背上。秋深天空蓝得格外高远,空气也清冽。而冬天夜晚的大雪总是来得没有声息。清晨推开窗,才惊觉天地已经白茫茫一片。”[17]
“童年体验是一个人心理发展的不可逾越的中介。它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大量的事实表明,个体的童年经验常常为他的整个人生定下了基调,规范了他以后的发展方向和成长,在个体发展史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18]安妮宝贝从小与祖母一起生活,在乡村与大自然曾有过密切的交流,这直接影响到了作家个人心灵的成长,并构成她日后创作的重要资源和动力。正如她在书中所说“一个孩子拥有在乡村度过的童年,是幸会的际遇。无拘无束生活在天地之中,如同蓬勃生长的野草,生命力格外旺盛。高山,田野,天地之间的这份坦然自若,与人世的动荡变更没有关联”[10]。
相对物欲横流、人情冷漠的城市,村镇仍是人情敦厚、灵魂清净的净土。因此,当人们无法认识城市或者对城市感到迷惘的时候,回归村镇或书写记忆中的村镇,便成了作家们的感情依托。但是,正如张柠所指出的“静止的乡土经验”的致命问题:“故事抽去了叙事的核心——历史,从而将乡村生活凝固化,我们看到的仿佛是一副死寂的民俗旅游图。”[15]大地、故乡、家园、自然,在成为作家们极力榨取的空洞的“观念”时,其实正在经历着当下社会变革的严格考验。我们有理由相信,出现在安妮宝贝作品中的那些村镇经验只是一种童年回忆,是用来摆脱现实困扰的一种无可奈何。
三、宗教圣地:阶段性的精神家园
许多学者都曾感慨中国缺乏真正的宗教信仰,并以此在西方文明前自短,钱穆曾认为:“中国自身文化传统之大体系中无宗教,佛教东来始有之,然不占重要地位。又久而中国化,其宗教之意味遂亦变。”[19]海派文学更多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创作资源,重视描写人欲和心灵苦闷,大多数作品更无明确的宗教意识。但是如张爱玲、施蛰存等人却对宗教文化都多有涉笔。
张爱玲曾在《中国人的宗教》一文中,对中国人缺乏宗教理想的心态进行了比较明晰的批判,她认为中国人的感受,只是“临风洒泪,对月长吁,感到生命之暂,但是就到这里位置,不往前想了”;而中国人的宗教“是许多不相联系的小小迷信组合而成的——星象、狐鬼、吃素”[20]。施蛰存则借《鸠摩罗什》《黄心大师》《塔的灵应》《宏智法师的出家》四篇小说,展示了他对佛教文化的态度:并非宣扬佛教思想和戒律人生,而是一反宗教神圣性,借佛教题材的改写,挖掘僧人潜意识中与凡人相同的世俗欲望,对佛门弟子的宗教光环进行祛魅和还原。
和海派文学的前辈相反,安妮宝贝却力图正向表明宗教信仰之于都市个人心灵救赎的重要性。2004年,安妮宝贝抛弃了个我世界里独自沉溺的哀伤,徒步去往雅鲁藏布江深处的小村落——墨脱,并在行走中完成了一部朝圣者的心灵史——《莲花》。写作此书时,安妮宝贝已经意识到了用“村镇经验的温情”来对抗现实灵魂的无所依傍。人不能靠对乡村生活的记忆从根源上解决精神归宿的问题——因为美好的故乡和乡土氛围早已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复存在,故土和家园、亲人和友情都是无法抵达的彼岸花。但是乡土村镇经验却可以在神圣信仰的支撑下,化身为穷乡僻壤中的宗教圣地,成为都市人心的现实归宿。
“在路途中寻找”是这本书的主题。这部小说写了内河、善生、庆昭三个人物。年轻女子庆昭身患疾病,滞留高原,在旅店里偶遇立意结束名利生活的纪善生,遂结伴步行前往西藏墨脱。在墨脱,有纪善生的旧友内河,她曾在墨脱支教。不同于安妮宝贝以往的小说,《莲花》在人物结局设置上摒弃了一味徒劳无功式的挣扎,取而代之的是对待命运从容淡定的接受——宗教信仰正在改造着作者和小说人物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这本书讲的故事,是三个人,如何与自己的命运妥协”[21]。
墨脱古称“白玛岗”,意思是“隐秘的莲花圣地”。安妮宝贝偕同她的主人公一起在向圣地迸发的途中,进一步洞穿了城市对人类心智的伤害。“城市的消费怪圈和物质信念失去作用。所谓的奢侈品、高级品牌、时尚……它们使人们信奉形式和虚荣,充满进入上流社会的臆想……离开城市之后,你会发现它的畸形和假象,对人的智力是一种侮辱。”[21]同时更深切地感受到了来自宗教的启示:“也许只有一种存在天地之间超越天地之外的力量,才能够永久地让人信服,愿意相信它为轮回的生命之道,这也是人所能获得的慰藉和信念所在。”[21]这种慰藉和信念最终呈现在人物人生选择上:内河命运多舛,却明白了“生命各有途径,不管它最终抵达的目的是卑微还是荣耀。这是力量的控制带给我们的界限所在”[21];而善生也终于变得通透豁达,学会接受命运中注定的残缺和世界上无法探明的真相;庆昭则决定一个人留在云南大理,过一种远离尘世的平淡生活。他们三个人有着各自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墨脱之行使他们一一蜕变并开始新的生活。
只是我们早已得知,作者意图、人物思想和作品意义都不能混为一谈。《莲花》借助宗教的力量,终于要让人物相信理想存在状态的人间真实性——善生、庆昭抛弃世俗羁绊前往墨脱的旅程可以看作一次将理想现实化的行旅,而在墨脱教书的内河则可以看作一个将理想现实完成的完美形象。然而小说的结尾,我们看到:内河早已死亡,理想终究只能是空中楼阁,不能在现实的土壤中长久矗立。而庆昭尽管最终以家庭主妇的形象示人,但安宁的家庭生活并不能稀释内心的孤苦无奈:“生命就是这样充满幻觉。始终有希望。也始终无望。我突然想到我与善生、内河,不过是路途上注定的失败者,但是我们却必须拼尽全力,走过此道。”[21]也就是说,宗教信仰背景下的乡村经验并不保证安妮宝贝和她笔下的人物从此超凡入圣。
有论者曾说,“整个20世纪的历史,都是人类家园惨遭失落的历史,也是人类久久‘在他乡流浪’,经历‘漫游之艰辛’的历史。当然,家园之失落并非是世纪人类历史的唯一旋律,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人类都在对家园的兴盛做出美好的贡献。只是在本世纪,或者说,尤其是在本世纪,家园之失落偕越了家园之兴盛,成为压倒性的时代问题”[22]。从《告别薇安》到《莲花》,安妮宝贝以其特有的真诚“将自我碎裂为世界”,直面物质的极度繁荣和由此带来的精神家园的坍塌,自觉地实现着小说的自我反思、自我治疗和自我拯救的功能。安妮宝贝和其作品中的人物一道,穿越了浮华的都市经验,穿越了童年阴影中的乡村记忆,然后在莲花盛开的现实圣地——墨脱阶段性完成了自己对人世真谛的追索与探寻。然而,在追寻精神家园的路上,安妮宝贝依旧没有止步,仍需继续前行。
[1][英]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吴福辉.都市旋流中的海派小说[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3]穆时英.公墓[M].上海:现代书局,1933.
[4]张爱玲.传奇[M].上海:上海杂志社,1944.
[5]安妮宝贝.击中内心很重要[EB/OL].http://www.china.com.cn/chinese/Rs/790304.htm.
[6]安妮宝贝.告别薇安[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7]安妮宝贝.八月未央[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8][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9]叶原.家庭:想象与虚无——论安妮宝贝小说中的现代性悖论[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4):42—45.
[10]安妮宝贝.彼岸花[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
[11][美]罗洛·梅.爱与意志[M].冯川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
[12]刘呐鸥.都市风景线[M].上海:水沫书店,1930.
[13]吴福辉.都市旋流中的海派小说[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14]郜元宝.向坚持“严肃文学”的朋友介绍安妮宝贝:由《莲花》说开去[J].当代作家评论,2006,(2):34—37.
[15]张柠.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6]安妮宝贝.告别薇安[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17]安妮宝贝.素年锦时[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18]王克俭.文学创作心理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19]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M].长沙:岳麓书社,1986.
[20]张爱玲.中国人的宗教[J].天地,1944,(11):12—16.
[21]安妮宝贝.莲花[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22]林和生.家园寻踪[J].书屋,2002,(11):2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