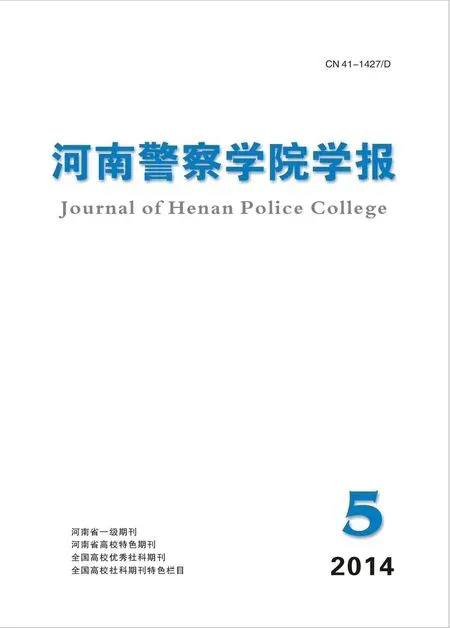《论犯罪与刑罚》的刑法学研究思维启示
马荣春,白星星
(扬州大学 法学院,江苏 扬州 225127)
自刑法学界家喻户晓的《论犯罪与刑罚》问世以来,先有来自方方面面的高度评价与赞誉,接着便是刑法学研究对其高频率摘引,再后来,我们便可间或见到专门论述这部刑法学巨著的刑法思想的论文和论著,并且有尝试“超越”之作出版。①参见姜敏:《对贝卡里亚刑法思想的传承与超越》,法律出版社2010 年版。但迄今为止,关注《论犯罪与刑罚》这部刑法学巨著的刑法学方法论的著述尚未可见。在某种意义上,这部刑法学巨著留给后世的刑法学思维价值或许要大于其所论述的刑法学思想本身,因为正如学者指出,刑法中的罪刑法定等很多部门法的基础理论都是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问题,由于属于接近信仰的领域,故难以证明,也无法从事科学的研究[1]。那么,我们应从这部刑法学巨著中去找寻一些刑法学研究思维的启示。
一、《论犯罪与刑罚》启发着刑法学研究的社会学思维
在某种意义或相当程度上,《论犯罪与刑罚》是一部刑法社会学著作。强调《论犯罪与刑罚》是一部刑法社会学著作,首先要表明的是这部刑法学巨著是把犯罪与刑罚作为社会问题对待的,或是放在社会问题的背景下予以考察和审视的,即这部巨著体现了刑法学研究的社会学思维。《论犯罪与刑罚》的社会学思维不仅集中体现在其提出的一个核心范畴即“社会危害性”上,也体现在用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来解释犯罪的成因上,还体现在采取一切办法消灭或减少社会动乱因素的预防犯罪对策上[2]。
社会学的思维启示对我国当下的刑法学研究究竟有着怎样的重要性呢?学者指出,按照社会功能主义的观点,由于也是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故不能把法律从社会因素中抽象地剥离出来。因此,社会科学方法的作用就是要使法学研究回归到它真正归属的上位概念中来,回到社会科学的精神家园。这样,研究者便可真正从社会的角度看待法律问题。于是,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法律制度,即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治理结构不发生根本变化,法律制度的提前大跃进注定要被彻底架空。因此,那种把法律条文本身当做研究对象的学问不是法学,是因为法律条文背后的东西是和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乃至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的[3]。可见,刑法学必须具有社会学的天然属性,否则刑法学将不具有科学性,因为刑法学的基本研究对象便是犯罪与刑罚问题,而犯罪与刑罚问题本来就是社会性问题。犯罪问题所能说明的刑法学的社会学属性自不待言,而刑罚问题对刑法学的社会学属性的说明便在行刑社会化和社区矫正等当下热门话题之中。
强调《论犯罪与刑罚》是一部刑法社会学著作,再就是表明这部刑法学巨著使用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通用规则。学者指出,引入社会科学方法并不意味着完全倒向某一门社会科学学科,而是要引入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通用的方法,且这种通用的方法是以因果关系为核心,即强调以解释现象、揭示成因为目的。那么,社会科学的方法意味着从问题出发开始研究,从而将本土的经验上升到一般理论[4]。那么,《论犯罪与刑罚》使得前述社会科学的方法即因果律得到了体现。以《论犯罪与刑罚》所提出的刑罚的必定性、及时性和相当性理论为例,刑罚的必定性、及时性和相当性所表述的实质上就是罪刑关系,而罪刑关系实质上就是因果关系。对刑罚的必定性,贝卡里亚曾指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5]。而如果让人们看到他们的犯罪可受到宽恕,或者刑罚并不一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那么就会煽起“犯罪不受处罚的幻想”[6]。可见,刑罚的必定性在直陈着一种事实:有犯罪这个因,就必有刑罚这个果。罪刑关系是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而罪刑关系这种因果关系是犯罪和刑罚这对社会现象和法律现象之间的当然连接。正是由于刑罚的必定性对罪刑关系给予因果关系的逻辑直陈,故公民的行为规范意识和法官的裁判规范意识便得以形成;而司法者在刑罚的必定性的约束之下便不可在司法个案中随意割断罪刑关系之链。对于刑罚的及时性,贝卡里亚曾指出,犯罪与刑罚之间的时间隔得越短,就会使得犯罪与刑罚这两个概念的联系越突出、越持续,从而人们就很自然地把犯罪看做起因而把刑罚看做“不可缺少的必然结果”[7];而只有使犯罪和刑罚衔接紧凑,才能指望相关的刑罚概念使那些粗俗的头脑从诱惑他们的、有利可图的犯罪图景中猛醒过来。推迟刑罚尽管也给人以惩罚犯罪的印象,但它造成的印象不像是“惩罚”,倒像是“表演”[8]。可见,刑罚的及时性能够通过缩短犯罪与刑罚之间的时间间隔而强化人们对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心理连接即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达到抑制犯罪意念,强化禁忌意识,以最终预防犯罪的效果。而刑罚的及时性显然是在刑罚的必定性的基础之上或前提之下,在时间的维度上对犯罪与刑罚之间逻辑关系即因果关系予以事实反映,并且通过“及时性”尽量使得犯罪与刑罚之间的逻辑关系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与矛盾运动,从而使得刑罚的必定性所征表的因果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说明。对于刑罚的相当性,贝卡里亚曾指出:“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9]可见,刑罚的相当性意味着犯罪与刑罚之间能够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中被进一步确证为因果关系。总之,不仅刑罚的必定性、及时性与相当性本身都隐含着因果关系问题,而刑罚的前述属性与预防犯罪的效果之间也可用因果关系予以把握。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各种社会现象也是普遍联系的。刑法是规制社会问题的,那么以刑法为研究对象的刑法学即刑法学研究不可能脱逸于社会问题的普遍联系之外,正如学者指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且其原因又是有着内在关联性的,而正是这种内在关联性构成了社会科学理论发端和发展的经验基础[10]。但在笔者看来,所谓“内在关联性”指的是“普遍联系”这张大网中的相互联系,那么为了从根本上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刑法学研究不可能对此普遍联系“眉毛胡子一把抓”,因为刑法对社会问题的规制也要讲究“对症下药”,而美国历史学家胡果则提醒我们:“原因的原因不是原因”。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包括刑法学研究中因果律就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而对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因果律的重要性,学者指出,提出某个概念或者某种理论来解读某个现象发生的原因,这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最高境界,也是最难成功的。因果关系又被称为因果律,其发展到极致便属于对某种规律、原理和定律的概括[11]。而将经验研究上升为因果律,是指从一个国家法制的经验事实中提炼出概念,解释大量经验事实发生的原因。当一个概念、理论能够解释大量现象发生的原因时,这就是一种能够揭示因果律的理论,而能够提出这种理论的研究便达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最高境界”。那么,我们的刑法学研究也应注重因果律的运用。具言之,在刑法的规制对象即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概括和提炼出能够解释该经验事实,并且能够规制该经验事实的概念、命题以及由之所构成的刑法理论,从而能够为刑法立法和刑法司法提供有力佐证。刑法规制什么和如何规制暗含着因果律,那么刑法学研究就不能回避因果律的运用。如果立于刑法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后一个法制手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刑法是“后盾之法”和“保障之法”,则在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或许刑法学研究应最为讲究因果律的运用。
学者指出,所谓因果关系的研究,是指社会科学研究中需要重点解释某种社会现象之所以发生的原因。而如果能够把原因、成因解释出来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这是学者的重大贡献[12]。由于在实证之中更容易找出问题的原因和成因,又由于在解释原因和成因之中所上升的理论有着实证的基础,故因果律能够使得刑法学研究避免两个极端:要么是基于资料展开的调查报告,要么是空洞无物的理论思辨。从而,我们才能由“法律的生命有机体”迈向“法学研究的生命有机体”。社会科学研究包括刑法学研究中的因果律隐含着已故语言学大师王力先生最早提出的一个方法论命题,即“先归纳后演绎”。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当下的刑法学研究并非不知晓刑法学研究的社会学方法,但其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可能或实际上还不得要领,故本文借《论犯罪与刑罚》再谈刑法学研究的社会学方法仍有实际意义。
二、《论犯罪与刑罚》启发着刑法学研究的实证学思维
在某种意义或相当程度上,《论犯罪与刑罚》也是一部刑法实证学著作。《论犯罪与刑罚》虽然区区几万字,但却渗透着较为浓重的实证法意识,然其实证却又具有明显的“简约性”,即没有大量的数据,也没有精致的图表,也没有对实证对象的小说般的细致描述,而其实证的“简约性”并不妨碍其实证的效果。因此,我们可以说《论犯罪与刑罚》在实证方法上是成功的,而这对于我国当下刑法学在研究方法上又有何启发呢?
我们首先要肯定刑法学研究的实证思维本身。学者指出,实证分析包含着逻辑实证分析和经验实证分析[13]。“逻辑实证分析”着重于对法律规则本身做出合乎逻辑的分析和考察以建立一定的理论体系,而将这种方法强调到极端便属于“分析实证主义(理论)学派”;“经验实证分析”是将法律实施视为一种社会现象并对之作出社会学解释,而将这种方法强调到极端便属于“社会实证主义(理论)法学”。尽管“社会实证主义(理论)法学”也强调研究应以“事实“为根据,但其所强调的“事实”则是法律规则以外的“社会因素”[14]。那么,当下的中国刑法学研究仍然强化实证思维:通过强化经验实证思维,以增强刑法学理论命题的科学性,以谋求一种“刑法之真”;通过强化逻辑实证思维,以增强刑法学理论命题的自洽性,以谋求一种“刑法之善”。
在刑法学研究的实证思维上,《论犯罪与刑罚》还启发我们:不要为实证而实证,即不要沉湎于数据、图表或事实描述本身,或在数据、图表或事实描述本身之中不能自拔而让研究成果停留于“调查报告”,而是要在实证的基础上作理论概括,以使研究具有更大的价值,或曰使得研究能够成为或堪当研究,正如贝卡利亚在对人们的刑罚心理作出一番符合心理学的实证分析之后提出刑罚的必定性、及时性和相当性命题所说明的那样。学者指出,没能实现“概念化”,只会使得历史研究变成“写小说”;没能实现“概念化”,只会使得人类学研究变成“太平洋小岛上的一次经历”;而如果没有将经验事实进行“概念化”的处理,则社会学研究最多是进行一种“社会生活的实录”。因此,真正有创建的学术研究必然会经历从“经验”跳跃到“概念”,从“事实”上升到“理论”的过程[15]。那么,在笔者看来,只有做到“从实证中来,到理论中去”,刑法学的实证研究才既是实证法学,又不停留于“对策法学”,而是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中提升着刑法学研究的应有境界。当然,这里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论犯罪与刑罚》在实证法上的成功还进一步提醒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只有数据和统计才等于经验实证分析。只要是研究法律制度的实施和客观的法律现象,都可以算作经验实证研究。而经验实证研究首先是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其次是一种对待学问的态度[16]。
有学者指出,如果只是提出改进当时意大利刑事立法的建议,或者一味地提出改革司法的对策的话,则贝卡里亚不可能成为法学大师。而真正使贝氏的《论犯罪与刑罚》名垂青史的,恰恰是他基于对当时刑事司法问题的深刻分析和以此深刻分析所提出的包括罪刑法定等在内的一系列法学思想[17]。这里的“深刻分析”,意味着《论犯罪与刑罚》具有相当的实证性,且其实证性在一种娓娓道来中让人心悦诚服。这里所谓“娓娓道来”,指的是贝卡利亚对问题的分析所依据的就是人们身边和每个人身上的某种事实,故其关于犯罪与刑罚的实证性是再“朴实”不过的了。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当下的刑法学研究并非不知晓实证之法,但其对实证之法要么不予重视,要么存在误解,故本文借《论犯罪与刑罚》再谈刑法学研究的实证之法仍有实际意义。
三、《论犯罪与刑罚》启发着刑法学研究的工程学思维
在某种意义或相当程度上,《论犯罪与刑罚》还是一部刑法工程学。《论犯罪与刑罚》的刑法工程学特征明显地体现在作者多处运用物理学思维来探究刑法问题,如其对刑罚是对犯罪的一种“政治阻力”的形象比喻,更如其对“罪刑阶梯”的恰当设计。那么,工程学思维是《论犯罪与刑罚》所能给予我国当下刑法学研究的又一大启示。
工程学的思维启示对我国当下的刑法学研究究竟又有着怎样的重要性呢?学者指出,我国学者们习惯于在揭示出研究对象所包含的“规律”或“道理”的同时,还要将自己所揭示出来的“规律”或“道理”运用于“实践”,即提出能够进行现实操作的“实践方案”或设计出具体的“社会工程”图纸来。这便导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研究”与“工程研究”的混沌不分。但随着人的理性的发展和社会与文明的进步,人类社会的制度与组织的完善主导人的“理性设计”而尽可能地远离人的率性而为,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工程研究”以及对这两种研究进行自觉而有意识的区分,便显得意义重大[18]。这里的“意义重大”,可以予以反面说明:一方面,我国法学学者不自觉地而且也是理所当然地将法律理论研究直接等同于法律工程设计,将法律理论在伦理上的正当性和逻辑上的合理性直接等同于其在实践(即“工程实施”)上的可行性,故法律理论研究成果在实践运用的失败,往往要么被归结为是法律理论的不成熟或不妥当,要么被归结为是法律实践者综合能力的不足或操作措施的不当,而很少意识到这恰恰是混淆了“法律理论研究”与“法律工程研究”以及法律实践之间的本质之别,混淆了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学术工程研究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另一方面,我国法学学者还习惯于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工程思维来“设计”法律理论,把自己对于现实的法律实践困境解脱的主观愿望、价值诉求或者社会效果期待转换成法律的“理论主张”,把法律工程的“应然”直接等同于法律规律的“实然”,把法律的“理想”直接等同于法律的“现实”,从而习惯于将我国法学学者的社会角色定位为既是“理论家”又是“社会工程师”[19]。联系我国当下的刑法学研究,很多学者或曰超过半数的学者乃至绝大多数学者,其著述流露出包揽刑法理论问题和刑法实践问题的欲望,意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其结果是对刑法理论问题和刑法实践问题都是“隔靴搔痒”。在笔者看来,在刑法学研究中,明确刑法理论研究和刑法实践研究的界限,对于分别深化和提升刑法理论研究和刑法实践研究,以最终深化和提升整体刑法学研究是极其重要的,毕竟每个刑法学者的精力都是有限的,而同时“学业有专攻”。
但正如学者指出,法律制度的创新、法律实践方式的创新以及对具体现实问题的法律对策的研究,都属于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如果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没有准确地揭示出法律的“规律”或“道理”,则一般不会对社会的制度运行产生实质性的消极影响。但如果法律工程研究没有很好地从法律的角度对社会结构及其模式加以研究,或者草率地对法律及其实践的模型进行“想当然”式的塑造并将这样的模型付诸实践,那就很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乃至社会结构的解体[20]。可见,法学中法律工程研究的重要性以及法学中法律理论研究和法律工程研究思维区别的重要性。而从此重要性中,我们窥见了刑法工程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刑法学中刑法理论研究和刑法工程研究思维区别的重要性,我们甚至还窥见了“刑法哲学”的重新界定的必要性。
在学者看来,法律工程研究乃是立足于真实的人的生活,充分考量人的生活目的,以一定的法律价值、社会价值和政治立场为路径控制根据,以达到理想的法律生活境界为指向,通过运用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成果,综合运用其他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理论资源、一系列相关的社会因素和条件所构成的历史与现实材料,以实际的社会效用与法律效果为指标,思考、设计和建构理想的法律制度框架及其实践运行机制的思想操作活动[21]。在学者看来,法律工程研究特别注重思想理论资源的选择和使用,而这里的思想理论资源除了法律理论研究的理论成果,还包括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思想理论资源,甚至包括自然科学的思想理论资源和工程科学各个学科的思想理论资源[22]。法律工程研究注重选择和适用思想理论资源,意味着刑法学研究应注重从他处汲取营养而克服故步自封。联系我国的刑法学研究,则其长期停留于“自说自话”,即其长期停留于刑法本体话语的逻辑循环的研究局面,还没有被根本打破,特别是在“规范刑法学”备受青睐和“刑法学专业槽”被曲解的当下。这或许是我国刑法学研究难以获得实质性创新的主要原因之一。须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对于我国刑法学研究走出“原地踏步”或低水平重复而迈向新的境界,不无启发。
在学者看来,法律工程研究具有自身的典型特点:一是问题和需要导向思维,因为“问题”和“需要”是法律工程研究的起点和根本动力;二是创造性思维,因为法律工程研究是在思想和观念上面向法律实践的未来型研究,而法律理论研究只是对法律“规律”或“道理”的“发现”而非“创造”;三是主体价值观引领或者参与式的思维,且此思维还表现出审美情趣;四是非逻辑化的思维,因为法律工程研究必须综合或者复合性地运用各种各样的“规律”或“道理”,考量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运用各种各样的社会材料,始终以法律工程建构所预期获得的社会效用为指向进行思考,故其思维逻辑不要求法律理论研究中的那种“逻辑一贯性”;五是系统性思维,这是由法律工程本身涉及社会方方面面和各个领域所决定的;六是效果检验的思维,而这里的效果指的是法律工程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伦理道德等社会生活领域及其相应的社会关系的调整而形成的秩序状态[23]。若将法律工程研究的前述特点拿来作一观照,则我国当下的刑法学研究还都存在着相当的不足。具言之,若将法律工程研究的问题和需要导向思维拿来作一观照,则正如学者指出,刑法学的理论构造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精巧,对问题的研讨越来越深入,学派尖锐对立且学说越来越多,但共识似乎却越来越少,而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刑法学似乎越来越脱离公众的生活常识,越来越成为公众看不懂的东西[24]。在笔者看来,刑法学研究脱离常识和共识,其实质即脱离“问题和需要”。若将法律工程研究的主体价值观引领或参与思维拿来作一观照,则我国当下的刑法学研究中那种对“规范性”的单纯追求,可以说是抛开了主体价值观的引领或参与,因为那种研究在骨子里视常识、常理、常情为“平淡无奇”甚至“俗不可耐”,而常识、常理、常情正是一种主体价值观和主流价值观。于是,这才有了学者所说的“刑法学似乎越来越脱离公众的生活常识,越来越成为公众看不懂的东西”。若将法律工程研究的非逻辑化思维和系统性思维拿来作一观照,则笔者首先要指出的是,学者所说的法律工程研究的非逻辑化思维和系统性思维,实质上是一回事并可统称为就是系统性思维。那么,在法律工程研究的系统性思维观照之下,则以刑法为主阵地的“刑事一体化”在“红极一时”之后,便在“雷声大,雨点下”之中变成了“有名无实”。至于学者所说的法律工程研究的效果检验思维,则在我们以往的刑法学研究中更是难见半点痕迹的。那么,当我们最终将学者所说的法律工程研究的创造性思维拿来作一观照,则我国的刑法学研究难有创造性便在情理之中了,因为创造性思维绝非想要创造的欲望或冲动,而是实现创造的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思路和方法。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刑法工程思维在社会转型和风险多元加剧的特殊历史时期,将有着越发突出的刑法学研究思维意义。
结语
毫无疑问的是,《论犯罪与刑罚》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如其用先验的“社会契约论”来解释刑罚权的根据。但“瑕不掩瑜”,我们概括和提升《论犯罪与刑罚》的刑法学研究思维的启示,不仅是对《论犯罪与刑罚》在刑法学历史上予以一种更新更高的历史定位,更是对该部著作的刑法学历史意义的一种“升华”。或许正是社会学思维、实证学思维和工程学思维,《论犯罪与刑罚》虽区区几万字,但仍堪称刑法学巨著,并为贝卡利亚赢得“刑法学之父”和“刑法学鼻祖”之美誉,因为社会学思维可以视为一种背景性的鸟瞰性思维,而实证学思维和工程学思维则是更加切实可见的运行性思维。
[1][3][4][10][11][12][13][14][15][16][17]陈瑞华.论法学研究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9.108 ~109.111.183.211 ~212.162.223.223 ~225.207 ~208.77.91.
[2]黄风.贝卡里亚及其刑法思想[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45.
[5][6][7][8][9](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2.110.47 ~48.48.17.
[18][19][20][21][22][23]姚建宗.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变革[J].中国社会科学,2012,(1):121 ~122.123 ~124.137.128 ~129.129 ~130.131 ~134.
[24]周光权.论常识主义刑法观[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1):82 ~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