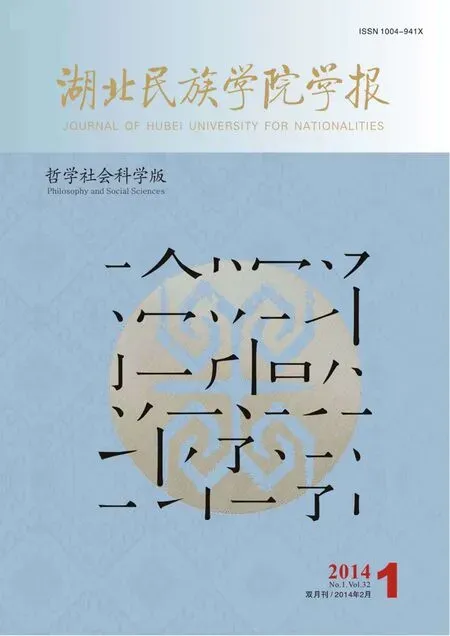20世纪上半叶的藏族史研究(下)
王启龙,姜方燕
(1.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北京100084; 2.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陕西西安710062)
二、1938-1949年间的藏族史研究
本时期藏族史的研究依然硕果累累,讨论的问题极多,涉及面极广,藏族史、汉藏关系史(西藏与祖国关系史)、帝国主义侵藏史、康藏交涉史、康青建省史、民国藏区治理史等无所不包。不过,与上一时期相比,也有一些不同特点:
首先,由于抗战的原因,许多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南下西迁,大批学者有机会直接与边疆人民接触,有机会就地从事田野调查工作;因此,凡是与实地调查密切相关的领域都得到了加强。①据刘洪记、孙雨志(1999),上一时期(1911-1937)历史类文章约1000篇,人文地理类约140篇。前者是后者的七倍左右。而本时期历史类文章有约350篇,而人文地理就有300篇左右,两者几乎持平。当然,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说的那样,真正的学术论文并不多,只占其中一小部分。同样论题的探讨方面,本时期著述挖掘得深入一些。
其次,由于时局的变化和发展,帝国主义在藏的势力逐渐削弱,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逐渐得到包括英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的普遍承认。在此历史背景下,帝国主义侵藏史的研究成果没有上一时期(1911-1937)那么多。同样,随着康藏局势的逐步缓和和康藏问题的逐步解决,康藏交涉史方面的研究也随之退出人们关心的视线,文章也相对较少。
此外,就是翻译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个热门,本时期只有少量的翻译著述(有些甚至是重译本)出版问世,更多的则是中国人自己撰述的著述。下文亦分文章和书籍两部分来叙述:
(一)文章
通论方面主要篇目有如赵盛铎的“西藏民族研究”②赵盛铎:“西藏民族研究”,载《燕京大学学术论文》,1939年5月。、马鹤天的“藏民族的历史概述”③马鹤天:“藏民族的历史概述”,载《新西北》月刊第5卷第4、5、6期,1942年6月。、张法隐的“西藏种族沿革地理考”④张法隐:“西藏种族沿革地理考”,载《中央亚细亚》创刊号,1942年7月,第45-51页。和冷亮的“西藏上古史之探讨”⑤冷亮:“西藏上古史之探讨”,载《边政公论》第1卷第3-4期合刊,1941年11月10日,第59-72页。等。其中张法隐的文章简述了藏族“种族来源”、藏族历史“沿革大势”和西藏“地理形势”,较为简略;而冷亮的文章最为引人注目,全文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中将西藏史分为四个阶段,即上古史——由西藏民族之起源至松赞甘普之出世(纪元前27世纪——纪元后623年);中古史——由松赞甘普至宗喀巴之宗教改革(纪元后 623年——1357年);近世史——由宗喀巴至英军之侵入拉萨(1357——1904年)和近代史——由英军侵入拉萨至现在(1904-1941年)。文章的重点是西藏上古史阶段,第二至第四部分相继讨论了“西藏名称境域之沿革”、“西藏民族起源诸说”和“西藏王室世系”诸方面。由于作者是长期从事藏学研究的学者,精通藏汉典籍⑥据翦伯赞“土番种族源流考”一文所载,冷亮曾经翻译过藏籍《西藏纪年史》。见翦伯赞(1943)530页。,因此论文中汉藏典籍互参共考,使得文章论据更加充分,论证更为合理,比如上述他对西藏历史时期的划分,与过去的著述相比就更加细腻,在当时是一种比较新颖的观点。而在第二部分,他通过对汉藏文史料的分析,认为“土番、乌斯藏、土伯特、唐古特与西藏等,为汉人之称呼,而藏人不知;藏人自称其地曰‘伯’,称其人为‘伯巴’;其境域藏籍载:‘古代西藏包有阿里上三部,卫藏中四部,车康下六部’。藏人称青海南方一带曰‘卓’。”在第三部分则详细考证和辨析了猿猴女魔相配说、印度释迦族之北移说、蒙古族之分支说、西羌之后裔说、汉族之分支说等各种有关藏族族源的说法。第四部分“西藏王室世系”以其扎实的藏文典籍基础详述了吐蕃历史上天赐七王系列、隆甘篡位战争、黑教传入与农业兴起、中利六王序列、地得八王序列、拉萨王与佛法起源说和美容术之蛙尸故事史料记载与传说等。在“结论”部分,作者罗列了始于纪元前27世纪,迄于松赞甘普(干布)出生这段“西藏上古史”的七个重大事件。上述这些如果不懂藏文,对藏文史料不熟是难以办到的。不管今天如何看待这篇文章的结论,但我们认为,作者广泛运用汉藏史料治藏史是值得称道的。
本时期,藏族族源、吐蕃王国史,西藏与祖国关系史依然备受关注。藏族族源方面的文章本时期首先发表的是黄子翼的“藏族名称之商榷”①黄子翼:“藏族名称之商榷”,载《边政公论》第1卷第7-8期合刊,1942年3月10日,第93-94页。,但值得一提的是如下两篇:
一篇是史学大家翦伯赞(1898-1968)的“土番种族来源考”②翦伯赞(1943):“土番种族来源考”,载《中山文化季刊》第1卷第4期(1943),第525-531页。刘洪记、孙雨志(1999)将此文标题记为“吐蕃种族来源考”。。此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简述吐蕃王国如何在中亚一带的争斗中兴起及其与中原唐朝曲折的关系史;第二部分叙述和分析了两唐书等汉文典籍中有关吐蕃传的史料记载,认为“羌族之南徙西藏,盖早在史前时代,发羌者,不过南徙之羌族之一支,所以土番的人种之主要的成分是南徙之诸羌,并非发羌一族,更非后来之秃髮族”③见上注,529-530页。;第三部分从一一辨析了西藏种族来自印度、来自缅甸等诸种说法之不可靠性,进一步认为西藏“种族之来源乃自史前以迄秦汉时代南徙诸羌之汇合”。
另一篇则是姚薇元的“藏族考源”。④姚薇元:“藏族考源”,载《边政公论》第3卷第1期,1944年1月,第50-53页。西藏即唐朝时之吐蕃,而唐以前之情况,则不明朗。“两唐书吐蕃传既谓本西羌属,又言出自秃髮,藏人自述为释迦佛种,英人则指为蒙古支族。各说纷纭,莫衷一是。”为此,姚薇元“斟酌诸说,参以旧史所载,试为诠释”,撰成“藏族考源”一文,以供治民族史者之参考。此文要言不烦,据有关史料比较分析了中外各种观点,认为“今之藏族,即古之羌人,部落繁多。约当东晋时其中一部名‘发’羌者,统一诸部建立大国,诸羌因皆号‘发’族,而对异族则称‘大发’(Teu Bod)。唐书之‘吐蕃’,蒙古语之土伯特,阿拉伯语之Tubbot,英语之Tibet,皆‘大发’(古读杜拨)一名之译音或转呼也。”⑤见上注,50页、52页。这一结论在当时是不乏新意的。
吐蕃史的研究,这一阶段可谓盛极一时,名家名篇辈出:韩儒林先后发表的“吐蕃之王族与宦族”⑥韩儒林(1940):“吐蕃之王族与宦族”,载《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1卷第1期,1940年9月。和“吐蕃古史与传说研究”⑦韩儒林(1943):吐蕃古史与传说研究”,载《文史哲季刊》第1卷第2期,1943年6月。、任乃强的“吐蕃开国考”⑧任乃强:“吐蕃开国考”,载《康导月刊》第2卷第4期,1940年。此文又载《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117-121页。、“吐蕃音义考”⑨任乃强:“吐蕃音义考”,载《康导月刊》第5卷第4期,1943年。此文又载《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137-1143页。,谭英华的“吐蕃名号源流考”[10]谭英华:“吐蕃名号源流考”,载《东方杂志》第43卷第4期,1947年1-2月,第25-32页。此文又刊《史地丛刊》第1卷第3期,1947年1-2月。等都是这方面杰作。
其中任乃强先生的“吐蕃开国考”是作者为刘立千先生翻译《西藏政教史鉴》所作注释之一。“西藏古史多出于僧人之手,故宗教附会与史实相混,令阅者扑朔迷离,真伪难辨”,鉴于此,作者借“为刘立千先生译本之机,于吐蕃开国事略作考辨”。值得一提的是,任乃强先生此文系其系列论文“吐蕃丛考”之一,他所发表的还有九篇文章属于“吐蕃丛考”系列:“佛家之宇宙构成说(之二)”、“释迦牟尼生卒年考(之三)”、“大昭觉阿佛像入华考(之四)”、“金刚座瑞像说(之五)”、“藏人之历史观念(之六)”、“司青王迎旃檀像考(之七)”、“蒙古世系(之八)”、“藏人与六字明咒(之九)”和“文成公主下嫁考(之十)”,[11]这些文章均刊于《康导月刊》,其中“之二”和“之三”载第2卷第11期(1940),“之四”、“之五”、“之六”、“之七”、“之八”均载第2卷第12期(1940),“之九”载第3卷第1期(1941年),“之十”载第3卷第8、9期(1941年)。蔚为大观,可谓本时期吐蕃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谭英华的“吐蕃名号源流考”对黄子翼、任乃强、姚薇元以及丁谦诸氏对于“吐蕃”考证之得失进行分析比较的基础上,结合大量汉藏史料及国内外有关成果,运用语言学音韵考证与史料补证的方式,对吐蕃名号的产生及衍变沿革进行了较为信实的考证。此外,金应熙的“吐蕃之兴起”[12]金应熙:“吐蕃的兴起”,载《岭南学报》第8卷第1期,1947年12月。、任乃强的“隋唐之女国”①任乃强:“隋唐之女国”,载《康藏研究》月刊第5-6期,1947年。此文又载《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第212-234页。等文也值得一读。李安宅先生1941年在《边政公论》创刊号上发表“拉卜楞寺的护法神——佛教象征主义举例(附印藏佛教简史)”(见本章第三节)之后,丁骕先生针对该文文末所附“印藏佛教简史”所涉赞普世系之疑问,与李安宅先生通信探讨,李安宅先生专门为此作复,并对藏王(赞普)世系及年代问题进行了一番考证,是为“关于藏王(赞普)世系及年代考证”②李安宅、丁骕(读者通信):“关于藏王(赞普)世系及年代考证”,载《边政公论》第1卷第3-4期,1941年11月10日,第218-219页。。当然,由岑仲勉“《隋书》之吐蕃——附国”一文引发的任乃强与岑仲勉关于吐蕃问题的争论更是本时期学术自由争鸣的佳话。③1946年4月,岑仲勉先生根据《隋书》中有关史料考证,认为“附国”即吐蕃,发表了“《隋书》之吐蕃——附国”(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5期,1946年4月)一文。之后,任乃强先生读后认为“隋之附国为今西康之道孚、甘孜、德格等县地,与岑氏之说相差甚远”,随即发表了“附国非吐蕃——与岑仲勉先生商榷”一文,以“相与研讨辨订”,从位置、河流、国名、王号、城栅、物产等六个方面论述,继而认为“隋之附国,为党项族(羌族)之农业古国”,而非吐蕃。接着又发表了“隋唐之女国”一文(载《康藏研究》第5-6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任文发表以后,岑仲勉先生又发表了“从女国地位再论附国即吐蕃(附任乃强答案)”,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和补证,而值得一提的是,此文就发表在任乃强先生主办的《康藏研究》月刊第10期(1947年)上,这在今天看来的确是值得珍视的学术争鸣!学者之间的友谊并不为学术观点之不同而有所损益。
汉藏关系史的研究,王光壁的“汉藏同源论”④王光壁:“汉藏同源论”,载《康导月刊》第2卷第11期,1940年7月。从种族起源的研究角度求证汉藏久远的渊源关系;徐方幹的长文“历代茶叶边易史略”⑤徐方幹:“历代茶叶边易史略”,载《边政公论》第3卷第11期(茶研究专号),1944年11月,第4-34页。此文刘洪记、孙雨志(1999)将作者名记为“徐方子”。和李光璧的“明代西茶易马考”等⑥李光璧:“明代西茶易马考”,载《中央亚细亚》第2卷第2期,1943年4月,第47-53页。一方面论述了边茶贸易的经济状况,一方面可以从中看出汉藏长期以来的合作关系;玄默的“西藏与内地关系史略”⑦玄默:“西藏与内地关系史略”,载《蒙藏月报》第11卷第6期,1940年6月。、冷亮的“中藏关系论”⑧冷亮:“种族关系论”,载《东方杂志》第38卷第4期,1941年2月。和谭英华的“历代汉藏关系研究概况”⑨谭英华的“历代汉藏关系研究概况”,载《康导月刊》第6卷第9、10期,1947年9月。都勾勒了汉藏关系发展的基本脉络,但玄文则简略一些,谭文和冷文详尽系统一些;孙祖绳的“唐蕃舅甥联盟碑”[10]孙祖绳:“唐蕃舅甥联盟碑”,载《边疆研究集刊》第1期,1940年9月。和任乃强的“唐蕃舅甥和盟碑考”[11]任乃强:“唐蕃舅甥和盟碑考”,载《康导月刊》第5卷第7-8期合刊,第3-10页。此文又刊《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9)第144-158页。都对于唐蕃会盟碑进行了一番考释,以说明中原李唐王朝与吐蕃王国之间的亲和关系。任文后出,当然后来居上,论述较为充分:文章将《旧唐书·吐蕃传》所载长庆元年京师盟文与乾嘉时期入藏人士携回的会盟碑汉语碑文的各种录文[12]这些录文可见于《竺国纪游》、《卫藏图识》、《卫藏通志》、《西藏记》、《大清一统志》(《四川通志》与之全同)、《西藏图考》、《西藏通览》等典籍中。进行比较研究,然后与英人贝尔在其《西藏的过去与现在》中对藏文碑文的英译文进行对勘比较,对“大唐与大蕃”、“唐蕃两帝名号”、“甥舅之义”、“唐蕃和盟旧事”、“疆界”以及“日月二石”等进行了考证。
元世祖忽必烈与藏传佛教萨迦派八思巴之联合,使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使中华民族再度统一和复兴,创造了多民族文化共同繁荣的一代盛世。蒙藏联合促进了蒙藏文化交流,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后为帝师),掌管举国佛教与西藏事务,藏传佛教文化在元代宫廷与民间得以广泛传播。谭英华的“喇嘛教与元代政治”[13]谭英华:“喇嘛教与元代政治”,载《东方杂志》第42卷第4期,1945年10月,第15-29页。对西藏佛教的源流、蒙藏联合与民族文化的交流、元代各朝宫廷与民间笃信藏传佛教以及藏传佛教在中原各地的发展盛况等进行了考述。此外,谭英华还撰写了“明乌思藏初通中国考”[14]谭英华:“明乌思藏初通中国考”,载《史学杂志》第1期,1945年12月。一文,对明代西藏地方势力与明代中央王朝的隶属关系进行了考证。
黄奋生的“清代设置驻藏大臣考”[15]黄奋生:“清代设置驻藏大臣考”,载《边政公论》第1卷第2期,1941年9月10日,第4-12页。是国人研究清代驻藏大臣制度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自然不同凡响,作者将驻藏大臣制度的发展变化历朝分为四个时期进行描述,即康熙朝的创始时期、雍正朝的明定时期、乾隆朝的确定与扩大时期和光绪朝的衰微时期,进而认为光绪年间边事不宁之主要原因不是王勤堉所说“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负荷”之故,而是国力衰微,是“西藏的行政,唯一的建筑在军事的基础上面;行政权的隆替以在藏军事势力的大小为转移,而忽略了文化的经济的根本建树工作,致使藏人之思想感情生活均不易与内地协调,因之常保持闭关自守的局面,如沙滩建屋,随时可为暴风雨所击倒,事有必至,理所固然,这是我们研究清代驻藏大臣制度和其兴替,自然得到的一个结论。”这在当时是颇为新颖、富有见地的观点。丁实存的“清代驻藏大臣考(上)”、“驻藏大臣述评”和“清代设置驻藏大臣纪要”①丁实存的“清代驻藏大臣考”、“驻藏大臣述评”和“清代设置驻藏大臣纪要”分别刊于《边政公论》第1卷第11-12期合刊(1942年7月10日,第81-92页)、《康导月刊》第5卷第5期(第1-5页)和第6期(第6-11页)、《民主评论》第10卷第8期(1948年4月)。等文对清代驻藏大臣制度进行了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的研究,有力的证明了西藏对中央王朝的隶属关系。丁实存之论述后来以专书的形式出版,我们将在下文谈及。
帝国主义侵藏史方面,文章不是太多:
“咸同光宣四朝,六十余年,使藏者不下数十辈;而能以藏事为务,力挽回既丧失之权利,发扬中原之德意,笼络番心之内向,不畏强敌之逼境,而谋抵御之方策者,仅文硕一人而已”,而清廷对其并不满意,后来论藏者对其亦多有非难,故而庚年(吴丰培)兹撰述“文硕筹藏政策及其处理隆吐设卡案之始末”②庾年(即吴丰培):“文硕筹藏政策及其处理隆吐设卡案之始末”,载《中央亚细亚》第1卷第2期,1942年10月,第25-35页。一文,详细地考述了清代驻藏大臣文硕一生的治藏功绩,重点放在隆吐山设卡之经过。全文分六部分:一、绪言;二、文硕之身世;三、清季中英藏交涉之概况;四、文硕筹藏政策之由来及其设施;五、隆吐设卡与藏英交涉之原委;六、结论。在结论中明确肯定了文硕治藏的历史功绩。吴传钧的长文“近百年外人考察我国边陲述要”③吴传钧:“近百年外人考察我国边陲述要”,连载于《边政公论》第3卷第5期(1944年5月,第30-36页)、第3卷第6期(1944年6月,第51-57页)。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871年以前;第二时期:1871—1888;第三时期: 1888年以后)详述了外国人近百年来考察我国边陲的重要史实,内容涉及蒙古、西藏、帕米尔、新疆、天山等地方。向人们展示了那些国外的考察者们如何为其主子侵藏所效的犬马之劳。解放前夕,李有义发表的“揭穿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阴谋”④李有义:“揭穿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阴谋”,载《新建设》第1卷第2期,1949年9月。等文对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行径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译文方面,有钟山译的“英侵西藏关系文件(1904年)”⑤钟山译:“英侵西藏关系文件(1904年)”,载《边疆研究集刊》第1期,1940年9月。和朱正明的译文“英国侵略西藏简史”⑥朱正明译:“英国侵略西藏简史”,先于1938年9月刊于《亚洲世纪》第3卷第2、3期,十年后又刊重于《亚洲文化》等,其中后者影响较大,曾在多种刊物发表。
康青方面,有关西康的文章较多,有关青海的文章相对较少。有关西康的文章《康导月刊》上发表得稍多一些:张植初的长文“赵尔丰如何解决西康交通问题”⑦张植初:“赵尔丰如何解决西康交通问题”,连载于《康导月刊》第1卷6-9期、12期,第2卷第1-3期、4期、8期,1939年2月-1940年4月。关于赵尔丰治康的文章还有王绍曾的“赵尔丰怎样经营西康?”(载《新宁远》第1卷8、9期,1941年5月)等。全面追溯了赵尔丰治康的功过得失中的一个侧面。陈启图的“三十年来康政之检讨”⑧陈启图:“三十年来康政之检讨”,载《康导月刊》第6卷第1期,1944年7月。和刘文辉的“西康过去经营之得失与建省之经过”⑨刘文辉:“西康过去经营之得失与建省之经过”,载《康导月刊》第6卷第5-6期合刊,第1-3页。都追溯和探讨了康区治理的历史过程和功过得失、经验教训。
明驼的“卓尼之过去与未来”[10]明驼:“卓尼之过去与未来”,连载于《边政公论》第1卷第1期(1941年8月10日,第91-99页)、第1卷第2期(1941年9月10日,第51-58页)。全面描述了甘肃西南部卓尼藏区的历史地理概貌。和刘历荣的“西康木里宣慰司政教概况”[11]刘历荣:“西康木里宣慰司政教概况”,载《西南边疆》月刊第8期,1939年,第64-74页。对西康木里地方的历史地理概况调查和记录颇详。等众多文章也是藏区史的重要成果。限于篇幅,这里不赘。
(二)书籍
本时期的与藏族史有关的书籍,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大约有30多本(册)。一般著述20余种、较为专门的论述约10种。在我们所知的20余种一般著述中,有些是旧籍重刊,清代的《藏纪概》(1940年吴丰培写印本)[12](清)李风彩著:《藏纪概》,不分卷,旧钞本,民国29年(1940)吴丰培写印本。和《金川琐记》[13](清)李心衡撰:《金川琐记》,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年8月初版,72页,32开。等如是。有些是调查报告,蒙藏委员会编印的《宁属洛苏调查报告》[14]蒙藏委员会调查室编印:《宁属洛苏调查报告》,民31年(1942)出版。、《昌都调查报告》(附杂羭调查报告)[15]蒙藏委员会调查室编印:《昌都调查报告》(附杂羭调查报告),南京,编者刊,1942年9月初版,42页,32开。,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编的《川西调查记》[16]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编:《川西调查记》,重庆,编者刊,1943年3月初版,92页,16开。,个人著述《康昌考察记》[17]朱碶著:《康昌考察记》,重庆,大时代书局,1942年9月初版,124页,32开。、《西康社会之鸟瞰》[18]柯象峰编:《西康社会之鸟瞰》,重庆正中书局1940年7月初版,102页,32开。“史地丛刊”之一种。、《甘肃夏河藏民调查记》[19]马无忌撰:《甘肃夏河藏民调查记》,贵阳文通书局1947年1月初版,44页,32开。“风土丛书”之一种。、《雷马屏峨夷务鸟瞰》[20]唐兴璧、毛筠如:《雷马屏峨夷务鸟瞰》,1941年出版,122页,32开。、《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21]俞湘文著:《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1月初版,168页,32开。、《西康综览》[22]李亦人编著:《西康综览》,重庆正中书局1941年初版,1946年5月再版,1947年10月沪1版。470页,25开。、《西昌县志》[23]杨肇基纂修:《西昌县志》,4册,民国32年(1943)3月出版。西昌设县始自汉,迄今2073年,以前无有完本志书。民30年(1941)邑耆杨氏由蓉返里,并得邑文化协会之助,纂成本书。和《西康剪影》①程裕淇著:《西康剪影》,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年3月初版,86页,32开。“地学丛书”之一种。等如是。更多的是西康省政府编印的资料辑要,②共有8种:《理化概况资料辑要》、《巴安县概况资料辑要》(以上两书合为一册)、《西康(康定县)概况资料辑要》、《泸定概况资料辑要》、《峨边县概况资料辑要》、《屏山概况资料辑要》、《雷波概况资料辑要》、《马边概况资料辑要》。均是根据实地调查报告及省县历年档案编印而成。上述著作中虽然包含有藏族史内容,但从总体上看,它们更像地方志,内容涉及藏区的方方面面,在此我们从略。
专述藏族(宗教、政治、民族)史的书籍只有十种左右,但其中有不少传世佳作,比如丁实存的《清代驻藏大臣考》,刘立千译的藏文史籍《西藏政教史鉴》,任乃强的《康藏史地大纲》等。
最值得一提的首推丁实存的《清代驻藏大臣考》。③丁实存著:《清代驻藏大臣考》,边疆丛书之一,蒙藏委员会印行,民国32年(1943)10月初版,37年(1948)4月再版。小32开,162页+2页目录+4页序例。曾在《边政公论》第1卷第11-12期合刊起开始刊载。有清一代,治藏成功之道关键在于驻藏大臣制度的设立与实施,驻藏大臣制度是清代治藏的主要政治措施。关于清代驻藏大臣的研究,前文已介绍黄奋生先生发表的论文。而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专著当推《清代驻藏大臣考》。此书是研究清代驻藏大臣的第一部学术论著,对清代通过设置驻藏大臣统治西藏的有效措施极其成就与问题做了较为忠实的描述,全面叙述了近代西藏政治概况、清代蒙藏宗教政策与五世达赖喇嘛的输诚,研究了清代创设驻藏大臣的起因和时期,并对有清一代约120位驻藏大臣的行状功过做了全面的描述、检讨和总结。此书为学术界后来深入研究清代治藏和驻藏大臣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除书前的著者序例而外,全书分九章:一、近代西藏政治概述;二、清代对于蒙藏之宗教政策与第五世达赖喇嘛之输诚;三、驻藏大臣创设之起因与时期;四、驻藏大臣之职权;五、雍乾时期之驻藏大臣;六、嘉道时期之驻藏大臣;七、咸同时期之驻藏大臣;八、光宣时期之驻藏大臣;九、对于驻藏大臣之批评与结论。从序例可知,著者有感于清代以来各种典籍对驻藏大臣之记载“至为零乱”,而“康藏书籍,间或偶载之,但更不成系统,片段而已”之现实状况,根据有关文献典籍和论著成果撰成此书。“兹篇所撰者,以全部驻藏大臣之姓名与其在藏之事业为主,而以各大臣之身世与其他事业附见之;在藏事业,多者撮其要,少者记其详,其无可考见者,暂从缺略,以待补充”。详细考证了诸大臣之派赴抵藏与迁职及实在离藏之时间。驻藏大臣中“有一人兼隶两朝者,均列于前朝之内,下不重见”。叙述方式,“诸大臣之事实,采用传记文字;亦有因材料上之限制,又杂以考证之文”。为了统一,以免错乱,西藏人名地名与官职及宗教上等名称,引用原文。可见,此书在编撰体例和写作过程中是至为严谨、科学的。
此书出版时有当代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所撰的跋文,题曰“跋丁实存《驻藏大臣考》”。他认为有关西藏的中、西、新、旧著述精品约有500种,并从点、线、面、体的记载四个方面进行分类和分析。随后评曰:“丁君此书,虽仅属于点的记载,然其选点之精博,展拓之广泛,纂组之周致,实足代表有清一代对藏政治之全面。谓为清代西藏政治史,亦无不可。”并总结了《清代驻藏大臣考》的五个优点,认为此书体系完备、取材广泛、“消化众材而纂述之,去其枝叶,植其体干,不必存用原文,而多志其出处,使读者浏览则可省时,钻研则知所趣,体大而端,文省而备,抗战期中出书,当以此为良范也”;对史籍中所载驻藏大臣赴、离任时间多有考订;“著字不繁,于上下二百年中人物臧否,藏政失,列于指掌”。评价如此之高,可见此书之价值何等重要。
沈朗绛村(Bsod-Nams-Rgyal-Mtshan)原著,刘立千译、任乃强校注的《西藏政教史鉴》④此书连载于《康导月刊》第2卷第11期(1939)及以下各期。著者沈朗绛村,又译福德幢,为宗喀巴之受业师。此著藏文书名为《Rgyalrab-nams-kyi-byung-tshul-gsal-bavi-me-long-chos-vdyung-bzhug-so》,融会当时史藏与经论数十部而贯通之,后代奉为信史,家诵户晓,视同经典。校注者感于中国直接统治西藏近三百年,顾无藏籍之译本行世,颇觉疚心,因厘定译述义例,请四川德阳刘立千先生翻译。由于原书运用佛学名词与其神名、印契名、法物仪式名,以及人名地名等,当时汉语中没有定译,只能直译,难期“达雅”,因此,多用注释帮助理解。此外,原著对于纪年之法尚欠完备,多有与阙略或汉史出入之处,译校者均补考于各篇之后。原书没有目录,也是译者所拟。原著107藏文叶,分18篇。其中第13篇(迎娶文成公主,附录“文成公主下嫁考”)和18篇(自松赞干布死后,直叙至元末明初),分别占30余藏文叶和40余藏文叶,占全书2/3内容;其余16篇主要为佛教内容,只占全书1/3。可见其重点在于汉藏关系史、松赞干布的历史功绩方面。藏人著史作风与中西史家迥异,内容芜杂,宗教色彩较浓,不合史法者颇多,且原书多杂整齐而不压韵的韵文,然而,这正是藏人著史之一贯作风,正可以见藏人之本来之面目。译者采用直译,以保原书特色,对费解或阙略之处则以注释或附考补之。应该说,用汉文移译藏文史乘,当时也是开创性的工作之一。刘立千的另一部重要的藏文史籍译著是语自在妙善(即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错,ngag-dbang-blo-bzang-rgya-mtsho, 1617-1682)著的《续藏史鉴》。①语自在妙善著、刘立千译:《续藏史鉴》,成都华西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1945年11月]出版,75页,16开。此书译自藏文《西藏王臣史》,此书藏文原名为Bod-kyi-deb-ther-dpyid-kyi-rgyal-mo-glu-dbyung,成书于明崇祯16年(1643,后金崇德8年),收在作者全集dza函中,木刻版113页。全书共26章,详述西藏地方有史以来至固始汗时期历代王朝大事与王统传承。内容安排总体特点是详今略古,详政略教,对帕木竹派政权的兴衰过程记述最为详尽,对格鲁派历史背景也着墨较多。由于作者的地位特殊,所据史料丰富,故为古今史家所推崇。此外,此书文笔流畅、词藻丰富、文采华丽,同样被人们视为难得的文学佳品。由于该书的前一部分已另刊发表,刘立千译本《续藏史鉴》只译从唐末至明末的西藏史,分4章,书后附录载史鉴年表及参考藏籍目录。
任乃强著的《康藏史地大纲》最先由又西康省地方行政干训团1941年5月出版,共2册页码分别为228页和132页,32开。共四篇:一、“康藏鸟瞰”;二、“康藏古史”;三、“康藏近事”;四、“西康之现在与将来”。随后,第二年又出版了此书的节略本②任乃强著:《康藏史地大纲》(节略本),雅安,健康日报社,[1942年4月]出版,266页,32开。,266页,32开。全书分康藏鸟瞰、康藏古史、康藏近史、康藏现况4章。叙述千年以来康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同时涉及康藏之地理、宗教、民族、风俗与社会生活。书前有作者序。节略本虽然篇幅有所减少,但内容反而有所增益,并增图三幅。不过其中“康藏现况”中有些内容今天看来不合时宜(比如有“红军西窜”之类的说法)。全书十余万言,取材系去肤吸髓,叙述为要言不繁,源流因果,掌指屏列,文省义备,是为特点。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著名藏族学者更敦群培(dge-vdun-chos-vphel,1903-1951)的《白史》(deb-ther-dkar-po)③更敦群培:《白史》(deb-ther-dkar-po),1905-1951)著于民国35年(1946),书名藏文全称为bod-chen-povi-srid-lu-gsdang-vbrel-bavi-rgyal-rab-deb-ther-dkar-po-zhes-bya-ba-rzhugs-so。拉萨木刻版共46页,系未竟之作。在本时期问世。此书著于民国35年(1946),书名藏文全称为bod-chen-povi-srid-lugs-dang-vbrel-bavi-rgyal-rab-deb-ther-dkar-po-zhes-bya-ba-bzhugs-so。拉萨木刻版共46页,系未完成之作。此书是藏族学者首次利用敦煌古藏文写卷和汉文史料,结合古代藏族史学著作进行系统考证和论述的史学著作,对藏文的产生、松赞干布的生卒年、藏族的族源、族名、地名、服饰、风俗等有关古代吐蕃松赞干布至芒松芒赞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证和论述。是一部研究吐蕃断代史的力作。作者的治学方法开创一代风气,对近现代藏族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④1980年,该书被收入《根顿群培文集》第3册,由西藏古籍出版社出版,另有汉译本和英译本流传于世。关于更敦群培及其生平事迹,杜永彬有专书《二十世纪西藏奇僧》⑤杜永彬(2000):《二十世纪西藏奇僧——人文主义先驱更敦群培大师评传》,系作者博士论文,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32开,537页。论及。在谈及《白史》的学术价值时,杜永彬总结了三点:(1)考证精当,见解精辟;(2)论证确凿;(3)利用敦煌文献。评价甚为允当。继霍康·索朗边巴之后,进一步指出了更敦群培是第一位利用敦煌文献研究藏族史的藏族学者。⑥在这方面,霍康·索朗边巴也曾撰文对《白史》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这部著作中,宗教和历史分得十分清楚,与过去许多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藏文史书截然相反;根据敦煌出土的古藏文吐蕃历史文书和历代碑铭等资料史料与实物,对当时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恰如其分的结论。更敦群培是第一位运用敦煌古藏文考证西藏古代历史的藏族学者。《白史》关于西藏自7世纪以来在宗教上与印度的关系,特别是在政治上与唐朝中央政府之间的密切联系所作的正确论述,为13世纪西藏正式归入祖国版图提供了有力而可靠的证据。《白史》充分体现了我们藏族人民的智慧,因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详见霍康·索朗边巴之文“更敦群培大师传·清净显相”,载《西藏研究》1983年第2期。在更敦群培与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的比较,杜永彬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从中我们可以窥探两位藏、汉学术大师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和异曲同工之妙:
在同敦煌学的关系方面,更敦群培与国学大师陈寅恪有可资比较的地方。他们两人都受到了法国东方学(主要是敦煌学)的影响,都是在国外接触到敦煌文献的,并且都以法国学者为媒介:陈寅恪是在留学欧洲时,通过法国著名汉学大师伯希和(P.Pelliot,1878-1945)首次接触到敦煌文献的;更等群培则是在游历印度时,通过法国敦煌学家巴考首次与敦煌文献结缘的。正如陈寅恪所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更敦群培是第一个利用敦煌文书研究藏族古代史的藏族学者,并写出了史学名著《白史》,由此开创了利用敦煌文献研究藏族古代历史文化的藏学传统,称得上是第一位藏族敦煌学家;而陈寅恪则是第一个提出“敦煌学”名称的汉族学者,早在1930年,陈寅恪就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首次提出“敦煌学”的名称,从理论上阐发了敦煌文献的珍贵价值,筚路蓝缕,推动了敦煌学研究的广泛开展。并在困难的条件下,利用有限的资料,在文史佛藏各方面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⑦杜永彬(2000):192-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