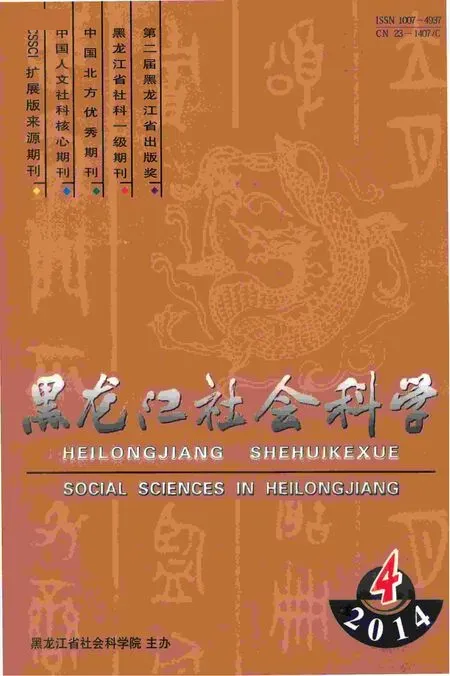辽代佛教世俗表象探微——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张国庆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沈阳110036)
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我国,为了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即开始了“中国化”的转变历程,融摄儒、道文化逐渐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唐宋时期,佛教发展臻至鼎盛,并迅速由庙堂高坛迈入了“世俗化”的境域。辽王朝踵唐之后,辽代佛教亦逐步贴近世俗,并对世俗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辽代佛教多有研究,成果显著,但遗憾的是,目前尚未见有人就辽代佛教世俗化问题进行研究。笔者不揣浅陋,钩沉辽代石刻资料并结合传世文献,拟对这一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辽代佛教世俗化的时代背景与信仰基础
所谓佛教世俗化,一般是指具有高深教义的宗派学理型佛教,向民间佛教转化,并最终变成“民俗佛教”。佛教与世俗原本互不相涉,但佛教的宏旨是救度众生——重“彼岸”是为了解决“此岸”存在的问题,重“来世”是为了对“今生”的所作所为给予指导,重“出世”的主旨在于悟道,而悟道的最终目的是为世间的人服务,因此佛教又是贴近世俗的。佛教在传播过程中,能够通过各式各样的佛事活动来沟通并调整与世俗社会的互动关系,与信众共同来维持或建构生命存在的理想范式,从而达到整个社会和谐并正常运转之目的[1]。辽代佛教的世俗化,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与深厚的信仰基础。
(一)辽代佛教深受唐代佛教世俗化的影响
唐代是中国佛教走向世俗化的第一个高峰期,其世俗化表现有三点:信仰对象多层化、信仰内容多样化、信仰方式简单化[2]。唐代的佛教信众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尤以中下层民众为主,具备了较为广泛的世俗社会信仰基础。段塔丽教授认为,唐代“中国化”的大乘佛教所关注的对象已转向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而关注的焦点也已指向民众的内心诉求与精神慰藉,这对于那些长期以来生计不保、难以把握自身命运的中下层民众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进而成为佛教信仰的忠实群体[3]。吴敏霞、李晓敏等人亦认为,出于对佛教所谓人世间生老病死、灾难祸福无非“因果报应”之说的笃信与敬畏心理,去寺庙烧香拜佛,求菩萨保佑,已成为那个时代民众的一种普遍心理需求与精神寄托[4]。辽代佛教信仰主要源自中原汉地,因而唐代的世俗化佛教对辽影响颇深。
明代高僧元贤曾对由隋唐经两宋到元明时段的佛教僧侣世俗化渐行渐深有过概括,见诸(嗣法)道霈重编之《永觉元贤禅师广录》卷三十:“唐以前,僧见君皆不称臣,至唐则称臣矣。然安秀诸师宫中供养,皆待以师礼。诸师称天子则曰檀越,自称则曰贫道。至宋,绝无此事,然犹有上殿赐坐,入宫升座等事。至近代,并此亦无之,僧得见天子者绝少。”这就是说,在隋唐以前,僧侣在皇帝面前还能表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姿态,故而常有“沙门不敬王者”的事情发生;唐宋以降,佛教僧侣则越来越受到世俗政治的制约。所以,辽代佛教的世俗化亦属大势所趋,在所难免。
(二)辽代佛教在民间普及广泛
辽代中后期,佛教基层信众群体十分庞大,为佛教的世俗化奠定了基础。这一信众群体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是人数众多的出家僧尼,二是难以计数的在家居士。有辽一代剃度出家的僧尼数量十分惊人,尤以辽代后期的道宗朝为突出。《辽史》卷二三《道宗纪三》载:咸雍八年(1072)三月,“有司奏春、泰、宁江三州三千余人愿为僧尼,受具足戒。许之”;大康四年(1078)七月,“诸路奏饭僧尼三十六万”。
关于在家居士的数量,我们可以从石刻资料记载的某些高僧设坛讲经时所度俗家信众的人数中略窥一斑。如道宗大安五年(1089)的《六聘山天开寺忏悔上人坟塔记》记载,忏悔上人曾经“放菩萨戒坛十余次,所度白黑四众二十余万”[5]413。又,大安七年的《法均大师遗行碑铭》载,法均大师于咸雍六年“自春至秋,凡半载,日度数千辈”。此后,“乃受西楼、白霫、柳城、平山、云中、上谷泉、本地紫金之请,所到之处,士女塞途,皆罢市辍耕,忘馁与渴。递求瞻礼之弗暇,一如利欲之相诱。前后受忏称弟子者,五百余万。”[5]438为满足广大民间基层信众的信仰需求,佛教必定要贴近世俗,并最终走进世俗化境域。
二、辽代佛教世俗表象阐释
辽代佛教虽贴近世俗,但客观地说,它还远没有达到成熟的“民俗佛教”的程度,有的仅仅是“世俗表象”而已。归纳之,辽代佛教的世俗表象,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皇帝赐授高僧荣誉官衔——僧侣上层趋俗涉政
辽代后期的兴宗、道宗二帝,经常向高僧赐授荣誉官衔。据《契丹国志》卷八《兴宗文成皇帝》记载:兴宗时,朝纲不振,而“尤重浮屠法”;兴宗在位二十四年,高僧“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6]82。而《辽史》卷二二《道宗纪二》则记载道宗分别于咸雍二年(1066)、咸雍五年和咸雍六年赐高僧守志、志福等人“守司徒”,高僧圆释、法钧等人“守司空”之职。皇帝向高僧赐赠官爵,并给予他们很多礼遇和宠幸,“出则乘马佩印,街司五伯各二人前导”[7],助长了某些高僧的乖傲之气,他们开始“非奉诏”亦肆无忌惮地“入阙”,并在讲经论道之余毫无顾忌地“妄述祸福”,出现了佛教干政的苗头。有学者指出,佛教的内证体验、超越哲学、佛国理想和修行仪轨等信仰内核,透过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层面,扩展到世俗文化领域,取得传播媒体及表现形式,以此实现改造并提升了世俗生活的本怀,在这一过程中,佛教也必然受到被超越对象——世俗社会的影响、改造乃至同化,从而偏离出原有的价值体系而走向“世俗”[8]。在世人的眼中,所谓高僧,应当是法德高尚、学养深厚,严守戒规、超然度外,专心弘法、远离朝政,视世间一切都是身外之物,有如电光石火、过眼烟云的。尽管辽代高僧是被动地接受皇帝赐授荣誉官衔,但也表明其并不排斥世俗,从而对辽代佛教贴近世俗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信众的孝亲与忠君——佛教义理的儒化倾向
孝亲与忠君是儒家一贯倡行的纲常伦理,早期佛教却主张无父无君。然而,自从佛教扎根于神州,孝亲与忠君便逐渐成为“中国化”佛教义理的组成部分以及佛教信徒的行为准则,辽代亦不例外。如咸雍七年的《李晟为父母造幢记》中的一则“五戒颂偈”即明确昭示,崇佛者必须“于家存孝,于国尽忠,一生慈善,性行敦柔”[5]347。“五戒”是佛门四众弟子的基本戒规,不论出家、在家皆须遵守。很显然,该石刻文的作者是将儒家的“五常”与佛教的“五戒”糅合在了一起,认为佛教信众坚持“五戒”就是践行了“五常”,也就达到了“存孝”和“尽忠”的目的。而由于佛教在辽代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扶持,辽代佛教信众便在诸多场合为国君祈福祷安。如圣宗开泰二年(1013)的《白川州陀罗尼经幢记》中的祝辞:“奉为神赞天辅皇帝、齐天彰德皇后万岁,亲王公主千秋,文武百僚恒居禄位。风调雨顺,海晏河清,一切有情,同霑利乐。”[5]146
(三)邑社组织与“福田”活动——信众佛事活动中的世俗内容
佛经上说,佛教信徒若散播布施、供养之种子,就能结出福德之实,以田地喻之,即称之为“福田”。从辽代中期开始,城乡基层的广大僧俗信众纷纷组织起一种泛称“千人邑”的民间佛教组织。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量力集资,参与各种佛教“福田”活动。
辽代信众从事的福田活动主要有如下四种。
第一,向灾民施舍钱财。道宗执政年间,自然灾害频现,地域之广,程度之深,受灾民众之多,历朝罕见。所以便有大安三年(1087)五月“海云寺进济民钱千万”(《辽史》卷二五《道宗纪五》)等类似的善举出现。
第二,开义仓发放粮谷。辽代许多寺院都设有义仓,贮存粮米,用以灾年赈济贫民。如天祚帝乾统八年(1108)的《妙行大师行状碑》即云,妙行大师“尝一次添香□□□□□□□随郡县纠化义仓,赈给荒歉,凡有乞者,无使空回”[5]587。
第三,架桥修路。辽代后期多洪灾,经常冲毁道路与桥梁。因此,每当洪水过后,许多僧俗信众便筹集资金,铺路修桥,以方便民众出行。如道宗大康十年(1084)的《重修桑干河桥记》即详细记载了大康三年至大康十年间,西京道宏(弘)州和蔚州当地僧俗信众在高僧崇雅等人组织下,捐施钱物,修建桑干河大桥的过程([民国]《天镇县志》卷三《金石志》)。
第四,建“义冢”掩埋无主尸骨。在辽代,每当大灾之后,郊野便会出现很多无主遗骸,这时,一些民间义士、佛教信众便行动起来,拾遗骸,建“义冢”。如道宗寿昌五年(1099)的《义冢幢记》载:“大安甲戌岁,天灾流行,淫雨作阴,野有饿莩,交相枕藉。时有义士收其义骸,仅三千数,于县之东南郊,同瘗于一穴。”然由于“厌其卑湿,掘地及泉”,结果是“出其掩骼,暴露荒甸,积聚如陵”。西京大华严寺僧人示化等人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虔择福地,时建道场,供佛延僧,洗心盥掌,运有委骨,置在坛内。”待法会结束,他们便将这些无主遗骸“迁葬于粟山之屺,目曰义冢”[5]495-496。
(四)寺院经济的畸形发展——僧侣物质生活的世俗取向
有辽一代二百余年间修建了大量寺庙,诚如咸雍八年《创建静安寺碑铭》所言,“三教并化,皇国崇乎至道,则梵刹之制布域中。”[5]360其中有不少大型寺院,它们拥有的寺田数量,十分惊人。大型寺院庄园化和僧侣物质生活世俗化在辽代中后期成为普遍现象,寺院的经济活动染上了浓郁的营利色彩。
辽代寺院田产之来源大致有三种渠道:一是寺院传承于前朝已经占有的寺田,二是社会各阶层俗家信众向寺院施舍的土地,三是寺院自己出资购买的田产。如大安九年的《景州陈宫山观鸡寺碑铭》即记载观鸡寺“广庄土逮三千亩……增山林百余数顷,树果木七千余株”[5]453。辽代有众多在寺院庄园中谋生的寺户,称为“二税户”,他们的劳动所获,除一部分上交朝廷外,大多为寺院所得。辽代寺院经济畸形发展的另一表现,就是寺院将余钱或余粮放贷,从中获取高额利息。宋人苏辙在《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中记载:“北朝皇帝好佛法……所在修盖寺院,度僧甚众。因此,僧徒纵恣,放债营利,侵夺小民,民甚苦之。”[9]卷十,199又,寿昌元年的《添修缙阳寺功德碑》记载:“……外,犹有余积,仍每年筵僧二百人。迄今二十余年,未尝有(下缺)粟一千硕,钱五百缗,每年各息利一分。”[5]465
辽代一些寺院靠收取寺田税赋以及放贷赢利,再加上社会各阶层信众的大力捐施,积累了大量财富。如乾统七年的《朔县杭芳园棲灵寺碑》即云,棲灵寺“仓廪实而积粟如阜,府库充而□□□□”[5]575。有学者认为,“在(辽)王朝灭亡时,佛寺的财产,除了契丹两大统治贵族(耶律氏和萧氏),可能没有其他家族能与之相匹敌。”[10]
(五)与士大夫交往密切——僧侣精神生活的世俗取向
石刻资料显示,辽代高僧与士大夫交往密切,接触频繁,主要表现在如下三点。
第一,诗文唱和。辽代高僧中有文学素养颇高者,他们不时会因“某事”而作诗,并求“和”于同样善吟的士大夫。此类事例中最具代表性者,当属寿昌五年的《玉石观音像唱和诗碑》刻记的组诗及其背景故事[5]501-506。寿昌年间(1095—1101),中京道兴中府的信众于府南的天庆寺刻造了两尊玉石观音像。佛像雕成后,寺中被道宗皇帝赐授崇禄大夫、检校太师、行鸿胪卿、英辨大师、赐紫等名衔的高僧智化,首唱“胎字韵”赞颂玉石观音诗两首,并求和于僧俗文士。于是便有二十四人各和诗一首,构成了一组“玉石观音像唱和诗”,并刻于石。二十四人中,除三位诗僧外,其余均是当时有不同官衔的士大夫。这组诗颇富文采,且禅味浓郁,一时传为佳话。
第二,理论切磋。在辽代,通晓“外典”(儒道典籍)的高僧经常与士大夫一起探讨某些理论问题,譬如“佛儒关系”。这其中,乾统三年的《柳谿玄心寺洙公壁记》的作者、乾文阁直学士杨丘文与他的朋友、高僧“洙公”(释号“了洙”)即是典型代表。据这篇文章记载,杨丘文与洙公经常在一起交流切磋佛儒互相援引与互为补充的一些问题。在文章中,杨丘文首先就儒之“仁”“智”与佛之“性情”的关系、“仁”“智”互养的结果以及“治性之道”等问题进行了一番理论阐述,揭示了佛儒相契与互融的关系;并介绍了洙公援引佛教禅学义理,潜心研究儒家学说的经过。但遗憾的是,洙公的理论研究不仅没有得到其同道的认可,反被指为异端邪说。好在杨丘文非常赏识洙公的学说与观点,为之正名道:“抑闻彼之所谓佛者,乃而党之所师也。倡之五教之说,以溢编轴。而后其徒若灿肇融觉观密之辈,比比而作,皆尔党之秀杰也。率有辩论篇藻以翼其术而抪之世也,不亦谓之文乎?是皆得吾仁智相养之道也。”[5]539-540杨丘文与洙公通过深入探讨与交流,最终均力主儒学与佛教在各自发展过程中要不断援引和吸收对方学说的有益成分,以便涵养和丰富自我。
第三,互写墓志。检索石刻资料,此类事例颇多。如圣宗统和二十三年(1005)的《王悦墓志》的作者“讲法花上生经文章赐紫沙门志诠”,为知名高僧;而墓主王悦是圣宗朝士大夫,官至宁远军节度副使,爵为太原公。志文最后说,“嗣子情哀陟怙,志忉为陵,铭志未休,函题见托,乃援其笔,为勒词云,”表明志诠与王悦及其家人相熟,与王悦之子王莹(厢都指挥使)、王凝、王福哥三人中的一人应是朋友关系[5]112-114。又如乾统七年的《普济寺严慧大德塔记铭》的作者署名为“朝请大夫、少府少监、知秘书少监、上骑都尉、汝南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南抃”;而严慧则是道宗末天祚初燕京地区的著名高僧,原为三学寺住持,天祚帝曾“特赐紫方袍,加号慈辩”。塔记云:“乾统七年春,燕京三学寺殿主严慧大德赐紫沙门等伟,痼疾作。始夏,疾有加,徙居右街福田寺,卧于西庑之一室。余往问焉,师以不起语余,且有事付托。四月旬七日仙逝,余又往吊焉。……(五月)初,门徒之隶甘泉者,敬谕、敬谣、敬浊与本寺都知僧敬度、持首座大众三纲等仅等状具师遗行,来谒余……余既与师有旧,又逼向之所请,不克以事辞,因以实而志之。”[5]571-572可见,南抃之所以为严慧撰写塔记,即因二人曾是朋友,平时多有交往之故。
三、佛教世俗化对辽代社会的影响
伴随着佛教世俗化,又会产生世俗社会“佛教化”的现象。按台湾学者郑志明教授的说法(转见于前揭王雷泉文),所谓世俗社会的佛教化,是指将佛教神圣性的宗教经验经由社会化的宣导与转化,成为世俗信众普遍共有的信念。它包括三个活动面向:仪式性活动(以佛教的各种仪式来为群众消灾解厄与增加功德福报,进而以佛教仪式取代社会原有的祈福仪式)、共修性活动(以集体的宗教行为与实践感受,改变个人的生命情操与生活态度)与传播性活动(将佛教知识与艺术传播到世俗社会之中,成为群众的主要精神食粮与教化系统)。辽代世俗社会的佛教化显然还没有达到上述程度,仅是出现了这种趋势而已,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世俗人生某些时段所受的佛教影响
譬如契丹妇女生育期间要建道场。宋人王易《燕北录》云:契丹皇后怀孕如过八个月,即“先启建无量寿道场,逐日行香,礼拜一月”。并“预先造团白毡帐四十九座,又内一座最大,径围七十二尺”,皇后临产时,“于道场内先烧香,望日番拜,八拜,便入最大者帐内。”“每帐各用有角羊一口”,婴儿娩出之际,令人“用力纽羊角,其声俱发”,以此“代皇后忍痛之声”[11]。
譬如起名好用佛号。圣宗耶律隆绪小名为“文殊奴”(《辽史》卷十《圣宗纪一》);道宗宣懿皇后萧氏小字“观音”(《辽史》卷七一《后妃传》);穆宗应历五年(955)的《北郑院邑人起建陀罗尼幢记》中有人名为“菩萨留”[5]11-12;道宗大安五年(1089)的《萧孝忠墓志》载孝忠“一男名药师奴”[5]416;天祚帝乾统八年(1108)的《耶律弘益妻萧氏墓志》言“夫人萧氏,名弥勒女”[5]590,等等。
譬如死后采用火葬。考古资料证明,位于河北宣化下八里的辽代后期张氏和韩氏家族墓,均是受佛教影响而实行火葬的。据出土墓志记载,张氏家族中的张匡正、张世本、张世古,韩氏家族的韩师训等人,生前诵经念佛,死后便依西天“荼毗礼”葬式,焚尸后将骨灰葬于墓内。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辽宁等地的一些辽墓中也发现了不少骨灰罐。
(二)世俗生活某些方面的佛教烙印
譬如将佛诞日纳入岁时节日。《契丹国志》卷二七《岁时杂记》载:四月初八佛诞日(又称“浴佛节”),“京府及诸州,各用木雕悉达太子一尊,城上堄行,放僧尼、道士、庶民行城一日为乐。”[6]251应历十五年的《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亦云:“风俗以四月八日,共庆佛生。凡水之滨,山之下,不远百里,仅有万家,预馈供粮,号为义仓。是时也,香车宝马,藻野缛川,灵木神草,赩赫芊绵,从平地至于绝巅,杂沓驾肩,自天子达于庶人,归依福田。”[5]33
譬如喜好素食及饮茶。如乾统五年的《白怀友为亡考妣造陀罗尼经幢记》载,白怀友的父亲“魁梧庞厚,乡闾畏惮,然性善崇尚我教……重和中,会吕上人传菩萨戒于里之驿亭,自是不食荤血,奉五戒,终生无惰”[5]550。而关于辽人喜好饮茶,可从前述河北宣化下八里辽代张氏、韩氏家族墓壁画《备茶图》和《备经图》中得以印证。
譬如将某种护肤方法称作“佛装”。据宋人庄绰《鸡肋编》记载:契丹辽地妇女“冬月以栝蒌涂面,谓之佛装。但加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涤去。久不为风日所侵,故洁白如玉也”[9]卷二四,436。栝蒌是一种多年生草本葫芦科植物,《本草》上说“栝蒌可悦泽人面”。契丹辽地女子入冬时将金黄色的栝蒌捣成汁,逐层地往脸上涂抹,最终形成一层面膜,至暮春才揭掉洗净。这种护肤方法因与佛像的髹饰相似,故以“佛装”名之。
结语
禅宗六祖慧能有言:“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寻兔角。”走向世俗化是佛教发展乃至繁盛的必由之路。佛教只有通过改变自身,关注并适应现实社会,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相结合,才能使广大信众理解并接受,作为一种西来文化才有可能在东方找到适宜的土壤,最终破土生根、开花结果[1]。有人认为辽代佛教继承了唐代学理型佛教传统,贵族化的义学宗派兴盛,学术特征明显,居于当时东亚佛教文化圈的中心地位。这话没错。尽管辽代还没有出现倒卖度牒和紫衣师号等现象,功利取向尚不十分明显,与同一时期的北宋佛教相比,二者的世俗化程度还有着较大的距离,但通过本文的分析可见,辽代佛教的世俗化,具备了相应的时代背景与应有的信仰基础,其表象多样,特征明显,对辽代社会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1] 杨富学,王书庆.从生老病死看唐宋时期敦煌佛教的世俗化[J].敦煌学辑刊,2007,(4).
[2] 王慧慧.浅析民俗佛教——兼谈世俗化与民众化的认识[J].敦煌学辑刊,2007,(4).
[3] 段塔丽.论唐代佛教的世俗化及对女性婚姻家庭观的影响[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1).
[4] 吴敏霞.从唐墓志看唐代世俗佛教信仰[J].佛学研究(年刊),1996;李晓敏.造像记:隋唐民众佛教信仰初探[J].郑州大学学报,2007,(1).
[5]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6]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M].贾敬颜,林荣贵,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7] [宋]洪皓.松漠纪闻:卷上[M]//金毓黻.辽海丛书:第1册.沈阳:辽沈书社,1985:207.
[8] 王雷泉.神圣化与世俗化——以《大金沃州柏林禅院三千邑众碑》为例[C]//吴言生.中国禅学: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02.
[9] [清]厉鹗.辽史拾遗[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0] Karl A.,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M].New York:Macmillan Press,1949:295.
[11] [清]杨复吉.辽史拾遗补:卷四[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