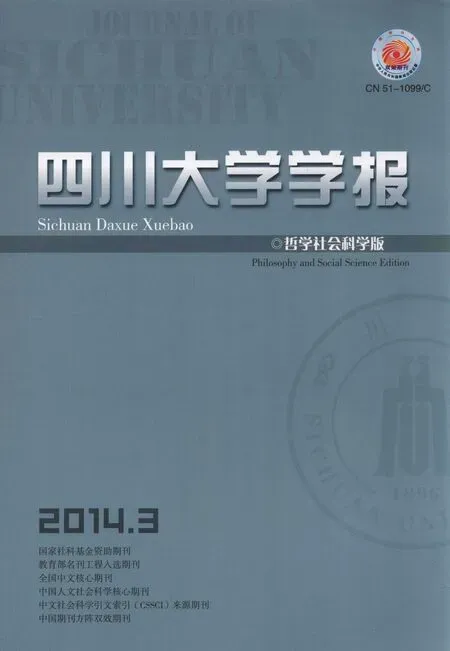由误解发现 “童年”:“阿利埃斯典范”与儿童史研究的兴起
辛 旭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1962年,英语世界翻译出版了法国人菲利普·阿利埃斯 (Phillipe Ariès)于1960年出版的法文著作《旧制度下的儿童与家庭》 (L'Enfant Et la Vie Familiale Sous I'Ancien Régime),并将其命名为《儿童的世纪》(Centuries of Childhood: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该书甫面世,即受到英语世界读者的广泛欢迎。最先对这本书表现出浓厚兴趣的是临床精神分析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他们认为题中“儿童”一词颇有兴味。因为该研究不但将目光投向家庭这一私人生活领域,同时特别关注到这一私领域中的“最小”构成因素“儿童”,这与其时欧美新社会史家更多注意社会分层与阶级分析、很少关注家庭的研究取向大不相同,而书中展现出的明显的精神分析路径也很吸引人。译者将法文书名中的“家庭”去掉而突出了“儿童”的巧妙心思,更是因应了当时的读者心理。此书不但在学界受到广泛关注,也引起了普通读者的兴趣;阿利埃斯本人也因此获得了日后广为人知的“儿童史家”的学术声名。①在实际研究中,学界常将“儿童史”与“童年史”混用。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两个研究概念的不同,但尚无有关这一概念区分的理论探讨,笔者拟日后专文讨论。本文倾向于采用更加大众化的提法“儿童史”,但为尊重其他研究者的本意,依据其意选择使用“儿童史”或“童年史”。正如此后著名儿童史家休·葛宁汉姆 (Hugh Cunningham)指出的,“所有的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历史写作中都绕不过一些‘关系’,童年史家绕不过去的即是阿利埃斯的《儿童的世纪》”,因为他的研究使读者确信“童年自有其历史”。②Hugh Cunningham,“Histories of Childhood,”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3,No.4,Oct.1998,p.1196.
阿利埃斯的研究激励了大批史家将目光投向儿童,同时,他关于近代家庭“情感革命”的论断,以及对儿童概念进行文化建构和对核心家庭内角色进行分析的方法也受到了许多批评,有些批评甚至相当激烈,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畴。但阿利埃斯也建立起了一个儿童史研究典范,而迄今为止的所有儿童史著作都可以被看作是对“阿利埃斯典范”的精炼和修正。用美国史家约翰森 (Dorothy Johnson)的话说,阿利埃斯典范“从没有被取代”。③Dorothy Johnson,“Engaging Identity:Portraits of Children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an Art,”in Anja Muller,ed.,Fashioning Childhoo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Age and Identity,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6,p.101.
从《儿童的世纪》诞生至今,有关儿童的历史研究著作已经汗牛充栋,其研究方法、取径和理论也得到充分讨论。①俞金尧详尽介绍了儿童史领域的重要著作,并大致勾勒出西方世界儿童史研究的编年脉络,参见俞金尧:《西方儿童史研究四十年》,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98-336页;《儿童史研究及其方法》,《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台湾学者陈贞臻对儿童史研究的学术史探讨较为详尽,指出阿利埃斯之后的儿童史研究主要遵循两条路线:1970年代开始的“社会建构”取向和1980年代在批评前一取向基础上兴起的“生活经验论”取向,参见陈贞臻:《西方儿童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阿利埃斯及其批评者》,《新史学》(台北)第15卷第1期,2004年3月,第167-188页。陈文并详尽分析了这两条主要研究取向的重要作品。但作为一个可显著区分出来的“学科”,儿童史仍是一个新生儿,其学科性质与归属也常被学者混淆。而这些模糊不清之处,很多都与学界对阿利埃斯个人和《儿童的世纪》这一文本的一系列误解有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作为一个具有自己独特疆界的研究领域,儿童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这许多误解催生的;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这一“误解”是儿童史学科产生的唯一原因,但这一面却是以往研究者注意不够的,本文的意图就是要弥补既往认知中的这一缺憾。
一、中世纪存在“儿童”的概念吗?
《儿童的世纪》一书最受人关注的地方是它对16、17世纪欧洲上层社会家庭中出现的关于“童年”的新概念的阐释。阿利埃斯认为,中世纪“家庭”处于亲属关系网络的中心,是由所有“住户”共同构成的小共同体。家长看重的是整个家庭在社会谱系中的声望,并不关注儿童的个人进阶。儿童处于家庭生活的边缘,通过模仿成人而“成”人。即便贵族家庭的孩子,也是很小就被送到别的贵族家庭,充当仆从,以为实习。在这一时期,“儿童的概念”来自其“依附观念”。即是说,“儿童”一词指涉的并不纯粹是处于某一生理阶段的一群人,它也用于对“儿子”、“男仆”、“服务生”等与封建关系或领主依附相关联的群体的称呼和界定。在此意义上,阿利埃斯断言:“那是没有儿童”的时代。②Phillipe Ariès,Centuries of Childhood: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trans.R.Baldick,New York:Alfred Knopf,1962,p.31.又,该书有中文版,但是一个节译本。见菲利普·阿利埃斯:《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与家庭生活》,沈坚、朱晓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本文征引,迳从英文版。16、17世纪后,情况发生了转变。核心家庭逐渐形成,父母在情感上体会到孩子与自己紧密相连,不但开始为他们考虑未来,也开始意识到童年是生命发展历程中的独特一环,儿童是与成人不同的“社群”。这样,有关“童年”的新概念出现了:“儿童”仅仅与人生的某一特定生理阶段相连,而不再和社会等级结构连在一起。进一步,直到17、18世纪,成人才“认识”到“童年”与“青少年”之间有区别。因此,在欧洲,“也许从13世纪开始”,但直到“16世纪末,而且主要是在17世纪”,人们才“发现儿童”。③Ariès,Centuries of Childhood,pp.31 -47.
吕西安·费弗尔 (Lucien Febvre)曾说, “人”是“历史学唯一的对象”,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更将史学家类比为“食人魔”,哪里有“人味”,哪里就有“猎物”。④转引自安托万·普罗斯特:《历史学十二讲》,王春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8、149页。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研究也可以被视为不断有“人”被历史学家“捕猎”到的过程。而今日史家大都同意,“儿童”是被阿利埃斯“捕获”的。阿利埃斯不但“发现”了历史中的“儿童”,也将其对象化,以儿童为中心来考察儿童与成人的关系。《儿童的世纪》也因此被人们视为“儿童史”成立的起点。
然而,如果我们回溯学术史,将会发现,阿利埃斯决非第一个把“儿童”摆在史学家书桌上的人。早在启蒙运动时期,文学家维克多·雨果就曾得意洋洋地宣称:“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不过是发现了新大陆,而我发现了儿童。”⑤转引自 Colin Heywood,A History of Childhood: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the West from Medieval to Modern Times,Cambridge:Polity Press,2001,p.26.将儿童的发现与新大陆的发现相提并论,体现出这一时期将儿童加以浪漫化的思潮的影响。在历史学领域中,阿利埃斯之前,提到儿童并以儿童为中心的著作也已出版不少。⑥Lamar F.Janney,Childhood in English Non-Dramatic Literature from 1557 to 1798,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24;J.Jeremias,Infant Baptism in the First Four Centuries,London:SCM Press,1960;E.Josephson,Political Youth Organization in Europe,1900-1950,Ph.D.Dissertation,Columbia University,1959.其他不一一列举。不过,人们把阿利埃斯视为“儿童史”的鼻祖,也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此前这些研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更没有引发学者有意识地追风式研究。这一切,都要从阿利埃斯开始。
那么,为什么阿利埃斯的研究会成为“儿童史”研究的起点呢?这里边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学术史本身的原因。①195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逐渐走向“封闭”,强调女性在家庭中的价值,由此引起一系列女权反抗。这类反抗在日常实践中便是对家庭成员、家庭关系的重新思考。而从学术内在理路上来讲,美国的心理史学自1920年代便已经形成研究特色,这一研究的重要取向便是关注儿童。因此,《儿童的世纪》一书的英译本在英语世界引起的反应远超乎在它故乡的反应。这些关键因素如何起作用,不在本文关心范围内,此处不展开。本文并不想全面探讨这些原因。这里想指出的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儿童史”吸引了众多史家的瞩目,在很大程度上是拜英译本对阿氏著作一些词句的“误译”所赐。如前所述,16、17世纪人们对“儿童”或“童年”的“发现”是阿利埃斯最为人所熟知的观点。但问题是,怎样理解阿利埃斯所谈论的这个“发现”(discover)?首先,阿氏在该书第一卷中检视的是“sentiment de l'enfance”的出现。在法语中,sentiment是一个含义广泛的词汇,既有“感受”、“感觉”,也有泛言“想法”的意涵。②此处法文理解承四川大学哲学系曾怡博士的指点。有学者指出:“sentiment de l'enfance”“可谓一个暧昧不清晰的短语”,它既暗示了作为一种现象的“童年意识”,也提示了对“童年的感觉”。③Carmen Luke,Pedagogy,Printing,and Protestantism:The Discourse on Childhood,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9,p.12.英译本将sentiment转译为idea(概念),有意无意间突出了其“价值观”的一面。④英语词汇idea在18世纪中期以前,含义较为广泛,主要指的是由具象事物产生的“概念”和“想法”(在这一点上,与法文sentiment有相合之处),但尤重与“经验”和“具体事物”的联系。19世纪后,这一词汇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倾向于“抽象”一面,并突出其“价值”色彩。英国著名史家罗伊·波特 (Roy Porter)曾专门论述过这一问题,见 Roy Porter,Enlightenment:Britai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London:Penguin Books,2000,pp.47-49.这样,它使得读者更多地把是否存在“儿童的概念”视为一个好和坏的问题。第二个错误则主要应该归咎于评论家和读者。阿利埃斯在原书中用了一章的篇幅,论证中世纪的人“不知道”(英文本译作“did not know”)儿童“概念”。⑤Ariès,Centuries of Childhood,pp.31 -47.但后来的评论家却把这个论述浓缩为一句斩钉截铁的判断:中世纪社会并“不存在儿童的概念”(the idea of childhood did not exist)。⑥这一判断深入人心,此处随手举出一例,见Sterling Fishman,“Changing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A Modest Proposal,”History of Childhood Quarterly:The Journal of Psychohistory,Vol.13,No.1,Summer 1985,p.70. 需要指出的是,最早指出这一误译的是英国历史学家休·葛宁汉姆,见Hugh Cunningham,“Histories of Childhood,”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3,No.4,Oct.1998,p.1194.不过,葛宁汉姆的意图在于澄清阿利埃斯的本意,本文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此一误解引发的始料未及的学术史后果。同时,英文本将书名从相对含糊也相对中立的《旧制度下的儿童与家庭》改为更加简练明晰 (然而也更为简单化)的《儿童的世纪》,进一步加剧了读者对此的印象。
随着英文本的传播,这一由“误读”而来的论断变得相当著名,被广泛接受。但是,它也引发了不少历史学家的批评——这又进一步推动了学界对中世纪儿童史乃至整个儿童史学科的研究热潮。
《儿童的世纪》引发的批评是多样的。比如,该书几乎涉及儿童与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除了非常明显的精神分析路径外,也可辨识出社会学、结构主义等多样理论的影响。人们面对这种丰富性时感到困惑,无法确定它是史书、社会学著作、人类学著作,还是心理学著作。⑦Adrian Wilson,“The Infancy of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An Appraisal of Ariès,”History and Theory,Vol.XIX,No.1,1980,p.132.不过,比起这种无法定位的困惑,更引起学者诟病的还是“中世纪不存在儿童的概念”这一带有价值观色彩的论断。剑桥大学的阿德里安·威尔森 (Adrian Wilson)就尖刻地评论道,阿利埃斯的论证是“胡说八道”。他指出:历史学家没有在一个社会中看到某种意识,并不等于这个社会就不存在这种意识。⑧Wilson,“The Infancy of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An Appraisal of Ariès,”p.133.这一批评清晰地表明,它所针对的主要就是这一论断背后潜在的价值取向。
面对这一论断,中世纪史家开始寻找证据为中世纪辩护。卢克·德芒泰尔 (Luke Demaitre)指出,心理史家和中世纪史家对“中世纪不存在儿童的概念”的观点“展开了全面的火力进攻”。他本人就研究了中世纪医学作品中的儿童概念以及有关儿童照顾的内容,认为“小儿医学是古代医学的穷亲戚”,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古代医学作品中儿童是被完全忽略的”。①Luke Demaitre,“The Idea of Childhood and Child Care in Medical Writings of the Middle Ages,”History of Childhood Quarterly:The Journal of Psychohistory,Vol.4,No.4,Spring 1977,p.461.
批评者们认为,这一论断和阿利埃斯使用的材料有很大关系。该断言主要建立在图像材料的证据之上。阿氏“遍”检中世纪视觉材料,发现除了圣子、天使形象外,几乎并无实在儿童的出现,这与以后几世纪大量出现的儿童肖像、雕像等形成鲜明对比。他据此断定,中世纪人们“缺乏”对儿童的感知。然而,这一方法很容易陷入泥沼。很简单,任何人都无法穷尽所研究领域的一切材料,只要有一例与之不符的新材料出现,便可轻易推翻这一论断。更何况,阿利埃斯对这些图像资料的阅读过于限于“字面”意义了。他只看到图像平面展示出来的信息,而没有看到图像背后看不见的东西,既忽视了艺术作品在传递过程中所涉及的社会实情的复杂状况,又缺乏对图像深层意涵的分析。此外,阿利埃斯还选用了人口数据、法庭记录等材料,这都被史家奥茨曼 (Steven Ozment)批评为“扭曲的记录”。奥氏本人则通过对家庭档案中的轶事记录、非正式的信函等材料的研究指出,并没有一个可以涵盖整个中世纪欧洲的统一的“儿童”概念。他以此挑战了阿利埃斯著作中明显的结构主义倾向。②Steven Ozment,When Fathers Ruled:Family Life in Reformation Europ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奥茨曼的批评涉及阿利埃斯著作中的另一个问题:有意无意把欧洲视为一个整体。安德鲁·马丁戴尔 (Andrew Martindale)的研究则立足于意大利,他通过对西蒙·马蒂尼 (Simon Matini)作品的分析指出:14世纪前后,儿童图像已经发展得更生动、更人性、更可信了。马丁戴尔主要探寻的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纠正了阿利埃斯将欧洲视为一个整体的倾向。③Andrew Martindale,“The Child in the Picture:A Medieval Perspective,”in Diana Wood,ed.,The Church and Childhood,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4,pp.197-232.另一位学者芭芭拉·汉纳瓦尔特 (Barbara A.Hanawalt)采用很多稀见的一手材料,研究了中世纪伦敦的童年概念与生命周期。她指出,中世纪的人们已经意识到,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生命的不同阶段,这直接反驳了阿利埃斯的论断——中世纪并没有对应青少年的词汇,小孩七岁后就直接“浸”入成年阶段。④Barbara A.Hanawalt,Growing Up in Medieval London:The Experience of Childhood in History,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史家在中世纪领域内倾尽全力进行探索,他们所着眼的并不是作为一个抽象术语存在的“儿童”,而是“童年”概念在中世纪的具象表达。尼古拉斯·奥姆 (Nicholas Orme)重新构筑了阿利埃斯的问题。他将问题设定为:中世纪的儿童与成人是否分享“同一个文化”?他利用考古资料发现,大量铅锡合金的玩具制作于1300年左右;另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当时儿童有自己的游戏、历法习惯及学校书籍。这都有力证明,虽处在同一时空中,但儿童拥有一个与成人世界不同的文化,强力反驳了中世纪“不存在”儿童概念一说。⑤Nicholas Orme,“The Culture of Children in Medieval England,”Past and Present,No.148,August 1995,pp.48 -88.
如果将这一类研究命名为“为中世纪辩护”系列,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极为详尽和冗长的列表——仅翻检1973年创办的《童年史季刊》 (History of Childhood Quarterly:The Journal of Psychohistory)的前几卷,便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辩护”研究到1990年代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一是舒尔玛迷思·沙哈 (Shulamith Shahar)的《中世纪的儿童》,在这本书里,沙哈论证了中世纪不但具有高度的“儿童”概念,实际上在对待童年的态度和与儿童的关系上还很“进步”。⑥Shulamith Shahar,Childhood in the Middle Ag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另一代表作是詹姆斯·舒尔茨 (James A.Schultz)的《中世纪德国的童年知识》,此书并没有覆盖“整个中世纪”,也不包括整个欧洲。舒氏利用中世纪高地德语文献,揭示出中世纪德国不光有“童年”的概念,更重要的是这一概念与启蒙运动以来统治西方的“童年”概念有很大不同。他指出,在中世纪德国,人们根据小孩自身的特点来标识童年,并不将儿童看成未来的成人,因此对待儿童的方式不会影响到他如何“长大”。①James A.Schultz,The Knowledge of Childhood in the German Middle Ages,1100 -1350,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5.这一研究使得人们对童年的认识更具“历史性”,同时打破了对阿利埃斯误译的“迷思”,将问题从“有没有”童年的概念转向人们“怎么看 (童年)”。
显然,1960年代之后历史学界将儿童对象化以及各种与儿童相关的研究的潮流,均以挑战阿利埃斯的观点为主。《儿童的世纪》一书所提示的问题,是此后许多儿童史家寻找证据来反对阿利埃斯的动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建立在阿氏著作英文本的“误译”及人们对此书的“误读”之上。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儿童的世纪》一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提出了中世纪是否“存在”对儿童的爱、是否有“儿童”或“童年”的概念这一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将“史学边界拓展到儿童”。②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0页。
今天,儿童史研究已大大超越了“阿利埃斯典范”。阿吉·缪勒 (Anja Muller)总结道,过去几十年,因为理论和方法论的变化,史家从关注所谓的“儿童本性”,转变为关注“儿童”概念的社会建构过程,之后又开始把儿童放入地方性视野中考察。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依据特殊的历史、社会、文化、经济状况而有不同的“童年”概念。在此意义上,作为今天的学者,我们可以对阿利埃斯更多地抱持一种了解之同情:阿氏展示的是中世纪的“儿童”概念,并不像他的批评者们所预设的那样——中世纪“缺乏”儿童概念。更重要的是,在后结构主义、福柯话语理论、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的冲击下,童年不再是一个静等着“被发现”的、“不受时间影响的分类”,而成为文化的建构,被视为成人社会在医学、法律、教育、文学、艺术话语体系的作用下,为达到不同目的而做的积极表述。③Muller,ed.,Fashioning Childhoo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美国文化理论家波茨曼 (Nell Postman)更是提出,面对当今全球化带来的新的文化危机,人们在重新思考和界定文化认同的同时,应该利用这一理念,对“童年”概念加以再认识。④Nell Postman,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New York:Delacorte Press,1982.中译本见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但无论如何,阿利埃斯的著作“歪打正着”地成为儿童史研究的起点,则不容置疑。
二、近代有一场“情感革命”吗?
《儿童的世纪》引发的第二个激烈批评,围绕着书中所呈现的“现代心态”展开。阿氏提出,17、18世纪,随着现代家庭生活新观念的产生,育儿方式也发生变革。婴儿由过去送往乡村寄养在保姆家,或由乳母喂养长大的方式,转变为母乳喂养,家长则抽出更多时间陪伴孩子,密切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这种种变革加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特别是对孩子的深切关怀,与中世纪家庭生活中对儿童的“漠不关心”形成了鲜明对比,“现代”情感方式与体验由此出现。这就是他所谓的“情感革命”。
对此,有批评家指责阿利埃斯以“现代心态去推论中世纪或近代早期的材料”,把近代之前的亲子关系界定为“残忍”、“淡漠”的,而他所描述的“儿童”概念和亲子关系的改变则呈现直线发展的趋势,“好像有一条笔直的大道直通现代社会”。儿童史家琳达·波洛克 (Linda Pollock)据此把阿利埃斯的研究称为“情感革命”的“现代化典范”,⑤Linda A.Pollock,Forgotten Children:Parent-Child Relations from 1500 to 19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认为它更多地关注现代与传统的“断裂”,而忽视了其连续性。
不过,有关阿利埃斯把传统与现代两分的指摘,激烈却也吊诡。在波洛克之前,最早对阿氏提出批评的人之一、史学大家劳伦·斯通 (Lawrence Stone)就曾提出一个与波氏截然相反的指控——《儿童的世纪》是一部“反现代主义”的著作。⑥Lawrence Stone,“Early Modern Revolutions:An Exchange: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1529 - 1642:A Reply,”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46,No.1,March 1974,p.106.还有一些学者,态度更加鲜明,称阿利埃斯“一向反对改革”、“憎恨现代的一切”,这甚至从阿氏所使用的“标点中”都可以看出:因为“他直率的称呼古代和中世纪,但要给启蒙时代精心地打上标点”。①Lloyd deMause,“Review of Western Attitudes toward Death,” History of Childhood Quarterly:The Journal of Psychohistory,Vol.2,No.2,Fall 1974,p.284.
这一批评实际来自他们对阿利埃斯个人政治态度的认识:1970年代的史家在这场学术论争中,带入了浓厚的个人立场。安德鲁·比尔基埃 (Andre Burguiere)曾对阿利埃斯有过一次访谈,并以“非凡的历史”(Singular History)为标题将其发表,这含义极其明显:阿利埃斯的研究是“超越常规”的史学。他尤其指出了阿氏的历史研究和其政治观点之间的关系。②Patrick H.Hutton,Philippe Ariès and the Politics of French Cultural History,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04,p.1.阿利埃斯本人在政治上非常保守,是一个“保皇党人”。这一点不但对阿氏本人影响巨大,使他长期游离于学术的政治场域之外,只能以“星期天史学家”自居;而且实在地影响了其同时代人对他著作的看法:劳伦·斯通对《儿童的世纪》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根据他对阿利埃斯政治立场的了解做出的。③吊诡的是,当英语世界称赞该书为了解法国历史提供新的视角时,法国国内保守的天主教杂志却刊文辱骂阿利埃斯为“穿着传统外衣”的“丢人的现代主义者”。转引自Fishman,“Changing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A Modest Proposal,”p.69.这和斯通的认知恰好相反,但背后都反映出各自的政治立场。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阿氏本人虽有其政治立场,但批评家们也错误地领会了他的立场。事实上,“保皇”对阿利埃斯来讲,主要代表了一种文化和社会价值而不是政治实践。所他珍爱的与其说是帝制,毋宁说是维系过去社会的各种“道德、观念、习俗”。这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立场 (这个立场也影响了他对近代“情感革命”的认知,详见后文),但评论家显然只是站在单纯的政治立场来理解阿氏对传统和现代的不同态度。④详论参考辛旭:《浪漫还乡:阿利埃斯与〈儿童的世纪〉》,《读书》2013年第8期。
不管批评家们对阿利埃斯的“现代主义”观点是支持还是反对,他们在一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认为阿氏在《儿童的世纪》一书中割裂了历史的延续性。而作为历史学家,他们的反应方式也是相同的:用实证研究反驳阿利埃斯的论点。正是在这一心态的激励下,产生了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研究。
首先是劳伦·斯通。他利用日记、通信、报刊、图像、人口数据、教区记录等各种资料,丰富且全面地研究了1500—1800年间英国的家庭生活,特别关注了儿童这一对象。斯通指出,此一时期英国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家庭成员彼此关系上的表现之一,就是对待儿童的态度以及儿童养育模式的改变。他将儿童养育和亲子关系放入更宽广的“家—国”关系变化脉络中,由此来解释17世纪英国子女养育的情感冷漠及体罚特征。而新的价值体系和世界观也经由家庭关系的改变传递到个人,并传遍全社会,最终成为社会全体的共识,藉由新的制度和习俗固定下来,从而建立了一种新型社会关系。⑤Lawrence Stone,Family,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London:Penguin Books,1979.又,该书有中文版,但同样是一个节译本,见劳伦斯·斯通:《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00—1800》,刁筱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阿利埃斯在处理新型亲子关系和情感问题时,因主要利用上层社会材料如哈罗德 (路易十三的宫廷私人医生)日记而受到批评。论者指出,哈罗德和他日记中的主角路易十三身份都过于特殊,不可据此得出一般结论。而相对阿利埃斯,斯通使用的史料更丰富,对材料的阐释也更立体。他将家庭关系置放于国家和社会变迁的宽广脉络中,并且注意到了阶级区分。不过,另一方面,斯通却强调,近代出现了“情感个人主义”,而这又显然步上了阿氏后尘。⑥事实上,1970年代中期以后,斯通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纠正了自己对阿氏学术的印象,从阿氏的批评者转为学术知己良朋。
劳合·德莫斯 (Lloyd deMause)同样反对阿利亚斯的“反现代主义”立场,而他的研究直接开启了儿童史研究中一条非常重要的路径——心理史研究的方法。
1973年德莫斯在美国创办《童年史季刊》杂志,创刊号与前几卷的副标题为“心理史杂志”。⑦《童年史季刊》后又称《心理史季刊》,一段时间后又改为合称,后又分化。刊名多次改变,也可看出心理史研究路径的许多困境。这一问题,容日后专文探讨。在发刊词中,德莫斯宣称,这份杂志是要呼应佛兰克·曼纽尔 (Frank Manuel)的倡议,推动一个历史研究全新领域的诞生。德氏在文中毫不讳言地指出了阿利埃斯在心理史学方面的“失败”;并转引曼纽尔的批评,指责阿氏作为“自称的精神分析 (心理)史家”,给读者的却是“有关西方家庭在经济和心灵 (精神)关系方面粗糙和有误解的断言”。不过,他话锋一转,又承认正是因为如此,才“开启了更广阔研究的可能”。他呼吁对社会史和精神分析有兴趣的史家,开发新材料,动用新手段,建立一种基于心理史学的童年史,填补知识上的空白。①Lloyd deMause,“The History of Childhood:The Basis for Psychohistory,”History of Childhood Quarterly:The Journal of Psychohistory,Vol.1,No.1,Summer 1973,p.1.
实际上,《儿童的世纪》虽展现了精神分析路径的倾向,但并非精神分析的著作。对阿氏来说,较之“精神分析”,更重要的是“集体心态”(mentalites collectives)的概念。②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第62-63页。他的心态史研究采用了“潜藏的意识”(secret)这一说法,这与弗洛伊德的“自我意识”虽然有对应关系,但阿利埃斯在研究中并未指向这两者的“相似”性。实际上,美国学者赫顿 (Patrick H.Hutton)指出,阿氏早就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产生怀疑,质疑“精神分析理论是否适用于人的早期阶段”。③Hutton,Philippe Ariès and the Politics of French Cultural History,p.87.
不过,自德莫斯之后,大批应用精神分析路径研究儿童的心理史学著作产生,德莫斯本人的研究便是这一取向的卓越代表。此一路径试图通过家庭语境重建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情感、行为和心理。它首先关注的是家庭内部成员的关系,而不是传统家庭史关注的社会经济、政治力量等因素。这类研究尤其受到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将重点放在“童年早期”和“性经历”上,同时也受到皮亚杰儿童心理学有关儿童“发展阶段”概念的影响。④关于儿童“发展阶段”,参考皮亚杰:《发生认识论》,范祖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这一建立在儿童“经验”基础上的研究目标宏大,却受到批评。如斯通就质疑,是否能找到基于儿童自身经验的儿童史材料?史家如何“进入”卧室、浴室、育婴房这些地方?⑤deMause,“The History of Childhood:The Basis for Psychohistory,”p.2.
斯通的批评既别开生面又一针见血。可是,德莫斯在此领域的贡献实不可忽视。对他来讲,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革皆是个性的历史变化,这种变化直接源自儿童的养育方式,反映了亲子关系的改变。他断言:“历史变化的中心力量既非技术因素也非经济因素,而是个性的‘心智性’变化,它是由于亲子关系的代际变化造成的。”他依据这一“心智发生”的假设,对欧洲历史上的儿童进行研究,结论为:“童年的历史就是一场噩梦,人类才刚刚从中苏醒。越是往前追溯,探寻古代的根源,就越能发现儿童被例行公事般遗弃、杀害、暴揍。(他们)在精神和身体上受到虐待,甚至性骚扰。”直到近代,有关童年的一切才发生了“变革”。⑥Lloyd deMause,The History of Childhood,London:Souvenir Press(E & A),1976,p.54.
与劳伦·斯通一样,德莫斯本来是反对阿利埃斯的,但最后的结论—— “童年变革”论却与阿氏殊途同归。不过,德莫斯仍将阿氏视为某种程度上的“反现代主义”者。他说:“阿利埃斯的中心议题与我相反。”因为阿氏“论证”传统社会的“儿童是幸福的”:“他们可以自由地混在不同阶级和年龄的人”中;而“今天人们熟知的‘童年’这个特别的阶段,在近代早期‘被发明’出来”,由此导致了“专横的家庭概念”,而这又进一步“摧毁了友谊的价值和社会流动性,剥夺了儿童的自由,让他们开始遭受桦树条的鞭打和进牢房的痛苦”。⑦Lloyd deMause,“The Evolution of Childhood,”History of Childhood Quarterly:The Journal of Psychohistory,Vol.1,No.4,Spring 1974,p.507.
因此,斯通和德莫斯虽在方法上各有擅场,但他们都把阿利埃斯视为一个“反现代主义”者,且在具体结论上都与阿氏殊途同归,认可了近代“情感”革命的出现。造成这一悖反式现象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他们误解了阿氏对“现代”的态度。事实上,阿氏笔下的“情感革命”并不是斯通和德莫斯理解的那种线性过程,而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面貌:从中世纪开始,欧洲家庭中的亲密情感确实处在“进步”之中,但这“进步”同时又深深根植于久远的传统。往昔和现代的交融在19世纪的“核心家庭”里达到了理想状态。可是,到了20世纪,社会却转而趋于封闭化,人们日益陷入爱的牢狱。这样,19世纪仿佛是情感生活中的黄金时代,20世纪却并不更加进步。①详见辛旭:《浪漫还乡:阿利埃斯与〈儿童的世纪〉》,第136页。阿利埃斯的思路是极为曲折的,但斯通和德莫斯却出于对其“保守”政治立场的不满,“先验”地扭曲了阿氏的意旨。
与他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波洛克,她批评这几人的研究都陷入了“现代性”范式。虽然她并没有否认累世以来亲子关系的变化,但她并不认同“情感革命”这种“断裂式”的论断。波洛克通过对儿童史研究的反思指出,与阿利埃斯论点的搏斗“已经使我们的解释陷入僵局。必须另辟大道进行主题研究,寻找一个新的更全面的取径”。她利用日记、自传、遗嘱等“第一人称”资料,对1500—1900年代的儿童生活场域进行观察,将重点放在“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成人“怎么看”儿童的问题上。她指出,古代到中世纪的儿童世界并不像前期史家断定的那样,充满了黑暗暴力和成人的漠不关心,对他们的处罚也并不是整体状况,而只是亲子关系诸面相之一。父母疼爱小孩自古有之,也一样期待孩子的到来,并关心他们的教育。同时,波洛克坚持认为,阶级、受教育程度、文化、宗教、道德价值等因素对亲子关系并不具影响力。②Pollock,Forgotten Children.
这种路径打破了此前研究的瓶颈,令波洛克跳出情感模式的现代“断裂”理论,建立了对历史“连续性”的关注,取得了突破性成果。与之思路相近的是凯斯·莱特森 (Keith Wrightson)。在有关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的研究中,他专辟一章讨论儿童,驳斥了以斯通为代表的“断裂”论者,指责他们“毫无理由地相信:在17世纪,父母对小孩的态度,经历了重大的变化”,③Keith Wrightson,English Society 1580-1680,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2,p.118.不过陈贞臻论断,波洛克的研究“首先得到”凯斯的“支持”,并没有坚强的证据;要厘清两者学术观点的关联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参见陈贞臻:《西方儿童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阿利埃斯及其批评者》,第183页。与波洛克有关历史延续性的论点形成桴鼓相应之势。
不过,虽说波洛克的研究被认为建立了儿童史研究中的新典范,④参见陈贞臻:《西方儿童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阿利埃斯及其批评者》,第182页。但她的预设针对的仍是阿氏有关中世纪父母对孩子“漠视”的看法。在这个意义上,波洛克本人依然陷在与阿利埃斯论点搏斗的“僵局”中,而没有完全达到“另辟大道”的目的。同样重要的是,波洛克对阿氏观点的修正也仍建立在对阿氏观点的误解之上。赫顿已经指出,阿利埃斯所谓中世纪父母对儿童的“漠视”是一种“良性漠视”,它深植于一种无法追忆的社会态度中——在那样的心态里,同样充满了对年轻人未来的期望,现代家庭与之不同的只是对孩童的期望更为多样化。⑤Hutton,Philippe Ariès and the Politics of French Cultural History,p.93.
这个解读是睿智的。“良性漠视”一词,不但回应了众多学者对阿氏的误解,也将亲子关系真正置放于历史的日常情境之中,为阿利埃斯的论点提供了一种更为贴切的诠释途径。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何阿氏饱受批评,却仍在1973年《儿童的世纪》重印本中“坚持认为”,传统社会“看不到儿童”,甚至“看不到青少年”;并重申“首先从过去的世界里找出差异”,然后才能“发现与我们世界的相同之处”。⑥菲利普·阿利埃斯:《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与家庭生活》,第6页。对于中世纪的亲子关系,阿利埃斯并不满意,但仍持一种“了解之同情”的态度。他的思路复杂,绝不像早期批评者所设想的那样简单。
对阿利埃斯意旨的诠释,恐怕还会不断进行下去。不过,对本文来说,更重要的是,无论阿氏本人怎么坚持传统与现代的“不同”,不可否认,他个人的“保守”立场和书中“现代主义”观点之间呈现的紧张感,导致了不少史家对其观点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误读,而这又进一步催发了更多的实证研究,使儿童史成为今日一个欣欣向荣的领域。
三、家庭史还是儿童史?
在《儿童的世纪》出版之前,阿利埃斯已经出版了好几部历史学著作,但都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他一直是法国史学体制的“槛外人”。《儿童的世纪》一书不但为他赢得了学界对其学者身份的认可,还使之一举成为“儿童史”的奠基人。西摩·白曼 (Seymour Byman)甚至提出,该书是“童年史圣经”。①Seymour Byman,“Lawrence Stone,The Family,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1500 - 1800,”History of Childhood Quarterly:The Journal of Psychohistory,Vol.5,No.3,Winter 1978,p.579.
不过,阿利埃斯本人却从未认为自己写的是一本“儿童史”。他在该书前言中开宗明义,告诉读者这是一本关于“家庭”的著作,是一位“人口学家”有感于“当代”家庭的一些特质而引发的思考和研究。②Ariès,Centuries of Childhood,p.7.回顾1950年代以来的欧美史学潮流,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史家更关注社会分层与阶级分析,很少关注家庭这一私人领域;而阿氏正是率先将目光从“公领域”投向“私领域”的学者之一。③阿利埃斯和乔治·杜比 (George Duby)主编的5卷本《私人生活史》,是迄今为止这一领域的扛鼎之作。他在此书中感兴趣的乃是往昔的家庭形态,“童年”只是他家庭史研究中处理的一个问题。但正是由于“私领域”这一研究空间的开启,使阿氏关注到了过去常被“隐蔽”起来的儿童——这是他成为“儿童史”开创者的重要原因。过去不少研究儿童的著作仅是经验性地把儿童当做研究对象,所缺乏的正是《儿童的世纪》具有的更为深刻和自觉的学术眼光。
阿利埃斯的这一初衷不乏解人。以劳伦·斯通为代表的许多史家都肯定了《儿童的世纪》对于推动西方家庭史研究的作用和影响,认为此书首先是家庭史领域的一本典范之作。④Lawrence Stone,The Past and the Present,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7,p.222.奥茨曼研究家庭史四十年,取得了众多奠基性成果。他坦率地指出,阿氏的研究直接鼓舞了他的家庭史写作,因为阿氏 (和斯通)使他对“家庭这一论题产生了内在的兴趣,而这一点,无论是以前,还是后来,极少有史家能够做得到”。⑤俞金尧:《西方家庭史学的新发展——与家庭史学家奥茨曼教授访谈》,《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德莫斯虽未如此明确褒扬阿氏,但他批评过去的史家“只关心奇幻的城堡、宏大的战事,而忽略了这一切的基石——家庭”;又说,在历史研究中,“私”的“单元”和“公”的“单元”同等重要。从学术史角度看,这无异于向阿氏致敬。⑥deMause,“The Evolution of Childhood,”p.506.
众多批评也把《儿童的世纪》放置于“家庭史”领域中。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芭芭拉·汉纳瓦尔特批评阿利埃斯想当然地认为中世纪家户既包括了扩大家庭也包含了局外人,他们竟然居于同一屋檐下。跟其他诸多家庭史家一样,她也指出,并没有一个整个欧洲范围内统一的家户模式,英、法、低地国家都有非常复杂的家户结构。⑦B.Hanawalt,“Childrearing among the Lower Classes of Late Medieval England,”in R.E.Rotberg and T.K.Rabb,eds.,Marriage and Fertilit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这一批评不但表明了阿氏作品被视为家庭史领域的成果,也揭示了他不同于惯常的研究路径。与汉纳瓦尔特等的批评态度不同,安德森 (M.Anderson)对阿利埃斯更具一份“了解之同情”。他把阿氏的研究取向称为“情感史”模式,还把斯通、奥茨曼、肖特 (Edward Shorter)、波洛克等人与阿氏并置,名之为“情感学派”。安德森指出,他们的共同研究特征是探寻态度、意义、情绪、观念的历史性变化,通过“情感”的视角观察家庭的历史。⑧M.Anderson,Approaches to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Family 1500 - 1914,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1980,p.39.
“情感派”家庭史家在很多方面继承并发挥了阿利埃斯的思路。劳伦·斯通在其经典作品《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00—1800》中指出,现代家庭的关键特征是家庭核心成员情感联系增强,邻居和亲属的重要性趋淡;个人的自主意识和拥有追求幸福的自由权利的意识增强;性欢乐与罪愆之间的联系渐趋弱化;身体的隐私权增强。他还特别揭示了童年的概念变化与家庭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彼得·拉兹莱特 (Peter Laslett)1965年出版的《我们消失的世界》,用教区记录、人口数据等材料研究往昔家庭结构,力图以经验研究取代价值判断。谈到情感关系时,他写道:“20世纪人们试图思索婚姻关系破裂对儿童情绪的影响,但再往前追溯则可能是不明智的。”在“前工业社会时代”,人们对于“猝死、孤寡、与继父母生活的态度完全不同”于今日;他们“习惯了丧亲和生命的短暂”,“显然必须如此”行事。①Peter Laslett,The World We Have Lost,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65,pp.69 -96.这些看似不具价值判断的表述,却在事实上支持了其他“情感派”的研究。爱德华·肖特认为现代家庭是“被制造”出来的。在其中,新的有关儿童“本性”的观念将儿童置于一个代表着未来的位置,但另一方面,它也表现了儿童身体和理性上的不成熟。而当人们意识到儿童“本性”的观念时,便意味着成人开始了对儿童的关注。②Edward Shorter,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Family,New York:Basic Books,Inc.,1975,p.xiv;又见 Muller,ed.,Tashioning Childhoo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p.2.
从他们的研究预设和学术关切来看,这几位史家都是在家庭结构内部将儿童对象化。因此,如同阿利埃斯一样,他们的作品既被当做“家庭史”著作,同时也被视为“儿童史”的研究典范;而他们本人,也既被当作家庭史家,又被看成儿童史家。
再来看前面提到的德莫斯心理史流派的情况。与对“情感史”模式的看法不同,安德森对心理史则持直率的批评态度。他不屑地说,“那种称自己为做心理史的”人,“甚至”还有“自己的杂志”!但其研究方法“在家庭史领域似乎已经证明不能解决问题”。因此,他本人并“不认为这一研究有值得关注的地方”。③Anderson,Approaches to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Family 1500-1914,p.15.抛开偏见不提,显然,安德森把德莫斯一派的心理史也放置于家庭史研究领域内。但在德莫斯本人的认知里,自己首先乃是一位应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儿童史家。
这一情形提示出“家庭史”和“儿童史”之间亲密而又暧昧的关系。从阿利埃斯开始,“儿童史”研究显然就是“家庭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史家对儿童的研究和关注都是在家庭结构内部展开的。这当然是由于“儿童”的特定社会角色决定的:在正常情形下,家庭是儿童最重要的生活空间,对儿童的态度也首先在家庭生活中体现出来。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帕特里克·邓恩 (Patrick Dunn)的一段评述。他将这两个概念并置,说:“童年史和家庭史是崭新而又困难重重的领域。”④Patrick Dunn,“Modernization and the Family,”History of Childhood Quarterly:The Journal of Psychohistory,Vol.4,No.2,Fall 1976,p.207.
另一方面,“童年史”和“家庭史”的并置,也暗示在邓恩的心中,二者是存在差异的;他把“童年史”放在“家庭史”前边,更表明他心香一瓣之所向。实际上,仅从人们对阿利埃斯的评论中就可看出这一新趋势的迹象:尽管阿氏本人把《儿童的世纪》定位为一部“家庭史”著作,而根本没有提到“儿童史”这个概念,但今天他却被视作“儿童史”的创始人。从理解阿利埃斯本人学术思想的角度看,这当然多少是个误会;可是这也意味着,在很多学者看来,“儿童史”应从“家庭史”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学科。
早在1972年,也就是《儿童的世纪》英译本出版十年后,约翰·萨默尔特 (John Summerville)就已经指出:“尽管‘专业’的史家长久以来忽视儿童的历史,以及童年的文化建构,但过去几年来出版物的数字已经明显地点明人们在这一领域汹涌而来的兴趣。”⑤John Summerville,“Bibliographic Note:Toward a History of Childhood and Youth,”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3,No.2,Autumn 1972,p.439.从萨氏注意到的这个时间段看,这种现象是和《儿童的世纪》引发的广泛争议分不开的。
不过,最先呼吁把“童年”视作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人还是德莫斯。1973年,他倡导发起了《童年史季刊》并在创刊词中提出:“童年的历史是这本杂志力图呈现的新取径。”他还明确表示,期望“我们的研究”能迅速地从“新近生发”的“家庭史”领域区分出来。这是学界首次提出专注于“童年”与“儿童”的研究取向。他们所关切的是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为成人的“群体幻想”所“扭曲”的个体经验,这是一个被过去史家忽略的重要议题。《童年史季刊》应用心理学理论研究儿童和童年的历史,推动了人们对历史上的杀婴、儿童对待、养育模式和亲子关系问题的理解。德莫斯本人还将精神分析理论生发为儿童史研究中的“心智生成理论”。应该说这个方法和刊物在儿童史学科独立方面居功至伟。
当然,儿童史的学科独立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直到1983年,波洛克还在质疑:研究儿童史有可能吗?①Pollock,Forgotten Children,p.viii.但到了2001年,希伍德 (Colin Heywood)讨论的已经是:儿童史应该坚持不同主题的研究。②Heywood,A History of Childhood,p.2.从对研究“对象”合理性的质疑,到对如何“提问”的关注,都意味着,一个独立的“儿童史”学科已经形成。
四、结 论
阿利埃斯既是“儿童的历史”议题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又是诸多儿童史研究者的“对手方”。几乎所有自觉的儿童史家都是在与阿氏的思想“搏斗”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对阿氏的批评涵盖了从史料到方法再到论点的所有阵地。在这个意义上,阿利埃斯从正、反两个方面形塑了儿童史的面貌。
同时,许多对阿利埃斯的批评其实都建立在对其著作和政治立场的误解之上,尤其是早期(1960年代开始至1980年代上半期)的批评家,对阿氏的误会更多。这些误解主要体现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中世纪是否存在“童年”或“儿童”的概念?如果存在的话,“它”是什么?有关“童年”的概念是唯一的吗?第二,近代是否发生了一场“情感革命”?亲子关系的变化究竟呈现出更多的“断裂性”还是“延续性”?阿利埃斯对家庭情感关系的“现代性”到底持什么态度?第三,阿利埃斯的研究隶属家庭史还是儿童史?这两个领域的关系如何?不管这些问题是否合乎阿利埃斯的本意,有关争论都大大推动了儿童史的研究与这一学科的成长。
从《儿童的世纪》出版至今,半个世纪以来的儿童史研究已经与最初的“搏斗”式研究面貌大为不同,儿童史家在这一领域所展现出来的成熟的理论观点、多样的研究方法和强烈的问题意识,已经远远超出了“阿利埃斯典范”。但是,阿利埃斯以及他的学术对手们对这一学科的奠基作用仍是不可抹煞的。在这个意义上,“误解”成为了一种积极的学术建设力量,产生了最初投身于这场辩论的人们始料未及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