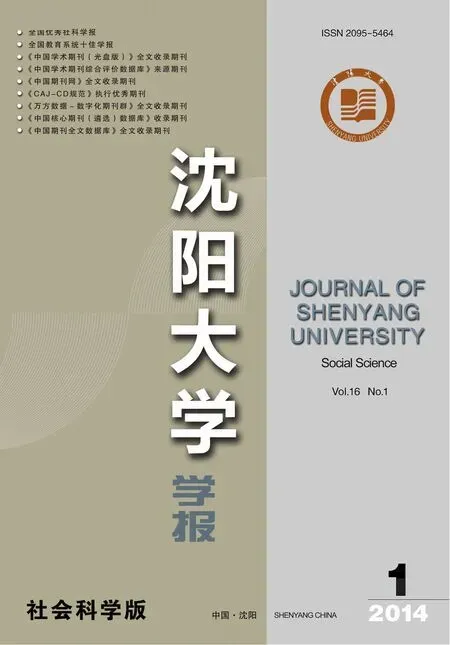《秀拉》的生死母题
徐 颖(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天津 300204)
《秀拉》的生死母题
徐 颖
(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天津 300204)
研究了托尼·莫里森的《秀拉》,分析了作品映射出的生死母题。从与生死母题紧密相关的三个方面通过仪式、再生和替罪羊原型出发来解读《秀拉》的主题和人物性格发展。
《秀拉》;生死母题;通过仪式;再生;替罪羊
托尼·莫里森的小说《秀拉》,以黑人秀拉的成长为主线,描摹了美国黑人社区“底层”的生活图景。故事设置在一战后至美国民权运动兴起之时,塑造了一位敢于挑战社会习俗的黑人女性形象。托尼·莫里森作为一名杰出的非裔美国作家,深受基督教文化和非洲民间神话传说的双重浸濡。她在这部小说里嵌入了丰富的神话原型要素,学者杜志卿已从情节出发研究过《秀拉》中的死亡主题[1]。本文将从原型分析的角度,聚焦小说中的生死母题。
莫里森对生死这一文学母题颇为关注(其硕士毕业论文即研究福克纳和沃尔夫作品中的自杀主题)。《秀拉》的各章故事情节,是以“生死”为主线串联起来的:“底层”社区面临被拆毁的命运、退伍军人夏德拉克创立“全国自杀节”、奈尔去参加曾外婆的葬礼、秀拉的外婆夏娃烧死儿子、秀拉失手将黑人小孩甩入水中溺死、秀拉母亲汉娜自焚身亡、秀拉出走和其梦想的破灭、归来的秀拉遭到“底层”黑人的排斥、秀拉去世、黑人群众在隧道塌方事故中丧生、奈尔在墓地缅怀秀拉。生与死是表现人类生存状态的两个极限,而生死母题是几乎所有生命仪式中表现永恒的重要形式。莫里森通过这一母题对人物命运进行了独具匠心的设计,揭示出黑人的成长和抗争主题。
一、生死母题之通过仪式
人类生命由于自然时序而呈现出生命仪式特征。人类学家凡·艮耐普(Van Gennep)将“社会中的个人生活”视作“随着年龄增长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通过仪式”[2]。这需要“一个特定社会仪式的分水岭,将一个年龄同另一个年龄以特殊的方式分隔开”[3]38。《秀拉》中就出现多个通过仪式。退伍军人夏德拉克在战争中几近失常,一双“疯长的怪手”令其痛苦不堪。莫里森描写了他重建自我身份的“通过仪式”在马桶的水中,他看到自己的黑人面孔,“当那张黑脸以其不容争辩的存在向他致意时,他再无他求了……疯长的手恢复了平静,他睡了新生命开始后的第一觉”[4]13。夏德拉克通过这一顿悟形式清除了被战争摧毁的身份碎片,自我疗救了对战争的恐惧,有了新生后的大彻大悟。他通过建立“全国自杀节”来帮助“底层”黑人直面死亡。在这个自创节日里,他独自在街头游行,“手里拿着一只母牛的颈铃……两眼大睁着,长发纠结在一起,吼叫声中充满不容置疑和震撼人心的劲头”[4]14。他以一种希腊神祇的威严来怒视死亡。黑人对死亡的恐惧是对种族迫害恐惧的转嫁,夏德拉克以夸张的行为将这一内在恐惧外显出来。“自杀”是黑人表现被压抑的主体意识的极端形式,是重建自我身份的重要“通过仪式”。夏德拉克正是用荒诞的行为来嘲讽和抗争种族现实。
夏德拉克在人们眼里疯疯癫癫,但其先知精神在后面情节闪现。秀拉失手将小男孩甩到河中后,走进夏德拉克小屋第一次与他交流。他们惊讶地发现彼此存在的契合。他对秀拉只说了一个词:“总是”,他刚说出这个词来,“她(秀拉)的面孔就容光焕发,痛苦感随之消失了”[4]147。“这其中的允诺始终追随着她的脚步”[4]59,支撑着她的一生,成为其抗争的精神指引。
黑人男孩“小鸡”的意外死亡,是秀拉和奈尔的成年“通过仪式”。秀拉听到母亲对自己的贬抑后渴望确证自我价值。书中描写的仪式体现了秀拉女性意识的最初觉醒。她和奈尔在河边草地上找来两根树枝,剥光皮(这一行动暗示了非洲男性的成年仪式);在地上挖出两个洞,将嫩枝、烟头、瓶盖和纸片等扔入洞中。这是对男性传统性别角色的挑战和象征式嘲讽。她们又仔细地培上挖出的土,还用拔出来的草盖满小小的坟头。这一行为俨然变形的宗教祭祀仪式,尤其发生在“小鸡”溺死之前,有死亡的预兆。在“仪式”之后,她俩沉默地向湍急阴郁的湖水中望去,“心头涌起难言的激动与不安”[4]55。这种复杂行为和心情恰恰衬托了人们在成年“通过仪式”中的不安和恐惧。秀拉拽住“小鸡”的手,抡起来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被甩到湍急的河面,阵阵笑声也随之在水面之下消失。在“小鸡”的葬礼上,秀拉无声地哭泣,她天真的少女时代在这次事故中终结了。
秀拉母亲汉娜死前也有类似的仪式:汉娜死前做了一个身着红色嫁衣的梦,预示她即将走向人生的“通过仪式”(结婚实际上是少女生活的终结),之后是奇怪的风起,夏娃在窗口看到火中焚烧的女儿。“小鸡”的死是被水吞噬的悲剧,汉娜的死是被火席卷的意外,两个仪式都有秀拉的旁观,对于前者她无能为力,而对于后者,她冷眼旁观。经过第一个仪式,秀拉正从少女阶段走出;到第二个仪式时,秀拉正进入成人阶段,对于死亡的“总是”有了很深的理解。
二、生死母题之再生
人的生命同自然生长的对应关系赋予了其再生意义,这使黑人在现实所承受的苦难化为艺术的美感。绚丽的死亡帮无助的生命摆脱前尘纷扰,使新生命得以成长。《秀拉》中的几次死亡,都与水密切相关,有接受洗礼、走向永生之意。秀拉外婆夏娃杀死亲生儿子“李子”。她的名字寓意博大母爱,而她本人也表现出无私的爱:当丈夫弃家而去时,她勇敢挑起生活的重担,不惜被轧断一条腿来获得救济;她不仅艰难地抚育亲子,还收养了几个弃儿。但她也像上帝一样主宰人的生死命运,住在顶楼的她“上帝”般俯瞰家中发生的一切,连男人们也要“仰望着她”[4]30。当看到爱子“李子”从战场归来、沉溺毒品逃避现实的样子,夏娃备感痛心,她用一把火结束了儿子的生命。“李子”的死被描述成了“火凤凰”式的涅磐仪式:“那湿湿的亮光卷成一团把他包围了起来,溅到他的皮肤上并且钻进了里面。他睁开眼睛,看到他刚才所想象的原来是一只鹰的巨大翅膀向他周身喷着湿湿的亮光。他想,大概是一种洗礼、一种祝福吧,那意思是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4]44。“李子”代表了被战争毁掉的黑人青年,他们曾经朝气蓬勃,而如今却只能苟活于世间,生活在已如地狱般的黑人生活最底层。烈火给了他解脱和洗礼。
“小鸡”的意外溺死也有再生的意味。他最终被掩埋,“鲜花从棺材顶部散落下来,在坟墓四周形成一个小堆”[4]61,这一情景与之前的埋坑仪式惊人相似。秀拉曾在“小鸡”死前帮他爬到树顶,使他看到从未看到过的风景。河水并不因吞噬了“小鸡”的生命而动容,一个黑人生命的失去更是遭到漠视。“小鸡”的棺木埋进地里,“那阵阵笑声和掌心中手指用力攥着的感觉将会永远停留在地面上”[4]62。黑人小孩弱小的生命消亡,然而却停留在最欢乐和灿烂的刹那。水的怀抱迎接他摆脱了生的苦难。
秀拉不到三十岁就病死了。她临死前出现幻觉,梦到自己“把双腿抬到胸部,闭上两眼,把拇指放进嘴里……她蜷起身子进到那沉重而柔软的水中,让水将她缠裹起来,负载着她”[4]139。这种幻想的姿势,仿佛婴儿在母亲子宫中的样子,这也是象征性的再生仪式。秀拉在弥留之际幻想返回子宫,正是她渴望归属感和安全感的体现。但同时,秀拉又是卓尔不群的,充满了青春和梦想。同龄的黑人女性,早已在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重压下变得伤痕累累,“把自己封闭在刻板的棺木中”[4]115。而秀拉年轻的眼睛永远是清澈明亮的,“她唱过了所有的歌”[4]128。死亡使秀拉的青春定格在永恒的一刻。
夏德拉克的身上也体现了再生精神。他总会出现幻觉:“手指像杰克的豆梗般地蔓延开去,杂乱无章地布满在小推车和病床上”[4]9。这藤蔓恰是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的象征。独居于河边的夏德拉克,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充满了酒神般的异质特征。他的“全国自杀节”哲学也映射了“再生之神”酒神的思想。夏德拉克的游戏在秀拉死后发展成为全社区规模的集体游行,俨然一种酒神式的狂欢仪式。“所有的人……全都处在这欢快的气氛中,笑啊,唱啊,彼此呼叫着,在夏德拉克背后形成了一对形形色色的流浪艺人般的队伍……在阳光下嬉戏”[4]149。他们在闪烁的阳光下高视阔步、蹦蹦跳跳地步入白人社区,来到未完工的隧道前面。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大家一齐动手,把这个白人不准他们黑人修建的隧道拆毁。由于走得太深,最终隧道坍塌,把他们全都掩埋在下面。“底层”黑人们尽管在秀拉死前排斥她,却不由自主受到了其反抗精神的感染。秀拉在世的时候,是种族制度最猖獗的时候;秀拉死后的“全国自杀节”,社区黑人全都不由自主地加入游行队伍,“撕开那道帷幕,让他们在焦虑中、在尊严中、在庄重中、在他们多年来不断增加的那一成年人痛苦的重压中喘一口气”[4]149。他们在死前宣泄了黑人民族的激愤,得到了精神上的重生。
三、生死母题之替罪羊原型
“替罪羊”的形象最早出现在《圣经》旧约亚伯拉罕献子的故事中。弗雷泽爵士(James Frazer)在《金枝》(The Golden Bough)中对“国王替罪羊”仪式的受难主题进行了探讨[5]。这个仪式发展至今,常常使一些少数族裔、弱者或恶者成为“替罪羊”,于是黑人、犹太人、老人、妇女、儿童或为世人所不容的人,背负着成年白人男性的罪责而受到替代性的惩罚,替他们赎罪。
秀拉作为一名黑人女性,敢于挑战世俗对黑人女性的不公要求,她的身上呈现出很多叛逆到为社区人所摒弃的恶行。人们叫她“螳螂”[4]106,认为她眼睛上方的玫瑰形胎记为不祥之物,将她视作女巫和一切灾难的源泉:知更鸟成灾、黑人摔跤、让鸡骨头卡住喉咙或是眼上长针眼全都归咎到她身上。“秀拉的邪恶已经确证无疑”[4]111,理所应当地被当做“底层”的替罪羊。
“替罪羊”是在“生与死之间强行加入的一个生命的转换形态对神谕的曲折抗拒”[3]306。“替罪羊”作为人的替代品缓和了人意识深层的暴力倾向,秀拉的存在则缓和了“底层”黑人的暴力倾向。黑人尤其是黑人男性,长期在种族压迫下处于“被阉割”的状态。他们将居住的贫瘠山顶自嘲为富饶的“底层”“一个拿黑鬼开心的玩笑”[4]5,他们无力抗争,后来只能让出家园供白人修球场;“底层”要修柏油路和隧道的时候,白人宁愿挑走瘦弱的白人,也不给成年黑人机会。黑人男性无力诉求,只能将心中压抑的痛苦用暴力形式投射到比他们更弱小的女性身上。秀拉拒绝成为家庭中的受害者,她随便和男人上床,轻蔑和她上床的男性,成为社区所有黑人的“替罪羊”。黑人们将绝望全都投射到秀拉身上,认定其死亡献祭可以使他们挣脱危机。但讽刺的是,秀拉的献祭非但没给“底层”黑人带来好运,却给他们带来了一系列的灾难,当年由于秀拉的嘲讽而被“底层”黑人找回的美德也丧失殆尽。“秀拉”式的抗争过程充满了生-死-再生的意味,而奈尔作为秀拉最亲密的伙伴见证了这些仪式,也反衬了秀拉的性格特征。奈尔很早(在和母亲去奔丧的火车上)便获得了自我意识,她的少女时代也受到了秀拉反抗意识的感染;她感到独立自我在结婚和秀拉离家后开始死亡,直到秀拉复返后才又“像去掉白内障之后,能用眼睛看东西了”[4]89。奈尔最后去参加秀拉的葬礼时忽然意识到自己长期以来牵挂的人是秀拉。小说以奈尔的大声痛哭而结束。秀拉的反抗个性在一系列生生死死中丰满起来,虽然这位女勇士英年早逝,但她的精神却融入小说结尾处所指明的黑人民权运动的高潮。秀拉·梅·匹斯(Sula May Peace)虽死,她可以安息了(应和了她全名的英文含义)。
[1]杜志卿.《秀拉》的死亡主题[J].外国文学评论,2003(3): 34 43.
[2]Gennep V.The Rites of Passage[M].London:Routledge,1965:3.
[3]彭兆荣.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Morrison T.Sula[M].London:Chatto&Windus,1973. [5]Frazer G J.The Golden Bough: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M].New York:Macmillan,1922:243 245.
【责任编辑 李美丽】
Life and Death Motif in Sula
Xu Ying
(School of English,Tianjin Foreign Language University,Tianjin 300204,China)
Toni Morrison’s work,Sula,is studied,and the motif of life and death in this fiction is analyzed.The theme and character development of Sula are interprete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motif of life and death:the rites of passage,resurrection and scapegoat.
Sula;motif of life and death;rite of passage;resurrection;scapegoat
I 106.4
A
2095-5464(2014)01-0118-03
2013 06 14
徐 颖(1977),女,天津人,天津外国语大学讲师,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