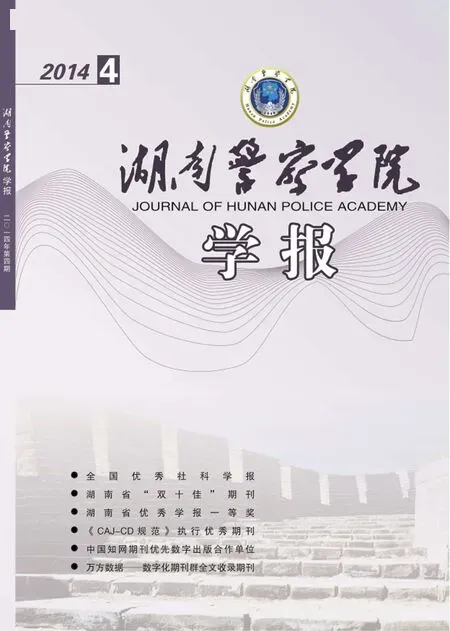探讨我国群体性治安事件的预防与处置
李岚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安徽合肥 230031)
探讨我国群体性治安事件的预防与处置
李岚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安徽合肥 230031)
当前,我国处于群体性治安事件的高发期,如何正确的预防和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应当准确定位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含义和性质,理性分析目前群体性治安事件的表现形式和社会影响,坚持以预防为主,完善预警机制,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相关部门协同作战,快速控制,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重要力量,应当准确定位自己的角色,当好党委和政府的参谋,积极预防和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
群体性治安事件;预防为主;公安机关;依法处置
一、准确的定位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含义与类型
(一)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含义
群体性治安事件,作为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突出问题,产生根源和表现形式复杂多样,因此理论界关于这一概念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政治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其称谓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例如曾被称为“群众闹事”、“群众性治安事件”、“治安突发事件”等等。这些称谓都揭示了群体性治安事件某个方面的特征。直到2000年4月5日,公安部颁发《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中明确提出“群体性治安事件”这一概念,并指出群体性治安事件是“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并对群体性治安事件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分类。这一称谓,突出了群体性治安事件的违法性和对社会秩序及公共安全的危害性。其分类所揭示的主要是触犯法律,构成犯罪的行为,过于强调其闹事的性质。
随着社会的发展,目前我国出现的一部分群体性治安事件往往带有正当利益诉求的性质,事件的参与者是为了维护自己正当利益而被迫采取集体行动,而且参与者所采取的方式也越来越新颖,例如2008年12月,广州出租车司机因为不满出租车营运环境的“集体喝茶”事件;2010年广州东莞市樟木头镇居民因为不满垃圾焚烧厂选址“集体散步”事件。因此,只强调群体性治安事件的违法性和闹事性未免带有片面性。
对于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含义,理论界虽然没有形成通说,不同的人对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定义的理解和研究方法有别。但是无论给群体性治安事件何种定义,构成群体性治安事件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群体性治安事件主要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从人数上说是由多人构成的一种群体行为或者集体行为;群体性治安事件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群体性治安事件总是伴随着具有一定程度的对抗性或者非法甚至犯罪的行为,并对社会秩序造成影响。
从群体性治安事件的类型、发生原因和采取手段角度出发,本文作者比较赞同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有关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定义①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指出群体性治安事件是“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有部分公众参与并形成有一定组织和目的的集体上访、集会、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聚众闹事等群体行为,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造成一定影响”。。因为其指出了“群体性治安事件”发生原因是“主要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在采取手段上包括“一定规模与组织的集体上访、非法集会、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聚众闹事等群体行为”;“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造成影响”的行为[1]。
(二)当前群体性治安事件的主要类型
我国面临社会转型期,经济发展的机遇期与社会矛盾凸显期并存,社会利益结构失衡,民众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以及公共预警机制的滞后等原因导致各种群体性治安事件的数量加速上升,规模日趋扩大,方式渐趋激烈,对抗性明显增强。我们可以从近几年来发生的典型群体性治安事件中总结三种主要类型。
1.利益诉求型群体治安事件
这类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利益受损的主体缺少利益表达的正当渠道或者地方政府没有足够重视利益主体的诉求,比如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抗议事件等等。这类事件的参与主体不以挑战现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为主要目的,具有较强的可协调性,只要我们理性面对这种冲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受损利益主体的正当诉求,往往就能迅速平息事件。比较典型的是2008年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2009年甘肃陇南事件②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是由于油价上涨、黑车、不合理的出租车管理体制等因素造成的;陇南事件是由于征地补偿问题引发的。。
2.泄愤型群体治安事件
这类事件的导火索多是突发的,偶然的事件,例如2004年重庆的万州事件,引发的原因只是街面的偶发纠纷,2006年安徽的池州事件的引发原因是发生在菜市场门口的一起小的交通事故,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的引发原因只是社会个体的自杀事件。这类事件的主要的参与者和突发事件中的当事人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往往是借题发挥,宣泄其对社会的不满情绪,非理性宣泄的冲动表现的非常明显,甚至采取暴力手段,比如冲击政府大楼,砸烧警车等等。表面上看,泄愤型群体治安事件最难预防和控制,但是突发性的事件演化为泄愤型群体治安事件背后都有一般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其发生数量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与当地社会治安环境的不稳定有密切联系。例如2008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就指出瓮安事件背后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主要是一些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和妥善解决,治安环境不好,干群关系紧张,工作方法有问题,群众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2]。
3.骚乱型群体治安事件
此类事件性质最为恶劣,对于社会治安的危害性最大。事件的对象可以迅速扩展到非利益相关者。事件的发生过程中伴随着严重的犯罪行为。例如2012年9月15日以来,全国反日游行中一些城市出现的打砸抢烧等暴力行为。这类事件是最为严重的群体性治安事件,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一旦被敌对分子或者不法势力所利用,甚至可能发生更大规模的社会动乱。
现实生活中,群体性治安事件表现形式往往是复杂,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事件往往交织在同一起群体性治安事件之中。利益诉求中夹杂着泄愤,在泄愤同时也存在着维权。当社会条件变化,尤其是政府处置措施出现问题的时候,利益诉求型的事件很快转变为社会泄愤事件,社会泄愤事件也可以将祸水从相关部门引向无辜的公众和社会,甚至发展成为成为骚乱事件。
二、深入分析群体性治安事件的性质和社会影响
(一)群体性治安事件的性质
群体性治安事件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世界各国采取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对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属性进行了分析。比较典型的学说主要有社会冲突理论和政治参与理论①社会冲突理论认为,社会冲突在任何形式的社会形态下都是无法根除的,它总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群体性治安事件正是社会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政治参与理论认为群体性治安事件是民主法治国家平民通过非制度参与手段影响政府决策的一种活动。。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广大人民所坚决拥护与支持,因此我国群体性治安事件基本目的是为了寻求涉众性矛盾的解决,从其政治性质上看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具有政治上的反动性,对国家政权没有直接的危害性。但是很多群体性治安事件体现出来的人民内部矛盾,在表现形式上比较激烈,一旦被敌对分子和敌对势力所利用,甚至可能会导致其性质的转变。因此对群体性治安事件,我们既不能畏首畏尾,惊慌失措,过度政治化解读群体性治安事件,也不能借口社会转型、体制问题或历史遗留问题来推脱责任,虽然我们无法杜绝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发生,但是可以在认识和把握群体性治安事件性质的基础上,通过积极预防措施,有效疏导改革和发展中的各种社会矛盾,尽量减少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发生和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从法律角度上看,依据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必须将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处置纳入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轨道,用法治的思维和法律的手段来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对于具体的群体性治安事件,必须严格分清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界限,采取各项措施,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如果离开法律规定采取行动和措施,处置工作就会陷入被动,留下无穷的后患,且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政府的信誉度。
(二)群体性治安事件的社会影响
群体性治安事件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和负面影响是主要的。发生群体性治安事件,必会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事件的参与主体认为只有把事情闹大,才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因此他们会精心策划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等等。例如他们往往选择在交通要道,人群比较集中的公共场所,要害部门和单位等地方,一旦群众围观或参与就会导致社会出现混乱局面;尤其是带有泄愤性质的群体性治安事件,参与者往往会采取打砸抢烧等极端暴力方式,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2008年贵州的瓮安事件就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1600万元②新华网:《瓮安事件是近几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标本性事件”》,(2008-09-08)[2013-12-01]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09/ 08/content_9847136.htm。。
群体性治安事件还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从近几年来发生的大量群体性事件来看,相当一部分参与主体的矛头直接指向党和政府机关,或堵门或堵路,或打横幅或喊口号,甚至出现暴力打砸抢和暴力袭警等等。这些现象必然会严重损害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权威和形象。同时群体性治安事件一旦爆发,也考验着地方党委和政府对社会大局的掌控能力以及对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的处置能力,如果处置不当,必然会使群众对党委和政府产生不满情绪,不利于党委和政府工作的开展。
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群体性治安事件对社会发展具有安全阀功能和社会报警功能。社会弱势群体不满情绪的积累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信号,群体性治安事件的爆发往往使心理失衡的公民宣泄了自己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心理平衡,也避免了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对此社会冲突理论的学者形象的说,社会冲突好像锅炉的安全阀,通过它把积聚的蒸气排放掉,不会损坏锅炉。
此外,一些群体性治安事件所反映出来的相关问题往往能引起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主动审视和改进工作方法和态度,从而对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对社会改革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加强和改进预防和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对策
近几年来,群体性治安事件已经成为影响治安稳定的突出问题,引起了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公安机关高度重视。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也对公共危机的处置提出更高要求,我们应紧跟时代步伐,进一步发展完善我国群体性治安事件的预防和处置对策。
(一)坚持以“预防为主”,完善“抓小抓早”的预警机制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群体性治安事件的预防为主,要做到居安思危,功夫要花在平时,事前预防总是胜于事后补救。很多的群体性治安事件,从表面上看,突发性表现明显,但是任何矛盾的激化都有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任何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发展一般事先都有迹象,并非临时集结在一起。从一些典型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很多的群体治安事件往往是由于一些部门负责人员对可能引发突发性矛盾的苗头不能妥善认识和解决,对一些事件的前期准备不够充分,处置不够到位或者错失处置良机而导致。
预防群体性治安事件,应从当前群体性治安事件发生的制度根源上着手,从源头上解决社会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化解社会不稳定因素。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关注社会弱势群体,通过建立各种政府支持系统,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措施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随着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健全各种利益和诉求表达渠道和协商机制;同时也要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和工具,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坚决反对那种“法不责众”,“不闹不解决”的错误观念,引导公民通过合法和正当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预防群体性治安事件,应当加快建立和健全灵敏畅达的预警机制,牢牢掌握处置工作的主动权。尤其需要强化对涉稳情报信息的搜集,调查和研判和处理等工作。各级党政部门应该将工作触角延伸至各行各业,广辟信息来源,广泛物色情报信息员和各种秘密力量,及时了解掌握各种社会和动态,建立覆盖整个社会面的情报信息网;各级党政部门要及时了解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反应,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要保持必要的政治敏感性,对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尽量依法为其解决,如果受条件限制,短时间不能解决也要加强疏导和说服工作,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尽量减少矛盾冲突;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相关部门应当迅速采取行动,尽早介入处理,力争把事件消灭于萌芽状态。
(二)贯彻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协同作战,迅速控制原则
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群体性治安事件必须在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统一领导下,整合相关社会资源,相关部门和单位形成统一整体,发挥合力效能,迅速控制事态发展。
1.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
各级党政领导作为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对维护地区社会稳定负有重大责任。对于群众反映的社会问题,他们最为熟悉也最有发言权。在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中坚持党政统一领导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和政治体制的必然要求。党委和政府领导,有利于掌控全局,短时间内平息事态,还可以使得党委和政府反思工作中存在那些需要以后改进的地方,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3]。
党委和政府必须强化责任意识,在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第一现场原则”,一旦发生重大群体性治安事件,党政主要领导和主管部门负责人,必须第一时间启动预案,第一时间上报情况,第一时间奔赴现场,与聚集人群进行现场沟通,面对面进行现场处置。相关部门的党政主要负责人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和权威,其在现场所持的态度和承诺较易得到群众认可,有利于缓和群众情绪,主要负责人在场也有利于针对事态发展,做出准确判断,及时调配各种资源和手段,果断处置。而且群体性治安事件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相信绝大多数普通群众的感情是质朴的,他们得到了尊重,往往怨气也会消减一大半。因此,党政领导要勇于到第一线做群众工作,发生群体性治安事件,绝对不能躲着群众不见面,找无法答复或者解决问题的人去应付群众,如果等到事情闹到无法收拾的境地才硬着头皮见群众,会使处置工作陷入被动,丢掉了第一现场原则往往处置工作不能成功[4]。
2.相关部门协同作战、快速有效控制
群体性治安事件作为社会消极因素的集中反映,光靠某一部门或某一方力量是无法有效处置的,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参与事件处置的相关单位和部门,应当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的前提下,贯彻谁主管谁负责,由引发事件的相关单位或部门作为第一责任人,同时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动员各方力量,明确责任分工,各负其责的同时,紧密配合,充分发挥合力效能,实现各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
发生群体性治安事件,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很容易导致事件迅速蔓延和扩大化。因此必须坚持迅速采取措施,快速控制,依法果断处置。在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过程中,首先应当将宣传与舆论引导放在重要位置。如果政府信息管理手段失当,政府或者相关部门“失语”,往往会导致小道消息和谣言满天飞,混淆视听,被别有用心的人恶意炒作或煽动往往导致事态失控①群体性治安事件中往往充斥着谣言的传播。例如,贵州瓮安事件中“初中生李树芬是被奸杀的而不是自杀死亡”、“民警指示黑恶势力对死者家属打击报复”的谣言。再如湖北石首事件中“武警抢尸”的谣言。。尤其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和手机等等新兴媒体能迅速诱发、传播甚至放大社会矛盾,更要需要强化网络舆情控制。因此,对于重大的突发事件,相关部门应当坚持信息公开透明,在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引导舆论导向,掌握话语权,占据舆论制高点。应当通过“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第三方调查”等制度满足社会公众对重大事件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对于热点或者敏感的社会事件与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建立良性互动,形成和谐共鸣。要通过各种传媒有效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不给恶意炒作或谣言传播机会和时间[5]。
在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中,应当采取有效地措施,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思路,即“可散不可聚”注意控制事件的规模和级别,不能形成大规模参与的气候。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参与主体具有多元化和多层次性。左右事件发展的主要是核心层和骨干层人员,因此在处置过程中,要善于抓主要矛盾,找准幕后策划者,找出骨干成员,将其险恶用心暴露在群体面前,使其失去煽动群众的市场;同时要分化大多数怀有从众心理的参与者,防止一般附和层群众向核心层转化,劝退围观群众,及时有效的瓦解“群体势力”,孤立打击少数。其次,在处置过程中,要讲究策略。很多群体治安事件,合理的利益诉求和不合法的表达手段交织在一起,因此在处置过程中,更需要相关部门倾听和回应群体不满情绪所表达的利益诉求,采取细致有效的思想工作缓解群众不满情绪,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在进行法律和政策的宣传教育上,要把握群众心理和情绪,可引入相关专家或者谈判专家等,在策略上刚柔并济,攻心方为上策;即“可顺不可激”、“宜解不宜结”。
在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中,虽不宜与群众直接对抗和冲突,强制手段和措施一定要慎用,但是如果出现暴力打砸抢等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和威胁人身、财产安全的刑事犯罪行为时,我们也绝对不能手软,搞无原则妥协,必须采取依法果断处置措施,将肇事者迅速拿下,防止非法行为的恶性蔓延导致事态的不断升级。同时,群体性治安事件具有反复性,一起事件的平息,并不代表所有矛盾和问题都已解决,快速处置本身并即刻消除深层次的社会利益冲突。因此,为了巩固处置成果,要做好善后处理工作,对于可能导致反复的因素要保持高度警惕,对于已经采取的措施要关注其实际效果,还要总结处置经验和教训,采取细致的化解工作,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三)正确定位公安机关在处置群体治安事件中的地位,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的作用
一些地方政府,由于少数部门和领导认识上存在误区,认为发生群体治安事件,肯定是公安机关没有维护好社会稳定,因此动辄把公安机关当作挡箭牌,推到最前线。公安机关既要完成政府交办的任务,又不能激怒高度情绪化的群众,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和困难。况且现实中公安工作没有做好也不是发生群体性治安事件的主要原因。认为处置群体治安事件只要“公安往前站,什么事都好解决”的思想,不利于公安工作的展开及公安机关与群众的联系。例如,2007年以来,瓮安县公安局为处置矿群纠纷、政府征地、拆除违章建筑和其他群体性事件,较大规模地出警就有十几次,在2008年发生的瓮安事件中,矛头直指公安机关。一些瓮安老百姓的抱怨:“政府和公安把我们当敌人对待,拿枪杆对准老百姓,我们心里能没有恨吗?”①新华网:《新群体事件观》,(2009-04-13)[2014-02-01]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9-04/13/content_11178520_4.htm。
一些地方领导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平安就是不出事”,采取”花钱买平安”的权宜型治理方式,对于一些苗头问题,则能压就压,能捂就捂,一味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和不讲原则的退让,使得一些诉求群体、个体不合理甚至不合法要求越来越多,尤其在处置过程中,如果对少数煽动群体闹事、打砸抢的违法犯罪分子,不运用公安专政手段及时的查处,会助长了一些人“法不责众”、“要想使得问题解决,就得制造点威胁稳定的事端”的心理错觉,这样就会严重冲击现有法律、政策和道德底线,损害社会公平和正义。长此以往,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
依据宪法、人民警察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安机关作为维护国家和社会治安稳定的基本力量,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安机关因为其职业的特殊性,尤其是基层公安机关直接处于治安管理的最前线,与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天然的、直接的联系,易于掌握大量及时的苗头线索和社情民意,而且公安机关所特有的网监部门可以适时对网络舆情进行监控,及早发现群体治安事件的隐患。公安机关应当发扬“情报信息主导警务”的理念,加强情报信息工作,发挥其群体治安事件预警机制中的作用。
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党委和政府是组织者、决策者和指挥者。公安机关是参谋助手和执行者,是辅助力量。公安机关是维护事发现场秩序的重要力量,是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力量;是化解群体性矛盾的重要力量;是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力量[6]。
因此,公安机关绝对不能大包大揽,不能片面强调通过警方的努力来解决问题,当然公安机关也不应对现场态势采取消极不作为,应在职责范围内做好疏导控制和处置工作,当好参谋,保持治安秩序的稳定。公安机关所承担角色还要随着事件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变化[7]。在群体性治安事件的早期和初期,公安机关应当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完善预警机制,加强情报信息工作,尽量不让矛盾激化和群体聚集。在现场处置过程中,公安机关必须维持事发现场秩序,保卫要害部门和单位和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公安机关应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调查了解情况,以疏导教育为主,武力震慑为辅,积极开展疏散和劝导工作,做好各方面的沟通工作。同时,警察权的运用一定要慎重,坚持慎用警力和强制措施、慎用武器和警械。当然慎用绝不意味着不用,公安机关作为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力量,对于那些打砸抢烧等群体性暴力行为,应当依法果断采取相关强制措施,依法予以打击,从而尽快平息事态。这样可以在打击犯罪同时可以警示组织者和积极参与者,减少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维护社会稳定和谐。
[1]何显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及其应急处置[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
[2]魏磊.大力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瓮安6.18事件再反思[J].理论学刊,2013,(8):74-78.
[3]钟婧.群体性治安事件处置原则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0,(7):74-78.
[4]师原兵,薛英俊.群体性事件处置中的经验和教训[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3,(11):41-42.
[5]潘庸鲁.谣言在群体性治安事件中的生成与消解研究[J].学术探索,2013,(2):47-51.
[6]公黎斌,徐腾跃.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对策分析[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3,(1):144-145.
[7]张敏.谈谈群体性事件中警察角色的法律问题[J].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1,(5).
The Prevention and Disposal to the Mass Public Security Events in China
LI Lan
(Anhui Vocational College of Police Officers,Hefei,Anhui,230031)
At present,China is in a peak season of mass security incidents,and how to prevent and tackle these incidents in an appropriate way has become a major issue that party committees and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must address.It is essential to accurately figure out the meaning and nature of the mass security incidents, and rationally analyze the forms and social impact of the current incidents.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prevention,and improve early warning mechanism.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arty committees and government,all of the departments should work together with joint efforts,and quickly control the situation.Public security organs,as an important force in maintaining social order and stability,should accurately locate their roles,and be a good adviser for party committee and government staff to actively prevent and deal with the mass public security events.
mass public secarity events;prevention;police;legal disposal
D631.4
A
2095-1140(2014)04-0066-07
(责任编辑:左小绚)
2014-03-15
安徽省2012年度高等学校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重点课题“我国群体性治安事件的预防和处置研究”(2012SQRW257ZD)。
李岚(1980-),女,安徽怀宁人,安徽警官职业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公安学、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