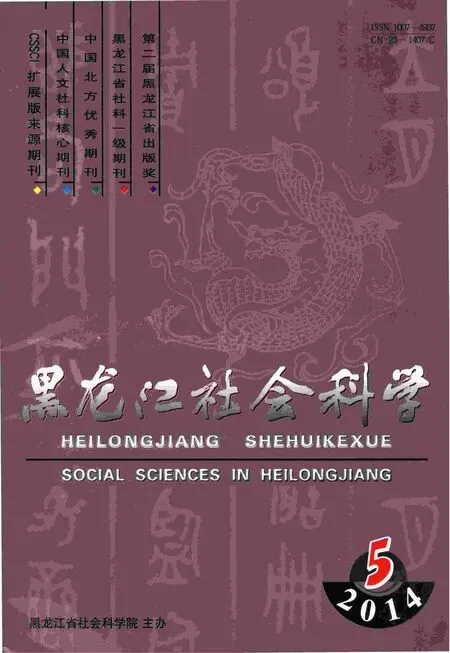主体“职业身份”与散文文体话语共性关联探究
王 雪
(延边大学 汉语言文化学院,吉林 延吉133002)
主体不同的“职业活动”会外化为不同的“职业身份”,职业身份从属于人类身份范畴。“人类身份不是自然形成的,稳定不变的,而是人为建构的”[1]。在建构过程中,“身份是一种主体间的、演现性的行动,它拒绝公众与私人、心理和社会的分界。它并非是给予意识的一种‘自我’,而是自我通过象征性他者之领域——语言、社会制度、无意识——进入意识的。”[2]因此,可以说,“他者之域——语言、社会制度、无意识”渗入“人的意识”之后,人的话语也就具有了相关层面的身份质素。同时,“身份是由承诺(commitment)和自我认同(identification)所规定的,这些承诺和自我认同提供了一种框架和视界,在这种框架和视界之中,我能够在各种情形中尝试决定什么是善的,或有价值的,或应当做的,或者我支持或反对的。换言之,它是这样一种视界,在其中,我能够采取一种立场。”[3]可见,人对诸多身份要素的“承诺”和“认同”,就形成了带有个性化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在文学创作中,“身份”的诸种因素都会自然渗入其中。
对散文而言,真实是其本体属性。无论细节是否真实,散文中情感与思想的流动都是真实而鲜活的,好的散文呈现的是创作主体一颗真实可信的灵魂。同诗歌、小说和戏剧相比,散文对灵魂的表达更真实、自由、直观、完整和具体。正因为散文的这种属性,“职业身份”所形成的日积月累的思想观念、职业思维、知识能力等因素,都会在散文文本中以“显意识”或“潜意识”的形式在精神指向、话语类型和文本结构等各个层面呈现出来,形成了散文创作宏观上带有“职业类”特点的写作现象。从主体“职业身份”类别的视角考察20 世纪的散文写作实践,可以发现学者、小说家和诗人三类“职业身份”从事散文创作具有人数多、创作成就高、影响大的特点,他们写作中的实践成就及“学者散文”的崛起与命名都为散文主体的“职业身份”类别研究视角提供了切实的依据。从文体特征来看,学者、诗人和小说家创作的散文宏观上呈现出如下几种共性话语倾向。
一、学者散文:学识、思想与智慧的自主表达
学者写散文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先秦诸子散文,到唐宋古文、明清小品,留存至今的古代经典散文的创作主体大都是当时的学问家。追寻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言文分离的文化现实使写作成为知识阶层的专宠;另一方面,也与古代散文所蕴含的文类十分宽泛有关。在古代散文范畴中,与韵文相对的散行文体都从属于此。因此,在古代散文的作者行列中包含着各个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如孔子、孟子、庄子、老子、司马迁、苏轼、韩愈、柳宗元等。到了20 世纪初,言文分离的写作事实缩小了散文的内涵和外延,狭义的散文范畴主要指“美文”。这时期的大多数作家同时也是在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从“五四”时期的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到三四十年代的林语堂、梁实秋、钱钟书,他们都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型作家。学者求实、严谨的思维方式和观察问题的思想深度,对他们的散文写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余秋雨、王小波、周国平、季羡林等人的散文在文化消费市场掀起了“学者散文”的热浪,“文化散文”“学者散文”的崛起与命名,进而引发对现代乃至古代散文的重新关注,使“学者散文”成为90 年代初“散文热”现象的主导力量,散文写作中出现的这种新兴的文体样式同样令读者耳目一新,它打破了以往散文自说自事、抒情叙事的文体形象,增添了博大宽广的文化内涵和深沉厚重的人文诉求。
韩小蕙对学者散文曾有高度的评价:“散文的写作可以分为四个境界:一靠个人才气灵动地写,此以天分取胜;二靠独特的人生经历直抒胸臆地写;此以真情取胜;三靠深刻的思索研究智慧地写,此以思辨取胜;四靠渊博的学识形而上地写,此以书卷气取胜。能达到以书卷气取胜者,才是大家。”[4]诚然,以不同的审美价值取向作为评价境界高低的标准尚需斟酌探讨,各家境界自成一格。但学者散文的确具有迥异于他者的思维方式。一般来说,作家具有敏锐地观察生活的能力,善于用形象思维描摹具体事务和生活的感受,而学者久居象牙塔从事教学和研究等活动,从事这种职业活动的人往往想象力和思辨力较强,而应对和创造生活的能力相对较弱。因此,学者型作家在散文中往往借助自己学术专业方面的优势,使智性与知性因素超拔于凡俗的世事之中,呈现出具有个性特征的思想和智慧光芒。以雷达为例,他在散文中就善于在现实所见所闻中生发出理性深沉的哲理思考,深入浅出,学以致用,知与行相互映现,智慧与思想相互照亮。比如,在《足球与人生的感悟》中,他把喀麦隆队踢球犯规的境遇和普适性人生际遇联系起来:
同样程度的犯规,对阿队作为一般问题,对喀队则不是黄牌,就是红牌,直弄到九人对十一人的局面。然而,喀麦隆还是赢了……
一个新生东西要崭露头角,要站住脚跟,总得经历一个逐渐被承认的曲折过程。这个过程有时还会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过早地要求公平、公正、合理,虽然有理,但要不来;企图省去被承认的过程,与时间作对,也不可能实现。
搞创作,做实验,推行改革,谁也很难不在歧视、轻蔑、刁难中忍耐,而后逐渐奋起。
面对复杂的现实生活,任何公正与公平都是相对的,一切质的变化都需要量的积累,承认也需要一个忍辱负重的过程。学者以广博的学识作支撑,通过对事物现象的分析,进而能阐释出社会本质的规律性,对事物的认识既有高屋建瓴的高度,又有入木三分的深度。
同时,学者散文的感情一般比较节制含蓄而深沉质朴,不善于浓墨重彩、大肆渲染,他们精于犀利而透辟的反讽和批判。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的批判是20 世纪学者散文的重要主题,鲁迅、钱钟书、王小波、余秋雨、张中行等都曾以不同的批判视角和文体话语涉笔于此。比如,王小波就常以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为圭臬,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虚伪与残酷予以痛彻地反击。在《人性的逆转》中他这样评述:
西方人认为,人的主要情感源于自身,所以就重视解决肉体的痛苦。中国人认为,人的主要情感是亲亲敬长,就不重视这种问题。
西方哲学是关注个体幸福的哲学,而中国哲学则强调“克己复礼”“三纲五常”,强调关系哲学,是在约制弱者行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平等的伦理关系,是以牺牲弱者个体幸福为代价的虚假的人际关系的平衡。同样,关于崇高,“西方人看来,人所受的苦和累可以减少,这是一切的基础。假设某人做出一份牺牲,可以给自己或他人带来幸福,这就是崇高——洛克就是这么说的。”孟子则认为:“有种东西,我们说它是崇高,是因为反对它的人都不崇高。这个定义一直沿用到了如今。”孟子概念中的崇高成为“成王败寇”的战利品,它附丽于统治者的最高利益,它同样是以牺牲个体的自由和幸福为代价,是因缺少恒定的价值标准而形成的带有欺骗性的价值观。“文革”时期,一个知青下水去追一根电线杆而牺牲生命被推崇为崇高,地中海荒岛的苦役犯在血腥暴力下每天做无用的劳动,也标示着统治者成功实现了人性的逆转。由此,王小波得出结论,要达到人类背离自己的人性欲望,实现“人性的逆转”,需具备三个条件:无价值的劳动,暴力的威胁和人性的脆弱。可以说,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受的苦就是“毫无价值的牺牲”,“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种有害哲学的影响下”,“我们的社会里,必须有改变物质生活的原动力,这样才能把未来的命脉握在自己的手里”。中国的传统哲学是束缚社会发展的观念范畴,而只有指导社会发展的理念转变了,才能实现社会运行模式的实质性转变。王小波以人本主义立场对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予以透辟地揭示和批驳,对于文明的进步、构建个体幸福观都具有见微知著的启示作用。
再比如余秋雨,作为文化散文的身体力行者,他的散文也是倾注着学识、理性和感情的互汇交融。学者创作风格虽各有特色,但从整体上说,都是在学识、思想与智慧的自主表达的底色中铺展与生发开来的。
二、诗人散文:意象营蕴出的诗情与诗意外化
自古以来,诗文不分家,很多大诗人同时也是散文家,古代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唐宋古文八大家,无不能诗能文。到了五四时期,朱自清和冰心的散文被奉为“白话散文的正宗”,而两者最初都是以诗歌创作蜚声文坛的。在20 世纪30 年代,诗人何其芳的《画梦录》、丽尼的《鹰之歌》和《黄昏之献》、李广田的《雀蓑集》和《画廊集》等都代表着当时散文的最高成就。新时期以来,周涛、刘亮程、苇岸、北岛等诗人的散文写作,也成为文坛显豁的景致,尤其为散文的创新开拓出一方新的场域。
“诗歌有独自的理想主义,而小品文则较为近人情。换句话说,诗歌有神秘的不可理解的幻想境地,而小品文大都是日常人生抓住现实的记录,最多在表现上幽默或深刻些。”[5]15诗人散文中诗情与诗意的外现是与诗歌本身创作的特征紧密相连的。诗歌侧重意象的营构、激情的迸发、思想的跳跃。诗人的散文也充满强烈的个性化人生体验,思维穿越古今中外,情感体验相对强烈,具有浓郁的诗情倾注,同时“追求诗意,经营意象,构思精巧,想象丰富,结构短小圆满”[6]。例如:
桌上放着一只烟灰盅。朝阳正在冬日的窗外冉冉升起。吸烟者拿起那只玻璃的烟灰盅,刹那间感觉到一份宇宙纯然的重量,仿佛宇宙自身孤独的分量全重压在他手上,在这个霜寒遍野、晨曦迷蒙的清晨……他眯眼朝四下的寂静张望,朝他的厨房看:白墙、乳白色结构精美的楼层。堆放墙角的啤酒。时间和日历。冬日的地平线尽头冉冉上升的一轮朝阳仿佛宇宙洪荒深处悄无声息的一只巨人之眼:第一把剑——傲睨之剑。
这是庞培《龙赋》中的篇首一段。庞培带着强烈的个人体验,吟咏着剑和人的交响,既有对人间真情的咏叹也包含着与剑相注释的诗人和刺客等人格精神的探访。思想跨越中外,情镜穿梭于古今,纵横捭阖、汪洋恣肆,这种语言和情感表述风格是颇能代表诗人散文的创作底色的。
诗歌和散文相比,“大概地说,诗歌感情想象的成分比较多一点,散文文学思想事实的成分比较多一点。诗歌比较注重情调,散文比较注重描写。诗歌比较接近音乐,散文比较近于图画。诗歌大多数是有韵律的,散文则无韵律。”[5]15诗人善于观察和发现生活中新奇的事物,诗人的浪漫情怀也使他们经常涉足异域的世界,他们笔下的景物意象常能渲染出颇具诗情画意的审美意境。“诗中有画”同样适用于诗人的散文,文中亦有画。比如周涛对于草原独特世界的描摹,于坚对于彝族文化的探访,都以他们新奇的意象画面为读者打开一扇异域文化之门。周涛在《阳光容器》中就描摹了一幅清沁澄澈的草原美景图。
阳光正是从这样一种蓝得发亮的容器中倾泻下来……触碰到白的岩石和各种颜色的明媚的野花……在宁静无人的夏季牧场上织出一片炫目的、灿烂的光芒彩雨。
在静谧的草原间,“有时候蓦然间会从天空中跌落下来一两只黄鸭……还有时候,会有三五只天鹅像一组大型客机在草滩上降落……它们像银子铸就的一般,把自己优美的身体合适地放在碧绿草毯的陪衬之中……几匹像是失散的无家可归的马,悠闲地甩着长尾……像一伙离家出走有些后悔但又想不起家来的流浪汉。”
西北草原的一切都沐浴在阳光之下,阳光以厚德载物的生命品性使万物获得生机,四季得以轮回。“阳光”“山体”“野花”“牧草”“黄鸭”“天鹅”和“马”等意象有静有动,一个动静参差的充满原生态生命力的草原“意境”被烘托渲染出来,大气磅礴,富有诗情画意。
对生命寓意的哲理性感悟是散文创作中常见的一种思维模式,尤其在诗人的散文中这种思维倾向更为突出和明显,不论是刘亮程舒缓的乡村笔调,还是于坚紧张的城市风格,都具有对生活本真状态的描摹,并生发出一种普适性的哲理思索。刘亮程笔下的村庄是他一个人与之交流的场域,有驴子、蚂蚁,也有柏树、花草、土地,虽然也有“村东头的人和村西头的人”,但都是人物群体,他的散文基本没有出现和其他个体人物的交流和接触,个体人物言行也是他观察的对象,他在以自我为主角——一个人感受到的村庄生活中,解读着自然本真的原生态乡村生活的单纯与荒谬,即使孤独地干着“剩下事情”,他“甚至已经知道他是谁”没干完地里的活儿,就仓皇而去,他也没有埋怨,他“想许多轰轰烈烈的大事之后,都会有一个收尾的人,他远远地跟在人们后头,干着他们自以为干完的事情”。这就是一种客观现实,因此“许多事情都一样,开始干的人很多,到了最后,便成了某一个人的。”这也成为一种生活规律,刘亮程就是在这样冲淡平和的心境中以清澈睿智之眼观察生活现实,看透生活的真意,同大自然对话,自言自语,刘亮程也因之获得了“乡村哲学家”的盛誉。可以说,同为乡土散文创作,“萧红、沈从文、孙犁、汪曾祺、贾平凹,用笔多在描述故事,人物,风俗,点染氛围,或添加一些抒情性的文字。无意于这一切,而集中于写一种哲学,一种心理文化,刘亮程是独步的。”[7]
诗歌常以具体的意象来渲染气氛或说明事理,具有浓重的象征意蕴,这种写作倾向也浸润到诗人的散文创作中。正如于坚在《城市记》中所说:“我的言说习惯是,要言说一个事物,我必须说出它像相似的什么”,也就是说诗人是以具体的意象来表述事物的本体特征的。同样是哲理的阐发,小说家呈现在故事的叙述中,学者善于缘事而发的哲理深化或根据旁征博引生发出来的价值思索,而诗人则善于缘物而起的抽象思考。比如,鲍吉尔·原野的散文集《脱口而出》就是短章碎片的合集,在叙事说理中闪烁着诗意的灵光。
痰盂可称是矛盾的化身。在一处高级居所,放痰盂有碍高级;又因其高级必放痰盂。痰盂的处境亦是一些人或事的处境。
从事物属性的角度看,痰盂本身的性质是它尴尬处境的根源。在这里“痰盂”被隐喻成一种人生的境况:有些人虽然是权力的附庸,但因其本身的龃龉而使人不愿意亲近他。
再比如,第三代诗人于坚也是以具体鲜活的意象来隐喻事理特点的:
大多数时间,你只知道事情正在发生,你通过蓝色的天空和风的速度知道事件在发展。是豹子的身上布满花朵,是蛇在花的洞穴中睡眠。而你远离现场,想象着那残酷的美。(《春天》)
黑暗可以说是一种精神力量,它掩盖具体的事实,让人在幻觉中征服了许多他在事实中无法征服的东西。(《在哲蚌寺看晒佛》)
无论是“天空”“花朵”还是“黑暗”都充满了隐喻性。意象的聚合形成“诗意”的写作,这种“诗意”是通过鲜活生动的意象构筑成的意境或者是一种事理的传达为旨归的。诗人在不时闪现着思想火花的浪漫想象之中,言说着属于个人和这个时代的事物和情感。“他们有的本是诗人,有的具有诗人的气质,所以在散文创作中必然倾注自己的诗情和诗艺。他们善于运用联想、想象、象征、幻觉、暗示、节奏诸艺术手段于散文,丰富、扩张了散文表现生活实感和内心世界的能力。”[8]
三、小说家散文:生活叙事的客观传神描写与思想精神的追慕
考察20 世纪的散文写作,我们会发现,小说家创作的比例最高。现代杰出的小说家如鲁迅、巴金、老舍、茅盾、张爱玲、萧红等创作的散文也都是现代散文经典。当代这种写作现象更为突出。如莫言、张炜、张承志、张抗抗、史铁生、王安忆、池莉等,可以说,20 世纪最好的散文创作是与小说家这个群体密切相关的。小说家广泛涉笔散文创作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散文这种文体本身短小精悍,更适合作家对生活和世界的直观表达。小说叙事的含蓄与虚构不足以更加完整具体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而散文对于景物和情感的写意性和思想、事件的写实性则成为作者灵魂直观书写的最为适合的文体。正像张抗抗在《以思想悦己》中评述张爱玲那样:“偶尔撩开了故事的帘子,走出来直接戏说女人,那女人就成了她手里的绝活,玲珑剔透、淋漓尽致”[9]162。正是因为散文更适于思想灵魂的表达,张承志在90 年代以后,主要致力于散文写作。小说家在散文中正是由人物与事件的幕后“导演”走到前台,散文中故事和人物是小说的原型,作家本人则成了文本中的主角。因此,作家的思想立场、情感结构与思维方式也都在散文中直观呈现在读者面前,与他的小说相互印证。同时,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而言,“写作首先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精神问题”[9]186,比如,张承志、史铁生、韩少功、张炜等,他们的散文话语既是思想传达的需要,也是精神话语的转换。他们发出了这个时代精英知识分子的生命强音,是对于凡俗生命的精神超越和对于现代文明负面因素的峻急批判,对自然和生命价值形而上的终极思索。
同学者散文以学识和理趣取胜不同,小说家的散文主要以深刻的情感体验和对生活事物的形象描述取胜。如小说家张贤亮所说:“学者讲道理,总要引经据典,如我之流,只能举个人经验。我想,学者与非学者的分水岭,大约就在此处吧!”[10]这句话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从选材方面讲,“非学者”的创作具有相似性,小说家作为一个群体创作的散文,从选材方面看不具有类的独特性,但“作者是小说家,他们偶尔写散文,也就有了小说的长处:比较客观,刻画,严整而不至于空洞、散漫、肤浅、聒噪等病——而这些却正是散文所最易犯的毛病。”[11]小说讲求思想的张力、生活叙事与结构的完整,所以,小说家往往可以规避思想的空洞和滥情的泥淖。在散文中他们也常以讲故事的视角,不动声色地讲述或亲切熟悉或遥远陌生的故事。他们的散文创作同样得益于从事小说创作而日积月累的表现技巧。尤其是对人情事理的传神描述,在小说家的散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试以贾平凹的早期创作为例,他的作品《丑石》中这样描述一块巨石的其貌不扬:
黑黝黝地卧在那里,牛似的模样;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留在这里的,谁也不理会它……它不像汉白玉那样的细腻,可以凿下刻字雕花,也不像大青石那样光滑,可以供来浣纱捶布;它静静地卧在那里,院边的槐阴没有庇覆它,花儿也不在它身边生长。
静默丑陋的丑石被认定是一颗陨石,在凡俗人眼中无用的事物却遮蔽不了它本质上的神奇。
是的,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正因为它不是一般的顽石,当然不能去做墙,做台阶,不能去雕刻,捶布。它不是做这些小玩意儿的,所以常常就遭到一般世俗的讥讽。
丑石的遭遇说明:每个微小的事物都有它独特的用途,只要是存在的就有它的根据和原因,名不见经传者暗藏韬略,有朝一日大器晚成也未可知,在丑石身上,也在传达着世间百态和生命传奇。
再例如贾平凹在《秦地游踪·延川城》中曾这样表达对故地秦川的赞美。
这个地方花朵是太少了,颜色全被女人占去;石头是太少了,坚强全被男人占去;土地是太贫瘠了,内容全被枣儿占去;树木是太枯瘦了,丰满全被羊肉占去。
带有西北地域特征的人性和物产特征揭示得别有韵致,这种欲扬先抑、对比衬托的描写手法形象生动地展现了秦地的风物人情。同样是对生活与人事物理的传神描写,各家叙述视角和风格又有很大的不同:贾平凹、冯骥才等的散文,是在带有鲜明地域印记的文化抒写中渗透出浓郁而理性的乡土情怀;张炜、张承志、史铁生等的散文,则成为他们追慕人类高贵精神的旗帜;王安忆和张抗抗的散文则是在以女性的敏锐来描摹平凡生活中的百态人物和细腻感受,即使是在对上海文化历史的追溯探访中,也要集中笔力聚焦城市变迁中普通男女的面相、身份和心态;在韩少功及余华的笔下,散文则是在追逐着思想和思维的乐趣。
相对于其他的职业身份作家,小说家在散文中往往热衷讲述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有人物、对话,呈现着对生活的个性化观察。在描述这种创作心态时,小说家林白曾说:“我的散文写作是一种个人化写作……个人化写作并不是一种风格,它只是一种立场,它以个体主体性来面对生命,这种写作所表现的世界也是个人的感官所感受到的世界。”[12]他们通过个人的视角解读历史、时代和社会中发生的人和事,“个性化写作”也是这个时代作家中较为通行的写作倾向,这种视角规避了传统写作的“宏大叙事”和“套版模式”,带有个性特征的语词呈现着个体生命的鲜活和个性化时代生活的多彩。在纷至沓来的个性化叙事中,一些作家自觉排扰消费文化语境下庸常生活叙事的琐屑,追慕人类独立自由之高贵的精神乐趣和人类思想的博远深厚,这类散文代表着这个时代散文创作的标高,比如史铁生、韩少功、张炜、张承志、张抗抗等,虽然审美创作倾向不尽相同,但他们在散文中彰显的高尚的精神指向和超越于物欲的价值追求,清新净化了喧嚣浮躁的时代空气,犹如受污染的滔滔大河中汇入一股纯净清爽的涓涓细流,他们的价值追求对消费文化困扰下的当代人确立自己的价值理想、价值追求,提供了大有裨益的参考价值。
诚然,学者、诗人、小说家这三类“职业身份”的写作主体都从事一定的写作活动。其中小说家和诗人拥有得天独厚的“文学身份”,学者长期学术研究的写作训练也磨炼出了缜密的思维和流畅的写作能力。这些写作训练给予了他们散文创作充足的技巧与笔力。这也是上述“职业身份”的散文家以一种宏观上“类的存在”卓立于整体散文园地的主要原因。同时具有这三类职业身份的散文作家并不存在整齐划一的界限和特点,源于散文自由和真实等属性,以及写作主体往往身兼多重“职业身份”,梳理“职业身份”类别的文体写作特征,只是在整体上考察的一种带有共性特征的话语倾向。作为个体而言,其话语特征和主体的童年经验、生活阅历、性别身份、个性气质等因素构成具有因果关系的动态立体的支撑系统,后者以合力的形式对个体的散文话语特征发挥作用。
[1] 萨义德.东方主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427.
[2] 程丽蓉.后殖民主义文化身份研究[J].中外文化与文论,2008,(1):133.
[3] 苏忱.中西方女性文学身份建构的比较研究[J].江淮论坛,2007,(1):170.
[4] 韩小蕙.太阳对着散文微笑——新散文十七年追踪[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152.
[5] 李宁.小品文艺术谈[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
[6] 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史[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345.
[7] 林贤治.一个人的村庄[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8] 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史[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345.
[9] 张抗抗.张抗抗随笔[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
[10] 张贤亮. 张贤亮散文集[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200.
[11] 李广田.谈散文[C]//现代谈散文作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330.
[12] 林白.死亡的遐想[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