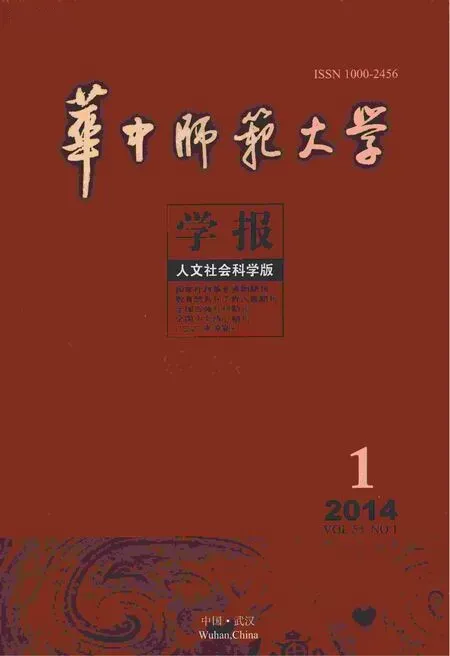论晚明的图书传播对社会舆论的影响
刘中兴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
晚明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形成,舆论传播的空间市场和消费需求逐渐产生。晚明时人很善于利用各种方式和工具营造舆论、表达意见,影响政治和社会生活,丰富的信息和活跃的舆论成为晚明的典型特征。
空前繁盛的图书出版业在舆论传播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图书 “本质上是一种传播媒介”,“实质上是人类文化的、精神的符号交流系统,是人类凭借组织编码的有序语义信息的文本,传播人类信息的重要传播媒介”,“承担着传播知识及文化的重要使命,既要在空间领域实现共时性传播,又要在时间范畴实现历时性遗传”①。在晚明血缘、地缘、阶层的限制被不断打破,社会流动性不断扩大的形势下,图书出版业繁荣,人们对于阅读有强烈的需求,于是图书成为了信息传播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围绕图书的编写、流传和阅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信息传播网。
在舆论传播过程中,图书对于 “信息的有选择性传递,将人们划归到非常不同的信息系统,而创造出各个 ‘群体’”②。相较于传统的经史子集,较为另类的时事小说、官员编书、妖书等几种重要形式的图书更能体现当时舆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由于作者的出发点、图书内容、图书功能的不同,这几类图书在信息传播和社会舆论传布与构建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但都是晚明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并推动了晚明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展。学术界关于晚明图书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学史、出版史以及文人与党社的关系等方面,本文试从社会舆论的角度对时事小说、官员编书、妖书进行考察,从图书这一更具象的角度考察晚明社会变迁。
一、图书与晚明信息传播网的形成
信息是社会的反映,晚明信息的传播有着典型的时代特征。明初对人口的控制相当严密,社会缺乏基本的流动性。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商业的发展,社会流动的频繁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特征。手工业的发展、商业市镇的激增以及地区性贸易市场的形成,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社会流动:既有地域之间的人口流动,又有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晚明信息的活跃与多样性,可以从这种广泛商业化的社会流动中找到社会根源。
嘉靖后,社会力量发生了新的分化,传统“四民”的区分也越来越模糊。时人姚旅提出了“二十四民”之说:“古有四民……余以为今有二十四民”,除士、农、工、商及兵、僧之外,还有道家、医者、卜者、星命、相面、相地、弈师、驵侩、驾长、舁人、篦头、修脚、倡家、小唱、优人、杂剧、响马、巨窝等十八民,“凡此十八民者,皆不稼不穑,除二三小技,其余世人,丰之如仙鬼,敬之竭中藏。家悬钟鼓,比乐公侯,诗书让其气候,词赋揖其下风,猗其盛哉!”③从“四民”向 “二十四民”的转化,反映了晚明社会大流动的一种必然,也加快了信息流动的速度和信息的多样性。
随着社会流动的频繁,士、农、官、商的渗透、融合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商人阶层的兴起及其财富大规模的积聚,为其社会交往渠道的拓宽以及向士人阶层的渗透提供了极大的物质便利。商人阶层不仅模仿士人的生活及品位,还投资于书楼、画室、古玩等等,活跃在士人的社会文化活动之中。同时,士商交往中更增加了物质利益的因素,士人为他人写墓志铭、寿序、文序、碑铭、传记以及为商人子弟授课,为书商写书评等等谋利行为成为平常之事。“富者余赀财,文人饶篇籍;取有余之赀财,拣篇籍之妙者而刻传之,其事甚快。非惟文人有利,富者亦分名焉。”④何良俊则描写道:“盖吾松士大夫一中进士之后,则于平日同堂之友,谢去恐不速。里中虽有谈文论道之士,非唯厌见其面,亦且恶闻其名。而日逐奔走于门下者,皆言利之徒也。或某处有庄田一所,岁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银几百两,岁可生息若干;或某人为某事求一覆庇。此无碍于法者,而可以坐收银若干,则欣欣喜见于面,而待之唯恐不谨。盖父兄之所交与而子弟之所习闻者,皆此辈也。”⑤
由此,人们交往的途径和范围得到较大扩展。商业利益的驱使,信息交换、社会交往需求的激增,使晚明信息传播的内容和层次更为多元,而丰富多彩的图书便是多元信息的有效载体。明代的图书出版事业和印刷技术,都可称为我国的极盛时代。尤其是明代中后期,印刷出版业高度商业化,成为当时商业活动的重要内容。查慎行《人海记》有言:“明刊二十一史于北雍,糜六万金有余。”⑥吴敬梓 《儒林外史》中描写,明代文人马静受雇为嘉兴文海楼书坊编选三科程墨,除食宿外,另得一百多两银子为报酬⑦。
明代刻书业的发达与下列因素有关:首先,印刷术的全面进步为明代出版业的繁荣提供了技术条件。北宋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由于当时技术条件以及其他方面条件的限制,雕版印刷术仍然占主导地位。直到明代,尤其是在嘉靖之后,活字印刷术才得到推广,从而推动了中国古代印刷出版业新的发展。明代活字印刷术中使用最为普遍的是木活字,效率高且费用低。其次,纸、墨等原料的降低。竹纸开始大量使用,虽然竹纸的颜色暗黄,易碎不宜久藏,质量比不上棉纸,但因其产量大而降低了成本此外,将用过的竹纸回槽后还可以循环利用,印刷成本得到进一步降低。再次,商业交通及邮驿的发达与书籍的社会化流布。明代依托运河和长江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为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隆庆四年,徽商王汴编 《天下水陆路程》,列全国水陆路程143条,其中南京至全国各地的长途路程11条、江南至邻近区域路程12条,更有15条水路连接苏松二府和各市镇县城,依赖于发达的交通网络,专业的渠道如书市、书肆、书摊、书船等,业余的渠道如考市、负贩、货、杂货铺等,明代图书交易相当繁盛。第四,书坊出版的高度商业化。明代刻书业由官家、私家和书坊三家经营,其刻本分别被称为 “官刻本”、“私刻本”和 “坊刻本”,坊刻本即为一般书商刻印的书。虽然受到官府的干预,但图书出版已经商品化,而民间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业化印刷业尤其繁荣⑧。明代书坊刻书的数量和规模都相当大。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中描述道:“今满目皆坊刻矣,亦世风华实之一验也。”⑨刻书中心分布地域广,较著名的有福建建阳、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以及浙江的杭州、湖州等地。南京可以考得坊名的有57家之多,其中 “以唐姓十二家为最多,次为周姓七家”⑩。据统计,到1600年前后,南京至少有93家商业出版机构,苏州有37家,杭州有24家;在以后的40年中,直到明末,这个数字至少在苏州增长了将近3倍。
当时出版业的竞争相当激烈,书商会通过各种手段制造有利于营销并能有效保护自身利益的商业舆论。书籍出版之后若是畅销,会有其他的出版商翻刊盗印图利。“福建书坊……专以货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开价高,即便翻刻。”冯梦龙也说: “吴中镂书多利,而甚苦翻刻。”崇祯时南京书商在其出版的 《道元一气》书前附有告白:“倘有无知利徒,影射翻刻,誓必闻之当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缘。”书坊主为了增加书籍发行量,获取可观的经济利益,还竞相在书籍上刊登各类广告,达到宣传与促销之目的。图书商业广告有牌记广告、序文广告、凡例广告、书名广告、征稿广告等多种,其形式之繁,内容之丰,技巧之新,令人叹为观止。
商业因素之外,明朝政府还采取了一些重要政策,以促进图书出版发行流通业的发展。一是在赋税方面,《明会要》载:“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同时被免税的还有笔、墨等图书生产的物料。二是鼓励文化教育,到明代末期,全国的生员人数达50万人之多。学校的普及,意味着文盲率的下降和读书人的增多。三是改变工匠的服役制度,规定可以以钱代役,使得工匠的时间更加自由,激发了印刷行业工匠的积极性。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晚明时期的图书出版业一派欣欣向荣景象。据 《中国出版通史》(明代卷)统计, 《明代版刻综录》共著录图书7740种,其中洪武至弘治时期的书共766种,正德、嘉靖、隆庆年间共2237种,万历至崇祯年间共4720种,其比例是1∶3∶6。地方志一类书,明初只有数百种,嘉靖以后共出版1688种。小说、戏曲类图书,明代初期、中期加起来只有百来种,晚明时期至少有一千多种。私人撰写的史书,明初和中期加起来不到一百种,明后期撰写私史成风,有关出版物不止千种。
与庞大的图书市场互为促进的,是明中后期人们阅读需求的增加及新的受众群体的形成。明代前期书坊所刻图书主要是传统的经史子集,读者也主要是士大夫阶层。而明代中后期市民阶层逐渐形成,他们大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闲暇空间,阅读无疑成为消遣的最好途径之一。但绝大多数市民阶层对于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等 “雅文化”并不感兴趣,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 “俗文化”。同时,受商业发展的影响,明中期以后很大一部分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以及审美情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与市民阶层趋同,于是产生了以市民阶层为主体的新兴读者群体。此外,一些晚明士人 “屈就市场”,参与商业性的写作和出版,他们撰写和编纂的书,无论是由政府、书坊或别的民间机构出版,都赢得了广大的读者群,把平民甚至工匠,“拉升”为可以泛泛地称为 “士人作品”的读者。由此,围绕图书的编写、流传和阅读,社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信息传播网。
二、时事小说:社会舆论的灵敏性
对于小说这种明代比较流行的文学形式,台湾学者王鸿泰对其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进行了很好的总结:“明中期以后,小说已成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可说是一种大众读物……小说在明末清初期间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它提供了一个公众化的管道,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 ‘公众场域’,就像个开放性的虚拟舞台一般,小说在明清时期已然成为个别信息与公众会面的场域。”
在晚明众多小说之中,自万历三十一年的《征播奏捷传》到明末清初,一大批讲述阉党始末、辽东战事、李自成起义、清兵下江南的小说集中涌现,在小说史上首次出现了大规模当代人写当代军国大事的长篇通俗小说,并且对事件进程展开细致描写,文学史上称之为 “时事小说”。这类小说从宋元话本中讲史一类衍生而出,但其与历史演义小说已有较大区别,所讲的是当代时事,因而渗透了更多的 “当代”意识。此时人们对于小说的价值和功用有了新的认识,不仅显示晚明的作者与读者急于了解和传播当下的舆论热点,也表明小说被认为是理解 “历史即时事”的一种新方式。时事小说类似于今天的 “报告文学”和 “纪实小说”,不仅在题材上和艺术技巧上独树一帜,而且成为时代的历史见证。晚明剧烈的社会变动、政治斗争以及即将发生的鼎革之变,使晚明成为时事小说的繁荣期。
与 《三国演义》等通俗小说不同,时事小说充分体现了社会舆论的灵敏性,一方面直接反映刚刚发生的、还在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对于重大时事比较敏感;另一方面成书时间比较短,对时事的反映比较迅捷。魏忠贤阉党集团覆灭后不到一年时间便有三部揭露其丑恶行径的小说问世,其中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从写作到刊行只用了九个月的时间,《警世阴阳梦》则在魏忠贤死后七个月便已发行。此外,《辽海丹忠录》的主人公毛云龙去世不久,该书就已刊行于世。《剿闯通俗演义》写李自成攻陷北都及清兵入关之事,书成时明廷与清兵仍在追剿起义军。
晚明时事小说的舆论灵敏性,与当时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大背景密切相关。广泛的读者群体是时事小说在晚明勃兴的直接推动力。随着市民阶层的出现,新的受众群体开始形成,市民阶层的兴趣爱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小说创作的流向和趋势。魏忠贤死后,朝野上下压抑许久的愤懑之情迸发出来,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先后有多部描写魏忠贤阉党的小说面世,其他时事小说也多有言及。
从时事小说的创作主体来看,作者都具有传播舆论的主观意图和现实需要,对重大事件比较敏感。虽然晚明的时事小说作者的社会地位一般不高,但由于饱受儒家正统思想熏陶,加上受明末启蒙思想的影响,因而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这也是他们创作时事小说的直接主观动因。《剿闯小说》作者自陈:“小生上观古烈,下抚时事,终宵披衣,毒恨入髓,既因秀才,又无大力,徒伤当食,但心刀割。”《定鼎奇闻》总结说:“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从资格,是以国破君亡,鲜见忠义。”
作者把时事小说作为发泄感情的载体,在反映魏忠贤的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陆云龙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自叙:“越在草莽,不胜欣快,终以在草莽不获出一言暴其奸,良有隐恨。然使大奸既拔,又何必斥之自我,唯次其奸状,传之海隅,以易称功颂德者之口,更次其奸之府辜,以著我圣天子之英明,神于除奸,诸臣工之忠鲠,勇于击奸。”《皇明中兴圣烈传》的作者也直言:“呜呼!从来逆贼狠毒有如此者乎?令人千古有恨,万世为恫矣!此事虽被魏忠贤逆贼所害,若不代他把逆天大罪恶彰扬出来,与世共知,使率土唾骂,普天怒责,却不便宜他,此亦草野公愤,不容不发泄一番者也。”
为了更好地发挥舆论传播效果,时事小说还具有较强的通俗性。由此,时事小说对舆论的传播更具有广泛性、公开性,作者可以很快将时事演绎成小说,使更多的人了解。《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序中言及,希望通过本书 “嗣此耕夫牧竖,得戟手而问奸雄,野老村氓,至反唇而讥彪虎”。《皇明中兴圣烈传》:“特从邸报中与一二旧闻,演成小传,以通世俗,使庸夫凡民,亦能披阅而识其事。”
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晚明高度发达的商业出版促成了时事小说的快速广泛流布。时事小说规模庞大、读者众多的特点,决定了它必须经过书坊这一中介环节,才能广泛传播。为了使时事小说在极短时间内成书并更为畅销,书坊主介入了时事小说创作,有的小说家还兼 “书坊主”于一身,如冯梦龙、凌濛初、陆云龙等,大肆推介时事小说。陆云龙吹捧 《斥奸书》“信一代之耳目,非以炫一时之听闻”,非 “寻常笔墨”,“文人墨士知必奉为一代信书”,“异于稗官野说”。《梼杌闲评·总论》则吹嘘 《梼杌闲评》“是非不在 《春秋》下”。
书商及作者为了迅速占领市场,也导致了时事小说大多草率成书,其中突出表现为大篇幅地录用奏章及诏书原文,而且错字、漏字、文句不连贯现象更是数不胜数。这些小说还存在着大量抄袭现象,同题材小说之间尤为突出。更有甚者,书中版画插图也剽窃他书。据谭正壁先生考证,《圣烈传》三面附图系剽窃 《警世通言》。这种“快餐式”制作,说明商业发展推动着市民文化进一步繁盛,同时又成为文化世俗化的动力,商品经济效益已成为左右时事小说产生、传播的重要力 量。
正是因为时事小说对舆论信息比较敏感,具有很强的舆论传播效果,因而对时事小说所依据的重大事件的当事人往往会产生很大影响,有时甚至引发政治斗争或是被用来作为政治斗争工具。《辽东传》的传播就是熊廷弼被杀的一个重要原因,《明史》记载:“忠贤愈欲速杀廷弼,其党门克新、郭兴治、石三畏、卓迈等遂希指趣之。会冯铨亦憾廷弼,与顾秉谦等侍讲筵,出市刊 《辽东传》潜于 (天启)帝曰:‘此廷弼所作,希脱罪耳。’帝怒,遂以五年八月弃市,传首九边。”在天启二年的广宁之战中,由于经 (熊廷弼)、抚(王化贞)不合,明军惨败,辽东失守,熊廷弼护溃民入关,熊、王皆下狱。而冯铨以书进谗,熊廷弼被杀。《酌中志》、《三朝野记》、《三垣笔记》等 皆 有 记 载。
可以说,所有时事小说都有传播舆论的意图,而且距事件发生时间越短,作者的这种意图越明显,这也是时事小说创作的基本出发点。时事小说也因此具有很强的传播功能,成为舆论传播的重要方式。
三、官员编书:对舆论主导权的争夺
晚明时人尤其是官员也善于用书籍来表现自己的身世和感情,以此来获得舆论的支持或同情。《明史》记载:“给事中潮阳陈洸素无赖。家居与知县宋元翰不相能,令其子柱讦元翰谪戍。元翰摭洸罪及帷薄事刊布之,名 《辨冤录》。洸由是不齿于清议,尚书乔宇出之为湖广佥事。”陈洸身居言路,又在朝中有靠山,宋元翰投告无门,遂写书感怀身世终于获得了舆论的支持。后来陈洸官复原职,但不久其他言官弹劾陈洸,在奏疏里附上了 《辨冤录》,于是舆论大起,最终 “除赦前及暖昧者勿论,当论者十三条。罪恶极,宜斩,妻 离异, 子柱绞”。
在当时,官员编印书籍影响舆论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在官员们中间,印刷的书籍常常作为礼物成为社会交往的润滑剂,帮助他们建立有利的社会关系。这些书通常包括一个官员自己的著作,或家庭成员的作品,或仅仅是他所喜欢的一部作品,大部分或完全是在某个政府机构资助下用政府资金出版的。明代的地方官尤其是巡按御史,常常用政府薪金款项和地方政府资金来印刷书籍,作为给朝廷官员的礼品。叶德辉在 《书林清话》中指出:“官吏奉使出差,回京必刻一书,以一书一帕相馈赠,世即谓之书帕本。”陆容也说:“今士习浮靡,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据晚明藏书家胡应麟记载,官员们中间流行赠送书籍,通常在官员们获得任命和提升时相互交换。这种做法尤为高级官员所欣赏,他们藏书的主要构成是赠书者的科举程文印本,可以很容易达到10000卷以上。
探究官员编书在晚明舆论传播中的独特意义,《万历邸钞》和 《万历疏钞》是不能忽视的。这两部书对于晚明史,尤其是研究东林运动,都是极为重要的文献。《万历邸钞》全三册,是共有2411页的大部头著作,从万历元年正月到四十六年六月 (一部分年度阙如),抄录和重要事件有关的邸报并加以若干整理,基本覆盖了万历时代。据粗略统计,万历邸钞总共有45.27万余字,其中篇幅最多的为万历三十六年,达3.8万余字;最少的是万历三年,仅600余字。该书是编年体,是和 《明实录》相补的极为重要的资料。据日本学者小野和子考证,该书出自于东林人士钱一本之手。
《万历疏钞》是万历时人吴亮所编纂。该书五十卷三十四册,将万历时代的奏疏按问题分类,全文收录,包括圣治、国是、臣道、言路等50个主题。在该书的序言中,顾宪成和吴亮谈到了要开通言路,这也是他们力促此书乃至 《万历邸钞》编行的最大目的。顾宪成从言路的视角,回顾了万历朝三十多年的历史:“溯丁丑纲常诸疏,政府不欲宣付史馆,遂迁怒于执简诸君。嗣是愈出愈巧率假留中以泯其迹,令言者以他事获罪,不以言获罪,至于迩年,且欲并邸报禁之。”顾宪成认为,当时最大的危机就是禁止邸抄。即使不允许政治批判,只要邸抄流布,他们的言论还是可以传播,还可以引发社会舆论。如果连这也被禁止,那么言论的传播就无法进行。
当时,工科给事中王元翰从国防的角度主张禁止传抄奏疏,但统治者则表现出由此扩大到一般奏疏,进而封锁言路的意图。对此东林人士以针对内阁抗议弹压言路的目的,编集了翁宪祥《乞亟通章疏以存清议疏》(万历三十五年十月)、吕邦耀 《章疏亟宜批发以开言路疏》(万历三十五年十一月)、金士衡 《乞亟宽时禁以通言路疏》(万历三十五年十一月)等奏疏,为了造成舆论,促成了 《万历疏钞》的刊刻。在这些奏疏中,也有统治阶层不愿意公开的内容。他们通过编纂这些书,明确自己的政治立场,宣传鼓吹舆论,同时也是为了在历史上留下这些事实。
《万历邸钞》和 《万历疏钞》中所收录上疏,围绕着具体的政治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政见。这些上疏,时而被隐匿,时而又被留中不发,时而还被禁止在邸报上传抄。东林人士把这些言论重新编辑起来,通过向在朝和在野人士的广泛呼吁,形成政治上的舆论,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与之相对,阉党也深谙借编印图书制造舆论之道。魏忠贤大兴冤狱、滥开杀戒之后,阉党也开始在舆论上大造声势,诬陷东林官员,意图为自己的罪行正名。阉党群小炮制各种花名册呈献魏忠贤,部分编印散布,作为整肃异己的参照,借以罗织罪名,网络异己之人,意图一网打尽。首辅顾秉谦亲手编订 《缙绅便览》,上列时任官员名单,并分为 “邪党”和 “正人”两派,用墨笔在名单上加圈加点。叶向高、赵南星等东林官员皆被列为 “邪党”,而王永光、徐大化等六十余名阉党追随者被视为朝中 “正人”。这份名单作为打击摈斥或提拔任用的依据。随后,崔呈秀又进献《东林同志录》,列叶向高等三百九十人。王绍徽还仿照 《水浒传》一百零八将的形式,将一大批东林官员编 《东林点将录》,以获取魏忠贤的欢心。这样从淮抚之议起与三党对立的官员以及后来与红丸、梃击、移宫三案相关的人也都被罗织在 “东林党”人之内。《东林点将录》中第一人是“托塔天王”李三才,为东林开山元帅,叶向高与赵南星为 “总兵都头领”,高攀龙与缪昌期被称为“掌管机密军师”等等。此外,阉党还编造了 《东林朋党录》,列赵南星等九十四人;编造 《东林籍贯录》,列孙承宗等一百六十二人,还有 《盗柄东林夥》、《夥坏封疆录》、 《初终录》、 《石碣录》、《伪鉴录》等等,名目繁多,不下数十种。
天启五年十二月,阉党成员、江西道御史卢承钦编造了一份三百零九人的 《东林党人榜》,言“近日邪党复炽,皆调停为害……犹有姑容不尽之虞”,并建议魏忠贤将党人姓名、罪状布告天下,榜示海内,让东林人士 “躲闪无地,倒翻无期”。魏忠贤又矫旨以 《东林党人榜》的形式将所谓的“东林党”人名单刊布,并刻于邸报,将东林士人视作 “邪党”,“生者削籍为民,当差仍追夺诰命,其一切党人不拘曾否处分,俱著该部院会同九卿科道……将姓名罪状并节次明旨刊刻成书,榜示海内,垂鉴将来,以永保清平之治”,东林人士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同时,魏忠贤又对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所发生的京察、梃击、红丸、移宫等重要事件,进行了全面翻案。顾秉谦担任总编纂,仿照明代大典,组织人手编写了 《三朝要典》,于天启六年八月刊刻颁行天下,对东林官员的作为予以彻底否定,为阉党一系列罪恶行为歌功颂德,以此为阉党的行径制造舆论。
“妖”,在先秦与秦汉典籍中也常通 “訞”,《荀子·非十二子》:“如是而不服者,则可谓訞怪狡猾之人矣。”杨倞注:“訞与妖同。”说明 “妖”在最初的解释中即与言论直接相关。汉代刘熙则进一步指出: “妖,殀也,害物也。”认为 “妖”具有负面色彩,因此 “妖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多被赋予贬义色彩的。秦汉之后的文献典籍针对“妖书”作了细致的规定,《唐律》规定 “妖书妖言”即是 “休咎及鬼神之言,妄说吉凶,涉于不顺者”,疏议对此条律文又有明确解释:“‘造妖书及妖言者’,谓构成怪力之书,诈为鬼神之语;‘休’,谓妄说他人及己身有休征;‘咎’,谓妄言国家有咎恶;观天画地,诡说灾祥,妄陈吉凶,并涉于不顺者,绞。”而元人徐元瑞认为 “怪异不常之书”为 “妖书”,更强调奸邪的成分。《大明律》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又解释道:“谶纬是诞妄休咎之言,组织未来之事,妖书如鬼神之书。”明代名臣王恕依此重点强调律 “妖书妖言能惑众乱民坏国家之事 ”。
具体而言,明代许多被称为 “妖书”的主要指与叛乱谋反有关并涉及宗教、天运、世道、鬼神等内容的书籍,冒犯或触忤了统治者忌讳的言论和书籍,用于政治斗争的党争文书,带有政治语言性质的谶谣类书籍,扰乱社会秩序的书籍等等。至于妖书的范围,余继登 《典故纪闻》列出了94种之多:“成化年间,因擒获妖人,追其妖书本图,备录其名目,榜示天下,以晓谕愚民。其书有:番天揭地、搜神记经、金龙八宝混天机神经、安天宝世、绣莹关、九龙战江神图,天空知贤变愚神图经、镇天降妖铁板达通天混海图、定天定国水晶珠经……”
在明代,虽然对出版的管制相对较松,但对这些 “妖书”则是严惩不贷:“造谶讳、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明朝皇帝曾多次颁令,严禁私藏和流传妖书。如成化十年五月,明宪宗 “申藏妖书之禁”;弘治十七年二月,明孝宗 “申藏讳妖书之禁”。从统治者深恶痛绝的态度,可见妖书在传播社会舆论方面的巨大影响。
明代初期,由于皇帝对思想控制比较严密,对舆论掌控较紧密,妖书相对较少。到明代中后期,一方面专制统治开始松动,朝政日渐宽大,舆论环境相对宽松,敢言能言成为社会及政治风气;另一方面各种思想交锋激烈,传统礼制束缚较少为妖书开始大肆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更重要的,是晚明发达的商业环境下,底层民众容易被蛊,或为谋生而传播和编造妖书;党争愈演愈烈,官僚为了政治斗争而利用妖书,统治者为维护话语权而创造了 “文字狱”式的妖书等等。妖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和历史合理性,同时,各个阶层对妖书的解构及利用,又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以及统治秩序造成了 重 要 影 响。
妖书在晚明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多是制造重大政治事件的有力工具。“有太原人李福达以妖书惑众,聚党至数千人,改年为乱,震动三河。”而万历年间的妖书案则成为晚明时期影响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事件之一。万历二十六年,万历皇帝将从民间收集的一本名为 《闺范图说》的图书赐给了最宠爱的郑贵妃,该书主要内容是妇德。郑贵妃自己作序并交由其伯父郑承恩编印出版散发。此时,民间出现一本匿名图书《闺范图书说跋》,又名 《忧危竑议》,“盛传京师,谓坤书一首载汉明德皇后由宫人进位中位,意以指妃,而妃之刊刻,实藉此为立己子之据。其文托 ‘朱东吉”为问答,‘东吉’者,东朝也。其名忧危,以坤曾有忧危一疏,因借其名以讽,盖言妖也。”当时文官集团正在与万历皇帝就立储一事展开着激烈的斗争,他们认为郑贵妃想通过《闺范图说》一书制造立爱子、不立长子的舆论,但作者并未查明。
五年后,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的一晚,“上寝重幄中,初寤,天未晓,忽于枕上得书一卷,呼嫔御取烛夜读,则皆陈说上过也。上骇,密令心
四、妖书:自下而上的舆论工具
腹大珰出察之,鸡人方传唱,闾阖诸宫未启,不知其何来。寻问阁部臣入对,诸内外大小臣俱于是夜从枕上得书,与所陈事同,无一逸者,众不敢匿,趋朝中各上之。上下大惊愕,相谓妖书。”这本妖书名为 《续忧危竑议》, “言贵妃与大学士朱赓、戎政尚书王世扬,巡抚孙玮,总督李汶,御史张养志,锦衣都督王之祯,都督佥事陈汝忠,锦衣千户王名世、王承恩,锦衣指挥佥事郑国贤等相结,谋易太子,其言益妄诞不经。”朱赓 “已邸门获妖书,而书辞诬赓动摇国本,大惧,立以疏闻,乞避位。”
实际上,当时朝政比较宽松,对 “国本”异议的朝臣大可通过正常的疏议程序表示不满,而不必担心被重惩。而散布者以 “妖书”的形式,不仅言辞诡谲,而且刊印散发,一夕间 “黏宫中与城坊皆遍”,显然其真正目的不在于论 “国本”,而在于通过 “国本”之争引起朝廷关注,进而趁机打击政敌。如御史赵之翰等便借此弹劾前大学士张位等 “太子党”官员,并使其遭谪戍,牵连者多遭牢狱之灾。
如果说这两份 “妖书”一开始还反映了民众对于 “国本”的舆论关注,那么到后来 “妖书”的内容被关注较少,而是成为朝廷内部各派势力政治斗争的有力工具,由此还牵连了一大批无辜受冤者。对于 “妖书案”,钱谦益感慨地说:“(沈一贯)与宋州 (沈鲤)同辅政,而门户角立,矻矻不相下,妖书之狱,宋州及郭江夏仅得而免。人谓少师有意齮龁之,海内清流,争相指摘,党论纷呶,从此牢不可破。雒蜀之争,遂与国家相始终,良可为三叹也!”
五、结论
尹韵公评价说,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书籍的出版发行与社会舆论有很强的联系,因为书籍不仅具有积累文化、弘扬文明的作用,而且还能传播思想、流布言论,进而形成社会舆论的现实作用。虽然明代的图书出版有着特有的发展规律与过程,但它也确实给予了明代的社会舆论以强大的和深刻的影响。如果说言论是社会舆论中的“无形”部分,那么书籍则是社会舆论中的有形部分。有形的比无形的更有力量,更成气候。商业发展的需要,市民阶层形成的必然,中国近两千年政治和思想发展的高峰,使书籍在晚明成为舆论的代表性符号。东林党议、魏忠贤乱政、万历三案、辽东战事、李自成起义、清军南下等晚明一系列的重大事件中,都能看到书籍的影子,感受到书籍所传播的社会舆论的力量。
然而,书籍只是舆论传播的一种工具或者形式,成为其编者、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一种媒介。通过书籍与社会舆论传播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书籍的舆论力量在晚明商业化的背景下被空前放大:书籍不再只是传播知识、传递文化的载体,更是制造、引导、控制舆论的有效手段,甚至影响时局。在中国古代社会,对于思想、文化的控制是统治者所竭力掌握的。而晚明时期,统治者却有心无力,反而被书籍制造的舆论严重动摇了对思想文化乃至行政权力的控制。这种控制力的“逆袭”,反映出晚明社会并没有形成一个信息畅达、有效的舆情社会,书籍的自由流通、社会舆论的肆意流布,反而映射出 “自由奔放”光彩外衣之下的 “混乱无序”。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书籍所反映的多元思想标志着多元社会的形成,但缺少大气、包容和坚忍、霸气的正统思想引领,王朝就会 “因财富积累而导致贫富不均、因国家承平而导致因循守旧、因社会开放而导致涣散动荡、因自由过度而导致规矩丧失。与此相伴而生的,则是国家主导作用的日渐缺失和对外防御能力的急剧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讲,晚明的书籍“见证”了社会舆论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高峰,也参与了晚明政治与社会的动荡纷争,记录并传播了晚明的风雨飘摇,成为晚明社会变迁最好的注脚。
注释
①周庆山:《文献传播学》,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4页。
②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7页。
③姚旅:《露书》卷9《风篇》,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6页。
④钟惺:《题潘景升募刻吴越杂志册子》,见徐柏荣、郑法清主编《钟惺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47页。
绿色生态示范区应在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编制绿色建筑规划专章,落实潜力地图及总体规划提出的总量目标,提出各个地块的绿色建筑星级要求。建议研究制定地块生态开发控制图则,加强在土地出让环节对绿色建筑相关规划指标的控制。
⑤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34《正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12-313页。
⑥查慎行:《人海记》卷下,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1页。
⑦吴敬梓:《儒林外史》第13回《蘧駪夫求贤问业 马纯上仗义疏财》,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第81页。
⑧叶燮元:《明代江苏刻书事业概述》,《学术月刊》1957年第9期;李致忠:《明代刻书述略》,《文史》第23辑;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文物》1980年第11期;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1-42页。
⑨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8“时艺坊刻”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34页。
⑩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文物》198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