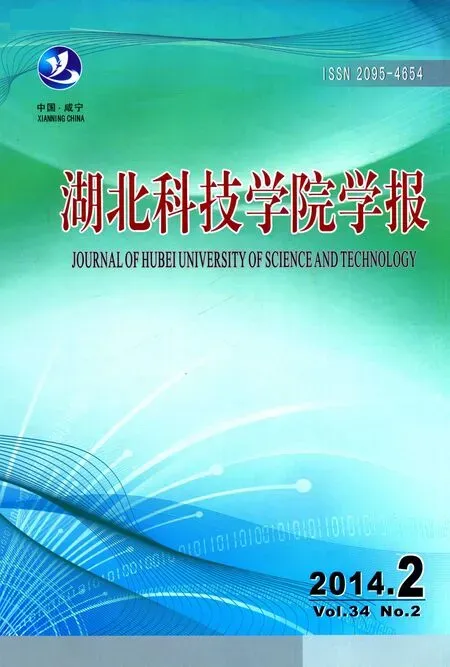“大德高僧”音乐史学家冯文慈访谈感悟
殷瑰姣
(湖北科技学院音乐学院,湖北咸宁437005)
2014年伊始,笔者有幸到冯文慈教授家对其进行录音采访,对先生的认识始于2011年笔者到中国音乐学院访学选修刘勇教授的《声乐古典文献》这门课程时建立的!刘教授上课时多次提及冯文慈先生,对冯先生膜拜有加,当时先生高大的形象就在我脑海里留下烙印。这次近距离的接触,更是让笔者对冯教授敬佩不已,幸庆自己能如此幸运能得到大师现场指导,感悟尤多。
一、文雅慈祥博学多思
初次相见,先生给笔者的印象就是:文雅慈祥。尽管先生已经八十八岁高龄了,但是先生耳聪目明,思维敏捷,此次访谈共进行了五次,每间隔三至四天访谈一次。每次的访谈历时将近三个小时,冯先生在没有撰写访谈提纲的前提下,叙述起来条理清楚,思维严密,措词讲究,充分的体现出先生的博学和多思的学术风格。先生从儿时所受到的教育谈起,最后落到他所攥写的论文及著作,娓娓道来。先生不断的强调音乐史学是门悠久的学科,又是一门不断更新的学科,所以先生一辈子都在不断的学习和研究。先生说:学术探讨不是跳高比赛,不同年代的人甚至与不同领域不同兴趣的各方面不同的人是不能够比的。先生说:关于学术,他愿意用马拉松接力来比喻更贴切,这里所说的“马拉松”是学术界一个特有的现象,不是指的是真的体育竞赛的那个马拉松。整个中国音乐史学,就好像是一个马拉松接力在那儿跑,我们可以研究它的起点,怎么开始的,但是终点是没有的。如果我们能够肯定音乐史学在不断的发展,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终点我们是“不确知”的。这代人跑完了,下代人接着跑。只有这样不断的接力,学术才会有生命力。先生的比喻精辟贴切。
二、严谨求真通达务实
此次访谈笔者充分领略了冯文慈先生严谨求真的学术作风。先生谈到他能有这样的学术成就是与他的儿时教育分不开的。他说:因为生来的机遇,本人小学教育是良好的。当时我是在天津南开小学读书,天津南开小学当时是一所一流的私立小学。在小学的阶段,有两个教师对我的影响很大,一个教语文,那个时侯叫“国语“,这个老师叫韩用六,是冀东人。在他的课上,我主要是学了若干唐诗。再有一个老师他叫徐秉仁,在他的课上我现在记得的学过《归去来辞》,另外还有些散篇,比如说:《列子》选取的小段落的故事,比如像《两小儿辩斗》等,还有其它的,像《桃花源记》……等,在小学阶段就都接触到了。后来到了中学,“国语课”就叫“国文课”了。头一年教我们国文课的是一位老先生,他是贡生,贡生应该说是比秀才要高一个层次。当时清末科举制度已经取消了。他的课我现在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周敦颐的《爱莲说》,还有龚自珍的《病梅馆记》,这两篇文章为什么记得那么的清楚呢?可能是由于后来也还不断的碰到这两篇文章的介绍,等于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吧。这些先生对我在文字学的功底上,应用学的功底上影响都是相当大的。比如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在这个地方不能读成“zhì”,应该读“chì”。再比如说什么“鲜为人知”的“鲜”应该读“xǐan”,绝对不能念成(xīan),这些在中学一年级的时候我都已经熟知了,不成为问题了。所以我有时候就想,不知道现在这些个主持人他们的中学教育是怎么学的呢?竟然还有念“(xīan)为人知”的。怎么会是这样呢?这才多少年呢?从这点来看,传统文化真是令人有些担心。从初二到高一的这三年的国文学习是一位叫王荫农的先生。他是北大国文系的毕业生。讲课很生动,很幽默。这位老师根据当时课程的规定,中学二年级开始就从《诗经.伐檀》讲起,《书经》讲的是《汤誓》……这情形多少年了也不会忘。从《诗经》《书经》这么下来到汉代的《乐府》,再到后来的《古诗十九首》,再到后来的《唐诗宋词》,《元曲》一直讲下去,这位老师就这么一个一个的跟我们梳理下来,跟我们讲解。到了高二高三,是一位叫裴汇川的老师跟我们讲“国文”课。这个人的学名叫裴学海,字汇川。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位老先生学问很大,我们也知道他是个文字学家,文字音韵,碰到的问题他都会说……但是这位老师的学养深厚我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有所了解,当时我在北京书店看到他的一本著作,叫做《古书虚字集事》。看了里面的序言,才知道他是清华国学院的学生,清华国学院里良好的学术氛围给这位先生以很好的熏陶。比如说,有一次裴老师上课举例子,讲到一个农民牵着一头马,有人问他,“你干什么去”?他说:“我饮(yìn)马去”。就是饮水的饮(yín)。就是带着马到河边喝水去的意思。但是这个“饮”字在这里就不能读第二声(yín),要读第四声(yìn)。这个例子给我以很突出的印象。所以说是这些老师在我中小学的时候就给我奠定了扎实的文学文字基础。后来在有一次的史学会上有人扯起汉字多音的问题,我就扯到《汉乐府》有一篇叫做《饮马长城窟行》,我就发表了我的意见,我说这个应该在这儿读声调的第四声(yìn),而不能读声调的第二声(yín)……冯文慈先生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给笔者的感觉就好像,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七十多年前,而是在昨天。
三、微观细腻眼界高远
笔者在近距离接触冯文慈先生时,真切的感受到了冯先生的微观细腻,眼界高远的学术态度。先生可以为一个标点符号这样的微小的问题写一篇论文。比如说:先生在谈到他与挚友史学家黄翔鹏先生的关于中国古代文献上提到的“九歌”解释的标点符号问题。黄翔鹏先生对“九歌”的解释的标点是这样划分的:昔彼九冥,是与帝辩同宫之序,是为“九歌”。而冯先生却认为黄先生错了,应该是这样划分:昔彼九冥,是与帝《辩》;同宫之序,是为“九歌”。最后经过冯先生的考证,证明冯先生的标明是对的。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说明了先生治学严谨,微小的问题也不放过的学术态度。同时,先生对待学术,对待知识,却是眼界高远的。在访谈中,冯先生讲到他撰写《释“宫商角徵羽”阶名由来》一文时的感受,他说:《释“宫商角徵羽”阶名由来》,就是解释“宫商角徵羽”是怎么来的。主要的看法是,根据天上星宿的名称来的。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带着点创新性。是过去史学家,音乐学家没有解决的。郭沫若这个大史学家在他的文章里,曾经提到他说不知道这五个名是怎么来的。音乐家王光祈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好像是从西方语言发音上来判断,是不是从“a”“o”“i”“e”这些字母的发音得来的,当然他也没有说出文献的依据。当时正好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很多文物,除了最著名的曾侯乙编钟之外,还有其它的。我记得有一个箱子,这个箱子上就画着中国古代的星宿,就是星座的示意图,还有名称,这二十八宿就在上面画着,在一个箱子盖上画着,我记得当时看到的资料上标注:这是我国已经发现的最早的星宿图,最早的星宿名称的记载。对于这样的资料,一般的音乐人是无暇顾及的。但是我一直遵循着这样一种治学原则,就是,搞音乐学的人的眼界必须要寛,你不寛,你就没有办法掌握一些材料,你眼界宽,多看些资料,多掌握一些额外的与音乐无关的知识是很有必要的。日积月累。必定会有很重要的收获。我当时大概是在《文物》这一类的杂志上看到的关于二十八宿图这样的资料。因此我后来在考虑到这个音阶阶名来由的时候,就把这个材料用上了。
冯先生说:一个音乐学教师或学人,可能像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布道者,将音乐文化的福音在大地上广为传播;他(她)又是一位佛门的大德高僧,拈香祈祷,要用音乐文化普渡众生,促成美、善、真境界的临近,而并不渴求个人的福祉;他(她)有时自然也会暂时忘却世俗烟火,沉醉于出神入化的精神境界,无论是西方的所谓“上界的语言”,或是本土的弥漫着泥土芳香的“原生态”,都可以使他(她)坠入恍恍惚惚、物我两忘的美妙境界,似乎是实现了道家的飞升。冯先生这样来诠释音乐学教师或音乐学学人的形象,富有深刻含义,十分生动精彩。冯先生在音乐学教学和研究领域就是这样一位不事张扬,默默耕耘,坚持不懈,不图回报的“大德高僧”。先生就是我心目中的“大德高僧”,给我以榜样,激励着我在音乐学的事业上努力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