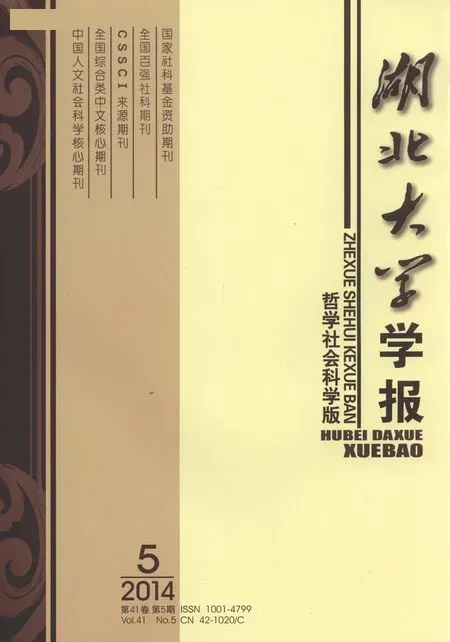论唐代经史编撰与佛经翻译的互动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100871)
论唐代经史编撰与佛经翻译的互动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100871)
唐代是中国史学、经学承前启后的一个时期:在史学方面,官修正史大放异彩,实现了从私人著述到政府修撰的决定性转变;在经学方面,《五经正义》的编订体现了与汉学、宋学不同的面貌,起到了过渡作用。学者们对此已多有关注。然而,唐代文治的另一项事业却往往被人忽视,即佛教译场的佛经翻译实践。其时,佛经翻译与史书修撰、经疏编订不仅在时间上一致,在参与人员的构成上也多有重合。从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开始,至唐佛经翻译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译场的分工合作或多或少影响了唐代集体修撰的风气,而佛经义疏的编写也与隋唐的儒经注疏互为映照,体现出折衷取长的倾向,二者之间存在深刻的互动关系。
唐代;经史编撰;佛经翻译;互动
唐朝刚结束从魏晋以来的分裂局面,高祖、太宗便着手对前代文化成果进行总结,组织了大规模的编修工作。武德五年,高祖下诏萧瑀等修魏、周、隋、梁、齐、陈史。贞观二十年,太宗又下诏房玄龄等修《晋书》,继承高祖的修史事业。贞观十二年,为了对魏晋南北朝以来儒学的新发展做一整合,太宗诏令孔颖达等编修《五经正义》。时至今日,唐初编修的《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依然是研究此期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而编订的《五经正义》则代表了与汉学、宋学截然不同的经学面貌,反映了从魏晋南北朝直至唐初的儒学发展概况。
然而,对于唐初集体编修的成果,历来便有许多争议。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就曾对《五经正义》加以指摘:“官修之书不满人意,以其杂出众手,未能自成一家。唐修《晋书》,大为子玄呵诋;梁撰《通史》,未见一字留遗;《正义》奉敕监修,正中此弊。”[1]141~142连带着批评了梁武帝所修的《通史》、唐初所修的《晋书》。刘申叔在《国学发微》中也指出《正义》的两大缺点:一是仅“守一家之注”[2]36,他注并废;二是取先儒旧说,“无一心得之说”[2]37。刘氏所指出的第一点未免是对前人求全责备了。第一,历经魏晋南北朝的数次战乱与书厄,多家之注已经亡佚,难以得见[1]139。第二,注家繁琐,已不再适应现实的需要。知识无限制的膨胀,必须做一决断取舍。《周书·儒林传》记载:“樊深经学通赡。每解书,尝多引汉魏以来诸家义而说之。故后生听其言者不能晓悟,皆背而讥之曰:樊生讲书多门户,不可解。”折衷众说,取定一家已成为迫切之务。第三,“守一家之注”,参考别注,或许是借鉴了六朝以来僧徒对同经异译的处理方法。牟润孙先生指出,日本有六朝写本《礼记子本疏义》残卷,“子本”之说或取自僧徒而有所变化[3]2。支愍度《合首楞严经记》:“今以越所定者为母,护所出为子,兰所译者系之。其所无者,辄于其位记而别之。或有文义皆同,或有义同而文有小小增减,不足重书者,亦混以为同。”佛经的义疏在当时大为兴盛,可被视为显学,影响到儒士解经也不足为奇。将时代风气归咎于一人,恐怕有失公允。刘氏指出的第二点“无一心得之说”,大约还是因为皮氏所指出的“杂出众手”的缘故。毕竟,要有心得,必须有独断之功,以一己之意贯穿于著述的终始。而唐人著述,往往采取集体合作的模式:“盖唐人之学,富于见闻而短于取舍,故所辑之书不外类书一体。《括地志》者,地学之类书也;《通典》者,史学之类书也;《文苑英华》者,文学之类书也;《法苑珠林》者,佛典之类书也。”[2]38末了,刘氏也不忘对唐初史学一并批评:“唐人修《晋书》、《隋书》,亦多出勦袭。”[2]38
虽然对唐初集体编修的成果多有批评,但以上两位学者都敏锐地看到:唐初集体修史与集体编定《五经正义》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联系。不过,一时风尚所及,未必仅止于文史创作。从贞观三年起,便有宰臣监护佛教译场翻译的先例:波颇译场,搜扬十九人参与,房玄龄、杜正伦监译,萧璟检校百司供给。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并不意味着逻辑上的影响关系。不过,既然同属太宗、高宗两朝的文化盛事,参与人员上又有交叉,两相比照来进行考察,或许会有新的发现。下文便结合汉地的文史传统与佛教的译场实践,拟对唐初的集体编修模式及儒家经典注疏体系进行探讨。
一、从历时的个人修撰到共时的集体合作
汉代以前,中国传统的著书模式大体是一种纵向的线性结构。或者是在某一类别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由一集大成者对先前的成果进行整理总结。所谓的“作者谓之圣,述者谓之明”,孔子即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他删《诗》、辑《尚书》、定《礼》《乐》、作《春秋》、撰《易》传。或者是由某一学派的后学者对先师的学说、言行进行记录发挥,代代传递,最后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文本面貌。先秦的子书便是这样形成的,如《孟子》、《荀子》等。或者是由王侯卿相组织门客对当下的知识进行整合撰录,如《吕氏春秋》与《淮南子》。到了汉代,私家著述增多。从贾谊、扬雄到司马迁、班固,或是独自立说、或是继承家学,目的都是为了“成一家之言”。随着书籍的增多与知识的累积,产生了编写类书的需要。魏文帝曹丕命王象、刘劭等编修的《皇览》为中国历史上有案可稽的第一部类书。概而言之,这种写作模式遵循的是一种时间上的历史传承原则。虽然也是集体的智慧,但更强调个人的能动性。即使是同时成于众人之手的《吕氏春秋》《淮南子》与《皇览》,也是由于文献本身的杂烩性质才要求多人的合作,并且未有明确的分工。
汉代虽也有石渠阁、白虎观的经学大辩论,最后由皇帝定夺、统一经义,形成的《石渠议奏》与《白虎通义》。但是有多人参与未必就是集体合作。相反,这两次辩论都是为了消除杂音、统一经学,从而让儒学更好地承担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就是说,会议上争论的都是经师家法,以取定一尊。汉儒最大的特点就是严守家法,而家法说到底便是知识在时间轴上的线性积累。同为解释《左传》,说公羊者与说谷梁者绝不混淆,互相之间攻讦辩难,虽也相争相长,但几乎没有主动合作的可能。
东汉末年,郑玄说经时调和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形成经学小一统的时代。儒士们再也不用限于家法的藩篱,互相之间的合作变得可能。然而,其间也是充满波折与翻覆。仅以古代帝国最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编订礼乐为例。《南齐书·礼志》追溯了从曹魏至南齐的修礼历史:曹魏王粲、卫觊创定朝仪,吴国由丁孚编采汉制,蜀国则是孟光、许慈草创众典。前二者史无明文,具体的过程已不得而知。但《三国志·蜀书》对孟光、许慈二人的事迹却记载颇详:
慈、潜并为学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值庶事草创,动多疑议,慈、潜更相克伐,谤讟忿争,形于声色。书籍有无,不相通借。时寻楚挞,以相震攇。……(孟光)好《公羊春秋》而讥呵《左氏》,每与来敏争此二义,光常譊譊欢咋。
由这段记载推测:所谓的“孟光、许慈草建众典”,不过是相互之间争论家法罢了。晋初由荀顗主持修订晋礼,任恺曾经谘问,后经挚虞改定;其他羊祜、庾峻、应贞等人的职责不明,大约是荣誉备员而已。据《南齐书·百官志》所载,刘宋一代曾以总明观代替国学,分“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正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干一人,门吏一人,典观吏二人。建元中掌治五礼”。建元为齐高帝萧道成的年号,可见南齐立国之初,制定典礼是以总明观为核心的。永明三年①徐勉的《上五礼表》作永明三年,《南齐书》卷九《礼志》作永明二年。据《南齐书》卷二十三王俭传,永明三年省总明观,于王俭府邸开学士馆,并将四部书移至俭家,故而此处定在永明三年较为合理。,省总明观,诏王俭制定新礼,将总明观一干人事都原封不动移至礼乐学士职局:“立治礼乐学士及职局,置旧学四人、新学六人,正书令史各一人,干一人,秘书省差能书弟子二人。”而根据《梁书》的说法,治礼乐学士、职局并非一开始即设立的:“尚书令王俭受诏撰新礼,未就而卒。又使特进张绪续成之,绪又卒。属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让胤,乃置学士二十人,佐胤撰录。”从这段记载来看,梁朝“治礼乐学士及职局”的设立,一方面既受到宋齐制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萧子良的干涉在其间起作用。而由玄儒文史四科发展到治礼乐学士局,即由异质的、松散的名义上的合作发展到有机的、实质上的合作,或许便是萧子良的功劳。萧子良本人深受佛教影响,那么,这种制度上的变革创新背后是否有佛教的因素呢?
佛教译场在翻译佛经时,由于本身工作的性质,从一开始便有分工合作的精神贯彻其中。有口头翻译的环节,有讨论文义的环节,还有笔头润饰的环节。译场中这一文本生产的方式也影响到了佛经注疏的编写。梁武帝萧衍曾撰《大品经疏》,在其序言里声称:“朕以听览余日,集名僧二十人,与天保寺法宠等详其去取,灵根寺慧会等兼以笔功。”法宠等人的职责或许相当于译场里的证义,与著书者讨论义理;而慧会等人的职责则类似于笔受、润文,负责对文本进行润饰加工。隋代智顗奉炀帝之命著《净名经疏》,秘书监柳顾言、著作郎徐仪负责文义。徐仪为徐摛之孙、徐陵之子,其文采可以想见。随着译场现象的兴盛及佛经的广泛传播,这种著书方式的影响还波及到世俗书籍的撰录。梁武帝还撰有儒家类经典《五经讲疏》与《孔子正言》。在编撰过程中,他专门命令孔子祛检阅群书,以为“义证”。此处的义证,与“证义”仅顺序不同,其职责也应与译场里的证义大致相当:均是考察文本的义理,确保与其他的经典没有抵牾之处。
到了唐初编定《五经正义》,不仅有明确的分工与工序,参与人员也大为增多,而不单是师傅带徒弟的模式。根据《新唐书·艺文志》的记载,《礼记正义》的编撰者有国子司业朱子奢,国子助教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頵,魏王参军事张权等六人;而《尚书正义》则历经了编撰、覆审、刊定三道环节,记录在案的刊定者更是有二十一人。显庆元年,参与《周易正义》、《尚书正义》编修工作的于志宁,监管玄奘译场的译文润色。而参与编撰《礼记正义》、刊定《尚书正义》的范义頵则助知翻译。可见,佛教译场的翻译工作与《五经正义》的编撰事业之间还有人员的重合之处。
而唐初的史书编修,以《晋书》最有代表性,包括太宗李世民在内至少有二十二人参与著录。虽然古代的史官建制早就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内史、外史的区分,但由不同史官记录的史料会以不同的文本呈现出来,如左史记言成《尚书》,右史记事成《春秋》。在唐代以前,真正由多个史官分工合作、著成一部史书的例子比较少,且结果都不如人意。如《东观汉记》,由汉明帝下令修撰,历经几代史官的前后数次续编,体例杂芜、内容残缺,在范晔的《后汉书》盛行后逐渐散失。三国时期,曹魏与孙吴政权都曾组织史官编修本朝历史,起初由多人合作,却历久无成,最后是王沈、韦曜独终其事,编定《魏书》与《吴书》。概而言之,唐以前的历史书写以私家著述为主流。若是官方组织多人合作,最后往往因体例不一而沦为史料的杂烩,还是需要后代的史家加以整合。如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史记》,班彪、班固父子的《汉书》,范晔融汇《东观汉记》的《后汉书》,陈寿整合《魏书》、《吴书》的《三国志》,均是个人玉成其事。而到了唐代以后,正史则均为官方组织编写,由多位史官分工合作。
唐代的史馆制度可上溯至北齐,首创以大臣监修国史的制度。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以僧官、大臣监管译场制度的萌芽。天保初年,高隆之监国史[4];天保七年,那连提黎耶舍到邺城,“敕昭玄大统沙门法上等二十余人,监掌翻译”(《大正藏》册50,页433)。此为译事由朝廷派遣人员监护始末的开端,之前后秦姚兴虽曾对晋公姚爽“任以法事”,但并非正式任职,也未形成制度。入隋之后,那连提黎耶舍的译事由“昭玄统沙门昙延、昭玄都沙门灵藏等二十余僧,监护始末”(同上)。不过,此期的北周却是由重臣监护翻译。保定四年以后,阇那崛多等于长安四天王寺为冢宰宇文护翻译佛经,大将军侯伏侯寿总监检校。其后唐代以大臣萧璟、房玄龄等监护译场的惯例,应该是沿袭了北周的经验。就此点而言,译场总知监护的设立,似是受到当时修史制度的影响。而以亲信大臣监修国史,原本是北朝统治者控制意识形态的一种手段[5]412~414。与官方修史类似,北方佛教译场的官方化(政府组织译场)也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统一历史观念也好,控制译场的翻译也好,目的都是为了皇权服务。因此,二者在制度上互相有所借鉴也不足为奇。
此外,受诏修撰《晋书》的人员中不仅有史学人才,而且还有不少文学之士,如崔行功便是因其文藻而入选。《旧唐书》对此现象颇有微词:“然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六朝隋唐时重视文学的风气使然,另一方面可能也受到译场中设立“润文”之职的影响。唐太宗于贞观二十年下令编撰《晋书》,历时三年,于贞观二十二年完工。而玄奘于贞观十九年春从印度回到长安,三月奏请太宗支持建立译场,六月人员召集完毕开始译经。二十年二月开译《瑜伽师地论》,由许敬宗监阅,至二十二年五月完工。也就是说,《晋书》与《瑜伽师地论》的成书约在同一时间,而参与人员也有重叠之处,如许敬宗等。唐代以文臣监阅译场译经的笔功,从贞观初年开始便有这一传统。如波颇罗那译经,就有左仆射房玄龄、赵郡王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伦、太府卿萧璟等人监阅详辑。《晋书》的修撰网罗了大批史学、文学之士,最后由敬播、令狐德棻、阳仁
卿、李严等四人汇总其事。而到了显庆元年,高宗又将参与修撰《晋书》的来济、许敬宗、薛元超、李义府等四人拨调给玄奘担任译经的润色监阅。
概括说来,唐初的经史修撰工作与译场的佛经翻译既有时空上的平行性,又有人员之间的互相交叉。二者同属唐初统一思想意识形态的文化运动,故而在运作模式上有相通的地方。这一编修、翻译工作的涉及面之广、参与人员之多,可谓中古时期的一大盛事,对后世影响深远。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佛教译场的实践,此时还是会自然发展出集体合作的著述形式。毕竟,随着知识的积累,以个人之功欲穷其边界已不太现实,势必会产生分工协作的需要。然而,既然有了译场几百年的集体合作经验,就更能丰富本土原有的协作方式。二者之间互为影响、互相借鉴,共同发展出成熟的集体修撰模式,以开唐朝的文治之鼎盛。
二、从固守家法到分章析义、融合众长
《隋书·经籍志》批评儒学的现状:“陵夷至于近代,去正转疏,无复师资之法。学不心解,专以浮华相尚。豫造杂难,拟为雠对。遂有芟角、反对、互从等诸翻竞之说,驰骋烦言以紊彝叙。”“芟角”“反对”“互从”三个关键词均为佛教术语,意指佛教的各种论难方法[6]。大约可以推测:魏征等人的这段批评针对的是儒家义疏所受佛教义疏的影响。大体说来,儒学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东汉之末,郑玄调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此后便无法谈及纯粹的师承关系了。而为何到了“去正转疏”时代,再次混淆师资传承呢?
义疏之体例,源自佛教讲经,因此在形式上多受佛教注疏影响[3]55~59。佛教的义疏之学虽然发端于道安,但道安的经注与后世义疏毕竟有所不同:“寻文比句,为起尽之义,及析疑甄解。”(《大正藏》册55,页108)由于没有流传后世,故而无法窥见其具体的内容,但想来与汉儒的章句之学更为接近,只是加上了科段的元素。而义疏重在疏通文义,大规模的著述似乎要到鸠摩罗什主持译场的时期。罗什在翻译的同时进行讲解,其译场弟子往往结合老师的解释与自己的理解,融汇成为注疏。如道融“所著《法华》《大品》《金光明》《十地》《维摩》等义疏并行于世”(《大正藏》册50,页363),昙影有《法华义疏》与《中论注》,道生“诸经义疏,世皆宝焉”(同上,页367),僧导有“《成实》《三论》义疏”(同上,页371)。此外还有间接受学于罗什译场的再传、三传弟子等,如僧镜“著《法华》《维摩》《泥洹》义疏”①《高僧传》卷七僧镜本传记载:僧镜于元徽中卒,春秋六十有七。元徽年号使用了四年,即从473年至476年,则僧镜生于406年至409年之间,曾入关陇寻师授法。从他的所学来看,属于罗什译经系列,应该是从罗什后学所传授。(同上,页373),法瑶“著《涅槃》《法华》《大品》《胜鬘》等义疏”②《高僧传》卷七法瑶本传记载:“河东人,少而好学,寻问万里。宋景平中来游兖豫,贯极众经,傍通异部。”景平年号仅使用一年,即423年,他此时的学问形态已颇为成熟,故而其求学阶段定在413年左右比较合适,而此期正值罗什在关中译经的末期,很有可能他便参与了盛事。汤用彤先生在《魏晋南北朝佛教史》讲述法瑶的一节内容中推测他可能是道凭的弟子,即罗什的再传,亦很有可能。(同上,页374),昙度“撰《成实论大义疏》八卷,盛传北土”(同上,页375),法安“著《净名》《十地》义疏”(同上,页380)。
此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前人往往将佛教注疏的科判法归功于道安③如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牟润孙《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然而道安仅指出了序分、正宗分和流通分的区别,实在是处于非常初级的萌芽阶段。真正将科判方法发扬光大的恐怕要属罗什译场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们。第一代弟子中:道融讲新《法华》开为九辙,隋代吉藏已明确认可其为“科章门”;昙影讲《成实论》,恨其支离,结为五番;慧询讲《十诵律》,“更制条章,义贯终古”(同上,页401);僧肇著《涅槃无名论》,开十演九折;道凭讲《法华》时,也是“取天亲意,节目经文”(《大正藏》册34,页1)。这里指出了科判方法的来源,《法华义疏》中也明确说明:无论是天竺还是震旦,讲经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分章段,另一种则是直接解释。前者的代表是天亲,后者的代表则是龙树。“天亲解《涅槃》有七分,龙树释《般若》无章门”(同上,页452)。可以说,这一群体已经在很自觉地实践天亲传下的科判之法了。第二代弟子中:法瑶继续“科分大经章段”(《大正藏》册46,页781);僧镜“区别义类,有条贯焉”(《大正藏》册50,页373)。由此可知:儒家注疏中科段之法的来源,与其说是道安的注经讲经,不如说是罗什译场的翻译讲解实践,而归根结底则可追溯至印度天亲(玄奘译世亲)的解经法。
接下来,本文要探讨的是:为何义疏体例会“无复师资之法”呢?这主要还是跟佛经译场的翻译实践有关。
其一,义疏是糅合同一译场中不同人员的注记而成。译主虽只一人,听讲的笔受、证义却人数众多,各自都带着不同师承背景的印记,对同一经文的理解便会迥异,《注维摩诘经》中所引罗什、僧肇、僧叡、
道生、道融诸人的理解各各不同,即可为证。这样,他们由听讲笔记加工成的义疏也会各不相同。然而,由于是出自同一译场,文本性质上有一定的相似度,好事者往往为图方便而将其整合在一起。《法华经义疏序》声称:“昔者姚秦什公亲翻妙经于震旦。上足僧融创开九辙,叡、生等林立诸曹,相继而有著作。在齐之时,刘虬居士共十名僧,务捃舆师之异言,撰为《注法华》。”若以此则材料来看,魏征等所批评的“去正转疏,无复师资之法”便很好理解了。若以罗什的讲解为师法,那么各大弟子的注疏便是家法。以汉儒的注经传统,源流必须泾渭分明,丝毫不可含糊。而刘虬等人居然“捃舆师之异言,撰为《注法华》”,混合各家之说,实在是大逆不道,并未严格遵循师资传统。或许是由于个别的注疏单行实在麻烦又不便检阅,故而历代都有混合注疏的传统。唐代道液便有《净名经集解关中疏》,将罗什、僧肇、僧叡、道生、道融等人的注汇集在一起。僧肇的《注维摩诘经》便是混合了五人注记的产物,前文已经提及。日本东大寺沙门凝然《维摩经疏菴罗记》卷第十三有言:“昔震旦国,罗什三藏翻译此经,即作经注,是别部也。僧肇法师亦别作注,道生法师亦别作注。三注别部,各行世间。后人聚集一处,次第载安。三注总为一部,即成八卷。”[7]67解释了《注维摩诘经》的文本历史,不过不是三注而是五注。
其二,义疏是糅合各个译场的译本、注疏而成。如李俨的《金刚般若经集注序》:
然流支翻者兼带天亲《释论》三卷,又翻《金刚仙论》十卷。隋初耶舍又翻无著《释论》两卷。比校三论,文义大同。然新则理隐而文略,旧则工显而义周。兼有秦世罗什、晋室谢灵运、隋代昙琛、皇朝慧净法师等,并器业韶茂、博雅洽闻。耽味兹典,俱为注释。研考秘赜,咸骋异义。时有长安西明寺释道世法师,字玄恽。德镜玄流,道资素蓄。伏膺圣教,雅好斯文。以解诂多门、寻覈劳止,未若参综厥美、一以贯之。爰掇诸家而为集注,开题科简同铭斯部。勒成三卷,号为《集注般若》,兼出《义疏》三卷、《玄义》两卷。
此序前文还指出了《金刚般若经》的五个译本:罗什本、菩提流支本、真谛本、佛陀耶舍本①李俨所录有误,隋代的译本应为达摩笈多翻译。、玄奘本。接下来便是引文中的三部解释性论著,又有四个注本。道世为了简便起见,计划将所有这些文本汇集成一个标准的集注本,并将自己折衷整合的意见著成《义疏》与《玄义》。这样成书的《义疏》,想在其中寻找罗什、谢灵运、昙琛、慧净的观点,恐怕如同要在盐水中找盐一样困难,如何谈得上清晰的师资脉络?当然,还存在另两种情形:一是义疏开始便经由众人之手而成。梁武帝曾令道生、僧亮、法瑶、昙济、僧宗、宝亮、智秀、法智、法安、昙准等十人撰《大般涅槃义疏》,除此十人外,疏中还引用昙纤、昙爱、道慧、慧朗等多家说法,总共七十二卷[8]389。二是义疏虽有单独的著者,但却是采合众师之说所成。这与齐梁以来佛教讲肆的发达有关。如慧基用了四五年时间“游历讲肆,备访众师”(《大正藏》册50,页379),以此著出的《法华义疏》必然是融合众师的讲解得来。其弟子慧集“遍历众师,融冶异说”(同上,页382),著成《毘昙大义疏》十余万言,盛行于世。正是由于义疏的杂糅性,所以无法从中清晰地整理出师承脉络,也可见佛教译场译经活动的影响之一斑。
[1]皮锡瑞.经学历史[M].周予同,注释.北京:中华书局,2004.
[2]刘师培.国学发微[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3]牟润孙.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M]//张曼涛.现代佛学大系:第26册.台北:弥勒出版社,1984.
[4]牛润珍.北齐史馆考辨[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4).
[5]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0.
[6]范晶晶.对《隋书·经籍志》经部后序一段评论的解读[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2).
[7]何剑平.中国中古维摩诘信仰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9.
[8]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黄文红]
B94;K242
A
1001-4799(2014)05-0143-05
2014-01-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资助项目:14CWW025
范晶晶(1984-),女,湖北黄冈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佛经翻译、印度文学研究。
-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略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基础
- 从“人口治理”到“关怀自身”
——资本、权力与生存美学 - 论晚清时期文官保举的基本特征①关于中国清朝保举制度的研究,无论是通史性,还是断代性的,学界已经有了不少著作,或涉及或设专章进行研究。如李铁的《中国文官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对中国古代的文官选用、保举、考绩、监察和惩处等进行了分析。陈茂同在《中国历代选官制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设有“荐举论”专章,认为保举是重要的选官途径,区分和确定了保举类型及标准,分析了保举的利弊。宁欣清晰勾勒“选举”制度变迁脉络,对中国的选人、任官制度进行了论述,其中包括了清朝的用人制度(《中华文化通
- 德沃金对罗尔斯分配正义理论的批评与发展
- 从协同正义看罗尔斯、诺齐克之争
- 德性伦理的启蒙话语
——休谟德性理论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