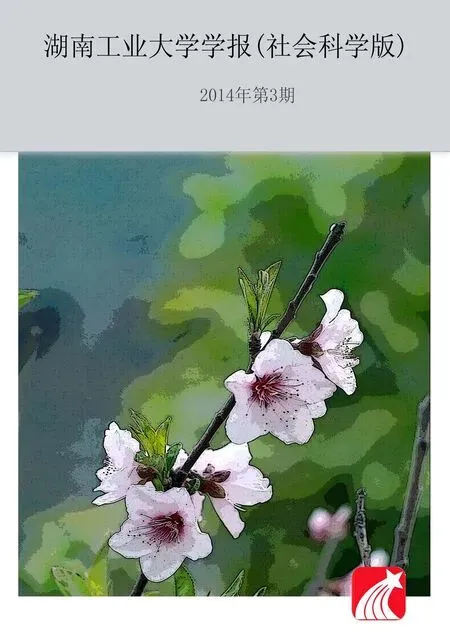地方性写作视域下的“新湘语”诗歌
吴投文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进入新世纪以来,湖南的诗歌在发生新的变化,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湖南诗歌的地域性特征开始引起诗坛的广泛关注,地方性经验在湖南诗人的创作中成为一个鲜明的风格性印记。湖南的诗人往往显得非常低调,在他们的血脉里跃动着一种特殊的楚人气质,他们的创作在寂寞中显出沉实的底蕴,以一种不事声张的写作姿态进行纯粹的艺术创造,彰显出独立的形象。一般地看,湖南的诗歌存在着被低估的情形,但在互联网语境下,原来的遮蔽也有所淡化。在新世纪以来湖南涌现出来的几大本土诗群中,“新湘语”在创作风格上最能代表湖南诗歌的地方性特色,对新世纪以来地方性写作的兴起具有某种先导性的影响。大体上说,这是一个以“口语诗”为主导风格的创作群体,不过,与国内诗坛流行的“口语诗”形成对照的是,“新湘语”诗歌是一种地方性的“口语诗”,具有非常鲜明的湖湘地域文化特色。
“新湘语”诗歌最初的集结性出现是在2000年,当时金色山庄、七窍生烟、研磨机、横、玄子等湖南诗人经常到杨黎主持的“橡皮”论坛贴诗,受杨黎的影响,他们所写的都是口语诗。后来“橡皮”论坛关闭,他们谋划着打出“新湘语”的旗号,以湖南的口语诗人为主体申请了一个免费的网络论坛,这就是2003年开张的“新湘语”论坛。这个网络诗歌论坛是“新湘语”诗群的主要集结地,比较活跃的诗人有金色山庄、七窍生烟、当、研磨机、横、黄二、哦该、紫梧、折勒、车攻、阿披王、米汤、用轻功、玄子、刘双红,等等,都是湖南土生土长的诗人。在湖南本土诗人之外,也有一些外省乃至海外的华裔诗人加入到“新湘语”论坛中来,这些诗人可以看作是“新湘语”的外围,这些诗人是宋晓贤、徐小爱克斯、余毒、阿斐、风妞妞、阿谁、Liawst、一莲,等等。与湖南本土诗人一样,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强调诗歌写作的地方性,追求诗歌语言上的实验性,往往把个体的情感体验用富有地方色彩的语言表现出来。此外,“新湘语”诗群的写作也有某种复杂性,一些诗人把现代性经验融入到个体的生命体验中,表现出果决的先锋性的写作趋向,与充满地方性经验的写作相映成趣。“新湘语”诗群举行过一些内部诗歌活动,经常有小范围的同仁性的聚会,2008年出版过一部500余页的诗选《新湘语》。这本“新湘语”诗选主要收录“新湘语”本土主力诗人的作品,金色山庄、七窍生烟、当、研磨机、横、黄二、哦该、紫梧、折勒、车攻、阿披王、米汤等本土诗人都有大量作品收入该书,“新湘语”外围诗人的作品也占一定的篇幅,杨黎、金色山庄、黄二等人写的一些评论文章和诗学随笔也收入其中。这本“新湘语”诗选可以看作是对“新湘语”诗群创作一个阶段性的总结,里面包含着一个谱系性的结构,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新湘语”诗群有明确的创作主张,按照“新湘语”主力金色山庄(庄宗伟)的说法,就是要写出“我们理想中的新湘语诗歌”,具体表现为“介入当下场景的独特视角、对母语(也即当代湘语)的独到把握、非常空灵的(也即诗意的)述说方式、平民式的浪漫”,[1]529要求诗歌“小说,小声地说”。[1]531“新湘语”诗群的写作比较接近“民间写作”的立场,对诗歌的“宏大叙事”充满厌倦,追求把诗歌的在场感、民间性和个性化统一在日常生活的诗性视野中,把看起来毫无诗意的日常生活转化为平民式的浪漫。诗群中的几位主力,如金色山庄、七窍生烟、横、哦该和研磨机等人都很认同杨黎的“废话写作”,他们的创作往往抽离“意义”对生活本身的遮蔽,凸显出日常生活诗性的然而又是琐碎的“无意义”状态,这与杨黎有某些一脉相承的地方。不过,真正构成“新湘语”诗歌自身特色的,还是在于“湘味”的呈现和地方性特色的发掘。“湘味”体现在极具特色的“母语”上,也体现在诗歌描述的对象上。大量的当下场景和即时性体验进入诗歌,这些场景和体验都是亲切可感的,大都显示出原生态的地方性特色,具有日常生活的内在诗性质感。[2]
金色山庄(庄宗伟)是“新湘语”理论的主要阐释者,也是“新湘语”诗群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的《走出围城的新湘语诗歌》是一篇关于“新湘语”诗歌最有代表性的论文,他在此文中这样界定“新湘语”:“新湘语,按其字面意思,应理解为新鲜的、活在人们口头的湖南话。”[3]这也是他自己的创作追求,他的诗歌具有浓郁的“湘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新湘语”诗群的主导风格。金色山庄的诗大都流连于生活的细微处,他往往能敏锐地在细微处发现日常的诗意和精彩,对宏大的事物充满怀疑和警惕,因此,他的诗是典型的“小说”,在“小声地说”中抵达自我的内心。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诚实的写作,在细微处并不回避生活的复杂性。他的诗纯粹、精到、近乎透明,对于日常诗意的捕捉具有惊人的敏感,以直接的方式呈现生活的复杂形态,对于生活的隐秘性质有独到的发现。他的诗《万年后的事情》是口语化的,却有一种高度抽象的意味,在时空的流转中揭示出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同时有一种神秘的况味,是一首难得的好诗。
哦该在“新湘语”论坛是一个活跃分子,他贴的诗可能最多,有时一天就可以贴十几首出来。另一个贴诗最多的诗人是七窍生烟,也是一溜烟的功夫就可以贴出几首来。当然,诗歌数量的多少对诗人并没有实质性意义,说到底还是要看诗的质量。哦该和七窍生烟都是有自己艺术立场的诗人,对写作是不肯马虎的,都追求把诗往某种高处写。可能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心中的高处,但哦该和七窍生烟心中的高处却和别人的有些不同,别人写别人的,他们写他们的,他们追求另开一途的写作。哦该的写作中有一些特异的因素,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写作印记,而且是“新湘语”的写作印记。比如他的一首《真的下雪了》:
昨夜的雪
在梦里
下了一晚上
今晚的雪
是真实的
不过
只在故乡的
马路上
斜斜地飘了
十分钟
哦该的诗与日常生活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几乎全从原生态的日常生活中掘来,以素朴、自然、诚实为基本特色,然而不是停留于日常的实写与描摹,而是“在司空见惯的日常状态中呈现出隐藏的诗意,以一种近乎自白式的晕眩与迷恋让人感动”。[4]对于诗,他的体认显得较为平实,但也许更贴近诗的本质,他曾这样表白自己的诗观:“诗就是诗,万物皆可入诗,主张反映当代生活,从客观具象进入,主观通过客观具象表现;反对主观入诗和抽象化的假大空式写作。”[5]他的这首《真的下雪了》一诗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把一场雪下得恰到好处,没有多余的语句,意象空疏却显得坚实,是对自己诗观一次极好的实验。
折勒的诗里似乎荡着一个恍惚的梦境,他的诗表面看来是写实的,其实有更深一层的用意。他用两个声音说话,一个是现实的声音,一个是梦境的声音,现实的声音是虚假的,梦境的声音才是真实的。如《斑斓大虎》里的荒诞梦境,不过是现实的辐射与转化而已,然而却不需要染指繁复的象征和运用过度的技巧,而是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呈现生活的本相。这只梦中出现的斑斓大虎是一种威胁性的力量,然而它并不比人更为可怕,诗人在惊慌中踢它一脚,这不过是发生在梦中而已,诗中有一种潜在的让人感到疼痛的紧张,指向梦境以外的世界。诗人在《故乡》一诗中写道:“一个人不能没有故乡,所以要离开此地”,这是让人感动的句子。诗人的故乡其实永远在梦境之中,也只有在梦境中,诗人的故乡才显得真实。折勒的诗表面上是柔软的,其实是质地坚硬的,有一种内在的锋芒促人思索。
车攻的诗似乎游移在现实与梦幻之间,想象开阔,句式特别,有一种内在的流动的气韵。《最后,只与一只苍蝇有关》一诗,在诡奇的背景中展开,海与苍蝇对比所形成的巨大差异具有喜剧性效应,诗人的言说以一种别样的方式表达出来,在具有荒诞性的呈示中含有一种峻急的拷问。诗人说:“在悬崖上我不得不/站得更加崇高一些/因南太平洋/而开始考虑一些博大精深的问题”,从中也许可以发现诗人某一方面的追求。车攻能较好地以艺术化的方式处理复杂的生命体验,以一个苍凉的手势掺杂异样的情绪,挽留生命中的过往事物,然而最后留下的却还是一个苍凉的手势和异样的情绪。
在“新湘语”诗群中,紫梧是一位富有才情的女诗人,她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新湘语”诗歌的纠偏和补救。紫梧有良好的古典文学素养,对中国古典诗词有特殊的钟爱,她的写作似乎是在古典诗词的参照中获得一份特别的文化皈依感,表现出对古典诗词意蕴的趋附和热情。紫梧的诗有着女性的细腻和古典的衷肠,连那一份忧愁的气味也似乎笼罩在唐宋时期的柔风细雨中。诗人用口语点化古典的意境,自有一份才情,却也失落在一个过去的时代里。《好望角》是现代版的鹊桥相会,《走过咖啡屋》和《女人的卷发》是古典式的廊桥遗梦,都在诗人的笔下翻成优雅的奇思妙想,把一份动人的感念停留在读者的心里。诗人把一份现代的心情撕成了两半,似乎在城市的广场放飞了李清照的声声慢。应该说,在“新湘语”诗群的口语化写作中,紫梧所找回的是一份特别的文化情怀,她的诗显示出女性的温婉和秀逸的气质,呼应了新世纪诗歌回归民族文化传统这一写作路向。
当的诗有着一种宁静与平和的调子,贴着日常生活的体温,往往以暖人的回味使人感动。他以一颗敏感的心和一双清明的眼向生活凝眸,从生活的细小处和纷扰的人事中发现隐含的诗意,绘出生活的光色与内心的波动,文字是地道的口语并杂以湖南方言,显出一种把生活当作诗的趣味哲学。他的诗对日常生活的介入在一个较为开阔的层面上展开,以叙事和对生活近乎陌生化的临摹作为基本的结构方式,这使他的诗在令人感到熟知的一面外,又感到惊异与新奇。他的诗《梦》是梦的实写,却不是梦的复制,在梦之外还有一个实在的世界,连着诗人内心的要求,驰骋在一片幻想的光影上。
用轻功的诗如他的名字一样,一招一式都用的是舒缓腾挪的轻功姿势,在柔缓中显出拳脚的功力。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在他的诗中似乎没有多余的细节,对于诗意“一刹那”的提炼和凝聚,他的轻功确乎是非常有效的。对情绪的精微把握和对情绪中那一点思理的点拨到位,是用轻功诗歌的一个重要特色。他的诗《户外》用寥寥几笔,把一种不可言说的心境放大和拉远,结末的两句看似调侃,却有悠长的韵味。《师大有条木兰路》和《南方县城的少妇们》把心中晃动的幻念和一瞬间的失神处理成一幅别致的图画,却又没有停留于画面的勾划上,似乎有着更深一层的隐秘,显出诗人难以测度的内心涟漪。
与金色山庄一样,在“新湘语”诗群中,七窍生烟也是一位重要的组织者,他的写作可能也最具代表性。作为一个从网络起家的诗人,七窍生烟在此之前已有一段相当长的创作历程,写的是那种看起来很纯美的诗歌,诗中的意象属于传统的一路,这种长时间的艺术积累无疑是他后来能够成功实现创作转型的一个重要前提。诗人易清滑曾在“新湘语”论坛上发过一个很长的帖子,题目叫做《讲述生活原汁的诗》,认为七窍生烟在开始网络写作后,诗里几乎淡到没有一个意象,甚至连一个形容词也没有,他的诗类乎一个人赤裸裸的日记,反映出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肉体与精神相会和碰撞的基本状态,显示出原汁原味的特色。这一概括自是一家之见,但确实切合七窍生烟网络诗歌的一些重要特点。七窍生烟的诗具有一种直接的在场感,口语的运用圆熟到位,往往能把日常生活的状态以接近本真的方式勾划在读者面前,诗人自己处身其中的生活环境和日常状态在诗中呈现出一个无处不在的诗性形象,因此,他的诗多呈现出温暖、明亮和素淡的底色。朋友和亲人的名字如此大量而繁复地出现在他的诗中,这是我感到奇怪的一个现象,却又感到这使他的诗散发出一种有着特殊亲和力的气味。同时,七窍生烟能较好地处理在场与不在场的关系,在日常生活的在场与不在场的诗性形象之间保持一种奇妙的平衡,通过在场的日常生活抵达其背后深层的诗性内涵和诗性形象,揭示出不在场的诗性本质更为可靠的真实性。他倾心于日常生活诗意的再造与转化,由此构成其诗中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的内在张力,从中可以发现日常生活隐秘的诗意和生活某一方面的玄秘性质,也由此显出七窍生烟诗歌的独特韵味。他的《完整与不完整的》一诗看似简单、直白,但在简单、直白之外,却有一种类乎混沌的真实感和对于生命存在具有直觉性的体认。七窍生烟的诗歌中有叙事性的一类,多把情节或近乎情节的事件在一个想象的空间展开,游离于梦幻与现实之间,如《一首伽太益帝国消失的诗》和《马达加斯加的千金子滕》等,则显出别样的情趣。七窍生烟的诗歌产量巨大,是喷发式的,也许适当的沉潜与节制是有意义的。他是口语诗的一员大将,在湖南开风气之先,影响所及,一批湖南诗人在口语诗写作上形成波澜之势,这是特别要提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优秀的“新湘语”诗人那里,还呼应着湖湘文化奇异诡变的内在魂魄,彰显出湘人骨子里的那种诗性浪漫。为凸显“新湘语”之“新”的地域文化特色,像七窍生烟和哦该等人还尝试用当代湘方言写作,或者把当代湘方言与日常口语杂揉在一起,形成一种具有多层次感的语言扩展性效应,可以带给读者某种新奇的语言体验。[6]尽管这种语言实验可能不宜推广,但作为一种地方性诗歌的语言技术路线仍然凸显出对诗歌语言的某种特殊理解,实际上延续着新诗草创时期刘半农等人的方言歌谣写作,不过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转化为一种隔代呼应而已。
在新世纪诗坛的地方性诗歌写作中,“新湘语”诗歌具有特殊性,在总体上显示出一种挖掘日常诗意、充分彰显地方色彩的创作追求。在有代表性的“新湘语”诗人那里,他们的创作似乎具有“目击成诗”的特点,往往出之于随意,信手拈来,却显出诗人的至情至性,从中不仅可以发现这些诗人基本的艺术选择,而且可以发现他们内心的洁净与轻微的波动。诗人的人生姿态是凡俗的,却在凡俗中显出诗意的光辉,另一面又是超然与疏离,在超然与疏离中抗拒现实的功利原则,还原内心的真实,接近诗人自己理想中的法则。这些诗歌的触须联结着生活的隐秘和诗意,在不经意中把一种人生的信守安置在心灵的最高处。这些诗歌的精神印记是充分个性化的,诗人对于生活的敏锐与敏感,在这些诗歌中以一种别样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新湘语”诗人中的多数,并不属于诗坛具有聚光效应的人物,然而他们沉默与充实的写作却处处显出一种踏实的品格。
“新湘语”诗群的写作在丰富中显出个性,每一个诗人的面孔出现在自己的作品中,也许像他们本人一样真实。平凡、自然与诚实是凡人的品质,也是艺术应当具有的品质。凡人的艺术似乎更应该执着于这种凡人品质的诗性挥发,与圣人或自命为圣人的高头讲章区别开来,但也不能落入琐碎的趣味和任性的自恋,把一己的天地放大成世界的全部,对于存在的基本承担和瞩目文化创造的诗性情怀应当也是凡人艺术的内在要求,而这恰恰是这一时代的艺术与诗歌的软肋所在。“新湘语”诗歌大约也属于凡人的艺术吧,属于真实、素朴和自然一路的创作,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丰富的世界,看到的是诗人对日常诗意的忠诚和湖南诗歌富有地方性的一脉,然而也有满足于趣味写作的琐碎和凡庸,在诗歌的内在品格上显出有过于虚弱的一面。
从总体上看,“新湘语”诗群迷恋“小说,小声地说”的艺术趣味主义,到底显得格局不大。一些诗人满足于日常生活原生态的复制性写作和对于日常生活的碎片式呈现,在一般读者看来,具有明显的非诗化倾向,也由此饱受争议。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热闹之后,“新湘语”诗群呈现出后继乏力的疲态,大概可以从中找到原因。“新湘语”诗群具有一定的网络号召力,对湖南倾向于口语诗写作的诗人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集结在“新湘语”诗歌论坛的诗人似乎都表现出某种特别的诗歌癖好,这对强化湖南诗歌的地方性特色是一个有力的推动。这种地域性写作无疑有利于形成湖南诗坛良性互动的诗歌格局,有利于新世纪湖南诗歌在诗坛影响力的整体提升。
[1] 庄宗伟.从新湘语到小说[M]//老庄,车攻,当,七窍生烟.新湘语.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8.
[2] 吴投文.湖湘文化的诗性抒写——当代湖南诗歌的整体考察[J].新文学评论,2012(3):97-108.
[3] 庄宗伟.走出围城的新湘语诗歌[N].湖南日报,2003-10-22.
[4] 吴广平.文学教育新视野[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174.
[5] 哦 该.地铁[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198.
[6] 吴投文.新世纪湖南诗歌概观[J].文学界·文学风,2013(5):3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