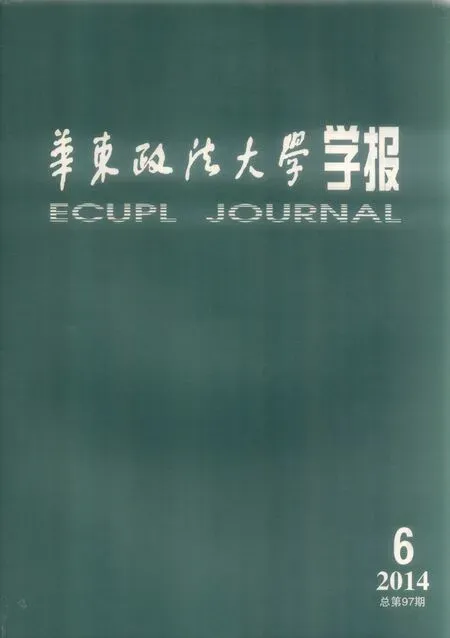法院地法适用的正当性证成
袁发强
国际私法中,作为系属公式和冲突规范的“法院地法”(Lex Fori)在各国立法以及涉外民商事司法实践中运用得并不多,但从各国涉外民商事司法审判实践的结果看,大量的案件最终都适用了法院地的民商事实体法(Forum Substantive Law or Local Substantive Law)。于是有学者就得出了晚近国际私法实践中存在法律适用的“回家去趋势”(homeward trend)的结论。〔1〕See Eugene F.Scoles,Peter Hay,Patrick J.Borchers& Symeon C.Symeondes,Conflict of Laws,§2(3d.ed.2000),pp.18-106.认为这不利于国际社会的正常交往和国际民商新秩序的建立;〔2〕参见李双元等:《国际社会本位的理念与法院地法适用的合理限制》,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另有学者以中国法院近年来公布的涉外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情况为例,对没有更多地适用外国实体法的现象提出质疑。〔3〕参见何其生、徐威:《浅析我国涉外民事法律适用中“回家去的趋势”》,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笔者以为,这不过是学界对适用外国法的理想主义热衷,而非现实的考察与评价。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考量、法院对最密切联系标准的理解、法院界定涉外法律关系当事人权利义务与裁决公正与否等对法律适用的影响应进行客观的分析。
一、法律适用的影响因素
(一)管辖权对法律适用的影响
从表面上看,除了“法院地法”这个系属公式外,任何一个抽象性连接点都存在适用法院地法和外国法两种可能,只有结合具体案情才能最终确定。那么似乎涉外案件法律适用的统计数据应该显示适用外国法与适用法院地法的比例大体相当,或者适用外国实体法的概率应当高于适用法院本地实体法的概率,但为什么统计数据却显示适用法院地本国实体法的情况居多呢?〔4〕李双元教授也承认:“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国家,对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法院地的法律来最终判决涉外案件的,无疑要比适用外国法判决的案件不知多了多少倍”,并认为“这也是不足为怪的”。参见李双元等:《国际社会本位的理念与法院地法适用的合理限制》,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要客观解释这个现象,不能仅从冲突规范本身出发,还要结合案件实际发生的情况考察。
国内学术界往往忽视当事人选择法院管辖在法律适用上的意义。当事人挑选在哪国法院起诉会考虑多种因素,如诉讼上的便利、管辖法院与争议中的法律关系有何联系、法院最终会适用何地法律做出裁判等。管辖法院的选择对最终法律适用的结果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跨国商事合同大多约定在英国的伦敦高等法院诉讼;即使合同中没有选择法律适用,英格兰的法院往往基于合同自体法理论选择适用英国法。〔5〕在英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官从推论当事人的默示选择意思出发,认为当事人在没有明确选择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时,选择管辖法院就隐含了选择法院地法的意思。无论学术界对“挑选法院”现象如何不满,当事人仍会出于利益的考虑进行选择。奇怪的是,鲜有国内学者统计英国法院受理的跨国民商事案件,并对英国法院大量适用英国法的现象提出批评。
在非商事关系案件中,选择管辖法院同样会影响法律选择的结果。例如,侵权案件的当事人选择在侵权行为发生地诉讼时,法院依据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的原则最后适用了法院地(同时又是侵权行为发生地)的实体法;有关不动产的诉讼在不动产所在地法院起诉后,法院适用了法院地(同时又是不动产所在地)的实体法;在涉外扶养案件中,被扶养人在自己住所地或经常居所地的法院起诉,法院依据有利被扶养人得到扶养的法律选择规范适用了法院地实体法;在涉外继承案件中,原告常常在遗产所在地法院起诉,而法院依据遗产纠纷适用遗产地法规范适用了法院所在地的继承法等。可见,受当事人选择法院因素的影响,即使法院完全依照法院地国的冲突法选择法律,仍会出现适用法院地实体法的概率明显大于适用外国法的情形。
在上述情形中,当事人选择起诉的法院地同时也是与争议的涉外法律关系有密切联系的地方,因此,管辖法院依据中性的冲突规范仍然可能出现适用法院地实体法的结果。即使这是一种“巧合”,也是一种经常出现的巧合!
(二)主观判断标准对法律适用的影响
现代法律适用理论与法律选择方法受“实质公正”导向的影响,出现了很多需要法官主观判断的选法标准,如“最密切联系”、“政府利益分析”、“政策定向”与“结果导向”等。这些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的选法标准客观上加重了法官选择法律的困难,同时也增加了法官选择法院地法的客观可能性。
1.政府利益分析标准
美国学者柯里主张在面对法律冲突时,对可能产生冲突的法律比较各自立法利益的有无和大小。〔6〕See Currie,Comment on Babcock v.Jackson,63 Colum.L.Rev.(1963),pp.1233-1245.“立法利益”的比较使得法官需要对不同国家实体法出台的立法背景、规制意义等多方面因素进行考察,而法院地的法官对外州或外国立法背景、立法意图和规制意义的了解非常有限,对本州或本国法律的熟悉程度远高于对外国法的理解程度。如果发生冲突的法律是法院地法和外州法(或外国法),法官难免主观上认为本州或本国的实体法更具有政府利益,甚至认为外州(或外国)的实体法在争议问题上没有真实的立法利益。
政府利益分析在美国司法实践中的影响很大。在有些州的司法实践中,虽然法官表面上是依照最密切联系标准选择法律,实际上却以政府利益衡量作为判断是否有最密切联系的标准。〔7〕See Generally Restatement(Second)of Conflict of Laws,§9(1971).美国学者莱弗拉尔教授也明确主张将政府利益分析方法与最密切联系标准结合起来,以政府利益分析作为衡量最密切联系的标准。〔8〕See Leflar,Comment on Babcock v.Jackson,63 Colum.L.Rev.(1963),pp.1247-1251.这样一来,柯里学说本身或许并无对法院地法的偏爱,却造成实践中适用法院地实体法情形增多的现象。
2.最密切联系标准
美国学者里斯提出的最密切联系选法标准同样具有很强的主观色彩。里斯主张把与案件有关的连接因素放在一起比较,看哪个连接因素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就适用哪个地方的法律。〔9〕See Willis L.M.Reese,Choice of Law:Rules or Approach,57 Cornell L.Rev.(1972),pp.322,323.问题是,里斯并没有进一步指出,在具体案件中,法官依照什么标准判断哪个连接因素与案件的联系“最密切”。这仍然需要法官做出主观判断。不可忽视的是,在不同种类的涉外民事案件中,法院地始终都是案件的连接因素之一。这就为法院最终选择法院地的实体法提供了可能。
有趣的是,这种标准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远不如在欧洲大陆法系和中国等成文法国家。区别是,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和中国不是将最密切联系作为法官的选法方法,而是在立法层面制定冲突规范时,以最密切联系为理念选择合适的连接点,同时将“最密切联系”作为“兜底”条款,当具体冲突规范所指向的准据法与案件实质联系不大或者无具体冲突规范可以适用时,允许法官选择与具体案件有更密切联系地的实体法。
当然,与美国不同的是,通过立法方法确定最密切联系标准后,“法院地”并不总是一种连接因素。这似乎降低了法院地法适用的可能,但对最密切联系的判断仍有可能增加实际选择法院地法的结果。无论是美国的选法方法,还是欧洲与中国的兜底条款,都没有也不可能回答最密切联系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有的解释为“最真实的联系”、有的解释为“最实质性的联系”,而何谓“最真实”、“最实质”仍然无法确定。因此,当案件当事人中有一方居住在法院地(例如消费者合同争议),侵权行为实施地和结果发生地中有一个是在法院地国时,都可能会导致法院最终选择了法院地的实体法。虽然所依据的冲突规范不同,但结果仍然会是适用法院地实体法的概率大于适用外国实体法的概率。
3.政策定向与结果导向标准
以法律选择应当体现一定的政策导向为标准决定法律适用的具体的方法,这是美国学者卡弗斯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的法律优先选择原则。〔10〕See David F.Cavers,Contemporary Conflicts Law in American Perspective,Recueil des Cours,1970.以法律适用结果是否有利于案件公正裁决为导向在不同国家的实体法之间进行选择的方法被称为结果导向标准。〔11〕See Symeon C.Symeonides,Result-Selectivism in Conflicts Law,46 Willamette L.Rev.12009-2010.例如莱弗拉尔的“较好的法”等。〔12〕See Robert A.Leflar,Choice-Influencing Considerations in Conflicts Law,41 N.Y.U.L.REV.267(1966);Also see Robert A.Leflar,Conflicts of Law:More on Choice Influencing Considerations,54 CAL.L.REV.1584(1966).这些方法在美国并没有得到多少实践的响应,因为实际审判结果仍然是适用本州实体法的案件居多。欧洲在涉外消费者合同案件、产品质量侵权案件、劳动雇佣合同案件中,提出了弱者权益保护的实质公正理念。通过对合同中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否定或限制,法院把法院地有利于保护消费者、产品质量侵权受害者和雇员的实体法适用到具体案件中。例如,消费者起诉的法院常常是消费者经常居住地国家的法院。法院适用消费者经常居住地法,自然就是在适用法院地的实体法。
此外,欧洲在跨国扶养、监护案件中,通过立法明文规定,在抚养人或监护人居所地、被扶养人或被监护人居所地等连接因素中选择能够使被扶养人或被监护人得到扶养或得到监护的实体法。当事人选择起诉的法院地常常是立法有利于得到扶养或有利于监护的国家,因而实际案件中也常常会使法院最终适用法院地的实体法。
我国2009年颁布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看起来只有两三个条文明文规定适用法院地法,〔13〕从2010通过、2011年4月开始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条文统计看,明确规定适用“法院地法”的条文有第8条(关于定性)、第27条(关于诉讼离婚)。第47条关于“知识产权的归属和内容,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律”也可以看作是要求适用法院地法,因为“被请求保护地”实际上是“法院地”。但结果导向的选法标准非常明显,而且在结果导向方面比欧洲更进了一步。例如,在扶养关系上,不是简单规定适用能够使被扶养人得到扶养的法,而是要求适用“有利于”被扶养人的法。这一方面会增加法官查明外国法的难度,同时又会迫使法官在无法了解哪个国家法律更有利于保护被扶养人时,武断地适用法院地(中国)的实体法。〔14〕依照该法规定,当外国法无法查明时,法院可以适用中国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0条第2款规定:“不能查明外国法律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总体看来,不论是政府利益分析还是最密切联系、结果导向等,其强烈的主观判断色彩都可能增加最终适用法院地实体法的可能性。出现这种倾向不能怪罪于实际审理案件的法官,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法官对本国法的偏好。法官选择适用法律不是为了对外国法表示出足够的尊重,而是为了裁判案件、在公平与效率之间达到平衡。适用法律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选择恰当的法律界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最终目的是为了做出公正裁决。这就是法律适用目的的双重性。
二、涉外民商事关系与纠纷处理的关联与分割
处理涉外纠纷的前提是理清涉外民商事关系,但纠纷的处理不限于对法律关系效力、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界定,还包括对纠纷的裁判或者说后果的处理。学界往往以为界定清楚了法律关系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就当然地能做出公正裁决。这就混淆了法律适用目的的双重性,把法律适用的任务和最终目的混为一谈。涉外民商事关系的界定与纠纷的处理之间虽然关系紧密,但却非完全重合。对于涉外民商事关系的界定,法官可能持开放的态度。而对于纠纷的裁决,法官却难免会受到本地法中公正观的影响。
(一)法律关系的成立、变更与法律适用
法官在对民事行为效力、关系界定以及权利义务的界定方面,自然要根据法律关系成立地的实体法来判断,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涉外民事案件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可能是基于法院地的实体法而建立的,也可能是基于法院地国家以外的实体法建立的。在此问题上,各国的法官一般不会强行要求适用法院地的实体法。成文法国家的立法中一般也不会这么规定,除非是对特殊的涉外民商事关系,法院地国家立法中才有强制性的规定。不过,这种强制性规定毕竟是极少数,因此,从理论上说,似乎审判实践中不应该出现适用法院地实体法比例更高的现象。然而,一国法院受理的涉外案件未必完全按照理论的逻辑推演出现。
其一,法院地的公共秩序会限制法官适用外国法界定依据外国法成立的涉外民事关系。不论法官如何谨慎处理涉及公共秩序的问题,现实是牵涉到公共秩序的案件并不在少数。例如,在涉外婚姻中,随着同性婚姻现象在部分国家的合法化,对于尚未承认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而言,其法院在面对依照外国婚姻法缔结的同性婚姻离婚、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上就不得不考虑法院地国家的公共秩序问题。另外,虽然过去西方国家很少基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否定依照伊斯兰法成立的婚姻效力,但在大量阿拉伯国家移民涌入西方国家后,在夫妻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纠纷、子女抚养和遗产继承等问题上,西方国家鉴于本国人权保护的宪法因素,也不会考虑依照阿拉伯国家的婚姻法处理夫妻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而是适用法院地的婚姻法。〔15〕See Andreas C.Limburg,Swiss Federal Supreme Court Rejects Recognition of Repudiation under Islamic Law,ITCP9.1,2002,pp.27-29.
其二,现代社会对外投资、贸易活动增多,各国对外资管理和外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都有一些强制性法律限制。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强制性法律规定多表现为外汇管制、外资审批程序等;〔16〕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关于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中第10条规定了六种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在西方发达国家,则通过国家安全审查、环境保护、劳动保护等限制外资和外国商品进入。因此,涉外投资争议和贸易纠纷大量发生,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不得不考虑本国的强制性规定。这并非中国的特有现象。国内学界部分学者对我国法律规定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三资企业强制适用中国法颇有微词,但客观地说,国外学术界对此问题的意见似乎并没有中国国内强烈。〔17〕当然,对于不涉及中国国内法强制性规定的争议,不必非要适用中国法不可。过去国内法院和仲裁机构确实存在扩大适用的现象,但远未达到滥用的地步。经常被诟病的是以违反审批程序认定协议无效,对当事人无法律约束力,而当事人之间又已经履行了部分协议内容。笔者以为,虽然这个问题值得讨论,但在法理上也未必完全站不住脚。
(二)法律关系的解除、消灭与法律适用
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解除或消灭如果已经发生在法院地以外的国家,当事人争讼到法院的问题是该民事法律关系解除或消灭的后续问题,那么受理案件的法院一般会依据外国法判断该民事法律关系解除的效力或是否已经消灭,除非牵涉到法院地的公共秩序,法官一般不会考虑适用法院地的实体法。这时候,在法院地以外国家已经解除或消灭的民事法律关系常常是作为先决问题出现的。例如,离婚后的当事人就位于法院地的财产分割发生新的争议,法院需要考虑先前离婚是否有效,就需要适用离婚地的婚姻法。对于法院需要处理的本问题而言,依然牵涉法院地的实体法。
如果涉外民事关系的解除或消灭正是需要法院裁判的事项,则不论该法律关系是否在国外发生,法院主要依据法院地的实体法做出裁判,而较少考虑外国法。例如,涉外离婚案件中法院依据法院地的婚姻法判断是否准予离婚,而不考虑该婚姻成立地的婚姻法如何规定。对于请求法院保护的涉外知识产权,法院也只会依据法院地的法律做出是否保护的裁决。当然,这也包括法院地国家参加的可以直接适用的国际公约在内。
(三)当事人权利的主张、实现、保护与法律适用
当事人权利的具体主张、实现与保护更多地需要适用法院地的法律。从国际私法角度看,一些国家常常将某些权利主张识别为程序性问题,因而不考虑适用外国法。例如,在海商案件中,几个当事人就同一船舶分别主张留置权、抵押权和船员工资优先请求权等。这些权利的形成分别依照其形成地的法律都是有效的,但依照什么顺序受偿则要适用法院地的法律。〔18〕See William Tetley,Maritime Liens,Mortgages and Conflict of Laws,6 U.S.F.Mar.L.J.1,1993.又如,当事人请求的惩罚性赔偿如果在法院地国家的实体法中没有类似规定,法院也不会支持该请求。〔19〕See Patrick J.Borchers,Punitive Damages,Forum Shopping,and the Conflict of Laws,70 La.L.Rev.2010.这些问题与法院地的公共秩序有关,但并非以公共秩序保留的名义出现。
我国法院受理的涉外商事案件以涉外海事、海商案件居多。这类案件因可以在网上公开查询到,在学者进行统计分析的涉外案件中占有重要比例。在涉外海事海商案件中,存在大量适用法院地实体法的现象,而我国海商法立法中极少要求适用法院地法这一冲突规范。法院在司法裁判中并没有违反我国海商法中的冲突规范立法,因而并非法官对本国法的偏爱。〔20〕我国海商立法中规定,船舶优先权争议、船舶在公海上发生碰撞的损害赔偿争议、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等都适用法院地法。另外,共同海损理算,适用理算地法律。如果理算地与法院地在同一国家,也会导致适用法院地法。相比较而言,涉外海事海商案件中,适用法院地法的实际比例远远高于其它涉外民商事案件。同时,这也是国际航运司法实践的普遍现象,并非中国所特有。所以,不应该因统计数据的表面现象指责我国法院适用外国法不力。
三、关于“国际视野”和“国际社会本位”的思考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倡导“国际社会本位”理念有利于打破“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促进国人以更开放的心态借鉴国外好的立法经验和司法实践。从国际私法角度,“国际社会本位”主要应该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立法上保持与国际社会立法趋势的一致性,促进中国立法的进步,以适应市场经济建设对法制发展的需要;二是在司法上克服保守倾向,通过恰当地适用外国法达到公正、公平对待涉外民商事关系当事人,促进中国与外国的民商事交往活动的目的。然而,以“国际社会本位”的理念要求司法裁判者具有“国际视野”,并以适用外国法比例的大小为衡量标准却未必合理。
(一)法院地法与国际民商新秩序
作为一种理念导向,“国际社会本位”概念对于我国涉外立法的积极意义远远高于司法审判。然而,“国际社会本位”并不是一国涉外司法审判的内在价值追求。司法审判的永恒价值追求是案件裁判的公正,当代涉外司法审判实践的趋势是从平等对待内外国法律到重视个人权益维护的回归。〔21〕参见袁发强:《人权保护对冲突法的影响》,载《时代法学》2004年第6期。
原则上,平等对待内外国法律作为一种观念在各国法官内心并无多少抵触,但法官更在意个案结果的公正。美国冲突法革命的理论纷呈,而司法实践却并没有特别倾向于哪种理论。譬如在侵权案件中,法官更在意让受害人得到保护和赔偿。在此倾向下,法官有目的地选择法律选择方法,有时为了结果更是将几种方法混在一起。〔22〕See Leflar,Conflict of Law:Arkansas,1973-77,32 Ark.L.Rev.1[J],1978,pp.2,3.由此,美国学者西蒙·西蒙尼德斯将美国冲突法分为学术的冲突法革命和司法实践中的冲突法革命。〔23〕See Symeon C.Symeonides,The American Choice-of-Law Revolution in the Courts:Today and Tomorrow,298 Recueil des Cours 1(2002).
当然,美国冲突法的实践在灵活性方面确实走得太远了。〔24〕See Symeon C.Symeonides,American Choice of Law at the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37 Willamette L.Rev.12001,p.74.这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法院过多地适用了法院地实体法,而是由于司法裁判中选法理由的含糊不清。这不但受到学术的批评,也对跨州民商事交往活动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带来困扰。不过美国司法实践对待跨国民商事争议的处理似乎比跨州争议的处理要谨慎些,说明司法审判并非不重视国际民商事交往秩序的稳定。
欧洲国际司法实践更多地关注欧盟区域范围内的统一化。在弱者保护理念和人权保护理念的影响下,欧洲采取了从立法上更直接干预实体结果公正的选法方法。这表现在选择法律时通过弱者权益保护干预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25〕See James J.Healy,Consumer Protection Choice of Law:European Less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19 Duke J.Comp.& Int'l L.2008 -2009,pp.556-558.以及在婚姻、家庭和儿童等问题上采取结果导向的法律适用规则。这自然会导致适用欧盟统一实体法(其实也是法院地的实体法)的几率增加。
因此,国际民商事新秩序的内涵并非简单地平等看待内外国实体法,更为重要的是强调实质公正。不考虑法律适用的后果,而从形式上平等对待各国法律,这是自巴托鲁斯提出法则区别说时起就深深扎根于国际私法学者内心的信念。各国涉外审判实践也基本上体现了这种信念的影响。对于实在“令人厌恶”的外国实体法,〔26〕See Nikitas E.Hatzimihail,Bartolus and the Conflict of Laws,60 RHDI 112007,p.23.才考虑通过公共秩序保留的方法排除其适用。事实上,各国涉外司法实践中滥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情形并不明显,远没有达到其他国家报复而妨碍跨国民商事交往活动的程度。在国际私法的司法实践中,不存在“国家本位”的倾向向“国际社会本位”过渡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法院不可能是“国际的法院”,法官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既不会完全站在本国的“国家本位”,也不需要具有“国际社会本位”的立场。
国际民商新秩序应该是尊重人、“以人为本位”的新秩序,〔27〕“以人为本”是当代国际法发展的趋势,这不仅表现在国际公法的发展中,而且也表现在国际私法的发展中。参见曾令良:《现代国际法的人本化发展趋势》,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是彰显不同国家人民实体权利义务平等的新秩序,是尊重当事人自由交往的新秩序。如果过分考虑当事人的国籍国法、住所地法,而不重视统一不同国家当事人交往的共同规范,反而不利于跨国民商事交往。〔28〕参见肖永平、袁发强:《新世纪国际法的发展与和谐世界》,载《武大国际法评论》(第1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国际私法的使命并不在于鼓励使用因人而异的社会规范,而是促进协调跨国民商事交往争议规范的统一化。在这个问题上,法院地的实体法并不是与国际民商事新秩序对立的法律适用结果,而只是依据冲突规范自然选择的结果。
统一各国实体法规范的路径不局限于国际条约这一种方式。在民商事关系领域,国际条约也未必是最成功的方式。以商业关系为例,如果商人们多愿意选择在英国法院诉讼,我们除了羡慕或嫉妒之外,修改和完善本国的商事法律,提高本国的涉外商事审判水平才是硬道理。这种努力的结果自然也会促使各国商事法律的趋同以及审判结果的趋同。
(二)“国际视野”与法院地的公共秩序
如果一定要为法官赋予“国际视野”的职责,这种职责应该体现为法官在审理跨国民商事案件时,不拘泥于法院地的公共政策,不对“私法关系”进行过多的“公法限制”。“国际视野”并不要求法官在裁判案件时过分迁就他国法院对类似案件的裁判结果。事实上,法官既无从了解、也不需要过分考察其他国家对类似案件的裁判结果。
所谓不拘泥于法院地的公共政策,也并非是要法官界定公共政策的“国内性”与“国际性”。所谓“国际公共政策”不过是变化了词汇的“一般法律原则”或者说各国法律中的“普世价值”。将多数文明国家法律的一般原则提炼出来,要求不同国家的司法机关共同维护,这只是学者的理想和愿望。在具体案件裁判时,法官并不会考虑这些抽象的精神和理念,但法官会关注案件审理结果的公正,以及裁判结果是否会妨碍以后类似民商事交往活动的进行。〔29〕国内外许多国际私法学者都认为,当代国际私法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已经从追求法律适用普遍性和一致性的形式正义向追求案件结果公正、保护弱者权益、充分保障当事人民事权利实现的实质正义倾斜。
维护法院地的公共秩序与促进国际民商事交往活动本身并不矛盾,只是偶尔会在个别具体案件中产生冲突。一方面,各国民商事法律虽然可能差异较大,但真正涉及基本原则的差异并不多;另一方面,多数国家并不以法律本身不同而轻易动用公共秩序保留措施,而是在考察适用外国实体法的后果后才决定进行保留。
最容易引起诟病的是法院地国家的强制性法律规定。这些强制性规定多牵涉公法,〔30〕See Michal Wojewoda,Mandatory Rules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Mandatory System under the Rome Convention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Contractual Obligations,7 Maastricht J.Eur.& Comp.L.1832000,pp.194,195.是国家管理社会,特别是管理对外经济活动的重要措施。这种措施的出现和维护不能仅从促进国际民商事交往角度看,不是国家主权与国际民商新秩序的绝对对立,而只是暂时的矛盾。总体上说,经济发达的国家,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比较弱,强制性规范比较少;而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健康发展,避免在自由竞争的形势中被他国控制和蚕食,不得不加强国家干预,出台比较多的强制性规范。这也是法院地国家追求实质正义的体现,不应给予过多的指责。
一国管理对外经济活动的强制性法律规定虽然是基于国家主权而出现的,但未必是不恰当的和不合理的。受理案件的法院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自然有维护本国利益的使命。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强制性管制法规会逐步减少,管制的内容也会发生改变。〔31〕当前经济改革中有关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就是很好的例证。而发达国家随着经济竞争力减弱和交易地位的转换,也会出台更多限制自由贸易和投资的法律和法规。西方国家虽然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外汇管制那么严格,似乎对跨国贸易和投资更为开放,但当本国经济竞争力下降时,也会出台很多打着环保旗号限制外来商品进口的措施。〔32〕如以环保为名的绿色壁垒。对于中国的海外投资,西方国家也会基于“国家安全审查”的法律机制限制中国企业进入其国内市场。
(三)法院地法与正当期待之间的关系
适用法院地的实体法是否违反当事人的正当期待呢?应当说,这种结果并不是必然的。〔33〕See Peter Hay,Flexibility versus Predictability and Uniformity,226 Recueil des cours 2821991.如前所述,适用法院地的实体法可能是基于各种抽象性连接点结合具体案情确定的,说明法院地的实体法与案件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在合同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某国法律时,想到的是该国实体法对待合同的具体规定,当事人将这些具体规定作为交易行为的准则判断行为后果,确定应当采取的措施;在当事人选择某国法院管辖争议,而不选择应适用的法律时,也是考虑到被选择法院所在国的实体法可能会被适用的后果。当事人不可能考虑选择法院地国的冲突法,因为这太间接而无法预见依据冲突法会得出什么结果。
当然,这种预见性对于早已形成的普通民事法律关系而言是不存在的。当事人不可能预见自己以前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会因为多年以后自己迁居的事实而适用另一国家的法律来衡量其效力。也正因为如此,很少有国家规定法院地法作为判断民事关系和民事行为效力的准据法,除非法院地的公共政策不允许承认这种法律关系和行为的效力。这是极少见的,不会从根本上妨碍正常的跨国人员流动和交往活动。
四、结语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涉外民商事审判实践的实证分析研究越来越多,这无疑是件好事。〔34〕例如,黄进教授、杜焕芳副教授等每年都会在《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上发表《中国国际私法实践述评》。贴近实践的理论研究才有生命力,才具有指导实践的价值。但是,带着理论的“有色眼镜”指责实践中发生的现象却是不可取的,简单的统计结果并不能说明实践的不合理。
法律适用的目的不仅仅是界定法律关系的性质以及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还包括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做出公正的裁判结果。界定清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虽然是前提,但不意味着就能做出公平合理的裁判。我们不可能要求法院只注意法律适用上的内外国法律平等,对外国法过多的“礼让”,而不考虑案件处理结果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