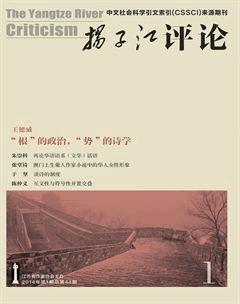“大时代”中的“小人物”
韩松刚
如果从1918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算起,中国现代白话文小说的写作已经历时近百年。这一百年,从五四到新世纪,有革命成败的阵痛,有文化转型的失措,有价值颠覆的悲欢,个中滋味,想必“凄惨”二字亦不足以道尽。然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且不管这样的时代的存在是否合理。古语云,时势造英雄。可是,一个时代英雄毕竟屈指可数,芸芸众生才代表了它最贴切的存在状态。于是,在作家的笔下,不管是风平浪静的清平岁月,还是风云激荡的混乱时代,“小人物”也永远是他们承载内心情感和人文情怀的艺术选择。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鲁迅笔下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我们早已耳熟能详,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张爱玲笔下的“七巧”、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钱钟书笔下的“方鸿渐”,也是尽人皆知的“小人物”。而到了五六十年代,柳青笔下的新人梁生宝、赵树理笔下挨批评的“小腿疼”“吃不饱”,都是极其普通的群众中的一员。即便是王蒙《组织部新来了个年轻人》里富有理想精神的林震,杨沫《青春之歌》里有着反抗精神的林道静,在广阔的现实生活里,亦是沧海一粟。新时期,在从革命走向改革、从改革转入日常的时代变化中,“小人物”已经成为作家笔下最常见的人物形象。如果说路遥笔下的高加林、高晓声笔下的陈焕生依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小人物”,并展现出各具魅力的人格特征和思想价值,那么,更多的时候,作家笔下的“小人物”却早已被大时代的洪流所淹没,在琐碎、平庸、机械的日常生活里,隐忍着,挣扎着,扑棱棱掉了“一地鸡毛”,但他们却毫无疑问地成为这个大时代最平实的注脚。
范小青笔下的苏州小巷也是如此,那些有点“小家子气”的小人物才是它最适合的一种生命形态,淡薄宁静,安于现状,却不缺乏生存的智慧。而到了新世纪,随着经济、文化、思想的激荡与变化,特别是城市化进程的急剧加速,时代的面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大都市、大时代成为社会发展和政治意愿里的一种普遍追求,相较之下,人类的精神状况也随之大相径庭。喧嚣与浮躁,正成为这个大时代背景下人们的一种普遍生命状态。
在这样的时代形势下,一个作家如何平静地展现自己的叙事艺术、彰显自己的现实情怀真正成为考量他(或她)是否称职、优秀的标准。范小青做到了。她以自己最敏锐的嗅觉,体味到了这个时代的巨大变化,以及在这种变化之下人们生存状况及思想状况的颠覆。这样的体味其实是有些残忍的,它不仅意味着一种生存状态和文化形态的失去和告别,而且要面对新世纪时代氛围的日新月异、烦扰纷乱,这其中有茫然,有迷离,甚至有不知所措,因为一切都来得如此突然、如此决绝。许纪霖说,“传统社会是以时间为脉络,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的根源无不在历史之中,个人的自我认同是在寻找历史的脉络感中实现的。相比之下,现代社会则更多地是以空间为核心。”①在时代的浪潮中,“苏州”已经不能承载时代这个宏大的主题了,在隆隆的机器声中,被推翻的不仅仅是时间、不仅仅是地缘,还有作家一直以来赖以维系创作灵感的历史渊源。在新的时代里,这种灵感只能逐渐在新的“空间”(包括都市这一物质范畴和新的文化社会关系)中去苦苦寻求,在凌乱的物质空间里,在喧闹的人声鼎沸里,在纷扰的现实生活里,去抽死剥茧般地结自己生命的“茧”。
时代在变,人在变,物在变,情也在变,这些变化凝结到作家的笔下,更增加了“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的感慨和惆怅。或许在我们的想象和经验中,苏州还是原来的苏州,巷子还是以前的巷子,人物也还是曾经的故人,但总感觉情绪变了,味道变了,精气神变了,那些颤悠悠的惆怅似乎还留着旧有的袅袅曲调,但却多了不少的焦虑和迷惘,巷子没那么安静了,情绪没那么淡定了,人似乎也都变得蠢蠢欲动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艺术的力量通常就是回忆的力量。正是因为它那不完美、不明确的性质,正是由于它通常只是‘一般的东西,而不是活的个别的形象或事件,艺术作品特别能够唤起我们的回忆。”②作为一名“苏州”经验的传承者,范小青对于苏州的把握和描绘是内在于心的,是细腻贴切的,她在其《裤裆巷风流记》等早期的一系列“苏味小说”中,借着这“艺术的力量”已经把其内心深处那古典的、浪漫的却又十分日常的苏州风情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这些令人怀念的、带着些许惆怅的经验和回忆,一方面与作者几十年苏州生活的经历有关,但更多的是作者人文、道德情怀的真实、真情、真诚再现。可以说,在范小青的苏州风情、世情小说中,苏州的“小桥、流水、人家”与她内心的美学诉求达成了一种完美的契合,水到渠成,没有任何的娇柔做作之感。尼采说,“具有古典思想的人和具有浪漫思想的人——总是会有这样两种人——总是怀有一种关于未来的幻觉:但是前者出于他们时代的强大,后者出于他们时代的衰弱。”③而当这两种思想同时在范小青的创作中激荡的时候,我想她对于这个时代的变化已经有了最初的、最敏感的体悟和了解,但绝不是一种“幻觉”。于是,在她后来的创作,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创作中,当这种古典、浪漫的思想正在慢慢脱离开以苏州为中心地带的文化渊薮之时,她没有像很多作家一样显得不知所措,甚至于搁置停笔,而是在新的现实和新的迷惘的迷雾中,呈现出自己越来越浓郁的现实关怀和理性思索。而要谈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作者新世纪长篇小说中所塑造的几个让人“会意”(范小青语)的人物形象讲起。
于老师(《于老师的恋爱时代》)。一个作家的写作与当下并不永远保持一种紧密的关系,有时候,或许是出于一种有意的疏离,或者是出于一种内心的情感派遣,也或者仅仅是艺术上的一种尝试,总是会出现偏离这个时代的创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小青的长篇小说《于老师的恋爱时代》便是她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中试图挣脱大时代的第一次有意尝试。这部小说妄图挣脱城市的大时代幕布,从而专心于写一位小学教师——于老师在农村的复杂人生历程。小说的主人公于老师,对孩子们来说,既觉得有些神秘,又特别地喜欢、尊崇。既是为了照顾受伤的月儿,又仿佛是一些不便为外人知的原因,于老师开始了他曲折的恋爱经历。小说在结构上处处设伏笔,语言既简单感人,却也不失一些幽默和诙谐,加上不时出现的民俗曲调,读来真是让人觉得既活泼又有韵味。然而,历史的变迁对人的影响又是无处不在的,所以小说到了最后也从叙事者的角度发出了自己的感慨:“你们是不是已经感觉到了,故事的叙述者变成了一个人,那个快活的勇敢的纯真的男孩不见了,取代他的是一个心情负重的情绪沉闷的男人,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我,改变了的我,我是被城市改变的,城市的力量无比的大。”④这其实不仅仅是叙事者的感叹,更是人物与时代关系不可被更改的深沉意味的间接流露和表达。
田二伏(《城市之光》)。其实被改变的,不只是“快活的勇敢的纯真的男孩”,还有千千万万普通的乡下人。怀着最初的梦想和期待,这些乡下人惴惴不安地来到城市,成为这个城市的“农民工”,也随即成为这个时代新的漂泊者和流浪者。与《城乡简史》中所体现出来的农民工对城市的适应和满足不同,《城市之光》中的农民工的生活则显得无序而且混乱,欲望、诱惑、挣扎、痛苦,一个时代的病症在城市这个无限扩张的空间里得到了最无情、最悲惨的展露。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艺术的第一个作用,一切艺术作品毫无例外的一个作用,就是再现自然和生活。”“它并不修正现实,并不粉饰现实,而是再现它,充作它的代替物。”⑤可以说,范小青对于城市农民工的描写,正如同其他“农民工”题材的小说一样,真正成为我们认识这个时代的一面镜子。在欲望的渊薮中,乡下人的淳朴、善良,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践踏,他们成为新一代的“被损害与被侮辱”的人。他们既感到了对这个城市和城市人逻辑的不适,但却无力做出彻底的改变,于是最终的结局往往只有“悲惨”二字。
万丽(《女同志》)。文学对于中国官场的描写历时已久,从古至今,皆不乏优秀的作品和典型的人物形象。范小青的《女同志》,却将官场的形态和女人的气质做了完美的结合,写的虽是官场的斗争和尔虞我诈,但却不缺少生活的质感和人性的温暖。所以,范小青笔下的万丽,“她是一个小人物,没有经历过大的官场风暴;她没有政治背景,很少攀龙附凤;她有理想,所以一直不曾失去对权力的警惕;她看重感情,所以常常心疼和流泪……这是一个复杂的人。”⑥在范小青的笔下,“小女人”的天性是对意识形态化的“同志”的消解,而这种消解并不是出于一种女权主义对男权政治的敌意,只不过是从人性的角度讲述政治视野中那“无法被消灭的温暖和坚忍”。波伏瓦在谈到女性在当代社会的处境时指出,“经济上摆脱了男人的女人,在道德、社会、心理状况中并没有达到与男人一模一样的处境。她从事和投入职业的方式,取决于她的生活的整体形式所构成的背景。然而,当她开始成人生活时,她身后并没有和男孩子一样的过去;她没有受到社会的同等看待;世界对她呈现出不同的前景。成为一个女人的事实,今日对一个自主的人提出了特殊的问题。”⑦而“女人正是在这痛苦的处境中投入了职业生涯,她们仍然受到女性身份传统上带来的负担的奴役。客观形势对她依然是不利的。一个新来者想在敌对的或者至少是不信任他的社会中开辟道路,总是很困难的。”⑧我想,“女同志”这个具有时代意味的概念和形象,必然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女性心理和官场的复杂形态在当下的特殊“困境”。
万泉和(《赤脚医生万泉和》)。洪子诚说,“对于生活现象,不仅看到它是‘现实的,而且它也存在于‘过去,也有它的未来;不仅从社会的角度去把握,而且从人生的角度去把握。这样,作家就不仅拥有观察生活的政治的、阶级的、经济的传统眼光,并在这方面继续开掘深化,而且获得了过去所缺乏的道德的、历史的和人生的眼光,使创作的主题,出现多元的现象,作品也具有当代文学以前较少出现的强烈的历史感和人生感。”⑨在《赤脚医生万泉和》中,尽管作者一直在试图隐却时代背景,但是依托于空间不断变化的“后窑大队第二生产队”,其实依然为我们提供了历史在时间脉络上顺延和前行的全面图景。正如有评论家所指出的:“从一种象征的层面上说,范小青对于后窑村近半个世纪以来乡亲们罹患的种种疾病的描写,完全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以农民为代表的中国国民普遍的思想、精神乃至于基本人性方面疾患的一种书写与表达。”⑩万泉和,一位极其普通的赤脚医生,却被作者赋予了广阔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思索,他的种种举止读来觉得荒唐、不可思议,读罢却让人生发出无限的苍凉和不尽的感叹。这样一个形象,我想应该是能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物形象长廊中留有一席之地的。透过这样一个人物,我们不仅仅窥视到了农村医疗状况的历史和现实,而且拨云见日般看见了人性在历史和现实折射下的既单一又复杂。万泉和是愚笨的,但又是可爱的,是乡土的,但也是现代的,且看小说结尾的几段描写:
我狼狈不堪地逃回家的时候,看到我爹坐在门前晒太阳,那一瞬间,我被我爹的平静的目光打动了,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挨着我爹坐下来。我的魂也回来了。我真没有出息,现在村子里的人都不守在家里了,外出的外出,进城的进城,开店的,开车的,反正干什么的都有,我却回来了,和我爹一起,呆呆地守望着村前的这条路。
坐在我家的院子里,可以守望我们村通往外面世界的这条路。
我和我爹一起守望着村口的大路。
这条路就是许多年来许多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的路。11
在失魂落魄的历史和当下,万泉和却找到了自己的“魂”,这是多么强烈的内心诉求,是有着禅一样境界的高蹈,更是一种生命的顽强姿态。
香火(《香火》)。“香火”这个称谓的复杂性,决定了这必然是一个值得让人认真回味的小说形象。在小说的叙事中,作为一种职业和家族传承的“香火”已经暗合在“香火”这个人物形象中,他承担起了叙事的重任,并负载着历史的驳杂意味和人性生死的重量。范小青说,“如果撇开最后因为写作手法带来的各种异议,我写香火的本意,是想写一种敬畏之心的当下的社会太缺少敬畏,有人杀一个人比杀一只鸡还无所谓我们太需要敬畏,对生活,对人生,对生命,对许许多多的东西和一切的东西都应该是敬畏的小说最后的走向可能与初衷有所偏差,但敬畏之心的想法仍然存在,一个百无禁忌的香火,最后他有了敬畏之心。”12在一个信仰全无,精神价值全面崩塌的时代,《香火》的书写有着强烈的历史意味和现实考量,而“香火”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真正应该引起我们的自我深思和反省。
加洛蒂在《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一书中讲道:“对于一个既定时代里的人和世界的关系,一部作品也许是很不完整,甚至是极为主观的见证,而这个见证却可能是真实而伟大的。”13范小青对大时代的最深切的体验和感触,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较为切身的表达和流露,而这“主观的见证”,正是一个作家内在思想的深刻之处,她对于这个时代的认识和思考,终将为我们认识这个时代提供一些感性的资料,而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人物”或许正构成对这个时代最积极、最无形的一种影响和塑造。当然,“典型人物既是一个人,又代表了一批人。生动、具体、个性独特——仅仅考察文学人物的这些特征远远不够,重要的是,这些特征为一批人的抽象综合。”14我们以期在这些小人物身上发现那永恒的人性光辉。
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时间,对于浩茫的文学史来说,不过是短短的一瞥,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却是极为宝贵的生命历程,而我愿意把这十多年的时间看做是范小青写作的“黄金时代”,在这段时间里,她以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不仅为我们奉献了一大批优秀的中短篇及长篇小说,而且为我们这个时代塑造了许多极为有特点又十分“会意”的人物形象。通过对这些形象的挖掘和认识,我们既看到了一个作家在小说艺术上的不懈追求和探索,也认识到了一位有情怀的作家对于现实、人生、历史的洞察和体悟。她的写作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是现实的,又是魔幻的,既有为我们能够极易感悟到的精神和意义,也有我们还没有探寻到的思想和价值。范小青说:“我写作的文化背景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织的一张网,我既生活在一个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古城,又习惯现代意识的思维。在现代的写作中,信息压力很大,但这就是信息时代,你想躲也躲不过各种各样的信息,生活中的事情超出想象时,只能让我感叹生活的了不起。所以我所理解的生活和文学的关系,就是写作者要敏感、用心、艺术地学习生活、了解生活、感悟生活,才可能有文学。同时,作家还应该坚持自己的精神立场,而我的精神立场,则在我的小说中体现出来。”15我想,我们对于范小青小说中的精神立场的判断和探究,或许正如她对于创作的孜孜以求一样,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注释】
①许纪霖:《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26页。
②[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4页。
③[德]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杨恒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1页。
④范小青:《于老师的恋爱时代》,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
⑤[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6页。
⑥谢有顺:《比权力更广大的是人心——我读范小青的〈女同志〉》,《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06期。
⑦[法]波伏瓦:《第二性2》,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545页。
⑧[法]波伏瓦:《第二性2》,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561页。
⑨洪子诚:《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4页。
⑩王春林:《乡村书写中的人性之旅——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的一种趋向分析》,《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四卷第2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
11范小青:《赤脚医生万泉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8页。
12范小青:《关于〈香火〉》,《扬子江评论》2012年01期。
13[法]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吴岳添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173页。
14南帆:《现实主义、结构的转换和历史寓言》,《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四卷第1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
15范小青:《关于成长和写作》,《小说评论》2010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