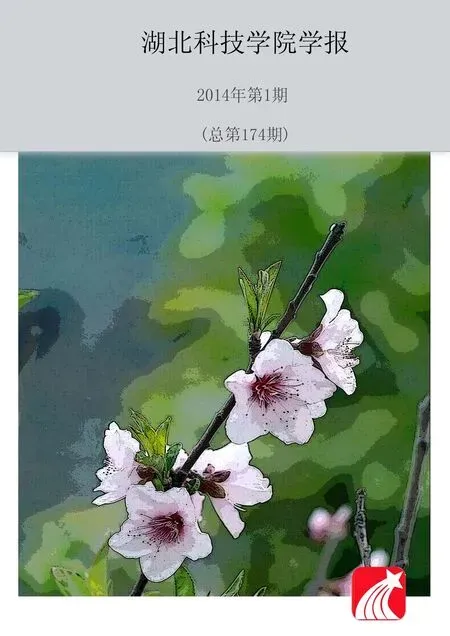鲁迅之刚烈和浙东民间文化 *
田 敏
(湖北科技学院 教育学院,湖北 咸宁 437000)
*收稿日期:2013-12-12
基金项目: 本论文为湖北科技学院“鲁迅人格与创作跟浙东民间文化”项目成果之一,项目编号BK1210
以一般平常人的眼光来看,鲁迅的一生就是一个悲剧人生。因为他的人生道路中悲苦、心酸、沉重居多,欢欣、快乐、喜悦很少,短短的56年的人生历程充满了家庭的破败、生存的艰辛、兄弟的失和、疾病的折磨、无爱婚姻的摧残、长期斗争的残酷……鲁迅遭受到了如此深重的苦难,却没有让生活击垮,更没有绵羊般向生活妥协,反而直至生命的尽头都奇迹般地保持了一种刚烈秉性。
鲁迅的刚烈之性由他的“硬骨头精神”来集中阐释。他在和社会、敌人作斗争时,没有丝毫的奴颜婢膝,为友为敌,立场分明,用如椽硬笔,绝不姑息地诛扫一切恶势力一切丑类。而且,终生不悔。“我的怨敌可谓多矣,……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1](第6卷,p635)正如毛泽东所言:“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不仅与外界恶势力和黑暗势不两立,而且还敢于同自我作深刻的反省和斗争。这个真正的精神强者,宁可“抉心自食”、“自啮其身”,也拒绝走任何精神逃路,终其一生,都在坚持与黑暗决斗,又固执顽梗地背负着种种精神苦痛:悲愤、绝望、虚妄、凄怨…… 他在斗争的过程中曾经对痛苦对斗争的结果产生了怀疑,甚至有不可改变的绝望弥漫在斗争的心房。“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其实……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1](第11卷,p21)
冯雪峰高度评价了鲁迅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认为他始终具有一种“中国民族的战斗的传统的精神”,具体表现为:一是孔墨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传统;二是宋末、明季的“士大夫”阶级为民族而壮烈牺牲的正义的传统;三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时代对社会的大胆叛逆的传统;四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伟大的生活热情和人类爱的大诗人们的精神传统。透过冯先生的文字,我们感受到了他对鲁迅先生人格的盛大赞誉,同时也获得了对鲁迅人格关照的方式和角度,即从传统文化和其人格生成的关系入手去研究它。成就鲁迅伟大人格有多种复杂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但我们不可忽视浙东民间文化这个角度,而应该截取浙东民间文化来关注、甚至锁定浙东民间文化,来深入研究鲁迅的刚烈和它的深刻联系。这样从外向内转后,进一步锁定鲁迅头顶上的天空,透过浙东民间文化来看鲁迅,发现他人格中的刚烈特性和浙东民间文化有着深邃的文化关联。浙东民间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加上现实生活的融会,构成了独特的浙东民间文化氛围。由于浙东民间文化的浸染,鲁迅以刚烈为核心的精神品格、思维方式、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浙东民间文化的深深印记。究其缘故,是浙东民间的文化思想精髓,通过文化的传承和民间的积淀或直接作用、或间接投射在鲁迅身上,产生了很大作用。
一、刚烈来自浙东民间
鲁迅独立不倚的刚强个性由挥戈一击的斗士风采,和克制自身的精神苦痛的顽强意志构成。深深懂得鲁迅的朋友沈瓞民在《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中称他“斯诚越人也,有卧薪尝胆之遗风”,明确地指出了鲁迅的性格内质直接秉承了浙东的民风中的刚烈因子,其刚烈之性和古代越文化性格有着不可割裂的深刻渊源。越地开发较迟,春秋时期,还是一片殊域蛮荒的原荒之地。越民断发纹身,水行而山居,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中磨砺成一种强悍、坚忍的性格。他们“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绝书》卷8)。作为姒夏苗裔,先祖大禹胼手胝足征服洪水的力行精神一直涌流在他们的血管里。这个原始、落后而充满野性的民族,当时即以顽梗不屈而著称于世。击灭强吴、尽洗国耻的史实中,君王的躬自蹈厉,谋臣的设计献策,固然功不可灭,但根本上却是整个部族坚忍强悍的必然结果。卧薪尝胆、自强不息,正是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在越族中承传下来并融铸于华夏的整体文明,成为华夏民族最可宝贵的传统性格之一。古越民族强悍善斗的性格在历史迁衍中孕育成一种好剑之风,并进而形成一种剑崇拜的观念。史籍载:“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汉书·地理志》第八卷下)越人好剑,且善铸名剑。《越绝书》卷十一以富于神话色彩的笔调,推出了一幅越地名匠欧冶子铸剑的绚丽神异的场面:“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雨师扫洒,雷公击橐,蛟龙捧炉,太一下观,天精下之。”(《越绝书》)终乃铸成湛卢等五柄名剑,赢得后人“越民铸宝剑,出匣吐寒芒”的赞叹。当这种原始剑崇拜观念于句践之世被引向战胜强敌、洗雪国耻的民族目标时,越剑便成为一种励志图强、绝处求生的生命力量的象征。浙东历史上的慷慨悲歌之士,之所以多爱将自己的理想追求及一腔磊落之气,凝聚为兵剑意宝象,从陆游的“少携一剑行天下”,秋瑾的“夜夜龙泉壁上鸣”,到章太炎的“时危挺剑人长安”,原因就在此。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周氏兄弟刚烈性格于古越精神承传的一个侧面。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于“兵剑”皆情有独钟。鲁迅从少年的以戛剑生、戎马书生自号,到晚年撰作历史小说名篇《铸剑》;从让“这样的战士”高举投枪,到以“能和读者一道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来”的匕首命名自己的杂文,到盛誉陶元庆《大红袍》“握剑的姿态很醒目”[2](p1293),这寒刃闪烁、可折不可弯,凝聚着鲁迅战斗锋芒与刚硬之气的“兵剑”意象,正是古越剑崇拜原始风尚的现代升华。少年周作人也自号跃剑生,渴求仗剑跃起,拼搏异域:“毛锥误我,行当投笔执戈,从事域外,安得郁郁居此,与草木同朽哉?”[3](p232)就读南京时还苦练骑术,纵马驰骤,并以“宁使人目为武夫”为荣。[3](p359)跃剑生,投笔执戈,策马击斗,同样可以视为越人剑崇拜古习与尚武精神的流风余韵。
鲁迅的刚烈,还表现于他承续了浙东大山胎育的那种民间文化所特有的厚重刚勇。浙东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位于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形复杂,既有平原和盆地,又有山地和海岸。浙东南北界限分明,是四明、会稽群山和宁绍平原组成的。鲁迅认为浙东的民性和大山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曾经说到过:“浙东多山,民性有山岳气,与湖南山岳地带之民气相同”[2](p317)。“山岳气”,这里包含有稳厚朴诚、笃实泰然、刚硬劲直等诸多品格,在鲁迅的很多著述中,都特别推崇浙东人物刚烈不阿、迂执顽梗的傲骨与硬气。其中有自称“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鲁评其脾气“始终都是极坏的”[1](第3卷p510),虽九死不悔的魏人嵇康。还有被鲁迅称之为表现了“台州式的硬气”且“颇有点迂”[1](第4卷p482)的明人方孝孺,鲁迅盛赞方拒绝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而惨遭灭族,致使老小七百余口累累弃市。更有近代章太炎,鲁迅称誉他“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1](第6卷p567)。他们莫不表现出站立民间立场的个性特征:一身傲骨、疾恶如仇。这是鲁迅对大山赋予浙东历史人物的精神个性的发现与颂扬,亦是他自身性格的披沥与呈现。嵇康的果决刚直更是浸润到了鲁迅的骨子里。从嵇康到鲁迅,浙东人物熠熠辉耀出大山一般厚重的、孤傲强项的民间人文品格。
特意将因为多山而具有刚硬特质的浙东民性跟同样多山的湖南民性相比,鲁迅是想告诉我们,他所称道的的“山岳气”里包含着强烈的复仇精神。湖南古属荆楚之地,川泽区域与山岭地带并存错杂,构成全境复杂的地貌特征。与江汉川泽地域食物丰饶不同,峻岭丛山地区逼仄险恶,其民“筚路蓝褛,以启山林”,在极为艰的环境中开辟草莱。更兼与中原悬隔,礼制文化影响不及于此,故民性以怨愤执著、不忘复仇著闻。《论衡·率性》篇记有当时的谚语,所谓“齐舒缓,秦慢易,楚促急,燕戆投”,“楚促急”三字,便透露出其中复仇的信息。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秦末之际就使其强悍的复仇精神声闻大炽。民性所及,楚地民歌亦以怨愤、粗豪之气韵、格调为特色,而被楚汉之际的雄豪之士所乐于采用。项羽之《垓下歌》,刘邦之《大风歌》皆慷慨悲凉,即其中为世所重之著例。鲁迅敏锐地把握了这一个现象,还评析了其深刻原因道:“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誓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1](第9卷p385)反映出鲁迅对楚地强悍民风以及受辱必报、矢志复仇民性的深刻理解。楚国历史上以复仇精神闻世者代不乏人。与吴越征紧密相关的三个人物,文种、范蠡与伍子胥,即是楚人而以复仇著称者。文种、范蠡在灭吴兴越大业中是两个不可或缺的人物,而这场征战始终是以雪耻为号召的。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不惜毁弃君臣大节,掘平王墓,鞭尸三百。人谓其行之过甚,他答之曰:“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怨毒之深,历历如见。遭诬陷而被夫差杀害后,传说中的伍子胥化为潮神,日夕二度卷狂涛千丈,以泄怨怒。这是一个矢志复仇执著如怨鬼式的历史人物。这样的一个为复仇雪恨不仅大胆拒俗而且敢于抗天的、个性强悍的人物,一定会引起鲁迅的强烈共鸣的。鲁迅曾明确以伍子胥自况:“我就是伍子胥转世的。”[2](p1346)表示他对伍子胥执著的复仇精神,对诞生伍子胥的楚文化的强烈认同。强烈的复仇精神是构成鲁迅性格的核心要素之一。鲁迅的复仇精神形成过程中,浙东文化的本原而深刻的影响作用,众多研究者已作了充分而有说服力的论证。如今不妨推进一步说,鲁迅的复仇精神,主要当孕自浙东的“山岳气”,一般笼统地归结于浙东文化,是有失偏颇、不够精准的。
浙东大山给予的鲁迅还有一种朴素固执,这种朴素固执就是鲁迅所说的柔石身上表现的一种“台州式的迂”:迂执,迂阔,认准了目标,一直走到底,不撞南墙不回头。过于天真,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1](第3卷p482-483)这正是浙东大山区朴鲁民风的一种反映。鲁迅并不完全以这种天真、迂阔之气为然,却并未全盘加以否定,甚至可以说,他从内心上是喜爱柔石这出自至诚的天真,和颇有书生气的迂阔的。事实上,鲁迅性格也具有天真一面。鲁迅曾这样说自己:“倘若有人问我,可曾预料在‘革命’的广州也会有这样的屠杀?我直说,我真没有料到。姑不论我也是抱着‘美梦’到广州去的,……说我深于世故,一切世故都会没有用的。……还是太老实,太相信了‘做戏的虚无党’,真上了大当。”[2](p571)在血的教训下,鲁迅拋弃了轻信,却并未拋却天真。朋友与他的交往中,都会感受到他的真诚,坦率。相对交谈过程中,鲁迅“常常发出轻松的幽默,笑嘻嘻的,胸无城府”,“像个孩子似的天真的人”[2](p1337-1338)。鲁迅与许寿裳终生不渝的友情也佐证了这一点。鲁迅曾评许寿裳的为人:“许君人甚诚实,而缺机变。”[1](p13)鲁迅与许性格自不可皆同,但鲁迅认为他们相处的秘诀就是“彼此略其小节而取其大。”[1](第13卷p316-317)所谓“取其大”,至少包括了“诚实”。这正是浙东故乡民间文化赋予他们相似的性格特征。
二、杂文中的刚烈
马尔库塞指出:“人格是文化理想的承担者。”鲁迅人格中的刚烈和浙东民间文化的特性分不开。正像鲁迅、周作人、曹聚仁、冯雪峰等人所言,浙东“民气顽强”,“有山岳气”。《越绝书》云:“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汉书·地理志》云,越地之民“皆好勇”。在浙东文化史上,品格刚健的人物代有传人,有骨气的叛逆者层出不穷,艰苦卓绝的大禹,卧薪尝胆的句践,毁弃礼法的嵇康,都是品性刚强的“节概”之士,在民间有着深远的影响,以至于王思任后来说:“越乃报仇复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这是对浙东民间中有一种传承很久、在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复仇精神的高度概括。鲁迅对这种勇猛和刚绝心仪不已,曾经多次表示“身为越人,未忘斯义” ,浙东民间文化传统中的这种精神是鲁迅一生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这种“硬性”的文化性格,已经深深内化成鲁迅的人格精神,并生动淋漓地展现在其杂文创作当中。
鲁迅认定杂文的品格天生就是刚性的,而决不是软性的,就似“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那时的心情就是“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特别是处在中国社会现实异常黑暗、民族危亡的时刻,鲁迅清醒地指出“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于是鲁迅和国民劣根性开战,与复古派、国粹派、学衡甲寅派和民族主义文学派开战,与第三种人、新月派、现代评论派、论语派和人性论者开战,等等。他是在与因袭或非因袭,有意或无意的封建思想遗毒开战,与险恶的世相开战,与卑劣的国民心理开战,“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其锋所指,势如破竹、纷纷披靡。林语堂有一个对鲁迅的评价深得其神韵:说鲁迅在战斗时“睚眦欲裂,须发尽竖”,“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为战士。”
鲁迅是这样定位杂文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因为他吸取了浙东民间文化中的“硬性”气质,通过手中的笔进行文化批判和文明批评,批判不合理的封建节义思想和宗法制度,揭露国民魂灵的奴性,他不断战斗,向国民劣根性、伪士、统治阶级、还有一切守旧落后的势力宣战。因此,他的杂文也就相应地充满了骨气和血性,有慷慨激越之风、金刚怒目之气。
首先,鲁迅对浙东人的“硬气”的秉承表现在其杂文中,就是爱憎分明、感情激越、言辞锐利,如《友邦惊诧论》就用精辟的句子直截了当地揭露事物的本质: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统治下的连年內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在一连串的质问后,作者再掷出一句炮弹般的话: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这篇杂文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鲁迅的愤怒毫不掩饰,其情绪高亢而激越,这种愤怒和情绪又和犀利的语言、直接明了的表达,构成一种悲愤,还透出一种庄严之气。鲁迅还在《纪念刘和珍君》中,也表现了对统治者暴行的抗议,同时用痛彻的语句表现了对群众沉默的悲愤哀痛,于控诉中可见其表情凝重、感情沉郁,但文中又自有一股铿锵之力: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鲁迅对保守成性的中国人因为拒绝革新而找的“保存国粹”的借口,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热风,随感录,三十五》)
但是,无论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而况保古。现状就是铁证,比保古家的万言书有力得多。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忽然想到六》)
鲁迅的每篇杂文,都充分显示出一种“战士”品格,将浙东民间的刚硬之气发挥得淋漓尽致:感情充沛、说理透彻、气势磅礴,每句话都如匕首和投枪,直插敌方要害,使其动弹不得,毫无反抗之力!
浙东民间对不达目的会誓死纠缠到底的一种人称作“破脚骨”,鲁迅对这种人的精神很是赞赏。他提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善于保守,连搬动一张桌子都要付出流血的代价的国家里,从事社会改造和国民灵魂改造的革命者,就必须具有这样一种浙东民间“破脚骨”的精神。他的杂文,就准确地实践了他的这一主张。他主张“痛打落水狗”(《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因为落水狗虽然一时难堪而貌似可怜,但一旦它上岸,并不痛改恶习,照样张嘴就咬人。鲁迅对于黑暗势力及其帮闲和帮忙,从来不吝给予连珠炮式的痛击,得理不饶人,抓住敌方要害,一口咬定绝不放松,直到置敌于死地。例如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鲁迅连续写下了《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等六篇杂文,集中抨击了北洋军阀政府制造的这一“死虐险狠”的暴行,从不同的侧面揭露了惨案的真相,批驳了帮闲和帮忙文人的造谣和中伤,激愤之情,溢于言表,一篇接一篇,以连贯的气势,形成一种排山倒海的力量。
其次,鲁迅也讲究把“刚烈”艺术地在杂文中表现出来。他提出,杂文的用语必须“曲折”,外表上的锋芒太露,也足以把“诗美”给杀掉。比如,他的《现代史》一文,目的在于揭露军阀政要虽然换来换去,但无非是搜刮民脂民膏,盘剥百姓。但鲁迅对于这些只字不提,只是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方,变戏法的人,不断地变换戏法,一会儿是孩子上天去了下不来,变戏法的人拿出铜锣,向观众要钱;一会儿是孩子死了活不过来,要他活过来,又向观众要钱,总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变换着手法,骗取民众的钱贱财。一旦有人要到幕后去观看真相时,变戏法的人就凶相毕露,动粗驱逐,或者动手打人。文章写到最后,说:“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这让人忍俊不禁,但却含蓄而形象地揭露了“现代史”的本质:那一部现代史,实质上就是军阀、要人变着法子搜刮民众的历史。文章虽然经过了层层的“包装”,看似幽默,而实质上是图穷而匕首见,寸铁足以杀人,一剑封喉!“幽默”的假面背后,站着的是一位金刚怒目式的“战士”。
除了擅长用擅长形象化的含蓄、曲折的表达之外,鲁迅也非常擅长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来击倒论敌。例如,在他和陈西滢有关“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的论战中,陈西滢把女师大比作是“毛厕”和“粪车”,并说鲁迅骂人,就像是赵子昂画马,对着镜子做个马姿势,所画的人正是他自己。鲁迅反击道:“赵子昂也实在可笑,要画马看着真马也就够了,何必定做畜生的姿势……倘若陈源教授似的信以为真,自己也照样做,则写法西斯时做一个法姿势,讲‘孤桐先生’的时刻立刻做一个孤姿势,倒还堂哉皇哉,可是讲‘粪车’也就伏地变成粪车,说‘毛厕’即需翻身充当便厕,未免连臭架子也有些失掉吧,虽然肚子里本来满是这样的货色”(《华盖集续编·不是信》)。笔锋之锐利,抓要害之准确,都充分显示出鲁迅是一位充满了智慧的“战士”,即他并不是许褚式的莽汉,而是一位有勇有谋的猛士。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绍兴的“师爷”笔法对于鲁迅的影响。正因为是擅长抓住要害,擅长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鲁迅几乎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让所有的论敌都甘拜下风。
总之,鲁迅总是和普通民众站在—边,生性耿介、质直,个性泼辣,充满了斗士的风采和气质。这种刚烈的性格特点,上溯远者有魏晋时的嵇康,稍晚有清代的徐渭,近者有章太炎,乃至最为亲近的更有鲁迅自己的祖父周介孚,到了鲁迅这里,真所谓斯文未绝,更见其发扬光大。鲁迅的刚烈之性由浙东民间文化滋养出来,其秉性和创作又丰富和发展了浙东民间文化中的刚硬特质。浙东民间文化的“硬性”传统,以丰富的血脉流贯于鲁迅的杂文创作当中,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鲁迅回忆录[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3]周作人.周作人日记[M]北京:.大象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