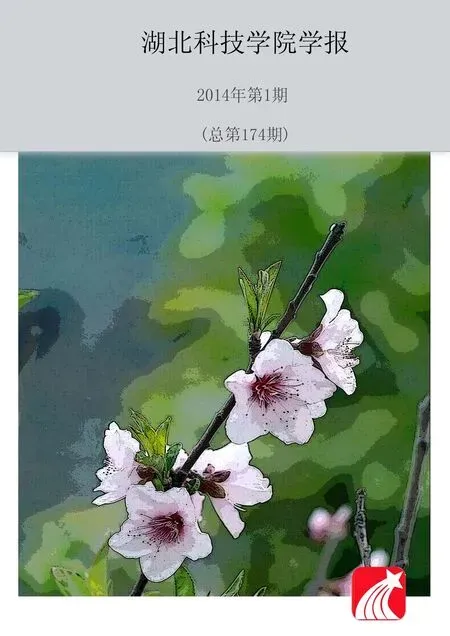对我国高校行政主体定位司法变迁之考察*
向 前
(四川民族学院 政法系,四川 康定 626001)
*收稿日期:2013-09-17
科研项目: 本文系四川民族学院校级项目“从高校侵权的司法实践看高校法律地位的变迁”阶段性成果之一。
司法实践显示,因高校教育侵权所引发的高等教育诉讼案件,均涉及到高校对学生受教育权的侵害,且在诉讼形态上多为行政诉讼,如以“田永案”和“刘燕文案”为例,就是因高校涉及对学生“学业证书、学位证书获取权”的侵害而引发的行政诉讼。然而,根据行政诉讼“民告官”的基本特性,对“学生状告高校”的行诉立案受理,首先必须证明:高校具有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主体资格。为此,对高校行政主体资格的确认,就成为该类案件行诉立案的关键。在此笔者仅以历年来高等教育纠纷的相关处理情形为视角,考察我国法院系统对当前高校行政主体的司法定位,以期为我国高等教育立法的完善提供司法实务上的参考。
一、对高校行政主体资格的感性认定:行政授权机关
1998年的“田永案”作为高等教育行政诉讼的第一案,也开启了对高校行政主体资格证明的司法历程。然而,就该案的司法判决分析,其对高校行诉被告主体资格的认定不仅显得过于粗糙,甚至有学者笑称似乎该案是出于“行侠仗义”的原因而受理。 判决中,北京海淀区法院对高校行诉被告主体资格证明如下:首先其承认高校的事业单位性质,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主体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而由于“这些单位、团体与管理相对人间不存在平等的民事关系”,“……为了维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将其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适用行政诉讼法来解决他们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 正如海淀法院的一位法官所说,“本案在确定被告时运用了一个“授权机关”的技术,这是法官为了使自己的判决具有合法性,获得社会的认可,而运用的一种技术。 为此,这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无论什么机构,只要它拥有一种权力,而这种权力是单方面的,就必须受到监督。 为此,有人批评法院的这种做法是“法官对法律的执意的歪曲和对判决极端草率而成为一个反面的典型。”
虽然在本案结束的五个月后,北京海淀区法院又迎来了一个纠正此前略显感性和粗糙的高校行政主体资格论证方法的机会——“刘燕文案”。但对于本案中高校行政主体资格的此种“毫无法律根据”的推理论证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却在此后的高等教育侵权纠纷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尤其是在该案为《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收录后,由这样一个“无根据的论证过程”所确认的“高校行政主体资格”,给各地方法院带去的不是普遍的清晰,反而“使得各地法院在面对高等教育行政诉讼案件时仍然显得谨小慎微”。 从而出现了在随后的高校涉讼案件中,对学生受教育权的保护严重失衡的局面。“各地法院对是否受理此类案件一直持不同的态度, 发生截然相反裁判的情况已不是个别现象……” ,究其原因其根本乃于各地法院对高校行政主体资格定位的不同。总体而言,主要有三种态度:
第一,承认高校行政主体资格的法院则受理学生的起诉。如2000年的“天津某校轻工业专业学生刘兵诉学校勒令退学案”,以法院作出裁决,准许其撤回起诉而结束。
第二,持否定态度的法院则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如2002年“重庆邮电学院女大学生怀孕案”以及2002年“北京某大学经管学院女学生严某因考试作弊被学校勒令退学案”等均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
第三,而对此把握不准的法院则裁定中止审理,等待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如2004年的“拥吻案”,法官介绍说,“……因公办院校作出的学校管理行政行为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至今尚未作出答复,因此才裁定中止审理此案”。
二、对高校行政主体资格的理性确立: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在经历了对高校行政主体资格的感性认定以后,我国司法实践在“刘燕文案”中迎来了对高校法律地位第一次理性认定的契机。从“刘燕文案”一审判决可知,尽管其一审行政诉讼所列被告为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但其有关行诉被告主体资格的论证方法具有明显的普遍性:其引入了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四款中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概念,即“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
为此,其认为“高等学校作为公共教育机构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是,其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等的权力是国家法律所授予的”,“北京大学作为国家批准成立的高等院校,在法律、法规授权的情况下,享有代表国家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位证书的权力”。“北京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九条的规定,设立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法行使对论文答辩委员会报请授予博士学位的决议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权,这一权力专由该学位评定委员会享有,故该学位评定委员会是法律授权的组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项规定,具有行政诉讼的被告主体资格”。 至此,我国司法实务以当前立法为依据,确立了高校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行政主体地位,为高等教育行政诉讼的立案提供了法律解释。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在一审庭审中败诉的北京大学提起了二审上诉,而二审法院在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竟意外的以“案件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而裁定“驳回起诉”。同一案件,同一个法院,竟先后做出了“出尔反尔”的判决。这一“惊天动地”的反复,损害的不仅仅是法院的司法权威,更重要的是,它激起了人们对这一最终裁定“背后所隐藏故事”的可能猜疑——这是否代表了国家某些更高层面对高校教育侵权纠纷的一种否定性态度?毕竟在刚刚几个月前为最高人民法院所收录的同类案件“田永案”,就因法院判决“缺乏法律依据”稍显感性,而引起了社会公众的负面议论。随后,各地方法院对于高校教育侵权纠纷在是否立案受理方面,各地的实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实现完全统一。
三、对高校行政主体资格的最终落实:法律、法规或规章授权的组织
或许是为了缓解我国司法系统在高校教育侵权案件处理中,司法保障严重失衡的尴尬。此后,在高等教育领域国家立法活动开始逐渐活跃起来,至此,随着相关教育法律、法规及规章的完善,对高校教育侵权纠纷的解决开始逐步走上了司法保障的正轨。尤其是在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程序提审“甘露不服暨南大学开除学籍决定案”后,其明确提出“学生对高等院校作出的开除学籍等严重影响其受教育权利的决定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其标志着最高人民法院对高校行政主体资格的明确肯定。
首先是《行政复议法》(1999年4月29日发布——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颁布,将受教育权纳入了行政保护的范畴。其第6 条明确规定,“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的”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为受教育权的行政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将行政诉讼受案的范围扩大到对“人身权、财产权以及受教育权”等合法权益的保护。
其次,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3月8日发布——2001年3月10日施行)的出台,再次扩大行政诉讼的被告范围,在原有“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基础上增加了“规章授权的组织”,即其第20条第三款规定,“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超出法定授权范围实施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实施该行为的机构或者组织为被告”。为此,将高校行政主体资格最终落实到“法律、法规或规章授权的组织”。
此外,作为对上述行政诉讼被告范围增加了“规章授权组织”的扩大回应,2005年3月29日教育部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并废止了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7号)、《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教学[1995]4号)。与此同期教育部还发布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等重要教育规章,并废止了此前教育部颁布的各有关国家教育考试的违规处理规定,后并与2012年1月5日再次对其作出重大修订。另外,鉴于司法实践中学历、学位证书颁发类教育案件频发,并且原有《学位条例》所存在的程序缺陷,2004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也及时作出了修订。
四、总结
目前为止,由我国高等教育侵权所引发的行政司法实践活动,已经走过了将近十五个年头,也正是藉由这一司法审判实践的大胆突破,推动了高等教育行政诉讼之勃兴。然而,必须正视的是,目前我国有关高校法律地位的定位,均来自于对司法实践活动经年累月的司法总结,属于司法解释的成果。但由于我国的大陆法系传统,并不承认法院判例的造法功能,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也仅具有指导意义,不能成为地方法院判决的法律依据。同时,就当前的教育立法来看,对高校法律地位的确立,也仅仅是为法院对高校的司法定位增强了解释功能,并未有相关立法对高校法律定位作出直接表述。为此,笔者以为,为保证司法实务与国家立法间的一致性,我们应当在未来教育立法中,将当前司法实践对高校的司法定位作为未来高校立法的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钟会兵.法律的误用与事实的偏差——从两个典型案例看教育行政诉讼的两点缺失[J].河北法学,2004,(08).
[2]李富宽.北大法治之路论坛[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3]毛美芳.高校教育行政诉讼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4]程燕雷.高校学生管理纠纷与司法介入之范围[J].法学,2004,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