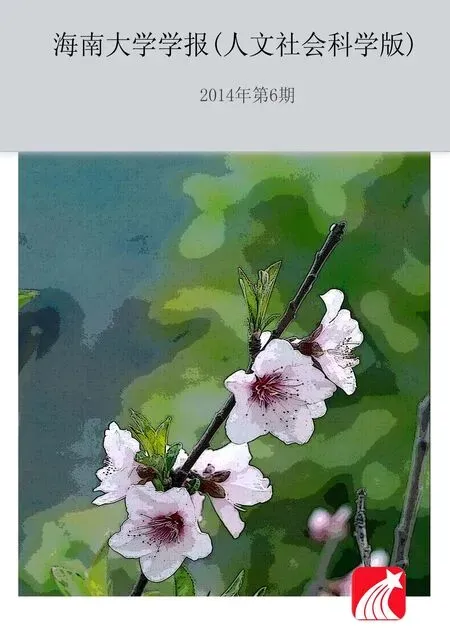“桃源”与“扁舟”
——从意象的选择看秦观与苏轼的贬谪心态
姚 菊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京,210023)
一 桃源望断无寻处:从“桃源”意象看秦观的贬谪心态
“桃源”最初出自陶渊明《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主题是“一个不乱而无税的理想世界”,王维作《桃源行》,桃源则成为“难见难觅的‘灵境’、‘仙源’”[1],都是代表了一种难以达到的理想境界,后作为一种具有独特象征意义的意象固定下来,代表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秦观笔下的“桃源”,以《点绛唇》(醉漾轻舟)、《踏莎行》(雾失楼台)为突出代表,吸收了陶渊明和王维诗中的象征意义,并且结合了刘晨、阮肇之典,重点转移到了虚无之主题,暗含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像《桃花源记》中的武陵人无意中到了桃花源,后来再寻找却已不见,立意已不再是桃花源中的理想境界,而是放到了整个过程上,突出美好的转瞬即逝,一切都是虚幻一场,强调了桃源的空幻性,暗喻了秦观对贬谪生活的绝望以及否定。而对桃源的孜孜追求,昭示了主体抵制的心理姿态。我们来看《踏莎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2]
“楼台”代表美好之愿景,“津渡”暗示济引之道途,“失”和“迷”说明无论是目标还是路径都已不复存在,仙境已经荡然无存,再也追寻不到,而“雾失”、“月迷”说明有外界阻隔,结合秦观在党争中之遭遇及目前贬谪之处境,旨意遥深。“雾”、“月”、“楼台”、“津渡”都是词人幻想之景,桃源亦非真实之境,都是作者意念中的产物,用来表现精神和心灵领域追寻不得、阻隔失落的孤独、怅惘、迷乱,而桃源的选择正与此心境互为表里,是悲哀之由,亦是必然之果。“雾失”三句因情设景,营造一种悲迷之境,而这种绝望不是无端而来,“可堪”两句触景生情,身之所感是孤馆春寒,耳目所接是杜鹃斜阳,是桃源“无寻处”的触发之源,又是引发“望断”的现实之因。“郴江”两句,更发凄厉之音。这两句实非一种理性的思考,而是迷狂状态下的心理渲泄,以一种看似无理却饱含沉痛的语言,借以自喻,发出感慨叹息之意,表达一种无可奈何的情感。秦观对于目前处境无法忍受,心理上排斥抗拒,一直到《自作挽词》中还说“奇祸一朝作,飘零至于斯”,他始终都无法忘记绍圣之贬,把眼前的一切困境都归咎于党争所带来的迁谪,如果政治清明,没有党争,就不会遭贬,再退一步,如果自己不卷入党争,就不会有后来之祸。不论归咎于哪一个原因,心理姿态是一致的,都是抵制,正因为抵制,又进一步造成心理上的恶性循环。
该词作于绍圣四年(1097年)春,是年二月秦观被编管横州,《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零二逐元佑党人条记载:“郴州编管秦观移送横州编管。其吴安诗、秦观所在州郡,差得力州职员,押伴前去,经过州军交割,仍仰所差人常切照管,不得别致疏虞。”[3]自贬谪以来,秦观的心理有一个变化过程:
绍圣元年(1094年)春三月,秦观改馆阁校勘,出为杭州通判,闰四月,在赴杭途中落馆阁校勘,改左宣德郎监处州茶盐酒税,后又改左宣议郎,为从八品,依旧监处州茶盐酒税。此时虽然遭贬,但有职务在身,秦观也在力图对自身的境况进行调节,总体比较乐观,心境也较为平和,意志上还没有消沉,苏轼亦云:“少游谪居甚自得。”(《与黄鲁直简》)[4]5744
绍圣三年(1096年)春,秦观再次被贬,《宋史》载其“贬监处州酒税,使者承望风旨,伺候过失,既而无所得,则以谒告写佛书为罪,削轶徙郴州”[5],《挥麈录》亦载:“两浙运使胡宗哲观望罗织,劾其败坏场务,始送郴州编管。”[6]秦观在《陨星石》中说“畴昔同列者,到今司赏刑”,所表达的愤怒盖与此次遭贬有关。此次被编管有专人押送,行程相当紧张,在赴郴州的途中,唯有一老仆滕贵相随。《祭洞庭文》有云:“绍圣三年十月己亥,朔十一日丁卯……老母戚氏,年踰七十,久抱末疾、尽室幼累,几二十口,不获具行,既寓浙西。方令男湛,谋侍南来。”[7]之前在作处州监茶盐酒税时,虽说遭贬,但还有职务,家人都在一起,心理上不至于太过孤单,但此时秦观已没有任何职务身份,也就意味着没有经济来源,此期处境及心理落差较大,心境亦趋向悲伤。
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编管横州之命下达,不但回归无望,还被迁到更远,这个打击更加沉重和巨大,加上悲伤之境的累积,在精神上很容易步入一个极端,《踏莎行》是其典型呈现。关于秦观贬谪之后的心理状态,《好事近》一词亦可作为参照:
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转空碧。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好事近》)
该词属于梦中所作*关于该词的系年有不同说法,本文取“处州说”,时间约为绍圣三年。,上片隔绝尘寰,但“飞云当面化龙蛇”,笔头一转,入为奇诡,这里选取“飞云”的意象变化来暗喻内心的变化,本来是天空卷舒有致的云朵,忽然间一下变成了龙蛇的形状;“夭矫”,用以形容飞云变化之状,笔力奇而且横,与秦观一向下语轻婉的特点截然不同,表达了内心对突发巨变的落差感受,“转空碧”,一下子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天空又回归一片碧蓝,这几句实可形容秦观在这次政治悲剧中最为敏锐的触觉与感受;“龙蛇”意象的运用,暗含其可怕与惨重,“夭矫”,说明其势头之劲无力承受,“转空碧”,变化之快,如同梦幻。最后只能“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在这种沉重的打击下,心灵不堪重负,宁愿选择醉中忘却一切,那么,对于美好的逝去以及突发的灾难或许就可以逃避,不用再承受沉痛的精神折磨。在经受了无数次的心灵挣扎之后,秦观最终把灵魂安放到了滕州的光华亭下,真正实现了“了不知南北”,所以后世以为该词为“词谶”。周济云:“隐括一生,结语遂作藤州之谶。造语奇警,不似少游寻常手笔。”[8]
词中有极深的绝望,是对一生之总结,亦是对一生之否定,可以说是秦观的情感承受限度达到极致的产物,所以有人把它当绝笔之作,不单单是因为“词谶”,主要是由于这首词中所透露的生命达到极限时候的奇诡梦幻,是情感不堪重负的精神变异在言语中的外现。秦观的词笔最善于刻画心灵最细微的颤动与体验,该词即是其灵魂痛苦之下极端的心理映像,把抒情诗在由外物通向内心的道路上,又推进了一层,笔触之深之细,都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龙榆生亦说:“其出笔之险峭,声情之凄厉,较之集中其他诸作,判若两人。此环境之转移,有关于词格之变化者也。”[9]
到贬谪后期,秦观的思想慢慢走向虚无与否定,当然这种否定是在深深依恋的基础上,继而走向了反面的极致。《望海潮》(梅英疏淡)、《千秋岁》(水边沙外)等词中对过去尤其是对元佑时期苏门诸人交游集会的反复追忆,说明了秦观对世情的牵系以及内心深处不能释怀的痛苦,他也在试图去解脱这种痛苦,却因此走向了绝望。因为苦痛太深沉了,心灵再也承受不起,只能去否定一切,尤其是对过去的否定,因为否定之后内心就不会再有过多的纠缠,一切只如梦一场。但这与苏轼的“人生如梦”又有所不同,苏轼是内心有着深远的忧患并且认识到了情累之后,积极的理性的去寻求思想与情感上的超脱,进而达到一种超越,在不能彻底摆脱情累的同时尽量最大化地达到主体的自由,在思理上有着明确的意识。而秦观的人生思考及判断更多地基于感性的层面,是最本能的内心直观感受,他对于情累的重大痛苦是深陷其中的,当生命承受的限度达到最大的时候,只能偏向另外一个极致,就是用否定去试图看淡,不再纠缠,进而寻求内心的安定。
可是,终究秦观也没能超越出贬谪的困境,《自作挽词》仍饱含沉重与哀伤。陶渊明曾有《挽歌诗三首》,虽亦有悲哀之语,但诗意的归结点实不在此,而是对悲哀的思考与超越,是对生与死的理性思考,进而达到一种冷静观察生命、置身生死之外的境界。而秦观作挽词,却是实实在在的悲哀心境。秦观在情感上太过于执念了,始终都不能从过去中解脱,更何谈生死?胡仔即说“东坡谓‘太虚齐生死,了物我,戏出此语。’其言过矣。此言惟渊明可以当之;若太虚者,情钟世味,意恋生理,一经迁谪,不能自释,遂挟忿而作此辞”[10],所以苏轼不无惋惜:“已而北归,至滕州,以八月十二日,卒于光华亭上。呜呼,岂亦自知当然者耶”[4]7727,这些与贬谪中悲哀绝望的心态恐怕多有关系。
桃源本身是一种理想,一种可望而不可即、永远无法达到的境界,秦观一直对桃源孜孜追求,这暗示了对现实抵制的姿态,用对另一种美好的追寻来抵御眼前的困境,可这种美好却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所以,这种属于无效抵抗,抵御的结果只能走向更深的绝望。
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从“扁舟”意象看苏轼的贬谪心态
苏轼笔下出现较多的则是“扁舟”意象,且看下面例子: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
来往一虚舟。聊随物外游。(《菩萨蛮》)
我梦扁舟浮震泽……明日西风还挂席。(《归朝欢》)
轻舟短棹任横斜,醒后不知何处。《渔父》
江边骑马是官人,借我孤舟南渡。《渔父》
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水龙吟》)
“扁舟”意象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楚辞·渔父》和《庄子·杂篇·渔父》中的渔父形象,是隐士的象征,代表着超脱旷达、恬淡自适的文化内涵。先秦时代,隐士颇多,他们畏世远遁,洁身自保,或躬耕田野,或避居山林,为后世提供了隐逸的典范。儒道两家深刻影响并调剂着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渔父扁舟独钓的意象遂成为诗歌中常用的艺术典型。另外一个是范蠡扁舟五湖之典,《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广皮,之陶为朱公。”[11]后世遂用以指功成身退、归隐江湖,并且常常与谢安的东山之志一起,成为士大夫身在庙堂之上而有归隐之心的效慕榜样。从上文所举例子可以看出,苏轼笔下的“扁舟”意象兼有以上两个方面。
苏轼反复使用“扁舟”,意在表达一种强烈的归隐之志,归隐意味着离开政治中心和世俗功利,获得主体的自由,实是一种自由人格精神的象征。这其实也代表了对眼前的一种逃离,但却是现实的,是可以达到的,具有主体的能动性,用另一种现实选择来代替目前的处境,“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也不是特别难以实现。苏轼的贬谪生涯有两个时段,一段是元丰二年(1079年)至元丰七年(1084年),因乌台诗案谪居黄州五年,另一段是绍圣元年(1094年)至元符三年(1100年),谪元祐党籍居惠州和儋州七年。扁舟象征着自由,取向于未来,小舟归去萦绕了苏轼的一生,对此的思考和实践在贬谪期间臻于极致,并且有着内在的动态变化与流动曲线。
苏轼在贬谪初期是悲伤、沉痛的,但是他能让内心很快适应眼前的处境,继而在悲伤中进行深刻的反思,寻求进一步解脱的方式,从而呈现出了由悲到旷的超越过程*王水照在《苏轼的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苏轼研究》,第84页)中把苏轼的贬谪心态概括为“喜-悲-喜(旷)”,本文意在凸显苏轼的超越心理机制,故大而化之,重点放在转变上。③ 王水照《苏、辛退居时期的心态平议》中说“苏对陶却是‘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的全身心投入”(《苏轼研究》第108页),陶渊明《拟古九首》其五为:“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勤无此比,常有好容颜。我欲观此人,晨去越河关。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第112页)苏轼所云“我即渊明,渊明即我”,是说陶诗中“东方有一士”和“我”均指渊明,意在表明对陶渊明之理想人格的认识与理解,或非自指。。在这个心态变化曲线中,有一个代表性的最高点,亦最能全面体现苏轼的生存性格及人生转向,那就是《临江仙》。“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终极追寻是苏轼超越型心理机制的基点,贯穿其思想的始终,在黄州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并在南迁之后继续升华、臻于极致。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12]190
词中有一种深深的自我矛盾与强烈的心理挣扎,虽说只有几句,但心思的流动脉络复杂而有序,很能体现“扁舟”在东坡生命和思想中的价值取向。醒了又醉,有忘却世事之感,力图去模糊主体的存在感,“归来仿佛三更”、“敲门都不应”,泯灭了时间,泯灭了空间,茫茫时空,只剩下一人一杖一江水。这里有两个自我存在,一个是社会束缚中的存在,“醒复醉”代表想要逃离这种存在,一个是个性自由的存在,“倚杖听江声”意在寻找并突出此种存在,“长恨此身非我有”,很好地表达了这两种存在感的激烈冲突,“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设想的理想方案,是挣扎过后思想与情感的最终归宿,虽然并不一定真能“忘却营营”而去实现它,但它提供了一种心理皈依,是主体在两种存在感激烈冲撞下的生存选择。
追寻主体自由,一是对社会束缚与压制的反抗,另外就是对自身思想局限的挣脱,归根结底也是对人处于现实中所接受的价值判断与影响的超越,即“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13],当价值观念和主体自身没有办法完美结合的时候,亦会出现极度不自由的矛盾状态,“长恨此身非我有”、“老去君恩未报”、“何时忘却营营”正是对此种矛盾的最好表述,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独棹小舟归去”,则是个体生命在社会中受到压制、自身价值观念出现矛盾两重因素所造成的逃离,代表的是对自由的极度渴望与倾心追寻。扁舟是自由的象征,在这里实是提供了一个桥梁与渠道。
超越是因为束缚,是因为被限制,超越是为了获得自由,即便身体及行为上不能,精神上的超越总能给主体赢得更多的空间。所以,宋代士大夫的超越精神是其现实处境极度压抑、极其不自由的产物,同时也代表了士大夫精神追求和人生思考的最高极限。苏轼超脱的根本在于总能在挣扎过后重新找回主体的自由独立,哪怕只是有限范围内的,他能够在极小的范围和环境中寻找到个体独立的空间,挖掘到自由的乐趣,这样,不管外在环境束缚性有多大,也磨灭不了主体的自由因子。这一特点在南迁的磨难中日渐成熟,并且很好地解决了前期深层的思想矛盾挣扎,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秦观南迁,绝望和悲伤的迁谪心态体现得比较明显,而苏轼南迁之后,因为有了黄州时期对痛苦的深切体验以及反思,已经具备了对贬谪苦难的承受能力,虽也有过短暂的悲伤,但那只是面对重大变化之时人的本能反应,很快苏轼就坦然接受了一切,不用费力地去排遣,不必建立强固的心理防线去抵御,接受一切的遭遇与心理反应,似其评陶所云“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书李简夫诗集后》)[4]7682对于一切物我得失,都不再执念,而达到一种完全顺应天然,身随百事而动,心与万物同化的心物一体阶段。这样,就在极大程度上淡化了主体的不自由,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当心物融为一体的时候,不论外物如何变化,心都能易地而处、顺境而动,心与物之间的矛盾被降到最低,精神和心灵的自由也就达到最大,在桎梏尘网中,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会因此而臻无上之境。苏轼亦有一首《和陶桃花源》,可与秦观笔下的桃源作对比:
凡圣无异居,清浊共此世。心闲偶自见,念起忽已逝。欲知真一处,要使六用废。桃源信不远,杖藜可小憩。躬耕任地力,绝学抱天艺。臂鸡有时鸣,尻驾无可税。苓龟亦晨吸,杞狗或夜吠。耘樵得甘芳,龁啮谢炮制。子骥虽形隔,渊明已心诣。高山不难越,浅水何足厉。不如我仇池,高举复几岁。从来一生死,近又等痴慧。蒲涧安期境,罗浮稚川界。梦往从之游,神交发吾蔽。桃花满庭下,流水在户外。却笑逃秦人,有畏非真契。[14]
苏轼在诗序中说:“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者乎?”对于王维以来关于桃源的神仙主题给予了否定,仙境是不存在的,这一点与秦观对于桃源的认识截然不同,接着又对陶渊明笔下的桃源进行自我发挥。“却笑逃秦人,有畏非真契”,进一步超越了简单的逃离、归隐,而上升到“凡圣无异居,清浊共此世。心闲偶自见,念起忽已逝。欲知真一处,要使六用废”,通过心物合一获得真正的身心自在,“子骥虽形隔,渊明已心诣”,虽身处谪居,却以自己的方式寻求个体的自由与解脱,这一点与东坡晚年和陶的精神实质是相一致的。且看《和陶东方有一士》:
瓶居本近危,甑坠知不完。梦求亡楚弓,笑解适越冠。忽然返自照,识我本来颜。归路在脚底,殽潼失重关。屡从渊明游,云山出毫端。借君无弦琴,寓我非指弹。岂惟舞独鹤,便可摄飞鸾。还将岭茅瘴,一洗月阙寒。
对于苏轼来说,“扁舟归去”的愿望由来已久,无奈命运多舛,既没能归老故园,也没能归隐山林,却在岭南瘴雾地,幡然顿悟,识却本心,人生无处不适意,何处不归来,对于主体自由的追求再也没有了重重阻碍,最终心诣渊明,殊途同归,超越贬谪处境,上达吾心自由。苏轼曾跋陶诗云:“此东方一士,正渊明也。不知从之游者谁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意即说东方一士是渊明,从游者亦渊明,合其二者是陶渊明对于本心志节的坚守如一,实本诗中的“屡从渊明游”,亦可如此看,表达深处贬谪安然适意之心境。
总之,扁舟的追求和归来的愿望从黄州时期解脱困境的精神支柱而演变为了另一种方式的躬身践行,扁舟所象征的自由和灵魂栖息,得到了最高程度的实现,也是苏轼一直以来在贬谪处境中心理调试与人生探索的极致。
三、为情所役、有情而不役于情:心态不同的原因分析
从意象本身的象征意义及文化内涵上来说,无论是陶渊明的无税世界还是王维的神仙境界,都是理想中的、不可实现的,秦观使用桃源的意象用来指已经逝去的美好的岁月,也是没有办法再回来的,都是通向引人绝望的虚无的世界;而扁舟归隐,却是一种已经有前贤实践的可行的现实选择,面对眼前的困境也想要逃离,但却不是回到已然逝去的时光,而是打算将来的去向,是为了要克服目前困难而给自己的一个希望和解决方案。另外,从时空逻辑上来说,回到过去本身就是对现在的一种否定,而计划未来却是对现在的一种接受,因为要通向将来的前提是走在现在。这种逃离实是对困境实现了一种心理上的缓冲,有利于对眼前事实的接受与化解,“扁舟”象征着心目中对眼前现实的超越之后的、更为高远的可以实现的境界,这在心理上有一种驱动力量,引领着主体接受并克服眼前的困难从而实现一种超越和解脱。因此,秦观词中的桃源意象和苏轼词中的扁舟意象都不是偶然的,它们分别代表了绝望和希望、抵制与接受两种不同的主体心理。
缪钺说:“吾国古人之诗,或出于《庄》,或出于《骚》。盖诗以情为主,故诗人皆深于哀乐;然同为深于哀乐,而又有两种殊异之方式,一为入而能出,一为往而不返。入而能出者超旷,往而不返者缠绵。……盖庄子之用情,如蜻蜓点水,旋点旋飞;屈原之用情,则如春蚕作茧,愈缚愈紧。”[15]秦观与苏轼亦可视为用情殊异的两种代表。在面对困境之时,秦观是一直抵制,不愿接受,反复挣扎,直至精疲力竭,是情累下的沦陷,最终为情所役;苏轼则是坦然接受,再行消解,尽力解脱,是钟情与体验后的超越,终至有情而不役于情。
秦观的情感是属于春蚕作茧式的,他一直都不能摆脱,不能超越于物情之上,词中有大量的追忆之语。追忆是因为不舍,是因为放不下,对于过往终究不能释怀。且看下面例子:
长记误随车。(《望海潮》)
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江城子》)
前欢记、浑似梦里扬州。(《梦扬州》)
天涯旧恨。(《减字木兰花》)
江山满眼今非昨。(《一斛珠》)
新欢易失,往事难猜。(《满庭芳》)
兰桡昔日曾经。(《临江仙》)
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千秋岁》)
前事空劳回首。虽梦断春归,相思依旧。(《青门引》)
回首落英无限。肠断。肠断。人共楚天俱远。(《如梦令》)
由着重号可直观地看到大量的追忆字眼,秦观总是想要寻找过去,想要通过对美好回忆的追寻来消解掉眼前的痛苦,无奈残酷的现实处境,使得回忆反而增添无数的伤感,这实是一种不愿接受现实、抵触的处理方式。人在面对痛苦时,都有自动防御机制,秦观选取了用追忆来抵触的方式,越是追忆,越是痛苦,最后沉溺于往事不能自拔。
人的心理与情感落到了一个最低点之后,反而会有一个回升过程,只是每个人心理最低点的承受水平不同。秦观也试图去接受过,可最终走向失败,也许是超出了他自身心理承受的最低限度。这与其自身的经历也有关。进士的身份在宋代的士大夫群体中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进入仕途以及士大夫生活的标签,而秦观却多年流连科场、仕途不顺,贬谪之后打击更是接踵而至,在苏门群体中,命运的悲剧性相对较强。
考上进士之后到贬谪之前的近十年间,秦观与苏门成员交游、诗歌唱酬,可以说是其人生中最为得意的一段时期,所以他后来在词中不断地追忆,留恋的不一定是官位声名,而是身份的认同感以及心理的幸福感,在秦观短短的五十二年的生涯中,十年的美好时光转瞬即逝,而后就是漫长的七年贬谪之苦,因此,这十年在作者的记忆中就变得异常的珍贵,总是追忆,总是复述。
过往是不可复制、不可重现的,秦观太过执着于追想记忆,而苏轼的时空意识是趋向于空幻的,有大量“吾生如寄”、“人生如梦”之语:
吾生如寄耳,宁独为此别。别离随处有,悲恼缘爱结。(《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其一)
吾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过淮》)
吾生如寄耳,何者为祸福。不如两相忘,昨梦那可逐。(《和王晋卿》)
聚散一梦中,人北雁南翔。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谢运使仲适座上送王敏仲北使》)
吾生如寄耳,何者为吾庐。(《和陶拟古九首》其三)
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郁孤台》)
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
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西江月》)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念奴娇》)
万事到头都是梦。(《南歌子》)
生如暂寓,则眼前都是转瞬即逝的,更勿言已经逝去的过往。宇宙的今古,人生的过往,都如同梦幻一场,既然是梦,一切即已终结,苦苦追忆何异刻舟求剑,这样就无谓再执着过往,而且在面对当下困境的时候,能清晰地认识到此时亦终将成为过去,所以更能超出现在而看到更远的将来。苏轼诗词中极少出现追忆的字眼,出现更多的却是“归去”,《哨遍》更是直接隐括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大量的“归去”字眼,与“扁舟”相得益彰:
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水龙吟》)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满庭芳》)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水调歌头》)
作个归期天已许。(《青玉案》)
独棹小舟归去,任烟波飘兀。(《好事近》)
此间“归去”,包含了对家乡故园的思念,但最重要是代表主体精神灵魂的安放与托寄,返归本体,最终落点在形而上,时间指向在未来,这些都是有可能脱离眼前现实障碍而得以发展和实现的,也是充满了理想和希望的,所以,它能够成为一个精神领域的追求与梦想,蕴含着无尽的向上的力量,这一点与“追忆”的心理机制正好相反。所以,在长期的贬谪生涯中,苏轼非但没有绝望,而且还更加坚信了对主体自由的追求,他解决困境的方案不但是可行的,而且坚守如一。
秦观是沉溺于过往的典型,词中反复不断的追忆缠绵悱恻、肝肠寸断,仿佛是生活在记忆之中,而这种记忆还是经过一番艺术美化的更加理想化的心理境界,把心灵存放在一片虚幻的美好之中,而饮鸩止渴却进一步加重了眼前的痛苦感受。
苏轼则尽量不去回忆,不去抵触,而是尽力地接受,并在接受中慢慢调适心理。现实是无法改变的,往事再也追寻不来,徒劳无力,面对痛苦,接受是最为理性的处理方式,越是逃避,所带来的痛苦会更加多。即使在心情最为沉重低落的时候,苏轼也是喜欢就地取景、借物拟人,把自己的一腔真情与内心幽怨全部投注到身边的事物中,借以传达天涯知己、同病相怜之感,缠绵悲切,而又柔情万种。如初贬黄州时的海棠诗,孤鸿词,杨花词,初贬惠州时的梅花诗等,所传达的孤凄感伤比秦观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情感取向一直都是在当下目前或者更遥远些的将来。晚年在惠州儋州,生活境况虽然恶劣,短暂的低沉之后,很快就被奇异的风景所吸引,心理上完全接受了岭南之行,并让自己从中获得极大的乐趣,处之安然并能怡然自得。
陈广夫云:“秦七词风流隽朗,其乐则伤飘荡(天年亦盖不永)。其人义气才华之士,实用根底,自非坡谷之比。故虽等为不遇,而千载下凛凛之思,相去悬绝,此亦可于声音中得之。”(杨希闵《词轨》卷五引)[16]秦观与苏轼虽然在贬谪中的心态有所不同,秦观为情所役,最终在沉重的情累中沦陷,苏轼有情而不役于情,最终在体验中走向超越。但“桃源”主题的缘起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剥削压迫的厌恶,“扁舟”意象的根源亦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17],都是基于对让人窒息的社会的逃避,不论“桃源”还是“扁舟”,其实都是极端困境之中内心的一种映现,都代表了对现实的无奈与想要逃离,长期的贬谪给两人的身心都带来了重大损害,唯有值得庆幸的是,相同的遭遇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并且都收获了大量佳作。
[参考文献]
[1]程千帆.古诗考索·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29-31.
[2]秦观,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92.
[3]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4]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十卷六八[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5]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四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113.
[6]王明清.《挥尘录》之《挥尘余话》:卷一[M].四部丛刊景宋钞本.
[7]秦观.秦观集编年校注[M].周义敢,程自信,周雷,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740.
[8]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词话丛编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5:1653.
[9]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07.
[10]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1.
[11]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59:3257.
[12]苏轼.朱孝藏编年.龙榆生校笺《东坡乐府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90.
[1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246.
[14]苏轼.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2196.
[15]缪钺.诗词散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4.
[16]孙克强.唐宋人词话(增订本)[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
[17]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