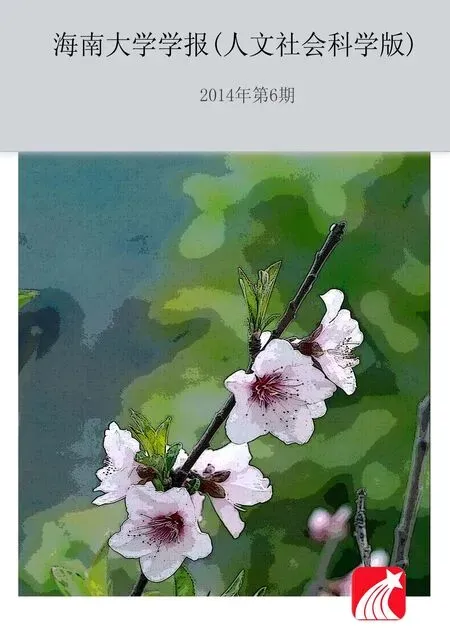古代文论范畴“脉”之衍生模式探析
熊 湘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作为古代文论范畴,“脉”具有独特的逻辑地位和理论意义。它一方面指涉文学作品表层的语言、字句的连贯,另一方面又与作品深层的气韵密不可分。在以往的文论范畴研究中,“脉”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为数不多的论著主要集中在对诗歌“意脉”的探讨上*如赵昌平《意兴、意象、意脉——兼论唐诗研究中现代语言学批评的得失》(《唐代文学研究》第三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分析唐诗表面的兴象与内在意脉间的关系。葛兆光《汉字的魔方》(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之第三章“意脉与语序”论述中国古典诗歌中意脉与语序的关系。屈光《中国古典诗歌意脉论》(《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梳理了诗歌的意脉结构。。古代文学“脉”论是依靠其派生范畴*搜集古代文论中的“脉”论语句会使我们发现一个特别明显的现象,除去诸如刘勰云“内义脉注”,严羽云“脉忌露”等少数“脉”以单字出现的情况外,绝大多数都是以词组的方式呈现。本文将这些词组统名为“派生范畴”,它不规定二者之间定有时间先后抑或地位高低之别,仅仅指出从字词结构上说,这些词组解释由“脉”派生出来。的广泛运用而得以发展和丰富的,它们共同构成古代文学脉络理论(包括诗歌理论、文章学理论等)的核心,而“意脉”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若要全面分析“脉”论,则须将诸多派生范畴纳入考察范围。本文所言之“衍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脉”论术语(即派生范畴)的引入及丰富,二是“脉”之所指向文本字句、章节、气韵等的多层面发展。在古代文论语境下,这两方面密切联系,共同形成“脉”论不断丰富、发展的较为清晰的路径和模式。由此,笔者可厘清“脉”及其派生范畴的内涵,借以探析文论范畴生成、发展的促动因素和文论体系的重要特征。
一、术语的文化内涵与文学本质规律的契合
“脉”是一个被广泛运用于中医学、堪舆学、文论、书论等领域的范畴,在将其引入文学批评之前,由于受到古人象天法地思想,以及中医学和堪舆学的渗透和影响,“脉”之字形、字义经历了一定的变化,其内涵也逐步丰富和完善。简言之,古人在对人体构造及自然风水的认识中,对“脉”这一字形成了经验性的、直观的认识。这种认识很难用定义式的语言解释清楚,但其最基本的内涵特征则是在形上有主干、有支流,在意上前后连贯、弥纶一体。而具有此类特征的,或取其形,或借其意,皆可冠以“脉”之名。如“叶脉”则取其形似,古代文学“脉”论则取其意。
然而,这只是“脉”论引入的一个大前提,它没有停留在如“叶脉”般简单的概念层面上,“脉”之所以能够成为文论范畴,就在于其文化内涵能够与古人的文学观念、文学的本质规律相契合。基于古人的同构思维,文学作品与人体一样具有完整的、统一的生命特性。古人论文,讲求外在结构的完整,故有律诗首、颔、颈、尾四联之说,文章则有头、项、心、腹、腰、尾之论*具体参见魏天应《诸先辈论行文法》,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册,第1087-1088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讲求内在的生命力,故有以血、脉、骨、气、心等术语来论文。“脉”对于人体至关重要,对于作品,其意义应当不言而喻。如宋吴沆《环溪诗话》云:“诗有肌肤、有血脉、有骨格、有精神。无肌肤则不全,无血脉则不通,无骨格则不健,无精神则不美。四者备,然后成诗。”[1]人体之血脉在于流通,作品之“血脉”在于连贯,这种直接的比附反映出古人眼中文学作品与生命体具有的共通之处。文学作品是由文字组合而成,字、句、章节之间显现出某种连接的状态,而这种连接是要被读者所接受的,换言之,字句章节的连接受到文学本质规律的限制,文意的连贯与否也成了文学作品形成的必然要素。古人论文,言及句意连贯、句断意连,以至章法结构,等等,均是从这个层面来说的。皎然言作诗“时时抛针掷线,似断而复续”[2],以线为喻,形象说明了诗歌创作的要求。然而,“线”并未成为描述作品连贯状态的范畴,相比而言,“脉”因与人体生命密切相关,其连贯性更容易被人重视,中医学、堪舆学的发展已经使其形成一套丰富的脉络理论和概念,如血脉、气脉、过脉、伏脉等,足够文论家所借鉴。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刘勰首先将“脉”引入文学批评。《文心雕龙》“章句”篇云:“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3]570-571“附会”篇云:“若统绪失宗,辞味必乱,义脉不流,则偏枯文体。”[3]651六朝是古代文论的发轫期,文学批评一旦讨论到具体的文学创作,那文意、文辞的顺畅必然是首先考虑到的基础性问题,而“脉”的本质内涵又实实在在契合人们对文学作品意义连贯状态的描述。因此,“脉”之内涵与文学作品的本质规律具有较高的契合度,这是“脉”之所以能够成为文论范畴的重要因素。
此二者之间的契合促进了古代文学批评“脉”论的发展,并且生发出两类派生范畴。一是直接从中医学、堪舆学引入的范畴,如气脉、血脉、过脉、急脉、缓脉、伏脉等。另一类是由相关文学术语与“脉”结合而成,如文脉、语脉、句脉、意脉等。严格说来,两类范畴在重要性和与文论的结合度上并无质的差别,他们反映出“脉”之内涵与文论相契合而形成的多层次特点。浅层次的比附和深层次的运用在古代文学批评中不乏其例。如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文》云:“青乌家专重脱卸,所谓急脉缓受,缓脉急受,文章亦然。势缓处须急做,不令扯长冷淡。势急处须缓做,务令纡徐曲折,勿得埋头,勿得直脚。”[4]2429尽管此言为直接比附,但其前提依然是急脉、缓脉之论符合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相比而言,气脉、意脉已经与作品内本身的意义、气韵密切联系,并能够形成相对独立的文学脉络理论。
二、基于文本的多层面衍生
“脉”之派生范畴不但反映出其词义、概念的丰富和发展,从描述的对象——文本来说,不同的派生范畴指向文本的不同层面,从内在的气韵到外在的文辞,都成为“脉”之所指。简言之,“脉”具有描述文本内在结构和外在结构的能力,因而其衍生模式并非单一、平面化的,它具有典型的多层次性。兹以“脉”之派生范畴为焦点,分析其内涵对于文本的多层面衍生。
(一)内在气韵的融通——血脉、气脉
古人论文重视其内在的精神、气韵,此属文学作品的深层结构,它通过章节字句等表层结构体现出来,但又不流于文辞之表面。便如人体之血脉、气脉,由内生发出来,是贯注生气之大要。
“血脉”本是中医学术语,指人体中血液流经的通道,大致可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血管。人体血脉往复循环、遍布全身,是维持生命的关键。唐王叡《多毂子诗格》将事义连贯视为诗之“血脉”,五代徐寅以“始末理道,交驰不失次序”来叙血脉,把血脉贯通之于生命的意义搬到文论上来。宋及其以后,诗论中言血脉者渐多,吴沆、姜夔将诗歌作品与人体相比拟,强调诗有“血脉”,体现了古代诗论的生命化特性。同时,更多的是以贯通、连属描述血脉,此种描述是基于对作品的整体把握,它建立却又超脱于结构、纲目之上,被视为文学作品内在、无形的存在状态。宋楼昉《崇古文诀》评诸葛亮《后出师表》:“一篇首尾多是说事不可已之意,所以不可已者,以‘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也。血脉联属,条贯统纪,森然不乱。”[4]1468赞此文“血脉”连属,既要求文章情理叙述的“条贯统纪”,结构的“森然不乱”,更揭示出一意贯穿全文的内在要求。文学作品诸要素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有机统一、生气关注的整体,便如人之血脉贯注全身,使其容光焕发。统一体的完美呈现是内部诸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若有些许缺陷,则有伤血脉,如明谢榛责韩愈诗句“露排四岸草,风约半池萍”道:“下句清新有格,上句声调龃龉,使无完篇,则血脉不周,病在一譬故尔。”[5]前后连贯之意在范畴“血脉”中甚至占据核心位置,但既将“血”、“脉”二字相连,那它必然具有体现文学作品融贯统一的生命特性,展示其整体生气的倾向。是以倪士毅《作义要诀》论作文之法则曰:“有开必有合,有唤必有应;首尾当照应,抑掦当相发;血脉宜串,精神宜壮。如人一身,自首至足,缺一不可。”[4]1499方东树评汉魏人之作品亦曰“血脉贯注生气”[6]27。故在文论中,“血脉”成为文学生命化特征之揭櫫。
在中医学理论中,“气脉”表示人体血气的流通路径;在堪舆学中,它则表示大地之气的运行。以“气脉”之贯通来品评诗文实为常见,如宋包恢《书抚州吕通判诗稿后》云:“盖八句之律,一则所病有各一物一事,断续破碎而前后气脉不相照应贯通,谓之不成章……今耐轩续稿似独不然,观其八句中语意圆活悠长,有蕴藉,有警策,气脉贯通而无破碎断续之病。”[7]其所言气脉超脱于物事等表层结构,同时也指出表层结构的破坏有损于作品内在气韵的圆转。文章之气由首至尾,如山脉绵延,应避隔断、短促,故气脉绵长为作文之一要。《朱子语类》云:“陆教授谓伯恭有个文字腔子,才作文字时,便将来入个腔子做,文字气脉不长。”[8]3321朱熹所言依旧是超脱于表面结构之上的。作为元范畴,“气”具有形而上的特征,且有足够的能力使其派生范畴染上自己的色彩,故“气脉”亦具有偏向于形而上层面的倾向,方东树直接将“气脉”与创作技法相对,他在《昭昧詹言》中云:“然徒讲义法,而不解精神气脉,则于古人之妙,终未有领会悟入处,是识上事。”[6]9然而,“气脉”绝不可能完全统属于“气”之下,在注重其关乎文学本体、形而上的层面时,它的形而下的技法层面也理应得到重视,对此方东树在后文中作了更为细致的分析:
有章法无气,则成死形木偶。有气无章法,则成粗俗莽夫。大约诗文以气脉为上。气所以行也,脉绾章法而隐焉者也。章法形骸也,脉所以细束形骸者也。章法在外可见,脉不可见。气脉之精妙,是为神至矣。俗人先无句,进次无章法,进次无气。数百年不得一作者,其在兹乎![6]30
钱仲联先生《释“气”》一文指出:“气脉是作品潜在的精神和用以驾驭章法脉络的艺术的统一体。”[9]人各有气,不同的人的作品自有不同的气韵脉法,气带有主体创作的精神特质,脉勾连章法技巧。如此以“气脉”来描述作者、作品的的创作特点是极其恰当的。尽管“气脉”可以指涉章法,但其描述作品深层结构的倾向甚为明显,章法安排的目的就在于使得气脉流转,方东树所言“章法在外可见,脉不可见”,即是承认了脉与作品内在结构的关联。
(二)意义、道理的连贯——意脉、义脉*“义脉”一词或许是出现得最早的“脉”论范畴。其若指文章的内容含义,自可归入到“意脉”之中;若指文章包含的义理,则又不出“脉理”之范围。故而自刘勰提出“义脉不流”之后,后来的论家没有推而广之、大加运用。故下文不再赘言。
任何文学作品都具备内在的文意,创作和阅读的过程可以看成分别是作者将一己之意付与文字,读者再从中获取文意。古人云“言不尽意”、“词不达意”、作诗讲究“言外之意”皆是从语言与文意之关系来阐述的。不论是立言尽意还是追求言外之意,“意”终究是创作主体所要表达的东西,也是贯注于文学作品的必然要素。元方回《瀛奎律髓》云:“以意为脉,以格为骨,以字为眼。”[10]点明了“意”要如人体脉络一样贯穿整体。故而对文学作品本身来说,意脉是其内在意义的连贯状态,对文学创作或者阅读欣赏的过程来说,意脉则表现为作者自己以及作品对读者所引起的思想的流动、情感的展开*诗歌意脉成为一些学者关注的对象,赵昌平先生认为:“(诗歌)意脉是意兴的流动轨迹,浅言之即诗的感情线。”(赵昌平:《意兴、意象、意脉》,《唐代文学研究》第3辑,第2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葛兆光先生给“意脉”的定义为:“诗歌意义的展开过程,或者换句话说是诗歌在人们感觉中所呈现的内容的动态连续过程。”(葛兆光:《汉字的魔方》,第5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在论诗重意的宋代,“意脉”得到格外的重视。宋周紫芝《竹坡诗话》记载:
《病起》一诗云:“病来久不上层台,窗有蜘蛛迳有苔。多少山茶梅子树,未开齐待主人来。”此篇最为奇绝。今乃改云:“为报园花莫惆怅,故教太守及春来。”非特意脉不伦,然亦是何等语。[11]
此诗未改之时明白如话,诗意也极为顺畅清晰,改后诗意婉转隐晦,上下稍有隔膜。同时代的吴可《藏海诗话》评吴申李诗句“潮头高卷岸,雨脚半吞山”道:“然头不能卷,脚不能吞,当改‘卷’作‘出’字,‘吞’作‘倚’字,便觉意脉连属。”[12]且不论以上二者各自的论断是否合理,前者重在全诗的意义分明、连贯,后者则着眼于句意的合理、通顺。他们都反映出诗歌意义连贯的重要性,这是具有一定道理的。从中也可以看出“意”的囊括性极强,所指可大可小,字义的推敲、句子的组合、段落的连贯皆可归到“文意”上来。而其目的在于使全篇之意通贯一体,无有隔断。
“脉理”这一范畴也不为古代文论所独有,在其之前已经被广泛运用于中医学、堪舆学等领域,且“脉”与“理”有一定的共通性*《说文解字》云:“理,治玉也。”《战国策》云:“郑人谓玉未理者为璞。”可知“理”原义即为对玉进行剖析。玉石的条纹处最易破裂,治玉者必须顺玉之纹(文)而剖析之,故“理”以表示玉石之条纹。其引申义指称对象内容,抑或形式上的规律性、规定性。而对于“脉”,《说文解字》云“血理分衺行体者”。简言之,“脉”即血理,王筠《说文解字句读》云:“??,如木石之有理,故曰血理。”《国语》云:“土乃脉发。”三国韦昭注曰:“脉,理也。”二者都指出了脉与理的共通性。。在古代文论中,“理”是指文章语言形式、内容意义上分合、连属的状态,这与文之脉所指相同。然这只是文学作品所体现的理的一个方面,文章所包涵的情理、义理虽与文脉密不可分,然到底还是居于文脉之外。文学作品广义上的“理”包括了“文理”、“情理”、“义理”等,而“脉”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其次,“理”经由历代文人学者的阐述、发挥,早已成为富有深刻意义的哲学范畴,其形而上的内涵远甚于“脉”,而“脉”始终停留在形而下的层面。因此,一方面,可将“脉理”这一范畴看成“脉”、“理”二字的同义复用,但另一方面也要明白在这个范畴表达的意义中,“脉”重在贯通而“理”重在遵循。
宋张耒《答李推官书》云:“自唐以来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为缺句断章,使脉理不属。又取古书训诂希于见闻者,挦扯而牵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复咀嚼,卒亦无有,此最文之陋也。”[13]缺句断章,语意突发而来,嘎然而止,无首无尾,定然谈不上脉络通贯,上下文理连属。即是“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也是有碍于脉理连属的。朱熹为《中庸集解》作序,以为:“唯哀公问政以下六章,据《家语》,本一时问答之言,今从诸家,不能复合。然不害于其脉理之贯通也。”[14]3957脉络通贯与文理连属本身就是一体的,以贯通等语描述“脉理”自然常见,不必多述。
汤显祖《孙鹏初遂初堂集序》云:“(文章)位局有所,不可以反置;脉理有隧,不可以臆属。”[15]刘熙载《艺概》云:“词中承接转换,大抵不外迂徐斗健,交相为用,所贵融汇章法,按脉理节拍而出之。”[16]词自有其章法和声律要求,若声律为节拍,那章法就为词之“理”,填词必须按其固有的文体特性和章法布置。“脉理有隧”,“按脉理节拍而出之”都是未发之前对其规律特性的遵循,故其重亦在“理”这一方面。杜甫《薄暮》诗云:“江水长流地,山云薄暮时。寒花隐乱草,宿鸟探深枝。故国见何日,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鬓发自成丝。”清仇兆鳌评曰:“上四暮景,下四暮情。此诗纵横看来,意无不合。晚花隐色喻已之混迹,夕鸟归林方已之避乱。此虽写景,而兼属寓言。故国生悲仍与流水相应,白头兴叹又与暮云相关。脉理之精细如此。”[17]此诗脉络井然,且章法细致、情理精微,可知诗文之要不仅在于连贯,其精细之处亦当如脉络之行,无所不至。将“精细”视为文之“脉”的一种全新的描述固无不可,但文理之绵密、情理之精微才是仇氏对杜甫这首诗最主要的评价,而脉络连贯显然被囊括在这样的评价之内,因为它是文理与情理达到完美统一和展现的内在前提。
(三)语义、句法的勾连——语脉、句脉
积字成句、积句成篇,故字句是作品的基本单位。古人论脉,不少即是从字句的勾连上来说的。从词语的组合上来看,“语脉”显然是评论诗文时特有的范畴。宋王得臣《麈史》云:“杜审言,子美祖也。则天时以诗擅名,与宋之问唱和,有‘绾雾青条弱,牵风紫蔓长’,又‘寄语洛城风与月,年年春色倍还人’。子美‘林花着雨胭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又云‘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虽不袭取其意,而语脉盖有家风矣。”[18]虽言杜甫之诗未窃审言之意,而所举的四联诗在句法和用语上实有相似之处,此即王氏所言之“语脉”。
朱熹好以“语脉”论四书等经典,《中庸或问》析“小人之中庸”一句:“王肃、程子悉加‘反’字,盖叠上文之语……若论一章之语脉,则上文方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且当平解两句之义以尽其意,不应偏解上句而不解下句又遽别生他说也。”[19]此即从上下文之语意出发,分析典籍中脱文衍字的情况,再如下面两则:
洛书九数而五居中,洪范九畴而皇极居五,故自孔氏传训皇极为大中而诸儒皆祖其说。余独尝以经之文义语脉求之,而有以知其不然也。盖皇者,君之称也;极者,至极之义,标准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极为在中之准的则可,而便训极为中则不可。(朱熹《皇极辨》)[14]3743
韩退之作《蓝田县丞厅壁记》……莆田方崧卿得蜀本,数处与今文小异,其“破崖岸而为文”一句,继以“丞厅故有记”,蜀本无“而”字,考其语脉,乃“破崖岸为文丞”是句绝。文丞者,犹言文具备员而已,语尤奇崛,若以丞字属下句,则既是丞厅记矣,而又云“丞厅故有记”,虽初学为文者不肯尔也。[20]
受印刷水平的限制等各种原因,古代典籍中多有纰漏、阙文、衍文、错置等现象,影响到人们的阅读和文献整理,故以上下文意进行本校、理校是版本校勘、修正纰漏很好的方法。故“语脉”在此类论述中时有出现,其作用正如《四库全书总目》“《诗牗》十五卷”所言:“推敲字义,寻求语脉。”[21]既然寻文章之“语脉”是文章考辨的重要手段,那文章语脉在写作和阅读过程中自是必然要考虑到的了。一方面,对于作品本身,要求其语意通顺,语脉连贯,自不必说。另一方面,人是文学创作和鉴赏的主体,对文章语意、句意、文意的把握本是阅读和鉴赏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步骤,这也是了解前人著述、思想之必备。故朱熹云:“读诗,且只将做今人做底诗看,或每日令人诵读,却从旁听之。其诂有未通者,略检注解看,却时时诵其本文,便见其语脉所在。”[8]2083
由上可知,以“贯通”、“连属”、“分明”描述语脉仍旧是最为常见的。除了具有“脉”范畴一般性的意义外,“语脉”往往从字义、句意等细处着眼,指称文学作品语意的连贯及其态势,它因此而具有较大的实用性。“语脉”在古人评析、注疏经典时运用颇多,而在文学评论,特别是纯理论的文学论著中极少出现,这正因它本身的特性所致。
“句脉”所指着重在句子结构以及上下句意方面。秦观云:“赋家句脉,自与杂文不同。杂文语句,或长或短,一在于人。至于赋,则一言一字,必要声律。凡所言语,须当用意曲折斵磨,须令协于调格,然后用之。不协律,义理虽是,无益也。”[22]此处的“句脉”便是指文章的句式以及内部的语言声律结构,并且秦观在此指出它与文章之义理无涉。再如张耒云:“古人作七言诗,其句脉多上四字而下以三字成之,如‘老人清晨梳白头’、‘先帝天马玉花骢’之类。而退之乃变句脉以上三下四,如‘落以斧引以纆徽’、‘虽欲悔舌不可扪’之类是也。”[23]此皆是以句子内部、句子之间的连贯方式来表达“句脉”之涵义。虽然其脱离不了句意、文意,但更侧重形式上的连贯状态。
三、范畴概念的模糊性与开放性
除了上述派生范畴外,“文脉”与“脉络”算是最为普泛的“脉”论范畴,古代文学之“脉”论所讨论的对象就是文,即文章之“脉”。在中医学中“脉”“络”有别,但将其移到文论上,其所指则完全相同,“脉”即“脉络”。严格说来,他们算不得“脉”之派生范畴,实即“脉”范畴本身。文论中所言“经脉”与“脉”实为一意,“命脉”近于“血脉”,是指创作的关键步骤和作品之关锁。“筋脉”近于“筋节”,注重脉络贯通,但偏向于文章曲折而具有的顿挫和灵动感,“骨脉”则注重作品的力度。
以上每一种组合方式都使得派生的范畴带上相关概念、范畴的特性,或者说在“血”、“气”等概念的加入使得相关派生范畴在“脉”的基础上产生了特定的偏移。如“血脉”重在指称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要素和文学评论生命化特征的揭示;“气脉”重在对象的气韵流转以及富有主体精神的气质;“语脉”指语义的推敲和上下语意的连贯;“脉理”偏向于文理与情理、义理的结合;“意脉”指通篇文意的连贯状态;“句脉”侧重句子内部的组合形式。然而,因其都本于“脉”,故在涵义上有重叠的现象,加之古人论文多凭经验性、直觉的判断,此种重叠变得极为突出。人们说“血脉”反映了古人论文的生命化特征,而“气脉”何尝不是如此呢?比之于“血脉”,它还更接近于人的主体气质和文章精神层面。将“脉”引入文论的过程本身就带着文论生命化的征象。对于“语脉”和“意脉”,汪涌豪先生说:“未发之前,上下连贯之旨为‘意脉’;已发之后,前后统属之词为‘语脉’。由于语词是用来传达意旨的,故这两者在宋人实际论述过程中并未被分为两橛。”[24]未发之前与已发之后本来就难以区分,语词与语意本来就相辅相成,故而言意脉处若改为“语脉”,于上下文意亦通,言“语脉”处若改为“意脉”也无碍于理解。再如,前面说到“语脉”为推敲字义、推寻句意、文意,以订正典籍之缺文、衍文、错置。而王澍《淳化秘阁法帖考正》云:“孤不度德以下二帖皆诸葛传中与昭烈问答语,有一段自孙权据有江东以下,与此文脉相接,误置第十卷。”[25]此便将“文脉”代替了“语脉”。
“脉”与其相关派生范畴的混用情况在古代文论中相当普遍,非但如此,古人在某些地方是否用“脉”也存在模棱两可的情况。宋吴曾《能改斋漫录·东坡用事切》云:“东坡《和山谷嘲小徳诗》末云:‘但使伯仁长,还兴络秀家。’盖伯仁乃络秀子耳,洪驹父《哭谢无逸》诗云:‘但使添丁长,终兴谢客家。’此学东坡语尤无谓,添丁卢仝子,气脉不相属。”[26]“东坡用事切”一条,宋胡仔《渔隐丛话》后集卷32所引之《复斋漫录》,宋吴幵《优古堂诗话》均有著录,二者皆云“气骨不相属”。或为吴曾录而改之,也或为后人抄录舛误,然于我们了解其意并不相碍。宋戴复《古东谷王子文死读其诗文有感》云:“议论波澜阔,文章气脉长。”[27]“气脉”一作“气味”,后者用于此也无不可。清吕留良《吕晚邨先生论文汇钞》云:“有用古文极熟套头语,而能化腐臭为神奇者,所争在气脉,不在皮毛也。”,又云:“先辈论文必高华。高华如庾、鲍、老杜,称其清新、俊逸,故知所争在气骨,不在词句也。”[4]3347-3349前后句意相近,两相比较,“气脉”一词运用的严格性便不言自明了。
总之,在分析古代文学“脉”论的时候,既要明白各个范畴之间的内在涵义和用法上的侧重,也要清楚在实际论文中又界限模糊。这种范畴边界的模糊性与古人范畴运用的经验性、发散性直接相关,它既有助于“脉”在古代文论中的衍生,同时又是分析脉的文论意义和理论体系所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四、总结
古代文学批评“脉”论的衍生、发展是多重因素共同促进的结果。“脉”之内涵的丰富,其在中医学、堪舆学中形成了一套脉络观念,且与文学本质规律相契合,此乃其前提;古人在对文学创作、鉴赏进行经验总结的过程中,逐渐把握文学的本质规律,也必然会关注到作品的连贯状态,此乃其内因;古人的比类取象的思维模式则是其外因。“脉”所衍生出的两类派生范畴,一方面丰富了古代文学批评的话语,另一方面则将“脉”论与古代文学理论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内在的气韵精神到外在的字词章句,无不体现着“脉”之内涵与观念,因而成为我们分析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线索。将“脉”之多层次、多向度衍生模式放到古人经验性、随意性话语方式特征的背景下考察,既有利于充分阐释各个派生范畴的内涵,理解其边界的模糊性,又能揭示出范畴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通过对“脉”之衍生模式的探析,梳理出了此范畴生发的逻辑路径,尽管每个文论范畴的复杂性和运用程度不同,但这一生发路径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通用性,因而对深入分析诸如“气”、“韵”、“势”等更为复杂的范畴,建立整个范畴逻辑体系,应有所助益。
[参考文献]
[1]吴沆.环溪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8:130.
[2]李壮鹰.诗式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13.
[3]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王水照.历代文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5]谢榛.四溟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99.
[6]方东树.昭昧詹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7]包恢.敝帚稿略[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7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761.
[8]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9]钱仲联.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M].济南:齐鲁书社,1983:237.
[10]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512.
[11]何文焕.历代诗话: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4:235.
[12]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6:340.
[13]张耒.张耒集: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0:829.
[14]朱熹.朱熹集:第7册[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15]汤显祖.汤显祖诗文集: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060.
[16]袁津虎.艺概注稿: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9:530.
[17]仇兆鳌.杜诗详注: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1036.
[18]王得臣.麈史[M]∥丛书集成初编:20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32.
[19]朱熹.四书或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1.
[20]洪迈.容斋随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673.
[21]永瑢,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5:142.
[22]李廌.师友谈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2:20.
[23]张耒.全宋笔记:第2编,第7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10.
[24]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260.
[25]王澍.淳化秘阁法帖考正[M]∥四部丛刊三编:31册.上海:上海书店,1985:16.
[26]吴曾.笔记小说大观:第29编,第4册.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86:1989.
[27]戴复古.石屏诗集:卷3[M]∥四部丛刊续编:66册.上海:上海书店,198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