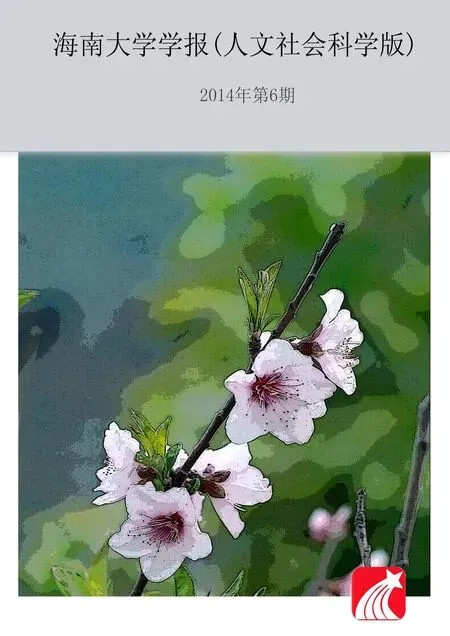先秦无为思想起源考论
李秀华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200433)
“无为”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作为一种思想,它是如何起源的?至今仍是一个没有得到认真回答的问题。研究者大多认为无为思想的根源在于老子,如刘笑敢先生说:“老子被认为是无为理论的创始者,因为老子第一个使用了无为的概念。”[1]并且将老子的无为论直接视为无为思想的源头。甚至另有研究者认为孔子是较早提出“无为”这一说法的人[2]。然而,老子于《道德经》中有一条关于“无为”的言论:“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①参见《老子·57章》。本文所引《老子》原文皆出自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帛书乙本写作:“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3]不管是“圣人云”,还是“圣人之言曰”,都表明老子这条言论是引述前人的说法。由此说明无为思想并非老子首创,而是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积淀。这也符合人类思想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完全凭空而出的思想观念几乎不可得见。本文就先秦无为思想的起源这个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无为”一词的语义解释
要考察先秦无为思想的起源,就必须先讨论“无为”这个词。通过界定“无为”一词的语言学含义,来大体揭示无为思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为判断老子之前有无“无为”思想或类似思想的存在提供一个可以衡量的标准。
按照现代汉语理论,“无为”是个合成词,可以析分出“无”和“为”两个语素,但同时“无”和“为”又可独立成为单纯词。这种复杂的语法现象,也存在于古汉语的使用中,使得“无为”一词在语言学上包含着多个义项②《汉语大词典》(第7卷)归纳出了12个义项。。在《老子》已知版本中,“无为”有多种写法:通行本写作“無为”,郭店竹简甲本和乙本都写作“亡为”,丙本有1处又写作“無为”,帛书甲、乙本全部写作“无为”,刚刚面世不久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本“無为”、“无为”同存。这一文本现象说明,“无为”一词中“无”的书写形式灵活多样,“为”则保持不变。这固然是出于书写习惯的不同,但从中可以反映出“无”在“无为”一词中的核心位置,显示古人对“无”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说文·亾部》:“無,亡也。从亡,無声。无,奇字無也。通于元者,虚无道也。王育说:天屈西北为无。”可见许慎之时“亡”、“無”、“无”三字就纠结难辨。“亡”字早出,“無”、“无”二字晚出。吴楚《说文染指》引俞樾说:“無非古字,古無字止作亡。亡,逃也,人人乚逃则無矣。故古無字多作亡。”[4]又马叙伦说:“《周易》唯王弼本用此无字,《荀子》《淮南》《风俗通》《群书治要》引《易》皆作無。他经记無作无字者,则无字晚出矣。”[5]这一现象也可以从《老子》及其他出土文献中得到证明。庞朴先生在《说“无”》一文中亦把亡、無、无这样的排列看成是三字先后出现的次序,并对这三字作了精到的解释。他认为,在殷人时代,“亡”之为“无”,是与“有”相比较、相对待而被认识的,即有而后无;舞是用以同“無”打交道的手段,这个“無”不等于没有,只是无形无象,永远看不见、摸不着而已,即似无实有;不必待有之“无”,是无之而无,为宇宙间所本无,它灭绝了与有的对待,因之是绝对的无,即无而纯无[6]。庞朴先生的解释,尽管与古代有的训诂家意见相左③如饶炯《说文解字部首订》:“亡以逃为本义,死亡与有亡为引借。盖人之逃而去者,灭踪入??,不有其人,与無一例,死入幽瘞,长与人辞,亦如逃者之不见于世,故死亡有亡皆借逃亡字为之。”(《说文解字诂林》第12404页)徐灏《说文解字注笺》:“有者自無而有,無亦自有而無,故从亡無声,而古通作亡,因之本無其物谓之無。”(《说文解字诂林》第12412页)徐锴《说文系传》:“无者,虚無也,对有之称,自有而無。无谓万物之始,未始有有始也。道者象帝之先,道者始初之为也,实無也。”(《说文解字诂林》第12411页)这些解释大都以字形而明,未能与历史相系,显得凝滞难通。,但实际上反映了人类思维从具体到抽象的进化规律,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相对于“无”,“为”的基本字义变化不大。学者大都不同意许慎“象两母猴相对形”的解释。罗振玉根据古金文和石鼓文的写法,认为“为”字是古者役象以助其劳事之义[7]。日本学者高田忠周说:“愚谓为字元从爪从象……《广雅》‘象,效也’,效者仿也,仿而象之,即作为也。以何行之?手以为之也,作为即作伪。”[8]可见,“为”是会意字,总脱不了“作为”、“从事”之义。
结合以上学者的说法,“无为”一词的语义可包含:其一,与“有为”相对待之义,换言之,一种总是否定现有作为的行为;其二,一种永远看不见、摸不着却总能支配其他作为的行为,常指天道之为、自然之为;其三,一种绝对不作为、不从事的行为,也就是零作为。西汉初期学者所理解的“无为”即有这种零作为的倾向,如《淮南子·修务训》:“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上述含义都是将“无为”视作名词来说的,若作动词看,则“无为”近于“毋为”,表示禁止施行某一具体的事情或行为。
在现存可靠文献中,“无为”一词最早见于《诗经》。《王风·兔爰》云:“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有兔爰爰,雉离于罦。我生之初,尚无造。我生之后,逢此百忧,尚寐无觉。有兔爰爰,雉离于罿。我生之初,尚无庸。我生之后,逢此百凶,尚寐无聪。”有趣的是,无为、无造、无用这三个词以后都成了道家哲学的重要概念。但在此诗中,“无为”非哲学概念,与“无造”、“无用”之义差别也不大。毛氏认为这首诗写于周桓王(?—前697年)之时,传曰:“尚无成人为也。”郑玄笺:“言我幼稚之时,庶几于无所为,谓军役之事也。”[9]309意指因年幼力薄而无法担当某种事情,相当于不作为、不从事。又《大雅·板》:“天之方懠,无为夸毗。威仪卒迷,善人载尸。”毛氏认为是刺讥周厉王(?—前828年)之诗,孔颖达正义曰:“言比天之王者,方欲威怒行酷虐之害,汝等无得为此夸毗,足恭前却,以体从之。君既为恶,臣又从之,则上下威仪尽迷乱矣。其善人君子则如尸然,不复言语矣。”[9]1350这个“无为”用作动词,是告诫大臣不要做阿谀奉承之人,属于禁忌用语。李生龙先生指出“无为”的字面含义包括“是没有做什么的意思,表示一种存在状态”和“是不要做什么的意思,是一种行为禁忌”两类[10],颇为恰当。
“无为”一词的语义与无为思想还存在很大距离,但可以借其语义来大致了解作为思想范畴的“无为”的含义。第一,无为是相对于有为而生,与有为是辩证关系。有为,从字面意思看,它概括了人类的一切行为,是人类欲望付诸实践的行为,但未必都符合人类预先的价值诉求。故有为也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这种后果给人们留下创伤,有思想的人就开始反思,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从而催生出它的对立面——无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无为是对有为的制约,是有为的消融剂。落实到现实社会,即是否定统治者的过度有为和某些世俗的价值与方法。自有为而无为,自无为而有为,人们试图在动态中找到两者的平衡。第二,自然界的行为总是支配人类社会的行为,而非人类支配自然界,即使摒弃人类社会,自然界还是一如往旧、有条不紊地运行,而这一切却看不到施为的主体,就像屈原在《天问》中追问的那样:“明明闇闇,惟时何为?”古人将这种无形而无不在的作为叫做无为,统称为天道之为、自然之为,以示畏惧、恭敬,并且拿来与人类自身行为相比较,从而产生顺从天道、因任自然的想法。第三,随着古人抽象思维的提升,他们对绝对虚空有了认识,无为随之被理解成游弋于虚无境界的绝对不作为,滑向一种神秘主义的精神体验。这一无为观念应是出现在老子之后,非本文讨论的范围。前面两种从“无为”语义而大致推演的无为思想,正可为讨论先秦无为思想的起源作出一定的导向。
二、无为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基础
无为思想非逻辑推断,也非直觉和迷信,而是建立在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考察的基础之上,近属于经验论。它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中国古代文化立基于农耕文化,农耕这一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地拉近了人与自然界的联系。自然界在农耕生活中显示出主导力量,人们对它最容易产生敬畏、依附、顺从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和效法自然界,有意保持与自然界的谐调一致。这一文化状态,笔者称之为原始自然文明。同时,人类自身又是一个独立于自然界的群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要建立政权,运用权力,实施以政治国,以政治人,此便是人类的政治文明。当人类政治文明陷入混乱、黑暗、腐朽而对人类本身产生巨大伤害的时候,就会有人将它与原始自然文明相比较,就极容易生发反政治文明的思想。因此,无为思想植根于原始自然文明的土壤,又常常滋生于或盛行于王朝没落或王朝交替之际,就不足为奇了。
传为帝尧时代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④沈德潜《古诗源》(卷一)以《击壤歌》为首,并解释说:“帝尧以前,近于荒渺。虽有《皇娥》、《白帝》二歌,系王嘉伪撰,其事近诬。故以《击壤歌》为始。”体现的即是顺着自然生活,无需政府干预的心态。《列子·仲尼》也载有一首尧时的童谣:“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其基调虽是颂扬尧帝的政治功劳,但实际上肯定的是尧帝能将自己的政治活动完美融入于原始自然文明中,让百姓顺畅而不觉有碍。这两首上古歌谣突出反映了古人顺应自然、无思无为的精神状态,其所塑造的政治消融于自然的社会模式亦为后来的道家所仰慕⑤《老子·80章》:“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庄子·马蹄》:“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可是并非每位统治者都能像帝尧一样出色,政治过分干预、甚至危害民众生活的情形时常产生。夏商及商周交替之际,政治乱象就给人们造成了深重灾难。夏桀暴虐,以致让他的子民发出“余及汝皆亡”[11]的绝望之音。周武王伐纣,宣告纣王的罪行:“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12],令人触目惊心。政治强调有为,但当有为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到处践踏庄稼的时候,其合理性自然就会受到怀疑。面对这种情况,有的人选择隐逸,如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吟出《采薇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吾安适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13]2123采取不合作态度,对统治者的政治妄为表示抗议;有的人选择拨乱反正,反思君道、治道,如周文王、吕尚,他们较早地思考了君道无为的问题⑥又有周文王时太史辛甲作《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左传·襄公四年》)万物各有所处,用政即在于顺其所处,避免干扰。。
但是,周代统治者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政治文明带来的负面问题,而且离原始自然文明也越来越远。权力至上,欲壑难填,使历代王朝的命运犹如走入一条死胡同,不断循环着。西周没落,人们在威权暴政下同样发出痛苦的呻吟。《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叹道:“黾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此诗被认为是刺讥周幽王⑦《毛诗正义》卷十二之二郑玄说:“当为刺厉王。作《诂训传》时移其篇第,因改之耳。”,郑玄笺云:“孽,妖孽,谓相为灾害也。下民有此害,非从天堕也。噂噂沓沓,相对谈语,背则相憎逐。为此者,由主人也。”[9]852最高统治者为一己之私的妄作妄为正是灾祸的根源。西周虽然亡了,但人祸还在延续,历史走进一个更加千疮百孔的时代——春秋。很多有识之士对此作过深刻反省,如周景王时期(前544—前520年)单穆公进谏说:“出令不信,刑政纷放,动不顺时,民无据依,不知所力,各有离心。上失其民,作则不济,求则不获,其何以能乐,三年之中,而有离民之器二焉,国其危哉!”[14]明显指出了不合乎自然的乱政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一些诸侯大国的君主和大臣,如齐桓公、管仲,重新意识到了政治应该顺天应人的重要性。当然,还有一些人继续选择隐逸以示抗议,如祝牧夫妻唱出《偕隐歌》:“天下有道,我黻子佩。天下无道,我负子戴。”[15]来显示他们的处世态度。这个时期,隐逸风气盛行。老子虽负绝世智慧,但也无可奈何,只能退隐。孔子所遇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都是世外高士,且《论语·微子》把这样一群人称作“逸民”。面对春秋时代的混乱、黑暗和腐朽之政治,正是这个群体对此坚定地加以否定,重启回归自然的意识,将无为思想推向了更深的层次。
三、老子之前无为思想的萌芽
关于老子和《老子》的年代,质疑声不断,近代甚至出现将其年代放置于庄子之后乃至秦汉之际的论调。但随着《老子》地下文献的面世,很多怀疑论调不攻自破。刘笑敢先生借助《诗经》、《楚辞》,用比较的方法得出司马迁有关老子的记述基本可靠的结论[16]14-67,极具说服力。老子生活年代在孔子之前,《老子》一书基本由老子自撰,几乎成为学者共识。本文所谓老子之前,是指大约公元前6世纪中期以前,也就是春秋中叶以前。
从学派归属来看,无为思想主要归于道家。《汉书·艺文志》载录道家文章993篇,在《老子》一书的前面,著录了《伊尹》51篇、《太公》237篇、《辛甲》29篇、《鬻子》22篇、《管子》86篇,而《黄帝四经》、《黄帝铭》等皆列于《老子》之后。显然,班固这样排列必有其由,是他在考察这些著作的年代之后而给出的说法。班固又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17]认为道家思想是来源于史官的君人南面之术,到了后来才出现反礼学、弃仁义的激进者,此即老聃、庄周等人。所以,就其学术渊源而言,老子的无为思想也应当是脱胎于君人南面之术,只是在论述上有了根本性的转向。
列在《老子》之前的几部书之中,《伊尹》、《辛甲》、《鬻子》三书已渺无可寻,只在一些文献中还能见到有关这几个人的只言片语。伊尹在回答商汤的提问时说:“设四佐以自辅,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禄。贤者进以显荣,罢者退而劳力,是以主无遗忧,下无邪慝,百官能治,臣下乐职,恩流群生,润泽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18]12-13百官分职、举贤任能而达致“不下堂而天下治”的观点正是君道无为思想的体现,亦是班固所谓“秉要执本”。鬻熊又称鬻子,乃周文王之师,楚人先祖。《列子·黄帝》引鬻子之言:“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强胜不若己,至于若己者刚;柔胜出于己者,其力不可量。”⑧杨伯峻《列子集释》卷一《天瑞篇》引梁章钜说:“诸子书以《鬻子》为最古,然其书有二。《汉书·艺文志》道家《鬻子说》二十二篇,又小说家《鬻子说》十九篇。列子所引《鬻子》凡三条,皆黄老清净之说,与今本不类,疑即道家二十二篇之文。”又《淮南子·缪称训》:“老子学商容,见舌而知守柔矣。”可见贵柔持弱已是老子之前较为流行的观点,亦即班固所说的“卑弱以自持”。这些都说明,班固关于道家学术源流的叙述并非虚言,无为思想也是早期道家的主张之一。
《太公》一书分《谋》81篇,《言》71篇,《兵》85篇,但班固那时就怀疑有后人伪作掺入,今仅存旧题周太师吕望的《六韬》。关于《六韬》的真伪、成书年代及作者,自北宋以来聚讼不已。银雀山汉简本的出土基本证实此书是先秦作品,虽然具体的成书年代各有说法,但多数学者认为此书是源于周代史官对吕望与周王对话的实录[19]。司马迁说:“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13]1480吕尚治理齐国,因俗简礼,实际上就是对君道无为的实践。他与周文王在这一方面有很多的思考。《太平御览》卷八十四引了《周书》中文王与太公的两段对话:
文王独坐,屏去左右,深念远虑,召太公望曰:“帝王猛暴无文,强梁好武,侵凌诸侯,苦劳天下,百姓之怨心生矣。其灾,予奚行而得免于无道乎?”太公曰:“因其所为,且兴其化,上知天道,中知人事,下知地理,乃可以有国焉。”[20]396
文王昌曰:“吾闻之,无变古,无易常,无阴谋,无擅制,无更创,为此则不祥。”太公曰:“夫天下,非常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国,非常一人之国也。莫常有之,惟有道者取之。古之王者,未使民民化,未赏民民劝,不知怒,不知喜,愉愉然其如赤子。此古善为政也。”[20]395
这两段话清晰地表明了两人对于无为而治的赞赏。文王认为,帝王由于不受任何限制,总爱以自己的意志妄作妄为,结果无非是扰乱天下,怨心四起,最终变成无道之君。太公进而提出,要避免成为无道之君,就要通晓天道、人事、地理,采取“因”和“化”的施政方法。“因”即要顺应天道、人事、地理之本然,不以自我意志为转移;“化”即要因循万物之自然,不强加自我意志于其中,达到“未使民民化,未赏民民劝”之境。在第二段对话中,文王连用五个“无”字,鲜明地反映出他对于有为转致乱为的一种担心。《艺文类聚》卷十二引《周书》记述文王对太子姬发的告诫也连用了七个“不”字:“吾厚德而广惠,不为骄侈,不为泰靡,童牛不服,童马不驰,土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时,以成万材。”[21]同样体现了文王顺自然、返质朴、不妄为的治国主张。这些主张在《诗经》中也能略见一二。《大雅·皇矣》:“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郑玄笺曰:“我归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虚广言语,以外作容貌,不长诸夏以变更王法者。其为人不识古,不知今,顺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尚诚实,贵性自然。”[9]1213又《大雅·文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孔颖达疏曰:“上天所为之事,无声音,无臭味,人耳不闻其音声,鼻不闻其香臭,其事冥寞,欲效无由。王欲顺之,但近法文王之道,则与天下万国作信。”[9]1131法文王之道,即如法天。由此看出,文王顺自然而治的理念和实践在当时已经深入人心。
在《六韬》中,文王、太公这种“因”、“化”而无为的思想也多有表露。《武韬·文启》载太公语:“天有常形,民有常生,与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静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从政,是以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与而自富。此圣人之德也。”天成万物而不显己功,圣人或因之,或化之,惠民无形而功勋自著。具体到政事就是《文韬·国务》所说:“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赋敛则与之,俭宫室台榭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可见,文王、太公鉴于商纣之暴政,对如何与民休息、如何无为而治进行了深入思考,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或传吕尚所作《金人铭》,语曰:“毋多言,毋多事;多言多败,多事多害。”⑨罗泌《路史》卷十四云:“世谓太公作《金人》。”是属于立身处世的行为禁忌,表现出对过度有为的一种谨慎态度。
吕尚受封于齐地,其治国思想旋即应用于齐国,并影响着他的继承者们,管仲是其中的佼佼者。司马迁评价管仲为政“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又能与民众同好恶,做到“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13]2132。管仲治国显然遵循了太公因俗简礼的理念,将因循之法的应用对象扩大化了。班固所见《管子》,今仅存76篇。尽管研究者已经形成此书非一人一时之作的共识,但在此书是否包含管仲遗著或学说这个问题上争议还是非常激烈的。张岱年先生认为,《管子》书中“经言”内的《牧民》、《形势》、《权修》、《乘马》等篇是管仲思想的记录,保存了管子的遗说[22]。《形势》篇说:“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释之。藏之无形,天之道也。”顺从天道而行,事成亦如自然,其状无为无形。《乘马》篇又说:“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不自以为所贵,则君道也。贵而不过度,则臣道也。”管仲推崇法天而无为的帝者,主张君道不贵有为,臣道则贵在有为而不越职。管仲的这些思想,较之吕尚更具有形而上的意味。
以上事实表明,老子之前无为思想确已萌芽。不过,这个阶段的无为思想集中体现在治道层面,即萌生于政治领域。一些长期处在权力高层的知识精英,经历过残酷的政治斗争,能够将自然与人事对照起来观察,发现自然界有着纷繁而不乱、简易而有序的运行规律。鉴于人类社会的混乱和残酷,他们主张最高统治者应该效法天地,尽量减少政治过度干预民众的行为。这种思想对于减轻君主独裁政体下人们的痛苦明显具有实际意义。
四、无为思想至老子、孔子而自成体系
进入春秋以后,周朝礼乐崩坏,知识阶层迅速分化,导致各种典籍以及各种思想观念流布四方。同时,新的社会土壤也孕育了许多新的思想观念。由吕尚、管仲等人倡导的无为而治的理念在齐国仍然有着生命力。晏婴为政尚宽省刑,曾担心孔子会将礼乐制度移植于齐国,他说:“今孔丘盛声乐以侈世,饰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以仪世,劳思不可以补民,兼寿不能殚其教,当年不能究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其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导民。今欲封之,以移齐国之俗,非所以导众存民也。”[23]明确指出礼乐制度繁琐而愚民的后果,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简易、不扰民的执政理念。这一执政理念在其他诸侯国也存在。据《左传·昭公六年》载:郑人铸刑书,叔向写信给郑子产称:“国将亡,必多制。”这与老子“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精神实质没有什么不同。晋平公向师旷请教为君之道,师旷回答说:“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18]1君上清静无为的背后需要有超强的素养、能力和手段。这里所体现的君道无为思想已显露出由外转内的倾向,更加注重君主内在的修为,而不单单是役人术了。《吕氏春秋·孟冬纪·异宝》载录伍子胥对江上丈人的赞歌:“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众矣,将奚不有为也?而无以为。为矣而无以为之,名不可得而闻,身不可得而见,其惟江上之丈人乎?”江上丈人内修无为,自隐无名,实近于老子眼中的圣人。当然,无为思想只有在老子、孔子手里才第一次明朗化、体系化,尤其是老子,将无为思想发展成了自己的核心思想。
据司马迁所记,老子本是楚人,供职东周很久,曾任守藏室之史,后见王朝衰败,遂归隐而去。史官的经历让老子有条件遍览群书,接触到各色各样的人物,接受到多元思想的冲击,能够目睹社会变迁,感悟兴衰之理,由此而成一家之言。老子以前,无为思想大都以君人南面术的面目示人,经老子一转,已基本褪去帝王术的色彩,表现为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一种普遍性思考。根据刘笑敢先生的研究,《老子》通行本中“无为”一词出现12次,在帛书本中也出现9次,“无为”不是一个孤立的语言形式,事实上,它只是老子的一系列否定式用语的总代表,是一个集合式的概念族,包括或代表了一系列与通常观念不同的处世方法和态度[16]111-112。这种现象在老子之前及老子同时代的其他文献中是不能见到的,足以证明无为思想得到了老子的极度垂青和创造性阐释。老子论述无为,虽零散而不集中,但综合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认识,可以自成体系。道是老子哲学的形上之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37章)、“道常无名”(32章),无为、无名本是道的性质,非由外入。“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40章),道从形上向形下的落实过程中,无为成了宇宙、社会、人生的普遍原则,而得道、体道的圣人自然就成为这一普遍原则的掌握者。圣人无为主要体现在治国治天下、处世接物和自身修养这三个方面。无为而治依然是老子无为思想的核心部分,与吕尚、管仲等人的治国思想也有相接的地方。比如,都反对无道之君的苛政,“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65章)、“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57章);都重视民众自治的能力,“万物将自化”、“天下将自定”(37章)。但是,老子论无为而治,已经完全脱离了君道的藩篱。全书论述无为只有1处提到“侯王”,圣人成了无为而治的施予者。圣人不以威权,不用役人,只是循道而行,通过自然法则和万物自理来达到“无不为”的效果,所谓“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2章)、“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64章)。更重要的是,圣人之治国、治天下绝对不以占有为目的。全书反复宣讲“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10章)的主张,这是老子阐述无为而治最具有创造性和闪光点的地方,摆脱了一般统治者贪功恋权的世俗目的,使得无为而治成为超越君主专制社会的理想政治模式。除政治领域以外,老子还将无为思想推向处世接物和个人修养等领域,具有开创之功。天道无为,“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73章),所以圣人效法于天道,“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64章),把柔弱处下、“不敢为天下先”、“为而不争”作为处世接物的原则。在个人修养方面,圣人也是循道而行,将人的品格与道的品格合一。“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48章),说明圣人是以不断减损的方法来进行内在修养的,正与世俗相反。世俗常汲汲于有为,所以圣人要“为无为,事无事”;世俗常“可欲”、“不知足”、“欲得”,所以圣人要“少私寡欲”、“去甚、去奢、去泰”,要“知足”、“知止”。基于上面的分析,可知无为思想在老子那里获得了全新的发展,成为老子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自成体系。
有很多文献记载孔子曾问学于老子,其思想恐怕难脱老子的影响。就无为思想而言,孔子与老子也有相通之处。孔子感叹:“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24]274又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24]118天道运行,寂然无声而万物成焉,圣君要做的即是效法于它。此与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章)的本质是一致的。孔子是第一个明确提出“无为而治”这一概念的人,但在如何达到“无为而治”这个问题上,他与老子的认识完全不同。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24]236这里的“恭己”、“正南面”并非后世黄老学派的君人南面术,与吕尚、管仲的“因”、“化”思想也不相同。“恭己”乃德政,“正南面”是礼治。孔子认为,由德政、礼治而致无为之治的前提是“正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24]193。这与老子崇尚“无名”的说法正好相反。正名之外,又要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24]196统治者先要“身正”,然后才能以德化人,以礼治人。“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24]188在孔子看来,道德的感化力量要远胜过刑罚的威慑作用,只有德政才能凝聚人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4]15德政、礼治犹如雨露,润物无声,不为而成。据《说苑·君道》记载,虞人与芮人相争,后进入文王境内,被当地百姓谦让的美德所感化,于是孔子由衷赞叹:“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动而变,无为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这是孔子“恭己正南面”所期望达到的最高境界,也是孔子眼中无为而治的极致。孔子论无为虽局限于治道,不如老子那样全面,也无老子形而上学的思辨色彩,但通过德政、礼治而致无为,则是他对无为思想的新贡献。
五、结语
综上所述,先秦无为思想的起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它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先民在农耕文化下敬畏自然、依附自然、顺从自然的心理和行为。随着政治文明的不断延伸,人们与自然以及自身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暴政、虐民、争斗等乱象频发,一些知识精英,如文王、吕尚、管仲,开始反思人类的行为,无为思想即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萌生,无疑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后来,更多的知识精英对此加以思考,其中以老子和孔子最为杰出。正是在老子那里,无为思想由萌芽而趋壮大,成为其标志性的思想之一,也成为后世道家无为思想的纲领性理论。孔子则立足于德政和礼治两方面来申明其无为而治的观点,同样成为后世儒家无为思想的纲领性理论。同时,老子的无为理论还被其后的法家所利用,被改造成一种较为阴暗的君人南面之术。先秦无为思想至此而完全成熟。
[1]刘笑敢.“无为”思想的发展——从《老子》到《淮南子》[J].中华文化论坛,1996(2):93-100.
[2]徐可超.《老子》“无为”辨[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9-13.
[3]高明.帛书老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6:106.
[4]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M].北京:中华书局,1988:17877.
[5]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卷24[M].上海:上海书店,1985:114.
[6]庞朴.庞朴文集:第4卷[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56-68.
[7]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中[M].东方学会石印本,1927.
[8]高田忠周.古籀篇:卷61[M].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2.
[9]孔颖达.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0]李生龙.无为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4.
[11]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0:128.
[12]孔颖达.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21-322.
[1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
[14]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110.
[15]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1963:17.
[16]刘笑敢.老子年代新考与思想新诠[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
[17]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32.
[18]向宗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9]杨朝明.关于六韬成书的文献学考察[J].中国文化研究,2002(春之卷):58-65.
[20]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1]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222.
[22]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M].上海:三联书店,1982:47.
[23]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2:491-492.
[24]何晏,邢昺.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