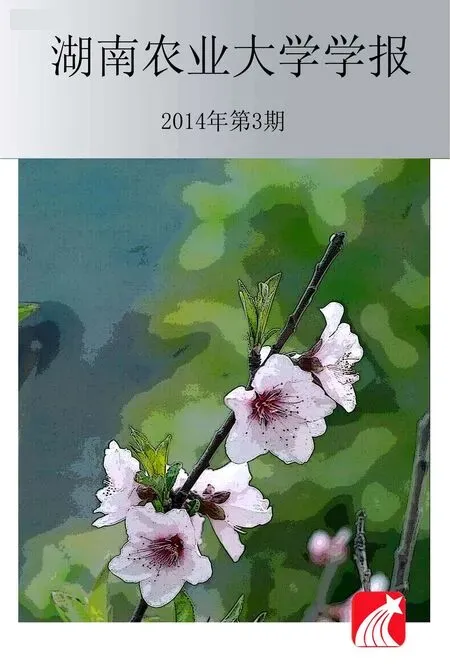农村产业化项目扶贫运作逻辑与机制的完善
马良灿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农村产业化项目扶贫运作逻辑与机制的完善
马良灿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产业化项目扶贫是当前中国农村扶贫、减贫与促进贫困地区乡村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产业项目扶贫运作逻辑受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体三个行为主体利益博弈的影响与塑造。这一运作模式存在一些缺陷,如项目立项与运行受到领导人意志支配,缺乏规范的议程,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基层扶贫工作人员和项目实施各单位之间缺乏有效配合;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联结出现断裂;产业化扶贫政策及其运行脱离地方实践和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导致国家意志和贫困群体的主体性需求难以实现。要使当前的产业扶贫真正惠及穷人,既要打破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权力关系结构,尊重和重建广大基层组织与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地位,又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助,形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有效连接,重视社会工作者的参与,推动扶贫工作由单一的行政主体运作向多方参与的社会化运作机制的转变。
农村产业化项目扶贫;运作逻辑;社会工作
2006年农业税费废止后, 以项目扶贫为基础的制度安排成为链接乡村基层政权与底层民众、国家与社会的一种中介性存在。在扶贫实践中,基层政权与贫困群体、基层组织与上级政府、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了微妙而复杂的社会互动。推动农村扶贫项目的基本动力机制是什么,是何种因素在主导当前中国农村的扶贫实践。这涉及的其实是对中国农村扶贫项目的运作逻辑的解答。只有明了扶贫项目的运作逻辑,才能弄清当前农村扶贫与反贫困实践面临的困境。因此,对扶贫项目逻辑的追问,就是对当前中国农村扶贫何以可能、如何进行贫困治理的回答。笔者拟以西部地区农村产业化项目扶贫实践为经验素材,探讨农村扶贫项目运作逻辑及其缺陷,以期为缓解当前中国农村扶贫实践与反贫困面临的困境探讨可能的治理路径。
一、农村产业化项目扶贫的运作逻辑
从农业税费改革以来,国家财政实现集权化,大量专项资金通过各种项目的形式下发给地方政府,项目制对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影响深远,不仅重构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各级政府之间的科层制权力结构关系,也重塑了地方政权组织行为[1,2]。近年来大量农村产业化扶贫项目的实际运作更是深刻地体现出以项目制为核心的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对基层政府组织行为的影响,折射出农民群体与基层政府、基层组织与上级政府的关系被重塑[3]。在扶贫项目的制度框架中,需要纳入分析的有“发包”项目的上级政府(地市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省级政府及职能部门、中央各部委及相关部门等),中间政府(县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特别是以乡镇政府为核心的基层政权)和农民群体三个行为主体。每个行为主体都在追求自身利益,他们的行为逻辑体现出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三者之间角色与行为既影响着产业化扶贫项目的运作逻辑,又被其塑造。
产业化扶贫项目由上级政府确立,最终落实者为以乡镇政府为核心的基层政权组织。乡镇政府的组织行为,即如何运作这些项目受到科层制权力结构关系的影响与制约。由于存在层级利益分化,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各级政府间存在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比如在项目运作中下级政府并不总是切实执行上级政策,而是在利益权衡中有选择地执行[4]。上级政府为了推动工作,便以强大的专制权力给基层政府巨大压力以达到其工作目标[5]。“目标管理责任制”作为在基层政府中普遍采用的动员机制,通过将上级政府所规定的行政总目标逐次进行分解和细化,形成一套目标和指标体系,再按照指标体系对下级的实际工作落实情况进行考核奖惩,以此调动基层政府官员的工作积极性[6]。西部Y镇的产业化扶贫工作就采用这一机制,乡镇政府领导采用包保负责的方式来负责涉农项目的具体实施,建立起了“五个一”的项目运作模式即“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人马、一个方案、一抓到底”,并将产业化扶贫项目建设直接与干部实绩考核挂钩,从而刺激基层干部完成工作指标。
除科层制权力结构关系外,农民群体同样影响着基层政府对农村产业化扶贫项目的选择和实施,影响着项目的实际运作。农村社区并非是产业化扶贫项目的单向输入方,农民群体同样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要求引进符合自身实情、能切实受益的产业项目,规避基层政府发放政绩工程项目并刻意追求政绩带来的风险,对项目的输入产生反作用力。产业化扶贫项目如果与农民群体的具体要求和切身利益不相符,若强制推行会强烈影响农民的生产生活,势必将引起农民的抗争与不满,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而基层政府由于上级对社会稳定的硬性要求,往往会被迫妥协,这是农民群体的“反控制”策略。在产业化扶贫项目推进过程中,因项目数量、种类、投入资金不同,经济水平相当的农民群体经常会认为别人分得的项目好、帮扶资金多,心生不满,造成新的社会矛盾。基层政府对此颇为头疼,在推行产业化扶贫项目时往往会向容易接受项目、不闹事的农民群体倾斜。
综上,作为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载体的产业化扶贫项目,其运作逻辑受到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体三个行为主体利益博弈的影响与塑造。上级政府意图和基层政府的运作都可能在给农村社区提供发展机遇的同时又带来相应风险。
二、农村产业化项目扶贫运作机制的缺陷
当前西部地区农村产业化扶贫项目实际运作实践表明,扶贫项目绩效与预期存在较大偏差。其运作机制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项目立项与运行受到领导人意志支配,缺乏规范的议程,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对项目立项的管理不够规范,空头支票现象时有发生。通常而言,在项目立项环节上,各乡镇政府均会投入很高的热情,感觉适合自己乡镇就去极力争取,并没有认真详实地实地调研,但是项目开始落实实施,特别在中期推进过程中,乡镇政府缺乏对项目实施具体有效的监管手段与力度,出现的问题无法及时发现与解决。许多项目就是中途出了问题但没有及时解决,导致问题积压,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最终导致项目流产。再加之项目设计过多地体现了上级部门和领导人的意志(即项目发包方的意志),并没有考虑到下面乡镇和农村的实际情况和真正需求;一些能够体现并利用地方优势的项目却缺乏关注、得不到重视,基层基础工作不到位,制作实施方案前期工作不够充分,缺乏预见问题的前瞻性,导致产业化扶贫项目在推行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因实施方案反复修改耽误项目进度的情况时有发生。许多基层干部将落实项目视为政治任务,报完帐就意味着项目结束、任务完成,项目也没有纳入滚动发展的机制。
第二,基层扶贫工作人员和项目实施各单位之间缺乏有效配合。2009年以来,因县域机构改革,乡镇扶贫工作站撤并入农业服务中心,造成大量的扶贫基础工作没有固定的部门和人员专门对接,有事找不到人做的情况经常出现,给产业化扶贫项目的落实实施、监督检查和管理报账等环节的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产业化扶贫是一项综合性工作,需要农业、畜牧、水利、林业、财政、科技等各部门分工配合,这些部门分别负责资金监管报账、技术支持服务、中后期监督检查、审计评估等方面的具体工作。随着产业化扶贫力度不断加大、产业扶贫类型的不断增加,产业化扶贫工作所涉及的协作单位也越来越多,工作任务更是日益繁重。再加上产业化扶贫工作成本高、资金程序复杂、责任重大,且多为长期项目,成效短期难显,部门在对待扶贫项目的态度上由开始的积极参与逐渐变成应付了事。总之,由于层级利益分化,各级政府和各部门间均存在着利益博弈,难免互相推诿,内耗日增。
第三,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联结出现断裂。由于各方面的制约因素,基层政府不重视产业化扶贫项目中公司、合作社和乡土能人等利益主体的示范带头作用。企业、合作社与农户的“风险共担”机制并未形成,三者联结松散,产业化扶贫项目的带动效应不强,农户依然面临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抵抗风险能力低下,遇到自然灾害或市场波动时便容易出现返贫现象。另外,在市场机制的决定作用日益凸显的今天,部分基层干部仍然停留在只抓生产不管销售的原始阶段,不知道怎样与市场主体打交道、更不知道怎样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当然这其中有乡镇政府与农民群体利益博弈的因素。显然,如果销售这条路打不通,农民群体无法真正受益。此外,各利益主体的合作大都止步于各自的基本利益连接,没有体现共同发展的核心主题,缺乏相应的规范制约,难以形成更大更强的合力。
第四,产业化扶贫政策及其运行脱离地方和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相同的项目在不同的乡镇落实实施产生的成效也不尽相同。对中国大部分省份来说,现有的省级产业化扶贫的政策规章制定得太过具体和细致,没有给基层政府留下灵活应对的空间,以根据地方发展要求整合项目。同时,产业化扶贫没有涵盖扶贫产业区的基础设施,部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属于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尚未完善的区域,农民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尚未得到保障,根本无法满足产业化发展所需的条件要求。因此,产业化扶贫项目在这里是不现实的。而在条件较好的区域,产业化扶贫项目往往大部分都是集中在到乡村能人和大户身上,少量贫困农民仅仅能够通过流转土地或者受雇做工的形式分得一小杯羹,而大多数的贫困农民却并未受益。
农村产业化扶贫项目运作问题重重,这与扶贫项目的运作逻辑直接相关。产业化扶贫项目的实施主体——乡镇政府的行为受到压力型权力结构因素和乡村因素的双重影响,其向下直接面对村庄中农民群体,向上应对的掌握着自身财权事权的上级政府,既要完成上级领导的意图,又要取得农民群体的支持与配合。这种夹缝中求生存的工作环境造就了其独特的组织行为。特别是基层政府迎合上级政府的领导意志、追求政绩的心理直接影响到反贫困的效果[7]。在科层制的权力结构体系内,上级政府通过掌握财权和事权来达到对下级政府的控制,基层政府处于一种“压力型体制”中[8]。基层官员升迁需要靠政绩,这造成了部分基层领导干部不正确的政绩观,他们会选择容易出政绩、直观且立竿见影的项目,而避开那些会使农民真正获益的但是需要投入精力多、时间长却不容易出政绩的项目。这就使得产业化扶贫项目带有强烈的领导人意志,背离了农村社区的实际和农民群体的真实需求。如将规模化养殖、连片种植等产业化扶贫项目全部实施在靠近公路的村组,大力打造“路边花”工程,与基层实际需求相背离。这种只考虑到上级领导下来考察时美观好看不管百姓实情的形式扶贫不但没有达到扶贫的本意,反而给农民生活带来更多问题。负责落实产业化扶贫项目的领导人想要得到上级领导认同,项目做完马上就要求评估,而不考虑农民是否真正获益,而上级下来检查验收也常起不到效果,因检查路线由基层政府事先选定,上级领导了解不到基层实际情况。项目验收结果又影响政策制定者决策,使决策发生偏差,更加难以解决基层实际问题,难以让农民能够真正获益。农民群体相对处于弱势地位,但是也有软武器来对抗产业化扶贫项目的输入,如不支持、不配合项目建设乃至上访,而上级政府对基层维稳有着硬性规定,基层政府往往会对非“刚性任务”采用变通的方式来稳定农村社区和农民群体[9],但变通的结果亦有可能使产业扶贫项目的运作与设计目的产生偏差。产业化扶贫作为近年来西部地区推出的战略扶贫模式,本应是持续稳定带动农民脱贫增收的有效途径,但现在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与原本预期产生了偏差。
三、农村产业化项目扶贫机制的完善
如何完善当前产业化项目扶贫机制,直接关系到贫困群体的切身利益和中国农村涉农项目的绩效。这种完善既要给基层减压、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又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沟通,形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有效连接、积极鼓励社会力量特别是专业社会工作者参与其中。
首先,可以适度下放产业化扶贫工作权限,给予基层政府适当的自主性。依据现行管理办法,产业化扶贫项目一旦审批,就要按照方案逐步推进。而作为最了解农村实际情况的乡镇政府和基层干部,在落实实施项目和应对项目推进中出现的问题时,调整工作的权限很小甚至没有。有些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明显暴露出严重的问题,但因基层政府没有即时处理甚至叫停的权力,需要上级政府批复,手续繁琐时间漫长,批复下来时已经错过了最佳调整时期,最终造成项目失败。对此,基层干部非常无奈。如果能将权限适度下发,让乡镇政府有权力能够根据农村社区和农民群体的具体要求和实际情况和项目推进中遇到的问题及时进行调整,让产业项目真正发挥出应有的效益,同时也可以避免项目资金不必要的浪费。提升基层政府自助权限的同时,事实上也增加了农民群体的参与度,提高了农民群体的满意度,维护了农村社区的稳定。此外,农村产业化扶贫工作运行成本较高,如果上级财政能在工作经费匹配上加大力度,将会有力促进基层政府对产业化扶贫工作的积极性。上级政府应将财权和事权适当下放,基层政府有了相应权限,可以适度对项目进行调整,规避压力性体制带来的弊端,避免出现项目体现强烈的领导人意志却不利于农村社区发展、农民群体脱贫致富的现象,特别是要杜绝当前农村扶贫过程中大量出现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
其次,加强各部门之间协作与提升人员素质。农村产业化扶贫项目的推行依然是靠基层政府集中高效的动员机制与程序[10]。因此,高效有力的机构组织和高素质的基层干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产业化扶贫力度的加大,参与进来的部门、单位也越来越多,各部门之间的协作也越来越多,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机构专职负责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调工作,明晰产业化扶贫部门的职能定位,进一步防止政府部门间的内耗现象。该部门应拥有相应权限,与各单位部门直接打交道,负责监督各部门人员与资金的投入,并与下面扶贫工作进行直接对接,可以直接与农民群体对话。各州县、乡镇应建立专门的扶贫机构,通过选拔、培训,培养一批优秀人才,解决基层工作找不到人做的实际问题。加强对扶贫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提高扶贫干部的业务素质与政治素养,使得扶贫工作顺畅进行。此外还要强化组织领导,加强责任机制和考核激励机制建设,建立健全人员管理机制,为扶贫工作开展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第三,加强各主体利益联结,建立风险共担机制,积极培养产业化扶贫市场主体,实现产业化扶贫项目的良性滚动发展。产业化扶贫本身是一种现代企业经营模式,因此,企业在进行产业化扶贫的同时必须建立与之对应的灵活高效的经营机制。产业化扶贫工作的最终目的是让贫困农民脱贫致富,其中的关键是项目要能产生效益。连片种植、规模化养殖丰收了,但是如果销售不力,收益依然无法装进农民口袋。所以基层政府在确立主导产业时,必须首先考虑卖出去的问题。这就要求既要着眼市场需求,又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还要看看自身的能力条件,风险相对小的项目比较容易被农民接受。产业化扶贫必须遵守市场化的经济规律,政府部门在帮助农民对接市场的过程中作用有限,需要依靠合作社、公司、企业这些经济主体来承担产业的市场风险。要建立产业化扶贫风险防范机制,贫困农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这就要求政府和企业要建立完善相应的机制,规避风险。因此,培养一批有实力有诚信的经济主体参与到产业化扶贫工作中来,是扶贫部门以后的重点工作之一。
第四,农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运作应当有社会力量、特别是专业社会工作者的积极介入。忽视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实践是当前农村扶贫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反贫困实践中,只有将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结合起来,中国农村扶贫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才有走向善治的可能[11]。而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力量的核心,在反贫困实践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社会工作在本质上是实践性的,目标是向社会提供专业化、优质化的社会服务,其基本精神是“助人自助”。社会工作者介入农村反贫困实践,不是要取代基层政府和社区的力量,而是要在政府机构和乡村之间进行斡旋和沟通,力争将各种行政性资源和社会资源引至社区中并转化为社区内部资源,通过资源合作实现社区增能,形成“合作型”的扶贫合力[12]。在农村反贫困实践中,社会工作者有助于整合并完善社区资源,促进社区参与,培育社区公共精神,拓展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社会工作者嵌入农村社区内生性组织建设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一种“嵌入性发展”[13]。这种嵌入不仅增强了农村反贫困的能力和合力,而且为社会工作专业本身拓展了新的领域和空间,这是一种双赢的发展过程。故而在农村反贫困实践中,应当高度重视社会工作专业组织的力量。
总之,农村产业化扶贫项目作为当前国家扶贫开发战略核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直接与扶贫项目的运作逻辑相关。如何改变现有的扶贫运作逻辑,使穷人成为产业化扶贫的真正受益者,这不仅事关国家扶贫项目的实效,而且关乎到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实践证明,产业化扶贫政策的落实与实施,不仅要依靠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权力体制与部门间的协作来驱动,还应当为基层减压,重视自下而上的底层民间力量和专业社会工作的广泛参与,形成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之间的有效合作。因此,在反贫困治理实践中,实现行政资源与非行政资源、行政权力与社会权力的有效对接,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三社联动”的农村社区建设机制,推动扶贫工作由单一的行政主体运作向多方参与的社会化运作机制的转变,将会对产业化扶贫的完善起到效率倍增的作用。
[1] 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6(6):100-115.
[2] 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J].社会,2012(1):1-37.
[3] 折晓叶,陈婴婴.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1(4):26-48.
[4] O'Brien,Kevin J and Li,Lianjiang,"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J].Comparative Politics, 1999,31:167-186.
[5] 周雪光,练宏.政府内部上下级部门间谈判的一个分析模型——以环境政策实施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11(5):80-96.
[6] 王汉生,王一鸽.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J].社会学研究,2009(2):61-92.
[7] 马良灿.项目制背景下农村扶贫工作及其限度[J].社会科学战线,2013(4):211-217.
[8] 荣敬本,崔之元.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8.
[9] 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C]//应星.中国社会学文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0] 陈家建.项目制与基层政府动员——对社会管理项目化运作的社会学考察[J].中国社会科学,2013(2):64-79.
[11] 许源源,陈书弈.空心社会、隐形社会、市民社会与行政国家:中国农村扶贫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解读[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30-35.
[12] 李文祥,郑树柏.社会工作介入与农村扶贫模式创新:基于中国村寨扶贫实践的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13(4):198-203.
[13] 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J].社会科学战线,2011(2):206-222.
责任编辑:陈向科
Poverty alleviation operational logic and mechanism perfection of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projects
MA Liang-c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using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projects is now a main method to relief and reduce rural poverty, and to promote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oor mountainous areas. There exist some flaws in operational logic of industrialization projects since it is influenced by the benefit game among government of higher level, basic government and farmers. The flaws present as following: it is haphazardly since the approval and the implement of a project are determined by the director; the grass-root staffs do not act in concert with unites in charge of project implementati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ain interest groups is broken; the policy and the implement are alienated from reality. In order to have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jects benefit the poor indeed,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break the power hierarchy; to respect and rebuild the subjective status of grass-root organizations and the disadvantaged group; to form an effective relationship among main interest group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workers so as to make the work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 multiparticipation mechanism.
poverty alleviation of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project; operational logic; social work
C912.82
A
1009-2013(2014)03-0010-05
10.13331/j.cnki.jhau(ss).2014.03.003
“农村社区治理与社会工作”笔谈
2014-06-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SH086);贵州大学文科重大科研项目(GDZT2012008)
马良灿(1979—),男,回族,云南昭通人,社会学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组织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