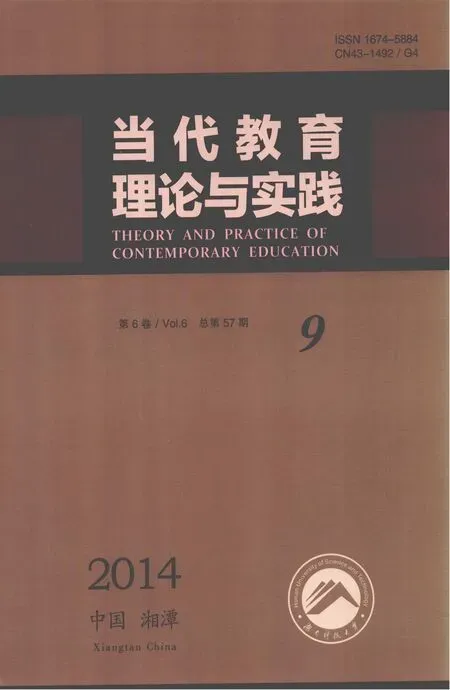浅谈张炜《古船》中的叙事者
王子安
(中北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山西 太原030051)
小说的叙述过程中,隐含一个叙述者的角色[1]。叙述者的作用不仅在于架构虚构世界和客观世界之间的桥梁,常常还暗含叙述中的客观意识。《古船》叙事者在叙述距离①的安排上精巧微妙。开篇以史诗般的笔触介绍了洼狸镇的前身——古东莱子国,然后才转入叙事主体——新时期洼狸镇的发展。在时间的跨度体现一种浩大的视野。叙述者在叙事主体中不断穿插人物回忆,对历史背景进行补充。小说还安排了一些小插曲来突显洼狸镇的历史,例如假借旧报纸上的新闻补述洼狸镇“文革”时期经历的苦难。
从秦汉时期起笔,纵横千年的史观基调展开叙述,让读者对洼狸镇镇史,特别是“文革”中的荒谬往事有客观的理解。第三人称的叙述帮助小说刻画人物纷繁复杂的个人经历,也为小说逐步揭露镇史的历史真相,捋清人物行为的内在动因打下基础。这种统领全文的叙事在后文深入个体人物回忆性叙事前,为深化小说形式起到了先手作用。洼狸镇新时期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中国大时代浪潮进程中的诸多相似。诸多新鲜事物与“文革”时的荒唐事重合:新时期的技术突破与“大跃进”过程中的“放卫星”前后对比,使洼狸镇的许多老人误以为“文革”又来了。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充当伏线,过往事件的错位放置与小说所在的现实叙事一同发展,演绎着“文革”前后中国的鲜活动态。
1 第三人称叙述
小说在叙事中避免单一的视角,虽然全文以第三人称叙述,但是在情结推进,特别是梳理洼狸镇镇史和人物回忆的过程中常有叙述视角的更迭。叙述的高度从俯视全局到细入个体自述,小说的叙述距离在不断拉近与缩小中循环往复。然而小说在时间上非线性叙事是严格遵循事件发展的前后一致,没有出现上下文的矛盾相左之处。个人回忆与洼狸镇镇史统一融洽,摆脱罗生门式真相的非确定性,在现代派风格中却恪守现实主义的严谨。
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往往比第一人称能为叙述带来更多的现实感,其效果是使用第一人称进行故事阐述所难以达到的[2]。小说运用第三人称,不同的人物回忆补充洼狸镇镇史粗线条的叙事,特别地,在第十五章大哥抱朴和弟弟见素的对话里的“伪第一人称”的使用,具有强烈的情感冲击。第十五章的叙述中除了着笔于少量的环境渲染,几乎全是兄弟两人的对话。这种类第一人称的叙述,阐明了见素对于场长赵多多莫名的仇恨,解释了抱朴寡言少语患上“怯病”的根源。此章节通过对话对叙事主体的真相进行步步紧逼,虚构人物的内心纠结的根源得到坦白。
叙事主体的真相在各个章节之间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进行叙述。通过不同人物的各自立场编制叙事主体的全貌时,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因立场的不同或者记忆的偏差造成的真相错位,甚至陷入“罗生门”式的叙事圈套。我们可以看出叙述者力图避免营造一个开放式的局面,于是第三人称叙述的优势在此处展现出来,摆脱“罗生门”机械式的全盘重复。
例如,母亲小茴之死是糅杂在几个不同事件中展示的,叙述者通过支配数个不同感情基调的侧面展开叙事,杂糅不同节点中的回忆萃取完整事件的真相。
(1)隋迎之
叙述者通过回溯的笔法讲述父亲隋迎之在一次算命之后大受刺激。此后每日策马外出,散尽家财,分送给乡镇的百姓。不假时日暴病而亡,母亲随之服毒自杀。
(2)隋抱朴
弟弟隋见素在母亲的死亡事件发生之时尚不记事,所以见素心中的母亲之死的事件真相是道听途说的。然而大哥隋抱朴和他人口中对于小茴的死,都只是含糊其辞的形容为“自杀身亡”。
(3)赵多多
在叙述者大范围补叙“文革”记事时,披露当时的革命团体荒谬而血腥的行径。赵多多作为当年“无敌革命团”头头,在第无数次搜查隋家的时候,碰见不堪迫害准备服毒自杀的小茴,强迫小茴脱下“带有资本主义毒荼”的衣服,要她死不安宁。在小茴不从之下,赵多多用剪刀连皮带肉地绞下衣服,导致小茴惨死,并在尸体上撒尿。
叙述者先运用虚构人物的话强调“小茴服毒自杀是真的”,给小茴之死的真相下一个结论,垄断读者的想象空间,使读者和案发时年幼无记忆的弟弟见素进入统一的定式思维之中。读者可以在纵贯整个叙事主体的情节跨度中,和主要人物见素一起找寻母亲小茴的死因真相。
在叙事主体的尾声,身患绝症的弟弟见素最后一次询问哥哥抱朴关于母亲的真实死因,哥哥才道出残酷变态往事的真相。此时,见素对赵多多的个人之憎加剧深化为家仇之恨,他拖着羸弱的身子提着砍刀去找赵多多。走过村子的时候,看到村口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他穿过围观的村民,却发现车毁人亡的赵多多。
小说意在还原叙事真相,并补充完整人物行为背后的心路历程,令二者成为同一个合理发生的事件。尽管人物都是虚构的产物,却在叙事中创造了自身性格和行为发展的合理性,赋予人物虚构的生命,且能够在矛盾冲突和个性发展中合理转型,达到一种超越虚构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真实感。小说在第三人称叙述的全知全能性与人物自身认知的局限性的共同作用下,不断地放大或者缩小叙述距离,产生了一种叙述的有机体。
2 客观意识
叙述者提供的不只是一个第三人称视角,还展现的是一个代表价值判断的客观意识。这一客观意识在微观角度对主体叙述加以道德层面上的微调,在题材上隶属伤痕文学中的理性批判,也在宏观上更准确把握对“文革”的反思。客观意识的存在使叙述距离的扩大与缩小过程中,提供了某种叙述的原动力,这一动力将所有任务的行为和背后隐藏的人性动因推向某种更高层次的交融。叙述者通过把握视角风格与审美形式奠定道德批判的基调,没有一味进行人性的控诉或反思,而在部分真相与全面真相的演绎中推进,诠释了客观意识的重要作用。
我们不难发现此客观意识提供了一个价值判断:即虚构人物在“文革”时期犯下的过错都不是本性使然,而是在时代重压下的自发行径。这一道德层面上的“无罪推论”集中体现在小说的结尾,经历过“文革”的两个人物赵多多,赵柄的去世与退场。不管他们生前的善与恶,叙述者在为他们结尾时都试图表现出同样地哀思,旨在为过去的时代划上中肯的休止符。叙述者对于“文革”中反面人物的暴行安排某种合理化的演绎,似乎暗示着洼狸镇人民的本质都是善良非邪恶的。但是,毕竟暴力在道德批判层面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客观意识掌控下结局中看到叙述者的巧妙安排。
(1)赵多多
“文革”中暴行累累的赵多多,虽然在承包粉丝场取得了经济利益上的成就,但因为粉丝掺假的质量问题曝光,导致资金链断裂粉丝场停产,最后不堪重压自杀身亡。关于恶人赵多多的一连串情节安排让读者得到精神上的补偿,也符合恶有恶报的儒家传统价值判断。
(2)赵炳
四爷爷赵柄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在小说前半段叙述中道貌岸然,实际在“文革”时暗中犯下许多权利暴力。曾暗中派人把“说错话”的技术员李其生吊在梁上打,自导自演充当及时雨宋江,救其于水火之中。通过暗箱操作获得李其生终生的恩报,好让他在死心塌地为自己工作。在那个视生命为草芥的血腥荒唐年代,掌权者仿佛被赋予生杀予夺的权利。当小说收尾阶段,三妹含章用剪刀侧向四爷爷的腹部,宣告了结束这一段历史沉淀的积怨恩仇。
“文革”中暴力的书写借助某种压抑人性的历史背景,通过不断加码受害者的心理包袱,引发最后反抗爆发的效果。赵多多和四爷爷的或死或伤,是道德上对其罪过的清算,符合客观意识对戕害人性的暴力控诉。多层递进式结构“镇史——回忆”创造了一个高度融合,且具有反复叙事的流动性叙事主体。“文革”中纷繁杂乱的沉重往事通过流动视角,通过多人的个体经历进行反复渗透,从不同角度寻求道德批判和再现诉求。风格别异的叙述层次与视角设计带有现代派的先锋性,实际上却流露出一种时间轴上的延展。叙述者采取渐进式的叙述视角,首先铺垫完成了外部宏观框架,然后才使人物性格的转变在历史背景的推进中逐步成型,最后才完整还原“文革”时期典型人物变态行径的全部事实。叙述者在权衡情节连贯与叙事推进中,先用客观的笔调进行零度叙事,简约描写事件本身的大体经过,铺设“非真相的真相”,即“部分真相”,然后静待后文中掺杂人性中阴暗面的“完全真相”的还原。这种层层推进的叙述距离有效解析出“文革”中反面人物变态行径发生的合理性。叙述者的客观意识利用这种合理性,通过不同视角的切换解释荒唐血腥的事件的因果关系。
叙述者遵循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淡化绝对化的是非判断标准,人物行为仿佛没有了错对之分。这种客观冷静地笔法赋予读者在爱憎立场上自由选择的空间。人物和与之对应的行径没有过多形而上的“左”“右”派别指向。叙述者抛却对人物带有偏颇基调的脸谱化分类,注重虚构人物自身发展过程中自我实现,形成拥有内在张力的人物形象。正是多个具有两面性的人物设定,使小说具有连续的,反思的元素,实现对于历史真相的猎杀。小镇中无知与暴力让我们看到“文革”时期洼狸镇人民生活中的道德异化。人的行为在“文革”浪潮中兽化,似乎不是一种人性的沦丧,而是处在非理性狂潮中的正常表现。
[1](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2](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