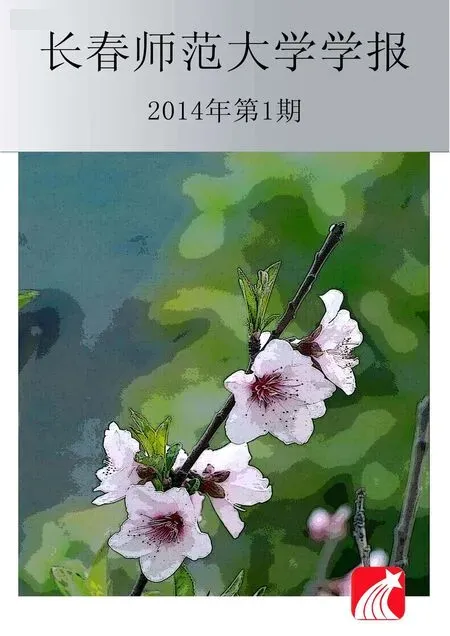多元识读培养与大学英语后续课程设置
梅 勇
(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当今的教育界不得不面对两大社会趋势:一是文化日趋多元化和各类语言变体(特别是英语变体)不断涌现;二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文字为主的表意方式逐渐被听觉、视觉和手势等其他表意方式取代,“人类进入社会符号学多模态化的新世纪”[1]。这两个变化都给英语教学和其他课程教学的内容和方法带来了影响[2],包括大学英语后续课程。
教育部2007年公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指出,大学英语应用提高阶段课程,作为完成基础英语课后的提高课程,旨在培养学生高层次英语交际能力和应用能力,以及提高他们的英语文化素养和文学鉴赏能力等。换言之,大学英语基础课程之后的使命将不再仅仅是基本的读写能力培养。就国内实际情况而言,现在大学新生、特别是重点大学的学生的英语水平越来越好[3]。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已非(计算机网络支持的)教学模式的改革,而应根据国家外语教育战略和社会对学生外语水平的需求,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开设相应的后续课程。许多高校亦意识到这一点,纷纷开设各类大学英语后续课程,从单一的语言技能课程和考试辅导课程逐渐演变到社会和文化等专业英语系列课程。[4]
遗憾的是,迄今大多数大学英语后续课程的设置仍以识读能力为目标,未能全面反映两大社会趋势所提出的诉求。胡壮麟教授指出,“传统以读写为主的识读能力在多媒体时代已不够用”[1]。在新的教育情境下,传统的读写能力(literacy)培养模式逐渐落伍,更紧迫的是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多元识读”能力(multiliteracies)培养。朱永生教授亦提出,培养学生的多元识读能力符合我国的“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2],同时呼吁教育界应充分认识到多元识读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建议在教学大纲中纳入多元识读能力的培养。朱永生教授还建议,为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多元识读能力,教师自身应具有较高的多元识读能力。
一、多元识读的提出及相关研究
(一)多元识读概念的提出
Multiliteracies(张德禄等译为多元读写,朱永生译为多元识读,本文侧重其多元识读含义)是相较于单一识读能力(literacy)而言的。1994年,美国的James Gee、英国的Norman Fairclough以及Gunther Kress,连同澳大利亚的Mary Kalantzis等著名学者成立了新伦敦小组(the New London Group)。他们在探讨分析当今识读教学的未来(the future of literacy teaching)时首次提出了多元识读能力[5]。该概念的提出基于两个重要因素:其一是交流方式和多媒体变得日益多重性,其二是全球间文化和语言的多样化程度日益显著。有鉴于此,传统的以文字为载体、单一文化为内容的识读能力培养已经落伍。如该组织成员之一的Kress就提出,无论何种语篇,包括口头的、文字的或者图像的,其意义总是通过多重符号模态来表达。而要理解这些由多重模态构建的语篇,必要前提是对Multiliteracies的充分把握[6]。
(二)多元识读的内涵
对于多元识读的内涵,国内外学者们进行了各自的探讨。Thwaites提出多元识读应包含六种具体能力,包括文化识读、媒体识读、科技识读、批评性识读、政治识读以及后现代识读[7]。其他学者如Gentle、Knight和Corrigan等人把多元识读能力细分为五种成分:语言成分、听觉成分、视觉成分、姿态成分和空间成分[8]。
在国内,胡壮麟教授指出多元识读分为文化识读能力和技术识读能力两部分[1]。文化识读是用来描述、包容和尊重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能力;而技术识读能力即多模态识读能力,指在信息社会中意义创造与构建的能力。张德禄教授则将多元识读能力归纳为以下三类:(1)语言读写能力。这与传统意义上的语言能力有所不同,更强调认识社会符号、不同模态的优劣以及各种模态之间的配合。(2)社会交际的能力。体现在文化读写、批评读写、政治读写以及后现代读写等方面。具体而言,指对目标语文化有深刻认识,具有良好的批评判断能力;还有对不同文化的理解、接受和调适能力。(3)技术读写的能力。体现在科技读写和媒体读写两方面。具体来说,是指能够掌握现代的媒体技术并熟练应用[9]。
尽管学者们对多元识读能力内涵看法或异,但基本上反映了新伦敦小组对当今教学环境和挑战的分析,只是在具体范畴分类上有所不同。
(三)基于多元识读的教学模式
新伦敦小组建议给学生展示已有的典型性多模态语篇,分析其中各模态以及总体特点,并引导学生将现有的语篇进行重新改造和设计,以此来综合培养他们的语言读写能力、社会交际能力和技术读写能力[5]。学生从中可以逐渐获得应对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交流表达方式多样化的能力。
新伦敦小组倡导“多元识读”教学,将设计构建意义作为教学理念,具体包括可利用的设计、设计过程和重新设计等阶段,揭示意义的建构是主动和动态的过程。这种教学模式强调利用多种符号资源来习得语言和文化。教师应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角度,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主动性,使语言和文化的学习不再是单一的吸收过程,而是通过理解、比较和评判来把握语言和多元文化[10]。具体步骤可以分为四步:实景实践、明确指导、批判性框定和转换实践[9]。
二、当前我国大学英语后续课程设置的主要观点
国内在后续课程建设的方向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专门用途英语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ESP),以蔡基刚为代表。具体可分为学术英语(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EAP)和职业英语(English for occupational purposes,EOP),且以学术英语为主[11]。另一种是大学英语通识课程(English for Liberal Education,ELE),以培养国际视野下的跨文化素养以及提升学业和职业竞争力为根[12]。简言之,大学英语通识教育就是给具备扎实英语语言功底的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以英语为教和学的语言开设一批高质量的以世界各国(含中国)文化为内容的英语课程。可以看出,无论ESP还是ELE方向的后续课程,都是以课程内容为主的设置(content-based),以图改变现有大学英语基础课程的技能性倾向。前者强调大学英语的工具性,后者强调大学英语的人文性。
基于已有对多元识读定义及内涵的探讨,可以看出,多元识读能力的培养应兼顾工具性及人文性两方面。
三、多元识读培养对后续课程设置的挑战
(一)多元识读培养在后续课程设置中的地位
对于多元识读能力的培养,学界存在着两种理解——同化观和调适观[13]。同化观立足传统、常规的读写教育,试图让新读写(即多元识读)为现存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时间服务;后者则更具革新精神,认为应该从根本上重新审视其带给教育教学的其他变化。同化观只关注意义以外制造意义的新方式。如在讲解新单词时,教师可以通过多种模态达到同样的目的,例如运用板书解释、PPT呈现,甚至上网查找语料库。而调适观还研究新的意义潜势和意义系统。对同样的教学任务,教师可以要求学生通过查词典了解新词的基本含义,制作PPT画面加强对用法的理解,以及运用语料库阐述新词生僻用法或常用搭配等等。在此过程中,学生不仅理解了单词的意义和用法,同时了解到如何查找词典、理解图片与文字的相互关系,甚至掌握语料库的操作方法等等。
多元识读的内涵十分丰富,只有全面、科学地规划后续课程的体系,才不至于顾此失彼。故而多元识读能力培养应作为后续课程建设的主要目标,而不应成为现有课程的点缀,事实上它也是体验和体现大学英语教改最终成果的一种展示。
(二)多元识读培养在后续课程设置中的体现
目前许多国内高校的后续课程设置少,忽略了学生的个性需求,表现为在实际的大学英语教学中,一些高校开设出的选修课程是为了满足教师的岗位要求,没有考虑到学生的个性需求[14],更遑论将多元识读能力培养科学地纳入课程设置之中。
总体而言,现有后续课程是专业课程与英语课程的有机结合,主要体现在四大类课程上——语言技能类课程、语言应用类课程、语言文化类课程,以及专业英语课程。这些课程已经部分地涉及多元识读能力的培养,但系统性有待加强。可以将以下因素考虑在内。
首先,多元识读能力的基本内涵是对多元文化要有深刻的认识,并能敏锐地意识到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对各种文化特别是目标语文化应有深入的理解,熟悉相应的基本准则、交际规范甚至是道德准则等等。这些都反映在语言文化类的课程之中,包括目标语文化介绍课程以及不同文化对比等课程。
其次,多元识读能力包括设计多种模态的能力,学生需要有选择地学习,把学习的重点放在语言以及经常与语言协同和搭配进行交际的模态上[9]。在后续课程设置时,应适当增加兼具图文模态、视听读模态以及听读写模态综合类的课程。这些课程可以通过分析典型性多模态语篇并对现有的语篇进行重新设计来实施。
再次,增设课程以提高学生的批评性意识,培养他们的批评性分析能力。具备了适当的批评能力,学生将能够客观地审视所学知识,并能进行建设性的分析和批评,最后能够创造性地应用这些知识。
最后,技术读写的能力也是多元识读能力不可或缺的部分,包括科技读写和媒体读写。尽管其初看与语言学习关联不大,实质上这是所有学习者要具备的现代媒体技术的知识和能力。后续课程中可以提高PPT制作、网络资源查询等技能的比重。
四、结论
当前我国以后续课程建设为重点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正不断深化。多元识读作为全新的学习方式,是多种文化交融情境下信息社会对学习者识读能力的新要求,这给大学英语改革提出了挑战,同时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为此,在大学英语设置后续课程制订时,应充分考虑到多元识读能力培养的重要性,有意识地将其纳入课程设置之中。同时,应改革过去的识读能力教学模式,注重学生学习英语时的社会互动和实践,而不是孤立地阅读和理解英语语言。
[1]胡壮麟.社会符号学研究中的多模态化[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1):1-10.
[2]朱永生.多元读写能力研究及其对我国教学改革的启示[J].外语研究,2008(4):10-14.
[3]马武林.大学英语后续课程内容设置探究(一)——学术英语[J].外语研究,2011(5):15-21.
[4]沈向怡,曾庆勇.CBI理论指导下的大学英语后续课程体系建设[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101-102.
[5]New London Group.A Pedagogy of Multiliteracies:Designing social futures[J].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1996(1):60-93.
[6]韦琴红.多模态化与大学生多元识读能力研究[J].外语电化教育,2009(126):28-32.
[7]Thwaites,T.1999.Multiliteracies:a new direction for arts education[EB/OL].http://www.Swin.edu.au/aare/99pap/thw99528.htm
[8]Gentle,F.,M .K night& M.Corrigan.Multiliteracies and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Ensuring Information Access in the Class room for Students with Vision Impairment[EB/OL].http://www.ridbc.org.au.
[9]张德禄.多模态学习能力培养模式探索[J].外语研究,2012(2):9-14.
[10]杨渝,丁年青.多元识读教学法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的应用及启示[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4):20-22.
[11]蔡基刚.关于我国大学英语教学重新定位的思考[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C(4):306-308.
[12]王哲,李军军.大学外语通识教育改革探索[J].外语电化教学,2010(5):3-8.
[13]陈瑜敏.多模态教学环境下英语读写研究的新进展[J].英语教师,2011(5):60-63.
[14]霍玉秀.大学英语后续课程体系的思考[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0(7):149-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