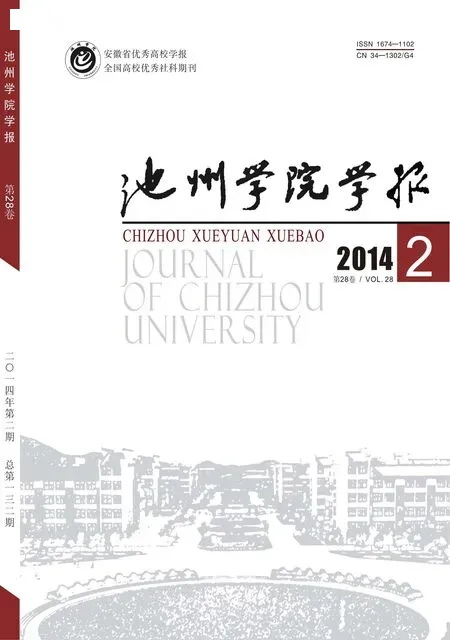世界文学的伦理性
柳士军,编 译
(信阳师范学院 大学外语部,河南 信阳 215123)
世界文学的伦理性
柳士军,编 译
(信阳师范学院 大学外语部,河南 信阳 215123)
世界文学研究与教学随着全球化的降临越来越普遍了。译介的这篇论文主要讨论了世界文学与世界的关系的分析以及它与伦理学关联性研究。世界文学的伦理思想准备的规范就是在“世界”本身这个概念危机上,世界文学伦理的内涵在不同的异议中寻找共同的利益。世界文学没有必要远离伦理之土壤。文章认为转向伦理学的文学批评与哲学批评是不会过时的,并且会长期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征。
世界文学;世界;伦理;文学批评
表面看来,世界文学伦理学的这个范例仅仅是深入而多样的文学与伦理学阐释的一个延伸而已。传统方法认为,如果我们采取适当、负责的生活方式,我们就会有一个美好的生活;尽管自康德之后,伦理学已经独立出来(因为它不仅是指做正确的事),文学是比道德哲学本身更加显著且具有影响力的向导。同其他人一样,文学批评的“伦理转向”也引起了我的兴趣,不仅是因为如同迈克尔·俄斯肯(2004)所强调的,文学与伦理学的结合,无论多么恼火,却是西方哲学的根本。一度,文学中的伦理学被其他更重要的关注挤出了轨道,比方一度对于文本自足性的职业性坚持,或者固执于枯燥晦涩的“高深理论”,很少考虑对于读者的责任。然而,表象往往具有欺骗性。比如,二战后哲学并没有排除伦理学,而是认为伦理是更为棘手的问题。战争中实施的集体屠杀,包括大屠杀中人性降到最低点,使得伦理学丧失了对行为和思考实践的吸引力。词汇好像被骗走了它们本身的内涵,如同成百万无辜的生命被剥夺了他们的全部体积一样。作为转换,人们就更为安全地追求起了价值,诸多重建项目如马歇尔计划就提供了资本积累的终极性的善。伦理学并没有消失,但是要用它来显而易见地应对20世纪所释放的种种恐怖还需要时间。
然而,不仅仅是战争要求一种新的伦理语言,而且战争最亲近的亲戚—帝国主义也在设法否定那些位于西方人文主义核心的、极具说服力而且值得重视的伦理表述。帝国主义越认为殖民掠夺适于西方理想的推进,伦理行为的缺陷也就越大。艾梅·塞泽尔用“文明与殖民?”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就使伦理学即使不像是骗局谎言也是微不足道的。而甘地却嘲讽道:“我认为西方文明将会是一个好主意,”他强调道德善行说教的受益者们看到了一个迥然不同的议程表。即使伦理学不单纯是意识形态,它也是在“应该”的口号重压下苦苦挣扎(如同在“它应该比现实更多”中一样)。
在伦理学最近的这段历史中,第三个因素来源于尼采,他对规范伦理学中的“应该”不感兴趣,正如他非常蔑视那些视来世重于今生的宗教思想。这里不再具体讨论尼采所发现的在道德和伦理学中的不足,在克服这些道德和伦理学观念方面,他影响力较大的的评论是基于表述虚无主义以外的某种东西。朱迪斯·巴特勒最近将尼采对伦理学的悖离与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相反的举措做了比较。尼采通过给予那些高贵者和高贵行为特权而扼杀他者(那种地位我们没几个人能够拥有);列维纳斯让他者呼吸(如同与“我”对应的一个生者),但也仅仅是通过这一途径:即声明它的伦理诉求是令人窒息的并且自行其是的。巴特勒取消了两者 的对立,但是她?既不是要以伦理学的名义去营救尼采也不是要以之去营救列维纳斯。事实上,她对伦理学的抵制更多是出于抵制的精神本身(基本如同辖制“做”的范畴),尤其当涉及到政治,这个任何伦理学中都包含的一个实质性条款的时候。如同巴特勒的细读企图论述的一样,转向伦理学不仅仅是对抽象高深理论的一种反动,而且也是理论关注其自身对于真理的主张的一个历史表现。在分析哲学范围内,这也许更多是对一个主题的变异,如,推理与伦理推理的重要不同,但是大陆哲学已经渐渐地把责任当作关于哲学方法论的一个独立话语从至高无上的主体性(“我”)中剔除出去了。阿甘本关于“赤裸生命”的著作就在此处进入了我们的头脑,即必须批判“奥斯维辛之后的伦理学”再建构所真正意指的东西(列维纳斯也对这个主题有所阐发)。
伦理学的转向无论是在文学批评还是在哲学批评,都不算姗姗来迟,而且它也是发生在在重要的哲学和历史争论领域内部的一个重新思考。世界文学伦理学是否是这些潮流的附带现象呢?它是否有自己的系谱学,而且它是否与全球化背景下商品化势力有不可回避的联系?在这个角度,伦理学是否受制于夹缝市场,如伦理购物,以致于世界文学可以被解读为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选择,在这样一个空间里,“唯心主义之后的伦理学”作为一个矛盾的物质表现可能会显得可以逆转?
然而,对于以上这样的问题,任何一个有创造性的回应,无论那些最初的假设显得多么不确定,就世界文学伦理学本身所突出的局限性而言,这个回应都需要一个更进一步的注解。的确,在那样的构想中,到底运用的是什么样的世界概念,这种观念根本上使世界文学伦理观的可能性发生了短路。对于纯文学主义者来说,“文学”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因为这个毫无疑问,是与价值判断,道德概览,以及值得关注的文化识别影响力相提并论的。对于正确与错误、好与坏等的“辨别”,看起来既高于也外在于“了解方面的不同”本身,这个不同被当做是关于“世界”作为一个观念的一种话语。世界的概念与世界文学的分别几乎是有过错的,因为前者是从哲学的范畴讨论伦理学,而后者则是从更接近于存在保证的某个东西方面来讨论:如果世界文学“存在”,它的存在本身就确保了它的诸多伦理,在一个没有这些伦理的“世界”上,文学没法宣称自己存在。“世界文学”这个术语仅导致描绘伦理学是什么,却不会导致对正在应用的世界概念中的这个哲学难题进行分析。在这里,至少,让我们想起列维斯(F.R Leavis)在阐述自己对于“伟大传统”的解释之后,最喜欢留给学生的问题:“事情不会是这样吧?”它是一个有效的判断原则,一个道义上确定无疑的事情,即凡是算作文学的东西都必须努力达成一个讨论,以讨论伦理学方面的任何限定性话语。就这个可能的原因而言,没什么东西显得必然不合理,同样,在激情昂扬地为伦理学实质辩护时,人们也不应该简单地排除掉文学的依据。事实上,转向伦理学的视野,如我们所描绘的那样,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是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色,尤其是在形式主义衰落以及现代主义后期表现出伪科学性以来。很显然,价值在世界和文学中都有着严谨的概念,但是推设可以用世界文学所体现的那样相同的方法来表述价值,也是很轻率的。伦理思想不能解决世界文学中的一些陷阱(政治学和经济学对于它的历史性出现可能提供更多的洞见)。相反,人们可能会考虑到伦理学能够为世界文学的思索性质提供视角,将伦理学多多少少视为一种未来本体论(存在会成为的东西),这种文学阐释会将伦理学变成与其是一个价值体系,倒不如是一个从社会交往而言更具有论战性的文化空间。
依照斯宾诺莎的精神本质,倒并不必然依照他的哲学,我愿意努力促成一个未来的世界文学,它不会忽略文学的伦理学之根,即歌德的原初伦理学,其曾经深受一个世纪前葡萄牙-荷兰思想家一元论诽谤的影响。对于大多数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读者来说,他们最不感兴趣的不是自然和上帝的同一性,而是这种伦理学是用几何学顺序来论证的,好像只有欧几米德用拉丁语的精确计算才能回避情感分类的不可捉摸。令人遗憾的是,斯宾诺莎是通过一个富有严密秩序的命题和推演过程来考察伦理学构成的,这些命题和推演通常与情感的不稳定性无关。但是,正如莫莱蒂(Moretti)通过绘图和阐释,指出世界文学意味存在问题一样,世界文学的伦理思想可以被视为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而不是通过反复陈述才不言不明的一个由证据和推演构成的系统。这一点并不必然地消减其抽象性,而是它倾向于抵制一种观念,即世界文学仅仅是道德哲学适度全球化的结果。这种几何性突出了一种开创性的、存在于渴求一种伦理学方法论和我们那些经常毫无系统的情感之间的张力。歌德喜欢斯宾诺莎方法的理由之一是因为它更强调伦理学问题的形式而不是将答案内容标准化(这个在文学依据本身中可以找到)。世界文学的复兴不能是将歌德的概念连同其随之而来的伦理责任简单地重新播放,而是一个深刻的重新组合,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一个危机决定的,即我们如何理解“世界”本身。危机的模式可能有些相似,但是具体的危机不仅需要差异方面的方法论,而且需要我们称之为中立方法论的东西,这种方法论不会臆断世界文学对于差异的庆祝(这个本身无可指责)会消耗殆尽当今“世界”危机所涉及到的伦理责任。
世界文学伦理学的第一个原则依赖于“世界”概念中的这个危机。至少可以说,世界文学作为伦理资源的作用是很矛盾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世界文学就体现了这种危机的症候。给世界下定义不是限制它(正如将世界作为复数,并不必然地扩展它一样)。这整个原则表明世界文学在“世界”的危机中发现它的伦理,从而制定这种伦理而不是克服它。这并不排除在世界文学的倡导者中有一种可贵的愿望,要求通过文学来推进全球性的理解;更准确地说,它强调所有的世界文学,无论它是别的什么,都应该试图思考世界这个概念,而且如此思考的必要性因为这个概念危机显得更加突出了,这个概念危机因为其光芒已成了主要事例。对于歌德来说,“世界”根本上是一个国家议程的延伸,借此,一个国家的文学通过其认可全球范围的文学作品,明确和丰富其文学特色(歌德认为这点低看了民族文学,但是它并没有损坏民族观念,这一点甚至随便阅读一下歌德之后的德国史就可以确认)。这一点在世界文学的当代表述中依然强有力地存在,就如同那些公认的全球化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基于最高独立权而构建互动一样。
总体看来,这种由来已久的论述是建立在民族自恋主义的诸多形式之上的。“世界”成了一个不在场的辩解:因为有“世界”我们才可以算作一个民族(这是一个对莫莱蒂精准阐释小说的相当严谨的阐述)。“世界”危机部分在于参入这个世界的种种民族特权的固执,已到了它们可以从中分离出来的程度。承认世界是对他者的欢迎,全球性地保持了一种对地区他异性的民族性外在化,可以说“世界”能够承载如此位移的重压。相对照的是,南希(Jean-Luc Nancy)认为世界的概念是自己本身的创造,不是一个允许民族自恋主义坚持的目的论目标。这就意味着全球一体化的暂停,我们所知的世界的意义是根本虚拟的,不是主观的。对于南希来说,全球化运动,或者世界化,是从无(ex nihilo)到有的一个创造过程,并且提前停止了分享世界是指内容传播扩展的这一观念(在我们的语境里,指的是文学的内容)。根据这种方法,“世界”不再指代一个更大的整体(对于每一个处于全球性世界的民族而言),相反,它标志着一个依据于自身的、与自身连接的关系。在世界文学中使用“世界”这个词汇的好处在于它使再现世界的文学与作为自己的世界的世界文学之间的张力有了生命力(后者是 Pascale Casanova世界文学的世界多系统理论体系的一个标志)。一方面,我们依然自由地承认文学有构成不同世界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说这样的文学,作为与自身创造更美好的世界的一种关系,如何流传或许并不必然丰富世界的形成。作为一种红利,全球化运动保持了某种不可译介性,而这个依然是对于世界文学形成一种比较文学式理解的一个深刻关注点。南希的理论仍然有一些弱点,它们没怎么修正我们主要关注的伦理学问题。首先,全球化运动不是全球化的一个替代选项,如果通过后者我们指的是一种特殊的资本积累和流通的逻辑。南希用来描述全球化特色的坚韧哲学(尤其是在术语的水平上)没法像经济学一样来探测世界关系的复杂性。当他评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第11条论纲时(“哲学家们仅仅解释了世界,关键却是要改变它”),他似乎在强调而不是在消除疑虑,即不是实践而是阐释处于危险当中。当马克思思考资本的革命性逻辑时,他不是从虚无(ex nihilo)中开始思考的。资本创立的世界是可以精确转化的,因为是资本创造了它。在世界形成中,“世界”的观念仅仅只有哲学的激情去养育它,因此,当南希问道“主权是否是人民反感的东西”时,对于这个世界我们所知道的还不够,还不能去想象它可能的轮廓。当然,这种反应也可能讲通,就是将作为一个概念的“世界”再次客观具体化,接着又将它背叛。我们尊重“世界”的概念与自身的联系,但依然怀疑它作为一个政治与经济的整体是否具有预知性。它是一个杠杆,一个对全球化化身观念的反应,被视为科技决定论的一种极为有效的方式。但是从杠杆转为全球公正的这种变化,也是南希的《世界或全球化创造》这本书的结尾部分,却承载着比“世界”陌生化所能承载的更多的概念性负荷。这也是给世界文学伦理思想的一个教训,世界文学必须满足于具体世界自身的文学叙述,而不是满足于对世界全球化所有相互影响的一种假定对应性。
但是很多批评家已经将世界文学降低为一个远为谦卑的诉求,与“世界”本身暗含意义相比较,那么为何还要在它概念的地平线上额外地笼罩一片阴云?如果南希目前所解释的“世界”已经内置了某种僵局或不可能,举例说,在区分流行的多种危机层次这一点上,还是有一些价值的;的确,也许是区分这些化合价的能力构成了世界文学伦理学本身。这方面的测试个案不是南希恰当地放置在“世界”概念之上的那些问题,而是“世界”在世界经典里面变成了“世界性”的那种轻巧。世界性经常被表述为在这个世界上对差异的开放,而不是我们在爱德华·萨义德的著作里所看到的强调之处,例如,他强调从这样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批判立场去进行思考。另外,这不是说,世界文学不利于激发开明的世界性。远非如此,应该认真对待世界文学,尤其是在它最近的表现方面,准确地说,因为它敢于讨论整个世界规模上的文化差异性问题。然而,如我所强调的是,这些关注常常暴露方法论的局限而不是减轻它。
世界主义伦理观一直处于激烈的辩论之中,自从全球化的到来则变得更加广泛了。世界主义越与文化资本和精英列表方式联系在一起,在全球化的理解上它就好像越少与伦理基础相对应。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比方说,后殖民主义的世界主义证明书遭到挑战,被认为是一种最近活跃的知识分子派别的证据,这个群体被天真地解读为来自全球化南方文化的真正代表。这种批评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而且激起一种更有希望的、对于部分来自重新思考法侬、萨义德和葛兰西的基本原则的批判性思考。今天在经济全球化的神盾下,重现了妥协性世界主义的世界文学问题沦落到了关于价值构成的世界文学伦理学的第二原则。如果“世界”的概念将世界文学作为认识论计划的启蒙程序加以置换或者去中心化,那么,价值将是世界文学拥抱世界这一愿望的麻烦空间。
世界文学与全球化之间的分离性吸引,似乎存在于文化与经济价值的二元对立中。正如在其他人中卡莎诺瓦(Casanova)所表明的,作为一个学科,组织世界文学的文学体系在目前的世界体系中,只是相对独立于对资本积累而言至关重要的剩余价值。前者的美学偏爱似乎破坏了后者粗暴的经济中心论,但是正如英国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最初机遇被亲近地联系上了帝国主义的宏观社会现实一样,当代世界文学的表现在冷战之后清晰可辨的、事实已然存在的全球化处境中被提纯了。当歌德与马克思都是在依据全球化流通与交易的语境下展望世界文学时,价值的问题已经变形,好像世界规模商品化那野蛮的力量已经瓦解了文化/经济分界线两边任一方所确认的价值命题。另外,问题不在于具体文学作品所支持的价值是否构成适当的全球伦理,而在于根据全球化形成的世界是否是决定性因素,以决定那些目前提出价值,包括文学价值的条件。
资本积累的世界性是伪造的普遍性,因为它所推行的普通等价物主要依赖的是抽象的劳动力价值。当斯宾诺莎将价值置于自治权中时,它不是为作为美好生活的商品服务,也不是为通过剥夺而积累的行为服务。的确,在《伦理学》中阐述的快乐和热情能够与他个人的禁欲主义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歌德,再次在斯宾诺莎的影响下(见贝尔1984年,举例而言)企图在他的作品中表达顺从与幸福的一致性。然而,如果歌德的世界文学依凭的是这种对于斯宾诺莎伦理学的癖好,那么它的价值体系就已经被商品学说庸俗化了。人性的培养,对于歌德而言在《教育学》和赫尔德的人性理想中都有概括性体现,这种培养很显然与以资本为基础的现代性有协同效应,然而这点却经常指出它的伦理学观点是唯心主义最后的凭借,并不是与资本主义非人化因素相对立的、恒定的并且批判性的“应该”。在这种群体关系中,价值就在虚无上面蹒跚而行,积累(资本的)悖论性地标志着这个虚无,显然不同于可能来自文学的价值增长。
根据以上虚无与价值的联系,世界文学的理想主义不是一个错误的意识,相反关于“世界”麻烦重重的物质化,它提出了一些问题,这种理想主义可以推定应当与物质化相对应并且/或者对其进行质问。总体而言,世界文学与世界的差距,连同未来的世界文学与曾经的世界文学的差异,一起构建了一个深刻竞斗的空间。在这里,世界文学的伦理观必须不同于那些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伦理观(对于你来说,市场就是好的),而且也不同于在全球化公民社会理论范围内看起来值得赞赏的异质性。后者已经从一种认识中浮现出来了,那种认识认为民族国家政体的特殊津贴不足以支持非政府性跨国主义的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却冒着风险,要么会忽视要么会低估(从这个词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独立国家对于尤其南方国家大力重新定位所做出的贡献。在这个层次上,伦理学的问题不是关于西方主要自由民主的道德说教,而是关于“世界”本身是否某种程度上是由非殖民化和脱离任何伦理实质而产生出来的话语的爆发,那种伦理实质在世界范围内曾经让政府和屈从稳定化和正常化。世界文学如何应对这个烦人的竞斗空间呢?
这里有一些限制和可能性存在。如果我们相信世界文学的思想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那么它的伦理场域就会随着现代性的结束而沉没。另一方面,如果世界文学被解读为一个创造性的辩论领域,关于文化价值轮廓作为一个有条件的跨国话语的,那么现代性的术语就不会仅仅为了确认或者嘲弄而存在。不可能有基于标准化的他者权利或者将他者权利乏力包容的世界文学伦理学。这并不意味我们会走向斯密特(Carl Schmitt)所探究的一种例外的恐怖状态,也不意味着甚至我们一直处在这种例外的条件中,却意味着世界文学的伦理内涵在非凡的异议中能找到它共同的利益。
作为一个逻辑问题,从单一中提出的伦理观却好像会对抗巨大“世界”承诺的包容主义。这个目的在于抵制“世界”与伦理是全球化人权纯粹理念的这一观念。相反,文学对于“世界”的微薄的贡献不仅仅在于追问“世界”在那个星群中的实质,还在于写出自身真理主张的种种矛盾(举例说,Jacques Rancière[2010],是将这种伦理观与公民和人类之间伦理观对立着解读的;这关键在文学与“世界”之间)。这种异议坚持它的单一性并不是因为一个具体的艺术品讨论与否与“世界”的不可代表性,而是因为它反对一种思想,即世界性主要是一个恰当道德内容的整体,这种道德内容信仰是简单而可以归纳的东西。在世界文学中,伦理观会发现自己对抗着自身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没有分裂成道德相对主义,却成了一个任务,要怀疑任何一个生活在一种臆断中的世界,这个想法认为对它的实践,对个人或集体,都会让我们在差异性方面轻松一些。
那么,伦理学就不会成为按照世界文学自身形象来生产世界文学的一个教育学蓝图。反过来,世界文学也不可能仅仅通过编选来自尽可能多地方的大量伟大文学作品来分泌出一个伦理学。在适度全球化的文学研究实践中,“世界”僵局并不能阻止可能的伦理责任。相反,相比基于世界性积累(事实上,通过文学来收集世界)其他方面不明确的姿态而提出一种道德指导而言,关注冲突过程自身要更重要得多。此时,“世界”概念不允许我们将之假设为一个伦理道德的渊源,而如果它凭借自身成了这样一种源泉,文学就将不再需要它来做修饰语。如果这似乎距离歌德那由斯宾诺莎激发的自然道德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的话,它依然将保留某种自身对快乐的信仰,将它也视为批判思考的愉悦。那些裁定这种努力的伦理的东西,就是作为自身基础的世界,如我所设法表明的那样,这个世界甚至只能用极为有限的术语将世界文学的领域变得可以深度争论。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应该”关注它,而不考虑康德绝对命令的精确原因。
(本文原载于Theo D’haen,David Damrosch and Djelal Kadir主编的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一书,第365-372页,Routledge 2012年出版。作者Peter Hitchcock,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巴鲁克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学与文化研究。)
[1]Ag amben,G.Remnants of Auschwitz[M].trans D.Heller-Roazen.New York:Zone Books,2002.
[2]Bell,D.Spinoza in Germany from 1670 to the Age of Goethe [M].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1984.
[3]Butler,J.“Ethical Ambivalence”[M]//J.Stauffer and B.Bergo.Nietzsche and Levina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 70-80.
[4]Casanova,P.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M].trans.M.B.de Bevois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5]Chow,R.Ethics after Idealism [M].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7.
[6]Eskin,M.The double turn to ethics and literature[J].Poetics Today,2004,25(4):557-72.
[7]Herder,J.G.Philosophical Writings[M].trans.M.N.Forst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8]Kant,I.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M].trans.M.Grego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9]Keane,J.Global Civil Society? [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10]Levinas,E.Otherwise than Being[M].trans.A.Lingis, Norwell.MA: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1.
[11]Marx,K.Capital:Volume One[M].trans.B.Fowkes.London: Penguin,1992.
[12]Moretti,F.Maps,Graphs,Trees[M].London:Verso.2007.
[13]Nancy,J.-L.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or Globalization[M].trans.F.Raffoul and D.Pettigrew,Albany:SUNY Press,2007.
[14]Nietzsche,F.W.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M].trans.D.Smith,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15]Schmitt,C.Dictatorship[M].New York:Polity Press,2010.
[16]Spinoza,B.de.Ethics [M].trans.E.Curley.New York: Penguin,2005.
[责任编辑:余义兵]
IO-03
A
1674-1104(2014)02-0015-05
10.13420/j.cnki.jczu.2014.02.004
2014-03-12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2AZD090);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13-GH-406)。
柳士军(1973-),男,河南商城人,信阳师范学院大学外语部副教授,苏州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艺理论与中西诗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