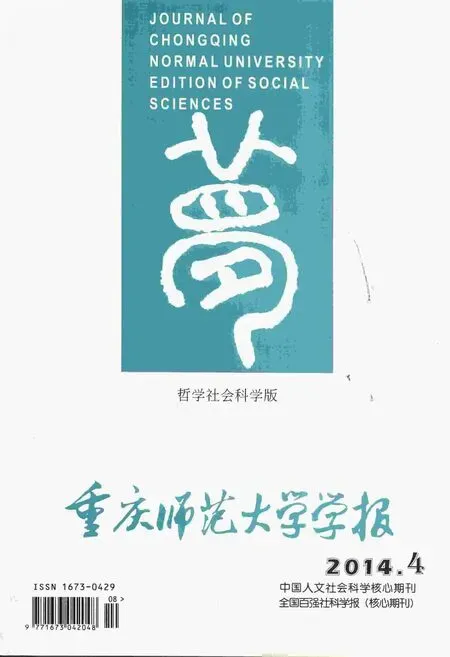“人民性”与“人民国家”主体想象——中国当代文学“人民性”话语历史考察之一
李祖德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主体性”问题,始终伴随着中国近现代思想建构民族国家和寻求现代性的进程,有若草灰蛇线般地隐伏于各种话语或概念诸如“国民性”“人民性”“工农兵”“社会主义新人”“人”之中。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心话语,“人民性”不只是中国当代文学知识生产和意识形态生产中的一个理论话语或概念,更是一种与“文学-国家”主体性建构相契合的观念、愿望与想象。从“国民性”到“人民性”,从知识分子的启蒙叙事到国家论述,勾勒出了中国新文学的主体想象和主体性建构的话语与意义的踪迹。
一
在现代性(modernity)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理论视域中,20世纪中国新文学(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被嵌入了现代民族国家(现代中国)建构的历史工程之中,或者说中国现代文学亦是近现代中国寻求现代性的诸种方案之一。正如有论者所说,“就其基本特质而言,20世纪中国文学乃是现代中国的民族文学。”[1]在这一现代性进程中,中国现代文学原初的、最基本的功能就在于为一个未来“现代中国”的降临建构或想象出一种“民族/国家”主体性。概括地说,这种主体性也就是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早期启蒙主义思潮所聚焦的“国民”与“国民性”问题。因为,要建构这样一个现代的“群”——民族国家,就“因此产生了的‘群’的知识,产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产生了有关‘公德’和‘公性情’的讨论。由于民族主义话语的规划,20世纪初形成了‘国民性’的知识讨论”[2]。正是因为晚清以降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促成了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巨变和全新的观念、知识的建构,这也便构成了20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根本性的话语与思想场域。
在某种意义上,对于现代“中国人”“国民”“国民性”的主体想象表征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层书写欲望和集体无意识。无论是梁启超的“新民”与“群治”之说,还是鲁迅对于“国民性”及“国民劣根性”的叙事,还是沈从文对于古旧中国乡村道德与文化理想的怀旧书写,甚至包括赵树理关于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与日常生活及伦理变迁的呈现,这些“故事”“能指”或知识论述都可理解为这一深层欲望(焦虑)与无意识的文化/文学表征。但历史的复杂性与可能性决定了“国民”或“国民性”这一意指的变化和延异。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中,这一“想象——意指”结构发生了潜在而深刻的衍变。
在5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建制之初,周扬曾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最伟大的启蒙主义者鲁迅曾经痛切地鞭挞了我们民族的所谓‘国民性’,这种‘国民性’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长期统治在人民身上所造成的一种落后精神状态。他批判地描写了中国人民性格的这个消极的、阴暗的、悲惨的方面,期望一种新的国民性的诞生。现在中国人民经过了三十年的斗争,已经开始挣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发展了中国民族固有的勤劳勇敢及其他一切的优良品性,新的国民性正在形成之中。我们的作品就反映着与推进着新的国民性的成长的过程。”[3]75周扬在此有意识地提到了“新的国民性”,或许意在将当代文学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传统建立起某种精神联系,从而为新中国文艺的创制寻找历史的资源和历史(新/现代文学史)的合法性,但在新的历史情势和政治、文化、意识形态语境中,“国民性”这一概念已经不能完全与新的历史视野相叠合,也渐渐失去了它最初的历史愿望和叙事效能。或者说,要与中国当代文学新的历史视界相“融合”,需要新的中心话语和理论概念。于是,“人民性”,而不是“国民性”成为当代文学新的主体想象。
从理论话语本身来看,“国民”“国民性”想象所投射的“民族国家”形象乃是近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关于“世界”的重新筹划,一种新的关于“历史/时间”、“地理/空间”的规划。这乃是所谓的“现代性”——现时代的人们对于自我、群体、他者及世界的新的感知、知识与观念,当然也是近现代世界的现实情境。“民族国家”因此而成为一种新的关于“世界/他者”与“民族/自我”的想象,一种新的关于“群”(民族、国家)的普遍性知识。正如马克斯·韦伯在其《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所说,“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4]92
对于20世纪初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启蒙主义知识分子来说,面临外部强势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冲击,以及自我的、内在的“王朝/天下”想象崩解的焦虑,建构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便成为拯救自我的“历史”以进入资本主义所规划的“现代世界”的唯一途径。“从那时起,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迅速地发展了一部线性的、进化的中国史,基本上以欧洲从中世纪专制制度获得解放的经验为样板。……梁启超批评中国传统史学按王朝纪年来划分历史,而忽略国民的历史。他的历史观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以致他使用区域性的比喻把线性的分期比做是民族国家之间用以标志各自辖区的条约。”[5]21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便萌生了这样一种现代“民族国家”的知识与观念。尽管一代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如梁启超仍然对自我的“历史”与“文明”心怀眷恋,但正如列文森在《梁启超与现代中国思想》中说的那样,由于“历史与价值的撕裂”[6]1,一代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对巨变时期中国的想象终究无可逃脱地被他者化,被迫陷入“民族国家”话语与想象的知识/认识范型。亦如列文森所阐明的那样,由于儒家文化秩序的断裂,“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7]87由此,“国民”“国民性”,而不是“人民”,当然更非传统的“臣民”或“子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启蒙叙事的深层欲望(焦虑)与终极目标。
另一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初,作为一个新生的现实的政治实体和“想象的共同体”,“人民共和国”也已脱离了早前一代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关于“现代/新中国”的想象,“国民”与“国民性”话语已不能满足建构新的国家和国家主体之需。从理论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概念及其内涵与外延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方社会政治理论中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概念,因为它并不是以“民族/国民”(nation)为主体的,也不完全是以政党和上层官僚系统为主体的“党国”(party-state),而是以带有特定阶级属性和阶级意识的“人民”为主体想象的“人民国家”(people-state)。在中国当代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中,通常被具体表述为“社会主义”或“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50年代初中国当代文学指导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中,亦已开始将“民族”这一想象逐渐转换为“人民”想象,从而将不同的“民族”想象并整合成一个新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同体,由此建构了内涵有异于“民族国家”的另一种国家想象和国家形象。
同时,对于这个新生的国家而言,“国家的合法性不是来自国家本身,而是来自人民。”[8]67因此,“人民”与“人民性”成为新的国家论述和文学话语。就文学的“人民性”概念本身及来源而言,这一概念较早见于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如普希金、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关于俄罗斯文学品格的论述。这与早期俄罗斯文学的本土化、民族化、现实性诉求有关。尤其是在别林斯基的论述中,“人民性”不只是带有“阶级/底层”的倾向,更带有“民族”(包括有教养的阶层)的意涵,是否具有“人民性”关键在于是否体现了俄罗斯文学的“现实性”。[9]83但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语境中,“人民”和“人民性”带有“阶级/阶层”的倾向是毋庸置疑的。陈晓明认为,“在漫长的社会主义文艺运动中,人民性是一个与‘党性’相互置换的概念,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运动中也同样如此。在正统的文艺学论著中,尽管也给予人民性更宽泛的含义,但其本质还是定位在‘党性’支配着人民性的内涵。”[10]因此,“人民”及“人民性”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心话语,更具有复杂的意涵。它们既是一个带有阶级/阶层色彩与政治含义的主体性概念和文学观念,也是一个关涉到对新政权、新国家的合法性来源的总叙事,同时也关涉到这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主体的想象与建构。
“作为民族主权的基础,人民很古老,可是他们必须获得新生以参与新世界……人民必须经过创造而成为人民。同样,在中国和印度那样的新民族国家,知识分子与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工程之一,过去是、现在依然是重新塑造‘人民’。人民的教育学不仅是民族国家教育系统的任务,也是知识分子的任务。”[5]19虽然杜赞奇仍然是在“民族国家”这一资本主义启蒙现代性的视野中来谈论作为民族国家主体的“人民”,但其论述也表明:新的现实政治条件、知识话语和文学建制需要新的主体想象,沉睡的、处于自然状态的“人民”必须经过“寻唤”和重塑,才能真正成为“人民共和国”的主体(带有阶级意涵的“人民”)。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当代文学”,正是这样的一门“人民的教育学”,由此展开关于“人民”“人民性”的话语建构,并试图界定其想象与叙事的范围。
二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建制中,尤其在文艺指导思想和文艺政策层面上,诸如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文艺界领导人讲话、“作协”和“文联”等文艺部门的政策方针以及《人民日报》“社论”等带有政策性和指导性的文本中,都存在着大量关于文学“人民性”的论述。这些论述既可能是针对文学创作的,也可能是针对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尽管这些论述之间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也隐含着一定的矛盾与冲突,但在总体上形成了建构“人民”“人民性”话语的一种指导性思想。
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中国当代文学“人民性”这一核心话语的确立及生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这一经典文本中。这一文本也直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建制的蓝本和依据。这一文本和毛泽东早期的一些文本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新民主主义论》(1940)等也有着较直接的思想关联,可以说它们之间形成了一种“互文本”(inter-text)的关系。考察这些文本和话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关于“农民”“革命群众”“人民群众”“劳苦大众”的论述隐藏着中国当代文学“人民性”话语的历史踪迹。
在毛泽东关于“人民”“人民性”的论述中,首先构想了未来的“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此目标和前提下构想了未来的中国新文化和新文艺。对未来国家和文化的主人——“人民”的构想的问题也自然同时提出。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就首先为20世纪中国和中国新文化设定了这样一个现代性目标:“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11]663具体而言,新文化和新文艺的基本特征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11]706-708,也是具有“中国性”的,即“新鲜活泼的、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2]534关于“人民”的论述由此展开:“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形成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11]708
建设“新文化”固然是重要的现代性目标之一,但最重要的在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要这种“新文化”,更要将其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这一现代民族国家工程建立起内在的关联。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新文化”与“新国家”的主体是谁?看起来,“中华民族”的“新国家”以及具有民族性与中国性的新文化,其主体自然应该是全体“民族”(nation)与“国民”(natives),但“工农劳苦民众”限定了这一主体的阶级属性和倾向性,它并不是笼统的全体“国民”,尽管它占“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以致后来毛泽东明确提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13]855尽管“人民”“人民性”是一个现代性的总体性概念,而且随着现实的革命和社会形势的变化,毛泽东会不时调整“人民”这一概念的外延,但“劳苦群众”和“大众”的阶级性与倾向性内涵始终贯穿于毛泽东的“人民”观。从早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本到《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思想中的“人民”论述始终隐含着“阶级/阶层”的倾向性。未来的“新国家”和“新文化”也被理解为一个始终与“阶级”“阶级性”相关的历史目标,其想象“视域”始终与“民族性”和“民族国家”的想象“视域”相互交叉而又游移开来。
同时,毛泽东的“人民”论述也始终隐含着“重塑”与“改造”的意图与愿望,即通过文化的“普及”与“提高”,“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起来”[11]707-708。这一方面正如杜赞奇所说的“让人民获得新生”,不但要将处于自然状态的“人民”(people)塑造成“国民”,而且要将其重塑为具有“国族”与“阶级”双重属性的“人民”(the people)。另一方面,这的确也因为毛泽东对“新社会和新国家”的想象与早前一代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想象着实不同。
作为一个直接针对文艺工作及文艺工作者的文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人民”“人民性”的表述同样具有如此复杂的张力和意蕴。在“引言”部分,毛泽东从革命斗争力量和战线的区分,论述了文艺工作中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和“工作对象”问题。在面向不同的“讲话”对象——“文艺工作者”和“人民大众”时,毛泽东的论述也同样表现出一种多重的视角与态度。在谈到文艺工作的“态度问题”时,毛泽东谈到:“至于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无产阶级中还有很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13]849而在谈到关于文艺的“工作对象”问题和“大众化”问题时,叙述者谈到文艺工作者应该具备的态度,那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13]851。
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诸多文本里,关于“人民”“人民性”的论述呈现出这样一种话语交织状态:“阶级(性)”与“民族(性)”的交织、“教育民众”与“打成一片”的交织。这可以表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人民性”论述并不是一种纯然的文化民粹主义,当然也不是纯然的文化民族主义,不是基于“民(族共和)国”的主体想象,而是基于对“人民共和国”及其文化的主体的独特想象。毫无疑问,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论述中,文艺属于“人民”,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也必须符合“人民”喜闻乐见的“中国/民族”趣味与风格。这可以概括其文艺思想中的“人民”观及“人民性”。如前所述,我们亦可以看到,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几乎所有关于“民族/国家”的问题都被理解和处理为一个“阶级”的问题,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启蒙工程也被转述为一场国际国内的、跨民族的“阶级”革命与解放事业。正如杜赞奇所说,“这里,民族观念成为具有超国界诉求的革命语言与民族确定性之间的张力之所。以阶级斗争的革命语言界定民族的另一种手法是把阶级斗争的‘普遍’理论置入民族的语境中。”[5]11
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关于“人民性”的论述与俄罗斯文学中原初的“人民性”概念有多少理论关联和意义的差异,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是怎样支配着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当代文学”的建制及中心话语的生产,并表征着近现代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在建构现代国家的知识讨论和行动实践中,其观念与想象发生了怎样的深层衍变。
三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配合现实的社会政治形势,文艺界相继召开了第一次(1949)、第二次(1953)文代会,并在其间开展了一系列文艺讨论和批判运动。第一次文代会固然意味着文艺界为迎接“人民共和国”的到来而举行的“大会师”,但它更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学共同体”的诞生。不妨说,此时的“人民共和国”还只是一个概念,它是一个未完成的政治实体或国家“意象”,它的历史尚未展开,或者说正在“土地改革”“社会主义革命”“镇反运动”“社会主义改造”“抗美援朝”等现实实践中展开。这个文学的“想象的共同体”与作为有待完成的现实政治实体的“人民共和国”之间,恰恰构成了一种想象关系。
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重申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意义:“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3]70同时,大会最后以决议的形式提出,将“文艺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作为新中国文艺的基本方针,“自此,开导了新中国人民文艺的主潮。”[14]25
同时,因为新中国政府的工作中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周扬曾及时地指出,和以往有多不同,在新的环境下应该多写工业生产和工人阶级的作品。[3]89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人民性”就现实的指涉来说,其中的“工农兵”更多的是指“农”和“兵”,而到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随着现实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对“人民”“人民性”的主体内涵需要调整,需要增补新的成分。因此,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上又指出:“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在逐步地和广泛地进行着社会主义的改造;在人民生活中社会主义因素正日益迅速地增长着并起着决定的作用。……因而进一步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对于我们来说就具有更迫切和更重要的意义了。”[15]新的现实要求文艺家们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去表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现实和现实性。同时,“劳动人民作了国家的主人;随着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他们需要新的精神生活。为满足群众的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创造优秀的、真实的文学艺术作品,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崇高思想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前进,这就是文学艺术工作方面的庄严的任务。”[15]这既是对当代文学创作的要求,也是对新时代新国家主体“人民”的想象和要求,当代文学中的“人民”与“人民性”有了“爱国主义”的品质蕴含和“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
第一次文代会和第二次文代会,可以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建制的完成。这两次会议一方面从指导思想、创作原则与方法、批评规范,以及组织机构、政策制度和作品出版等方面完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建制,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根据现实变化探索和阐述“人民性”的内涵和倾向性,在当代文学这一“文学共同体”中展开对新中国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主体的阐述与建构。
在此期间,除了指导思想、组织结构和相关政策制度等方面的建设,为倡导“为人民服务的文艺”这一宗旨,全国文联于1949年出版了周扬主编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包含延安文艺和解放区文艺时期的一些重要作品,如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李有才板话》及新歌剧《白毛女》等。这一丛书既是对解放区文艺的创作实绩和经验的总结,也是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建制梳理历史资源和奠定基础。另外,为体现新中国贯彻“工农兵”文艺方向取得的成绩,由《文艺报》组织了“文艺建设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文艺建设丛书”,收录了建国初期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一些重要作品,如柳青《铜墙铁壁》、孙犁《风云初记》等。[14]28-29这些丛书的出版对当代文学“人民性”话语和观念的铺展具有“示范”和“典范”的意义,在50年代初的语境中,当然也具有很大程度“规范”的意义。
50年代初,与文学制度建设同步的,是对一些“陈旧的”文学观念、趣味和经验的清理,文艺界先后展开了关于“旧观念旧趣味”“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等问题的争论,以及文艺界的整风学习运动。如对电影《武训传》和肖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清晰地告诉文艺家们,书写“工农兵”既是作家的世界观、文学立场问题,同时也是创作方法和经验的问题,或者说这些本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写什么”和“怎么写”变得同等重要。50年代中期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以及胡风“主观战斗精神”论的批判运动,意在进一步肃清文艺观念和理论上“陈旧的”“错误的”思想观念与立场。这些讨论甚至也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建制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文学“人民性”话语的制度化甚至意识形态化,不仅需要观念上取得共识,也需要剔除那些芜杂的、“不纯粹”的因素,要保证“立场”“经验”和“趣味”上的纯粹的“人民性”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文学“人民性”话语建构中对古典文学遗产的讨论。“人民性”不仅要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文学理论、新/现代文学史上找到精神的谱系,也要在漫长的古代文学中找到历史踪迹和渊源。如果“人民性”本身只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史无前例的“发明”,那又如何对待和处理如此丰厚的古典文学遗产?因此,当代文学对文学“人民性”的讨论需要返身于“历史”之中,有相当一部分讨论便集中在古典文学的“人民性”问题上,如陆侃如《一封公开信:给研究文学史的同志们》、陈涌《对关于学习旧文学的话的意见》、冯至《关于处理中国文学遗产》、谭丕模《掘发古典文学的人民性、斗争性》、黄药眠《论文学的人民性》等论著就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古典文学中“人民性”的存在。[16]饶有兴味的是,50年代初,当代文学“人民性”话语的建构并未像五四时期文学革命论者如陈独秀等人那样,断然地否定和拒绝古典文学,而是迅速地以“人民”观和“人民性”建构了一种线性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但毋宁说“人民性”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建制的一种“认识性装置”,需要具有某种整体性和连续性的“中国文学(史)”来观照现实的“人民共和国”。发掘古典文学中的“人民性”“阶级性”与“斗争性”,是为了赋予中国近现代革命和“人民国家”乃至“民族国家”想象的历史性与历史感。
从1949年到1953年,当代文学的建制意味着文学不再是一种“自由的”艺术创作活动,而是变成了一种国家化、组织化和制度化的文学“生产”。这种组织化的生产机制及生产方式保证了“人民性”作为一种中心话语的权威性和统摄性,同时也在不同的方面限定并调整着它自身的话语方式。正因为有了制度和政策的保障和规约,“人民性”话语具备了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特征。由此,“人民性”话语开始参与并主导当代文学的意识形态生产和知识生产,乃至现实社会政治条件的再生产:为这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建构和生产与之相匹配的主体与主体性。的确,在当代文学的建制中,文学的“人民性”更多地被理解为“工农兵”品格与属性,有一定窄化的取向,具体体现为“人民”的“阶级性”、“阶级意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地获取、增长和形成。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和20世纪50、60年代的当代文学来说,“人民”及“人民性”并不是词义上自明的概念,也不是自然客观的社会存在,需要不断地提炼、重构、重塑与“再生产”,才能让其“获得新生”(杜赞奇),以参与到文学、历史与现实的实践中。不过,这也正说明,“人民共和国”这一政治实体的确溢出了早前一代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经验与想象,它并不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意义上“普遍的”“民族国家”形态,而是20世纪全球各地“民族国家”兴起与解放的“现代性”经验在全球撒播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地方性”经验与形态——“人民国家”。“中国当代文学”及其建制就在这样的历史进程和历史实践中创造并展开了特殊的文学想象与主体想象。
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论述以及50年代初“中国当代文学”的建制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文学的“人民性”话语,并非完全是政党/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它还根植于近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性的总体性叙事的历史理性和逻辑。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想象和书写实践中,对于早前一代启蒙主义知识分子而言,“国民性”表征着这一历史理性;对于左翼文艺、解放区文艺及“中国当代文学”而言,“人民性”表征着这一历史理性的深刻变异。
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与文学想象变革的双重建构中,文学“人民性”话语及其话语实践,表明了一种“另类现代性”——“人民”主体和“人民国家”的可能性。它同样饱含着近现代中国寻求变革、自由与解放的深层焦虑和创伤经验,尽管它不时裹挟着那些丰富的、复杂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以及乌托邦色彩。如果说以现代“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呈现了一种可能性,那么,以“人民/阶级(国家)”拯救历史则呈现了另一种可能性。
[1]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民族意识——“20 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J].读书,1985,(12).
[2]旷新年.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J].文学评论,2003,(1).
[3]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R]//.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北京:新华书店,1950.
[4]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M].甘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5]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M].王宪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6]Levenson,Joseph R..Liang Ch'i- 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
[7]约瑟夫.R.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郑大华,任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8]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车槿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9]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M].梁真译.北京:新文艺出版社,1958.
[10]陈晓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J].文学评论,2005,(2).
[1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M]//.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M]//.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5]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1953年9月24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文艺报,1953,(19).
[16]陈 斐.60年社会批评视野下的古典文学研究[J].学术研究,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