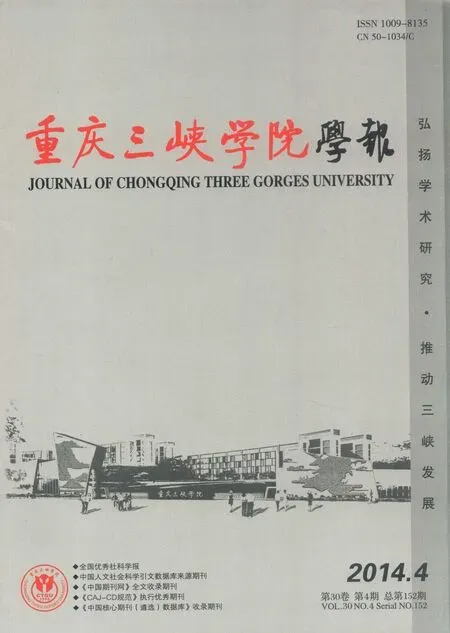论中国戏曲“大团圆”与作品悲剧性之关系
高 晨 田婷婷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 541006)
论中国戏曲“大团圆”与作品悲剧性之关系
高 晨 田婷婷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 541006)
中国古代戏曲独具特色的“大团圆”结局,与作品的悲剧性之间具何种关系,其对作品的悲剧性具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目前在学术界还是悬而未决,并需要深入辨析探讨的。文章对此问题的浅析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大团圆”背后的悲剧性;二是“大团圆”背后的反悲剧性。认为符合艺术逻辑的大团圆结局会增强带有悲剧内容作品的悲剧性,而不顾现实和艺术的客观事实和逻辑的大团圆结局,会损害带有悲剧内容作品的悲剧内涵,甚至完全毁掉作品的艺术价值。
大团圆;悲剧性;反悲剧性
一、引 言
自西方悲剧理论引入中国后,中国古代戏曲小说有无悲剧,就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辨析,直到20世纪上半期前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有许多文人学者都不承认中国古代文学有真正的悲剧,甚至完全否认中国古代文学存在悲剧。这些观点虽然有些偏激,但以当时引进的西方悲剧理论为唯一参照,这么说也确实有一定道理。而从20世纪后半期至今,随着我们自身学术的发展和相关学术理论的自我建构,大多数学者则已经否定了先前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中国的戏曲小说是存在悲剧的,可以说中国不存在西方式的悲剧,但中国至少有东方式的悲剧文学。至此,中国古代戏曲小说是否存在悲剧,就没有了太多的争议。然而,与此相伴随的问题却还没有公论,那就是中国古代戏曲小说,尤其是中国古代戏曲那独具特色的“大团圆”结局,与作品的悲剧性有什么样的关系,对作品的悲剧性有什么样的影响,是排斥,还是共融,还是井水河水两不相犯?对此,学术界还存在着较大争议。
例如美学大师朱光潜认为,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结尾[1]221。还例如学者邱紫华认为,大团圆的结局方式正好表现了中华民族思想意识中的“阿Q”式思维方式存在的普遍性。其本质,就在于它是处理人生悲剧的“精神胜利法”,不能一悲到底,最终走向大团圆是中国悲剧的弱点,它是中国悲剧精神受到腐蚀、淡化后的产物[2]278-289。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很多,他们基本上都认为“大团圆”结局与作品的悲剧性是排斥的,“大团圆”削弱了悲剧意蕴,概括地说是“大团圆”具有反悲剧性的性质。而持另一种观点的学者,例如邵曾祺则认为,“大团圆”或许会相对削弱悲剧的气氛,但却不能改变悲剧的性质。决定一个剧本是否是悲剧,要看整个剧本是否具有悲剧的性质,悲剧的气氛,而不决定于它是否有“大团圆”的欢乐尾巴[3]17-18。宋常立提出中国悲剧的正副结构理论,其结论也与邵曾祺大致相同。概括说就是虽然不认为“大团圆”的结局是悲剧的真正有机部分,但却不会改变一部悲剧作品的悲剧本质。还有许多学者,尤其是当代的一些学者又更进一步,认为“大团圆”结局不但不会削弱改变悲剧作品的本质,作为悲剧艺术的民族特征,还对悲剧作品的悲剧性有积极的提升作用。持此观点的学者有苏国荣、张哲俊、杨建文等。
以上相互分歧的三派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哪一种说法才是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这还是悬而未决、需要深入辨析探讨的。本文虽无力对此问题盖棺论定,给出一个最正确的答案,但还是希冀做再深入一步的探讨,提供可以解决这个争论的可能。“大团圆”结局到底对小说戏曲作品的悲剧性有什么样的影响?在进入探析之前,须界定清楚几个关键词语的定义内涵。第一,“大团圆”,是古典小说戏曲审美命题,是传统戏曲故事结局的普遍特点。一般情况下是剧中主角经过一番周折磨难后,最终是悲者欢,离者合,困者达,贫者富,受屈者伸冤,枉死者复仇[4]65-70。而在很多特殊情况下,“大团圆”之义更在于精神世界的圆满结合。第二,悲剧,在美学领域里可以得到大家公认的内涵有:悲剧亦可称为悲剧性或悲,是从人类在实践过程中的不幸、苦难或生命毁灭的现象里面发现其中蕴含的美,并有对悲剧人物在遭受到不幸或毁灭时所持的态度进行审美的判断和评价[5]1-2。悲剧至少具备三大要素,一是人物遭受巨大的灾难,陷于两难处境,无论选择哪种行动,都会遭到更大的打击甚至毁灭;二是人物陷入悖反定律,目的与行为的结果正好相反相悖,造成巨大的痛苦、灾难以至毁灭;三是作品中的人物必须有毁灭中的抗争和抗争中的毁灭,这种抗争与毁灭对人物来说,不论是否是肉体上的,但必须上升到精神的层面。对文学作品包括戏曲来说,如果具有以上鲜明的特征之一,那就具有悲剧性,可以称之为悲剧作品。
二、“大团圆”结局对带有悲剧内容作品的悲剧性的影响
(一)“大团圆”结局背后的悲剧性
首先以著名的中国爱情悲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例,谈一谈其“团圆”的尾巴对作品悲剧性的影响。《梁祝》的结局是相爱的男女主人公被代表宗法专制的世俗权力拆散,继而含恨而终,被合葬了在一起。“团圆”之处则是二人死后又化为彩蝶双宿双飞。对此,有许多学者指责这个“团圆的尾巴”破坏了整个作品的悲剧性,并与西方经典的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结局作对比,指出前者是一种逃避现实,自我欺瞒等等国民劣根性的体现。其实不然,我认为这顶大帽子真的不应该扣在这部作品的头上。因为这里的“团圆”结局不仅没有削弱破坏作品里诚挚感人催人泪下的悲剧性,反而蕴含并且加深了作品的悲剧性。回到悲剧性的定义里来看,在美学范畴里的悲剧性必须是能够体现人在灾难面前的主体抗争、毁灭、再抗争过程中人性的光辉[6]。如果在永恒且不可抗拒的灾难打击面前,作品里的人物没有展现出永恒且至死不渝的抗争精神,那么读者观众还能看到什么人性的光辉,体会到什么悲剧的美感,还会因何而感动?“化蝶双飞”的结局则正好蕴含着一种肉体被毁灭后,精神上的再抗争的深意,而这种“团圆”也就明显地预示了人类正义精神的圆满和人性光辉的璀璨,也因此加强了作品整体的悲剧性,使读者观众得到心灵的震撼以及悲剧美的陶冶。如果这部作品没有这个“化蝶而飞”的团圆结尾,其悲剧性会减少许多,甚至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就变成了惨剧,而不是悲剧。说到西方经典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其实许多学者的评论都没有深入下去,只看到表面的情节是中国的“梁祝”死后化蝶了,而西方的“罗朱”死得彻底,什么也没化,因此就说西方的是纯正的悲剧,彻底的悲剧,而中国的就是不真的悲剧,不纯的悲剧。如此看法确实有些肤浅。其实这两部爱情悲剧在结尾处是具有深层次的相同之处。这个相同之处便是“团圆”,就是上升到精神层面上的“团圆”,你看《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男女主人公死后没有化蝶双飞,但是结尾处作者点明了他们各自的家族成员,摒弃了两家世代的仇恨,把他们合葬在一起。这不正好预示了因伟大的爱情,仇恨“化蝶而飞”了吗?这种精神的“团圆”正体现了上文所说过的由灾难到抗争到毁灭然后到再抗争这个至死不渝的过程,也就是蕴藏了深刻的悲剧性,且加强了整部作品的悲剧蕴意。所以从这点上来看,此种“团圆“结局本身蕴含悲剧性,同时也就加强了整部作品的悲剧性。还例如关汉卿的经典剧作《窦娥冤》,其结局简单说是沉冤得到昭雪的“团圆”。不过从深层次来说则是窦娥从生前到死后一直不曾停止的震天动地的抗争所得到的悲剧性的“团圆”,在毁灭中抗争,在抗争中毁灭,这个“团圆”正体现了这一点,所以具有很强的悲剧性。再例如享誉中外的《赵氏孤儿》的结局,还是一个大仇得报的“团圆”,这也受到了很多学者的指责,认为破坏了悲剧性。其实同上文所述不尽相同,这个结局对于程婴、公孙杵臼等人,是一种抗争复仇,为正义而战精神的延展,对赵氏孤儿而言,又是一种身处于义父之恩与家族血仇之间两难处境的主动抗争。这同样是一种深层次的悲剧性。
总之,在中国经典的悲剧戏曲中,虽然都被学者指出过有“团圆的尾巴”,以至削弱影响了整部作品的悲剧性。这其实是不正确的,在大部分经典悲剧曲目里,都有一种高超的“团圆”结局,这种结局通过分析来看,与西方经典悲剧的结局是具有深层次的相似之处,其本身蕴含着悲剧性,是整部作品的有机整体,并且深深地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和悲剧性。
(二)大团圆结局背后的反悲剧性
上文谈到“大团圆”结局背后的悲剧性,这里又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小说戏曲中,存在着大量的低级的团圆结局,破坏了戏剧的悲剧性,以致成为中国小说戏曲的污点。什么是低级的“团圆”呢?什么又是高级的“团圆”呢?其实分区高低之别,大体也就是两点:其一,“大团圆”结局是否符合当时社会的面貌情状以及市井人情;其二,“大团圆”结局是否符合人物情节发展的艺术逻辑,是否是整个作品艺术构思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满足这两点的,当然是高级的,而一点都不符合的,当然是低级中的低级。若以这种低级的团圆收场,说其破坏作品的悲剧性也都是一种委婉的批评[7]。
例如中国大部分爱情戏曲中,最常见的模式之一是“状元娶妻”,也就是“公子逃难,小姐养汉;状元一点,百事消散”的故事结构。甚至包括《西厢记》《牡丹亭》《玉簪记》等一批名剧都不能幸免地采用了这个模式及烂透底的结局。其实若没有这样的结局,上述剧目都会体现出很强的悲剧性。只是采用了这个结局,虽然从外表上看人物似欢喜美满大团圆,但在精神层面上,这里面又出现了极大的断裂,悲剧性的抗争意蕴被彻底消解,也就让人感受不到多少悲剧性。还例如这个剧种的常见模式二“状元负心”,也就是“士子做官,高枝另攀;前妻来认,马踹刀砍,高官主婚,破镜重圆”的故事结构,例如《赵贞女蔡二郎》《张协状元》《琵琶记》等。其结局与模式一的相比,低级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琵琶记》还能保留强烈的悲剧性以外,其他作品的悲剧性甚至艺术价值都因这种背离人情,消解冲突的大团圆结局而丧失大半。这个模式的结局本质也同模式一的一样,虽表面看人人都恭喜发财阖家团圆了,但在毁灭中抗争,在抗争中毁灭的悲剧精神则被中断了。
还例如大量的续编戏曲,对一些经典悲剧的结局进行改编。像《后石头记》《红楼圆梦》《南桃花扇》《烂柯山》《青衫泪》《说岳传》……等等这些续编作品。对这些作品,早在产生之时,就已经有清醒的人在批判了(卓人月《<新西厢>序》和沈成垣《<桃花扇>序跋》[8]331-333),即使到现在对它的口诛笔伐都不绝于耳。这些续编戏曲都把人物死的改成活的,分的改成合的,不完美的都改成最最团圆的,彻底毁掉了作品本身具有的悲剧性,使自身完全失去了艺术的真实和价值,而换来的仅仅是那点虚妄的幻觉及自欺欺人的精神鸦片。这不啻为一场中国戏曲史的劫难,在带走严肃认真令人深省的悲剧的同时,又戏剧性地把这个“大悲剧”送给了我们现实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很多学者批判“大团圆”以及其中所反映的国民劣根性,着眼点其实就是在这里。我认为这些批判的声音直到现在都具有学术和现实的价值。
总之,低级甚至是烂透底的“大团圆”结局,虽然表面上让人物团团圆圆,事情圆圆满满,使观众嘻嘻哈哈,乐乐呵呵。但却根本上中断了毁灭中抗争,抗争中毁灭的悲剧精神,在深层次的精神领域,悲剧性没有得到圆满性的展现。所以这样的“大团圆”确实破坏了甚至完全毁掉了作品的悲剧性,而由于历史上有大量的续编团圆作品的出现,使这一情况变得更为恶劣,所以也就更应该受到有识之士的批判。
三、小 结
从以上中国戏曲小说“大团圆”结局对作品悲剧性影响的分析中,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如下结论:1.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中的经典悲剧作品里,有许多“大团圆”结局,由于这种团圆结局设置的手法高超,符合悲剧性的发展,所以本身具有悲剧性,且又增强了整个作品本身的悲剧性,是值得褒奖和传承的。2.中国古代小说戏曲里也有大量粗制滥造的续篇作品,这些作品的作者为了迎合国人肤浅虚幻的“大团圆”梦,而不顾现实和艺术的客观事实和逻辑,编造出烂透底的“大团圆”结局,从而损害了原作的悲剧性,甚至完全毁掉了作品的艺术价值,这点是应该继续批判和纠正的。3.中国古代的经典悲剧与西方相比相对较少,但整体质量却毫不逊色。可是由于大量粗制滥造的模式作品和续篇作品的出现,导致了中国戏曲史上留下了一大片污点。4.“大团圆”作为一种戏曲小说等叙事文学作品的结局构成模式,本身无可厚非,且它还是一种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上升到精神层面的“大团圆”往往是伟大悲剧作品必不可少的元素。5.由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存在大量粗制滥造虚幻缥缈不合逻辑的“大团圆”结局,所以应从总体上批判这些低级的“团圆”,并且继承发展经典悲剧作品中如何运用设置“大团圆”的艺术手法和技巧,这才是提高我国戏曲小说创作水平的一条重要途径。
[1]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古典悲剧喜剧论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4]谢柏梁.中华戏曲文化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郭玉生.悲剧美学:历史考察与当代阐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6]宋康,颜婷婷.清代宫廷戏曲中的承应制度初探[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4(1):81-86.
[7]易勤华,邓莹辉.冲突的诗意化:古典戏曲的人物关系[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
[8]熊元义.中国悲剧引论[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张新玲)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g Happy Reunion” of Chinese Ancient Opera and the Tragic Nature of Literary Works
GAO Chen TIAN Tingt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Guangxi,CN,541006)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ig Happy Reunion” of Chinese ancient opera and tragic of literary works? What influ ence t he form er can cast on th e latter? Th ese questions are still academically controversial yet to be discussed. The articl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Big Happy Reunion”strengthens t he tr agic conno tation; th e secon d p art is "Big Happ y Reunion" weakens and damages t ragic implic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m from two aspects: there is a tragic nature behind the “Big Happy Reunion”of Chinese ancient opera; and there is an anti-tragic nature behind the “Big Happy Reunion” of Chinese ancient opera. Those “Big Happy Reunions” complying with the artistic logics will increase the tragic nature of some tragic works while those “Big Happy Reunions” that go against the objective reality and logics will hurt the tragic connotations, even can utterly destroy the artistry of literary works.
“Big Happy Reunion”; tragic connotation; anti-Tragic
J05
A
1009-8135(2014)04-0113-04
2014-04-24
高 晨(1989-),女,辽宁营口人,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