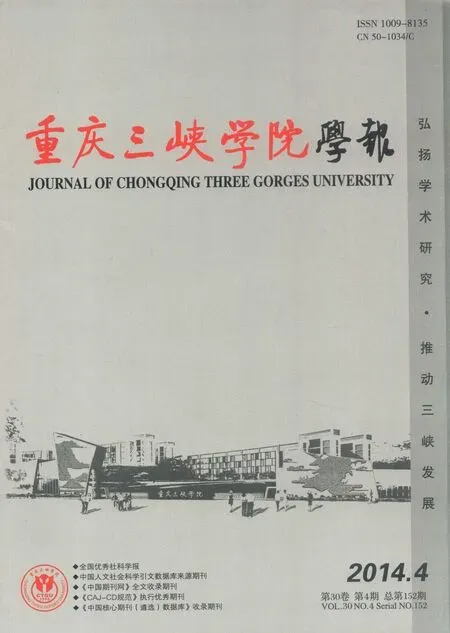论周作人序跋文的文体创造
——以《苦雨斋序跋文》为例
刘抒薇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论周作人序跋文的文体创造
——以《苦雨斋序跋文》为例
刘抒薇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序跋文是周作人散文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散文文体的一个分支,从侧面丰富、深化了对周氏散文文体创造力与风格特征的认知,是解读周作人的一个重要向度。表述方式、文体风格、文学语言三位一体,相生相成,共同呈现了周作人序跋文体独特的审美创造,使其真正成为中国现代散文的亚类型体式,具备鲜明的文体特征和审美价值。
周作人;序跋文;文体创造
周作人重视序跋创作,一生所作序跋共计30万字左右。1933年,他从所著文集、集外文、未刊稿的所有序跋类文章中筛选出五十三篇,自编为《苦雨斋序跋文》,这是他对自身序跋创作一次慎重的审视,更具代表性和研究价值。序跋文作为散文文体的一个分支,从侧面体现了周作人独特的文体创造与美学追求。纵观现有的周作人研究成果,以其序跋为研究对象的专著空缺,相关论文仅有4篇,分别为:《周作人序跋中的散文观管窥》(2008年)、《周作人序跋艺术管窥》(2011年)、《周作人序跋研究》(2012年)、《周作人序跋的写作艺术》(2013年),且大多侧重于序跋对其人格思想、散文观念的说明,甚少从文体角度予以切入,序跋的独立品格和文体价值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因而,从文体角度切入周作人的序跋文研究是必要的。
一、多元糅合的表述方式
周作人将《苦雨斋序跋文》自分为自序和他序两个部分。第一部分36篇皆是自作题记,即为自己作序跋,第二部分17篇,皆为他人所作的序跋,这是从序跋服务的对象角度作的初步划分。然而从文体角度体察,笔者认为可以依据表述方式的不同,将其进一步区分为记叙序跋、议论序跋和抒情序跋。
序跋文细分为“序”和“跋”两个部分,都是用于说明出版意旨、编次体例、写作经过或评介文章内容的一种文体。鉴于序跋固有的说明介绍作用,周作人的序跋中记叙表述的成分颇浓。他或以叙事的形式交代写作缘由,又或以叙事的口吻讲解命题原因,此外还在序跋中插叙自己的人生经历。《苦茶随笔·小引》大篇幅插入其庚子之次年于南京充当水兵、随后公派前往日本改习建筑并从事外文翻译的事迹;《发须爪·序》在评价绍原礼教的过程中穿插回忆与绍原君在北京大学的交往趣事。不论对人生轨迹的总结,抑或介绍文人间的友谊,周作人都能在序跋文中娴熟使用顺叙、倒叙、插叙等技巧,以人、物、事件为中心的叙述方式使其序跋文脱离了说明性文字常有的晦涩,更显温润、亲切。同时,他以自我经历为切入点,以自我的情绪为旨归,看似散漫的平铺直叙中带有纪实性和记录性特征。
新文学运动以来,序跋不仅具有对正文的说明、补充作用,同时更强调它是表达作者思想主张和文学见解的载体,优秀的序跋文也因渗透着作者的评判标准而具备高度的思想价值、史传价值、文体价值、审美价值和学术价值。周作人重视序跋的批评作用,认为:“做序是批评的工作,他须得切要地抓住这书和人的特点,在不过分的夸扬里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才算是成功。”[1]122那么如何发挥这种批评作用呢?笔者认为,周作人主要是通过议论的表述方式来实现序跋的批评价值。与锋芒毕露的传统议论类散文不同,他的议论序跋是以柔取胜,既没有固定的样式和写法,也没有高深的理论和大声的喧哗,却也不是任意为之,而是以温婉明净的文字深入浅出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例如在《儿童剧·序一》中,周作人开篇即肯定了“我近来很感到儿童剧的必要”,然后大篇幅引用作家阿尔考忒排演的童话故事,接着再过渡到自己,以温情的笔调回忆起童年曾将现实中略有异样的人戏剧化,“在有两颗桂花树的院子里扮演起日常的童话剧”,认为“演着这剧的时候实在是得到充实的生活的少数瞬间之一”[1]74。周作人通过自己的经验证明儿童剧的必要,以故事的形式取代枯燥的说理,最终达到论证的目的。“议论人家的事情很不容易,但假如这是较为熟识的人,那么这事更不容易,有如议论自己的事情一样,不知怎么说才得要领。”[1]103为此,他的应对方式就是“杂说”,即闲散地议论。虽然没有丝丝入扣的论证过程,也没有模式化的论证方法,但是却能够在漫谈的过程中阐发自己的观点,形成了周氏序跋独特的浪漫主义的议论风格。
除了运用记叙和议论的表述方式外,周作人之于序跋的文体贡献还体现在对抒情性的追求,他在创作中往往夹带着个人体验,将主体的喜怒哀乐投射于序跋中形成一种带有自我倾向性的情感。一方面他渴望宣泄,但另一方面他的抒情表述又介于言与不言之间,形成一种独特的抒情话语,笔者将其称为“隐形的表达”。以《茶话·小引》为例,通篇83字,找不到直接抒情的痕迹,但是从“事实上我绝少这样谈话的时候,而且也不知茶味,——我只吃冷茶,如鱼之吸水。”[1]33的表述中,可以隐约地体会到作者心境的清冷与苦涩。周作人的抒情方式不是一泻千里,更像涓涓细流,曲折低回,他将情感浓缩于一个“冷”字,以高超的炼字能力将千言万语化为一腔无言的沉默,在沉默中品味自己的内心,形成了无声胜有声的抒情效果。周作人之所以重视序跋的抒情效果,与他的文艺观有很大关系。“五四”落潮后,现实的忧患使周作人缺乏归宿感,他决心经营自己的园地,提出“表现自己”的文艺观,主张“文艺以自己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2]走上了返归自我的个人主义道路。因此他不满足于传统序跋的记叙、议论作用,而选择抒情的表述方式来达到“表现自己”的目的。好的抒情是个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也是情感释放与审美创造的辩证统一,对于抒情性的追求使周作人序跋文往往带有“情志体”的特征,抒自我之情,载自我之道,自然随意,娓娓道来。
周作人的序跋文充分启用了散文丰富多样的表述方式,不仅继承了传统序跋记叙、议论的特点,而且凸显了序跋的抒情作用。他自言:“我相信批评是主观的欣赏不是客观的检察,是抒情的论文不是盛气的指谪”[1]20,因此他的序跋往往夹叙夹议,注重主体的情感体验,在鞭辟入里的议论中又蕴含着行云流水般的抒情,呈现出多元糅合的特征。那么周作人是如何实现三者的糅合呢?笔者认为主要是通过以下两个渠道。
第一,闲话语体的使用。周作人的序跋文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闲谈,他在《自己的园地·旧序》中说:“我平常喜欢寻求友人谈话,现在也就寻求理想的友人,请他们听我的无聊赖的闲谈。”[1]22强调作者与读者的互动,这促使他有意地以记叙和抒情的方式冲淡单纯议论所造成的枯燥的阅读感受。一方面自由地论述观点,但又不追求议论的逻辑严谨性,另一方面又在论述的过程中穿插记叙,抒发自我的情感,形成一种随意的谈话风格,以此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实现“自由”与“节制”的统一。糅合议论、记叙、抒情于一体的表述方式,使其序跋文摆脱了传统序跋形式上的桎梏,更显率性自然。
第二,为文无法的行文方式。周作人认为,“文章切题为妙,而能不切题则更妙。”[1]119因此他的序跋创作脱离既定的行文规范,呈现出散乱的态势。以《点滴·序》为例,周作人开篇提出论点——翻译要采用“直译的文体”[1]14,随后笔锋一转,娓娓讲述自己和林琴南、章太炎先生交往的故事,最后转入对人道主义精神的探讨,抒发了对于文学的期望与寄托,将不切题的宗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同一篇序跋文中周作人的表述方式不断交织变化,他所追求的不是纯理性的议论,而是叙事化的论述,或抒情化的评论,让读者在听故事的同时自发地感受观点的正确性,使叙事更好地服务于议论的效果。传统序跋文的创作者往往是为了作序而作序,因此他们讲求严谨的议论方式,主体的情感是隐蔽的。然而周作人将序跋文看作是“表现自己”的载体,在论述过程中始终穿插着个人的情感诉求,形成了具有主体情感倾向性的议论表述,实现了“主观的欣赏”和“抒情的论文”的追求。
二、新颖独特的文体风格
序跋附于正文前后,起着解释、说明、补充作用,具有附属性。同时,它表写了作者对于序跋对象的感悟、认知与评判,又具有独立性。附属性与独立性相互作用,一方面限定了作家要按照文体规范进行创作,另一方面又驱使作家尝试突破规范桎梏,创造新颖的艺术风格。作为一个积极的文体实践家,周作人的序跋文在传统与新变的二维互制中,营造了自身的文体风格。
(一)真实自然的言说
周作人的序跋文体现为一种真实自然的言说。首先,从描写内容上看,既有生活层面上的饮茶、读书、游戏,也有立足于文化层面,抒发对神话、翻译、民俗学的见解。将高深的文学问题生活化,以真实的生活情景引起读者共鸣,使其序跋文不再是居高临下的宣讲,更显自然与亲切。其次,从表达方式上看,他的序跋文大多是一种“闲话”,体现出对话的特征。他不惮将自己不周密的言论推向人前,因为“我们的思想如何浅陋,文章如何平凡,但自己觉得要说时便可以大胆的说出来,因为只是自己的表现,所以凡庸的文章正是凡庸的人的真表现,比讲高雅而虚伪的话要诚实多了。”[1]21他希求与知心的读者分享喜悦愁苦,因此他的态度总是亲切、自然的。“我只是喜欢讲话,与喜欢乱谈文艺相同,对于许多不相干的事情,随便的批评或注释几句,结果便是这一大堆的稿子”[1]46虽然这不乏周作人自谦的成分,然而笔者认为也恰恰体现了周氏序跋真实自然的文体旨归和言说诉求。
(二)苦涩清冷的风味
张中行曾以“寓繁于简、寓浓于淡、寓严谨于松散、寓有法于无法”[3]总结周氏散文平淡闲散的特点。就连周作人自己也坦言,“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1]22。然而笔者认为,周作人的序跋文在本质上却是极不平淡的,反而体现出苦涩与清冷的风味。他在《自己的园地·旧序》中说:“反正寂寞之上没有更上的寂寞了”,抒发了知音难觅的寂寞之感;在《谈龙谈虎集·序》中又说:“我这些小文,大抵有点得罪人得罪社会,觉得好像是踩了老虎尾巴,私心不免惴惴,大有变色之虑。”[1]49,体现了缺失安全感所造成的焦灼;在《艺术与生活·序一》直言:“我如有一点对于人生之爱好,那即是它的永远的流转;得到一个人官能迟钝,希望‘打住’的时候,大悲的‘死’就来救他脱离此苦,这又是我所有对于死的一点好感。”[1]44抒发了豁达的人生观,也是饱受生活忧患之后的彻悟。序跋是一种纪实性的文体,它为作家提供了自我审视的平台,与散文相比,它进一步排除了文学的虚构性,更贴近创作主体内心真实的情感。尽管周作人以闲谈的方式,纡徐的文风极力淡化自己的情感,然而人生的局限,现实的忧患,知音难觅的痛苦迫使他的内心无法真正的平静,对自我的怀疑投射于创作,形成了阴郁的气氛,使其序跋文自然流露出苦涩之味。
以苦涩论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并非新见,黄开发也曾评价他“是以‘苦味’自重的”[4]。然而除苦涩之外,周氏序跋的独特之处还在于——“清冷”,《雨天的书·序一》最能体现这一点。周作人首先从外部环境下笔,冬日细雨营造了缠绵阴沉的背景,带来嵌入肌肤的点点寒意。接着又言“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无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由外在的“冷”过渡到心情上的“冷”,没有痛苦的呻吟,也没有激烈的愤慨,化浓烈为舒缓, 寓尖锐于婉曲,形成了清冷凄婉,欲言又止的抒情方式,也映衬出中国诗教传统 “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影子。周作人的序跋文以闲适平淡的叙述为表象,实则蕴含了不平淡的情感,在平淡与不平淡的交织作用下,更加凸显了苦涩、清冷的文体风格。
(三)知性的审美趣致
周作人的序跋文广征博引,知性的审美效果十分突出。他在序跋文中既征引外国译著,也博采中国传统诗词典故,似信手拈来又恰到好处。周作人是自觉的文化传道者,他的部分序跋,如《红星佚史·序》、《黄蔷薇·序》、《苦茶庵笑话选·序》等大量引用外国译著内容,在实现说理目的同时也使其作品成为中外文化传播的媒介。如果说对外国典故的引用,多少带有文化传道者普及知识的愿望,那么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引用则更加体现了博学多识,信达雅致的本色。周作人在为废名所著的《莫须有先生传·序》中大篇幅引用庄子对于“风”的言说,随后澄明庄生此言说尽了好文章的理想——“能做好文章的人他也爱惜所有的意思,文字,声音,典故,他不肯草率地使用他们,他随时随处加以爱抚,……好像是风遇见能叫号的窍穴要使他叫号几声,可是他仍然若无其事地流过去吹过去,继续他向着海以及空气稀薄处去的行程。”[1]111-112周作人通过征引传统文学典故来代替主观的说教,将思考的空间让渡给读者,淡化了批评议论的效果,无形之中给人一种气度雍容,博学多识的长者风范,也造就了周氏序跋文气象开阔、渊博淡雅的风格。
周氏序跋文知性的审美风格有赖于他对文本引用的宽容态度,他说“文字本是由我经手,意思则是我所欢喜的,要想而得不到,欲说而说不出的东西,固然并不想霸占,觉得未使不可借用。正如大家引用所佩服的古人成句一样,我便来整章整节地引用罢了。”[1]59此外,他对知识也是敬重的,认为好的散文应“以科学知识为本”、“有知识和趣味的两重的统制”,因此,周作人的序跋文博采众长,营造出知性的审美效果,不仅是“杂学”的结果,也是思想的宽容与理性的通达。
三、文学语言的审美创造
文学语言是表述方式和文体风格的物质载体,最能体现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和审美基调,是探究周作人序跋文体创造的基石和中心环节。周作人序跋文具有鲜明的语言特色,既有浅俗易懂的白话文,又有典雅别致的文言文乃至骈文,从中既可窥见明人小品的风格,又兼具西方随笔的特色和日本俳句的风味。
(一)质朴真切
为了达到“表现自己”的目的,周作人的序跋文摒弃了传统序跋中的官腔套语和陈词滥调,体现了质朴真切的语言风格。
首先,在遣词造句方面,不使用艰深晦涩的难字,在句式上也以舒缓的句子偏多。以《绿洲·小引》为例,“偶尔也有一两小时可以闲散的看书,而且所看的书里也偶然有一两种觉得颇惬心目,仿佛在沙漠中见到了绿洲一般,疲倦的生命又恢复了一点活气,引起执笔的兴趣,随意写几句,结果便是这几篇零碎的闲笔。”[1]17此类句子是作者情感的剖白,不在字面上故作玄虚,同时一逗到底,结构松散,用舒缓的笔调阐释了自作序跋的特殊心境,流露出慵懒、随性、本真的气息。其次,与散文纯个人化的叙述方式不同,周作人的序跋文十分强调读者的感受,他往往以直截了当的发问来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在《草木虫鱼·小引》中他说:“现在姑且择定草木虫鱼,为什么呢?第一,这是我所喜欢,第二,他们也是生物,与我们很有关系,但又到底是异类,由得我们说话。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罢。”[1]65周作人称呼“我们”,仿佛闲话家常一般,邀请读者共同参与到序跋创作的过程之中,在书面表达的过程中甚至插入口语,使语言更显直白质朴。
作为一个浙东人,江南水乡清淡简朴的地方气息在幼时早已植入他的性灵,成年以后,周作人受日本的影响颇深,欣赏日本人“在生活上的爱好天然与崇尚简素”[5],此二者共同促成了他崇尚自然的审美理想。将审美理想融入序跋创作,导致周氏序跋以“简单”为语言审美的旨归。别林斯基曾说“文体里表现着整个人”[6],作家的思想气质转化为文体特色。“措辞质朴,善能达意,随便说来仿佛满不在乎,却很深切地显出爱惜惆怅之情”[7],正是周作人序跋文质朴真切的言辞之美。
(二)含蓄幽默
周作人深谙文体特质,将语言置于文体创造的重要层面。然而,他对于语言又持矛盾态度:希望把自己的话说出来,又怀疑语言是否可以完全表写情意,担心自己的文字被世人所曲解。因此他重视含蓄的言说,使其序跋文在看似随性而为的外表下形成了“犹豫的表达”[8]。那么周作人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语言含蓄的意境呢?笔者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幽默。
郁达夫曾对比鲁迅和周作人的幽默,以为前者“辛辣干脆,全近讽刺”,后者“湛然和蔼,出诸反语”[9]。首先,周作人在序跋文中好用反语。他说自己为小朋友抄录诗文的行为,“在高雅的大人先生们看来,当然是‘土饭尘羹’,万不及圣经贤传之高深,四六八股之美妙。”正话反说,似贬实褒的语言表达强化了讽刺、幽默的效果。其次,周作人擅用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将部分中国人比作“疯狂和痴呆症患者,倘若有牢骚只好安放在肚子里,牢骚发作时,就用上好的黄酒将他浇下去。”[1]40将中国社会的内忧外患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营造了轻松与沉重、淡然与庄严相反相成的氛围,使读者目睹怪诞言行而放声大笑之后又陷入沉思,这就是幽默所带来的深层次的效果。此外,周作人还善于自嘲。“至于我写这篇的原因,十分之一由于想供传说学的资料,十分之二由于觉得很是好玩,十分之三由于想不再讲俏皮话,以免找怨,十分之四——最重要的是怕得罪了人,法庭追问时,被报馆送了出去,虽然是用着别号或匿名。因此我就找到这个讲不负责任的笑话办法,倒是十分合适的一种办法。”[1]27看似周密严谨的列数方式和似是而非的内容形成鲜明反差,这既是他的自嘲,也是自谦,更是对文化专制的反讽,在含蓄的语言表达下形成了强大的感知效果。
(三)雅俗共赏
周作人自称心里住着两个鬼,一个是绅士鬼,一个是流氓鬼——“我对于两者都有点舍不得,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10]这也表征在语言运用方面,即古代文人雅言与民间俗语并存,形成了雅俗共赏的审美效果。试看《雨天的书·序二》中的一段文字:“我从小知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古训,后来又想混迹于绅士淑女之林,更努力学为周慎,无如旧性难移,燕尾之服终不能掩羊脚,检阅旧作,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呜呼,我其终为‘师爷派’矣乎?”[1]25
这段话在选词和句式上将文言笔法引入现代序跋写作,相比于同时期巴金、郁达夫“纯白话”的序跋文创作,更加凸显典雅气韵。然而,虽然周作人提倡采纳古文以补白话之不足,但作为一个深受五四启蒙思想熏陶的文学家,其序跋文的语言亦不乏浅近俗白的一面。他善于从民间文学中汲取养分,将地方方言和俗语融入序跋创作中。如“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火筒里煨鳗”、“旧性不改,依旧落海”等,充分发挥民间智慧,在轻松诙谐的气氛中闪现理性的光辉。至此,语言上的雅和俗并非完全对立,民间化的俗白与文人的腴润交织出雅俗共赏的审美效果,这是周氏序跋与同时期其他作家序跋作品最大的区别。
周作人是一个具有高度文体自觉意识的作家。在序跋文创作中,他灵活运用记叙、抒情、议论等手法,形成多元糅合的表述方式,突破传统序跋文对作品的依附性,拓展了序跋的描写领域,深化了序跋的精神内涵;在文体风格上,他融入个人的精神特质,使序跋体现为一种真实自然的言说,在看似平和冲淡的外表下流露苦涩清冷之气,蕴含知性理趣之光;在语言方面,既吸收中国古文雅致的风韵[11],又兼纳民间俗语的生气,使语言最大限度地发挥审美功效,呈现出质朴真切,含蓄幽默,雅俗共赏的风格表征。
[1]周作人.苦雨斋序跋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2]周作人.自己的园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3]张中行.负暄续话[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
[4]黄开发.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5]周作人.知堂回想录[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6]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M].梁真,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
[7]周作人.苦竹杂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8]魏继洲.周作人散文文体特色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7(1):36.
[9]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10]周作人.谈虎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11]王猛.试论明代小说序跋的文体特征与文学价值[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
(责任编辑:郑宗荣)
On the Stylistic Creation in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by Zhou Zuore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Ku Yu Zhai Xu Ba Wen
LIU Shuwe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c onstitute an integral part of Zhou Zuoren’s prose writing, and it partly enriches and deepens people’s cognition of the creative power and characteristics of Zhou’s prose.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to read Zhou Zuoren. Th e exp ression, style and literary langu age t ogether reflect th e aesthetic creation of Zhou’s and make it a sub-type of modern Chinese prose style, which is of distinctive stylistic features and aesthetic value.
Zhou Zuoren;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stylistic creation
I206.6
A
1009-8135(2014)04-0088-05
2014-04-23
刘抒薇(1990-),女,福建福州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