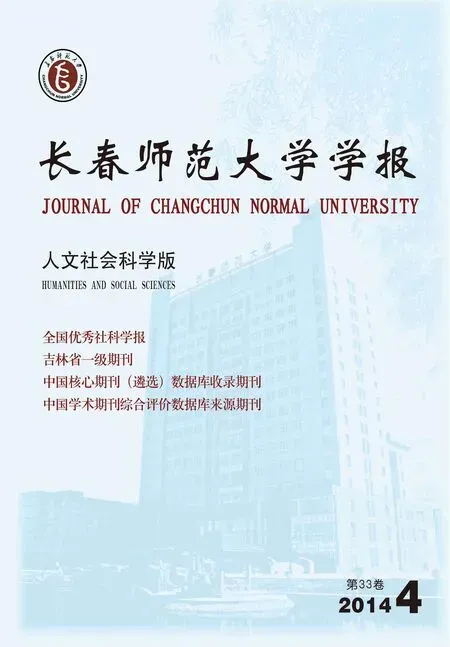浅析《静静的顿河》中的生态意识
张丽艳
(忻州师范学院 外语系,山西 忻州 034000)
浅析《静静的顿河》中的生态意识
张丽艳
(忻州师范学院 外语系,山西 忻州 034000)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以顿河流域哥萨克人的生活为主要题材,对两岸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同时,源于作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作品中充满了对于土地的眷恋和对于自然的敬畏。作品摒弃了人类中心主义,在自然书写中寻找着那已经失去的土地与心灵的家园。
肖洛霍夫;生态意识;自然书写;家园
肖洛霍夫的著作《静静的顿河》以其史诗般的风格,记述了20世纪早期顿河两岸哥萨克人的生活。就题材而言,《静静的顿河》算不得一部生态文学的作品,但全书中充满了对顿河两岸自然与人文景观的描述,更为重要的是文本中对“自然”那独特的再现方式,迫使人们对“人与自然”这个永恒的母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多重的阐释。
一、“土地之子”与肖洛霍夫的生态思想
肖洛霍夫并没有关于生态思想的专门著述,但是孕育他的这片土地却赋予了他对于生态与自然的深刻认识。肖洛霍夫出生在维约申斯克镇,他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这里位于顿河的北岸,被称为哥萨克之乡。
早自公元14世纪,由于不堪忍受农奴主的压榨以及沙皇政权的迫害,众多农奴、城市贫民以及农民纷纷出逃,聚集在俄罗斯南部的辽阔草原,他们就是哥萨克的起源。他们最初以渔猎为生,到17世纪逐步演变为农耕,公社式的农耕生活使得他们对于土地有着特殊的眷恋。
在肖洛霍夫生活的年代,连年的征战使得哥萨克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土地、投身战斗,如同《静静的顿河》中所描述的那样:在战争的岁月中,那些背井离乡投身战斗的哥萨克老兵眼中含着热泪,因为耕种的日子到了,他们清晰地听到大地的召唤,但这个时候他们却要离开这片土地,因为他们将要奔赴战场。当走过耕地的时候,每一个哥萨克都会抓起一把散发着春天气息的泥土,随之发出一声叹息。这种对于土地的眷恋已经超出了生计的范围,而成为一种精神上的依赖。
对自然的敬畏是肖洛霍夫生态观的基石。在自然面前,肖洛霍夫表现出了十足的谦卑。在他的作品中,时刻都可感受到那种来自人类意志之外的强大力量。正如《静静的顿河》中所描述的那样,“每年顿河都要涨水,草原会鲜花盛开,月圆月缺,冬去春来,自然贯穿其中,庄严而沉默”。逝者如斯,让人感到宇宙苍凉,万物皆为过客,唯有自然永恒。
二、走出人类中心主义——《静静的顿河》中的自然书写
用“自然书写”来界定具有生态思想的自然描写作品已经被普遍接纳。判断是否属于自然书写范畴的依据主要在于作者写作的视角。同样描写自然,同样抒发对于自然之美的热爱,一种将人的意志凌驾于自然之上,将自然当作人类征服的客体;另一种则将人视为自然的一部分,以一种整体观的思路去除傲慢的中心化,强调整体与整体内部的联系。显然后者属于自然书写的范畴。
在《静静的顿河》这部作品中,作者传达着强烈的去中心化的思想。我们能够看到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在战乱、革命、杀戮中上演的人间的悲剧世界,一个是生生不息、默默无语的大自然。前一个世界构成了故事的主体,后一个世界则使这部作品具备了普世的价值。当人类的世界被仇杀、血腥笼罩的时候,自然时刻都在召唤着这些迷途者的皈依。作品中,血腥暴力的场面与宁静美好的自然时常前后交错出现,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描写似乎是一种来自大地的召唤,唤醒那些沉醉于血腥中的人们的心灵。例如:葛利高里的妹妹杜妮亚希珈向家里人描述安尼库希加死亡的惨状:他的脑袋几乎没有了,只剩下了“稀烂的一滩”。这使得父亲潘苔莱难以承受,感到压抑窒息的他走进树林,这里火焰般的野蔷薇、红色的浆果和金黄的落叶让老人似乎忘记了那些残忍的现实,他甚至不合时宜地下河捉鱼。此时,人类似乎是一个受伤的孩子,在母亲的怀抱中安然沉睡了,而那些残忍的行为似乎显得那样的任性与乖戾。
同时,作品表现出了对那些践踏自然、践踏生命者的愤怒。那些自视伟大的征服者们在此显得无比可憎和可悲。一个红军战士来到李斯特尼次基家的庄园,要掠走一匹正在哺乳的小马,看马的萨希加恳求他们手下留情,但这个傲慢的战士开枪打死了小马,又一枪打死了萨希加。在这段故事之后,作者的一段描述颇能表现出他的愤怒。“……云雀在流动的蜃气当中歌唱,远处的干涸的山沟里,有一挺机枪顽强地、凶狠地和沙哑地哒哒响着,表示着人类确实是万物的灵长”。这种反讽是对那些缺乏敬畏感的无知之人的愤怒。
作品中的自然是一个充满了灵性的世界。为找回生命的意义,作品将目光投向自然。自然本身似乎在诉说着生命的价值,诠释着生命的伟大。在这里一草一木似乎都饱含了生命的意蕴,例如“忧郁地低着头”的苦艾草;有着“孩子般清澈眼睛”的紫罗兰;“坚忍不拔,冷若冰霜”的陈葛,他们让我们感到自然在与人类共同呼吸。奔流的顿河“重现了人类历史的流动”,这汹涌的波涛有如人类的历史,有湍流、有漩涡、有浅滩,但最终都会静静地流向大海。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生命与自然的深切关怀,使《静静的顿河》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用谦卑的笔触写下了自然的诗篇。
三、家园的失去——自然书写背后的深层意蕴
按照阶级分析的观点,哥萨克对新政权的抗拒是由其固有的阶级性质决定的。然而,深层的原因也许并非如此。作品中,几百年来形成的哥萨克与土地的联系被割裂了,革命摧毁了这种绵延下来的乡土文明,将他们带进了一个冰冷的工业时代,使他们产生了一种痛失家园的无根的漂泊感。
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集体意向,家园具有双重的意义:一种是抽象意义上的心灵的家园,一种是具体的地理意义上的家园。前者涉及正义、良知、关爱等这些神圣的母题,而后者则是指大自然。
在作品中,传统的农耕生活方式被打破了,哥萨克的家园变得陌生、满目疮痍。“被炮弹炸得坑坑洼洼的公路”、“被枪弹扫射过的艾篙”、“烧焦的木桩”、“弯曲的战壕”构成了一副令人黯然神伤的悲惨画面。随着自然家园的破坏,人的精神家园也同时出现危机,正如书中感叹的那样:“魔鬼般的生活,可怕的年月!谁也不知道谁心里在想什么”,“在这个不是他们杀死我们,就是我们杀死他们的年代……只有你死我活的杀戮”。在这种人与人高度异化的关系中,那些还没有掌握杀戮本领的人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创伤,失去了对于生命的敬仰。
四、结语
《静静的顿河》这部诞生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主义经典著作,丝毫不见革命的浪漫情怀,相反充满了悲苦与痛楚。然而,那湍流不息的顿河、生生不息的自然似乎赋予了那片土地永恒的生命力,也使得这部作品具有普世的价值。这部作品探讨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话题,折射出人类精神的失落与回归。
[1]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M].金人,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
[2]孙美玲.肖洛霍夫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3]刘亚丁.顿河激流——解读肖洛霍夫[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
[4]马晓翔.《静静的顿河》中的风景描写[M].兰州大学学报,1987(2).
2014-02-14
张丽艳(1977- ),女,山西临汾人,硕士,忻州师范学院外语系讲师,从事中西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I512
A
2095-7602(2014)04-01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