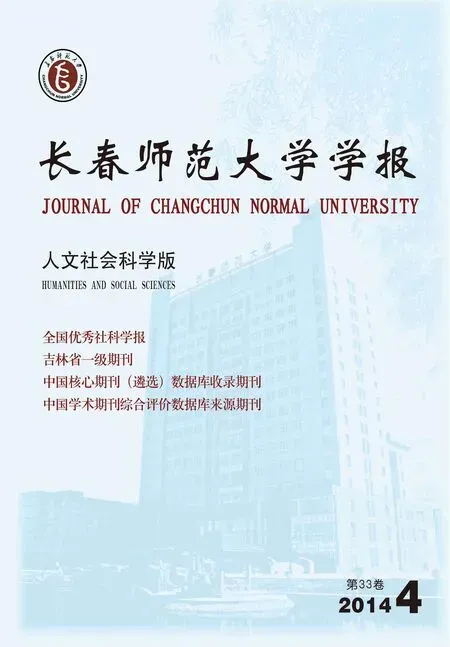唯美主义旗帜下的道德重建
——浅析奥斯卡·王尔德的艺术风格
史玉明,陈丽敏
(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 英语系,天津 300270)
唯美主义旗帜下的道德重建
——浅析奥斯卡·王尔德的艺术风格
史玉明,陈丽敏
(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 英语系,天津 300270)
奥斯卡·王尔德作为英国19世纪唯美主义运动的先驱,曾大胆直言“为艺术而艺术”,倡导艺术无道德、唯形式至上的艺术追求。其作品在唯美的表象之下,蕴藏着深刻的道德忧思。本文以王尔德小说、戏剧和童话作品的艺术特色分析为切入点,旨在探究王尔德唯美主义旗帜下的道德回归和重建。
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道德
奥斯卡·王尔德,这个在世时饱受争议,甚至一度因为“有伤风化”而身陷囹圄,最终埋骨他乡,在遭到毁誉近一个世纪后才被迎回故国的唯美主义重要代表人物,高举“为艺术而艺术”的大旗,用独具艺术特色的小说、戏剧和童话,构建起一个奇特的艺术世界:道德在被狠狠地抛离之后,经过一次次的挣扎、努力,实现了一种凄婉的回归和重建。
一、唯美主义思潮下艺术的道德剥离
唯美主义从法国起航,迅即经由英美影响到全世界。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基人康德在《判断力的批判》中大胆地提出了“纯粹美”和“审美无利害”的美学理念,道德判断和审美判断依据截然不同的规定;美不等于善,审美活动不能涉及利害计较,只以它的形式来产生美感。这很快成为后来的法国唯美主义旗手戈蒂叶“艺术无功利”观点的催化剂,19世纪唯美主义思潮的理论出发点自此形成。戈蒂叶首先借用莫里哀的经典之作对指责浪漫主义作品败坏社会风气的道德主义批评家予以批驳。他认为“在莫里哀的作品里,道德总是受到羞辱和沉重打击”[1]223,艺术应独立于道德和政治之外。他进一步指出,艺术与道德无关,它不但不对社会道德的好坏负责任,相反倒是丑恶的社会要对艺术负责任。功利性不再成为衡量艺术好坏的标准。任何美的东西都不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只有毫无用处的东西才是真正美的。艺术有自己独特的目标,这目标就是艺术本身,与任何外在因素无关。因此,当艺术摆脱了道德、政治、物质等一切实用主义的标准,“为艺术而艺术”顺理成章地成为唯美主义的最高理想。其典型表现就是,道德从艺术的世界里被剥离,艺术创造的终极境界变成了对形式的自在追求。在戈蒂叶看来,艺术等于美,美等于形式。
在戈蒂叶理论的影响下,英国文艺界唯美主义早期最重要的代表佩特提出了“纯美”的概念,“艺术美是脱离社会现实的、孤立的和独特的,是纯美;纯美主要体现在形式上”[2]22。永远保持对形式和纯美的关注,才是最理想的人生态度和最高的生命境界;只有在艺术中度过一生的人,才是最聪明、最幸福的人。道德再度被排斥在艺术的美学范畴之外。
佩特对艺术形式的强调,被王尔德接受并发展到极端,变成了“形式就是一切”。赫拉克利特认为艺术摹仿自然,而唯美主义画家惠斯勒却反其道而行之,倡导自然摹仿艺术。惠斯勒的组画《夜曲》系列,在画面处理中注重线条、形体和色彩,其初衷是为了反映事物在光线下所呈现出的特殊形式,从而传达对伦敦夜景音乐般的感受。这些画作更多地是为了引导人们对形式产生兴趣,而不适用于从像与不像的角度进行评判。王尔德在惠斯勒的理论基础上进行了更充分的例证。他以“雾象”来解释自然对艺术的摹仿:人们看见雾不是因为有雾,而是因为诗人和画家教他们懂得这种景色的神秘可爱性。雾没有存在,直到艺术发明了雾。[3]133基于对人生丑陋、不完美的认识,王尔德认为人生根本不值得艺术去摹仿。他直言,“人生是破坏艺术的毒剂,是毁灭艺术之宫的仇敌”[4]。艺术不表现时代,只表现自身。在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序言中,王尔德大胆提出,艺术家的责任是创造美的事物,一本书只有好与不好之分,不存在道德与不道德一说。艺术不依赖于道德而存在,艺术有自己的追求,那就是美。
但是,艺术自产生之初,就被有意无意地赋予一种道德的责任。苏格拉底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该是“功用”的,就是说有用即美,无用即丑,导致了西方长期善美不分、以“功用”代替文艺全部本质的倾向。鲍桑葵指出:“从最广泛的历史意义上来说,毫无疑问,艺术是人民的教育者。”[5]127这也成为道德批评出现的文化动因。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情节和性格的论述蕴含着深刻的道德考虑:悲剧人物的性格必须具备善良、合适、与一般人相似和一致性的特征;当善良被看作悲剧人物性格的第一要素时,道德也就成了判断艺术的重要标准。善良的俄狄浦斯为了逃避作恶的命运,选择了逃离,却在无知中一点点接近大逆不道的既定命运,一直到事实证明自己就是杀父娶母的凶手,悲痛欲绝地刺瞎双眼,这激起了观众的怜悯,悲剧的艺术效果因此产生。贺拉斯也主张寓教于乐。但是,对艺术作品道德教化作用的强调一旦发展到极端,毫无疑问会演化成“重教轻乐”。艺术创作自然会被加上沉重的枷锁,失去绝对的自由,逐渐变成道德标准束缚下千篇一律的庸俗产物。
单纯从道德的角度来说,唯美主义固然存在着种种不足,但这种道德的剥离对艺术形式的探索和革新有着极其积极的意义。“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赋予艺术家一种文学创作的自由,这种自由意味着对传统手法和技巧的彻底颠覆,其积极意义在于更有新意的艺术形式从此产生。
二、唯美主义者的道德受难和挣扎
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的英国,社会风气比较保守,且极为注重礼教,稍微偏离常规就会被视为脱离正轨。但太多的事实证明这一切都只是伪饰的假象,以伦敦为代表,表面辉煌,实则藏污纳垢,社会底层一片混乱,上流人士丑闻不断。传统的社会价值和美学信念已被动摇,新的价值观和美学观尚未形成,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英国文坛“世纪末”景象甚嚣尘上。
在伦敦的社交界,王尔德是有名的,但这种名声却是“道德的颠覆者”。他那标志性的着装,即镶着黑穗的天鹅绒紧身上衣、长丝袜子和平绒灯笼裤,完全颠覆了英国绅士坚守千百年的严肃着装风格,和戈蒂叶当年参加雨果戏剧《欧那尼》演出时那件刺眼夸张的“红背心”一样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如果说着装并不能绝对反应一个人的道德水准,那王尔德与道格拉斯勋爵之间超越性别的情感,则让他彻底沦为道德法庭的受审者,甚至因此狼狈入狱。但是,抽丝剥茧寻找背后的原因,不能不说,王尔德因此承受的苦痛挣扎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社会道德对人性的束缚和压抑。
如果忽略性别的问题,王尔德和道格拉斯之间的情谊是深刻而又真诚的。王尔德情愿一人受过,也要把道格拉斯完好地藏在身后。面对法庭盘问他:“什么是不敢说出名字的爱?”王尔德回答:“不敢说出名字的爱,如同你在米开朗基罗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找到的,它支配并渗透了伟大的艺术……”这种反驳是狂放的,也是强有力的。如果没有那个同为须眉的“青年才俊”(fair youth),莎士比亚的百余首十四行诗就缺失了重要的情感基石。如果没有兰波,法国大诗人魏尔伦的才情可能很快就会枯竭。恰是这种非一般的情感,成就了艺术之美,成就了《泪散落在我的心上》的传世名作。忘却兰波和魏尔伦的性别,诗作中的情感营造出一种令人动容的艺术美感,艺术实现了美感的传达,也就实现了对伟大的追求。王尔德和道格拉斯犯下的最大错误,是他们选择了一条被传统道德彻底否定的路。王尔德对伟大艺术是狂热的,狂热到不去计较世俗的责难,甚至忘乎所以。
王尔德曾经说过,只有三种方法能使你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即迎合、逗乐或是震撼这个社会。在现实生活和艺术世界里,他拼命挣扎,想要置身道德之外,并试图通过一种唯美的方式来实践这种震撼。但现实人生中,王尔德的挣扎归于失败,受尽非议,最终凄凉辞世。在艺术的世界里,他尝试用唯美主义的大旗来掩盖所有创作的创新性尝试,并勇敢地把颠覆了的道德毫不掩盖地表现出来,但这种艺术的挣扎依然没有取得绝对的胜利,文艺创作并没有完全脱离生活和现实,对现实的冷嘲热讽被敏锐犀利的语言直白地表达出来,显现了王尔德的道德思索。
以天才自居的王尔德,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在矛盾中去寻求一种解脱的途径,甚至幻想艺术的纯美境界能安抚困惑的灵魂,只可惜这种追寻受制于强大的现实,一次次被挫败。誓为唯美主义奉献全部的王尔德并不能够完全实现对艺术与现实以及艺术与生活二元划分的理想,但他对艺术与自然、人生、时代和道德关系所作的探索,对形式主义、直觉主义,甚至20世纪的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都有重大影响。
三、唯美主义视角下道德的重建
当道德成为艺术的负累和枷锁、成为抹杀艺术家创造力的罪魁祸首时,王尔德大胆选择了舍弃。唯美主义把对艺术形式的完美追求凌驾于一切考虑之上,将自然、人生、时代和道德当作前进路上的牵绊,狠狠地予以清除,创新性地主张借用色彩和光等手法技巧,从平凡、怪诞、丑陋中发现美,将形式放在艺术创作和批评的首要位置。明亮的色彩,如银色、琥珀色、淡黄色常被使用;忧郁美、怪诞美、恐怖美也开始革命性地出现在文学艺术中。如《道连·格雷的画像》中,画像在道连每一次作恶之后都会变得越发狰狞恐怖,这样的处理技巧是荒诞、不现实的,但这恰恰解释了王尔德对艺术至高无上的坚定信仰。这些都在细节上反映了唯美主义者对传统艺术审美的颠覆。
道连在霍华德和亨利勋爵或为善或为恶的双面夹击中,一点点地走向堕落。道连曾经挣扎过,试图终止这种堕落,但是正如亨利勋爵所说,“我们竭力压抑的每一种欲望都在我们的心中作怪毒化我们。而肉体一旦犯下罪恶,也就摆脱了作恶的念头,因为行动是一种净罪的方式。事后留下的只是甜蜜的回忆和悔恨的快感。摆脱诱惑的唯一方式是向它屈服。”
画家霍华德对道连的关注,对绘画作品的喜爱,都象征了他作为艺术家对艺术的潜心追求;但亨利勋爵享乐主义人生态度终究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道连,使其个性由单纯变为世故,灵魂由纯洁转为污秽,最终滑下了罪恶的深渊。情感和理智、堕落和道德、清醒与困惑在小说的世界里拼尽全力地较量。在道德和良善险些被彻底扼杀的紧要关头,道连刺向画像的那一刀竟然结束了自己罪恶的生命,道德败坏遂遭惩罚,其深意不言而喻。在戏剧《莎乐美》中,年仅16岁的妙龄美女由于向约翰求爱被拒,愤而请希律王将约翰斩首,把约翰的首级拿在手中亲吻,以这种血腥的方式拥有了约翰。王尔德用《莎乐美》这个血腥的故事告诉人们,不道德的作恶有多么的令人发指。惊悚的美是怪异的美,它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吓人,而在于用一种更强烈的冲击力把观者所有的感受力和思考力全部调动到极致,从而促成更深刻思想的产生。莎乐美和道连,这两个精神荒原里拼命挣扎的灵魂,从不同的角度刺激人们审视道德的是是非非,体现了王尔德的独具匠心:荒诞惊悚的表象之中,彰显艺术奇异的魅力。
王尔德的作品中还蕴藏着细腻、感性的道德思辨和关怀。如果说《道连·格雷的画像》是王尔德“为艺术而艺术”,向艺术道德性发起攻击的战书,那他的戏剧和童话则代表一番挣扎、绝望之后的妥协和让步。王尔德的一生就是各种矛盾和苦痛纠结的写照,离经叛道的他竟然拥有纯真的童话情怀,包括《快乐王子》、《夜莺与玫瑰》、《自私的巨人》、《忠实的朋友》等在内的九篇童话都有一个凄美的结局。曾经镶满黄金叶片,拥有蓝宝石做成的双眼,剑柄上的红宝石闪闪发光的快乐王子,因为悲悯,从此告别快乐,一次次眼含热泪,守望身边的疾苦众生;金叶、宝石一点点被剥离,只为了让病中的孩子得以康复,让穷困剧作家的创作不至于被饥寒扼杀,让卖火柴的小女孩不至于被父亲毒打……美丽的外表被一点点摧毁,铅做的心裂成两半,最终在市长和参议员众口一词的丑陋批斗中,快乐王子的雕像被轰然推倒。原址上市长的雕像拔地而起,快乐王子为了悲天悯人的道德,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却被如此贱弃。夜莺坚守成人之美的道德境界,以身刺荆棘的勇气,用鲜血和生命成就了玫瑰的鲜红灿烂,却抵不过珠宝强大的现实诱惑,“人人都知道珠宝比花儿更值钱”。曾经自私的巨人,追求博爱的道德,诚邀孩子们到花园中嬉戏玩耍,最终死在大树下,浑身覆盖着白花。小汉斯恪守忠实的道德品质,在磨坊主貌似温言善语的圈套里,为了给他的孩子请医生,不幸在暴风雨之夜溺死在冰冷的水坑里。
幻想美、意境美和感伤美体现了王尔德作为一个唯美主义艺术家在极度的悲情和失望中追寻救赎的艺术尝试。艺术和现实终究是矛盾的,完美的道德构想和努力在现实虚伪、冷酷的重击下归于失败。天真、纯善和美好在邪恶、伪装和丑陋的陷害和折磨下奏起了一曲曲道德的悲歌,久久回响。王尔德把深厚的道德忧思包裹在唯美主义的外衣里,貌似离经叛道,实则至纯至真,让读者体会到强大的道德力量。这种悲情的世界观和尼采不谋而合:从悲剧中看到由于个人的毁灭而解除了一切痛苦,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获得狂喜。尼采的悲剧世界又不等同于悲观主义:获取欢乐而不是丧气,肯定生命而不是否定生命。艺术变成了纯粹的谎言来掩盖某些可怕的真理:“真理是丑的,我们有了艺术,依靠它我们就不至于毁灭真理;把现实世界艺术化,把人生的苦难化作审美的快乐。这就是悲剧给人的形而上的慰藉,也是艺术对于人生的终极意义。”[6]320
在戏剧艺术的构建中,王尔德对道德和艺术的矛盾思索成为推动剧情跌宕起伏的重要因素。在《温夫人的扇子》中,上流社会温尔文雅、道德高尚的伪装被一层层撕下。天真的女人不一定好,世故的女人也不一定坏。同时,习于顺境的温夫人若非在欧琳太太的感召下悬崖勒马,早就滑向了道德堕落的泥潭。温德米尔夫人对丈夫说:“我现在认为不能把人简单地划分为好人和坏人,所谓好女人身上可能有很可怕的东西,有疯狂、固执、嫉妒和罪恶。所谓坏女人身上可能会有悔过、同情,甚至牺牲。”[7]
由此可见,完美的道德只能是一种纯粹的艺术想象,这种令人沮丧的认知,促使王尔德在艺术的追求中偏离道德,只为艺术而艺术。但是,王尔德对道德的抛弃并没有做到极致,丑陋、阴暗、有悖道德的东西在他的作品中时有出现,但最后都无一例外被纠正、美化了过来。如果说艺术代表王尔德作为一个唯美主义艺术家的终极理想的话,那么道德则是阻碍他理想实现的障碍,但理想和现实本身就是对立统一的矛盾综合体,道德和艺术的界限也不可能如此泾渭分明。对道德的摒弃,只是为了美化对艺术的追求。
现实和理想、道德和艺术在王尔德的世界里是矛盾的。正如这位悲情的艺术家自己所说:“我们都在阴沟里,但仍有人在仰望星空。”[8]王尔德怀揣着纠结的道德观,在艺术的世界里浮浮沉沉、拼命挣扎;当这种追求得以实现,道德也以一种合乎常理的方式实现悲壮的回归和重建。
[1]伍蠡甫.西方古今文论选[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2]伍蠡甫.现代西方文论选[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3]赵澧,徐京安.唯美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4]王尔德.谎言的衰落[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
[5]鲍桑葵.美学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6]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
[7]王尔德.温夫人的扇子[M].吉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8]王尔德.王尔德全集:第6卷[C].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
The Reconstruction of Ethics under the Veil of Aestheticism——An Analysis of Oscar Wilde’s Artistic Style
SHI Yu-ming, CHEN Li-min
(Binhai School of Foreign Affairs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70, China)
Oscar Wilde is undoubted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s in English Aesthetic Movement. The aestheticists all hold a strong belief in “art for art’s sake”, showing strikingly revolutionary individuality differing from literary traditions. Thus literary production doesn’t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of moral correcting and guiding. However, Oscar Wilde, a sinful gay who suffered a short imprisonment, tried his best to achieve the reconstruction of ethics in an aesthetic world. With a careful study on his artistic features, Wilde’s identity as an idealist will be clearly shown.
Aesthetic Movement; art for art’s sake; ethics
2014-02-16
史玉明(1978- ),女,河南南阳人,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英语系讲师,硕士,从事英语教育、英国文学研究。
I561
A
2095-7602(2014)04-009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