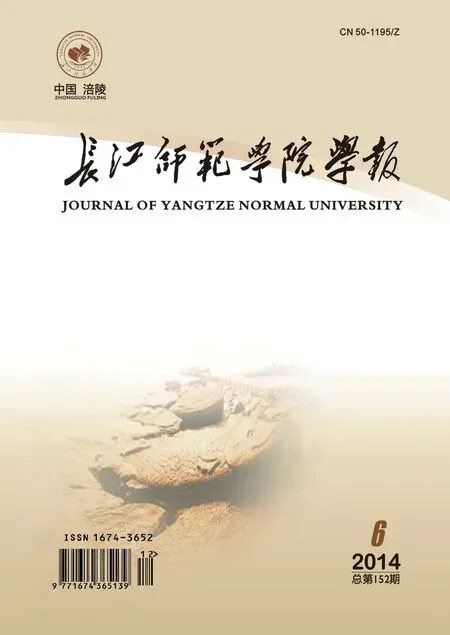现代化进程中的日本农村题材小说
——以藤本惠子的农村题材小说为例
韦玮
(南京晓庄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现代化进程中的日本农村题材小说
——以藤本惠子的农村题材小说为例
韦玮
(南京晓庄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藤本惠子文学中的农村题材小说以战后日本农村从恢复进而走向现代化进程为时代背景,在新时代背景下,主人公们继承了日本农民文学中对 “土”的概念的重视,他们在有着脱离农村倾向的同时,又感受着 “田地守护人、人也守护田地”的意识,体会着 “守护农田、守护祖坟”的宿命感,这也是他们最终又能回到农村的原因所在。但与日本乡土文学中与城市文明对立的乡土本位意识不同,藤本惠子笔下的主人公们以一个更为宽容、更为开放的态度来面对现代城市文明,他们也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在农村实现了作为农村人的自我认同。
日本农民文学;藤本惠子农村题材小说;自我认同
一、问题的提出
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农村题材小说又被称作乡土文学或者农民文学,实际上处于一个边缘化的地位,“志贺、谷崎自不消说,就是他们以前的或以后的一代小说家,也很少有人描写农村和农民的。几乎所有人都不愿意走出城市中产阶层之外。”[1]378这是因为日本的作家大都出身于脱离农村或农业生产的工商业者、武士或士族家庭,他们没有对农村深厚而复杂的乡情,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农村题材文学,往往是站在城里人立场上对农村的观察,带有俯视和不屑的态度。而随着城市文明弊端的暴露,日本的乡土文学开始关注农村本身的价值,提倡一种以乡土为本位的文学。其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进行,日本乡土文学产生了变异,成为法西斯文学的一部分。
战后日本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经济现代化的进程,而这也是作家藤本惠子本人的成长背景。藤本惠子1951年生于日本滋贺县大津市,曾先后获得 “作家奖”、文学界新人奖,两次获得芥川奖候补,2001年以 《响彻筑地的铜锣》获得开高健非小说奖。藤本惠子文学涉及到农村题材、团塊者题材以及边缘人物题材等方面。《百合鸥》《水芹》是其农村题材小说的代表作,这两部作品以日本战后的民主化、现代化进程为时代背景,描写了阿雪、吉夫以及他们的孩子冬夫两代农村人的生活历程。阿雪、吉夫以及他们的孩子冬夫都有着对脱离农村的渴望,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感受到农田、祖坟的束缚,感受到一种继承家业的责任感,最终他们也都又回到了农村,在农村实现了自我认同,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农村也得以凭借其自身价值实现了自我认同,展现出完全可以凭借本身价值立于世上的可能。
新时代背景下藤本惠子笔下来自农村的主人公们如何实现自我认同,这也关系着农村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如何才能以自己的本来价值实现自我认同,避免沦为城市的附庸。对这些问题的考察也有助于理解新时代背景下藤本惠子对日本乡土文学的继承和突破之处。
二、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农村题材小说
1910年 (明治30年)前后,国木田独步、田山花袋、岛崎藤村等一批作家在创作中开始涉及农村题材。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日本的作家把农村作为纯客观的描写对象,他们以城市人的优越感,带着一种不屑和歧视描写乡村和农民。以真山青果的 《南小泉村》为例,这部作品描写了农民的愚昧无知,露骨地表现了对农民的厌恶和蔑视, “再也没有像农民那样悲惨的人了,尤其是奥州的贫苦农民更是如此。他们衣着褴褛,吃着粗粮,一个劲儿地生孩子,就仿佛是墙上的泥土,过着肮脏邋遢、暗无天日的生活。好像那地上的爬虫,在垃圾中度过一生。”
长冢节的 《土》中主人公是贫农,他在距村子约78km远的利根川开垦工程工地打工,其间因妻子患病,他抛弃工作赶回家来,可是村子里没有像样的医生。妻子因破伤风而死,其原因是堕胎时感染所致。后来,留下来的主人公与老丈人相处不和,而双方都没有财力可以分开过日子。主人公从他人的地里偷了东西,被偷者上告,他被揪了出来,遂向地主求情。地主婆认为他很可怜,便向被偷者做了工作,警察方面也说只要主人公说声没有偷,事情就可以了结。尽管如此,他还是害怕警察,“可俺一到那里,就不能不坦白呀”。
总的来说,《土》展现了1910年前后,利根川水域贫农的日常生活,详尽地叙述了农民的悲惨、无知,农民身上有着人品好、狡猾和温顺这些互相矛盾的属性。在长冢节的小说中,有着对农民的人道主义同情,也有着对大自然的亲近,字里行间都散发着乡土气息的芬芳。但作为茨城县富农 (后来是县议会议员)的长子,长冢节是站在地主的立场上观察和描写农民的,他的作品也更多地表现了农民的刁钻古怪、狡猾世故等品性。
日本的乡土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进入了自觉时期。在此期间,日本的乡土文学在对现代城市文化的否定和批判中,表现出了对乡村文化回归的倾向。就时代背景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充分暴露了以城市文明为本位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和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重新把目光投向了乡村。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或农民文学,强调作家要站在乡村农民的立场之内,把思想意识和思想感情融化于农民,设身处地表现农民。日本农民文学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犬田卯指出,以前的乡土文学和田园文学是 “走向土地”,现在必须 “从土地出”,也就是 “从生产自耕农的意识中产生的东西”[2]26。犬田卯将这种意识称为 “土的意识”或 “农民的意识形态”,把具有这种意识的文艺称为 “土的艺术”。
在这一时期,日本乡土文学的作家们提倡以农民、乡土为本位的文学。他们主张用乡村文化、农民文化来治疗现代城市文明、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种种弊端。这也导致当时文坛弥漫着一种浓厚的 “归乡”情绪,展现出一种对城市本位主义价值观背离的倾向。为了强调农村文化的唯一价值,乡土文学的作家们甚至把农民和工人、乡村和城市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为了养活城市这只 “大壁虱”,农村被“剥皮碎骨”,所以农村阶级是和资本主义城市文明对立的,城市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不过是资本主义的附属物。
此后随着20世纪30年代侵华战争的发动,日本乡土文学走上了异化的道路。1934年1月,直木三十五、吉川英治等作家以法西斯文学团体 “五日会”为基础,发起成立了 “文学恳话会”。1938年底,以 “农民文艺会”及 《农民》杂志为中心的日本农民文学运动或称乡土文学流派成立了 “农民文学恳话会”,而 “农民文学恳话会”实际上就是“文艺恳话会”的一个分支机构。至此,日本的农民文学运动被完全纳入到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体制。原属农民文学运动成员的作家们,按照军国主义政府的要求,写作了大量的有关如何增产粮食、服务“大陆开拓”的作品,其中许多人获得了政府颁发的各种 “文学赏”。“农民文艺恳话会”成立之后,“农民文学的大部分完全改变了它的性质。也就是说,它堕落了,顺应时势,丧失了此前它所主张的存在权利这一重大要素中所包含的革命性,乃至下层的阶级性”[2]161。这一阶段的 “农民文学”实际上是 “农民文学的变质”[3],并非我们这里讨论的农民文学。
三、“从土地出”的 “土的意识”与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自我认同
日本农村文学曾提倡站在农村立场上,把思想感情融于农村,这也是犬田卯所说的 “从土地出”的 “土的意识”的内涵所在。藤本惠子的农村题材小说继承了日本乡土文学对 “土”的依恋,在城市化面前,来自农村的主人公固然有着脱离农村的渴望,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又对农田有着命运般的束缚感,感受到有责任继承家业。实际上,这种束缚感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精神枷锁,而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
《百合鸥》中的主人公阿雪12岁开始就到京都城里人家做佣人,精神上、生活上都已经远离了农村。时隔8年回家省亲的阿雪,对老家并没有过多的留念,很快又匆匆回到了城里。阿雪在心理上跟主人家融为一体,对他们的孩子呵护有加,甚至产生了把他们当成自己孩子的错觉。这些都无不弱化了阿雪作为佣人在城市的从属性地位。事实上,她成为种田人家媳妇的时候,一想到自己成为村落共同体的一员,阿雪心里感到的是痛苦。这些都充分说明了阿雪对脱离农村充满了渴望,流露出一种明显的对农村背离的倾向。
跟阿雪类似,她的丈夫吉夫也是来自农村的种田人家,并没有多少生意天赋的吉夫一直尝试着做不同的生意。对他来说,农田、坟墓是把他束缚在农村的枷锁,像他的生意伙伴野田宏那样到处做生意的人才是他所向往的。在 《水芹》中阿雪和吉夫的孩子冬夫也是如此。从内心而言,冬夫也去京都、大阪这样的大城市,而他之所以选择离家近的研究所上班,只不过是出于交通便利的考虑。等湖西线开通、跟外界联系更为方便以后,冬夫就离开了家乡,一个人跑到东京,工作了3年。
在农村主人公们脱离农村倾向的背后,是农村在农村主人公们的自我认同上的关键作用。所谓“自我认同”(Self-identity)是 “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4]275。而对这些渴望脱离农村的主人公们而言,在他们的反思性理解到的自我中,都感受到农村精神家园的属性。吉夫的哥哥英夫在濑户内海训练的时候,还想着家乡的农田。他最喜欢栽种完了的绿田,“看到绿田感到劳作的辛苦得到了报酬”,对他而言 “绿田就是一枚奖状”。类似的心理,阿雪也曾感受得到。阿雪学习缝纫机遭到挫折,为此经常受到城里人妙子不客气的批评,在这样的情况下阿雪看着田园风景,“感觉稍微得救了”。在藤本惠子文学当中,农村具有着这样的精神家园属性,有着疗伤的现实效果。在其团塊者题材小说 《团塊者》中,城里人岩田、佐山在城市工作、生活中 “受伤”,体验着人生热情的低下,最后也是通过在农村干活疗伤才恢复了人生的热情。
在藤本惠子笔下主人公对农村的精神依赖,有着坚实的基础。这表现在农村在供给食物问题上的作用。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的普通民众都经历着物资不足的问题。农村虽说也受着食物短缺的困扰,但是跟城市相比总要好一些,阿雪甚至还能藏着食物去送给城里主家。就连带有城里人高傲气质的妙子也曾因缺乏食物的缘故,带着和服到阿雪家里恳求换一些米,还提议把家里的缝纫机便宜一点卖给阿雪。这似乎也喻示着在城市面前农村有着完全不逊色于城市的价值,这也是在城市面前,农民得以凭借自身价值实现自我认同的前提所在。
对农村主人公而言,土地在食物供给上的功能是其起着精神家园功效的物质基础,但农村人对土地的精神依恋又绝不仅源于土地在食物上的供给功能。实际上,“农民的恋地情结是多重混合物:与土地的身体接触、对土地的物质依赖以及这样的因素——土地蕴藏着记忆、承载着希望”。农田改革以后,吉夫一家获得了田地,吉夫母亲看着自家的田地,一方面感叹 “活着真好”,另一方面又想着“早点被阎王带走”。吉夫母亲这看似矛盾的话语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正是农田在强化农村人代代血脉联系上的 “记忆”功能。而吉夫母亲对吉夫、阿雪说 “可以把自作田传给他们的孩子”,这话本身也体现了农田在强化一代代人血脉联系上的纽带和“希望”功能。实际上,阿雪、吉夫、冬夫也都一直感受农田的这种记忆、希望,体会着守护农田、祖坟的宿命感,这也是促使他们返乡的内在原因。
田地在横向上强化了家族的血脉联系,而在纵向上也决定了农村人之间的地位属性。吉夫一直感受到地主家和佃户之间不可磨灭的地位差距, “从孩提时代就被这种无力感所折磨”。吉夫所感受到的地位上的鸿沟正是由田地所决定的,而现在吉夫也有了自己的田地,也就重新确认了自己在农村的身份与地位。
农田改革以后,吉夫一家又有了农田,一家人都兴致勃发,吉夫母亲尤其是如此,乘着兴致跟阿雪谈着自己的经历。刚到吉夫家的阿雪体会到成为了农村共同体的一员的时候,她心理上觉得很痛苦。现在吉夫母亲趁着兴致谈着田地,谈着自己的经历,在心理上把阿雪拉到了农村共同体内,使之在内心也成了共同体的一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雪跟婆婆心相通的这两三个月,也是农地改革的功劳。”由此可以看出,田地也有着巩固农村人家庭成员之间感情纽带的功能。
正因为对来自农村的主人公而言,田地有着如此重要的功能,所以丧失这个归路对农村主人公而言实际上就等于是丧失了自我认同,冬夫在研究所的同事今井的命运正体现了这一点。因为父亲选择补偿金而放弃农村的营生,使得今井失去了回到农村的退路。最终选择开出租车的今井实际上是一个依附着城市生存的人物形象。他的出租车主顾是色情街上的女郎,而色情街是属于城市而非属于原先的农村。其后色情街衰退,今井的生意一落千丈,这似乎也喻示着来自农村的主人公倘若只能依附于城市,其生存状态会是何等的脆弱。今井本人也一直为失去农村这个归路而痛苦着。今井的痛苦源于自己成为了林德所说的 “自己家园的世界的陌生者”形象,“在意识到我们不能信任我们对 ‘我是谁’、‘我属于何处’等等问题的解答时,我们体验到焦虑……伴随对信任的周期性的冲击,我们重新成为一个在异己的世界中不能确定自身的儿童。”[5]46-47今井正是这样一个无法回到农村、只能游离于城市边缘的人物形象,感受着无法实现自我认同的痛苦,成为了一个 “异己的世界中不能确定自身的儿童”。
冬夫在研究所的另外一个同事澄子则因为在城市做着酒吧女郎,被村民们视作耻辱,自家兄弟也不让她回家,对她而言这是 “终生徒刑”。另外一方面,澄子本人也失去了回到种田人家的意愿,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她已经习惯了城里的生活,她 “喜欢城市”。但酒吧女郎的身份早已经揭示了她在城市只不过是一个边缘人物,并非真正地融入城市。从橙子给父亲买了螃蟹却不能亲自给他送过去这一细节也能看出,橙子实际上处于一个多么痛苦的生存状态之中。
相比之下,冬夫回到农村的身份认同则要顺利得多,这是因为一方面冬夫家坚持不卖田,使得冬夫没有丧失农村这个原点。不过,冬夫在个人意愿上也一直感受着农田的束缚,对守护农田有着宿命似的责任感。实际上,冬夫在小说的初次登场极具象征意义,冬夫帮着母亲阿雪在田里干活,俨然就是一个地道的农家种田人。对冬夫而言,选择附近的纤维公司上班,只因为离家近,上班方便。而去京都、大阪这样的大城市的话,“上下班是个大问题”。这也可以看出冬夫考虑问题的立足点还是在农村,尽管研究所的工作跟种田无关,但在心理上他还是站在农村这个原点的。
母亲阿雪曾经经历过饥饿,她看到农田 “感到得救”自然有着自己亲身体验在里面,而冬夫则没有经历过饥饿,可他的自我认同也继承了上一代农田守护人的这种意识。从东京回来后的冬夫也感受到 “人保护田、田也保护人”。冬夫尽管之前有着强烈的脱离农村的渴望,可现在也明确地感受到“不想失去田”,他体会到只要有田,“一家人吃饭的米就够了”,这样一来 “就算失去工作,只要有吃有住就能再起。”没有经历过饥饿的冬夫也有了这种田地守护人的意识,这正体现了农村人的代代传承包括了农村人自我认同上的传承,而并非仅仅是生命体的延续。可见,冬夫此时完全站在了农村这个立场上,实现了自己作为农村人的身份认同,而这实际上也是城市化进程当中农村凭借自身价值实现自我认同的前提所在。
四、乡土本位与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的自我认同
犬田卯认为,农民艺术 “就是反抗近代文明,对近代社会组织进行挑战”[2]34;他认为,日本农民文艺运动的出发点,就是对都市、机械、劳动等所造成的现代社会的所谓 “繁荣”加以纠正[2]94。这正体现了日本农民文学在自觉时期试图张扬乡村田园文明,排斥及纠正现代城市文化、工业文明带来的弊害的倾向。而藤本惠子笔下主人公也有着返乡的倾向,但与其说是反抗现代文明,倒不如说这些来自农村的主人公是对现代文明敞开怀抱的。在藤本惠子笔下现代化进程当中农村的自我认同,所面对的正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阿雪们对脱离农村的渴望也验证着这一点。但是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实际上就是农村受到城市侵蚀的进程,这不仅仅表现在外在上,更重要的是内在价值上,农村只能依附于城市。在藤本惠子笔下的农村也摆脱不了在城市化进程中沦为附庸的命运。被众人赋予希望的湖西线的开通,的确使得内外交流更为便利,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当地被开发成了东京、大阪及神户的卫星城,卫星城的定位正表明了现代化进程当中农村的附属性地位。而在农村土地上开发的高档住宅、色情街,这些并不属于农村,而是属于城市的。在住宅街里面住的也不是原来的村里人,而是企业高层、大学教师这样的社会精英。这些无不尖锐地突出了城市与乡村两种文明、两种生活方式的对立,反映出所谓的现代化进程正是农村受着城市侵蚀,无法以本身价值实现自我认同的过程。
在农村受城市侵蚀,无法以自身价值实现自我认同的过程中,则是主人公们基于农村本身价值的返乡过程。从东京回来的冬夫此时也感受到 “人保护田,田也保护人”,以 “大众食堂”的开办为标志,冬夫的返乡体现了其站在农村人立场上实现了自我认同。法国料理店以色情街女郎为主要顾客,在色情街衰退以后,法国料理店的生意也大受影响。最终大厨因为跟员工私奔,将法国料理店以优惠的价格卖给了冬夫。表面上来看,经营饭店这似乎是跟田地耕作无关,并非强调农田本身的价值,但实际上,冬夫这里所看重的还是农村这个共同体本身。法国料理店是为城市服务的,以色情街上的女郎为主要生意对象,而冬夫将之改办成大众食堂的时候,他所意识到的是 “这个土地是村人先祖代代耕作的,不能忽视这个”,大众食堂要以村人为客户对象。犬田卯曾指出,“即使作家住在城市,也不影响他被称为一个农民文学家或 “土的作家”,最重要的是作家有没有 “土的意识”[2]32。同样的,冬夫即便没有直接地从事与种田相关的工作,但是由于他在开办大众食堂的过程当中有着这种 “土的意识”,因而也不影响我们将其行为定性为实现农村本身价值的 “返乡”。
“该做什么?如何行动?成为谁?对于生活在晚期现代性的场景中的每个人,都是核心的问题”[4]80-81。 “而这之所以是核心的问题,是因为我作为自我或我的认同,是以这样的方式规定的,即这些事情对我而言是意义重大的,而且,正如被广泛讨论的那样,这些事情对我意义重大,而且,只能通过已经接受的关于这些问题的有效表达的解释语言,才能制定我的认同问题。”[6]47当初阿雪想到其成为了农村共同体的一员的时候,心里是痛苦的,而现在第二代人物冬夫终于意识到这个土地是村人先祖代代耕作的,要根植于这个共同体之上,这对他来说意义重大,也制定着他的自我认同。正是因为冬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才可以将其开办大众食堂认为是其以农村人的身份实现了自我认同,由此农村本身也才得以凭借本身价值实现了自我认同。
除冬夫这样来自农村的主人公们的返乡能看到农村凭借本身价值实现自我认同以外,在藤本惠子笔下来自城市的主人公选择到农村去,这同样能看出是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凭借本身价值实现了自我认同。冬夫的妻子是城里来的女大学生,家庭条件优越,妻子本人是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在大公司有着体面的工作,可她毅然决然地来到乡下跟冬夫成亲,成了种田人家的媳妇。冬夫妻子之所以能够下定这个决心,就是因为在拜访冬夫家时,在手工做东西的过程当中,感悟到 “以前吃的东西都是都市化的俗称”,而这种手工做食物的生活才是她所要追求的,这种生活 “比讨论着所谓的家国天下还要勇敢”。“生活风格可以界定为个体所投入的多少统一的实践集合体,不仅因为这种种实践实现了功利主义的需要,而且因为它们为自我认同的特定叙事赋予了物质形式”[4]92。冬夫一家坚持着原先的生活方式,这体现出他们坚持以原先农村人的身份实现自我认同的倾向,而冬夫妻子被这种生活所 “感动”,觉得这就是她所追求的生活,也就意味着她也愿意接受这种生活风格背后的自我认同。从实际行动来看,嫁到农村的冬夫妻子完全适应了这种身份转变,“比种田人家的姑娘还要对农业上心”,俨然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的形象,丝毫看不出来这是一个城里家境优越人家的女儿,也看不出来这原本是一个英语专业毕业的、在大公司有着体面工作的女性。
冬夫一家站在农村这个立场上,实现了自己作为农村人的身份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农村也得以凭借自身价值实现了自我认同。冬夫一家坚持着原先的农村生活方式,阿雪不愿意去有着现代化设施的老人之家去养老,而更愿意在家里跟年轻人生活在一起,这些都能看出冬夫一家站在农村立场上的坚守。但与所谓的对近代文明的反抗不同,在藤本惠子笔下农村的主人公对近代文明是充满渴望的,这从他们对湖西线开通的期待上能够看得出来。而面对着厕所变成抽水马桶这样的城市化改造,阿雪也感叹 “乡下变成城里了”,可见在藤本惠子的笔下,来自农村的主人公以一种更为现实的态度,更为宽阔的胸襟对待现代文明。他们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实现了自我认同,而农村自我认同的实现,也是处在这个背景当中的。
五、总结
日本早期的农民文学在城乡两种文化、两种生活方式的对比与反差中,以城市 (现代)文化的价值观,对乡村文化加以对照和批判。他们或以城市人的优越感看待农民,或站在地主的立场上居高临下地 “俯视”农民,在这个过程中也有着 “施恩”似的有限的 “同情”。在其自觉时期,农民文学在对现代城市文化和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否定和批判中,表现出了对乡村文化回归和认同的倾向。至于走向法西斯文学道路的农民文学,这已经属于变异而非本真的乡土文学了。
作为农村出身的作家,藤本惠子本人对农村有着感情,在 《水芹》后记中就流露出 “记录”这种手工耕作的农业面貌的兴趣。在藤本惠子农村题材小说中延续着之前日本乡土文学 “从土而出”的“土的意识”,其笔下人物在渴望脱离农村的同时,又感受到继承家业、守护田地的责任感,这也是他们之后又能回到农村、在农村实现自我认同的原因所在。而主人公们的这种自我认同也决定了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农村能以自身价值实现自我认同。实际上,日本乡土文学在自觉时期也有过价值观从城市到农村的回归,但是与所谓对现代文明的反抗、用农村文明纠正城市文明不同,藤本惠子笔下的主人公对融入现代文明是充满渴望、敞开怀抱的。这与他们以农村人本身价值实现自我认同、坚守农村生活方式是并行不悖的,这也是一种更为包容、更为现实的态度。
[1][日]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下卷)[M].叶渭渠,唐月梅,译.北京:开明出版社,1995.
[2][日]犬田卯.日本农民文学史[M].东京:东京农山渔村文化协会,昭和52年(1977年).
[3]亓华,王向远.中国的乡土文学与日本的农民文学[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9(1):7-14.
[4][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M].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5]Helen M.Lynd.Shame and the Search for Identity[M]. London:Routledge,1958.
[6][利比里亚]查尔斯·泰勒.自我认同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黄志洪]
I106.4
A
1674-3652(2014)06-0083-06
2014-09-06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重大招标项目“20世纪70年代以来外国文学研究”子课题“藤本惠子研究”(〔2010〕2号);南京晓庄学院校级科研项目青年专项(2013NXY61)。
韦玮,男,江苏盐城人,主要从事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