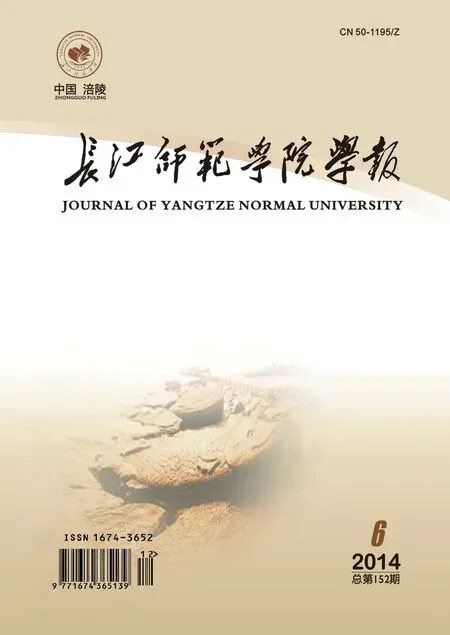“怀旧”语境中的 《长恨歌》
——一种势利价值观的体现
刘永丽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茅盾文学奖作品研究
“怀旧”语境中的 《长恨歌》
——一种势利价值观的体现
刘永丽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产生于怀旧语境中的 《长恨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怀旧文化特色:其一是对“殖民”文化的复制及宣扬;其二是对 “高雅”之享乐主义的膜拜。在这样的怀旧语境中产生的《长恨歌》在某种程度上是 “隔绝了底层社会的利益代言角色”的一种行为,是典型的势利价值观的体现。
怀旧; 《长恨歌》;势力价值观
一、前言
丹尼尔·贝尔曾指出,美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文化趋向的特质,即 “中产趣味(middlebrow)”。在这种趣味的影响下,“文化并非是对严肃艺术作品的讨论,它实际上是要宣扬经过组装、供人 ‘消费’的生活方式。”[1]90这种中产阶级趣味的一系列特征,包括:“时髦的娱乐”“视文化为商品”“假装尊敬高雅文化”,尤其突出的是贝尔指出了中产阶级社会,“长期视文化为商品,并从它的交换中获得了一种势利的价值观”[2]90。有论者指出,当前中国的文化,也存在着如贝尔说的中产阶级趣味,“它所代表的是一种删除了精英知识分子的启蒙批评立场的、同时也隔绝了底层社会的利益代言角色的、与今天的商业文化达成了利益默契的、充满消费性与商业动机的、假装附庸风雅的、或者假装反对高雅的艺术复制行为。”[3]13以 《长恨歌》为代表的怀旧作品,就体现着这样的中产阶级趣味。
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是对上海的怀旧。90年代文化领域里的 “上海怀旧”拉动了有关怀旧的商品消费需求,突出的一点即是带动了上海大规模的街区改造,营构了新型的消费空间。各种以 “怀旧”为营销手段的消费场所开始流行,新天地、衡山路等 “老上海遗风”和 “异国情调”融于一体的咖啡馆酒吧处处可见。1990年,在哈同花园的旧址,建立了奢华的五星级酒店——上海波特曼酒店。王唯铭著有 《欲望的城市》,表达出对其中奢华的总统套房的震惊:
宽大的盥洗室,足有四五十平方米。浴池的把手、龙头和其他附件都渡了金,水流旋转而出,围绕着这个莲花形的浴池。这情景只有在电影中我们才可能目睹—西方的、有关上流社会生活的电影。一切都是进口的,从造型精巧的水晶吊灯到办公桌上泛着微光的钢笔到脚下踩着的软软松松的地毯。
1500美元一晚,你能想象吗?无法想象。惟一有把握的是,从总统套房朝外瞥去,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广大的、灰朴朴的上海,它活似某水泥厂的作业区。二氧化碳大规模地毁坏着上海的能见度。而单调、粗糙、毫无想像力的工房群落则超大规模摧毁着上海的空间感。[4]64
这个场景的描绘意味深长。一方面,是总统套房的奢华;另一方面,是从总统套房窗外望出去的真实上海——败落、“灰朴朴”、由 “单调、粗糙、毫无想象力的工房群落”组成的上海。总统套房的豪华和真实上海的距离,如同怀旧作品中描绘的上海和真实上海的距离。上海怀旧不仅是文学界的行为,而是一种文化产业。“除了文学、文化以及学术研究等的参与外,政府、经济 (机构)等也主动营造上海身份。如石库门的开发,世博会的宣传等,他们都共同参与了上海城市身份认同的营造。继续了1949年前的痕迹,浓缩了90年代消费文化的打磨,上海成为了一个被改写、被重写的城市文本。”[5]111-119无论哪种形式的怀旧,其尽力打造的都是上海作为繁华之洋场社会的城市身份。 《长恨歌》即是出现在这样的怀旧语境中,整个小说文本,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诸多怀旧文化特色。
二、怀旧作品对 “殖民”文化的复制及宣扬
以 《长恨歌》为代表的怀旧作品首先是以描绘旧上海洋场社会遗留下的诸多物品,尤其是以西式物品为特色,如:洋房中的各种装璜、旗袍、月份牌及各种精美的西式器具等。王安忆在 《长恨歌》中,处处写到古物的风韵。如在平安里,作者不惜笔力地写到严师母家里的 “富丽世界”,“椭圆的橡木大西餐桌,四周一圈皮椅,上方垂一盏枝形吊灯,仿古的,做成蜡烛状的灯泡”以及 “床上铺了绿色的缎床罩,打着招皱”“绣花的桌布”“绣花的坐垫和靠枕”“金丝边的细瓷茶碗”,等,重点突出其西式的精致。康明逊看到在平安里生活的王琦瑶的不同寻常,是因为看到其房间里的几件家具。小林在王琦瑶家也是通过零星半点的旧家具,看到了些 “货真价实”的老日子。而王琦瑶看小林 “是好人家孩子的面相”,也是因为其所居住的 “新乐路上的公寓房子”。“他家的公寓,王琦瑶不用进也知道,只凭那门上的铜字码便估得出里面生活的分量,那是有些固若金汤的意思。……那是安定,康乐,殷实,不受侵扰的日子,是许多人争取一生都不得的。”[6]290门上的铜字码成了某种社会阶层的标志,展现了作者深厚的中产阶级身份意识。繁华年代遗留下的器具成为作家怀旧的最好的道具。作家笔下的物质,如同让·波德里亚所说的,物品不仅作为物理的或自然的东西而存在,而且作为受某种规则支配、表达某种意义的符号载体而出现,是铭刻了某种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的东西。而其中最重要的文化符号,是象征科技的西方器具。鸦片战争后,西洋器具以精美绝伦的风貌征服中国民众,自此,便无形中出现了对西方物品的拜物倾向。怀旧作品中的物品,是洋场社会风物的象征,突显的也是一种西化的物品。在作家笔下,西化的物品才能代表那个繁华时代的上海。 《“文革”轶事》中的赵志国,到了张思叶家里,找到的旧上海的遗迹也是西化的日常生活用品,“壁炉架上欧洲风景的瓷砖画,浴缸上生了锈的热水龙头,积起灰垢的热水汀,裸着的电话机插孔。这些遗迹流淌出典雅的气息。”[7]437“这些遗迹就好像是一个破落贵族的光荣的徽号”,它们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繁华上海的代征。在 《长恨歌》中,王安忆这样说:
虽然他们都是新人,无旧可念,可他们去过外滩呀,摆渡到江心再蓦然回首,便看见那屏障般的乔治式建筑,还有哥特式的尖顶钟塔,窗洞里全是森严的注视,全是穿越时间隧道的。他们还爬上过楼顶平台,在那里放鸽子或者放风筝,展目便是屋顶的海洋,有几幢耸起的,是像帆一样,也是越过时间的激流。再有那山墙上的爬山虎,隔壁洋房里的钢琴声,都是怀旧的养料。[8]326
在这里外滩被视为是怀旧的重要养料。那 “乔治式建筑”“哥特式的尖顶钟塔”“洋房里的钢琴声”,都是怀旧情怀之寄托处。以 《长恨歌》为代表的所有的怀旧作品都把东方剔除在外,极力推崇那个欧化的殖民城市——上海,被殖民时期遗留下的异国情调成为想象那个浮华四溢、纸醉金迷、风情万种的洋场社会的重要依据,而属于东方的民族性的东西并不在他们的怀恋范围之中。展露了怀旧作品中一个重要的倾向,即是对殖民地上海的怀恋,体现了怀旧作品中去民族化的殖民化倾向。
詹明信在谈到美国的所谓 “怀旧电影”时也提出:“‘怀旧’的模式成为 ‘现在’的殖民工具,它的效果是难以叫人信服。……换句话说,作为影片的观众,我们正身处 ‘文本互涉’的架构之中。这个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特征,已经成为电影美感效果的固有成分,它赋予 ‘过去特性’新的内涵,新的 ‘虚构历史’的深度。在这种崭新的美感构成之下,美感风格的历史也就轻易地取代了‘真正’历史的地位了。”[9]459需要指出的是,詹明信说的美化历史是美国电影实行的殖民策略,而中国的怀旧作品,也同样滤去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被侵略、被殖民的屈辱化的历史,滤去了殖民侵略的血腥和暴力,更袪除了民族歧视,而重新虚构了一种超越于现实之上的繁华历史,一种美化了的历史中的西方有灿烂辉煌的物质文明及精神文化,有自由、人性化的生活氛围,有公平竞争的生存理念,有举止优雅的西人——总之是代表一切正面的、美好的东西,完全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乌托邦式的存在。不难看出,这个存在正是应合了西方殖民文化的营销策略——对西方美化的同时,展现的是对自己民族身份的不满意,甚至是一种竭力去民族化的倾向。在西方引领的全球化幻象中,怀旧在某种程度上无意中成为西方建构东方、进行殖民文化侵略的工具,自我殖民化、他者化。
列维—斯特劳斯指出:“一个世纪以来,所有的文明一个一个地承认它们中的某一个具有优越性,这个优越的文明就是西方文明”[10]37。晚清以降,随着外国文明的入侵,民众在接受西方思想时,时不时地有批判的声音,尤其是知识分子,还是有强烈的民族自省及反思意识,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怀旧作品中,对西方文明呈现出一揽无余的认同心理。特别是西方文明中的贵族、优雅的生活方式,成为怀旧作品大肆张扬的生活趣味,体现出了如前所述研究者所说的一种 “删除了精英知识分子的启蒙批评立场”的 “势利价值观”。
三、怀旧作品对 “高雅”之享乐主义的膜拜
对西洋器具的艳羡,同时展示出来的还是对一种奢华生活方式的向往。就是这些器具,构筑了一个个精美、奢华的日常生活图景。使人引发了对旧时代悠闲、重享受的日常生活的艳羡。如同陈丹燕所说:“那是只有上海的孩子才能有的心情:对欧化的、富裕的生活深深的迷醉。对自己生活的城市曾经有过的历史深深的自珍。到那里 (和平饭店)去的上海年轻人,希望自己有更好的英文,更懂得怎样用刀叉吃饭,更喜欢西洋音乐。有一天,可以拿出一张美国护照,指甲里没有一点脏东西。”[11]38而这就是上海十里洋场的历史所要给予人们的生活,由此,一种重享乐,求奢华的生活方式再次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以 《长恨歌》为代表的怀旧作品就是这样尽力地描绘上海日常生活的富贵、精致,重在对吃喝玩乐各种感官享乐的满足。程乃珊对上海老克勒的赞颂,说到他们的 “品位、衣着、见识,远远领先上海的小青年”,“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日,姜还是老的辣,吃可口可乐和麦当劳长大的新生代上海人,无论是汽车、手表、相机这些充满阳刚的时尚的宏观认识,还是对跳舞、美食、追女人等软性时尚细节上,他们肯定不是老克勒们的对手。”[12]34
有意味的是,老克勒们的见识,都只是在声色享乐方面,与民族、国家有关的宏大叙事全然不在他们的关心范围之内,这是以 《长恨歌》为代表的怀旧作品人物的一个特点。怀旧作品所渲染的生活是与主流政治话语、宏大叙事相疏离的生活。所有的上海怀旧 “普遍将上海的失落归咎于一九四九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13],所以在怀旧作品中占主导地流的是王琦瑶、严师母之类被政治边缘化的那些人。这些人共同的特点是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与政治无关。他们 “不谈政治,也不谈是非”,只谈吃喝玩乐。他们有自己的消费场所,华山路上的 “红宝石”、华侨大楼等乃至一些今日新生代上海人眼睛都不会瞄一眼的上海昔日华都:国际饭店、上海大厦、和平饭店……,总之都是上海的高档娱乐场所。程乃珊笔下的老克勒们注重身份意识,没有为国为民的宏伟理想,只和上海有名有姓的人交际,面对底层人表情生硬。如医师小方,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受不了和地位低下的小市民打交道,竟然辞职自营其业。更值得深思的是,拉三轮车的老人竟然如此诉说对旧上海东风饭店的记忆:“从前这里是最高级的地方呢,上海最有钞票的人去开销的地方。那时候这里干净啊,出出进进的全都是头面人物啊,像现在,弄成这种瘪三腔调。你们是没有见过,上海从前兴旺的时候,你们的爷娘大概还拖鼻涕呢。”[14]104值得注意的是,说话的人是拉三轮车的底层老人啊!这个底层的三轮车夫对 “最有钞票的人”“头面人物”的景仰,并由此感叹现在的 “瘪三腔调”。我们从中看到的只有无可言说的奴性意识——而这些,竟然也是作家们津津乐道而宣扬的东西。
怀旧作品就是通过对西洋器具的赞叹、对精致之贵族生活的垂涎展现了一种中产阶级趣味。在怀旧作品中对奢华生活的艳羡、对拥有钱财阶层的尊敬与膜拜,正是迎合当前商业文化的一种复制行为。怀旧复制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个繁华的上海,正是应合了消费社会中广告语制造的对欲望的张扬、对奢华生活的追求、对上流社会生活的企盼的营销策略。对品味的张扬、对高档场所及物品的艳羡,在无形中增加了商品品牌的魅力,使商品在社会上的符号体系进一步强化——这些,都无形中增加了商品的暴利。怀旧作品所宣场的这一切都与底层的无经济基础的人无关,甚至面对底层人,展露出了强烈的优越感及蔑视倾向。怀旧作品以攀附权贵为荣,对民生疾苦不仅无视,而且冷酷厌恶。尤其在程乃珊的笔下,透露出严重的等级森严意识。在她的观念中,上海的西洋人及西化的成功人士最令人膜拜,是优雅、可追忆的浪漫情调,而内地人是没见识、不足挂齿的 “土老帽”,“上不得台盘”的上海底层人更是不值一哂。对成功洋派人士“好时光”的流逝的缅怀及哀叹,恨不得回到旧时贵族生活中去的情怀,是她的怀旧作品中一再抒写的主题。所以怀旧书写在某种程度上是 “隔绝了底层社会的利益代言角色”的一种行为,是典型的 “势利价值观”的体现。
四、怀旧文化语境中的 《长恨歌》
在这种语境中出现的 《长恨歌》也避免不了只是某个阶层的 “势力价值观”的体现。王安忆曾说,在 《长恨歌》里她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15]192,是 “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那么让我们来看看,王琦瑶是否真的能来代言上海现代到当代的历史呢?《长恨歌》中涉及到的城市历史从1940年代的民国时代一直延续到共和国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其中历经了抗日战争后的三年内战,建国后 “三反”“五反”及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文革”及改革开放,在这样巨大的历史大变革中,王琦瑶这样的弄堂女子都能作为社会上的另类女人而游离于政治话语之外,各种政治运动并不伤及王琦瑶的任何皮毛。不管外界时代风云如何变幻,各种宏大话语是如何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王琦瑶依然系心于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衣着装扮,与友人的麻将娱乐及围炉茶话,与情人的娓娓叙情。这群在主流话语看来不事产业、不求上进的浪荡子,其日常生活却过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难道这就是包容多种生活形态的上海的 “城市的故事”?很显然,如果这也算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的话,那只不过是被过滤的片面的历史。如果以王琦瑶作为上海的代言人,那不仅是剔除了精英知识分子的话语权,而且也 “隔绝了底层社会的利益代言角色”。不可否认的一点是,20世纪40年代后的上海城市发展,是离不开精英知识分子的技术投入及底层社会的力量创造的。那么,作为上海城市代言人的王琦瑶,真的能代表上海这座城市的 “气氛”以及 “城市的思想和精神”吗?
如果我们来分析王琦瑶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就会发现,按照传统的人物分析法,王琦瑶的性格特征是很模糊的,是被拼贴的、不完全的。王琦瑶似乎只是繁华上海的一个符号。她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是漂亮,而这种漂亮是具有某种艳情或者说风情的漂亮,在李主任眼中是 “坦白、率真、老实的风情”。让·波德里亚在 《消费社会》里,认为“最美的消费”是 “身体”,“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承载的内涵更沉重——这便是身体。……它彻底取代了灵魂。”[16]138王琦瑶的漂亮在其时以消费为主导的上海社会中,也成了被追逐的承载了某种意蕴的商品。20世纪40年代的人们追逐王琦瑶的漂亮,只是追逐某种商品的符号,与真正的人却很疏离。如女同学吴佩珍、蒋丽莉找她作朋友是因为她的漂亮能无形中提升自身的身份地位,却并没有真正的心灵方面的交流。程先生对她的追逐也是因为其漂亮的外壳,而不涉及精神及灵魂层面。而王琦瑶对自己的漂亮也是有价值期许的,她如此快地成为李主任的外室,与李主任的 “要人”身份密切关联,这种身份与她的漂亮是等值的。而李主任确实也把她的漂亮换算成金条。所以王琦瑶的外婆认为孙女的不幸根源于她的美貌,也因为身处在上海那样一个消费社会:“她想这孩子的头没有开好,没有开好头的缘故全在于一点,就是长得忒好了,长得好其实是骗人的,自己要不知道还好,几年一过,便蒙混过去了,可偏偏是在上海那地方,都是争着抢着告诉,惟恐你不知道的。所以,不仅是自己骗自己,还是齐打伙地骗你,让你以为花好月好,长聚不散”[17]78。王琦瑶因漂亮成了 《上海画报》上的沪上名媛,又成为上海小姐,这使她的身体进入公众视眼,成为大众娱乐的一部分而存在。
漂亮之外,王琦瑶最辉煌引以为傲的经历是见识并亲历过繁华场上的生活,她所有的知识资源、生活智慧都来源于此。王琦瑶最辉煌的时期是在20世纪40年代被选为 “上海小姐”并作为政界要人的情妇住进爱丽丝公寓的短短时间,而她一生的特色就定格在这一繁华时段。换言之,王琦瑶作为小说主人公的主要特点即她曾经是 “上海小姐”。原本为弄堂女儿的王琦瑶,作为上海贵族的短暂的繁华以及繁华中所沾染的那种风情,所蕴含着的那种气息,成为其日后生活的资本及一切的生命养分。她今后的命运无一不受其影响。从周围的人际交往,到生活情趣,到婚姻状况及最后的命运结局,无不是上海小姐的余音缭绕。在平安里,与她相识的严师母肯与王琦瑶为伍的原因是因为王琦瑶的繁华场上的气质,“她第一眼见王琦瑶,心中便暗暗惊讶,她想,这女人定是有些来历。王琦瑶一举一动,一衣一食,都在告诉她隐情,这隐情是繁华场上的。”[18]153而康明逊之所以被王琦瑶吸引,也是因为王琦瑶繁华场上遗留的风情,是那昔日情怀的“一点影,绰约不定,时隐时现”,能迎合他的繁华旧梦;“他在王琦瑶的素淡里,看见了极艳,这艳洇染了她周围的空气,云烟氤氲,他还在王琦瑶的素淡里看见了风情,也是洇染在空气中。”20世纪80年代年代老克勒对她的畸形爱恋,也归根于他对上海都市之 “光华和锦绣”的强烈怀想及爱恋。与其说周围人追逐的是王琦瑶,不如说追逐的是王琦瑶所代表的曾经繁华锦秀的贵族生活。除这一点繁华外,王琦瑶还有什么吸引人的魅力?尤其是人格上的魅力?从人格的丰富性来看,王琦瑶似乎什么也没有。她的世界 “非常小,是个女人的世界。是衣料和脂粉堆砌的,有光荣也是衣锦脂粉的光荣, 是大世界上空的浮云一般的东西”[19]162-163。作者津津乐道于她的吃穿,说这是 “一种精雕细作的人生的快乐。这种人生是螺蛳壳里的,还是井底之蛙式的。它不看远,只看近,把时间掰开揉碎了过的,是可以把短暂的人生延长”,小说借严师母的口表达对 “吃”“穿”的高论:
要说做人,最是体现在穿衣上的,它是做人的兴趣和精神,是最要紧的。萨沙就问:那么吃呢?严师母摇了一下头,说:吃是做人的里子,虽也是重要,却不是像面子那样,支撑起全局,作宣言一般,让人信服和器重的,当然,里子有它实惠的一面,是做人做给自己看,可是,假如完全不为别人看的做人,又有多少味道呢?[20]251
做人的 “兴趣和精神”是穿衣,而不是内心精神活的丰富自足,因为穿衣让人 “信服和器重”,展现了只重衣冠不重内容的海派拜物传统。而 “为别人看的做人”才有 “味道”,突显的是传统国民性所注重的一种 “面子”人生。小说中的王琦瑶为了这种面子的 “支撑”,几乎是把所有生命都用在上面。小说中写道,20世纪80年代的王琦瑶,“那心只是用在几件衣服上”,因为那衣服是 “她们的人生”。“她们对一件衣裙的剪裁缝制,细致入微到一个裥,一个针脚。她们对色泽的要求,也是严到千分之一毫的。在她们看起来随便的表面之下,其实是十万分的刻意,这就叫做天衣无缝”[21]。人过中年之后,王琦瑶依然只注重虚浮的面子人生,而没有更为丰富的心灵滋养及豁达的生命历炼,在她的生命中除熟知衣物的搭配、饭食的精细以及一些小市民式的人际交往心计外,她的生活和普通小市民没有什么两样,“王琦瑶是好莱坞培养大的一代人”[22]83。她的心灵养分似乎只局限于年轻时代所看过的好莱坞电影,之外,只有所谓的日常生活与生存智慧,尤其是没有书籍的养育——如果有的话,也只有娱乐画报。而且,她的这些日常生活知识只是20世纪40年代海派繁华场上的传承,而没有创新,包括她本人的人生,也是享乐大于创造。如果没有李主任给的金条,她很难维持她的面子人生。她的大部分人生都是与书本、与知识、与文化无缘。除漂亮及经历过上海的繁华外,王琦瑶似乎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作者津津乐道的是她日常生活的精细——衣饰方面的讲究及吃食层面的精细,却没有内心情感的丰富体验及形而上的生存智慧,没有文化的熏染只有繁华交际场上皮毛的拼贴——很难想象,如果这就是上海的 “城市的思想和精神”,那么上海还有它的发展吗?上海还有它的魅力所在吗?
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在作者的眼中,代表的是底层人永远所无法企及的 “真正的华丽”,“她就像一个摆设,一幅壁上的画,装点了客厅。这摆设和画,是沉稳的色调,酱黄底的,是真正的华丽,褪色不褪本。其余一切,均是浮光掠影。”[23]294这个漂亮的躯壳,在作者眼中竟然是上海社会超越于一切的本色,其余所有各色人等 “均是浮光掠影”,似乎除了繁华,其他一切都不值得一提。这样的言说,很难说不是一种势利价值观的体现。
王安忆涉及怀旧小说中的诸种人物,也都如王琦瑶一样,作者的突出特征大多是:见识过20世纪三十四年代的繁华上海,熟谙洋场社会的各种娱乐消遣方式及生存法则,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衣着、吃食方面的讲究。如在 《好婆与李同志》中的好婆,只是一个曾经在富贵人家见识过繁华生活的佣人,但其面对南下进城干部李同志时,表现出极大的优越感。这些优越感在于她懂得穿衣方面的各种搭配,熟悉精美饭菜的各种做法,及人际交往方面的分寸——除此之外,好婆作为人的其他人格特征很模糊,空洞、空虚而又乏味的。除炫耀自己通达繁华上海的生存法则,其他的日子,好婆 “是非常无聊的”。小说中这样写闲下来的她,“心里空落落的,想着:过日子是多么没有意思啊!”好婆的人格构成只体现在对繁华上海之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熟知上,除此之外,她似乎没有其他方面的知识或者见识。所以这样的人物与王琦瑶一样,只是繁华上海的一个道具而已,而难真正深入占据上海的真髓所在。
[1][2][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3]张清华.我们时代的中产阶级趣味[J].南方文坛,2006(2).
[4]王唯铭.欲望的城市[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
[5]杜英.对于1949年前后上海的想象与叙述——以90年代的上海创作为例[J].文艺争鸣,2005(2).
[6][8][18]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
[7]王安忆.“文革”轶事[M]//王安忆自选集之三.香港的情与爱.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9][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10][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种族与历史·种族与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1][14]陈丹燕.上海的风花雪月[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12]程乃珊.上海探戈[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34.
[13]朱晶,旷新年.九十年代的“上海怀旧”[J].读书,2010(4).
[15]王安忆.重建象牙塔[M].刘成富,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16][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7][19][20][21][22]王安忆.长恨歌[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
[责任编辑:庆 来]
I206.7
A
1674-3652(2014)06-0043-06
2014-08-22
刘永丽,女,山东烟台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都市文学研究。
——笔画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