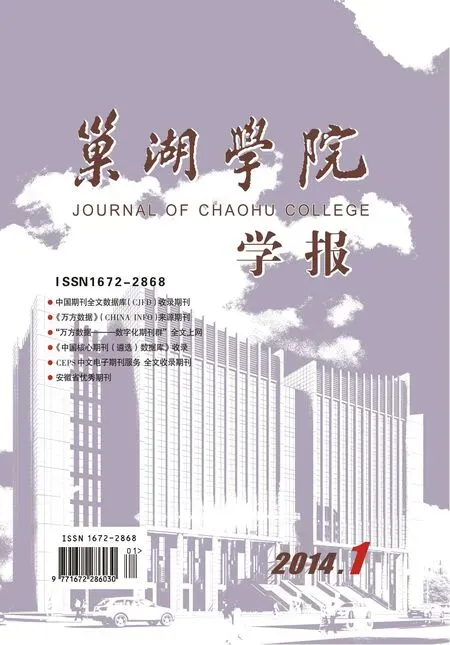《恋爱中的女人》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祖华萍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1 引言
D.H.劳伦斯是20世纪英国文坛上一位备受争议的作家,他的部分作品曾因大胆直白的性爱描写而一度被禁,他本人也受到众多卫道士的强烈批判。然而,劳伦斯在作品中对人物心灵深处的困惑与挣扎的刻画以及感人的艺术描写也使其在后世受到人们的追捧。他的作品《恋爱中的女人》以英国的一个工业化小镇为背景,描述了姐妹二人——厄秀拉与戈珍不同的爱情经历与心理体验。在这部小说中,劳伦斯通过展现工业化小镇的肮脏混乱以及女主人公厄秀拉的情感经历成功地揭示了自然与工业文明、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二元对立,在批判工业文明对自然的残酷掠夺、男性对女性的冷漠压抑的同时,也试图建立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两性关系,文本中体现出来的生态意识与女性意识,与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不谋而合。本文试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通过发掘人类对自然的统治与男性对女性的压抑之间的联系,揭示劳伦斯在文本中体现出的超前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2 生态女性主义与劳伦斯
生态女性主义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是第三次女权运动浪潮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是女性主义运动和生态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由法国作家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首次提出。她在其著作《女权主义·毁灭》中指出:“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1]这一观点力图寻找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相似性,特别是男权社会对待二者的态度的相似性,它为女性主义批判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环境危机来源于人类对理性及现代科技的盲目崇拜,对于未知领域的不断探索与发现,使人们相信自己已拥有控制自然的绝对权力,进而无所顾忌地对自然施暴。和自然一样,女性在过去的历史中也曾遭受一系列的压迫,而对自然和女性的压迫都同时来自于男权社会及父权统治,“特别是男性身上那种征服、主宰、压迫和剥削他们所痛恨且比他们弱小存在物的天性。”[2]所以,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者认为,只有推翻人类对于自然的残暴统治,恢复自然的主体性与本来面目,才能真正取消男性对于女性的压抑剥削。要使女性重获自由,必须同时还自然于本真。
文学大师D.H.劳伦斯出生于一个英国煤矿工人的家庭,儿时的生活经历使他切身体会到现代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变革给自然和人类(特别是女性)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和苦难。因而劳伦斯在其诸多作品中都强烈地抨击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展现工业文明与自然对立的同时,也表达了自身对自然生态的关切之情。20世纪初,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行,女权运动在英国得到广泛的开展。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劳伦斯深受其影响,并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在其随后的小说创作中,劳伦斯试图塑造追求独立自由与思想解放的新女性形象,并强调两性关系的和谐。这一创作理念在《虹》和《恋爱中的女人》等著作中均有体现。劳伦斯的大多数作品都赞美了原生态自然的美好与生命力,呼吁人们关爱自然,实现工业文明与自然的和谐。与此同时,他又极为关注女性的社会地位与生活现状,努力塑造追求自我价值的新女性形象。这些都强有力地展现了劳伦斯超前的生态女性意识。
3 女性化的自然与工业文明
自然作为有机体的观念自古便有,以有生命的、女性的大地为中心的有机理论认为,自然“尤其是地球与一位养育众生的母亲相等同:她是一位仁慈、善良的女性”。[3]在人类生活早期,人类的蒙昧无知使其极度敬畏变化无常的自然。古希腊人将自然誉为“大地之母”盖娅,她控制万物生长、赐予人类生活所需,同时又暴虐无常,难以捉摸。此时,自然是凌驾于人之上的神明,人类不得不服从她的统治,屈服于她的力量。人对自然的崇拜顺从使二者处于一种原生态的和谐之中。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人们更加了解自然、掌握自然,人们逐渐改变对于自然的原始认知,开始形成人类中心主义观,这一观念促使人们渴求摆脱自然的统治,甚至要求“控制自然”。工业文明的发展使人类更加狂妄自大,将自己视为无所不能的上帝,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一种主仆关系,人成为自然的主人,对其肆意掠取。“征服和统治自然成为现代世界的核心观念,自然作为女性的神圣性、高尚性渐渐被机器粉碎。”[2]
《恋爱中的女人》以19世纪的英国为背景,此时欧洲工业革命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工业化进程不断向英国的各个城镇与乡村推进,而这一过程对原始的自然环境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在小说伊始,劳伦斯就向读者描摹了一幅受工业化文明侵蚀的破败的乡村景象:“姐妹俩沿着一条黑色小道穿过了黑暗肮脏的田野。左边是散落着一座座煤矿的山谷,山谷两面的山坡上是小麦田和森林,远远望去一片黝黑,就像蒙着一块黑纱似的。灰色的烟柱徐徐升起在黑色的空气中。”米德兰小镇原本是一座风景如画、纯净安宁的小镇,而科技的进步与工业的发展使人们对自然的征服欲望不断膨胀,而人性中本存的贪欲更使得人类无视生态失衡的恶果、疯狂地攫取自然资源以满足一己私利。劳伦斯借主人公戈珍之口对此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这儿的农村像在地狱中一样”,“这儿的人全是些吃尸鬼,这儿什么东西都沾着鬼气。全是真实世界的鬼影,是鬼影、食尸鬼,全是些肮脏、龌龊的东西”。人们对于自然的无度索取使得小镇的生态环境每况愈下,肮脏与混乱成为它的代名词。然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却并未意识到这一可怖的变化,只是一味沉浸在占有与掠夺的狂喜之中。小说中的另一位主人公杰拉德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典型代表,是英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先锋军。“他的意志就是要物质服从他的目的,在与自然条件的抗争中实现自己的愿望,获取利益。”[4]在物欲的不断诱惑下,他无视生态平衡,一味地采取新技术和工业化机器疯狂地开采地下煤矿。在他看来,“人的意志是决定的因素,人是土地狡猾的主宰”,矿工们是他征服自然的工具,而他是机器的上帝。通过对杰拉德这一形象的刻画,劳伦斯向读者展现了工业文明的发展使整个社会物欲横流,人们肆无忌惮地掠夺自然资源,完全忽视了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失去了自身原有的道德责任感。在工业巨轮的碾压下,不堪重负的自然变得千疮百孔,失去了往日的勃勃生机。自然母亲这一隐喻的形象也随之消亡,完全沦为工业文明的牺牲品。这些形象描述,表达了劳伦斯对于工业文明的强烈谴责,呼吁人们关爱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4 自然化的女性与男权统治
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者们始终相信自然与女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系。“大地之母”的理论展现了女性与自然的相连性,这种相连性“建构了一套规范女性的‘自然法则’,以自然现象来界定女性的职责”。[5]从古典时期开始,“妇女被看作隶属于自然,而男人则隶属于文明。”[6]自然与文明的对立必然导致女性与男性的对立,在男性眼中,女性和自然一样,她们情感细腻、柔弱被动,却又无序混乱、具有野性,所以她们需要进步、主动、理性的男性的指引和征服。因而生态女权主义认为,在父权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和处境与自然极其相似,她们始终处于弱势,总是受到男性的压迫和统治,是父权社会中被边缘化的他者,处于“第二性”的地位。而女性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困境,继而奋起反抗,敢于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与权力。
在小说《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力求塑造渴望自由独立、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新女性形象,而女主人公厄秀拉便是典型的代表。厄秀拉热爱自然,渴望纯净安宁的世界,她对给自然带来无尽灾难的人类工业文明心存厌恶,“她喜欢大草原中的马和牛,它们各个儿我行我素,很有魔力”,“她怨恨人类,‘人’这个词所表达的含义令她感到厌恶。”在杰拉德家举办的水上聚会中,厄秀拉与妹妹戈珍独自划着小船来到一处远离喧嚣的小溪口。这里安宁纯净,有着大片枝叶繁茂的树丛,与米德兰小镇的肮脏混乱形成鲜明对比。在如此静谧和谐的环境中,厄秀拉将自己完全投入自然母亲的怀抱,她赤着身子在树林里奔跑,并感叹“自由是多么美妙啊”。此刻,厄秀拉与自然完全融为一体,全身心地接受着自然的赐予与精神洗礼。
“生态女性主义伦理主张,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内在联系的、相辅相成的和相互依存的伙伴关系。”[2]因此处于父权社会统治下的厄秀拉并不甘于自己边缘化的缄默地位。她渴望独立自由、希望得到尊重。为此她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以坚韧的毅力和勇气与整个男权社会相抗衡。当伯金饲养的公猫米诺欺侮一只野母猫时,伯金对此大加赞扬,认为米诺保持了男性的威严与优势地位。而厄秀拉却对此极为恼怒,她直言:“米诺,我不喜欢你,你想所有的男人一样霸道”,“什么男性的优越!统统都是鬼话!没人会理会这套鬼话的。”厄秀拉在此直接否定了父权社会所标榜的男性至高无上的地位,渴望两性平等。在《月色朦胧》一章中,有这样一个经典场景:伯金“弯下腰去拾起一块石头,用力把石头扔向湖水中。厄秀拉看到明亮的月亮随着水的波动在跳动着、荡漾着,月亮在湖中已经变形了”。在劳伦斯的很多作品中,月亮这一意象经常出现,有学者认为 “月亮在劳伦斯的作品中……是一种女权胜利的象征”。[7]因而,在这段描写中,月亮实际上是厄秀拉女权主义的象征,伯金将石头狠狠地扔向月亮,其实就是在发泄他对厄秀拉女性权威的不满,因为她的自我、独立使伯金感到自己的男性权威受到了损害和挑战,他在爱情和婚姻中的主动权被女性剥夺。但是在他一次次将石头扔向月亮之后,“那生动、白亮的月亮在震颤……这闪着白光的躯体在蠕动、在挣扎,就是没有破碎。它似乎盲目地极力缩紧全身。它的光芒愈来愈强烈,用以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表明它是不可侵犯的。”[8]这暗示了厄秀拉不惧男权挑战和压迫的勇敢。而她的独立果敢也使得伯金对其更加钦慕。劳伦斯曾在多数作品中试图建构和谐的两性关系,而《恋爱中的女人》中伯金与厄秀拉的情感历程便是这种两性关系的最佳体现,这也与生态女性主义一直强调的和谐的两性世界观不谋而合。
5 结语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存在一种密不可分的纽带关系,揭示男权社会统治与其所倡导的工业文明给女性和自然带来极大的苦难和不幸,并呼吁女性实现与自然的融合,在反抗男性权威的同时建立和谐的两性关系。劳伦斯在《恋爱中的女人》这部小说中强烈谴责了工业文明给自然生态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赞颂了原始自然的安宁纯美;同时,他也赞赏女性敢于反抗男权,争取独立自由的勇气,并为建立和谐的两性关系作出努力。他在文中的诸多观点与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相契合,表明与同时代作家相比,他具有超前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1] 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艾晓明,朱坤领,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70.
[2] 袁玲红.生态女性主义伦理形态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0,160,190.
[3] 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M].吴国盛,吴小英,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2.
[4] 余巧云.从生态批评视角解读《恋爱中的女人》[A].聂珍钊,陈红主编.2008文学与环境武汉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404.
[5] 罗婷,谢鹏.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J].求索,2004,(4):176.
[6] 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67.
[7] 冯季庆.劳伦斯评传[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148.
[8] (英)D.H.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