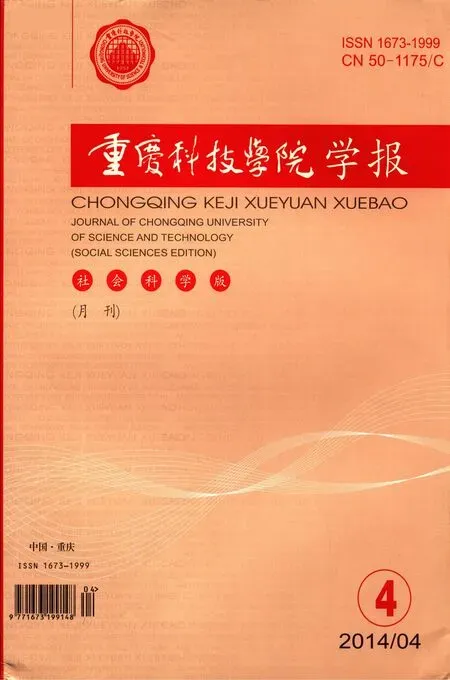《绿阴山强盗》的隐喻解读
杜荣芳,李泽坤
George Lakoff和Mark 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里指出:“隐喻遍存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只是在语言中,也表现在我们的思维与行动中。就我们的思想与行动而言,我们通常的概念系统在本质上是隐喻性的。”[1]3他们认为,每一个概念都是一个独立的心智领域,里面包含许多概念实体。在两个概念系统间,彼此内含的概念实体存在一种本质上的对应关系。因此,在二领域模式之下,隐喻是藉由来源域来概念化目标域的方式。简言之,隐喻是“在概念系统中的跨领域映射”[2]203。由来源域投射到目标域是具象化的图景式的转换,无论来源域,还是目标域,都是形象化的、图景式的,是与表达的环境融合在一起的人类的具体生动的生活经验,是一种有生命的意象[3]。运用隐喻理论细读文本,深入到所指的目标域,能更深刻地理解作品中的时间、场景、事件等隐含的更深层的寓意,把握作品的主题思想,领会作家的创作意图。
约翰·契弗的短篇小说《绿阴山强盗》讲述了郊区的中产阶级主人公赫克在现实生活中陷入困顿,经过艰难的思想挣扎后,他通过游离的方式——黑夜里的盗窃来摆脱困境,以保持自己在郊区的地位,但在他似乎毫无退路的时刻,雨水浸润下的顿悟和意外的工作机会又让他戏剧性地回归,恢复了其在郊区的正常生活。小说中主人公活动的时间、思维中出现的意象、活动场景都具有隐喻意义。从隐喻的角度来探讨该小说,能更深刻地揭示赫克在生活困顿、梦幻游离和戏剧性回归过程中的真实,进而表明赫克焦虑的必然性和夜幕下回归的虚幻性,同时也显示作家本人对郊区爱恨交错的情感。
一、黑夜里的自白隐喻:现实生活的困顿
《绿阴山强盗》中,黑夜是主人公活动的主要时间。小说以主人公在黑夜里的自白开始,在黑夜中回归结束。黑夜在小说中具有隐喻意义,起着掩饰的作用,让主人公能够“赤条条地在黑夜里自白”[4]253,揭示目前的真实想法和生活现状。
首先,主人公黑夜里的自白揭示出自己身处郊区的满足感。小说一开始,赫克就说明他的年龄、身高和体重,介绍他的出生、接受洗礼、学生时代的生活以及恋爱和婚姻。他有四个孩子,住在一个叫绿阴山的郊区,有漂亮的房子和花园,还有一个屋外烤肉的地方。与妻子、孩子在一起时,他总是“感到兴奋”。这种满足感为赫克后来不惜以盗窃的极端方式维持即将失去的郊区生活埋下了伏笔。
其次,黑夜里的自白也道出了赫克的焦虑和困顿。赫克在工作场域中面临男性气质丧失的危机。他在一家聚闪锌膜包装制造公司工作,“公司实行家长式统治”[4]253,老板“什么事都插手”“在他面前,我循规蹈矩,就好像是他亲手用泥巴捏出了我,并把生命之火吹进我的身体。他是那种需要有人替他出面的专制君主”[4]253。 在公司工作,赫克没有自尊,常处于压抑状态,生活得没有自主性,缺乏男性气概。
同时,赫克透露了自己失业后的危机。赫克的上司巴克纳姆由于酗酒,老板叫赫克去巴克纳姆的公寓解雇他,但赫克心存善心未能完成任务,结果是赫克自己被老板算账。当老板找他算账时,赫克认为“如果我本来的命运是做一个俄国芭蕾舞演员,或者去制造巧夺天工的珠宝首饰……就是这样,我也绝不会碰上比我在聚闪锌公司所遇到的男男女女更古怪的人了。我决定自找出路”[4]254。这里赫克列出的所有工作,都具有阴性化的特征,但他仍认为比目前的工作更有吸引力。但读者却清楚地看到,离开公司,他可能面临的更是毫无男性气质可言的工作。无论是留在公司还是另谋出路,都面临着男性主体地位、男性气质的丧失,由此可以体味赫克难以言说的困顿。
在夜色降临以后,在一个没有光的世界里,没有他人的干扰下,人才能脱下白天防御外界的外衣,赤裸面对自己的内心。因此,人内心深处最柔弱、最真实的部分会暴露出来。此刻,赫克在黑夜里自白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他对郊区的满足和对自身的焦虑是真切的,表明其对郊区深切的依恋和害怕失去郊区的恐惧。
二、思维中的意象隐喻:梦幻游离的催化剂
赫克常常陷入痛苦的思索,忧虑家庭的经济和情感上的困顿,愤懑郊区生活中他人的奢华,其思维中出现的意象具有深刻的隐喻意义,成为赫克梦幻游离的催化剂。
在家庭和社区生活中,赫克都试图维护自己作为男性的主体性。小时候母亲就教他“不要谈钱”,妻子克里斯蒂娜是个对金钱的合理使用毫无概念的女性,所以他没有告诉妻子自己失业、银行已经透支的事实,而是独自承担焦虑和折磨。他重新创业,却又以失败告终。由于顾及作为男子汉的尊严,赫克不能向朋友们求援。忧困交加,半夜他梦见了彩色聚闪锌膜包装的面包和与自己疏远了的母亲。梦醒后咳嗽,他甚至想到了自己可能会死于支气管癌。
面包、母亲和咳嗽在这里都具有隐喻的功能。聚闪锌膜包装的面包喻指财富或经济地位,表明赫克目前入不敷出的境况和重拾失去的工作和财富的热望。赫克以前在聚闪锌制造厂工作,工厂给他提供了足够的收入以使他在郊区过着体面的生活。失去工作和独立创业的失败是他焦虑的根源。梦中的聚闪锌膜包装的面包以广告的形式出现,如果他有足够的金钱,面包就可以属于他。对母亲的怀想则反映出他对亲情和田园牧歌式的自由欢愉生活的渴求和梦想。一直以来由于母亲反对他的婚事,母子关系紧张,几乎没有来往。而此刻,他期望“纠正这种现象,在更淳朴、更有人情味的基础上重建与母亲的全部关系”“用一种阿卡狄亚式的感情把这一切重新做起”[4]257。赫克对咳嗽的臆想则喻指他对健康、疾病、死亡等方面的思考。对生命的看重和对死亡的恐惧更坚定了赫克想要迅速获取财富的决心,思维中的意象促使赫克决定采取游离的方式解决困境。
另一方面,在赫克眼中郊区人的富有、生活中的挥霍也成为他游离的驱动力。小说特别描述了邻居沃伯顿夫妇的富有,他们一家“总是在花钱,这也是人们和他们谈话的永恒主题”[4]255。小说也描述了沃伯顿家的房子,“他们前厅的地板是从里兹来的黑白两色大理石,位于海洋岛有凉台的屋子正在装御寒设施”[4]255。 在此,房子具有深刻的隐喻意义。 19 世纪后半期以来的工业化社会中,“私有、以家庭为中心、具有抚育功能的理想家园是中产阶级身份和自我定位的核心”。郊区人拥有的房屋成为消费繁荣和个人成就的重要能指符号。郊区房屋所有权给白人居住者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上的优势。“郊区总体上象征着在自己的房子里的美好的生活、生活的梦想和幸福的梦想”[5]。赫克非常看重自己位于郊区的房子,担心因失业而失去房子。沃伯顿家的富有诱惑着他,沃伯顿的房子的豪华刺激着他,自己的郊区理想催促着他,同时,黑夜也给他以掩护,为其脱轨游离助长了勇气。经过一系列的梦幻、怀旧、恐惧和担忧后,他开始铤而走险,悄悄潜入沃伯顿家,窃取了主人的钱包。
三、回归中的场景隐喻:夜幕下回归的虚幻性
“成功的盗窃者是使自己融入令人尊敬的郊区生活的人。”[6]成功盗窃、表面融入了郊区生活的赫克却在自我体验、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中经受着更大的折磨和良心的谴责。他对新闻中有关盗窃的报道倍加关注,而关注之后总会面对自己是“一个普通的贼和骗子的事实”[4]259。他的良心受到强烈的自我谴责,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4]259,还伴随着身体的痉挛。他有时甚至需要“用手按住左颊,压住脸上的抽搐”[4]262。 在家庭中,面对不明真相的妻子和孩子们精心为他准备的生日庆典,赫克表现得不近人情,导致家庭矛盾。在社区生活中也遭遇尴尬。在星期日早上的圣餐仪式上,赫克被膝垫下的老鼠分心以至错过了圣餐。老鼠穿过教堂的膝垫喻指堕落、混乱已侵入中产阶级生活所象征的文雅与秩序之中。
赫克在夜色下的盗窃僭越了白天郊区所象征的秩序,这种僭越让他备受折磨,也暗示赫克回归正常的郊区生活的必然性。接下来的两次游离,让他最终毅然回归。他去梅特兰家盗窃,却误入梅特兰的园丁的卧室,结果空手而归。回家后,他想着自己“命途多舛的一生”和“绿阴山在茫茫夜色中和在光天化日之下是多么不同”[4]268。 这里的夜色具有掩护功能,喻指黑暗甚至罪恶,与白天的郊区呈现出的秩序和稳定形成对照。最后,在去皮特家的路上,赫克想起了自己出生的偶然性和坎坷的命运。突然,他感觉到“一片猛烈的骚动声,好像一股风吹过一个火堆”[4]268。 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声响,直到雨水滴落到”他的“手上和脸上”[4]268。 他蓦然醒悟:“如果我愿意采取一些办法,我是能够摆脱困境的。我还没有到不能自拔的境地。我之所以生活在世界上是出于自己的选择。”[4]268他“转身走开”,回家进入了梦乡。“风、火与水在圣经意象中与启示的出现紧密相联。这里,启示性的水与火传达的不是毁灭而是新生与笑声。”[7]雨水喻指新生,火喻指笑声。带着新生的喜悦,赫克混沌的世界恢复了秩序。
新生后的赫克接到了巴克纳姆的电话,告诉他老板命在垂危,希望他回去工作。赫克的困境就这样戏剧性地解脱了。故事最终又回到了黑夜。赫克拿到预支的工资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把钱如数放回了沃伯顿的房间里,在返回的路上,一辆警车停在了他的旁边。出现了下面的有趣一幕:一位我认识的巡警摇下车窗问道:“赫克先生,夜里这个时候,你在外面干什么呀?”“我在遛狗”我笑着说。周围看不见一只狗,但他们根本没看。“过来,托比!过来,托比!过来,托比!好狗!”我喊道。然后我走开了,在夜色中愉快地吹着口哨[4]269。
此情形暗示赫克对郊区秩序的妥协和对自我的重新确认。警察是秩序的隐喻,赫克只能在郊区规范、合法的界限内让自己的奇特行径得以表达。赫克刻意表现出来的一切行径与郊区的行为规范毫无差异之处,所以郊区居民、警察都看不到他任何的僭越。但读者却明白,赫克不可能回到先前的生活中去,他的内心无法真正忘记自己的游离和僭越。但是,夜色掩盖了这种回归的不真实性,夜色下的回归实则隐喻了赫克回归的虚幻性。
四、结语
“契弗笔下的郊区是一个蕴含病症和神经质威胁的不稳定之地,但他又赋予郊区虽有争议但本质上值得颂扬的身份。”在郊区美好、优裕的家庭和公众生活中,也存在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小说在消解郊区的稳定感和安全感的同时,又肯定其秩序。“契弗经常建构焦虑和挫折,但其纯净的结尾常常使得对郊区的批评显得较为温和。”[8]在《绿阴山强盗》中,作家借用黑夜的多重隐喻,反映主人公的游离和挣扎,并为其设置归途,肯定了个体遵从郊区象征秩序的能力,显示了作家对郊区人的理解和为郊区的辩护。
[1]Lakoff,George,Johnson,Mark.Metaphorswe live by[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2]Lakoff,George.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m]//Ortony A.Metaphor and Thought:2nd e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3]陆燕.《麦田里的守望者》的隐喻研究[J].世界文学评论,2011(1).
[4]Cheever John.The Housebreaker of Shady Hill[M]//The Stories of John Cheever.New Jersey:American Book-Straford Press,Inc.,Saddle Brook,1978.
[5]Jurca Catherine.White Diaspora:The Suburb and the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Novel[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5-6.
[6]Wilhite Keith.John Cheever’s Shady Hill,or: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suburbs[J].Studies in American Fiction.2006,34(2).
[7]W.Hunt,George.John Cheever:The Hobgoblin Company of Love.William B.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1983:272.
[8]Anderson Lars.Burglary in Shady Hill and Sarsaparilla:the politics of conformity in White and Cheever[J].Australian Literary Studies,2006,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