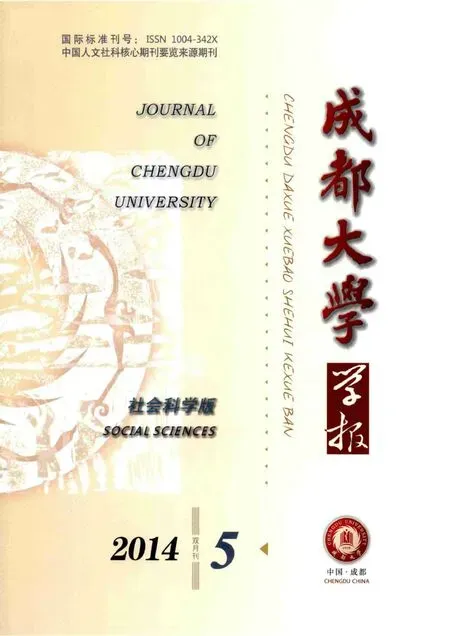羌年祭祀仪式与艺术*——以汶川县绵虒镇羌锋村为例
叶 健
(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陕西咸阳712082)
羌族是中国56个民族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最早的成形文字甲骨文有古羌人的记载,在武乙时期,卜辞说:“甲辰,贞,来甲寅,又伐上甲羌五,卯牛。”《说文解字》曰:“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羌民族分布在四川省、陕西省、甘肃省、贵州省,核心区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县、理县、北川县。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共有309,576人。
一 汶川县绵虒镇羌锋村概况
羌锋村正是羌族核心区域汶川县绵虒镇的一个小村寨,被誉为“西羌第一村”。它位于岷江西岸,簇头沟旁,都汶高速公路出口处。南离成都126公里,北距县城威州22公里,与绵虒镇隔河相望,距离绵虒镇2公里。寨的周围:东面与岷江对岸的高店村相望,北紧连高东山、和平村。南与小坪寨毗连(藏族),西与克约寨接壤,一条溪水从寨中穿过汇入岷江。寨子四周的高山:东面为东山刳儿坪,南面有马里山,西面为终年积雪的雪隆包山(海拨5313米),是全寨祟敬和祭祀的最高神山,北面为高东山。[1]
羌锋村,现有村民187户、784人,既是一个以羌族为主的民族聚居村,又是完好保存羌语和家神崇拜的民俗村寨。现今,它还较为完整地保留着古朴的羌式石砌民居、传统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精美的挑花刺绣以及生产、生活方式。不仅如此,羌锋村更是藏羌文化走廊的一处重要节点。寨内有释比、竹口弦、羌绣、羌房建造、推杆竞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二十余人。1996年,中国文化部授予羌锋村“中国民间羌绣之乡”的称号,1997年,费孝通先生为其题写了“西羌第一村”字样。[1]
二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羌年
羌年,羌语称“日美吉”,即欢乐吉祥的节日,现称“尔玛节”,是羌族最具民族特色的节日,也是羌民族一年之中最为隆重的日子。羌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一样,有过春节的习俗,他们称其为过大年。如此一来,羌族便将过羌年称为“过小年”。以前,羌年的时间并非一致,一些地方在正月举行羌年庆典,一些地方在八月份举行,还有一些地方在十月份举行。对于羌锋村而言,过去是每年八月份举行羌年。十月初一进行羌年,是北部羌区的习俗。后来,不论羌区何地,当地政府统一将羌年定在农历十月初一举行。于是,羌锋村的羌年庆典也改为农历十月初一。
为什么羌年是农历十月初一的这一天?它是有一定依据的,相传秦汉以前已经形成。羌族没有文字,只能靠口耳相传本民族的风俗习惯。羌年的习俗,源于羌族的史诗《木姐珠》。据说阿巴木比塔的小女儿木姐珠,喜欢上凡间羌族年轻男子斗安珠,并执意下嫁斗安珠。下界时,她的父母将树种、粮种和牲畜作为其嫁妆。木姐珠下凡后,很快繁衍了人类,树种变成了森林,粮食连年丰收,牛羊肥壮。木姐珠感念父母的恩德,把丰收的硕果摆在原野,向天祈祷,这天恰好是十月初一。此后,年年如是,最后演变成为今天的羌年。上述是羌年来源的一种说法。也有说,古羌人以羊角卜推算时日计羌年,秦汉以前羌人使用的太阳历(夏历),农历十月是夏历的一年之始,喻义辞旧迎新。[2]羌年的大型祭祀仪式大概可分为三个内容,即还报天愿、祝祭禳灾降福和庆吉,分家庭祭祀和集体祭祀及节日欢庆活动。[3]
羌年期间,正逢粮食丰收完结之际,其宴会亦称“收成酒”。这天羌族村寨节日气氛浓郁,男女老少身穿新装,不出远门,团聚在家中蒸“瓦达”吃,即一种用荞面做成半月形肉馅大蒸饺,有的则用面粉做成形状各异的祭品,最为常见的是牛、羊、鸡等形状的祭品,用此祭拜祖先和天神。喝砸酒、吃猪膘肉、跳欢快的“萨朗”也是必不可少的项目。过年期间,禁止一切劳作,更不允许杀生打猎。传说天神“木比塔”曾点化羌人过年,所做的食品要着上颜色,且将这些物品供奉于火塘之上,或带到山上在集体载歌载舞后分而食之,或互相馈赠、分享。[4]
解放前,羌族地区有着各种集会,正月上九会、龙灯会、二月观音会、三月娘娘会、五月防虫会、六月龙王会、十月牛王会或者羌年等等,其中以羌年、祭山会、封山会最为重要。[5]不过解放之后,许多集会被看作是封建迷信活动,故而被禁止举行。直至改革开放以后,羌族的一些集会节日才得以恢复。1987年,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正式成立,是年恢复羌年。1988年汶川、理县、茂县、北川四县在凤仪镇举行了第一个羌年庆祝会。10月,阿坝州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羌年放假的通知》,羌年期间全州放假两天。2006年,羌年入选四川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又被列为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10月,在第四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府间委员会上,羌年成为《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6]
三 羌年祭祀仪式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之于国家乃是头等大事。又《礼记·祭法》曰:“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毋庸置疑,祭祀对于羌民族同样重要,它在羌族社会中地位十分显著,且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诚如《北史》卷九十七《西域》载:古羌人“……岁初以人祭,或用猕猴,祭毕,入山视之……”又,《汶川县志》卷五《风土》称:“……巫师常击鼓迎神,杀羔羊以祭天地……”每年农历十月初一的羌年,不论是祭祀祖先、羌民族的神灵,还是降福禳灾,都必须举行祭祀仪式。
“仪式是由社会来规范化的、重复的象征行为……仪式行为带有正式的品质,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标准化的系列,并常常在自身也带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特定的地点和时间被上演。”[7]换言之,仪式就是对一个特殊庆典的规定。羌年作为一种庆典,有关仪式的举行是被规定的,无论是祭祀仪式的时间、地点、物品等,皆需要精心地准备。羌锋村羌年祭祀仪式,分为家庭祭祀和集体祭祀。家庭祭祀是在农历九月二十九日的晚上,集体祭祀则是在农历九月二十九日的晚上和农历十月初一清晨。
(一)仪式准备
1.祭祀仪式空间的准备
家庭祭祀空间主要有三个部分,堂屋大门口、神龛和火塘。农历九月二十八日,羌锋村的村民把房屋的里里外外、前前后后打扫干净,在大门张贴门神,大门的两边贴上对联。然后,布置神龛。神龛上方有三个代表神灵的方格空间,神龛最上方换贴新的横批,诸如“福禄寿喜”、“国泰民安”字样。每个方格空间两边换贴新的对联,并在神龛两侧换贴新的图画,每边分别五张,代表羌族的五位最高神灵。神龛中央摆放一个大木制方格香炉,神龛两侧上方各放置两个小木制方格香炉。另外,堂屋的火塘村民也会清理得干干净净。
集体祭祀空间大致分为五个部分,即村寨通往祭祀平台的道路、祭祀平台(一块40多平方米的平地)、山神庙、神树林、山神庙左边三米处的小空地。集体祭祀之前,村民主要的准备工作有为村寨通往祭祀平台的道路两边“挂红”,布置祭祀平台,在山神庙上方檐口“挂红”,并在其正前方摆放一大一小的木制方格香炉,羌年前三天举行“封山会”、禁止进入神树林。再有,在山神庙左边的三米处小空地插上代表寨首神、山神、土地神、天神、太阳神的白旗,同时在进入祭祀平台的台阶处插上两只白旗,一公一母。白旗,绵篪镇羌语称“厄”,大旗叫“厄巴”,小旗叫“厄卓卓”;公旗称“厄比”,母旗称“厄媔”。
2 祭祀仪式物品的准备
家庭祭祀所需的物品有长条凳一个、托盘一个、盛有玉米的木制方格香炉一个、香蜡纸钱若干、饭碗一个、盘子两个、酒杯两只、猪膘肉一块、蒸烧白一块、白酒一瓶、鞭炮一挂、筷子一双。
集体祭祀所需的物品有木制方格香炉一个、香蜡纸钱若干、九只白旗、神羊一只、猪一头、鸡三只、白酒、柴火若干、神树枝、面粉做成的面塑(太阳馍馍、月亮馍馍)。另一方面,集体祭祀由释比王治升及其助手完成,准备的法器有羊皮褂或法衣、猴头帽、铜铃①、羊皮鼓②、猴头杖③、释比单刀④。相较于传统羌年的集体祭祀而言,羌锋村的祭祀牺牲与其他地方有所差异。过去,汶川县阿尔巴朵的白家朵寨羌年祭祀仪式准备的祭祀牺牲是五只神羊,猪不在祭祀牺牲品之列。猪成为祭祀牺牲品是羌锋村羌年祭祀的独特现象。依据历史传统,祭祀神羊原则是纯白色或纯黑色,不得有杂毛。这次羌年,羌锋村只准备了一只神羊,且颜色不纯、黑白两色相间。羌锋村出现这样的现象,皆因它地处羌区的最东部,紧邻汉族地区,与汉族交流密切,深受汉族祭祀文化的影响。故而,学习了汉族将猪作为祭祀牺牲的习惯。
羌年的第一天早晨,集体祭祀前后,村寨每家每户的主人都会到山神庙前各自祭祀。村民所带的物品主要有香蜡纸钱、白酒、太阳馍馍或是月亮馍馍。
(二)仪式过程
1.家庭祭祀仪式——以村民GYB⑤家的家庭祭祀为例
2013年11月2日(农历九月二十九日)晚上,GYB家举行了家庭祭祀仪式。首先,GYB的父亲G大爷点燃六根香,将其放置在托盘上。紧接下来,G大爷点燃纸钱,唱着《获芭经》,把纸钱在大门门框两侧四角绕了一圈,一则希望驱除秽气,带来新年的吉祥;二则让门神前来领受主人家孝敬的纸钱。纸钱最终放在门槛前方的位置,燃烧殆尽。与此同时,GYB点燃了两只大蜡烛、四只小蜡烛。G大爷双膝跪地,先后端起一碗米饭、一碟蒸烧白、一碟猪膘肉和豆腐,在空中示意两次,这样以示邀请守护家宅的诸神前来享用,希冀来年神灵继续庇佑家宅安宁。
尔后,G大爷将盛有祭品的托盘端放在火塘之上的圆桌上面,GYB在盛有玉米的香炉里插上了已经点着的大蜡烛和三炷清香。接着,G大爷在堂屋右方角落的神龛中央的香炉里面插上三根之前点燃的清香,而后又在神龛右侧的两个香炉分别插上一炷清香。此时,GYB则在神龛左侧的两个香炉里分别插上一炷清香。插香结束后,G大爷分别在火塘的四角敬献了纸钱,并将供奉的两杯酒倒在地上未燃尽的纸钱之上,口中唱着《木古色经》敬请火神领受供奉。火神祭拜完毕,GYB家的成员按照长幼之序,分别向家神实行了三跪三拜之礼。跪拜之礼完成之后,GYB运用本民族的语言羌语,唱颂释比经典,唱经过程中主人家燃放了鞭炮,以期除旧迎新,新年大吉大利。迎请家神、祖先领受供品的唱经仪式完结后,GYB一家人围坐在圆桌之上享用羌年的团圆宴,相互之间赠送祝福的话语,希望羌历新年万事如意。
2.集体祭祀仪式
集体祭祀仪式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3年11月2日(农历九月二十九日)晚上的祭祀仪式,第二阶段是2013年11月3日(农历十月初一)早晨的“国若”仪式。
(1)第一阶段
2013年11月2日晚上晚餐后,村民们走过通往祭祀平台的曲折道路来到祭祀地点,准备参加即将开始羌年集体祭祀仪式。仪式的主持人是释比王治升⑥,助手由其徒弟GYB担任。
19时30分,羌年祭祀正式开始。王治升在山神庙正前方放置两个大小不一的香炉,大香炉插上四只大红蜡烛,小香炉插上两只白旗。尔后,王释比指导了村民将象征羌族最高的五位神灵的白旗插在山神庙右边约三米处的空地之上,五只白旗成一字形。白旗插放完毕,羌锋村的村民,把祭祀所用的柴火平放在祭祀平台中央,随后点燃了这些柴火。紧接着,GYB将一个大的太阳馍馍放在小香炉前面,又点燃一把祭祀所用的香,并在小香炉插上三根、大香炉插上九根。之后,GYB将四只大红蜡烛点燃,同时还在山神庙的左侧插了两炷香、右侧插了一炷香、正前方插了两只大红蜡烛。香、蜡烛插好之后,王治升、GYB一边念念有词地向神灵“通白”且撕着纸钱,一边向山神敬献燃烧的纸钱。与此同时,GYB的兄弟,一边将点燃的两只大红蜡烛插放在代表羌族五位神灵的白旗前面,一边点燃纸钱以祭祀五位神灵。
释比王治升敬完山神、释比祖师、羌族祖先后,他戴上猴皮帽、手持两个两孔的圆形铜铃,行至神树前的五只白旗前面开始一边摇动着铜铃,一边演唱羌年祭祀经典,经典大致内容是迎请各路神灵前来领受村民敬献的供奉品。铜铃唱经结束,王治升来到山神庙前面,一边手持羊皮鼓击鼓唱经;一边跳释比舞步,其步式称“禹步”,又称“猴步”。“禹步”为巫步,巫源于舞,释比跳禹步是希望以舞降神,达到娱神之效果。它反映了羌人的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图腾崇拜。大禹为羌人之祖先,《史记·六国年表》云:“禹兴于西羌。”《三国志》引《蜀王本纪》载:“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在释比经典中,有专门敬颂大禹神的经,称之为《竽巴热色经》。释比舞跳完后,王释比变换了唱经方式,即坐在长条凳上,手持羊皮鼓,一边有节奏地敲着鼓,一边唱经。因为他年事已高,不能长时间站立唱经。据笔者观察,王释比一共三段经典,即迎请释比祖师爷的经典、羌族祖先创业经典、羌族起源经典。几段经典唱完,前后持续一个多小时。唱经完毕,王释比向山神等神灵敬献了先前准备好的酒菜,然后参加祭祀典礼的所有人员分享神灵享用过的酒菜,以沾染喜气希望来年顺顺利利。第一阶段的羌年祭祀仪式到此结束。传统的羌年祭祀仪式,是不会中断的,一直持续至次日早上才宣告完成。因为王释比年近八十,体力难支,所以祭祀仪式的程序也简化了。正因为如此,羌锋村的羌年祭祀仪式被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二阶段的祭祀仪式,即羌年最高仪式“国若”,被放在新年的第一天清晨举行。
(2)第二阶段
“国若”是羌族羌年的最高祭祀礼仪。⑦国若,意为“和天、神说话”,“给天、神送愿物”。[8]“国若”是羌族社会中规模最大的、通天的、与神交流的、全民参与的集会。羌文化里面不存在“看客”,人人都要做“巴掴”(会首),人人都有监管国若的权力,他人即神灵。[8]
2013年11月3日早餐后,笔者跟随村民一起,来到神树林前面的祭祀平台。7时30分,燃放鞭炮,村民开始了集体祭祀的前奏——每家每户各自带着事先准备好的酒、香蜡纸钱、太阳馍馍,到山神庙前面进行祭祀。祭祀村民点燃蜡烛、香插放在庙前,献上太阳馍馍或月亮馍馍和燃烧的纸钱,口中念着“感谢诸位神灵一年来对家人的祝福与庇佑,请你们前来领受祭品”等。随后,村民请在场的人喝神灵享用过的酒、馍馍,希望所有人和他们一样在新年一切安好、行好运、免除灾祸。之后,村民将已经宰杀好的祭祀猪抬放在祭祀地点,接着村寨妇女们把准备好的神树枝平放在山神庙右边神树的前面。先前准备好的三只鸡(一公两母)被带到祭祀平台。是时,王释比手持神杖来到祭祀点,他的助手拿着羊皮鼓也来到现场。不一会儿,神羊被牵到祭祀点,一个村民将鸡颈上的毛拔掉为祭祀中宰杀做准备。
王释比身着祭祀法衣,头戴猴皮帽,手持羊皮鼓,他的助手也身着法衣,手持羊皮鼓,两人开始主持羌年的“国若”仪式。首先,王释比在山神庙前面的香炉插上猴头杖,然后与助手一边步调一致地敲着鼓,一边富有节奏地唱念释比经典,经典的内容主要是迎请寨首神、山神、土地神、天神、太阳神以及古代羌族人的起源、婚姻、天地断裂、释比来源等。尔后,他们从庙前面边唱经边击鼓,同时移至插有代表羌族五位神灵的白旗前方。在白旗前方的空地,王释比及其助手一边“咚咚咚……”击鼓、唱经,一边跳着特有舞步,不时变幻阵型。
在王释比他们唱经的过程中,村民用释比单刀宰杀了神羊,将羊血洒在草地上,画了一个大圈,示意诸神灵受领。期间,他们点放了鞭炮。一会儿,一只公鸡、两只母鸡先后被单刀祭杀供奉给诸神,村民将鸡血洒在草地上画了一圈。又一会儿,抬猪的村民将猪头砍下,将其端正地供奉在正对五白旗的青石上祭天、祭神,随后再次点放了鞭炮。杀生祭祀完毕,王释比和其助手继续有节奏地吟唱对诸位神灵歌功颂德、感谢诸神护佑的经典。约8时30分,羊皮鼓舞及经典唱诵结束,结尾前王释比唱“色颇喂”(音译),众人紧跟着喊“嘿哟”三次。
“国若”仪式结束后,参加祭祀的所有村民拿着神树枝,一人一支将神树枝高举头上,拿回各自家中的田地里插上。笔者入乡随俗,也拿着神树枝跟着一户村民到他家的地里插上。据羌锋村村民解释说,经过羌年祭祀加持的神树枝是存在着一种神力,把它插在自家田地里,希望在土地神的护佑下,来年家中五谷丰登。在神树枝入土前,需要燃上一炷清香、一叠纸钱,为土地神敬献太阳馍馍、白酒,且双膝跪地示意磕头三次,以示对土地神的感谢。尔后,起身在庄稼地插上神树林,再次重申土地公、土地婆庇佑粮食不遭旱、不遭涝、不遭病虫的话语,接着对插好的神树林点头三下退出地里。
欢庆羌年。2013年11月3日上午,仪式结束后,村委会作了一个简单的“汶川县绵虒镇羌锋村老年协会”挂牌活动。中午,村民们在祭祀平台一起享用了“坝坝宴”,跳起欢快的“萨朗”。晚上,羌锋村举行了“烤全羊—篝火晚会”,村民载歌载舞,欢度羌年,祝福美好未来。
四 羌年祭祀仪式与艺术
羌年祭祀仪式,属于民间信仰的一种类型,仪式之中蕴含着多种艺术形式:音乐、舞蹈、美术等,且为人们展示羌族独特的艺术魅力。可以说,这些艺术形式与艺术魅力贯穿在羌年祭祀仪式体系之中。
羌年祭祀仪式,称作“刮巴尔”仪式或“国若”仪式。祭祀仪式历史悠久,有着成套的仪式体系。1988年,赵曦教授在汶川县阿尔巴朵的白家朵寨的调查,认为完整的“刮巴尔”仪式共由11个单元组成,分别是仪式前的准备、迎树制器、授“直”封羊、取火解秽、鼓舞请神、青稞颂神及其他、驱邪关害、羊入天门、送神迎日、议话封山、欢庆羌年。[8]笔者观察到,羌锋村的“国若”仪式一些环节出现了变化,即仪式简化、缺失,如神羊只准备了一只、没有草扎物件,环节缺少了羊入天门等等。虽然如此,释比仍是整个国若仪式的核心主导人物,国若仪式的艺术以释比为中介。仪式过程之中,释比亲自塑造了仪式空间,给信仰者呈现神灵的世界。他通过神画像、法器以及具体物品的摆放、悬挂,营造了仪式空间的神圣性。
从“国若”仪式过程中,我们能够得出羌锋村年祭的艺术是依托仪式而存在,仪式与艺术同等重要,双方不能独立存在。“从发生学上考察,艺术的产生和祭礼仪式有一种共生关系。正是在这种关系中,艺术开始了它选择某种超出信仰目的的审美倾向”。[9]羌年艺术展演不能脱离祭祀仪式,寻找羌年年祭的艺术价值应从释比空间展演与祭祀仪式的交接状态中着眼。
窥观羌年释比祭祀与艺术的表演,我们发现祭祀是为了更好地与神灵沟通。“国若”仪式之中,释比最有效的通神、驭神方式即唱经、舞步、阵型。王国维指出“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10]又,《说文解字》:“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也。”由此可见,歌舞的产生与祭祀关系密切。
古羌人早期祭祀,完全依靠巫师与神灵之间进行沟通,正如《辽史》卷一百一十五《西夏》说:“……召巫者送鬼,西夏语以巫为‘厮’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羌年祭祀仪式中,释比通神、娱神的方式变得多种多样。释比通过祭祀空间的布置,主要是神龛的设置,通过歌舞让人们感受到神灵如临现场,又通过图画、面塑、法器,将神灵、神灵生活的世界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另一方面,世俗人的因素在仪式及其艺术得到充分展示,仪式不单纯是驱秽迎新,还展演了历史与世俗生活的主题。
从羌锋村羌年祭祀仪式考察,能够看出上述观点。羌年祭祀空间分家庭祭祀空间和集体祭祀空间两个部分。家庭祭祀仪式堂屋大门口、神龛的布置,如挂红、张贴门神、对联、图画,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挂红的红色,是羌文化最为重要的艺术色彩之一,是吉祥、喜庆的象征符号,还象征着羌族崇敬的太阳神。“象征符号是指某物,它通过与另一些事物有类似的品质或在事实或思维上有联系,被人们普遍认作另一些事物理所当然的典型或代表物体,或使人们联想起另一些物体。”[11]为神龛挂红,使得人们联想到红日带来的光明。有一则民间传说故事说,很久以前,猿猴把天宫水缸打翻,水流入人间,洪水滔天,人类绝迹。天神木比塔感念,为太阳与月亮兄妹讲述了人间与天庭的故事,让其下凡结为夫妻。一开始,兄妹俩并不愿意。后来,木比塔许了几件难事,都全部实现。兄妹俩为其关怀人间而感动,遂下凡结为夫妻,繁衍了人类,使得人间兴旺。[12]羌族村寨村民利用面塑太阳馍馍、月亮馍馍祭祀神灵,一方面是酬谢诸位神灵一年的辛劳、护佑,另外一方面是歌颂太阳、月亮为人们做出的功绩。
家庭祭祀空间,分为堂屋大门口、神龛、火塘,是人神共存的地方。大门和神龛的对联、神龛两侧下方的图画、神龛简单雕刻书画内容,把羌族传统文化的居家观念形象地表现出来。这些文字书画内容,其实是羌民族固有的家风和居德。“福禄寿喜”、“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恭喜发财”、“五谷丰登”、“欣欣向荣”、“荣华富贵”、“家和万事兴”等等,均显示出居家之人的理想与愿望。不难看出,羌族深受汉族儒家文化的感染,其所追求的理念正是儒家文化涵盖的传统的吉祥内容。换言之,是对人生美好未来的憧憬与祈盼,儒家文化精神支配着民居的格局与气质,影响着羌族的观念,形成了十分独特的羌族民居文化。[13]
羌族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春节或过年都会张贴门神画。羌年之际,村寨每家每户全都张贴了门神,并举行门神祭祀仪式,他们认为房屋之中有门神,对其的祭祀与否关系到家人的安全。门神的出现与“五祀”信仰习俗紧密相关。《礼记·祭法》:“大夫立三祀:曰族厉,曰门,曰行。适士立二祀:曰门,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14](P225)门是房屋最为重要的位置,只有神人把守才有安全感。贴门神,历史悠久。《神隐》:“元旦三更迎灶毕,……贴门神钟馗于门,以避一年之祟。”[14]《月令广义·正月令》:“黄帝之时,神荼郁垒兄弟二人性能执鬼于桃树下。令人画其像于桃版,列于门户,书其名于下。”[14]人们对门神的崇拜与敬畏,使得门神画得到发展。以羌锋村房屋门神画为考察对象,门神画至今十分丰富,如武将、文臣、朝官、童子等等。门神画各式各样,分为单幅式、对开式,有三大类:文门神、武门神、动物门神。文门神多为福禄喜寿的文官形象,武门神为武将或传说神人,动物门神以鸡、虎、狮、鹰居多。[13](P74-75)
集体祭祀所用的供奉类物品,是与民间信仰、民俗宗教相关的艺术品,甚至有些直接就是释比的法器或道具,更是美化了祭祀空间。从村寨通往祭祀平台的道路沿途“挂红”,“挂红”不仅说明了羌族人对红色的崇拜,它还指明通向祭祀的方向,点缀了村寨的自然风光,使得整个村寨充满节日喜气。羌年祭祀仪式的艺术品主要有《刷勒日》图经、释比法器、草扎物件、白旗、面塑。
《刷勒日》图经为折叠式两面绘图图牒,全长在1.6米 ~1.8 米,宽 0.16 米。每个画牒高 0.16 米、宽0.1米,图画分布于图牒的两面。一般60个图牒组成一幅完整的《刷勒日》图经,包括各类神灵持各种法具、各类神仙图、十二生肖图、龙蛇图、林林总总的宗教器物以及数十个箭形图。[8]不过,羌年祭祀唱经不会手持图经。释比图经《刷勒日》为人们传达出羌族是兼收并蓄、亲和他族文化的民族。《刷勒日》吸收了汉文化的天干地支、五行、星宿、易学的思想,蕴含着释比文化深层次的宇宙观、人生命运、生灵信仰,三位一体的易、卦、象之文化,承载着羌文化的核心观念、秩序、作法、易算、占卜等理念。换言之,《刷勒日》不仅亲和了羌汉的民族关系,丰富了彼此文化的多样性,还充实了少数民族艺术文化的内容,更甚者,使得少数民族对汉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情感,故而增强其对国家的认同感。
释比法器如猴头杖、猴皮帽、铜铃,它们不仅体现了羌族的雕刻艺术,还展现了羌族文化。羌族雕刻以独特的美术方式对话外来文化,形成本民族特有的美术作品形象。释比作为羌族文化的集大成者,其所用之雕刻法器也是出自释比之手。
猴头杖雕刻:释比的主要法器,精美的美术作品。传说,羌民族的祖师,在取经过程中,经书被羊偷走,一只金丝猴前来相告。他发现经书被羊吃了,后来盘缠用尽,金丝猴施法将他送至家中。金丝猴去世,祖师为报恩,将其崇为猴头祖师。尔后,释比将猴头刻于神杖之上,猴头也成为羌族崇拜的图腾之一。像羌年祭祀仪式这样重要的集会,释比会手持神杖,以显示其身份与权利。猴头帽装饰雕刻:猴头帽是释比祭祀必戴的法器。帽前端装饰上圆下弯的星月的两银牌,上圆盘中浮雕太极图,四周是从小到大的小圆点,代表星星。下方的月亮形饰牌中央雕有类似小铜钱的图案。铜铃:外部是八卦图的浮雕,里面有一金属物体,一摇动即刻产生声响。[15](P283)
羌年祭祀仪式涉及的手工艺术品有草扎物件、白旗、面塑。草扎物件,其制作原料是青稞草、麦草、荞麦草,形态各异,有的呈飞虎状,有的呈飞龙状,也有神鸟状。这些作品基本上是变形、抽象的。现在羌年祭祀基本没有这样的道具。白旗是白纸裁制而成的物品,多为三角形。白旗分为两种,一公一母。公白旗的造型是下部为两个分丫。母白旗下部是三个分丫,三个分丫的这个小的部位加“厄枝”。面塑一般是用青稞面、小麦面制作而成,有面塑的太阳、月亮、星星、野牛、羊、鹿、野鸡、金鸡、神鸟。现在,羌年祭祀仪式涉及的面塑,最常见的是面塑太阳、月亮,其他面塑十分少见。
要而言之,羌年祭祀仪式的艺术品体现了羌族的自然生态文化观——亲和自然。祭祀艺术品的原材料“源之自然、取之自然、归之自然”,羌区地处岷江上游、涪江上游,高山峡谷,密集的原始森林,许多村寨分布于山地河谷的高台上,像青稞草、小麦面、木料、皮毛等物品,随处可得。这决定了在工业化环境与工业产品充斥着人们生活的情况下,羌族人民仍然能够保持着朴素的生态文化。另一方面,它还反映了羌族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万物有灵”的宗教观。猴头帽,“帽冠高耸,象征正神凛然,释比法力齐天绝地。法冠正面基本呈现平面方形,帽主体为圆形,包含有羌族人早期的天圆地方的意念。正面壁立向上高耸,象征羌族的神山顶天立地。正面又分为三个构成块面,最上有三个特制的小凸出之皮质制作的冠峰,彼此独立高耸,表征三个神圣意象:中间是通天绝地、通灵通神之峰柱,象征释比戴上此法冠,与天同高,通达天意,它象征羌族的宗教理念中的万物由一个混元一气、一体分化出来。”[15]。猴头帽、猴头神杖以及面塑的太阳、月亮、牛、羊等,说明羌族人民一直延续着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动物崇拜。羌族的原始宗教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风俗通》:“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因以为号。”《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羌人“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羊是羌族人民衣食来源,他们以羊毛、羊皮为衣,以羊肉、羊奶为食,晒干的羊粪为其燃料。祭祀活动之中,羊是牺牲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载:党项羌“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直至现在,羊仍然是祭祀活动中主要的牺牲,它被羌族人民视为沟通人、神、鬼三界的使者。
除了羌年祭祀的艺术品外,羌族歌舞也是羌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给羌族人民和人类的艺术宝库增添新的养分。在羌年祭祀仪式中,羌族歌舞为人们展现出来了它的魅力。作为羌年最高仪式的国若,有一个极其特别的环节即欢度羌年。喝砸酒就是欢度新年的一种形式。在开坛喝酒之前,德高望重的老人要唱《开坛酒歌》,以酬谢神灵的恩赐。
欢度新年的形式除了喝砸酒、唱酒歌外,跳羊皮鼓舞、舞龙舞狮,跳萨朗也是欢庆羌年的重要内容。羌年“国若”仪式之中,释比手持羊皮鼓,边唱边舞。“头戴猴皮帽的释比在自己作舞的时候,指挥着其他副手在仪式过程中表演各种舞蹈的方向和应做的次数。他们各自舞姿各异,有的边挥动法器边向各个方向弯腰曲背祭拜;有的轮流替换着左右腿做前后蹦跳、有的却在原地左转右旋……”[15]“国若”仪式结束后,村民们会在本寨广场上,伴随着音乐跳起集体性的萨朗,庆祝新年的到来。萨朗音乐曲调流畅、节奏欢快,歌词内容丰富。萨朗舞蹈跳法大致如下:男前女后,不限人数,围广场一圈,不封口,向逆时针方向边歌边舞。开始时,先男女轮唱一遍舞曲,然后共同起舞,速度由慢到快,跳到激烈时,领舞男子加快舞步,带头交换各式不同的舞姿,或左右旋转,或两腿交替重踏,男女之间相互竞争,气氛渐渐热烈。舞至高潮以后,男子叫喊“吓喂”,女子应和“哟喂!”一曲至此结束,紧跟着变幻新的舞曲和步伐。[15]
不难看出,不论是酒歌、羊皮鼓舞、萨朗舞,还是羌年“国若”仪式涉及的其他歌舞,都为世人展示了羌族人民积极向上的生活价值观,反映了羌族人民的审美取向与艺术情操,体现了羌区的地域民族风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正如,特纳所说每一个仪式都有其治疗功能。换言之,仪式之中的艺术也有治疗功能。当羌族人民遭遇天灾人祸之时,国若仪式及其仪式之中的舞蹈艺术,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治疗羌族人民的心理创伤的功效,使之面对失败、挫折、不幸仍然能够保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结 语
通过羌锋村羌年祭祀仪式的研究,说明了仪式和仪式中的艺术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具有互补性。一方面,“仪式的艺术化表达,是基于艺术本身直接作用感官体验,善于表达艺术行为者情感,易于引起观赏者共鸣的特质所决定的,这与直指人类心灵感受的宗教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于是艺术成为了在仪式中表达宗教情感的重要手段。”[10]“国若”仪式涉及的艺术形式有祭祀品、书画、雕刻、歌舞,起到了强化仪式的世俗性和淡化仪式神圣的宗教性。仪式时空构建的神灵虚幻世界,与现实的世俗生活有很大差别,但它又高于世俗生活,且为其服务。所以它必须以音乐、美术、歌舞等世俗化的艺术形式,达到娱人又娱神、雅俗共赏、人神沟通的效果。另一方面,羌年祭祀仪式既是羌族家庭向心力的象征,又是羌族族群内聚力的象征,还强化民族认同感。家庭祭祀仪式,增进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协作,强化了家庭成员和睦之情。在“国若”仪式上,强化羌族族群内聚力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举行全村寨上上下下的仪式活动,从活动规模和人口数量上突出集体感;二是塑造了一种强化集体感或族群力量的媒介,这种媒介便是“国若”仪式。“国若”仪式里面的群舞——萨朗,它并不是特别复杂的舞蹈动作,而是追求动作的协调统一,它有效地集中体现一种特定的情绪,并能渲染和烘托出独特的气氛,是一种具有激烈情感色彩的艺术形式。
注释:
①铜铃:“为铜制,挂在铜铃里面的锤为牛角制作的,以铁链与铃把连接,把上饰以辰布。法锣:多为铜制,其直径约15~20公分,凹凸两面,法锣外沿有一皮制手柄。”——转引自周毓华:《白石·释比与羌族》,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第111页。
②羊皮鼓:“羌语称为日博,圆形,单面,直径约40~50厘米,鼓梆约高15~20厘米。相配有一只鼓槌。鼓槌的特别之处是用长约30~35厘米的一节刺木为鼓槌柄,木质密度厚实,不容易受蛀虫侵害蛀损,刺木的弹性韧性也非常好,敲击省力,而且弹力增加鼓柄的频率,在打击连音鼓点时,非常灵活,跟得上快节奏。鼓槌用山驴皮、麂子皮或獐子皮,……它们生活在高山丛林中,身上有着独特的神秘性与灵气。这种鼓槌传达的声音是神灵的声音。”——转引自赵曦:《神圣与亲和——中国羌族释比文化调查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38页。
③猴头杖:“用刺棍或树藤制作,也有铁质的,杖长五尺左右。杖的上端有铜质或铁质的神像,代表鬼王,其形象造型有十几种,神像下面是一铜铃,或为三叉与环状铁环和小铃铛,使用时哗啦作响,杖杆或为光滑的木棍,或为密布节疤的粗糙木棍,或为野藤缠绕在树枝上的样式,下端为铁尖,用以刺邪鬼邪魔……”——转引自周毓华:《白石·释比与羌族》,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第111页。
④释比单刀:“铁制,单刃刀。刀尖特别锋利,一些刀背上有神秘图案。释比刀是释比曾经亲自参加寻铁冶炼铁制作不同铁具的物化见证。释比单刀主要用于宰杀祭祀牲口和制作祭祀法具,专门用于神圣法事,不是用于人间的杀伐。”——转引自周毓华:《白石·释比与羌族》,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第111页。
⑤GYB访谈。访谈人:杨娅、邹莹、叶健、王明利、叶志强。被访谈人:GYB,男,羌族,40岁,四川汶川人,释比。采访点:汶川县羌锋村;时间:2013年11月2日。
⑥王治升,男,羌族,80岁,四川汶川人,释比,2009年6月被中国文化部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羌年代表性传承人”,编号:03-1477;2012年6月被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授予“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
⑦羌语方言使得羌年最高祭祀仪式的称谓有所差异,羌锋村称作“国若”仪式,汶川县白家朵寨叫“刮巴尔”仪式。
[1]《西羌第一村——羌锋村》,http://www.scxxty.cn/template/9/902/detail.aspx?wid=2842&cid=19468&id=251542.
[2]周锡银,刘志荣.羌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114
[3]阿坝州文化局.阿坝州藏族羌族自治州文化艺术志[M].成都:巴蜀书社,1992:285.
[4]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汶羌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茂汶羌族自治县志[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7:677.
[5]俞荣根.羌族习惯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529.
[6]周毓华,孙婷婷.异地安置羌民的“第一个羌年”四川省邛崃市南宝山木梯村羌年田野调查报告[J].民族学刊,2011(08):40.
[7]王霄冰.仪式与信仰:当代文化人类学新视野(新疆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与民族社会研究丛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6.
[8]赵曦.神圣与亲和——中国羌族释比文化调查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76,148,194,149 -192.
[9]朱狄.信仰时代的文明——中西文化的趋同与差异[M].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79.
[10]何明.仪式中的艺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59,205.
[11](英)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高丙中主编,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9.
[12]四川阿坝州文化局主编.郑文泽(羌族)编.羌族民间故事集[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1-2.
[13]王海霞.透视:中国民俗文化中的民间艺术[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6:65,74 -75.
[14]宗力,刘群.中国民间诸神[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222.
[15]周毓华.白石、释比与羌族[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109,272,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