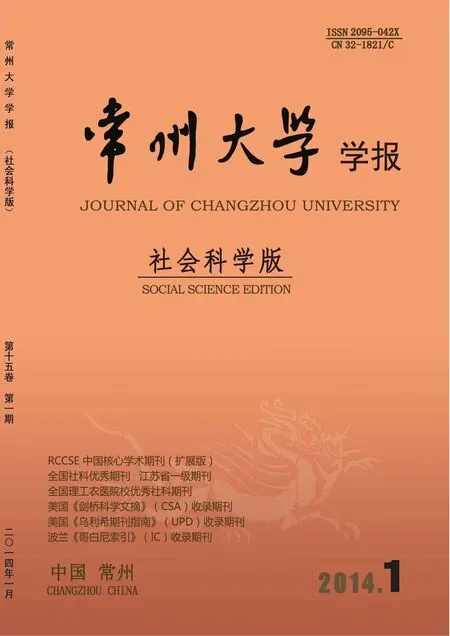从乌台诗案看北宋官员犯罪司法程序的特点
郭艳婷
(中共平顶山市委党校,河南 平顶山 467000)
从乌台诗案看北宋官员犯罪司法程序的特点
郭艳婷
(中共平顶山市委党校,河南 平顶山 467000)
乌台诗案是北宋中期著名的诏狱。这个由皇帝直接掌管的需皇帝下诏书始能系狱的审判高官犯罪的案子,其司法审判也是按从劾奏到圣裁等七个程序逐一进行,是诏狱审判制度的具体实施,最终的处罚结果也符合当时法律规定。官员犯罪的司法程序是围绕查明犯罪事实、促使犯罪官员认罪伏法设计,包括诏狱在内的绝大部分案件能够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即所谓“法在有司”。而统治者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亲自下诏书最终定罪,除了训诫教化作用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显示权威的政治意义,是所谓“恩归主上”。
乌台诗案;北宋;官员犯罪;司法程序
北宋元丰二年(1079)发生的乌台诗案,历经千年反响不绝。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乌台诗案做出不同的解释。政治史学者认为乌台诗案是北宋熙丰党争的结果,和王安石及其推行的大变法有着必然的联系[1]①。文学史学者研究的重点是乌台诗案对苏轼人生和创作的影响,认为诗案以后苏轼的人生发生重大转折,完成了个体精神的自我超越,诗案后苏轼的文风随之发生了很大的转变。[2]非仅如此,乌台诗案中苏轼在狱中写下万余字的供状,对自己前期创作的诗歌作品作了解释和说明,这本身就是研究苏轼文学的第一手宝贵资料。法律史学者则将乌台诗案作为一个经典案例来研究宋代的法制,认为乌台诗案是北宋中后期变法派与保守派斗争过程中的政治案件,案件的审理和处罚过程体现了宋代法制的诸多内容。[3]整体来看,学界对乌台诗案的研究主要是对案件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氛围进行考察,侧重探索乌台诗案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和历史影响,对其本身的研究并不充分,尤其没有注意到乌台诗案审讯过程所体现出来的司法程序。作为北宋官员犯罪的典型案件,乌台诗案的审讯过程和处理结果都彰显出宋代司法审判的特点,我们有必要在法律史的视野下重新解读这一千古名案。
一、乌台诗案始末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四月,祠部员外郎、直史馆苏轼被任命为湖州知州,到任之后,苏轼按照惯例上谢表。这份谢表中有这么几句话:“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御史们认为这些言语涉嫌诽谤朝政,怨望,遂提起弹劾。
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何正臣奏称: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为恶不悛,不可不杀。且提供了证据——苏轼谢表的镂版。神宗皇帝接到劄子后,将其批转中书省。
七月二日,太子中允、集贤校理、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又在崇政殿向皇帝呈奏弹劾劄子,认为苏轼在谢表中讥切时事,社会影响极坏,并对苏轼的三篇诗文进行分析。同时附上苏轼印行诗文三卷。皇帝又一次将劄子批转中书。
国子博士李宜之也宣称自己也有苏轼大逆不道的证据,那就是曾见宿州灵璧秀才张硕家有苏轼写的张氏园亭记,并对其中的“不必士,必不仕”加以分析,从而认为苏轼大不敬,请求根勘苏轼。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李定上劄子认为苏轼坚持作恶、不肯悔改,口吐狂言、不可一世,虚伪善辨、道德败坏,怨天尤人、是非不分。请求皇帝对其绳之以法。神宗皇帝将四状批与御史台。
次日,苏轼被罢免并接受御史台的调查和审问。随后,苏轼被押赴京师入狱。紧接着,御史中丞李定和知谏院张璪审讯苏轼。苏轼供述并为自己辩护直至最后招认。
勘问结果:涉嫌的六十九首(篇)诗文,苏轼自认涉及讥讽朝政的有五十九首(篇),并一一列出承受文字讥讽的对象。审讯过程中,逢太皇太后病体加重,因服药,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释之。[4]7312
十一月三十日,御史台的根勘结束。差遣权发运三司副使陈睦录问,苏轼别无翻异。
御史台将苏轼一案移交大理寺,大理寺根据根勘结果作出判决:当徒二年,会赦当原。然后将案卷和判决意见呈送神宗皇帝。十二月己未,神宗皇帝作出最终处罚决定:祠部员外郎、直史馆苏轼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4]7333
二、乌台诗案的司法审判程序
(一)劾奏
乌台诗案是由4份状子引起的,告状的人包括一位御史台的长官、两位御史、一个国子博士。御史台是专门的监察机关,监察御史的职责就是“分察百僚”,依法弹劾涉嫌犯罪的官员。御史们弹劾苏轼是履行法定职责,而李易之的控告则说明官员之间相互纠举也能够启动案件调查和审讯。
(二)立案
从乌台诗案中可以看到,启动对官员的调查审讯是有条件的。所有的弹劾奏章都提供了苏轼犯罪的证据——涉嫌讥讽朝政、心怀怨望的诗文。皇帝接到状子,征求中书省的意见后决定立案是有事实基础的,即已经有证据证明犯罪发生。所有调查和审讯决定都是由皇帝本人做出,调查和审讯机关、官员也是由皇帝指定,苏轼诗案指定的审讯机关是御史台,御史台别称乌台,因此本案就被称为乌台诗案。
(三)逮捕
立案之后,皇帝立即做出罢免苏轼湖州知州的决定,同时令御史台选派官吏去湖州勾摄苏轼,中使皇甫遵和御史台官吏赶赴湖州执行逮捕、押解任务。此时的苏轼已被控犯罪,按照皇帝命令需押赴京城御史台狱接受审讯。执行逮捕时,对涉嫌犯罪官员是否采取强制措施必须听从皇帝的命令。皇甫遵在临行前向皇帝请示,可否将苏轼每晚都关押到回京所经地方的牢房里,神宗认为只是根究吟诗事 ,不需 关 押 。[5]454
皇甫遵到湖州恣意威吓,使人心疑惧,但也只敢催逼上路,“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5]452,却不敢使用械具,更不能监禁。
(四)审讯
苏轼诗案是皇帝交给御史台审讯的案件,即所谓“制勘”,又称“诏狱”。皇帝委派主持审讯此案的官员是御史中丞李定和知谏院张璪,使用御史台的监狱及其属吏。审讯的主要目的是追取苏轼的有罪供述。追取的过程并不顺利,苏轼开始只供认《山村》诗讥讽时政,拒不承认其他诗文干涉时事。因怕牵连亲友,更不承认与他人文字往还。审讯官员出示了收集到的诗文证据,反复勘问,八天以后,苏轼招认,做除了根勘结论。
“李定、何正臣、舒亶杂治之,侵之甚急”,李定、张璪是皇帝委派的主审官员,何正臣、舒亶是御史台的监察御史,而直接逼取口供的还有御史台的狱吏,这些身份卑微的差役对苏轼进行詈骂侮辱,为取口供不择手段。隔壁牢房的苏颂有诗描述当时的情形:“遥怜北户吴兴守,通宵诟辱不忍闻”,自注云:“所劾诗歌有非所宜言,颇闻镌诘之语”。[6]这些诟辱苏轼的人就是逼取口供的御史台的狱吏。②
除诗文之外,还讯问苏轼与驸马都尉王诜的交往及请托情事。
乌台诗案中,没有发现使用刑具和拷讯的记录。根据刑不上大夫的礼制原则,审讯享有议、请、减的朝廷命官,原则上是不适用刑讯的。
(五)录问
录问是指案件审讯结束后,检法官议刑前,对徒以上的重大案件,差派未参加审讯且依法不应回避的官员对案犯进行提审,核实口供,以防止冤案的发生。也就是说凡是有可能判处徒刑以上的案件,要派专人讯问犯罪人口供是否属实。本案中,十一月三十日御史台根勘结束之后,朝廷委派权发运三司度支副使陈睦录问,此时苏轼若有冤情,可以推翻原供,或称审讯时受到不公对待,皇帝将另行指派其他官员重新审讯,即翻异别推。由于苏轼没有翻异,陈睦的录问也就迅速结束,案件被移交大理寺。
(六)拟判
御史台的审讯结束,案件材料和根勘结论送往大理寺,由大理寺根据犯罪事实检断法条,做出判决意见。“御史台既以轼具狱,上法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
大理寺的判决意见认为:
熙宁三年至元丰二年十月德音前,苏轼与驸马都尉王诜交通往来,王诜多次向其索取祠部度牒、紫袈裟等物,准律不应为事理重者杖八十断,合杖八十私罪。又到台累次虚妄不实供通,准律:别制下问按推,报上不以实,徒一年,未奏减一等,合杖一百私罪。作诗赋等文字讥讽朝政缺失等事,到台被问,便具因依招通,准律:作匿名文字,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徒二年;准敕:罪人因疑被执,赃状未明,因官监问自首,依按问欲举自首;又准刑统,犯罪按问欲举而自首,减二等,合比附徒一年,私罪系轻,更不取旨。
作诗赋及诸般文字寄送王诜等,致有镂版印行,各系讥讽朝廷及谤讪中外臣僚,准敕:作匿名文字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徒二年,情重者奏裁。
根据这个判决意见,苏轼触犯了三项罪名,第一,交通王诜,受请托索取官府度牒,属“不应为”罪,合杖八十私罪;③第二,到诏狱之后,不如实供述罪行,属于报上不以实,当徒一年,因尚未奏明皇帝,减一等,合杖一百私罪;④第三,作匿名文字谤讪朝政和中外臣僚,当徒二年。在审讯中,苏轼有两种情节,一种是一问便招认(如山村诗),属于按问欲举自首,减罪一等,徒一年;私罪,情节较轻,不用奏裁。另外一种是将匿名讪谤文字寄送他人且有镂版印行,审讯时又拒不招认,情节严重,徒二年,奏裁。
根据当时的法律,大理寺作出判决结果:准律:犯私罪以官当徒者,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准敕:馆阁贴职许为一官,或以官或以职,临时取旨。据案:苏轼时任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曾历任太常博士。其苏轼合追两官,勒停放,准敕比附定刑,虑恐不中者奏裁。[7]
(七)圣裁
御史台审讯结束,大理寺拟判完毕,将案犯的供状、审讯记录、证据材料、判决意见一并呈送皇帝。我们在乌台诗案的记载中看到,除案卷材料外,就连苏轼在狱中预作的遗诗都呈送给了皇帝,“东坡坐诏狱,御史上其寄黄门之诗”。皇帝根据案卷材料,在大理寺判决的基础上做出处罚:苏轼可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苏轼追两官(直史馆、太常博士),当徒二年。保留员外郎的官充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事,其实就是停职。
对于苏轼的处罚结果是依照律文和编敕做出的,并未法外施刑。和北宋不同时期触犯相同罪名的官员相比较,也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如苏轼被指控的一项罪名是报上不以实,依律当判徒一年私罪。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知绵州李说报上不以实,罚铜十斤私罪;[4]1773天圣六年(1028)二月,内园副使王世融上书诈不实,法寺议罪当追官勒停,贬为内殿承制、监虢州税;[4]2464熙宁十年(1073)十月,皇城使阎士良报上不以实,夺两官,勒停。[4]6991准律:犯私罪以官当徒者,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五品以上官员可以纳铜赎罪,流外官员处罚不能以官当徒,只能追官勒停。
苏轼被指控的另一项罪名是谤讪朝政和中外臣僚,依法当徒二年。开宝六年(973)六月,商州司法参军雷德骧为文讪谤朝廷,知州奚屿“召德骧与语,潜遣吏绐德骧家人取得之,即械系德骧,具事以闻”,上贷其罪,削籍徙灵武;[4]303至道元年(995)五月,王禹偁谤讪朝政,翰林学士、知审官院兼通进、银台、封驳司罢为工部郎中、知滁州;[8]9795⑤天禧三年(1019)五月,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官李仲容、同提点刑狱官王遵诲奏左谏议大夫、知郓州戚纶有讪上语,纶责授岳州团练副使;[4]2146在著名的进奏院案中,王益柔醉作《傲歌》,涉嫌讪谤,由殿中丞、集贤校理贬为监复州税,并落校理;[8]9634庆历八年(1048)十一月,李淑作周陵诗,有“不知门外倒戈回”之句,国子博士陈求古上淑诗石本,且言辞涉谤讪,下两制及台谏官参定,皆以谓引喻非当,遂黜之。以翰林学士、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侍郎、知制诰、史馆修撰落翰林学士,依前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加龙图阁学士、集贤殿修撰、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8]9741元祐七年(1092),曾肇以宝文阁待制知颍州,时方治实录讥讪罪,降为滁州。[8]10394就处罚结果而言,苏轼案的处罚结果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与北宋时期触犯相同罪名的官员处罚结果相比,也很相似。
三、结论
通过乌台诗案的司法审判,我们会发现北宋官员犯罪司法程序的特点:
(一)北宋官员犯罪的审判程序以查明案情、促使犯罪官员认罪伏法为核心
案件处理的重心是调查程序,几乎所有的案件都是以调查案件事实为中心。主要对犯罪官员采取问、按的调查审讯方式,通过讯问案件的相关人,案件发生地监司的调查,直接讯问涉嫌犯罪的官员本人,查明案件事实的可能性很大,同时也给了涉嫌犯罪的官员自我辩解的机会。在这种程序之下的审判逻辑是这样的:有官员受到犯罪指控——查明指控是否属实(问〈如果引伏、供认就讨论如何惩罚,如果不承认就要按或推。也或者直接按,直接进入推鞫的情况比较少见〉)——法司论罪——皇帝决断。也就是说,调查案件事实是整个案件处理的核心。
推鞫则是在掌握一定犯罪证据的基础上审讯犯罪官员本人,通常以取得犯罪官员的口供为中心。以口供为目的的侦查中心主义的模式必然会造成两个后果:第一,被审讯的官员特权被限制或免除;第二,官员辩解的空间被无限压挤。官员的审讯与社会隔离,在封闭的空间内和高压的态势下,官员将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这将直接影响审讯结果。神宗熙丰以后,诏狱频兴,低级的官吏甚至狱卒也参与到审判中来,这就使涉嫌犯罪的官员倍感耻辱,官员们对下狱“付吏”都是非常恐惧,因为这不仅意味着官员身份权力被剥夺,而且人格尊严也受到威胁,这对于视名誉声望、人格尊严为生命的宋代士大夫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下狱的官员往往自诬服,以免受到人格的侮辱。这样,本来欲查明真相的审讯就离真相越来越远。
在众多的审判程序启动方式中,御史台的弹劾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原因是御史台是专门的监察机关,在许多官员犯罪案件中,御史台既是指控机关又是审讯机关,主导着案件的进程。在宋代,台谏官员经过严格的选拔,具有正直无私的品行和公正执法的精神才有可能入选。他们也属于士大夫群体,占据着道德优势,职责就是纠举官员犯罪,肃清官场的风气。台谏奏劾犯罪官员时一般会提供相关的证据,调查审讯就是沿着指控的罪状展开,最终要让犯罪官员引伏。这种制度的运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台谏官员的素质,庆历年间,欧阳修、余靖、尹洙等人任台谏官员时,官场风气为之一肃,而熙丰时期蒋之奇、王子韶等人任台谏官就会制造流言和冤狱。同样的机关,在北宋前期就是悬在官僚群体头上的一把利剑,促使之奉公守法,而到熙丰年间,台谏官却成为中书的喉舌和工具。
(二)为查明案情防止冤滥,北宋设置了比较合理的司法审判程序
首先,北宋时期官员犯罪的控告力量多元化加强了对官员行为的监督,防止官员以权谋私和滥用职权、为害百姓。除了专门的中央和地方监察机关,受害人可以逐级上告。特殊情况下可以击登闻鼓告御状,朝廷设有登闻鼓院专司此责。宋代官员之间的相互纠举明显增多,不同地域、不同系统的官员只要知情都有举报、纠举的义务。
其次,就官员犯罪案件本身而言,为保证查清官员的犯罪事实,防止个人专断导致冤案发生,宋代沿袭了前朝的鞫谳分司、翻异别勘和录问制度并贯彻执行,在一个审讯机关内,也设置左右推司、左右军巡等机构,通过机关之间、机关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监督保证审讯取得案件的真实情况。
最后,官员犯罪案件在根勘结束和圣裁之前,其他官员皆可以上书的方式,或者在皇帝召集的廷议上对案件的处罚发表自己的意见。既可表达对案件事实的看法,也可对法寺的拟判提出意见。客观上,这些表章和意见起到了加强指控或者辩护的作用,影响到皇帝的最终裁决。
(三)宋代官员犯罪司法程序的最后环节是圣裁,实际上只具有训诫、教化和政治意义
就北宋官员犯罪的司法程序来看,形式上是皇帝主导着整个程序的运行。官员犯罪案件是否立案、调查,采取何种调查审讯方式,是否采取强制措施,是否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审讯人员如何组成,审讯机关如何设置,录问官员如何指派,最后的裁决如何等等都是由皇帝决定的。
但官员犯罪的司法程序设计却决定了是法司在主导着官员犯罪案件的司法审判过程。皇帝对罪状明显的犯罪官员如果一味袒护,不调查审讯,百官就会以守国家大法的名义不断进行催促,若皇帝一意孤行,会导致官员们强烈的指责和抗议。调查过程中皇帝只是听取汇报,对审讯不力的主审官员进行督促,必要时更换。法寺的判决意见,皇帝可根据犯罪官员的身份、品级、功劳、与皇室的关系等个体因素减轻处罚,但减轻的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不是毫无原则的为所欲为。比如太宗时期,祖吉守郡为奸利,事觉下狱,案劾,爰书未具。郊礼将近,太宗疾其贪墨,遣中使谕旨执政曰:“郊赦可特勿贷祖吉”。普奏曰:“败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国家卜郊肆类,对越天地告于神明,奈何以吉而隳陛下赦令哉?”太宗善其言,乃止。[8]8940皇帝也很难将法寺的判决再加重,这将面对法寺官员的抗议,因为皇帝也要遵循“法在有司,恩归主上”的原则。皇帝代表的是法律之外的恩宠,他的处断结果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参照意义。时间长久,也可能形成惯例,约束后来皇帝对相同案件的最终处理。
注释:
①相反的观点认为和王安石本人基本没有关系。参见李炜光:《乌台诗案始末》,载《读书》2012第3期,69—78页。
②狱吏作威作福的事情并不罕见,宋朝另一件诏狱——著名的岳飞案载:岳飞下大理寺狱,“飞初对吏,立身不正而撒其手。旁有卒执杖子,击杖子作声叱曰:‘叉手正立!’飞竦然声喏而叉手矣。既而曰:‘吾尝统十万军,今日乃知狱吏之贵也。’”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六,绍兴十一年十月十三日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8页。
③《宋刑统·杂律·违令及不应得为而为》:诸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谓律、令无条,理不可为者。事理重者,杖八十。疏议曰:杂犯轻罪,触类弘多,金科玉条,包罗难尽。其有在律令无有正条,若不轻重相明,无文可以比附。临时处断,量情为罪,庶补遗阙,故立此条。情轻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
④《宋刑统·名例·以官当徒除名免官免所居官》:私罪,谓私自犯及对制诈不以实、受请枉法之类。议曰:私罪,谓不缘公事,私自犯者,虽缘公事,意涉阿曲,亦同私罪。对制诈不以实者,对制虽缘公事,方便不吐实情,心挟隐欺,故同私罪。《宋刑统·诈伪·伪造宝印符节》:若别制下问、案、推(无罪名,谓之问;未有告言,谓之案;已有告言,谓之推),报上不以实者,徒一年,未奏者,各减一等。
⑤《长编》卷三十七的记载略有出入:至道元年五月甲寅,翰林学士王禹偁兼知审官院及通进、银台、封驳司,制敕有不便,多所论奏。开宝皇后之丧,群臣不成服,禹偁与宾友言“后尝母天下,当遵用旧礼”或以告,上不悦。甲寅,禹偁坐轻肆,罢为工部郎中、知滁州。
[1]曾枣庄.论眉山诗案[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3):59—64.88.
[2]杨胜宽.乌台诗案前后的苏轼[J].宜宾师专学报,1993(1):102—106.
[3]殷啸虎.乌台诗案与宋代法制[J].法治论丛,1993(5):63—66.
[4]李焘.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孔凡礼.苏轼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8.
[6]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记东坡乌台诗案[M].北京:中华书局,2004:667—668.
[7]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M].台北:宏业书局,1968:6.
[8]宋史编纂者.宋史·张璪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6:10570.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udicial Procedures of Crimes Committed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Wutai Poem Cas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GUO Yan-ting
(Party school of CPC Pingdingshan Municipal Committee,Pingdingshan 467000,China)
Wutai poem case is famous for the imperial edict imprisonment in the middl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case was directly presided over by the emperor and the imperial edict was required to imprison high-ranking government officials.Also the judicial trial was carried out through seven procedures one by one from impeachment to sentence by the emperor.It was the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mperial edict trial system.Besides,the final sentences were in line with the prevailing legal provisions of punishment.Judicial procedure was to make the official criminals plead guilty by the identification of crimes.Including the imperial edict cases,most could be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laws.After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ed various factors,the emperor delivered the conviction edict,mostly for the purpose of displaying the authoritative power,in addition to reprimand enlightenment,which was?the so-called“all should be owned to the emperor”.
Wutai poem case;Northern Song dynasty;crimes committed by government officials;judicial procedure
D929
A
2095—042X(2014)01-0057-05
10.3969/j.issn.2095—042X.2014.01.013
(责任编辑:朱世龙,沈秀)
2013-11-06
郭艳婷(1978—),女,河南扶沟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刑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