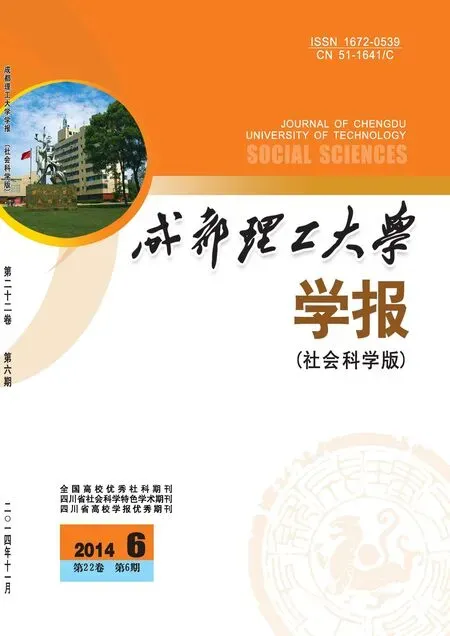惆怅的献祭
——《纯真年代》中阿切尔的伦理选择及动因诠释
秦丹丹
(金陵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南京 211169)
伊迪丝·华顿的《纯真年代》以对人物内心世界精湛细腻的描写而蜚声于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之林,“从心理和道德层面描写了那些生活在一个浮躁不安却又备受压力的社会中人的悲剧”[1]。小说在表现人物内心时,既有“画外音”式的解说,如上卷第二章及第四章中对曼森·明戈特太太果敢、刚毅性格的陈述;也有通过人物自身动作和神态间接揭示其内心情感,如上卷第五章对阿切尔母女感受的描写;而当人物思绪以意识流般的形式铺陈开来时,这思绪的主人,一定是男主人公纽兰·阿切尔。小说家华顿倾其满腔的情与爱,集中笔力描绘了这个纽约贵族男子订婚后却又陷于对另一个女人的爱恋中难以自拔的情感画卷。书中对阿切尔内心世界的直呈俯拾皆是,有的连篇累牍,几乎独成一章(如上卷第六章中阿切尔对婚姻的思考),有的穿插洒落在事件进程里(如下卷第二十二章阿切尔在去普茨茅斯的路上对内心的拷问),有理智审慎的思绪,有纷乱模糊的意识,有高尚人文的“超我”感悟,也有卑劣羞贱的“本我”欲望,还有的连阿切尔本人也说不清道不明。可以说,这是一个善感多思的头脑,同时也是一个含蓄内敛的心灵,小说对他的诸多行为选择并没有给出直白的解答。正如华顿本人所指出的:“人物性格的边界无法通过线条分明的方式得到重现,但读者却能像流水般悄然不绝地进入到相邻的人与事之中。”[2]下面拟从文学伦理学角度分析阿切尔的情感历程,逐一考察其伦理选择及动因。
一
小说描写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纽约上流社会的爱情故事,男主角纽兰·阿切尔与美丽温柔的梅刚刚订婚,遇到梅归宁的表姐埃伦并与她相识。埃伦厌恶她在巴黎的恶棍丈夫和痛苦的婚姻生活,只身回到纽约,正在考虑离婚。阿切尔与埃伦在交往中互生情愫,他瞒着梅多次拜访埃伦并与她促膝长谈。婚后的阿切尔不满乏味空虚的家庭生活,着了魔似地寻觅埃伦,创造与埃伦见面的机会。他瞒着梅一次次与埃伦约会,坚定地决定与她私奔到异国他乡。然而,三十多年后,梅因病去世,她与阿切尔的孩子们也都长大。在长子的安排下,阿切尔前往巴黎与独居的埃伦见面。可是,拥有了选择自由的他此时却选择失约,“慢慢站起身来,一个人朝旅馆的方向走了回去”[3]288。
初读这部措辞精微的小说,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深究。阿切尔既然爱上了埃伦,为何又选择与梅成婚?阿切尔既然决心与埃伦私奔,又是什么让他选择留下?三十多年后站在埃伦窗下凝望的他又为何选择默默离去?阿切尔的情感迁移和内心的巨变与他的“生命之花”息息相关,正如小说最后一章中阿切尔回首往事时独自沉思的,“他知道他失落了一件东西:生命之花……他所失落的一切都会聚在她的幻影里”[3]276。生命之花是美的,但选错物候开放的花却只能在风雨侵袭中凋零。已然与梅订婚的阿切尔却无可抑制地爱上了埃伦,是遵从理性意志的召唤还是释放自由意志的激情?这一段曲折迷离的纯真年代往事,是阿切尔内心理性意志和自由意志此消彼长的现实映射。正如聂珍钊教授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中指出的,“两种意志之间的力量消长,导致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变化和故事情节的发展”[4]13。阿切尔对其婚姻伦理身份的回归是惆怅的,他对家庭伦理秩序的重建是悲情的,他诸多看似令人费解的行为选择都可以从其伦理观的嬗变中得以作答。“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这是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5]。阿切尔的选择是对老纽约道德秩序的一份惆怅的献祭。
二
小说上卷——阿切尔婚前——共与埃伦有过四次私下会面。第一次是应埃伦之邀去看她。去之前,他思来想去,是否要告诉梅。一方面他意识到“他不再是个自由人”,“婚约”在束缚着他;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他拜访埃伦是按照梅的意愿行事,因为“梅特别希望他善待她的表姐”。因而他思量后做出的选择是“只要他乐意,他完全可以去拜访他的表姐,而无须事先告诉她”[3]54。看着埃伦的客厅,他想到梅会怎样收拾客厅,并因自己瞒着梅独自来见埃伦而心怀不安,他为没有告诉梅而懊悔,担心万一梅也来访,“发现他坐在这儿,只身在一位夫人家炉边的昏暗中等待着,对这种亲密的样子她会怎样想呢?”[3]55谈话高潮时,阿切尔因自己忘情地直呼两遍埃伦的名字感到有负于未婚妻梅,“他刚才居然叫她‘埃伦’,而且叫了两次……他觉得心头滚烫……他依稀看见梅·韦兰的白色身影——那是在纽约”[3]62。阿切尔自省的发现,以及圣奥斯特雷公爵和斯特拉瑟斯太太的来访,“天助神佑般地”[3]75止住了这种亲密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离开埃伦住处时,“他羞愧地发现,早上竟把这事(每天给梅送一匣花)忘了”[3]63。次日,阿切尔“说服梅脱出身来”[3]64一起散步,谈话间漫不经心地提了提送花给埃伦的事,但犹豫着还是没说出拜访之事。
初访埃伦,阿切尔甚为不安。内心深处,他明白一个定了婚的男子是不应该独自造访一个已婚太太的。受过良好家族教育的他明白自己的伦理身份——梅的未婚丈夫,明白埃伦的伦理身份——奥斯兰卡伯爵的夫人,更明白三人的伦理关系——埃伦是梅的表姐;然而,刚刚订婚的他对这一伦理身份和伦理关系还没有达到强烈的认同。因此,尽管他隐约地觉得此行不妥,但还是好奇地前往赴约。“阿切尔的好奇心超过了窘迫。屋子里的气氛是他从未体验过的,这种差异非常之大,以致他的局促不安已为冒险精神所取代。”[3]55交谈时他曾一度失言,险些逾越伦理界限,是内心的道德律以及圣奥斯特雷公爵和斯特拉瑟斯太太的不期来访,“天助神佑般地”[3]75制止了他。他之所以一再犹豫而终未启齿他的拜访行动,是因为他尊重刚刚建立的伦理关系,敬畏他们之间的伦理禁忌,珍惜他引以自豪的伦理身份。“按照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逻辑,人类由于理性而产生伦理意识,这种伦理意识最初就表现为对建立在血缘和亲属关系上的乱伦禁忌的遵守,对建立在禁忌基础之上的伦理秩序的接受和理解。”[4]18一见到漂亮的未婚妻,“占有者率直的幸福感清除了他内心深处的烦恼”[3]64,此时阿切尔的内心,理性因子占据上风,约束、质疑指导着自由因子,他的感情的偏向仍是她美丽的未婚妻,心灵坚守着的仍是他自出生以来便因袭着的伦理道德律。
第二次拜访埃伦,是在律师事务所老莱特布赖先生——抑或是梅家人的“指名”[3]75安排下,作为律师身份,前去办理埃伦离婚案。去之前,阿切尔是不太情愿的。这原因有对梅家人专横态度的反感,“这个家族认为他们有权强迫未来的女婿去干些什么,他被这种角色激怒了”[3]75;有对埃伦广交男士的看法,他不无尖酸地想到那些送鲜花给埃伦的老绅士们,想到埃伦对他们的信赖,想到在她面前,他只是一个能力有限的年轻人,她不需要他私下的安慰,也不需要他为了她的离婚案来公开地捍卫她[3]75。然而,当阿切尔读到埃伦丈夫信中对她与秘书私情的指责时,他明白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下,一旦这一秘密暴露给别人,埃伦将成为众矢之的。“‘发生这种事’,对于男人无疑是愚蠢的,而对于女人——不知何故——却是罪恶的”[3]77,想到这,“一股同情的洪流已经冲走了他的冷漠与厌烦。她像一个无人保护的弱者站在他面前,等待着他不惜一切代价去拯救”[3]。护花使者的豪情、争宠于埃伦的虚荣心,外加官方授予的律师与委托人这一身份关系,阿切尔堂而皇之地走到埃伦的门前。“他觉得自己被一种难以名状的妒忌和同情引向她那一边,仿佛她默认的错误将她置于他的掌握之中,既贬低了她,却又使她让人喜爱”[3]77。
为了确保会谈的成功,阿切尔对自己的身份定位非常明晰,“必须设想自己进入与过去(价值观)有着惊人差别的境界”[3]93。于是,他站在律师而非倾慕者的角度,劝告他的委托人放弃离婚。虽然阿切尔“读过各种各样的新书”[3],对埃伦的婚变向来持人道主义态度——宴请杰克逊先生时他就明确表示希望埃伦摆脱她那畜生丈夫[3]32-33。但当他亲自处理这桩案子时,他必须克制内心的欲望,选择站到大家族伪善的立场上。看似令人费解的举动背后隐而不露的是一个精明的上层谦谦君子在利害面前必然做出的利己选择。越位的伦理关系以及混乱的伦理秩序将会给他即将与之结合的家族带来耻辱,而他选择对埃伦婚案进行“审时度势”的处理,这无论在职场上(老莱特布赖先生那里)、婚姻上(梅·韦兰家里那里),还是情场上(埃伦那里),都为他赢得了夸赞和(他认为的来自埃伦的)崇拜。
第三次会面,是当梅随家人外出度假,阿切尔有感于自己生命无足轻重并为之落寞烦恼之际,他让信差给埃伦送去信函,询问可否前往拜访[3]102。他焦灼不安地等了三天才收到回信。得知埃伦在斯库特克利夫度假,他更改了原定的周末读书计划,收回对奇弗斯邀请的拒绝,直奔奇弗斯正在度假的海班克——离埃伦仅几英里处,到达后次日便独自前往斯库特克利夫。两人这次在庄园主住宅里的会面,感情的交流近乎直白,激情的斗争濒于高潮,尽管阿切尔“渐渐领悟到这些话的诱惑性”,他却努力“阻止这种感受”;尽管“阿切尔的心激烈地跳动着”,但他“不肯就范”[3]108;即使如此,“假如那种事情要发生,就让它发生好了”[3]108。阿切尔知道“就范”是有违他们伦理身份,为当时的伦理秩序所不容的。在强烈原始欲望的驱使下,幻觉产生了,“阿切尔想象着——几乎是听见——她从后面悄悄走上来,要伸开轻盈的双臂,搂住他的脖子。他等待着,正在为这一奇迹的即将来临而身心激动”[3]108。博福特的不期而至惊醒了阿切尔的白日梦,博福特与埃伦的暧昧关系令他烦躁不安,埃伦期期艾艾、不置可否的态度令他不解,出于对埃伦的不满和回击,他决定搁置她的来函和邀请,不予她任何复信,而是选择赶上当天下午开往梅度假地圣奥古斯丁的轮船。
婚前第四次会面,是在阿切尔恳求梅早点结婚却未得首肯之际,偶遇埃伦时他主动提出去见她。为了阻止埃伦外出约见博福特,他小心策划了他到达的时间和要谈的话题。为了“让她把今晚的时间给他”[3]135,他不愿再让含蓄的言辞、“口舌的障碍把他们隔开”[3]133,直言提起埃伦感兴趣的关于他的“另一个女人”的猜测。这次阿切尔一改他在庄园主住宅里的“不肯就范”[3]108,“时间的流逝使他不顾一切”[3]133,伦理、道德、禁忌、自持抛诸脑后,他只想在身体和心理上与埃伦更亲近,他亲吻、拥抱、下跪、恳求、冷笑、讥讽……情感的挣扎与起落似乎不亚于任何一位热恋中的人;可是埃伦是理智的,对家族名誉的顾虑令阿切尔的求爱再次无果。“她神色态度中那种不可思议的冷漠,以及他对她的认真所产生的敬畏,使他依然与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3]14这时,梅的电报不期而至,婚礼的提前举行将阿切尔从背离伦理的悬崖拉回,纯真年代的故事得以延续。
从阿切尔在订婚后到结婚前与埃伦的四次约会分析,阿切尔是有自己的道德操守和伦理底线的,他第一次拜访埃伦至始至终都伴随着不安和忐忑,他所接受的伦理观不断拷问着他的行为。然而从第二次会谈开始,他内心的自律和理性便让位于自由意志。他从一个订婚男子应坚守的伦理身份渐行渐远地走向偏移。频繁地与埃伦私下约会,长路跋涉前往求爱,缠绵悱恻难以成眠的夜晚,灵与肉的背叛……他在迷失了伦理身份的道路上愈行愈远。试想,假如与梅的婚期依旧遥遥无期,假如埃伦应许了阿切尔的求爱,那么阿切尔很有可能选择背弃与梅的婚约,与埃伦走到一起。但是出走以后又会怎样呢?阿切尔会对埃伦的感情负责吗?婚前的阿切尔与埃伦的感情,更多的掺杂了一个有爱但不真诚的男人证实自我的虚荣、与情敌一争高低的醋意、摆脱孤单寂寞的无聊、为自己利益考虑等不纯因素。三次的会见,阿切尔自始至终都纠结甚至记恨于埃伦与其他男人的交往。“她手下有博福特、有范德卢顿先生像保护神似的围着她转,而且中途等待机会的候选人(劳伦斯·莱弗茨便是其中之一)要多少有多少”[3]97,但与此同时,“作为已经订婚的人,他不愿太显眼地充当奥兰斯卡夫人(埃伦,笔者注)的保护人”[3]97,更不愿为他对埃伦所示意的爱作出任何承诺。甚至当埃伦考虑逃离婚姻的羁绊、重新争取寻找幸福的自由时,阿切尔出于私利考虑,充当起封建的卫道士,奉劝她个人必须成为集体利益牺牲品[3]90。四次约会,除了第一次是应埃伦之邀,后三次无不掺入了阿切尔虚与委蛇、无聊作戏的心理。因此,读到梅的同意提前结婚的电报,阿切尔自然会选择与梅成婚,这是当他的自由意志受阻、同时理性意志又被给予了一个不失体面的生存环境时,他所做出的退而求其次的精明选择。
三
婚后的阿切尔,越来越多地发现他与梅在诸多事情上的龃龉。纽波特射箭比赛时他遇到埃伦的姑妈梅多拉,唤醒了他珍藏心底的对埃伦的思念。在海滨凝望埃伦的背影时,阿切尔自问:“我是什么人?一个女婿——”[3]172这句设问是一句自省式的提醒,对自己伦理身份的提醒。他无法断定他是否能克制自己澎湃的情感,于是他选择让机缘安排,帆船越过了灯塔,埃伦依旧未转身,阿切尔默默离去。这相遇却不相见的一刻,让阿切尔的心发生了一种奇怪的变化。“此时此刻,却是韦兰的家,以及这个家里等待他的那种生活变得虚幻而无足轻重,而海滨那短短的一幕,他站在半坡上踌躇不决的那一幕,却像他血管里流的血一样与他贴近。”[3]174接下来,得到独处的第一时机,他借口为梅物色种马,启程到普茨茅斯寻找埃伦;借口出公差,连夜坐班车到波士顿寻找埃伦。他想起了为偷情而欺骗家人的花花公子莱弗茨,“一时间心中感到不安。但这并没有困扰他很久,因为他此时已无心细细琢磨”[3]182。当他们双双进入“专供情人幽会的庇护所(船舱的小包间)”[3]190时,阿切尔再次想到伦理关系中埃伦的身份,“一个逃离了丈夫的女人——据说还是跟另一个男人一起逃离的——很可能已经掌握了处乱不惊的艺术”[3]190。然而此时的阿切尔已然没有偷情的不安心理,在他看来,他们是“两位有许多话要谈的老朋友,找个僻静的处所是很自然的事”[3]190。事实也正如此,“阿切尔意识到自己对她的肉体存在有一种奇怪的冷漠……这种难分难解的爱却是表面的接触无法满足的”[3]193-194,清凉的海风似乎将他们的心灵也净化得澄澈通透,他们抛开了世俗的顾虑——“既不为意外遇上熟人而担心,也不因有那种可能而过分得意”[3]189——珍惜这历经了千辛万苦才换来的时间,互诉衷肠义、互剖金兰语。这次盛夏之日的海上约会,是纯净无邪的情感交流,是摈弃了任何私欲的柏拉图式爱恋,阿切尔的内心情感得以净化。埃伦“问心无愧的真诚……使他(阿切尔)心中充满一种温馨的敬畏”[3]196。阿切尔庆幸自己没有坠入邪念,没有亵渎他们之间圣洁的情感。“现在危险已经过去,他更是谢天谢地,自己没有受个人虚荣心与游戏人生的意念的诱惑而去诱惑她。”[3]196他明白埃伦的意思,只要自己不践踏伦理观念、不背离他们共同确立的“对他人忠诚又对自己忠诚”[3]196的准则,埃伦就会选择留在近处,不离开他。
两人再次相会是四个多月后的事了,这四个多月里,阿切尔无一日不在期盼和思念中度过。见不到埃伦的日子里,他只好在内心筑起一座圣殿,恭请埃伦执掌王权。渐渐地,这圣殿成了他理性行为的唯一背景;而对他所生存的现实生活,他却怀着一种与日俱增的虚幻感和缺憾感[3]209-210。终于,外婆中风的消息把埃伦从华盛顿召回,阿切尔自告奋勇去接站。在从车站往回开的梅的马车上,他们再次坐到了一起。然而,这却是一次不悦的交谈。埃伦无心地对马车的赞叹被阿切尔误解为讥讽,他立即提到埃伦心中的伤痛以示反击。“她提起他们坐的马车是他妻子的马车,激发了他报复的冲动。他要看一看,她听到他提及里维埃是否比他听到梅的名字更好过!”[3]228阿切尔焦急地想谈一谈他们俩未来的打算,然而在埃伦看来,“根本不存在我们!我们只有在互相远离的时候才能互相接近,那时的我们才能是我们自己。不然,我们仅仅是埃伦·奥兰斯卡表妹的丈夫纽兰·阿切尔和纽兰·阿切尔妻子的表姐埃伦·奥兰斯卡,两个人企图背着信赖他们的人寻欢作乐。”[3]231阿切尔幻想着和埃伦逃到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地方,埃伦却指出那样的地方与“旧世界根本没有区别,仅仅是更狭隘、更肮脏、更乌七八糟而已”[3]231。面临着本能与理性的交锋将会带来的伦理尴尬,埃伦的态度是现实的、理性的,她冷峻地指出现实是无法也不能割断的,只有两个相爱者的国度是子虚乌有的,放弃责任寻欢作乐是罪恶的;而阿切尔的痛苦源于他无法以超然的态度接受他们“在一起——却又不能结合”[3]229的现实,他的痛苦更源于他幻灭的憧憬。
接下来的日子是难熬的,憧憬幻灭的打击和单调窒息的家庭生活令阿切尔越来越烦躁,他的想法也越来越放纵可怕,他甚至凶残地想到梅的死才能让他解脱。“猛然间,对这个词的玩味使他产生了一个疯狂的念头:假若是她死了又会怎样?假若她快死了——不久就死——从而使他获得自由!站在这间熟悉的、暖融融的屋子里看着她,盼望她死,这种感觉是那样奇怪、诱人,那样不可抗拒。”[3]235此时此刻,阿切尔的理性不仅逾越了伦理界限,更逾越了人性的界限。根据文学伦理学的观点,“人作为个体的存在,等同于一个完整的斯芬克斯因子,因此身上也就存在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一旦人身上失去了人性因子,自由意志没有了引导和约束,就会造成灵肉背离……没有伦理,不辨善恶,与野兽无异。”[4]10所幸的是,兽性因子虽然蠢蠢欲动,但它没有吞噬阿切尔的人性因子,邪恶的念头并没有付诸邪恶的行动。虽然这可怕的念头一直支撑着他,他选择的是“听天由命,在思想深处的某个地方,怀着当他从图书室的窗口探身到冰冷的黑暗时所产生的那个主意。靠这股力量的支持,他不动声色地安心等待着”[3]236,等待着他可以孤注一掷的机会。
两人最后一次私下约会安排在出土文物博物馆,他们是来商讨他们的未来的。尽管双方都不愿将他们的感情降格为偷偷摸摸的私通,但价值观的迥异让两人的交谈再次出现分歧。埃伦坚持不能“对别人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3]248,然而阿切尔却下决心“无论她去哪里,他都会形影相随……自己不仅有足够的勇气,而且还迫不及待地期望着采取这种断然的行动”[3]242。在真爱的动力下,阿切尔决心背离自己在婚姻中的伦理身份,用自我伦理身份的牺牲给对埃伦的爱一个作答。
四
然而,在阿切尔的骨子里,传统伦理价值观仍然占据重要位置。梅的适时怀孕留住了阿切尔,大家族的联合绞杀送走了埃伦。“在小说的叙述中,‘纯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为了扮演‘家庭港湾’的角色和展现上流社会的稳定,梅写信给阿切尔,劝他回到自己的社会阶层和家庭中来。她发给埃伦的电报和与她进行的交谈占据了小说两个重要的章节,由此阻碍了阿切尔逃往外面世界的企图。”[6]
三十多年的忙忙碌碌令他的岁月过得充实而体面,尽管当阿切尔回首往事时,他知道他失落了他的生命之花,然而,他的心情是超脱平静的:“只要婚姻能维持双方责任的尊严,即使它是一种枯燥的责任,也无关紧要。失去了责任的尊严,婚姻就仅仅是一场丑恶欲望的斗争。”[3]276婚后阿切尔与埃伦的每一次会面,都是阿切尔伦理观中“爱”的概念的升华过程,与埃伦交谈时,阿切尔更多在意的,不再是埃伦手和脸庞,而是两人心灵的交汇与聚合;他更多领会的,不再是卖弄风情的不可思议,而是阅尽沧桑后为更多为他人考虑的内心准则。婚后的阿切尔,真正爱上了埃伦。然而他最终选择放弃一己之爱而留在梅的身边,承担起父亲对孩子、丈夫对家庭的责任,这就迈出了由一己之爱向利他之爱的步伐。阿切尔对其婚姻伦理身份的回归是惆怅的,惆怅在《辞源》里解释为,“因失意而伤感、懊恼”[7]1136。阿切尔不得不放弃了他的爱情和自由,将自己的身心献祭给了维系社会与家庭的伦理秩序。当他回首往事时,“他认为这应是一个人的全部追求”[3]276。三十年后物是人非,当阿切尔再次站在埃伦窗下,他默默转身离去。三十年前的选择已经铸就,这是一份无悔的选择,也是一份无奈的选择,阿切尔的选择,是对老纽约社会道德秩序的一份惆怅的献祭。
参考文献:
[1]Nina Baym.TheNortonAnthologyofAmericanLiterature. second edition, Vol.2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85:658.
[2]Edith Wharton.TheWritingofFiction. New York: Octagon, 1966:7.
[3]伊迪丝·华顿.纯真年代[M].赵兴国,赵玲,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4]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J].外国文学研究,2011,(6):1-13.
[5]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19.
[6]Pamela N. “Forms of Disembodiment: The Social Subject inTheAgeofInnocence.”TheCambridgeCompaniontoEdithWhart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9.
[7]吴泽炎,等.辞源(修订本)[K].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