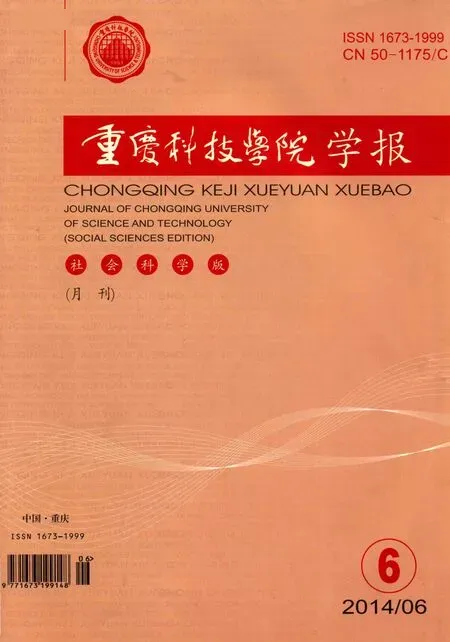《青门里志》的思想意蕴分析
汪 注
2012年初,美籍华人作家袁劲梅的长篇小说《青门里志》悄然问世。和她之前发表的《忠臣逆子》、《罗坎村》、《九九归原》相比,袁劲梅一方面沿袭了她所惯用的中西文化对比视角,忠实履行文人对社会变迁进行“进谏”的文化职责[1],另一方面则在国民性分析的话语框架外自创新意,通过横向构设双重文化场域,纵向排布多个历史时期,设置出视域开阔的棋盘式布局,描摹出了当代中国屡屡以除旧、布新为鹄的,却总以混乱、内耗收场的悲剧,同时通过审视与剖析,揭露了20世纪举国皆以“快”、“新”为宗旨的社会变革诉求的荒谬与群体理性缺失之害。
一
《青门里志》(下文简称《青》)以“我”(小说女主人公苏邶风)的生物——人类学观察日志总领全篇,在日志里,“我”与黑猩猩、博诺波猿朝夕相处,记录这两种灵长目动物的群体行为。随着观测的深入,“我”日渐发现了它们与我们(人类)之间在群体秩序的建立与维护、资源分配方式等方面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譬如族群内部的等级制及对异端、越规、犯上的容忍程度为零,等等。这些“共通点”诱使、引导“我”返回历史源流的上游,开始回忆、追索。由此生发,情节的幕布缓缓拉开,一幕幕活剧得以上演。
“我”出生、成长的地方叫做青门里,这是个高级知识分子扎堆、家家弦歌绕梁的所在,离此地不远处,名唤剪刀巷,那里的常住民无一例外都是胼手胝足的劳苦大众。前者如同自成一统的乌托邦,以一道竹篱将世界分成彼此无涉的两端,身处其中的文化人因自我身份而自矜,彼此之间总是以礼相待;后者自明太祖问鼎金陵起便是一种顽固的存在,它聚拢、消化着数目庞大的城市贫民,人际之间以血缘划分亲疏远近,既讲求尊卑有序,也讲究锱铢必较。总体而言,青门里象征着“文明”,剪刀巷象征着“传统”。在文革的风暴未曾侵袭到这两处以前,青门里、剪刀巷的居民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秉承着清静无争的生活理念。对于“我”和青门里的同龄人小喇叭、小竹子、陈榆钱、贺燕吟而言,这是个尽情欢乐、无忧无虑,身体和心智像野草一样疯长的金色时代。然而,文革的号角声惊天动地而来,打破了往昔的宁静安逸。
最先对青门里展开“革命”行动的是女红卫兵领袖皮旦,她出身军人世家,根正苗红,本是一个的唇红齿白、举止文雅的温婉女子,却在一夜之间成了带队抄家、组织游街的风头人物,率领一众男女干将呼啸来去,在青门里抡起皮鞭,对一向以清高自许的文化人痛下毒手。而剪刀巷内,贫民之子魏青山也纠集了一干“战友”清剿“封建”余毒,破除四旧。然而,皮、魏所掀起的“革命”并不能撼动“文明”、“传统”的坚韧内核:戴上高帽、挂上胸牌的臭老九在批斗会结束之后,仍旧会以书为友、坐而论道,不改书生本色。在风暴最烈的时刻,陈榆钱的爷爷、儿童文学翻译家陈仪铨虽横遭侮辱,也坚持给身边的孩子们讲好听的故事,全然不计己身之荣辱,用童话世界为孩子们的想象力和无瑕性灵搭建了一所最后的庇护所。和皮旦遥相呼应,魏青山一伙在剪刀巷闹起了“革命”,他搜出并焚烧了堆积如山的古董、字画、珍玩,甚至连麻将、牌九也没有放过。这边厢,“旧物”的灰烬余温尚存;那边厢,剪刀巷的老住户们已经搓起了自制的麻将:
在剪子巷,“人”另有一番定义。那么疏松,那么情感,那么自私,那么现实,那么血脉相连,又那么曲里拐弯。外面再革命,这里麻将还是要打的。死了人,还没死的也要活出乐子来[2]184。
就这样,“文明”与“传统”愣是熬过了充斥着暴力与杀戮的“史无前例”。斗转星移,所有人都一下子跨上了改革开放的快车道:“人们还没看清道路,就驾着车跑上了一条新路。自己也不知道方向,干脆不管,以功利论成败。当时的流行词语是‘白猫’、‘黑猫’,意思是:猫不要再互相吃了。团结起来,手段不限,抓老鼠去。‘老鼠’就是致富”[2]239。为了“抓”“老鼠”,青门里的陈榆钱、剪刀巷的八爷率先做了吃螃蟹的人,他们分工协作,通过贩卖古籍字画赚了大钱。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钱竟做了推倒“文明”、摧毁“传统”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当中,为了重现十里秦淮的风情,明初建成的街坊民居被整体拆除,使一贯信奉“秦淮河的水照样要在黑瓦白墙下流,鸡鸣寺的钟照样要在杨树柳枝间敲。”[2]69的青门里、剪刀巷居民们真真切切地感到了无“根”之苦与丧“家”之疼。伴随着“根”和“家”的覆灭,知识分子也好、平民百姓也罢,都在急剧分化:早年的保姆吕阿姨慢慢老去、曾经才高八斗的蔡教授罹患老年痴呆、八爷公开与养女姘居、小竹子等儿时玩伴和“我”或为求学或为谋生远走他乡,穿越数百年沧桑、磨难而沉淀下来的朴素信念(如重情尚义)、诗性情态(如吟诗作画)、和谐关系(守望互助)在市场经济的冲刷磨洗下纷纷崩解离析、一去不返。可问题是,对“过去”的惋惜遮蔽对它的反思,而潜藏、埋伏在“过去”中的罪与恶压根没有得到应由的省与罚。怀旧浪潮中,非理性的毒素披着“革命”、“改革”、“发展”的外衣继续淤积、流布。
文革的烟尘甫定,开放时代扑面而来。岁月更替,“人”依旧是原班人马。在尘埃落定之后,人们默契地选择了集体性健忘。当年在皮鞭下残喘的青门里老人们保持着缄默,当年散布红色恐怖的大小干将也对往事闭口不谈。一时间,所有人都在自我漂白,以不了了之的方式遮盖尴尬的记忆,匆匆跨过时间的门槛,迈入举国皆狂的经济大发展运动里。斯时斯刻,人兽性中的嗜血因子被暂时抑制,而贪婪因子则被唤醒并剧烈发作:小喇叭从事地质勘探搜求大自然的储藏;小竹子从事建筑设计,按照上级单位的指示到处“扒”上年头的“房子”来创造效益;陈榆钱先是去美国镀金,后返回祖国大搞现代主义而赚得盆满钵满,而“我”小时候捡来的女婴安无为也顺利地从乡下进城,完成身份蜕变,开了餐馆并做了陈榆钱的第二任太太;皮丹早早地倚靠高贵的门阀做了父母官,专管拆迁工程……看上去大家都比以前要“好”,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但是,“新”的表象背后,传统文化被荼毒、破坏的速度不仅没有片刻停滞,反而在大幅加快。从人性的大悲剧中走来,人的觉悟竟不曾出现,而人的欲望倒是压倒了一切。青门里、剪刀巷的生命最终因此而被终结:随着一栋栋全新的住宅楼、一条条全新的仿古商业街拔地而起,它们消失在了“老城区改造”的烟尘之中。
二
《青》的字里行间中,时时闪现着群体性癫狂。
在作品的开篇部分,作家就以孩子的视角叙述了文革前与文革中的暴力场面,用看似不动声色而非触目惊心的笔触来叙述普遍暴力。群体非理性是它的主要成因,有识者曾评价道,文革是执政者“猴性”与“虎性”与当代中国人改变中国社会的混合产物,释放巨大的反社会破坏力[3]。而在苏邶风的视域中,文革则是“黑猩猩政治”的人类翻版:在黑猩猩的群落里,集权、驱逐及杀死异类都属于维护整体秩序的常态。而这段由人类亲手缔造的特殊时期中,人的社会属性被扁平化,人我关系被简化、二元对立化。对待“与共产党领导的‘新群体’不一样”的文化人,标准的处理程序是先扣“帽子”,再抡“棒子”,那些“在旧社会是名人,还留过洋”“有了‘敌人味’,犄角一样让大家看不顺眼”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统统“用‘帽子’给标记出来。这种‘帽子’原来就是‘人等’标记,让没有这些经历的人去‘仇恨’,抓住‘戴帽子’的就可以打。敌我一定要分清”[2]41。依照美国当代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 Zimbardo)的解释,常人变成刽子手有赖于陌生化(即通过掩盖受难者、施刑者两者的身份,消除施刑者的罪恶感)与标签化(对待刑者添加“有罪”标签,强化其原罪感)为首的心理机制协同发挥作用[4],兼以法制荡然,打杀“坏人”不仅无罪、反而有功,出身高贵的青少年们体内的嗜血性完全爆发,变得六亲不认、面目狰狞,对传统文化及其载体(鲜活的生命)实施无情剿灭。深陷红色的漩涡,人的理性缺位,兽性占据绝对优势。而在《青》的更多篇幅里,作家则尽力引导读者将注意力从可感可见的非理性表现转向对蕴藏在种种理性背后的非理性(无论是意识还是行动)的叩问与思索。为了实现这一写作目的,袁劲梅并不直陈“非理性”的涵义,而是为我们呈现出了三种别具意味的“理性”来做反向解释。
首先是文化人“自带”的奴隶的理性。青门里的“先生们”多多少少都具有这一恶根性,它使得他们纵使引颈受戮犹“冷静地”心忧社稷,无辜受难仍“清醒地”自污不已。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我”妈在饱受造反派监禁、毒打数月后侥幸逃出罗网。伤痕累累的她想到的并不是鸣冤或躲藏,而是毅然独自进京“面圣”,要向毛主席反映,“说他老人家被坏人蒙蔽了。为了表示忠贞、剖白心志,她在临行前给“我”留下了一封遗书,表达了对党、对国家的忠诚不二。而“我”在若干年后才弄懂了她那些文字的真正含义:“她要把自己当做一句金光闪闪的诗句,和其他的一些环环圈圈缠在一起,一起呈’螺丝钉‘状,真心实意地站在那里,以维护圣事为天职。情愿为圣明着急,却不愿意怀疑圣旨的合理性”,这使“我”不由地感叹,“哪国的文人也没有我们中国的文人投入。有这样的文人,是中国的福气,也是中国的悲剧。要是一个体制拿它的人民当牺牲品,而那个当了牺牲品的人民还对它感恩戴德,为它献身尽忠,这个体制何等了得! 没三千年的工夫,成不了”[2]142。应注意的是,“我”妈绝非食古不化的村愚野老,而是进化论的虔诚信徒,早年也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走上街头,解放后在大学里担任“马哲”讲师,恰恰是这么一位昔日的热血“愤青”,竟在此时心甘情愿、一往无前地踏上“文死谏”的老路,其文士品格的顽固与文化性格的孱弱无不令人嗟叹。与“我”家比邻而居的蔡教授则更是另类:他具有自主发明了新中国第一台机器人的才智,却缺乏起码的情商,他专爱用自制弹弓射杀街坊饲养的鸡鸭,理由是干扰自己午休。文革初,蔡教授因不堪受辱而触电自杀,未成功,遂蜗居陋室不复问世事,以扑克自娱,做了个颓然的遁世者。
青门里中的文化人够“理性”,青门里外的老百姓也有他们专属的生存“理性”,即为了“活着”而不惜伪饰真相、放弃追究、委曲求全的“理性”。它显露的是平民阶层耻感文化中最脆弱、敏感的部分:为了邻里间的和睦、人际之间的和谐,大家都 “不提过去”、一致“向前看”。偶有分歧,作为劝解者的第三方都会及时出现,用随身携带的食物、随意寻找的话题等手段岔开纷争,寻找到新的共同点,达成即时的和解。处于避祸的考虑,“我”的父母找关系将“我”送到剪子巷寄养一段时间。刚进巷口,“我”就亲历了八婶子、四姑娘为偷水一事而产生的争吵。两人正在赌咒发誓、不可开交之际,同住一个大院的吕阿姨用分食冬瓜汤、馒头的方法将摩擦轻轻化解,两人竟亲密地如同姊妹一般。出于对“和”的追求,凭借“求”“和”的技巧,百姓之间总能化“昨天的仇人”为“今天的亲人”,且不管明天是敌是友,恒久地共同生活在一块狭窄的地域。“民”的生存智慧(或者说生存理性)驯化他们时刻恪守屈居社会资源分配链条末端的本分,既一味地畏“官”、怕“官”,又每每想从“官”的那里分得一份好处。文革结束后,造反派头头魏青山为皮丹背了黑锅,在身陷囹圄多年后,出狱了的他和皮丹有过多次交集,但他从不向皮丹要个说法,相反,摄于皮丹后来的现实身份(区城建局副局长)及其可能带来的实际益处,魏青山对皮丹唯唯诺诺,颇有敬畏之心。在一次聚会中,“我”刻意跟皮丹念及旧事,皮丹顾左右而言他,魏青山急忙将“我”拉到一边,示之以不念旧恶的“大义”。对比之下,魏青山的沉静倒让“我”的冲动显得不顾大局、有失偏颇了。
如果说前两种理性带有一定的地域性、阶层性、群体性,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教育程度、文化水平影响的话。那么,文本中的第三种“理性”则是全民性的,那就是为了达到急速变革而不计后果、不计手段。诚然,寻求国家、社会、个人的发展本无可厚非,然而,“国强”、“民富”两大主题培育出的却是非理性、自戕式的荒诞行径:为了征服近代以来的贫弱、落后,中国人先是膜拜科学,续之以顶礼政治,于今则迷信发展。逾半个世纪的各个阶段,中国人不断地“革”旧、“立”新,唯“快”是举,唯“彻底”、“全面”是问。吊诡的是,促使祖国获得新生的强大愿望(或者说伟大理想)孕育出的乃是循环不止的变乱与层叠不休的否定,形成了当事人无法、无力跳出来的怪圈:一方面,陈爷爷留洋求学、学成后著书报国是爱国;“我”的父母奔赴解放区、洗心革面也是爱国;蔡教授放弃海外优越条件、北雁南归同样是爱国;年轻人造反行凶也可以是爱国;搞活经济依然是爱国……另一方面,清政府被陈爷爷否定、陈爷爷被“我”父母否定、蔡教授被政府否定、“我”父母被造反派否定,造反派被改革派否定……变动的,是否定的主体与客体,不变的,是否定自身。就在这一轮轮走马灯也似的轮替中,中国社会受到一次次的冲击(或曰洗礼)并酿造一系列灾难,要么以人命为代价;要么以大规模破坏为祭品。换言之,每次的理念先行(有动机良好的理性思考和设计为先导)得到的都是事与愿违的反向冲击,致使20世纪的中国时而暗流汹涌,时而云谲波诡,时而迂回曲折,时而翠荡瑶翻,无一时不在“动”,无一刻不在“变”,就是没有一分一秒的“静”与“思”。
三
值得悲叹的是,正是基于前文所述的三种 “理性”,青门里、剪刀巷里的芸芸众生饱尝恶果:知识分子被肆意打压迫害;平民百姓本打算过“帝力与我何有哉!”的安稳日子,可秉承鸵鸟政策的人们一逃不过日本人的残酷屠戮(见《青》第四章),二躲不开眼花缭乱的社会运动。而置身这一连串的 “变”、“动”中,蹉跎了近百年的几代中国人愣是一直没能“立”起来,值得一次次游移在黑猩猩(喜好破坏、厉行专制、爱搞权力斗争)和博诺波猿(放纵肉欲、沉溺食货)这两个结点之间,沿着“变—乱”怪圈无穷无尽地兜圈子,没有逃逸、挣脱的自觉,并因此没能成为敢于自揭其短、勇于反思己过、不再故作忘却、懂得向被自己戕害的人大声说出“对不起”的真正的“人”。
此外,袁劲梅还摹画出了“变—乱”怪圈的深层荒谬性:无论圈子中的因素怎么旋转、沉浮,圈子固有的封闭性都将使它们得以变相的保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的“新”本来只是“旧”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重复与再现,只不过,某些因素会在特定的时候显示(或隐藏)地比常态更明显些而已。沿着这个理路再进一步,我们甚至可以追问:数代中国人的奋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无谓的“折腾”?对“新”、“变”的疯狂沉迷有没有真实的价值?……文本中所闪现的细节似乎在为这些问题提供相应的答案:与老建筑、旧街巷被彻底摧毁而文化风尚整体庸俗化相同步,男性对妻妾成群的嗜好没有变(八爷有钱了之后,立即与领养的丫头姘居生子)、权力寻租的官场生态没有变 (皮丹最终从公务员变成了海外寓公)、狎妓招嫖的传统再次复苏、繁荣(曾为青楼女子的吕阿姨在90年代被“后起之秀”找到,后者高薪聘请她做“顾问”,培养“小姐”们的职业操守,云云)。
由此观之,打破怪圈才是中国人的务本之道。对此,袁劲梅屡次提到“民主”这个关键词。在她看来,民主并非政治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更不是“权力交易,你杀我的价,我杀你的价。你一派不容我一派,我一派不容你一派”[2]105,而应被理解、解释为个人从自我的良知良能出发,以协商的方式与他人建立共同承认、合力维系的思想、道德体系,进而既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也容忍他人在前述体系框架内的行为,从而实现包容与正义。造就这样的民主委实不易,它要存活,“只能存活在把正义和道德当做信仰的人群中”[2]252,不仅如此,民主还需要其信仰者培育建立在行为反省、觉悟、修正机制之上的自控与约束力,“等到有勇气打人的人,也有勇气反省了,才是民族的觉悟。被打的人、没参与的人,反思来反思去都不够”[2]125。
在《青》中,陈爷爷为“我”们所说的最后一个故事是,“古希腊人说,人的灵魂由三部分组成:两匹马、一个驭手。一匹好马,白色,毛色光亮,器宇轩昂,追求真理、人格和光荣,不需要鞭策。另一匹坏马,黑色,眼睛不好,耳朵不好,脾气大,力气大,上蹿下跳,满身兽性,要不停地鞭打,才能跟着白马拉着车子往前跑。所以,驭手只能是理性。驾驭好马,管住坏马”[2]133。即是走出怪圈的要诀之一。
时移世易,沧海桑田。为追赶时间,人们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快步伐、不辨路标、不顾来时,姑且埋头向前冲刺,罔顾探究自己所奔驰的路径是直是弯、抑或巨大的循环,于是续之以奔命无功、人我相残,终以徒劳心力收场。这样的悲—喜循环理当被废止,人们有理由为冲破怪圈的羁绊而放慢脚步、放眼四顾,卸下奴才的“理性”、文过饰非的“理性”、“唯发展论”的“理性”,脱胎换骨,探索在新世纪获得新生的可能。
[1]傅小平,袁劲梅.文人对社会的责任在于“进谏”[N].文学报,2012-8-16.
[2]袁劲梅.青门里志[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3]杜兰.文革是一场反社会运动[J].二十一世纪,1996(4).
[4]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M].孙佩妏,陈雅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