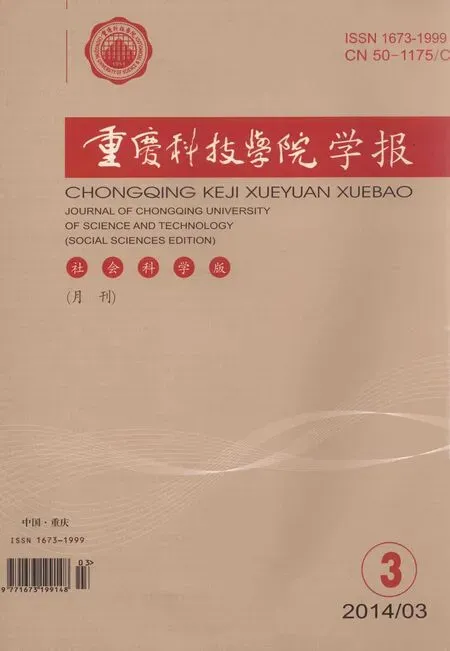对我国劳务派遣法律规制的思考
刘 勇
为迎合劳动力市场的多样化与灵活性,以劳动力租赁为内容的劳务派遣逐步发展起来。早在1997年,国际劳工组织就将临时雇员纳入到了劳动法以及社会保障法的范畴。我国改革开放后,不断进行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探索。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正式确认了劳务派遣的合法地位。但伴随社会变迁的加速和立法中的诸多模糊,近几年来劳务派遣关系主体之间纠纷不断。2012年,我国《劳动合同法》围绕劳务派遣展开修订,修订后的《劳动合同法》虽对劳动者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大,但仍存在不少缺陷。
一、新劳动合同法中关于劳务派遣规制的变化
(一)对派遣单位经营资质要求进一步提高
新《劳动合同法》提高了从事劳务派遣业务组织的市场准入门槛。首先,将派遣企业最低注册资本要求从五十万提升至二百万,增强了派遣企业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其次,增加要求派遣企业必须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固定的经营场所和设施”。第三,引入派遣企业设立的前置许可程序,进一步规范了劳务派遣市场,遏制了劳务派遣企业遍地开花的现象。这些新要求从法律层面提升了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权能,促进了整个劳务派遣行业重新洗牌,促使行业升级转型与国际劳务市场接轨。
(二)明确提出劳动者拥有“同工同酬”的权利
新《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用工单位应当对被派遣劳动者实行与本单位同类岗位劳动者相同的劳动报酬分配办法。该条款旨在对劳动者权利的保障从法律制度层面加以落实,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同工同酬”的实效性。《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权利,不受任何歧视”。对同工同酬原则的细化,是对劳动权利的尊重,也是反对劳动歧视的重要内容。
(三)对派遣岗位做出了进一步的限制
原《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适用的岗位仅做出了原则要求,修订后的《劳动合同法》则对“三性”类岗位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首先,将临时性岗位的存续时间限定在不超过六个月;其次,对辅助性和替代性岗位的含义也进行了具体说明,最后,针对当前劳务派遣用工主流化的趋势,对劳务派遣的用工数量与比例做出了原则性限制,强调了劳务派遣仍然只是劳动力市场用工形式的补充。
(四)增大了劳务派遣中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56条许可登记制度的规定,对未经许可的劳务派遣单位,有违法所得的,可处 “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五万元以下罚款”。配套保障了许可制度的实施;同时,还提升了派遣单位的处罚标准,由原来 “每人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提升至“每人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通过加重法律责任的形式将劳务派遣行业的发展拉回立法本意,引导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
二、新《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规制的不足
(一)未明确规定劳务派遣的法律适用范围
我国法律未对劳务派遣概念做出明确立法界定,造成法律适用上的困惑。
首先,劳务派遣与外包容易混淆。劳务派遣将传统劳动关系中的“雇用”和“使用”相剥离,劳动法律关系、劳务法律关系和一般民事合同关系交织其中,若不从立法上明确界定,则极易把承揽合同、劳务外包与劳务派遣混为一谈。外包实质上是在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形成一种劳务法律关系,劳动者权利的保护由承包方负责,这是不同于劳务派遣的[1]。《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就有用工单位利用劳务外包来逃避劳动合同法上对劳务派遣的硬性规定。
其次,转派遣与反派遣无法规制。转派遣,是指用工单位将派遣机构派遣到其处的劳动者再次派遣。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用工单位不得自设劳务派遣单位进行派遣,但对于用工方的二次派遣行为没有规制。劳动者被派遣的中间环节越多,对劳动者的中间盘剥概率就越大,如果用工单位进行了二次派遣,实际上其已成为了一个职业介绍机构或者派遣单位,这与我国的《就业促进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相抵触,必须明确禁止。目前我国某些地区已经出台了相应文件对这种转派遣行为进行规制。反派遣,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后,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而是要求其与劳务派遣公司订立劳动合同。一般派遣应当是派遣公司向不特定用工单位派遣员工,一旦采取定向派遣,实际上劳动者的雇主是用工单位,但用工单位却规避了部分本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第三,未对劳务派遣做出具体的分类。从其他国家的立法来看,一般将其划分为常雇型和登记型两类。常雇型派遣是指派遣机构将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一般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派遣到用工单位。对此类派遣,无论劳动者是否被派出,派遣公司均有给付工资和福利的义务,并且劳动者能够享受到一般劳动合同的解雇保护。登记型派遣是指劳动者在派遣机构登记,当其被派遣时,劳动关系在派遣期间成立,派遣公司也仅在劳动关系成立期间才向劳动者支付工资。对于登记型派遣,如果派遣期间届满或派遣公司与用工方的派遣协议解除,则劳动者与派遣公司的劳动关系随之解除。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务派遣从类型上看,本应属于登记型派遣,但又限制了两年以上的劳动合同期限,这势必会使劳务派遣企业为满足两年期限的要求而将此压力转移给用工单位,且劳务派遣面向临时性岗位,派遣企业是否有能力充分调配各类企业的岗位资源仍然存疑。而对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能否适用于劳务派遣,《劳动合同法》也未做出任何规定,导致相关劳动争议产生。
(二)“同工同酬”的落实不容乐观
我国《宪法》和《劳动法》均规定了“同工同酬”的基本原则,《劳动合同法》修订后对“同工同酬”进行了一些规定。但在运行中,“同工同酬”仍然难以落实。首先对于“工”和“酬”二者之间的标准,没有法律法规进行具体规定。劳务派遣面向各行各业,不同行业之间近似岗位的待遇千差万别,用人单位和用工单位本身的薪酬设计也各不相同,除去工资之外的福利待遇是否纳入“同工同酬”的范围,以及恶意的异地派遣以降低派遣工人社保缴费等问题仍然无法处理。
其次,据王全兴教授的观点,劳务派遣无法做到“同工同酬”的主要症结在于劳务派遣偏离了市场定位,本应作为补充地位却被滥用成主流化、低成本和歧视性的用工形式[2]。全国总工会《国内劳务派遣调研》指出,派遣工主要集中在国企和机关、事业单位之中。一方面,国企、事业单位由于体制转型和经济改革,存在许多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员工,这些员工之中工资虚高的不在少数,并且不能随意降低工资,如果派遣工人实行“同工同酬”,使用虚高的工资标准,则会增加企业不必要的成本,亦不符合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国企中的员工管理从正式工与临时工的“旧二元”转变为了正式工与派遣工的“新二元”,本质上无太大区别。派遣工人仍然被贴上“二等职工”标签,升职渠道堵塞,员工激励缺失,严重影响了职工的稳定和企业的发展。
(三)“三性”岗位的界定仍有争议
首先,新《劳动合同法》将劳务派遣的岗位适用从“一般”改为了“只能”,但从国外劳务派遣市场的发展来看,诸如IT、绘图设计、翻译等行业的劳务派遣呈现上升趋势。这类劳动者的权利保护意识强,利益受损机会小,将劳务派遣限制在“三性”类岗位,无法满足各行业的多样需求。
其次,修正案将临时性岗位的存续期间限定在六个月,又规定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签订两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当派遣期限届满时劳务派遣公司必须按月支付劳动者最低工资。在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限制比较严格的情形下,劳务派遣机构将会消极招工,使本来比较难就业的劳动者群体更难就业。此外,必要时可否申请适当延长工作期限也未规定,造成用工单位使用劳务派遣工人不便。
第三,对于辅助性工作岗位中确立的主营业务没有相关标准。在司法领域,企业并不当然受经营范围的限制,在用工企业中的派遣岗位上认定非主营岗位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过程,实际操作中难度较大。
最后,《劳动合同法》第66条还对用工单位使用派遣用工的数量进行了规制。但其规定的是在“用工总量”上不超过一定比例,这就为被派遣劳动者在岗位的使用比例上留存了可操作空间。而对于在用工比例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适用岗位没有遵循“三性”的限制,法律责任如何确定亦不明确。
(四)劳务派遣中的责任分担不明确
首先,《劳动合同法》将劳务派遣单位作为用人单位履行对劳动者的义务,又同时规定用工单位给派遣者造成损害应当与劳务派遣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使得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的责任划分出现虚化,《劳动合同法》中架设的“共同雇主责任”被模糊。
另外,新《劳动合同法》将“劳务派遣单位给劳动者造成损害与用工单位形成的连带责任”修订为“用工单位为损害行为主体时,与派遣单位承担连带责任”。这排除了派遣单位对劳动者造成损害时用工单位的连带责任,降低了被派遣劳动者获得有效赔偿的几率[3]。
(五)其他应当规制的部分
1.辞职权缺失。辞职权是劳动权利中的一项基本权利,《劳动合同法》对被派遣劳动者解除合同的规定排除了提前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变相造成了被派遣劳动者与普通劳动者的不平等。
2.经费来源不明。《劳动合同法》第64条赋予了劳动者选择参加派遣单位或用工单位工会的权利,但对于工会经费的支出由谁支付却没有规定。工会经费在实际中无法落实,会阻碍劳动者参加工会活动,参加工会的权利被架空。同样,对于用工单位进行培训所支出的费用由哪方支付也不明确,派遣属于弹性就业,用工单位支出培训费用后,难以获得有效回报,而劳动者亦不直接为派遣单位劳动,派遣机构也没有较大动力支付培训费用,培训也会成为用工单位敷衍的一项法律义务。
3.《劳动合同法》第65条第2款规定了劳务派遣中退回员工的情形,但对于第42条规定的用人单位禁止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能否适用于禁止退回被派遣劳动者未进行规定[4]。如孕期妇女被退回后,虽能通过派遣机构领取按机构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报酬,但与在用工单位实际工作领取的报酬之间仍有差距,且这一部分劳动者很难在被其他用工单位接收,这部分的成本如何弥补应予以明确。并且,被派遣劳动者被退回后,能否享有法律上的继续履行请求权也是一项空白。此外,员工被退回后,如果派遣单位重新进行派遣能否属于对劳动合同的变更,如果员工不愿再被重新派遣,出现了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可否适用经济补偿也未规定。
4.由于劳务派遣三方关系的特殊性,劳动合同在实际履行时是发生在用工单位所在地,而《劳动合同法》规定了约定试用期的权利在用人单位一方,那么试用期的效力是否及于用工单位。并且,用人单位只能规定一次试用期,但劳务派遣往往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内存在被派遣劳动者被派遣到多个不同用工方,试用期条款如何适用也是一个难题。
三、对劳务派遣法律规制完善的建议
(一)对劳务派遣进行明确的法律定位
我国《劳动合同法》虽使用了“劳务派遣”一词,但实际运行中却会被各种形式包装起来的 “劳务派遣”所规避。有台湾学者指出:“以一个非专法规范劳动派遣相关事项之法治而言,劳动合同法中所罗列者,已有相当程度涵盖所可能发生之法律问题。 不过,最大的遗憾是合同法中未能先针对劳动派遣予以定义,否则将来也许会出现劳动派遣与承揽关系之认定疑义也说不定”[5]。在立法上厘清劳务派遣的概念,可以减少企业规避法律的机会,减少法律适用的模糊性。
此外,还应当建立许可证制度的例外情形。例如,同一集团下内部公司之间的员工借调以及对驻外使领馆的劳务派遣应当排除在许可证制度外。
(二)对适用劳务派遣的岗位采取列举式说明
修订后的《劳动合同法》虽有对“临时性”的刚性描述,却过于僵硬,而“辅助性”和“替代性”的标准仍然模棱两可。从域外法律规范来看,对派遣岗位适用大都使用列举式说明。如韩国规定了可以使用劳务派遣的26种岗位以及禁止使用劳务派遣的10类工作。日本禁止在建筑业、保安业及海港运输业等特殊行业使用派遣工,英国、荷兰等也对派遣用工的限制做出了列举。
对于派遣期限而言,美国、英国等均未规定劳务派遣的最长用工时间。比利时则规定在法定期限内得到工会许可,可以延长派遣的时间;韩国可以通过派遣关系三方协商延长派遣的时间,日本则通过立法根据派遣业务的种类规定了不同的时间。我国可以参照日韩法律根据当事人之间的协商以及不同行业的属性灵活确定劳务派遣的用工时间。
(三)设立保障金制度和信息报告制度
尽管对派遣公司提升了最低注册资本的要求,但注册资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抽回。对此,许多欧美国家设立了保障金制度,以保证派遣公司能够支付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如在西班牙,派遣公司必须提供全国当年最低工资25倍或最近一年工资支出十分之一的担保金。法国的劳务派遣公司必须在金融机构中存一定数目保障金,金额由政府定期调整。我国在设立许可证制度的同时也可参照设立保障金制度,以使劳动者在派遣业务中的风险最小化。
(四)改变以罚款为主的处罚形式
《劳动合同法》修订后,虽然对用工单位与派遣单位的罚款力度有所增加,但相较于其违规使用派遣员工所获得的利益,仍然较低。如果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在《劳动合同法》中以“转正”作为用工单位承担的主要法律责任形式[6],以罚款作为补充性惩罚,那么不仅能够有效遏制反派遣的情形,同时也能强制企业遵循“三性”岗位的适用原则,为被派遣劳动者提供最有利的法律救济渠道。
(五)明确一般性规定的适用范围
劳务派遣“雇用”和“使用”的分离,出现了试用期、退回、解除合同等一系列不同于一般劳动法律关系中的问题,对《劳动合同法》赋予劳动者的一般权利应当为被派遣劳动者予以确认,针对劳务派遣中某些特殊的地方,应当进行适当变通,使《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的规制更为全面和具体[7]。
(六)鼓励行业协会的发展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行业协会对派遣行业的规范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英国的招聘与就业联盟通过《良好行为规范》和其他审查项目对劳动力服务市场进行指导与监督。德国也有派遣企业协会对派遣单位、雇员、客户、政府、大众等之间的关系进行规范。并且,行业协会通过与工会签订的集体协议可以更好的保障劳动者的权益。我国也可引导行业协会的建立和规范化,同时也能够减轻政府部门的职能负担。
四、结语
劳务派遣市场的发展是伴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入而产生的。此次《劳动合同法》的修订致力于更好的规范劳务派遣市场,本次修订在劳务派遣的岗位适用、派遣企业的资质要求、劳动者权利的保障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然而,由于立法“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以及长久以来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双轨制”运行等原因,使得此次修订后的《劳动合同法》在对劳务派遣进行调整的实效方面仍让人存疑。结合国外相关经验和本国的具体国情,对劳务派遣从法律层面进行的再思考,是为理顺劳务派遣中的法律关系,以期在劳务派遣中更好的实现劳动正义。
[1]郑东亮.劳务派遣的发展与规制:来自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的调查研究[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1.
[2]王全兴,杨浩楠.论劳务派遣中的同工同酬:兼评2012年《劳动合同法修正案》[J].苏州大学学报,2013(3).
[3]谢德成.我国劳务派遣法律定位的再思考[J].当代法学,2013(1).
[4]李余文.劳务派遣法律适用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法律硕士学位论文,2013.
[5]邱俊彦.劳动基准法释义:施行二十年至回顾与展望[M].台湾: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212.
[6]苏应生,陈春梅.浅析《劳动合同法(修正案)》对劳务派遣的影响[J].中国劳动,2013(2).
[7]董保华.论劳务派遣立法中的思维定势[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