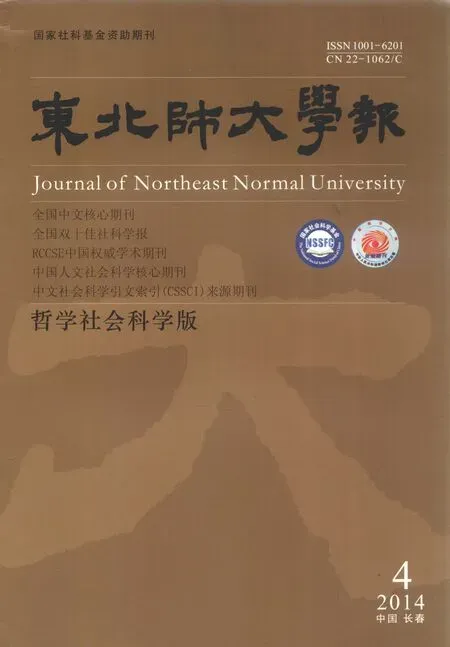美学视阈中的综合艺术教育
张 波,张 群
综合艺术教育的繁荣与发展已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一大重要景观。在综合艺术教育日益繁盛的时代,对其进行哲学澄清,既是艺术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哲学具体化、现实化的最重途径。让综合艺术具有哲学性,使其能够与美学进行形而上学照面,能够使综合艺术教育的实践主题、价值追求与形上意境得到本质的提升,从而能够真正将综合艺术教育与人性的生成与完善结合起来。综合艺术教育作为具有兼容性、丰富性和代表性的艺术教育形式,与人生命的双重性、矛盾性、开放性与未完成性是内在契合的。以美学的视阈来诠释综合艺术教育,能够将其历史性、社会性、文化性与多元性特质与现代人的素质养成和自由个性培养有机结合起来。
一、直指世界观构成的综合艺术教育
综合艺术教育观念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盖蒂艺术中心。目前,“综合艺术教育”这一教育模式遍布于美国各个学校使其中小学艺术教育实践活动迈上了新的台阶,从而使得综合艺术教育也成为当代教育学与哲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在教育实践环节中,综合艺术教育模式利用艺术创作、艺术史、艺术批评和美学四个学科的互动互补关系,将艺术教育建构成一门交叉性的人文学科,从而提高艺术教育效应与受教育者的综合人文素养。在此意义,综合艺术教育使“美就是人类经验的组成部分”[1]成为可能。
综合艺术教育的提出与实践,首先是对艺术教育理论创新与拓展。“教育并非是成熟的结果,而是一种文化的发明。”[2]138综合艺术教育的理论包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美学前提、教育理论前提和艺术教育理论前提,是一种均衡的艺术课程。综合艺术教育采用综合教育方法,其教学方法和课程计划不仅仅局限于青少年,而是普遍适用于艺术教育基础之中[3]。它以多学科为基础,其实践核心是将艺术批评、艺术史、美学和艺术创作融入课堂教学。因此,综合艺术教育是追求一种均衡的艺术课程,对来自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创造与美学这四门学科的内容给予了同等的重视。
这样的艺术教育形式,更为当代人世界观的建构开创一条别样的路径。我们知道,一种全面的教育能培养个人全面思考的能力,使个人通过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通过综合艺术教育使受众熟知各艺术学科的各个方面,能够用艺术媒介来表达思想,能够读懂艺术中的内在价值、评论艺术、了解艺术史以及美学中的基本概念。综合艺术教育给予受众是一种自我解放的手段,是一种在其他文化形式中不可能获得的内在自由。
二、建构“审美生活”的综合艺术教育
“美”是人生命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维度。“美学之父”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首先对美的本质进行了哲学反思,在学科的意义上强化美的形而上学意义,也提出了建构审美生活的必要性。尽管13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美的事物是那些让人心旷神怡的东西”[4],但是,这种知觉与美关系的阐释还没有真正确立建构审美生活的自觉意识。对此,英国艺术教育家里德的观点极具启发性,“美学,或称知觉科学,涉及感性知觉与形式组合两个活动阶段,而艺术也许包含着比情感价值更大的东西。在探讨美的观念时,我们曾引入了一些仅同艺术史有关的见解;艺术的目的旨在传达感受。它与美的特质,即通过一定形式传达的感受常常混在一起。无论我们怎样界定美感,我们务必先从理论上加以证明。抽象的美感仅仅是艺术活动的基础。艺术活动的阐述者是活生生的人,而人的活动容易受到各种生活激流的影响。”[5]
建构审美生活的艺术教育体系是当代艺术教育中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在上世纪中期艺术教育的转型期是巴肯明确提出教育改革应该包括“审美的生活”。而后诸多的学者从艺术教育的人文主义本质、艺术教育提升审美经验的独特意义,以及反思艺术教育本质方面推动了巴肯教育理念的实践与创新。弗尔德曼认为,当时的艺术教育领域过分重视艺术表演的发展,忽视了学生其他方面的创造性潜能,如对艺术的欣赏、批评与反思。艾斯纳批评了以艺术创作为中心的艺术教育,他认为艺术教育包括三个学习领域,即创作、批评与历史领域。L.谢普曼强调艺术必须成为学校课程表上的一门基础课程。艺术教育的对象是面向全体学生。她认为对艺术品的审美反应与艺术创造同等重要;审美反应不仅针对“学校艺术”,也针对传统艺术杰作乃至现代的各种艺术形式[2]20。
质言之,如果在艺术教育中仅以美学的方式对审美经验与艺术评价进行自然的批判性反思不可能真正建构“审美生活”。而综合艺术教育则通过培养受众对艺术的深层次理解、强化艺术与生活的结合、转换思考艺术的思维方式、确立体验与评价艺术品的批判性原则、反思艺术存在与表现形式、提升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的视野与技巧、体验艺术发展史的辉煌与曲折等方式,将美学的抽象反思与艺术的鲜活及感性结合起来,使之成为生命与生活的现实内涵。综合艺术教育不单是某种特殊的教育手段与方式,而是建构“审美生活”的生活实践。这样的教育,使人现实的“感性活动”[6]不仅锤炼了创作与欣赏艺术的人的身体,而且建构了人的现实的形上生活。
三、综合艺术教育的“美学”内涵
美学研究的抽象化与艺术教育的具体化使得人们在艺术教育中更关注艺术史和艺术评介。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美学反映了艺术与生活的结合,美学审视着我们思考艺术的方式,美学检验的是概念性问题,是源自人们言行方式的问题”[7]10。美学侧重两个方面:其一,审美价值与人们用以解释、评论某艺术品的标准;其二,艺术品获取意义与内涵的途径。但是,我们也更应该关注艺术品通过直接再现真实的世界获取意义。甚至可以这样认为:第一,艺术的本质、艺术体验以及人们用来谈论艺术的基本概念都是理解“我们是谁”、“我们有什么样的价值观”等问题的一部分;第二,考察艺术信仰能够增强人们对单个艺术品的敏感性,使人更具辨别力,更好地选取某种艺术来欣赏、保留与创造;第三,艺术教育的普遍价值在于以美学视阈分析艺术本质、形成适用于视觉、造型及触觉艺术的阐释与评价原则[8]。
因此,综合艺术教育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在于拓展艺术教育的内涵,更是以具体化的形式与感性的方式培养学生的美学潜质。首先,综合艺术教育以助学生提高理解特定艺术作品和艺术整体能力的方式,使学生在困惑与争论中获得具体的美学体验。其次,当艺术作品、谈论艺术史、艺术评论真正回归到生活世界之中时,任何在综合艺术教育中所提出与探讨的问题就自然会超越对艺术的直观理解,将对人生命的本性与本质及其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思考和艺术勾连起来。再次,综合艺术教育在教育中力求将美学与受众经验联系起来的方式,既是认真对待受众的艺术理解力的重要方式,还能在受众的艺术体验中直观和表征其世界观[7]257。
在一个艺术教育与艺术本身都深刻变化的时代,将价值观念的教育与价值体系的建构贯穿于综合艺术教育中就是一种必然。从艺术教育与艺术本身变化的特点上讲,其变化是多样化、非连续性,甚至是碎片化与解构性的。帕森斯与布洛克将这种变化称为“后现代主义”。而且,当今时代充斥着其他文化和传统的信息,艺术家与大众不能自动地形成相互理解,而艺术教育的目的也就是为了促进这种理解,艺术教育要更具有反省性和哲理性。拉尔夫·史密斯所讲,“人们从艺术中得到的最大利益,是一种理解,对世界的理解,一种与自我认识或心理洞察不同的东西。在美术博物馆待上几个小时,我们再走出来,会发现眼前的世界不同于原先看到的世界。我们看到了过去没有看到的东西,而且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观看。这些表明我们学到了知识。……‘一件物品或事件是如何以艺术品特有的方式起作用的事实,向我们证明,这种作用方式可以通过某种指涉功能,造成一种全新的观看世界和创造世界的方式。’……艺术造就一个最高级的善,对于这种善,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去追求和培养。既然古德曼认为艺术品向我们提高什么的过程不仅需要时间,而且需要训练和培养,我们就有理由认为,正规学校的教学理应把这种训练和培养包括进去。”[7]60
我们知道,在多元化与全球化的时代,多元与平等、差异与尊重、民族与世界等之间的矛盾冲突越发具体与现实。因此,如何看待不同群体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不同艺术形式与作品的社会内容与功能如何体现特定群体的价值等问题就成亟待解决的问题[7]52-53。如果我们想要回答此问题,我们有意识地进行探究,那就是美学研究,因此美学研究也是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是如何思考某种艺术形式,我们可以说美学自然地产生于艺术和生活中。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美学家,美学课程就是要努力持续地追踪这些问题,并且给予足够的理性严谨。
四、结 语
艺术哲学是与多种艺术课程相联系的,与艺术创造、艺术批评、艺术历史,以及对艺术作品的概括性理解相联系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把美学与其他课程的学习相联系,艺术教育学习的各种课程是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则最为清楚地表现于美学。我们希望学生们既能接触艺术,自由自在地喜欢艺术,但也能够拥有审美的眼光去理解艺术,学习其有价值的东西。在对综合艺术教育的思考与实践中,美学占有特殊的位置,而美一直是美学的中心题目,而对于美的分析则被认作是美学的主要题目,美学像艺术一样难以被准确定性,因为它是随着艺术家的实践而变化的。当新的意义出现时,它们不是取代旧的意义,更多的是与之共存。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审美文化传统,我们要建立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美学体系,当然也需要吸收国外先进的美学成果,同时,针对本国的艺术教育实践的研究,弘扬我国民族优良的审美文化,当然,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还不足。
当前,我国艺术教育研究中对美学的研究要有新的突破,笔者认为要做到两个必须:首先,必须要在美的哲学方面下功夫,没有哲学基础,就不能讲清任何美学问题。美学的发展不能停留在对审美文化研究的层次,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方法和内在规律,所以,从美学的实际出发,以哲学为指导,美学研究才会有新的突破;其次,必须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在艺术教育中,美学研究作为一门科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下,不能局限于精神范围之内,而要必须发挥自己在实际生活中应有的社会作用,要引起社会对其的重视,要能够更好地生存与发展。
[1][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90.
[2]R.A.Smith.Discipline-based Art Education [M].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1989.
[3]Dobbs,Stephen M.Learning in and through art:aguide to discipline-based art education [M].U.S.A:The J.Paul Getty Trust Press,1998:4.
[4]R.A.Smith and A.Simpson.Aesthetics and Arts Education[M].Urbana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onois,1991:18.
[5][英]H.里德.艺术的真谛[M].王柯平,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7.
[6]涂良川.马克思“感性活动”的形上意义[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31-34.
[7][美]帕森斯·布洛克.美学与艺术教育[M].李中泽,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8]王伟.当代美国艺术教育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