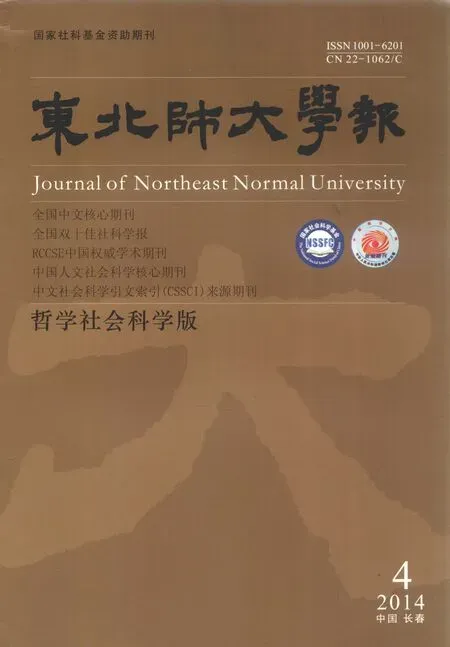语言类型学视野下语言、思维与文化关系新探
李锡江,刘永兵
(1.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吉林长春130012;2.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语言类型学视野下语言、思维与文化关系新探
李锡江1,2,刘永兵2
(1.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吉林长春130012;2.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语言、思维与文化关系之辩是久富争议的哲学论题,曾一度在语言相对论的推动下达到顶峰,后又在普遍语法理论的强势兴起下陷入沉寂。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语言类型学的跨语言对比研究为这一论题提供了新的证据,使之以“新沃尔夫主义”的崭新面貌重回公众视野。在语言类型学视野下,本文将重点围绕普遍认知与即时思维之争、普遍语法与双轨进化之争这两大关键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对语言、思维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作出新的求索和解读。基于语言类型学的新沃尔夫主义向我们揭示:不同的语言类型本身蕴涵着不同的文化模式和思维方式,这对加深人类自我认识、丰富语言学理论以及推动二语习得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语言类型学;语言、思维与文化;重新解读
虽然从古希腊时期关于语言、思维和文化关系的论述就已开始,但把这一话题推向顶峰的当属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又称语言相对论)。该假说自诞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饱受争议,命运多舛。在经历了初期广受推崇的辉煌之后,20世纪60年代后期逐渐式微。现在看来,语言相对论走向衰落具有内外双重因素:其外因主要在于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理论的强势兴起,同时柏林和凯基本颜色词实验所揭示不同语言中语义普遍性的客观存在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其内因则是学界批评萨丕尔和沃尔夫提出语言相对论的依据只是翻译过来的零星词汇或例句而不是通过实证方法得到的系统数据,因此不足以证明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因果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特别是一批基于语言类型学的研究为语言相对论提供了新的证据[2-3],使其重新焕发生机,出现了所谓的“新沃尔夫主义”(Neo-Whorfism)[4],这标志着语言、思维和文化关系的研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新沃尔夫主义认为把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简单粗暴地二分为语言相对论和语言决定论是对原著的曲解或误读。新沃尔夫主义者们在研究方法和实验设计上都做了创新,并强调从跨语言对比研究中获得系统数据来重新考察和解读语言、思维与文化之间的微妙关系,从而使得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
语言相对论能够重新回到公众视野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当代语言类型学研究在背后的推动。早在1992年,面对学界对语言相对论的质疑,露西就高屋建瓴地指出语言相对论的出路在于系统的跨语言对比研究,即语言类型学研究[5]。当代语言类型学不再以给语言分类为目标,而主要是通过跨语言比较来发掘人类语言共性,同时探索人类语言变异的边界,对语言外部特征的深层动因给予解释。过去20年里,语言类型学的发展突飞猛进,成果丰硕。其中斯洛宾、伊凡斯和莱文森的研究对于新沃尔夫主义发展的贡献巨大。前者基于对运动的跨语言对比研究重新论证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为言而思假说”(Thinking For Speaking Hypothesis)[2][6]。后者在对多种语言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生物—文化双轨进化论”(Bio-cultural Hybrid)这一新的语言观[7],重塑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进而对乔姆斯基基于普遍语法理论的语言观提出挑战。他们的研究为揭示语言、思维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基于此,本文将重点围绕普遍认知与即时思维之争、普遍语法与双轨进化之争这两大关键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对语言、思维与文化关系这一久富争议的哲学论题作出新的求索和解读。
一、普遍认知抑或即时思维
学界通常把沃尔夫的以下两段话作为对语言相对论内涵的经典阐述:“‘语言相对论’就是使用明显不同的语法的人,会因其使用的语法不同而有不同的观察行为,……也势必会产生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世界观。”“语言系统(即语法)不仅是一种用来表达思想的再生工具,而且它本身也在塑造我们的思想,规划和引导个人的心理活动。……我们从自然现象中分离出范畴和种类,并不是因为它们客观地呈现于每一个观察者面前;相反,……它们是通过我们的大脑组织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我们大脑中的语言体系组织起来的。”[8]
我们注意到在论及语言的作用对象时,沃尔夫使用了“世界观”、“思想”、“心理活动”、“范畴”和“种类”等词汇,而这些词汇在现代认知科学领域分别涉及“概念”、“概念化”和“范畴化”等术语,分属不同层次。“概念”是指对客观世界中相同或相似事物的心理表征,它依据对某一特定概念的原型性和代表性构成。“概念化”是指发生在人脑中的认知过程,是对既有概念的激活。“范畴化”则是指对客观世界事物进行主观概括和类属划分的心理过程。显然,在沃尔夫的理论阐述中并没有明确这些术语的差别,我们只好将其笼统地概括为普遍认知。但这一模糊表述却为后人解读“语言相对论”留下了发挥空间,导致了理解上的分歧,同时更成为该假说招致诟病的症结所在。其中,尤以语言影响世界观这一观点受到的抨击为最。
在这一背景下,斯洛宾摒弃了沃尔夫的“世界观”和“思想”等提法,谨慎地提出了“为言而思假说”。借鉴塔尔米的语言类型学研究(根据路径在不同语言中典型表达形式的不同,塔尔米将世界上的语言分为“动词框架语言”与“卫星框架语言”两种类型),斯洛宾设计并实施了系列实验。他选择说不同语言的多国儿童为实验对象,要求他们在看过无字连环画之后对其内容进行口头复述,所用语言涉及英语、德语、汉语和希伯莱语等多种。实验目的是考察不同类型语言对相同场景中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表达方式的异同。结果显示,不同类型语言的描述主要在四个方面存在差异[6]:(1)运动事件中时间的标记(即时态和体)方式不同。例如,英语和西班牙语语法中具有进行时态标记,而德语和希伯来语语法中则没有。(2)运动方式和方向的编码方式不同。在卫星框架语言中,动词表达运动的方式,小品词和介词表达运动的方向。在动词框架语言中,运动方式的表达是可选择的,在语句中并不一定得到体现。(3)描述视角或表达施事和受事、主题和焦点、前景和背景的方式不同。(4)语篇连接手段不同,如选择使用句子连词、非限定动词或省略结构等。面对这些差异,斯洛宾富于创见地提出,它们反映出了不同语言类型背后说话者的认知差异,从而把语言相对论和语言类型学联系起来。
对有特定时序的事件进行序列体验,将物体置于一定位置并不是人类独有的能力,其他动物也可以做到这些。但语言要求我们将事件作为“进行”或“完成”状态和将物体作为“静止状态”或“运行终点”范畴化。这样,人们的经验经过语言的过滤而成为语言化事件。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把事件语言化过程中,“我们在儿童时期所学的语言不是对客观世界中立无偏的编码系统。相反,每种语言都是对人类经历世界的主观导向,而这种导向却影响我们说话时的思维方式”[6]。“每种语言都训练它的使用者在谈论事件和经历的时候关注不同的方面”[6]。久而久之,人们在说话时就会习惯于采纳母语最常用语言编码视角去看待事件。因此,可以说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在描述相同运动事件时的思想体验是不同的。在说话时,不同语言的说话者要对物体和事件的特征进行选择,一方面要适合概念化,另一方面要易于被说话者所用语言编码[2]。这一心理过程就是斯洛宾所谓的“为言而思”(thinking for speaking),它是指“说话者在说话过程中调动起来的一种特别的即时(on-line)思维”[2]。值得指出的是,斯洛宾把语言相对论所论述的语言(language)和思维(thought)的关系转变为说话(speaking)与说话之前发生的即时思维(thinking)的关系。换言之,斯洛宾认为操不同语言者对在现实世界中经历事物的大脑意象完全相同,但不同语言使说话者在把思维变成语言时从这些大脑意象中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包括选择哪些因素、这些被选择因素的组织形式等。即“为言而思假说”不认为语言会影响人的概念认知,而只是影响人在说话过程中的即时思维方式,即概念化,从而回避了语言影响“普遍认知”的笼统论述以及由此产生的质疑。从这个意义上说,“为言而思假说”把人们对于语言与思维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
二、普遍语法抑或双轨进化
前面提到,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理论的强势兴起是语言相对论走向衰落的直接外因。普遍语法理论提出“人类生物天赋的一部分就是具有专门功能的‘语言器官’,即语言官能。它的初始状态是一种基因表达(即普遍语法),类似于人类视觉系统的最初状态,为人类所共有。”[9]普遍语法为各种不同的语言提供了共有的基本参数,以此推之,无论人们的国籍、肤色和性别,只要在出生时语言官能没有损伤,那么编码在语言官能中的普遍原则与参数设置的可能范围都是一样的。普遍语法因为对儿童习得语言的完美解释有力地驳斥了行为主义的“白板说”和“环境决定论”,从而使得相对主义不得不让位于普遍主义。
在雄踞西方语言学界近半个世纪后,普遍语法理论新近受到严峻挑战,伊凡斯和莱文森提出了一种新的语言观——生物-文化双轨进化论。两位学者曾先后在世界多地对多种语言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并分别就人类认知的几个基本概念域(如颜色、空间和亲属关系等)在不同语言中的表达方式做了对比研究[10-11]。这里仅以颜色为例。莱文森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种名为“Yeli Dnye”的土著语言进行了调查,经考察未发现它与任何已知语言具有语系亲缘关系。莱文森发现在该语言中没有表达“颜色”的上义词,因此在该语言中不能提出“某物是什么颜色?”一类的问题,只能间接地问“某物是什么样子”,而这样的问题针对的却不只是颜色,还涉及诸如大小、味道等其他知觉信息。和上义词“颜色”的缺失相匹配的是该语言中也没有明确表达具体颜色的下义词。在涉及具体颜色表达的时候,该语言中主要有两类表达方式:第一类使用表物名词的重叠。如kpaapikpaapi(白)。kpaapi在Yeli Dnye语中是指浑身纯白的凤头鹦鹉。可见,对颜色的表达是通过表物名词所指(nominal reference)实现的。另一类使用短语。如yi kuu yaa(绿)。yi kuu yaa在Yeli Dnye语中意为“生树叶,没有被煮熟的树叶”,即嫩树叶。调查还发现,该岛上居民并不掌握彩绘和印染等技术,他们所能接触到的都是自然界颜色而没有人工合成颜色。前面提到,柏林和凯曾就颜色认知提出了著名的基本颜色词理论[1]。他们通过对20种分属不同语系语言的调查发现,任何语言中都有一定数量基本颜色词的存在,这些基本颜色词构成了各种语言色彩语码系统中最基本的部分(称为焦点色),它们是人类色彩范畴化的基础。各语言对于焦点色的基本认同体现了人们色彩视觉的神经生理普遍性。莱文森的调查表明,在Yeli Dnye语言中,没有专门表达颜色的词语,也没有基本颜色词的存在,对颜色的表达是借助实物通过隐喻的方式实现的。该语言对色彩的范畴化也由于该社会文化中与颜色有关的科技的落后而受到限制。毋庸置疑,Yeli Dnye语言作为反例否定了柏林和凯的基本颜色词理论的普遍性。
一直以来,先天论(Nativism)认为语言的形式(即句法)和内容(即语义)基本上是由生物内在或先天因素决定的。形式由乔姆斯基提出的“普遍语法”主宰,内容则受福多的“思维语言”控制。根据普遍语法理论,语言之间的差异是表层的,这种差异可以通过构建一个更为抽象的深层句法结构来消除。至于语言内容,福多认为人类的大脑禀赋具有生物普遍性,语言是人类大脑中业已存在的“思维语言”的外在表达,因而不同语言表达出来的概念范畴也带有普遍性[12]。但是基于各自所作调查,伊凡斯和莱文森指出世界上语言的结构差异,或语言的多样性(diversity),远远超出认知科学家的预测。根据国际权威的民族语言网(http://www.ethnologue.com/)统计,目前世界上的语言大概在5 000到8 000种之间,其中约82%的语言使用人口不超过100 000人,约39%的语言使用人口不超过10 000人,而语言学家的研究对象尚只限于为人们熟知的500种语言样本,对于更多的语言,学界还缺乏系统的调查和深入的了解。两位学者认为不同语言之间在每一个层面(语音、词汇、句法和语义)都存在根本差异,很难抽取出各种语言之间的共性规则,更不可能找到一个彼此共享或涵盖一切语言的单一结构。因此,他们坚称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具有局限性,因为其理论的建立仅仅是依据对少数欧洲语言的分析概括,无法对世界上众多语言表现出的多样性或变异性作出充分的解释。相反,伊凡斯和莱文斯提出语言是生物和文化的混合体,是生物和文化双轨进化而来的产物,生物-文化双轨进化论这一新的语言观可以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
支撑起生物-文化双轨进化论的有三条论据:第一,语言的生物性表现在人类具有共同的生理基础,这包括相似的发音器官、适宜的声音频率、加工言语的大脑区域、相近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经历等。生物性是语言的基础,也使得跨语言交际成为可能。其次,语言的文化性表现在语言结构的出现是有意交际行为的非有意结果。文化通过两种机制来选择语言结构的出现:其一是语言使用频率对语言结构的影响。由于社会生活需要而被经常重复的语言结构会逐渐演变成语法的一部分。其二是语用推断和语法化对语言结构的影响。根据语用会话理论,话语除了字面意义之外还有语用意义。语用意义的理解要靠说话人彼此共享的背景知识或世界知识,而这一过程就涉及文化因素。经由文化作用而逐渐语义化或语法化的语言结构可以脱离当初的语言环境而独立存在,但是文化因素却已经不露声色地隐含在其中了。语言的多样性或差异性是多样性文化的体现,是文化选择的必然结果。最后,语言不是造物者之功,而是进化的产物。语言的进化由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交织而成。前者指早期人类日益增强的掌握语言的神经能力,后者指人类所用语言的日渐复杂和多样。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日益增强的神经能力允许更为复杂多样的语言发展进化,反过来复杂多样的语言又会选择更为发达的神经生物平台。生物—文化双规进化论既解释了为什么唯独人类能够拥有学习掌握高级语言的能力,又解释了众多不同的语言“软件”何以能够在同一质的人类“硬件”中得到运行发展。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建立在笛卡尔“灵肉”两分的哲学思想之上,人为地割裂了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相比之下,生物-文化双轨进化论主张语言同时具有社会和认知双重属性,人与社会、语言与文化是有机的整体,主客体相互交融,内在统一,这更加符合西方哲学认识论的历史发展趋势。
三、结论与启示
过去20年里,基于语言类型学的跨语言对比研究为语言、思维和文化的关系这一论题提供了新的证据和诠释。其中,“为言而思假说”用“即时思维”取代“普遍认知”,细化了语言相对论的内涵。生物—文化双轨进化论则突出强调在语言进化中社会文化因素与生物认知属性相互匹配缺一不可。二者共同向我们揭示的命题是:语言类型本身即蕴涵着特定的文化模式和思维方式,这一认识给我们带来了重要启示。
第一,从哲学层面,对于语言、思维和文化关系的争论历时已久,但基本都囿于空泛的哲学思辨,难免陷入莫衷一是,各说各话的窠臼。而基于语言类型学的新沃尔夫主义研究则重视调查和实验,突出跨语言对比分析的必要性,以翔实系统的数据对这一古老哲学问题作出了确凿有力的新论证,从而把人类的自我认识又向前推进一步。
第二,从语言学层面,生物—文化双轨进化论的提出丰富了现有的语言学理论。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侧重从心理层面,即天赋能力(大脑中的语言机制),去解释语言现象。与普遍语法理论相比,语言类型学通过跨语言比较对人类语言的共性进行概括,对语言的变异进行探索,从生物和文化(或心理和功能)双重视角去解释语言现象。如果说现在判定这一新语言观的是非还为时尚早,那么它所引起的强烈争鸣无疑对于促进语言学的理论发展善莫大焉。
第三,就二语习得而言,如果说不同的语言类型本身蕴涵着不同的文化模式和思维方式,那么,当学习者在学习二语的时候,其受母语及文化影响所形成的认知思维模式必然会影响二语习得,具体表现出来就是语言迁移。“概念迁移假说”就是新近发展起来的专门关注这一领域的语言迁移理论[13]。依此观之,二语习得不应是行为结构主义视角下单纯语言习惯的形成,也不是心灵认知主义视角下可以脱离实际的真空学习,而更应该是基于人类真实社会文化生活体验的语言学习[14],牵涉到全新文化模式的介入以及思维方式的转变。因此,基于语言类型学的新沃尔夫主义研究为二语习得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
[1]Berlin B,Kay P.Basic color term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
[2]Slobin D.Learning to think for speaking:Native language,cognition,and rhetorical style[J].Pragmatics,1991(1):7-25.
[3]Levinson S.From outer to inner space:Linguistic categories and non-linguistic thinking[A].In Nuyts J.&Pederson E.(ed.),Language and Conceptualization[C].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13-45.
[4]Levinson S.Spa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Explorations in Cognitive Diversity[M].Cambridge:CUP,2003.
[5]Lucy J.Language diversity and thought:A reformulation of the linguistic relativity hypothes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6]Slobin D.Adult language acquisition:A view from child language study[A].In Perdue C.(ed.),Adult Language Acquisition: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s[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239-252.
[7]Evans N,Levinson S.The myth of language universals: language diversity and its importance for cognitive science[J].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2009(32):429-448.
[8]Whorf,B.Language,Thought,and Reality.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C].Edited by John Carroll.Cambridge,MA:MIT Press,1956:212-213.
[9]Cook V.Chomsky's Universal Grammar:an Introduction[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30.
[10]Levinson S.YélîDnye and the theory of basic color terms[J].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2001(10):3-55.
[11]Evans N.Context,culture and structuration in the languages of Australia[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2003(32):13-40.
[12]Fodor J.The language of thought[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13]Jarvis S.&Pavlenko A.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M].New York:Routledge,2008.
[14]刘永兵.西方二语习得理论研究的两种认识论取向——对我国外语研究的启示[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86-92.
A New Interpret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Thought and Culture from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LI Xi-jiang1,2,LIU Yong-bing2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The debate 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thought and culture once reached a crest spurred by the Hypothesis of Linguistic Relativity.With the rise of Chomsky's Universal Grammar,however,Hypothesis of Linguistic Relativity fell into decline.Since 1990s,a number of cross-linguistic studies based on linguistic typology have shed new light on this controversial issue and eventually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Neo-Whorfism.By focusing on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issue of general cognition versus on-line thinking,and Universal Grammar versus Bio-cultural Hybrid,this paper intends to make a new interpret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thought and culture.It is revealed succinctly that any language of certain linguistic type entails a distinctive mode of thought and pattern of culture.This enlightenment contributes considerably to deepening the self-knowledge of human being,enriching theories of linguistics,and promoting the research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inguistic Typology;Language,Thought and Culture;Reinterpretation
H0-05
A
1001-6201(2014)04-0148-05
[责任编辑:张树武]
2014-03-1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740050);吉林大学科学前沿与交叉学科创新项目(2012QY014)。
李锡江(1974-),男,吉林双辽人,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讲师,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永兵(1954-),男,吉林白城人,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