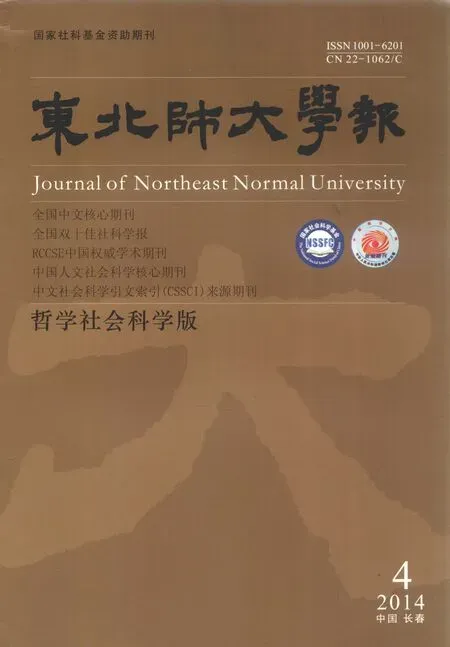政治的马克思何以可能?
——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宋晓杰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开封475004)
政治的马克思何以可能?
——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宋晓杰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开封475004)
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对《大纲》的激进政治阅读,旨在重建政治的马克思之可能性。他们将经济学语境重构为革命主体性话语和阶级斗争的革命政治学,将方法论理解为基于阶级对抗—主体性转型—创构性筹划的革命空间,并立足实质吸纳和一般智力视域,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型中,发掘新的政治主体模式和替代性的革命图景。这种解读路径力图走出纯粹客观层面的历史分析构架,确立阶级斗争的根本地位,并将社会转型的动力归结为阶级意志间的冲突,以突出马克思充足的主体性视域。然而,历史的彻底主体化、社会运行机制的过度简化和不确定的未来视域,使其不可避免地带有唯意志论的色彩和乌托邦的嫌疑。
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的马克思;革命主体性;阶级对抗;唯意志论
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立足《资本论》的科学性、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建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同,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①五月风暴革命性的乌托邦精神和文化启蒙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福特制转型,为左翼思潮提供了批判资本主义新的反思起点和激进根基。1940年代产生于美国托洛斯基运动并于50年代解体的所谓“Johnson-Forest Tendency”便认识到工人自主和工人阶级自我运动的社会现实,反对列宁的政党思想。以此为背景,意大利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兴起于19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以特洪迪、奈格里、维尔诺、哈特和克里夫等人为代表。他们立足革命主体性话语,强调后福特制模式下劳动—工人阶级—自我价值稳定过程相对于资本—资产阶级—价值稳定过程的本源性、自主性和充足性,拒绝任何外在于工人运动的组织调解,重构传统左派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的革命政治学。他们以回归工人阶级立场的“阶级构成”颠倒劳动对资本的传统依附地位,主张通过“拒绝工作”战略,彻底实现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决裂,从而与晚期阿尔都塞、福柯、德勒兹和瓜塔里在某些方面形成思想上的灵魂伴侣关系。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现代政治传统和革命政治图景,均作出极富创见的理解,直到当代仍然对世界范围内的激进政治运动产生着巨大影响。则试图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为根基,走出徘徊在二者之间的两个马克思的对立逻辑,创建经济学语境中政治的马克思形象,确立革命主体性话语的根本地位。
一、走出《资本论》的客观主义范式,回归《大纲》的政治构架
对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而言,《大纲》的以往理解总是不自觉地将它视为其他文本产生的中介环节,只是“满足于起源的连续性和观念的发展,却没有关注或没有充分关注跨跃、突破、视域的多重性和实践的紧迫性”,而忽略《大纲》自身,这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的方法论”[1]15。这些解释主要包括四重路径:它是马克思在强大灵感下的即兴之作;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复兴;构成《资本论》形成的中间环节;内含着经由资本主义权力结构的调解所实施的自上而下的革命。第一种观点过于拘泥于马克思书信的字面意思,把《大纲》当成青年马克思的最后著作,认为它再次确认了人道主义、唯心主义和个体伦理学的形而上学,其共产主义思想仍然携带综合18世纪唯心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的倾向。实际上,它深入揭示了资本的固有矛盾,并把之推进为无法消除的对抗,没有为人道主义留下任何空间。维果斯基虽然认识到《大纲》中对抗维度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地位,但仍将它与苏联教科书体系对《资本论》的庸俗解释和斯大林主义经济主义的阅读方式结合起来,未能将阶级对抗普遍化为马克思的范畴总体,最终使其终结在封闭的经济理论之中。罗多尔斯基把《大纲》当作筹备《资本论》的纲领及其附属物,并将后者视为马克思思想的最高点,从而完全沦为极端的客观主义,甚至通过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来创建其必要性。最后一种观点则未能看到《大纲》贯穿始终的“由无产阶级能力引导的绝对无法克服的对抗”,由此,它才是对“自上而下革命”的批判和对“自下而上革命”的确认,并“孕育着旨在解构脱离现实运动的所有理论或政治之自主性的最大潜能”[1]19。
事实上,《资本论》和《大纲》最大差异在于,前者构成马克思客观主义地理解资本主义的首要场所,后者则是马克思脱离这个倾向回归革命主体性话语的根基。“只要从资本主义开始,他就会返回《资本论》,反之亦然:唯有把《资本论》的方法转换和转译为资本主义分析,才能去谈论这个方法。”[2]《资本论》总是把批判简化为客观的经济理论,以在客观性中消除主体性,把无产阶级的解放潜能屈服于资本主义权力的重组。《大纲》则是政治性文本,即马克思革命筹划“在理论和政治层面上的综合”[1]2。它由革命实践构成,并“使由即将到来的危机所产生的革命可能性和面对这个危机的工人阶级之共产主义行动充分综合的理论意志结合起来……《资本论》范畴的客观化阻碍了革命主体的行动。”[1]8《大纲》作为马克思理论发展的中心和至高点,代表着“马克思革命思想的最高峰”与“马克思革命意志中想象和分析的最强点”,“所有的形式二元论……(资本的理论分析反对政治分析、辩证法反对唯物主义、客观性反对主体性)都将燃尽”[1]10。因此,必须透过《大纲》重新阅读和批判《资本论》,“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超越《资本论》的《大纲》?或许。”[1]14显然,《大纲》构成超越客观主义范式进而创建“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的思想源头。
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虽然意识到第二国际实证主义模式的固有缺陷,但以此将《资本论》视为客观主义范式和纯粹经济学理论的滥觞,显然有失偏颇。事实上,《大纲》和《资本论》并无本质区别,二者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处于不断深化的历史和逻辑的连续性之中。前者标志着马克思历史观和方法论构架的基本成熟。后者则使原本未能彻底统一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完全融合起来,将历史观、方法论和革命政治学根植于经济学批判之上,全面弥合了自然—历史、事实—价值、客体—主体的割裂,意味着马克思思想的完全成熟。因此,基于《大纲》走出《资本论》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做法。
二、重建革命主体性的现实性:经济学语境下的政治话语
奈格里指出,《大纲》中的马克思主义是“反经济的理论”,“首要的实践对抗都内在于任何范畴的基础之中”[1]23,其范畴系统的动力因素和方法论基础一并使政治因素成为分析话语的中心,真正地批判科学再现的是对抗运动,它“完全由危机和革命主体性的出现所统治。这个关系如此根本以致于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命名为危机和颠覆的科学。”[1]10奈格里把“货币章”以及“资本章”的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和第三篇“资本作为结果实的东西”作为第一部分的主题,主要包括资本的生产理论,把“资本章”的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作为第二部分的主题,主要包括资本的流通理论。
从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从剩余价值理论转向流通理论,既意味着对抗逻辑的不断深化,又揭示了革命主体从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变。“如果像维果斯基理解的那样,剩余价值的发现在经济理论中引入了阶级斗争,那么流通分析则把阶级斗争理论发展为革命主体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构成《大纲》第一部分的对象,它是革命主体之可能性的定义,否定的定义。集体阶级主体的现实性则与流通理论设定在一起”[1]17。从中“使我们可以意识到被集体工人和集体资本家之间并以危机形式出现的对抗所创建的根本时刻。这里存在两个基本的理论路径:……以剩余价值形式而得以定义的价值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首个发展了的构想;……在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机制中剥削规律(剩余价值规律)的拓展,因而被转译为通向共产主义的危机规律和阶级斗争。”[1]4于是,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被分别发展为剩余价值理论和革命主体理论,劳动—资本的阶级对抗也被推进为以工人阶级之新主体模式为契机的共产主义筹划。这从根本上确立了“资本的对抗理论和社会剥削理论的杠杆”,以向“作为斗争主体性的阶级构成”倾斜,“剩余价值理论……因而变成动力中心……是资本的客观分析和阶级行为之主体分析的汇合点。”[1]9
笔记本Ⅰ—Ⅱ的分析由货币直接走向价值,价值呈现为货币的形式,货币规制和组织社会关系本身。对货币而言,物的价值(社会属性)和实体(自然属性)是分离的,本质上同属一体的割裂,使其处于社会对抗和剥削关系的中心,即使它拥有等价物的本质,也只是社会不平等的一般等价物。于是,“货币……立刻把价值展现为受指令和被组织以获取剥削的交换。……货币只有一个面具,资本家的面具。”[1]23由此,以货币为形式的价值规律以阶级对抗的方式被描述为剥削规律,“总是并只能成为遍布阶级冲突的社会政治之多元决定的虚构”[1]24。货币既“稳固了危机的可能性”,又在“在宣告其独有的趋势功能所隐藏和代表的对抗的社会关系之危机中”和“处于这个经由危机所宣告的趋势下”,将价值理论重构为“作为对抗之社会中介的一个具体代表的货币之暗指。”[1]28-29货币—价值的连接再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两大阶级主体的对抗语境,并预先描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从形式上看,价值描述了趋势和对抗的动力,从实质上看,货币又在其具体动力中,直接宣告了价值规律的危机:价值运动是不确定的,其稳定只是趋势性的,它受制于必要劳动的社会平均值与价格之多元决定的不断变化,这恰好预示了剩余价值理论的社会基础。因此,价值理论只能作为剩余价值理论的一部分,唯有如此,阶级斗争的规律才能得以创建。
笔记本Ⅱ和Ⅲ确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其形成始于剥削构造整个政治社会的过程。“从剥削一般,从命令到剩余价值是这个方向:它是支配这个攻击剥削之角度的阶级逻辑。”[1]61阶级关系构成剩余价值理论的客观目标,从货币转向剩余价值只是“提供阶级武器的政治途径”:货币构成资本关系的“隐线”,剩余价值理论则专注工人阶级的革命政治,构成摧毁和重组资本结构的“红线”[1]63。一方面,使用价值是工人抽象的无差别的劳动能力,交换价值则构成从劳动过渡到资本的基本前提,隐约描述了剩余价值的抽取机制。另一方面,作为主体能力的劳动(主体性劳动)与作为直接使用价值的劳动(对象化劳动)的分离是根本性的。前者作为所有财富的总体力量和来源,描述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对抗,并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由此,剩余价值理论作为剥削理论,才能真正得到解释并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中最重要的运动规律。
笔记本Ⅲ—Ⅳ和Ⅶ将重点放在利润理论,它是剩余价值理论和剥削理论的深化。当资本的生产方式渗透到整个社会领域时,对抗关系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也从生产领域拓展至社会的各个层面。资本对活劳动的剥削获得广泛的社会维度,社会剩余价值便是社会资本(资本的充分社会化)统治社会劳动的结果,作为社会剩余价值的利润则是“全球剩余价值的社会表达,融合了对社会生产力的无偿剥削”[1]88。从剩余价值理论转向利润理论,旨在以普遍激化的社会对抗,重构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对抗政治已成形于从资本—剩余价值到社会资本—社会剩余价值的发展过程中。利润也具体化为“政治力量和社会对抗的极点”:工人阶级主体性理论反对资本主义主体性的利润理论[1]93-94。危机构成阶级斗争的首要领域,它建基于“阶级斗争发展的最高强度和剥削规律之确定性的最广泛拓展”[1]102。利润率的下降规律则在另一层面表明,资本日益失去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力,工人阶级却逐渐巩固了作为资本固有界限的地位,并自主地实现自身的价值增值。
笔记本Ⅳ和Ⅴ则从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从剩余价值理论转向流通理论,旨在将前者关于革命主体的否定性隐喻推进为积极主动的革命政治学,从而使革命的马克思真正拥有社会根基,革命主体的可能性进而被设定为“集体阶级—主体”的现实性:“一个在阶级斗争的真实层面上更加接近革命主体的复杂路径。一个实现马克思方法论之基本准则的路径,一个在主体性方面以富有成果的方式对本质关系的把握……主体变得更加真实和具体”[1]106-107。资本通过时空的充分流动实现自身作为集体力量对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控制,资本的社会化伴随着劳动的社会化,社会资本对活劳动的整体征服与被重组为社会性联合力量的社会劳动结伴而行。资本的扩张看似释放了自身的潜能和权力,反而在不断设置内在限制的过程中,描述了工人阶级不断脱离资本实现自主性的转向。世界市场—帝国主义已经成为革命主体由可能性走向现实性的根本条件。它们代表着资本不断突破空间障碍操控社会的最大限度,是社会对抗的普遍化和最高程度的矛盾潜能。“资本主义的世界联合和世界社会对资本发展的实际吸纳程度越高,扩张的和空间的帝国主义主题就越与深度的剥削、剩余价值和阶级对抗的主题符合。……资本扩张和帝国主义过程及其朝向创建世界剥削的普遍性冲突,同时是革命主体性条件的前提和结果。”[1]121这是一个新的工人阶级,即超越工厂工人渗透至整个社会领域的社会工人。它打破了活劳动对经济必然性的屈从,并使活劳动的创造性力量重新复活。这种力量关系的根本颠倒并不源自对资本主义命令的解构,而是对剩余劳动的否定和再占有。它是对资本及其同源性的否定,是多元的和差异的而非同一的和抽象的。以剩余价值的矛盾本质为基础,立足工人阶级立场去粉碎资本,从内部加深资本关系的断裂,才是《大纲》的唯一路径。它“既解放自身,又筹划了一个可能总体……一个新视域……既是汇集和重组所有事物的熔岩,也是享乐、建议和创造的流通网络”[1]149-150。这是一种新的革命主体性模式,工人阶级在自我充足的创构性潜能中,既彻底弃绝于资本结构,又积极谋求自身的欲望、需求和利益的不断增值。
总体而言,奈格里将《大纲》的经济学语境彻底政治化为重建革命主体之可能性和现实性过程,既将主体化的劳动—资本的二元对抗逻辑,一元化为立足工人阶级的革命政治学,又以资本在时空上的全面扩张和阶级对抗的不断激化为基础,重建工人阶级新的主体模式。基于阶级斗争的逻辑构架,以劳动—劳动力—工人阶级为轴心,审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构成其一以贯之的核心路径。这虽然为从马克思的宏观历史分析转向福柯的微观权力批判提供了一定的启发性,也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纳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和主体性模式的生产之上,避免了革命主体的空心化,但阶级斗争的根基过度简化了历史运行的深层机制,革命前景的实现途径既没有得到充分揭示,又最终囿于工人阶级主体意志的自我充足而带有明显的唯意志论色彩。
三、对抗性分离—主体性转型—创构性筹划方法论的政治空间
在奈格里看来,笔记本M(“导言”)不该与《大纲》放在同一版中,二者的连续性不是时间上的,只能相互再现马克思的同一个写作计划。然而,维果斯基将其中的方法论归结为1840—1850年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延续,并未携带剩余价值理论的痕迹。法国和意大利学派和处理《大纲》一样,坚持将它归属于《资本论》。事实上,“导言”虽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一以贯之的政治和革命的张力,甚至还存在一些细微的庸俗唯物主义限制,但其四重方法论因素(“规定的抽象”、“趋势”、“实际上真实的东西”、“创构原则”)已完全内化于《大纲》实现的理论飞跃中,二者既来自同一创造过程,又相互阐明对方。《大纲》是马克思将“导论”中的“唯物主义方法嫁接在精致的辩证实践上”的首次应用,辩证法路径试图发现每一规定的主体化“动力和趋势”,“干预规定和趋势的关系,使抽象和逻辑的启发式反思主体化,并赋予其资质和历史动力”。唯物主义路径则将“历史的具体的规定”视为根本基础,“就其彻底主体化并完全向未来和创造性开放而言,决不能封闭在任何辩证总体或逻辑总体中”[1]12-13。二者的结合“不为向规定提供极权主义的解答,而是为了认识作为分裂之可能的结构总体。”[1]46它以分裂和差异来寻求总体,在它之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拥有“主体性之多样性”的开放动力,总体也表现为基于主体化动力而承载主体之结构。于是,阶级对抗的分离辩证法,将唯物主义从属于自身,从结构走向主体,即不是源自结构—资本主义而是基于差异和对抗创建结构的主体性:“两大斗争阶级”[1]44。
“规定的抽象”意指在具体中谋求实在的抽象。它表明科学的认识道路不以具体为前提,而以直觉和表象的综合过程为基础,规定是利用一般抽象在思维过程中进行综合和再现的产物。“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3]43因此,认识过程便意味着主体性的“意志和智能”,它使原本的主体性路径表现得更加充分:“规定的抽象过程、接近的过程和抽象地占有具体的过程,是集体过程,是集体知识的集体过程……完全在这个集体无产阶级的光辉中被给予:因此它是批判因素和斗争形式”[1]47,即通向革命主体性的理论。
“趋势”指在抽象中谋求其规定的具体。简单范畴和较为具体的范畴的成形不与思维进程的逻辑顺序完全符合,但总体而言,二者分别只有在复杂和未充分发展的社会形式中得到充足发展,而且“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3]47,经济范畴的自然次序与“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不同,后者取决于它们在资本主义中的相互关系和位置。这意味着趋势方法的确立:“由历史的主体性和作为标志的能动的共同体所激活的动力论”,即由主体性和主体化动力开启的动态过程,它是“由生产和阶级斗争决定的历史运动”[1]48。这完全压倒了谱系学方法,后者把主体从属于某种超验权力和知识本体,呈现出反主体性的路径。前者则基于未来视域的开放空间筹划“当前的阅读”,以“点亮未来”,充分释放了狄奥尼索斯的主体潜能[1]49。
“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构成连接规定的抽象和趋势的中介环节,它处在马克思对“劳动一般”的分析中。各种具体劳动早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已存在,但劳动一般只有在资本主义中才得到充分发展,才真正表现出科学的历史抽象,从而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作为“一个转型概念与转型力量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在它那里,“抽象找到了焦点,并获得与历史现实的紧密关系”,没有这个“通向实践的真实和血肉之躯的历史”,范畴的发展将不可能取得科学进展[1]50。事实上,三者的连续性不过是主体性创构逻辑的不断深化,它们将历史现实与主体动力的结合始终置于对抗和分离之上,不可避免地向未来视域敞开。由此,唯物主义方法被趋势激活,被“实际上真实的东西”主体化。它将趋势提升为“作为主体性化约的趋势”[1]55,破除了计划趋势平息对抗的危险。
前三个要素揭示了对抗性—差异性—主体性的政治空间:范畴的更替实为对主体力量对比关系及其转型的确认,认识不是主观的被动反映,而是积极的主体实践,现实不是在连续性幻象中创建历史总体的封闭结构,而是在差异—对抗、分裂—分离的现实性中不断转型的主体创构过程。“到此为止所看到的标准必须在最后的原则中得以重构。它带有历史过程的多种替代性选择、其质的改变、现实的转折和飞跃以及这个发展过程的主体参与”[1]56。“主体的替代”和“创构原则”是关于断裂、变易、转型和多样性的规则,是完全主体化和力量化的本源性机制。作为马克思方法论的核心视域,它“把冲突因素的重构和斗争的发展相伴随的理论框架的替代,视为肯定前提……把新结构、新对抗形式和新情境的建构当作综合”[1]56。彻底断裂、质性变革和根本转型引入“一个可以归结为集体力量关系因而……是动态的创构性的历史概念”,从而“使趋势不能归结为计划,使抽象不能化约为范畴客观性的基础,使实践标准不能归属于历史连续性之现实主义的拜物教”[1]56-57。
在这四重视域的观照下,主体化及其创构性的无限开放彻底拒绝所有的封闭机制,马克思自然弃绝于黑格尔。前者以主体性路径,使历史完全主体化、动态化为非线性的创构过程。后者则以抽象的辩证总体,将整个形而上学体系封闭在循环的回返逻辑中,以综合取代对抗,将矛盾、对抗和革命消除在极权主义的大写逻辑中。将马克思与黑格尔在方法论上彻底割裂,不仅会重蹈一切科学化马克思主义思潮立足历史经验论的不归之路,而且无法真正阅读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与黑格尔的深层连接。
在一定意义上,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虽然坚持历史现实(唯物主义/结构)与主体动力(辩证法/主体)的结合,但马克思的方法论仍被其彻底主体化了,结构构成创建主体的因素,主体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他们不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抽取社会运行的深层机制和本质规律,并在根基之处透视其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而是在即将到来的未来视域中,将历史重构为以主体性转型为中轴的动态创构过程和绝对革命前景,从而使其建基于主体意志、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之上,和抽象的人道主义并无二致。
四、基于两个圣经式文本的主体性——替代性的政治实践
在自主主义思想家看来,对马克思的一般分析往往忽略了两个极为重要的文本:《资本论》第一卷手稿中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一文和《大纲》中“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节。他们分别称二者为“消失的第六章”和“机器论片段”,以其为根基,将阶级斗争和革命主体性话语切入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当中,力图创建一个与资本主义发展完全不同的政治实践。
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资本家往往通过不断延长劳动时间获取绝对剩余价值,而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借助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机器体系的引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4]。二者分别对应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形式吸纳”)和“实际上的从属”(“实质吸纳”)。其最大不同在于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及其引发的资本的充分社会化,这从根本上变革了工人—资本家的关系和整个劳动过程的性质。在自主主义者看来,这个文本“考察了主体性的条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效果”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或趋势及其内在的历史性”,并“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与主体和生产方式的内在关系一同呈现出来”[5]。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与工人阶级的转型相伴而行。
奈格里指出,马克思未能将实质吸纳拓展至整个社会,“当资本已经征服了所有的生活时间,不只是工作日而是所有的一切时,反抗资本的斗争又意味着什么呢?再生产就像生产,生活就像工作。”[1]xvi德勒兹也有相似观点。资本作为资本主义“无器官的身体”,使机器负责生产剩余价值,“机器和主体与资本如此紧密相连,以致于其运行看似被资本附体。任何事物在客观上似乎被作为准原因的资本所生产”[6]。首先,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已渗透至日常生活层面,彻底吸纳了所有生产性的社会力量,同时伴随着阶级对抗的不断深化。其次,资本主义由工场手工业转向机器大工业,由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生产方式也由福特制转向后福特制。再者,工人阶级的阶级构成转向社会化工人,确立了自身的自我组织和新制度性。因此,实质吸纳已经清楚地预见到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根本改变,并且“仍然存在某物,它既与这个转型的内在本质相关,又将其颂扬为根本革新”[7]:活劳动及其生产网络的变革,即资本主义内部狄奥尼索斯潜能的充分释放。这是主体性—替代性—差异性的政治实践:工人阶级不断获得自主性,并把资本的发展史变成“资产阶级试图从工人阶级中解放自身”的回应的历史[8]。
与“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呼应,“后福特主义是马克思‘机器论片段’的经验实现”[9]100。在这个文本中,马克思集中讨论了自动化的机器体系引发的生产过程的巨大变化。机器取代了工人的技能和力量,并使其活动从属于机器的自动运转,创造和运行机器的科学则作为工人的异己力量,通过机器支配工人劳动。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占有,最终成为机器体系或资本价值增值过程中的“有意识的机件”和环节。知识技能和社会智力之生产力的累积一并被纳入到资本之中,工人的直接劳动只是作为监督者和旁观者丧失了生产过程中支配地位。机器体系使一般的社会知识成为直接的生产力,生产的基础变成实体化的一般智力和人类知识,生产过程开始取决于社会的一般智力水平,科学知识和固定资本成为大工业生产的首要目标。个人始终与社会知识创造出的机器体系紧密相连,只能是“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人”,他们不断再生产这种关系,以同时更新现实财富和自身。
自主主义思想家对其圣经式的援引旨在“明确工人罢工、在生产线中引入机器人、在办公室引入计算机的行为……的史无前例的性质。对‘机器论片段’之连续解释的历史是危机和新开始的历史。”[10]“机器论片段”运行的是阶级斗争的分离逻辑,一般智力虽然充分激活了资本对劳动的占有,但最终形构了一个独立的主体性:工人阶级的自我增值过程,由此,“劳动的集体力量”才表现为“自主的生产力”[11]。总之,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试图透过这两个文本,发掘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特征,甚至找到了智识型资本主义的运作痕迹,以寻找新的革命主体、革命条件和革命方式:“他们揭示存在于当今‘涡轮式资本主义’中的矛盾本质,并力图在这个资本主义的动力体系中寻找革命的潜能”[12]。
在他们看来,马克思虽然一定程度上预见到科学知识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却将一般智力等同于机器体系中的“客观的科学能力”,忽略了“科学、沟通和语言”的巨大潜能。一般智力意指“正式和非正式的知识、想象、伦理倾向、心性和‘语言游戏’”[13]5,是“累积的知识、技能和技巧创造的一种集体社会智能”[14]415。在后福特制模式下,劳动力被普遍化为创造性的生产力量,知识—生产的连接充分融入语言性的合作和沟通性的相互作用之中,一般智力不再是固定资本的化身,而是活劳动的属性即“活主体的沟通、抽象和自我反思”,“不能与活主体之多样性的相互作用分离”[9]65。它表明“剩余价值的抽取……源自遍布社会和在社会个人之‘社会活动的联合’中的各种不同且更加复杂的力量,……总体系列的能力和知识是创造性的和剥削性的”[15]。作为“以劳动力之使用价值为特征的主体性之生产条件”[16],它渗透着人类的交往、沟通和协作的主体理性、道德理性和虚拟性特征。它总是假定“对精神生活的共同参与”与“一般的沟通和认识能力的初始共享”,甚至能够成为全新民主的现实基础[13]8。
建基于劳动的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工业资本主义模式,伴随高度发展的生产合作和社会生产的复杂沟通网络,走向深度危机,原本占据霸权地位的工业劳动已让位于非物质劳动。它意指“创造非物质性的产品,例如知识、信息、交际、人际关系或情感反应的劳动”[17]。智力或语言性的劳动总是带有分析型的创造性和符号性的日常象征。指向身体模式生产的情感劳动则关涉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生产、组织和调控。劳动过程日趋智能化更加要求高度知识化的生产主体,自主的社会劳动力或智识型无产阶级既可以组织自身的生产,又彻底独立于资本结构,“一种多形态的自雇式自主工作已经显现为主导的形式,一种他或她本人就是企业家的‘知识型工人’被嵌入到了一个变动不居的市场之中,被嵌入到了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可变的网络里”[18]145。于是,非物质劳动的霸权在更高程度的抽象化社会化生产中,从根本上造就“劳动之自主政治组织”的现实基础。因此,非物质性劳动的社会学力图定义一种“新的价值”、“新的劳动的概念”和“新的剥削形式”。它表明,当代的资本主义生产不只是生产“剩余价值”或“劳动产品”,也生产“社会形式”、“价值体系”和“社会经验的结构”[19]。这是一种新的主体生产模式,“不再仅仅是那种(维护商业关系再生产的)社会控制工具,并且变得具有了直接的生产性”[18]148。它“在展现自身的创造能量中,似乎为一种自发而根本的共产主义提供了潜能”[14]341。
在非物质劳动和一般智力的生命政治框架中,社会化的沟通和合作作为“不依赖于工业的前提”,“先于资本主义机器”[20]。这意味着“在生产劳动的科学从属中,在日益抽象化社会化的生产中,后福特主义的劳动形式变得更加独立自主”,从而预示了“新无产阶级定义的可能性因素”[21]。“后福特主义的无产阶级”即诸众(mulititude),代表着“情感劳动与身体和智能之连续创建的无产阶级主体的力量”[22]。它是“一般智力的身体”:以非物质劳动、信息化智能化的生产和活劳动的社会合作为特征的生产模式。诸众的肉身蕴含着创构性的本源力量和绝对开放的革命筹划,是“纯粹的潜能、未成形的生命形式、存在的因素”[23]118。其首要特征表现为共同性(the common)的经验:“变动但仍然有效地被创构的即将到来的虚构角色”[23]109。它保证了诸众内部个殊性的相互沟通和集体行动,只处理超越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政治实践,唯有透过“剥削的解构……和生产性的激进民主化”[24]来构想,孕育着共产主义成熟的基本条件。
总之,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力图在这两个文本中辨识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进而创建基于诸众政治的革命图景。他们过于专注于资本主义变化对创建新革命主体的积极意义,却没有透视其负面效应。同时,诸众政治重在批判和解构,并未提出系统而具体的政治纲领。它简化了政治过程的复杂性,无法充分说明政治的逻辑:反抗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自动运行的自发机制,它源自复杂的社会建构,并拥有外于自身的可能性条件。后福特主义的无产阶级因社会根源的虚拟化与界限的模糊性和宽泛性,而缺乏具备统一阶级意识的代言人,不足以承担共产主义的重任,只会通向乌托邦情怀的政治实践和英雄式暴力的革命神话,最终因其去革命的本性而沦为资本的帮凶。
从本质上看,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大纲》力图塑造政治的马克思之可能性。它将《大纲》重构为政治性文本和马克思革命理论的最高峰,将经济学语境塑造为革命主体性话语和阶级斗争的革命政治学,将方法论理解为基于阶级对抗—主体性转型—创构性筹划的革命空间,并立足实质吸纳和一般智力视域,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型中,发掘新的政治主体模式和替代性的革命图景。这种解读路径基于革命主体性的脚手架,试图走出纯粹客观层面的历史分析构架,确立阶级斗争在历史运行中的根本地位,从而将社会转型的动力归结为“敌对的阶级意志之间的冲突”,最终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唯意志论的社会理论”,即赋予阶级剥削关系以首要性的唯物主义的“控制社会学”[25]。历史的彻底主体化、社会运行机制的过度简化和不确定的未来视域,使其不可避免地带有唯意志论的色彩和乌托邦的嫌疑。
[1]Antonio Negri.Marx Beyond Marx: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M].Massachusetts:Bergin &Garvey Publishers,1984.
[2]Steve Wright.Storming Heaven:Class Composition and Struggle in Italian Autonomist Marxism[M].London:Pluto Press,2002:2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66.
[5]Jason Read.The Micro-Politics of Capital:Marx and the Prehistory of the Present[M].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103.
[6]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Anti-Edip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11.
[7]Antonio Negri.The Politics of Subversion:A Manifesto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Cambridge:Polity Press,1989:72.
[8]Mario Tronti.The Stategy of the Refusal[M]//Working Class Autonomy and the Crisis:Italian Marxist Texts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 Class Movement:1964-79.London:Red Notes &CSE Books,1979:10.
[9]Paolo Virno.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M].Los Angeles &New York:Semiotext,2004.
[10]Paolo Virno.Notes on the“General Intellect”[M]//Marxism Beyond Marxism.New York·London:Routledge,1996:265.
[11]Finn Bowring.From the Mass Worker to the Multitude:A Theoretical Contextualisation of Hardt and Negri's Empire[J].Capital &Class,2004(83):115.
[12][斯洛文尼亚]齐泽克.哈特和奈格里为21世纪重写了《共产党宣言》[M]//许纪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84.
[13]Paolo Virno.General Intellect[J].Historical Materialism,2007,15(3).
[14][美]哈特,[意]奈格里.帝国[M].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5]Nicholas Thoburn.Autonomous Production?:On Negri's“New Systhesis”[J].Theory,Culture &Society,2001,18(5):84.
[16]Carlo Vercellone.From Formal Subsumption to General Intellect:Elements for a Marxist Reading of the Thesis of Cognitive Capitalism[J].Historical Materialism,2007,15(1):32.
[17][美]哈特,[意]奈格里.帝国与后社会主义政治[M]//许纪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31.
[18][意]拉扎拉托.非物质劳动[M]//许纪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19][美]哈特,[意]奈格里.“帝国”与“大众”[M]//许纪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60-61.
[20]Antonio Negri.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 Situation Today:Methodological Aspects[M]//Open Marxism: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Pluto Press,1992:78.
[21]Antonio Negri.Constituent Repubilc[M]//Radical Thought in Italy:a Potential Politic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nesota Press,1996:216.
[22]Antonio Negri.Empire and Beyond[M].Cambridge:Polity Press,2008:171.
[23]Antonio Negri.Reflections on Empire[M].Cambridge:Polity Press,2008.
[24]Antonio Negri.The Porcelain Workshop:For A New Grammar of Politics[M].Los Angeles:Semiotext,2007:73.
[25]Alex Callinicos.The Limits of Political Marxism[J].New Left Review,1990(184):112-114.
How Can Political Marx Be Possible?——Grundrisse in the Horizon of Autonomist Marxism
SONG Xiao-jie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4,China)
The radical political reading by Autonomist Marxism manages to reconstruct the possibility of political Marx.They take its economic context as discourse of revolutionary subjectivity and revolutionary politics of class struggle,comprehend its methodology as revolutionary mechanism based on class antagonism-subjective transformation-constitutive project.Furthermore,established in real subsumption and general intellect,they discover new mode of political subject and alternative revolutionary prospect.This understanding path tries to move from historic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n pure objective aspect,institutes basic position and reducts motion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o conflict between class wills to give prominence to Marx's abundant subjective horizon.However,complete subjectivization of history,excessive reduction of social moving mechanism and uncertain future horizon make it inevitably possess voluntarist character and utopian suspicion.
Autonomist Marxism;Political Marx;Revolutionary Subjectivity;Class Antagonism;Voluntarism
B089.1
A
1001-6201(2014)04-0058-08
[责任编辑:秦卫波]
2013-01-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CZX004)。
宋晓杰(1980-),男,河南襄城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