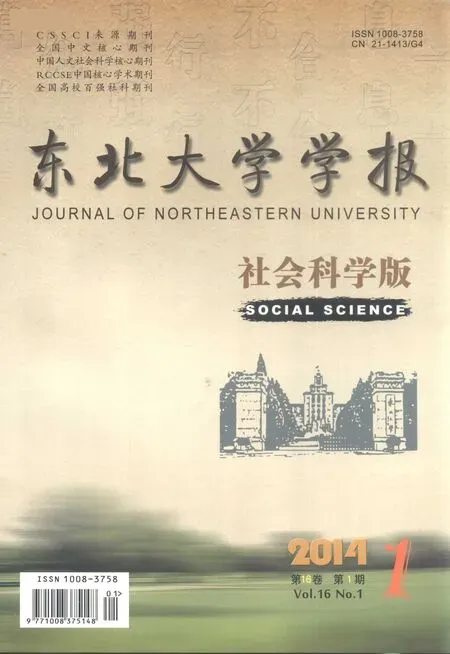福利行政中受领人的资格识别
郑智航,郭志博
(1.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2.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法学部,辽宁 沈阳 110014)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福利制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即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城镇职工所享受到的无所不包的福利待遇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需求来设立福利项目的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中国的福利制度不再是寻求一种平均主义的利益分配模式,而是要在追求效率、实现利益适当分化的前提下兼顾社会公平。具体到福利行政领域,它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哪部分人能够成为福利的受领人这一问题。就福利受领人资格识别的内容来看,它包括识别程序和实质资格两部分。就中国福利受领人的资格识别程序的具体规定来看,它大致包括当事人申请、审核、公示三个环节。在这三个环节中,行政机关在资格识别中居于主导地位,当事人则处于从属地位。他们很难对行政机关的资格识别行为提出异议,并且法律也没有相关的程序保证当事人提出异议。另外,法律对入户调查是否需要经过当事人同意、邻里访问应当访问哪些内容等内容都未作具体规定。就福利受领人资格识别的实质资格来看,中国相关制度作出了一定的规定。例如2007年《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规定将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纳入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规定凡持有非农业户口,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居民都应当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但是,这些制度并没有过多考虑当事人处于窘迫境遇的原因,而是主要将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作为资格识别的依据。即使以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依据,国家层面的法律也是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确定权授予给地方。中国当下福利行政的这种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对福利行政中受领人资格识别是否受法律正当程序的规制和受领人的资格识别的标准应当如何确定这两个重要理论问题进行思考。
二、福利行政中受领人资格识别的法律程序
在世界范围内,福利行政中受领人的资格识别受不受法律正当程序的制约都是一个重要的宪法学问题。从宪法中正当程序条款的起源来看,它主要是基于对犯罪嫌疑人的保护和对个人合法财产的保护。在传统行政法看来,“普通法的正当程序条款适用于政府限制和剥夺公民财产的行为,而不适用于公民从政府直接受益的行为”[1]。如何在理论上论证宪法中的有关正当程序条款的规定能够适用于福利受领人的资格识别过程就成了探讨如何运用正当程序来对福利行政主体进行制约的一个前提问题。
1.午夜检查
20世纪50年代,美国许多州都在福利受领人资格识别过程中,采用“午夜检查”的方式,即行政机关往往在午夜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对福利申请人的住所进行检查。根据州和地方的法律,接受福利的资格可以根据其家庭环境的许多方面来确定,这些环境包括家里是否存在能够养家糊口的成年劳动力。偷袭性搜查作为一般的辅助性检查手段而存在[2]。
然而,这种方式在实践中受到了广泛质疑。反对者认为午夜检查违背了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但是,支持者认为没有相关授权而检查申请人的家是否违反第四修正案,可以通过以下三因素来判断:第一,检查者是否根据申请者明示的或暗示的同意进行检查;第二,搜查的目的是否是为刑事控告或罚款确定证据;第三,在具体的情境中,搜查的方式是否具有合理性[2]。在Frank v.Maryland案中,高等法院认为调查者在没有授权的前提下可以对健康条件处于弱势的家庭进行调查,其理由是:第一,调查仅仅是为了救济健康的目的,不是为了刑事控告或惩罚的目的;第二,存在合理怀疑的根据;第三,调查是在白天进行;第四,调查者没有强行进入民宅[3]。该判决强调了福利调查的非刑事搜查性,并强调福利调查应当在白天进行,这在事实上对午夜检查在时间上存在的瑕疵进行了谴责。在1961年的People v.Shirley案中,被告Tressie Neal向社区的社会工作人员说她仅有的收入是她的福利救济金加孩子们偶尔挣的一点钱,家里也没有能够供养他们的成年劳动力。因此,她为她自己和她的小孩领取了福利救济。一天,社会工作者进入了她家里,发现有一个衣着完好但穿着拖鞋的成年男子在那里。两天后,调查者在凌晨2∶30来到她家,发现那个男人在被告的卧室里。被告承认这个男人在此至少生活了六周,并且这个男人供养她。被告最终被判有罪[4]。这一判决在事实上承认了尽管福利调查的目的不在于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而在于识别当事人的福利受领人资格,但是,从结果上看,福利受领人资格识别过程可能给当事人带来一定的刑事责任。因此,该案件在事实上是对Frank v.Maryland案判决中所强调的调查的非刑事性进行了反驳。这也为福利受领人资格识别适用正当程序条款提供了第一个基础。
2.“新财产”与法律正当程序
在传统的宪法和行政法领域,权利往往被从消极的角度来加予理解,人们甚至将宪政主义的本质定位为对政府干涉的豁免。正当程序条款的目的就在于保障这种权利。传统的财产权观念也主要是从这种消极的角度来把握。这种观念认为财产权是个人对自己所拥有的财产进行占有、支配、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以及当这种权利受到非法干预时,请求政府或司法部门帮助其恢复到非法干预之前的那种态度。国家或者政府从功能上讲,并不为个人创造财产。至于国家为个人创造财产的行为,如提供福利的行为,显然不属于这种财产权的范围,它是国家给“贫穷的陌生人”一种“特权”或“恩惠”。既然政府提供福利是个人的一项特权,政府也就有权取消,它就不应当受宪法正当程序的限制[4]。因此,福利行政领域和福利受益人资格识别过程中并不适用正当程序条款。
这种财产权观念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变化。在新财产学说中,政府不再处于传统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那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是以直接的金钱给付的方式和间接隐形增加的方式为社会公众创造财富[5]。这种新财产主要包括:收入与收益、工作、职业许可、特许、合同、补贴、公共资源的使用、服务等[6]。在这种“新财产”观念看来,个人从国家或政府获得财产与个人从他人那里获得财产没有实质的区别。就福利而言,它在本质上是个人通过平时缴纳税收的形式向政府所购买的一种保险。当个人生活处于窘境时,个人有权要求国家或政府支付必要的救济金。这种“新财产”观念在事实上改变了人们过去对于财产权的消极属性的认识,以及对国家在财产权实现方面的作用的认识。这种观念一经产生,就在美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联邦高等法院在事实上愈来愈认为获得福利不是一项特权,而是一项权利,因此,正当程序条款也被适用于福利行政领域。这也就是所谓的“正当法律程序的革命”。
3.资格识别中的听证程序
是否适用听证程序是福利受领人资格识别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1970年发生的戈德博格诉凯利案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在该案中,布莱克法官认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该国政府提供社会救济金的力度。倘若过分强调福利受领人的资格识别程序,那么,那些确实需要得到社会救济的人就有可能得不到必要的救助。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评估听证程序[7]。但是,布莱克法官的这种观点受到了人们的反对和批驳。那些主张在福利行政中适用听证程序的人认为,当事人在申请福利津贴之前有权要求行政机关举行包括通知、口头倾听、聘请法律顾问、传唤证人和交叉质证、公平的裁判等在内的听证,并有权要求行政机关对其不予授予福利的行为说明理由。最后,支持者占了上风。然而在六年后的埃尔德里奇案中,最高法院却作出了不同的判决。最高法院认为在社会保障残疾保险停发前不需要进行口头听证。
在上述两个类似案件中,法院之所以要作出不同的判决,其原因在于法院是从“效能模式”的角度来对待福利行政中的听证程序的。所谓“效能模式”,是指“关注各种形式的行政决策过程的成本和收益,力求在保全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不受错误剥夺和通过政府行为实现集体目标之间达成某种和谐”的模式。它是“工具主义、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结合体”[8]序Ⅵ。戈德博格诉凯利案与埃尔德里奇案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针对的是生活处于困难境地的人,而后者针对的是残疾人。在政府所能提供的救助一定的情况下,根据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将救助给予最需要给予的人,救助在社会功效上最大。在这种效能模式的指引下,最高法院认为停发家庭补助的领受人处于“濒临绝望”的境况,而残疾人的生活状况具有一定的恒常性,残疾补助并不能即刻改变其生活状况,但是生活困难者的贫困是暂时的。只要他们渡过这个难关,生活状况都会得到改善。因此,当事人在家庭补助计划中避免错误剥夺要比残疾人保险计划中更为重要[8]121-123。相应地,对于贫困补助的资格识别适用听证程序,而残疾人补助的资格识别则不适用听证程序。
三、福利行政中受领人资格识别的具体标准
1.日本具体标准的测定方式
迄今为止,日本在确定受领人资格时采用了以下几种测算方式[9]:
(1)标准生活费方式。物价部门对每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开支进行调查统计,然后以统计的数据为基础计算和规定生活扶助基准的费用。
(2)“菜篮子”方式。该方式首先根据人们生活的现实需要测算出维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食品、衣物、家具、什器等的数量和次数,然后将这些物件按照市场价格作价,从而测算出每个人维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费。
(3)“恩格尔系数”方式。该方式认为人们可以通过一个家庭的食品开支大体测定出该家庭的生活水平。具体来讲,人们可根据家庭食品开支费用与家庭总收入之比例关系,来计算出最低限度生活水准。饮食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很高就意味着家庭生活水平很低,收入只能维持最低生活。反之,则生活富足。
(4)差距缩小方式。该方式以缩小一般家庭与获得救助家庭生活水准之间的差距为目的,以政府发布的经济预测为依据,以下一年度国民消费支出的增长率为基础来决定社会救助基准的变动幅度。
2.美国具体标准
(1)养家糊口的男人。美国的福利救济主要是针对单身的女性和小孩,因此,福利救济申请者家里是否有一个养家糊口的男人就是一个重要的实质性标准。例如,许多州就规定:有未成年人的家庭要想申请救助就得确定这个小孩的父亲不在了或者离异了,并且这个小孩被带到一个地方政府的办公室去进行调查[10]。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之所以盛行“午夜检查”,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确定家里是否具有养家糊口的男人。在美国主流观点看来,一个成年的男子具有养活一家人的能力。倘若一个存在成年男子的家庭还要申请救济,这也就意味着该男子没有尽到勤勉之义务,因此,也就不能获得相应的福利救济。
(2)道德标准。在美国,并不是所有处于贫困境况的小孩都能获得救济。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小孩是合法生育的还是非法生育的作为一条道德标准被强加给了受领人。路易斯安那州删去了给予所有贫困儿童以救济的规定,而是规定母亲在申请救济后非法生育的小孩是不能够领取救济金的。其他的许多州也纷纷效仿,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就规定非法生育孩子的母亲不得领取救济金,否则将可能承担刑事责任[11]。当妇女生活处于窘境状态时,她应当意识到非法生育一个小孩所带来的实际后果。因此,非法生育的处于窘境的妇女在道德上是有过错的,不给她救助也正是对这种过错给予的一种惩罚。
(3)居住标准。美国是个联邦制的国家,州享有包括征税权在内的许多权力。根据美国宪法,各州都保留了征税权,联邦政府不得剥夺州的这项权力。宪法只是对各州征收关税的行为进行了明确禁止[12]。而就税收的用途而言,它除了用于公共行政开支和财政支出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用于福利救济。公共救济基本上是地方关注的一个问题,因此其结果便是仅仅只有该州的居民才有获得救济的权利。许多州也否定对不是本州的居民进行救助[11]。
(4)贫困标准。从美国各州的具体法律实践来看,它们大都首先根据一定的方法确立一个合理的贫困线,然后将申请者以家为单位的收入与这个贫困线进行对比。倘若申请者的收入低于这个贫困线,就可以证明该申请者生活处于困难的境地,然后,结合上文中提到的一些标准作出一个综合性的决定。
四、中国福利行政中受领人资格识别的完善
1.美国理论与实践对中国的启示
首先,中国福利行政中受领人资格识别过程中要处理好福利与隐私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具体实践来看,受领人资格识别过程中也采用了类似美国“午夜检查”的“入户调查”的方式,并且调查的主体多为居民委员会。然而,居民委员会作为居民自治组织并不具有这种调查的权利,这也就意味着居民委员会侵犯了申请人的隐私权[13]。在调查过程中,申请人并没有获得事先通知,而是被“突袭检查”。另外,为了发挥社会民众的监督作用,行政机关或居民委员会往往会将申请人的相关信息以“张榜”形式公之于众。这无疑会为生活困难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其次,美国福利受领人资格识别中的听证程序对中国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美国通过具体判例的形式确立了受领人资格识别中适用听证程序。这对保障福利受领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听证程序在中国行政程序法中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特别是在福利受领人的资格识别中,中国目前尚未建立听证程序。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美国福利资格识别中的听证程序的“效能模式”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这种“效能模式”在实现福利最大化的同时,却忽视了少部分人的利益,从而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另一方面,这种“效能模式”忽视了听证程序本身的价值。
最后,美国福利行政中受领人的资格识别标准既与自由、平等、人权等基本价值存在冲突与矛盾,又存在操作上的难题。这是中国在借鉴美国受领人资格识别制度时必须给予充分重视的地方。具体而言,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福利救济与隐私权的冲突与矛盾。无论是是否有养家糊口的男人,还是小孩是否是合法生育的,都涉及到妇女个人的包括私生活在内的隐私权的问题,并且,当事人自己的收入状况也属于个人隐私的范围。在实践中,行政部门往往采取向社区和亲属进行调查的方式。这种调查方式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是使申请者的隐私进一步暴露,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恶化邻人之间的关系。其次,道德标准与小孩生存权的冲突与矛盾。其实,父母行为的道德与否与小孩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小孩的出生本身不是由小孩自己来选择的。倘若在资格识别过程中过于强调母亲生育小孩的道德性,以及小孩出生的合法性,就会使小孩生存权的实现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发育受到严重威胁。最后,资格识别过程中的举证困难。在资格识别中,申请人往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她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不能工作、没有存款。这种举证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在要求申请者提供抛妻弃子、舍家而去的负心汉的地址的情况下,申请人进行举证的难度相当大[10]。
2.具体措施
第一,建立健全中国福利受领人资格识别的具体程序。笔者认为中国需要针对资格识别制定详细的程序。例如,在审核环节中,入户调查的时间应当事先告之。对邻里访问的适用应当借鉴美国的作法给予必要限制。美国就规定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进行邻里访问:①接受救助者竭尽全力去获得事实,但是没有成功;②接受救助者获得的事实需要澄清,并且工作人员被说服直接与信息的来源进行接触而不是再次通过接受救助者,将产生更好的结果;③工作人员怀疑接受救助者伪造或公然地拒绝提供基本信息,并想去确定他有罪;④审核机关认为由接受救助者自己去直接获得信息是不可能的[10]。至于公示程序,针对目前存在的“张榜公示”制度对受领人隐私权可能造成的侵害以及造成的贫困“标签化”效应,“或许,更为可行的是建立某种电子化的档案制度,限定一定的查询条件,以此保障受益人的权利”[13]。除此之外,针对中国福利受领人资格识别过程中的听证程序缺失的状态,建议可以建立事后听证制度。
第二,完善受领人资格识别的实质标准,增强实质标准的灵活性。中国福利受领人的实质资格主要坚持的是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就这种确定方式的科学性而言,它不及“恩格尔系数”方式。另外,中国福利受领人的实质资格过于单一,并且显现出僵化的趋势。其实,“从理论上讲,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资金来源于政府,接受‘低保’的人只要收入低于当地的‘低保线’就可以申请低保,而不需要其他外加条件”[14]。因此,我国可以增加一点标准的灵活性,而不必在确定福利受领人时附加其他一些因素。
[1]理查德·B.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M].沈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70-71.
[2]Reich C A.Midnight Welfare Searches and the Social Security Act[J].The Yale Law Journal,1963,72(7):1347-1348.
[3]史蒂芬·霍尔姆斯,凯斯·R.桑斯坦.权利的成本[M].毕竟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0.
[4]罗英.美国福利行政正当程序模式研究[J].行政法学研究,2011(1):132.
[5]于立深.行政给付中的警察权力[M]∥杨建顺.比较行政法: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38.
[6]Reich C A.The New Property[J].The Yale Law Journal,1964,73(5):733-737.
[7]高秦伟.论社会保障行政中的正当程序[J].比较法研究,2005(4):88-97.
[8]杰瑞·L.马肖.行政国的正当程序[M].沈岿,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9]韩君玲.日本生活保护基准制定行为的法律规制[J].法学杂志,2007(1):65.
[10]Reich C A.Eligibility Determinations in Public Assistance[J].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1967,63(8):1316-1321.
[11]Reich C A.Individual Rights and Social Welfare:The Emerging Legal Issues[J].The Yale Law Journal,1965,74(7):1247-1249.
[12]周沂林.默示权力与司法理性[EB/OL].[2012-12-11].http:∥ 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20508.
[13]胡敏洁.福利行政调查权和受益人权利保障[J].当代法学,2008(2):84.
[14]周沛.社会福利视野下的发展型社会救助体系及社会福利行政[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50(6):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