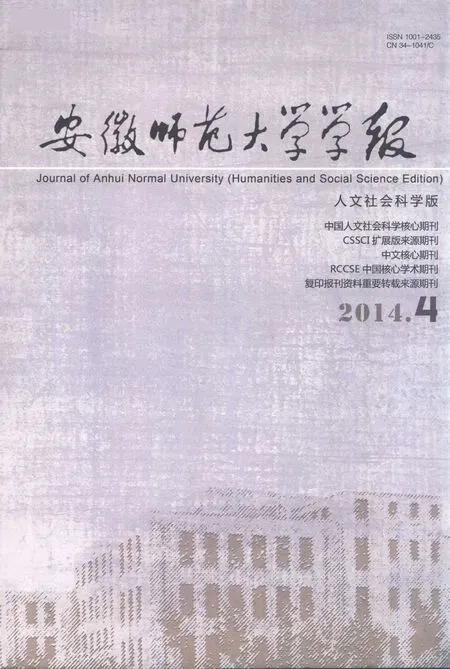单一与多元:两种国际体系单元观的比较研究*
徐步华
(安徽师范大学 法学院,安徽 芜湖,241003)
现代国际关系肇始于17世纪中叶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一体系确立了现代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唯一构成单元的地位。换言之,国际体系是在主权平等原则基础上组合起来的,它是一个水平的权威结构,由唯一的单元——国家的互动所建构。[1]66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国际体系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和转型,其构成单元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国家这一单元本身的地位和功能发生了转变 (即由政治—军事单元向经济—社会单元的转变),另一方面是国际行为体的多元化。由此在国际关系学界引发了单一与多元两种单元观的争论。本文在梳理国际体系单元观演变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两种单元观的分歧及原因。
一、国际体系单元观从单一到多元的演变
肯尼斯·沃尔兹认为:“系统是由结构和互动的单元构成”。[2]79换言之,国际体系是由结构和单元两个层次构成。不过,究竟哪些国际行为体是构成国际体系的单元,存在争论。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科的主流观点是单一单元观,这是由于主张 “国家一元中心论”的现实主义理论在国际关系学界长期占据垄断地位。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假定是:国家——无论是古代的城邦还是现代的民族国家——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单元甚至是唯一的单元。[3]150单一单元观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在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提出,战争的原因要从主要城邦国家 (即斯巴达和雅典)的行为中探寻;奠定现实主义理论大厦的汉斯·摩根索也强调,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国际政治即 “国家间政治”,国家 (尤其是大国)[4]36是国际体系中的基本单元。在冷战初期美苏尖锐对峙的背景下,国家中心主义的单一单元观牢牢占据了理论主导地位。
在20世纪60年代全球化发展和经济繁荣、美苏冷战的缓和以及跨国公司与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增强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学派对现实主义的单一单元观发起挑战,开始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研究。1971年,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指出 “国家中心”范式将国家视为国际体系的基本单元,局限于国家间关系的研究,存在着忽视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跨国关系对世界政治之影响的缺陷。据此,他们提出 “世界政治”范式[5],从两个方面质疑现实主义“国家中心”范式的单一单元观:首先,国家不是一个整体性的单元,地方政府、国内利益团体乃至个人都参与到国际政治之中;其次,国家也不是国际体系中的唯一单元,跨国公司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等跨国行为体也是国际体系中的行动单元。[6]41一些激进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跨国公司已经取代国家成为主要行为体。如雷蒙德·弗农认为跨国公司 “使主权国家陷入困境”;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提出对外直接投资使民族国家蜕化为经济单位。[7]508这种观点对单一单元观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但未免有失偏颇,遭到坚持单一单元观的现实主义学者的反对。例如罗伯特·吉尔平提出,跨国公司本质上是国家 (尤其是美国等大国)的工具,跨国公司并未取代民族国家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国际体系中的 “基本单元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民族国家”。[8]419此后,基欧汉和奈又将跨国关系纳入相互依赖理论之中,他们指出,“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9]9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政治图景:主张国家不是唯一重要的行为体——跨国行为体也是重要的角色,[10]288进一步质疑了 “国家是唯一重要的行为体”的现实主义假设。可见,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在跨国主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国际行为体 (单元)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作为对跨国主义研究和相互依赖理论的反应,肯尼斯· 沃尔兹提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复兴了以国家为中心的单一单元观。沃尔兹强调:“国际结构是根据一个时代的主要政治单元——无论是城邦国家、帝国还是民族国家——来界定的。”[2]91“正如经济学家以公司来界定市场一样,我以国家来界定国际政治结构……只要大国是主要的行为主体,国际政治的结构就根据它们来定义。”[2]94换言之,国家尤其是大国是构成国际格局 (结构)的唯一单元和决定性单元。更为重要的是,在与新现实主义的论战过程中,新自由主义从多元行为体的立场上开始后退 (尽管其并未完全放弃对跨国行为体的强调),向沃尔兹的单一单元观靠拢,比如基欧汉就坦承自己曾经强调非国家行为体的意义,但后来认识到,非国家行为体仍然是从属于国家的,所以将注意力转回到国家上来。[11]8由此,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出现所谓 “新-新”合流的趋势,研究的重心都集中于国家间关系而不是非国家行为体与跨国关系。[12]11总之,时至20世纪80年代,国家一元中心论仍然是学界的主导性话语。
冷战终结之后,单一单元观在学界仍然有着强大的影响。例如,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强调,大国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最大,所有国家的命运都从根本上取决于大国的决策和行为,[13]4-5换言之,国际政治即大国政治。这种单一单元观也体现在建构主义理论主要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的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①不过,温特也强调,他所说的 “国家中心论”并不排除非国家行为体 “对于国家从事有组织暴力的频率和/或方式会有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的可能性,而且 “可能,非国家行为体正在成为比国家更为重要的变革发起者”,但是国际 “体系变化最终要通过国家得以完成”,因为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只有通过国家的中介才能输入到国际体系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仍然处于国际体系的中心”。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0-11.虽然温特的主要意图在于批判新现实主义,强调行为体 (单元)身份与利益的社会建构和观念因素以及体系与单元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但他接受了沃尔兹的 “国家中心主义”的国际体系研究方法,将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首要分析单元,认为没有国家就没有国际体系,坚持国家是单一行为体的现实主义假定并认为这是国际体系理论研究的起点。
单一单元观在国际政治学中历史悠久、根深蒂固;但全球化的发展和冷战的终结对多元单元观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在全球化发展的作用下,主权国家权力的 “流散”和 “退却”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中影响的证据日益增多;围绕全球化所产生的学术争鸣 (即 “全球化争论”)促使学界更多地聚焦于日益增加的非国家行为体和跨国跨政府关系层面,从中逐步认识到整合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研究即促进国际政治研究和国内政治研究之间结合的必要性;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没能有效地预见世界政治的内在趋势,特别是冷战终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使得一些学者对国家一元中心主义进行反思,主张重视国内政治和跨国政治研究,并对其进行重新评价。[14]258在这种背景下,多元单元观萌发了新的发展动力,学术界对跨国政治的兴趣再度兴起,产生了新一波的跨国主义研究热潮,这些研究以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活动及其影响为研究重点,探究了非国家行为体勃兴对于理解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意义。[12]11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跨国主义对非国家行动单元的研究由跨国公司拓展至跨国非营利部门,重在探究国家和非国家两类行动单元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国际体系结构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制约,大多聚焦于非国家单元在促进和传播因果知识与国际规范方面的独特作用。
在新跨国主义研究的热潮中,多元单元观获得了更多的认同。不过,其勃兴则是以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为标志。这是因为全球治理理论本质上就是一种多行为体的世界政治研究视角。[15]191詹姆斯·罗西瑙早在1988年就指出,国际政治正在演变成为全球政治,这是因为在 “国家中心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由各种非国家行为体所组成的 “多中心世界”,这两个成员彼此重叠且相互作用的两个世界共同描绘着全球政治的图景。[16]327此后,他又论及,二者 “时而合作、时而竞争,且不断相互作用”“共同组成了一个高度复杂的全球治理体系”。[17]75虽然,全球治理理论是从全球化辩论和跨国政治研究中孕育而生,但它不仅强调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作用,而且将其视为国际体系中的独立单元,所持的是一种真正的多元单元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方面,全球治理理论从单元多元化的视角出发,强调多行为体治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主张单一单元观的学者事先将非国家行为体排除在国际政治分析框架之外。另一方面,全球治理理论认为非国家行为体不是独立于全球治理体系之外的行动单元,而是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立场不仅超越了一元论的国家中心主义,而且是对跨国主义的一种超越。因为,在跨国主义学者眼中,非国家行为体不过是国际体系中有一定影响的外部游说者。诚然,游说依旧是非国家行为体影响国际政治的一种主要手段,但它们也被国家及其政府邀请参与谈判,甚至亲自设计、实施和监督国际政策。[18]8可见,全球治理理论摒弃了国家中心主义的单一单元观,强调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一样都是国际体系中的独立单元,从而把理论建构在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共存与互动的多元单元观基础之上。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和世界政治演变的背景下,国家中心主义的单一单元观遭遇来自经验和理论两个层面的挑战,多元单元观在国际关系学界赢得更多的支持,特别是在一些主张全球治理理论的学者当中。
二、两种单元观的比较分析
单一单元观与多元单元观的观点分歧和争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单一vs多元
单一单元观持国家一元中心论的观点,即认为现代国际体系是在主权国家体制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主权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因而,只有主权国家才是国际关系的唯一主角。换言之,国家虽然不是国际社会唯一的行为主体,却是建构国际体系的唯一单元。就现实主义学派而言,他们大多并不否认非国家行为体的存在,但认为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无足轻重,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例如,罗伯特·吉尔平强调,“有关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的观点,并非否认其他个人和集体行为体的存在……但不管怎么说,国家还是主要的行为体,因为国家的本质以及国家间关系的类型,在任何特定场合都是国际关系特征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19]18肯尼斯·沃尔兹也认为:“国家不是,也从来不是唯一的国际行为体。”[2]93但 “国家是通过彼此互动塑造出国际政治系统结构的单元,而且它们将长期保持这种作用。”[2]95要之,单一单元观尽管并不否认非国家行为体的存在,但认为现代国际体系的结构是以民族国家为单元互动建构而成,而国家之外的施动者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基本没有什么活动的空间;非国家行为体从属于国家、不是国际体系的独立行动单元。
多元单元观认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是国际体系中的行动单元,二者之间没有等级之别,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也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对世界政治的任何观察和研究都离不开对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考察,绝对的国家中心主义论点已经过时。当然,主张多元单元观的学者并不否认国家这一单元的重要作用。国家依旧是世界政治中的关键行为体,但不似先前那样在国际体系中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其地位和作用也在全球化的作用下不断发生变化。而且,国家的权力、权威和功能是相较于非国家行为体 (单元)而言的,会因具体背景条件而不同,也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变化乃至再分配和再建构。
总之,单一单元观认为国家的作用和地位至今未曾发生实质性变化,国际政治仍然是国家一元主导的体系。多元单元观则强调国际体系构成单元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在不否认国家行为体重要性的同时,突出非国家行为体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
2.统治vs治理
单一单元观假定,国际体系的结构是以主权国家作为单元构筑而成,国家垄断了合法使用暴力的手段,并在其主权管辖范围内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因而,国际政治是一种以国家为单元的单向线性的统治结构。在国内层面,统治的主体是政府,以国家的权威和强制力为后盾,与之相关联的是权力运行方向的自上而下性和等级制特点。在国际层面,单一单元观视角下的当代国际体系也是以大国主导的线性统治结构,体系内单元 (即国家)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等级制,无论是 “大不列颠统治下的和平”,还是 “美利坚统治下的和平”皆是如此。
而多元单元观则认为,以主权国家为单元、自上而下和等级制的 “统治”概念,已转变成注重非国家行为体角色的、多元互动的 “治理”概念。与国家中心主义的统治概念不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部门 (政府),也可以是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的行为体。治理不是通过建立世界政府来统治或管理世界事务,而是通过各行为体(单元)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协调来寻求全球事务的良治。在国内层面,治理是各种经济、政治和行政权威在各个层面对一国的国家事务进行的管理;而在国际层面,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拥有主权的国家,也可以是私营机构 (如跨国公司)和全球公民社会 (如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并且,在治理体系中,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各单元之间不再是主导和隶属的等级制关系,而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平等关系。
可见,单一单元观以国家为国际体系的唯一单元,因而得出国际政治即国家 (尤其是大国)实行自上而下 “统治”的国家间政治。而多元单元观则从国际行为体 (单元)多元化出发,强调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 “时而合作、时而竞争,且不断相互作用”,协同参与到国际事务的全球 “治理”之中。
3.权力政治vs权利政治
单一单元观之下的国际政治就是国家中心的政治,由于国家间尤其是大国间的互动决定着国际体系的走向,因而,大多强调权力 (尤其是军事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权力或者是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或者是国家利益实现的重要手段。在始终秉持单一单元观的现实主义视角下,国际政治与权力政治几乎是同义语,而且这种国家主义和权力政治逻辑深嵌于全部政治的行为与规范之中。
多元单元观则强调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权力政治的效力不仅在下降,而且受到国际制度和规范乃至国际道德的更多制约,由此,权力政治正在向权利政治转变。①秦亚青指出,权力和权利是政治学的两个重要概念。权力指政治上的强制力量,权利则更多地强调依法行使的权力和享有的利益。在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发展过程中,似乎有一条日趋明显的发展脉络,这就是从权力政治走向权利政治,权利逐渐成为政治的目的,权利政治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内容。秦亚青.从权力政治走向权利政治 [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5).在多元单元观看来,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多元化发展表明全球化进程不仅导致霸权的衰弱和大国主导国际秩序能力的下降,而且促使全球意识和社会自主意识的增强。一方面,国家的权力和权威在全球化的作用下不断流散,虽然以强制性权力为基础的国家统治权威不可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但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 “分享权力已是大势所趋”,[20]28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并非运用传统的权力 (军事力量)来影响国际体系的走向,却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国家(尤其是大国)权力的影响力,要求国与国之间在全球公民道德基础上、在国际制度和规范的框架内进行协调与合作,并以制度和规范、正义和道德等观念取代权力作为处理大国关系的基础与标准。这实际上消解或否定了传统国际关系中“权力出真理”的政治逻辑。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全球性问题或危机日益突出的情况下,非政府组织和跨国社会运动等非国家行为体倡导关注人类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因为这种全人类的安全和利益无法在原有的国家政治和狭隘的民族利益诉求中得到有效的表达。权力政治理论强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是关乎国家生存的核心问题,那么,在全球化世界中,人的利益和人的安全则是当今世界政治中关乎普通个体以及人类整体生存的核心问题。后冷战时期对非传统安全和人的安全的重视,彰显了浓厚的权利政治色彩。在当下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需要以 “人的安全”取代 “国家的安全”思维,这在 《禁止生化武器公约》 《国际禁雷公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21]在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跨国社会运动的推动下,最终人道主义代价战胜了军事利益的考量。
总之,由于两种单元观对全球化背景下权力的效力和作用、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等方面的不同认识,进而对国际社会的本质究竟是权力政治,还是权利政治产生了分歧。
4.“极”vs“元”的国际格局观
由于国际体系是由结构和单元两个层次构成,而结构是由互动的单元来界定的,那么,两种国际体系单元观的分歧也影响着二者对国际结构即国际格局的判断。
单一单元观认为,国际格局是由国际体系中国家这一基本单元来界定的。例如,根据沃尔兹的理论,国际格局是由一个时代的主要政治单元来界定的,由于国家是国际体系中主要单元,因此,国际政治的结构只能由国家尤其是大国来定义。在国际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大国即所谓“极”。国际体系中的 “极”作为一种单元其性质、功能、类别是相同的,它就是构成权力中心的大国。由极的概念和极的数量的不同进而延伸概括出国际格局的三种类型:单极、两极和多极格局。
多元单元观则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体系中的单元愈益多元化,再用过去那种“极”的概念来判断当今时代的国际格局已经不适合,而应代之以 “元”的概念,这里的 “元”即性质、功能和类别各不相同的单元,它既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非国家行为体。由此,过去以大国权力为基础的 “极”的国际格局将不可避免地被以不同性质、不同功能和不同类别的行为体共同作用为特征的 “元”的国际格局所取代。这就意味着,国家 (甚至是大国)在今天的世界中也仅仅是影响国际格局变化的一种单元,而与之性质、功能、类别不同的、拥有新型权力的非国家的单元 (例如跨国公司、政府间国家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等)也在同时对国际体系的发展形成巨大的影响。在多元单元观视角下,当代世界的发展变化因此是在这一系列性质不同的单元的互动中展开的,由此,当今国际格局逐渐超越了主张单一单元观的现实主义学者们所分析和推演出的单极、两极或多极结构的范畴,向着 “无极多元”网状结构方向发展演变。[22]当然,国际体系超越 “极”的国际格局而向 “元”的国际格局发展是一个复杂且持久的过程,持多元单元观的学者也并不否认,国家 (尤其是大国)这一单元依然在现实的国际体系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但是,即便是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也只能是 “多元”国际格局中的一 “元”。
综上,由于国际关系学界在单元观上一元还是多元上的分歧,进而延伸出二者在国际体系的管理方式 (统治vs治理)、国际政治的本质 (权力政治vs权利政治)和国际体系的结构形态(“极”vs“元”的国际格局)等方面的不同观点。
三、两种单元观论争的原因
单一与多元的两种国际体系单元观之间存在上述的诸多分歧,主要在于二者对非国家行为体勃兴、全球化影响以及时代观等方面的不同研判。
1.对非国家行为体勃兴的不同认识
多元单元观的发展及其与单一单元观之间展开论争首先是由于非国家行为体的勃兴及其影响的不断增强。一是二战之后跨国公司的崛起,它们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由此促使一批学者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展开了对跨国政治的研究。二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社会运动与非政府组织勃兴所引发的 “全球结社革命”“可能会永久性地改变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23]109其重要意义不亚于民族国家之兴起。三是冷战后全球公民社会的勃兴,为国际行为体多元化的发展注入了更大的动力。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之间权力发生着非同寻常的重新分配,民族国家政府不仅在全球化的经济中失去自主性,而且还必须与商业公司、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分享政治、社会和安全等方面权力,而这些权力都是主权的核心内容。[24]50
对此,一些学者坚持单一单元观,认为非国家行为体的勃兴及其作用的增强,并没有改变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单元。例如,肯尼斯·沃尔兹强调,尽管 “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以及跨国行为扩展的广度显而易见,但是,由此并不足以得出国际政治的国家中心观念已然过时这一结论。”[2]93根据沃尔兹的理论,国际政治的结构是根据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而不是活跃于其中的所有行为体来加以界定的。与之相对照的是,多元单元观则重视全球化背景下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日益凸显,得出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及其作用的增强促使国际体系的构成单元由一元向多元转变的结论。在多元单元观看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参与国际事务的行为体不断增加,以及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对国际体系的走向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再坚持单一单元的 “国家中心论”已经不合时宜。
由于学术界对二战后至今非国家行为体作用和地位提升的判断不同,催生出单一与多元两种单元观以及二者之间的争论。非国家行为体数量和影响的不断增加是多元单元观的现实依据,也是双方论争的直接原因。
2.对全球化影响的不同判断
全球化客观上推动了非国家行为体的发展,加剧了权力的分散趋势。首先,在全球化的作用下,二战后跨国公司的数量和影响都极大地增长,与之相伴随的是,民族国家大大减少了跨国贸易、投资、生产和服务供给的障碍,减弱了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正向市场和跨国公司倾斜。其次,面对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传统的民族国家统治形式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独立且有效地应对和解决。因而,民族国家试图通过政府间国际组织来解决这些挑战,这样,权力的中心由国家层面转移到了超国家的和地区的层面,一些国际组织尤其是全球经济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一些地区性国际组织(如欧盟)权力日益增大。最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改变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跨国社会运动等非国家行为体发展和维持跨国联系的能力,大大降低了相应的成本。随着冷战的结束,在传统的民族国家政治之外出现了更为开放的政治机会。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和民主善治的主张在全球的扩散及其对公民社会作用的强调,使得国际非政府组织等跨国公民社会行为体愈发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有学者认为,当前全球化进程的深化表明,当今世界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根本的历史变革时期,其重要性犹如欧洲四五百年前发生的工业革命。[25]73
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促使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平衡发生转变。在当今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尽管国家的重要性和主导性作用依旧无法撼动,然而非国家行为体 “建构全球政治和经济的能力”却在与日俱增。[26]1从跨国公司到国际非政府组织等跨国行为体的确给国际体系留下了深远影响,而且如果不将其影响考虑进来,我们甚至无法着手对当代世界体系进行理论概括。[14]255由此,他们转而接受多元单元观。而与之相对照的是,另一些学者尤其是现实主义学派,拒绝认为全球化给国际政治带来实质性的变化。例如,肯尼斯·沃尔兹坚定地认为,“国际政治仍然是国家间的政治。全球政治或世界政治还没有取代国家政治。20世纪是民族国家的世纪,21世纪仍然如此。”[27]696罗伯特·吉尔平也不同意那种认为经济全球化的跨国性力量已经削弱民族国家以及认为国际组织和非政府行为体正在取代民族国家成为国际体系中主导行为体的观点,他认为 “民族国家继续是国内和国际事务中主要的行为体”。“如果说经济全球化和跨国经济力量正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削弱一国的经济主权,这也是确切无误的。然而,人们把全球化程度和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严重夸大了。不管怎样,今天的世界仍旧是以国家为主导的。”[28]328总之,在单一单元观看来,全球化并未对国家作为国际体系唯一单元的主导地位形成实质性挑战。
可见,国家中心地位的相对下降和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提升实质上是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结果,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体系的行为体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然而,全球化是否打破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平衡,非国家行为体是否应该被视为国际体系的独立单元,对此,国际关系学界产生了分歧,而这正是单一与多元单元观分歧和论争的主要原因。
3.时代观的分野
两种单元观分歧与论争还要归因于二者各自所持的时代观不同。即使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冷战终结的时代背景下,一些新现实主义者仍然坚持国家中心主义的单一单元观立场。比如,约翰·米尔斯海默强调,国际体系的大国强权政治特征在21世纪初并没有变化,世界仍是有在无政府状态下生活的国家所组成。[13]509罗伯特·吉尔平断言,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历经数千年一直也没有发生变化。国际关系仍然是处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独立行为体之间争取财富和权力的循环斗争。古希腊的修昔底德仍可以理解当今的世界。[19]7难怪乎苏珊·斯特兰奇大声疾呼:现实主义者醒醒吧,“这个世界已经变了。”[29]新自由主义者基欧汉对现实主义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现实主义特别不擅长解释变化……尤其不擅长解释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以及国家的国内结构的变化。”[3]146这也是现实主义阵营始终坚持单一单元观的一个主要原因。
与之相左的是,主张多元单元观的学者强调,任何国际政治都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背景和总体环境,而时代本身是在不断变化的,其中非国家行为体力量的增强就是一个明显的变化。例如,詹姆斯·罗西瑙就指出,当今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 “一个以边界迁移、权威重构、民族国家衰落和非政府组织在地区、国家、国际和全球等诸层次上的激增为特征和标志的时代”。[30]55在这种背景下,从单一单元观的 “旧本体论”走向多元单元观的 “新本体论”才能使我们的视野跟上时代的步伐。[30]61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学派开始修正其立场,前述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出现新-新合流的趋势,向一元单元观靠拢,但新自由主义者并未完全放弃多元行为体的立场。随着冷战终结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他们再次强调了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例如,约瑟夫·奈指出:“从质的角度来看,跨国行为体几个世纪来一直起着作用,但是20世纪下半叶所发生的量变标志着国际体系的一个重大变革。”[10]298基欧汉和奈还共同提出全球主义的概念,指出以国家为中心的多边合作俱乐部治理模式正 “处于危险”之中,并将被一种多元的全球主义治理模式所取代。[20]23总之,多元单元观反对再将国家视为国际关系中的唯一的和主要的行为体,强调单一单元观在冷战后的今天已不能恰当地解释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各种行为体的作用和相互间的关系。
不同时代观,就有着不同的国际体系观。国际体系观的分歧又必然决定着对国际体系的构成单元及其结构 (国际格局)的不同判断。由此可见,时代观的分野是单一与多元两种单元观之间产生分歧和争论的根源所在。
四、结论
通过对国际体系单元观问题及其在国际关系学界所引发的争论的探讨,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首先,单元观问题及其争论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在国际关系理论上的一种投射。自从二战之后,在全球化发展和新兴科技革命的助推下,国际体系发生了缓慢而深刻的变革,从单一单元观向多元单元观的转换实际上是对这一深刻变革的一种反映。非国家行为体的数量和力量的增长和扩大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随着非国家行为体的广泛而深入的介入,国家已经被,而且仍将继续被重新构建,“并逐渐融入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网络)的结构性互动关系之中”。[31]242新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增加、新的行动舞台的涌现,以及国内政治与国家政治之间界限的模糊似乎都表明,以国家为中心的、一元等级制的国际格局正朝着多元网络状的全球格局发生转变。如果继续沿用单一单元观的视角而不把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纳入世界政治分析框架之中,我们就很难对当今世界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多元单元观既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的理论产物,又是透视当代世界政治变革的一种新的分析工具。
其次,单元观问题及其争论为探讨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之间理论分歧与争论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理想主义、跨国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众多的国际关系流派对现实主义理论及其国家中心论提出质疑或发起挑战,但大多并未真正突破现实主义单一单元观理论框架的束缚。例如,冷战终结之前的英国学派 (以赫德利·布尔乃至马丁·怀特为代表)提出 “国际社会”的概念,但实质上也是单一单元论者,①现实主义不仅自始至终认为国家是建构国际体系的唯一单元,而且认为由于国家之上没有共同的政府,国与国之间处于所谓的自然状态或战争状态,即国际无政府状态。与之不同的是,英国学派则强调了一个由国家所组成的国际社会的存在。不过,马丁·怀特和赫德利·布尔等早期英国学派学者所主张的 “国际社会”本质上是 “国家社会”,即依然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唯一单元,只不过,国家的行为受到了外交、均势、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等方面的制约。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也在 “新-新”争论中不同程度地同意单一单元观,虽然后来又做出了自我修正。可见,两种单元观很难以学派来划分,现实主义直到当下依然强调一元论,而其他学派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冷战的终结修正了单一单元观,比如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的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以及英国学派的巴里·布赞等。②后期英国学派代表人物巴里·布赞等人将国际社会发展成世界社会,并将世界社会视为国家间社会、人际社会与跨国社会这三个领域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结合体,并认为这三种领域或者单元类型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主导其他两种,但它们之间是相互作用的。换言之,在冷战终结和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布赞根据国际体系所发生的变化将英国学派传统的单一单元观转变为多元单元观。参见Barry Buzan.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sa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xviii.但总的看来,单一单元观与多元单元观的阵营此消彼长却是一个可见的趋势。
最后,单元观问题及其争论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再建构。至今,单一单元观在国际关系学界仍有着很大的影响。例如,国内相当多的学者都赞同:“国际格局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国际关系构成中,在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集合的基础上,以主权国家和国际集团等战略力量角色及其组合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结构状态和局面。”[32]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实际上是单一单元观版本的国际格局定义。可见,理论需要跟上现实的步伐,因为国际格局在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已经发生了改变,当代国际体系正发生着广泛、复杂和深刻的变革,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国际体系的构成单元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变,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国际体系结构 (即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这就意味着国际关系学界对当代世界政治发展演变的主观认识必须随之变化,才能建构起更为准确地反映当代世界政治规律的新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理论。
[1] 俞正樑.国际关系与全球政治——21世纪国际关系学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2] 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Reading,Mass.:Addison-Wesley Pub.Co.,1979.
[3] 罗伯特·基欧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M].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M].徐昕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5] Joseph S.Nye,Jr.,Robert O.Keohane.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A Conclusion[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71,25(3):729-736.
[6] 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Jr.Transgovernment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J].World Politics,1974,27(1):39-62.
[7] 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阎学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8] Robert Gilpin.The Politics of Trans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71,25(3):398-419.
[9]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0] 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M].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1] 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M].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
[12] DaphnéJosselin and William Wallace.Non-State Actors in World Politics:A Framework[C]∥DaphnéJosselin and William Wallace.Non-State Actors in World Politics.Houndmills:Palgrave,2001.
[13]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4] Thomas Risse.Transnational Actors and World Politics[C]∥Wal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 and Beth Simmon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 et al.:Sage Publications,2002.
[15] Klaus Dingwerth and Philipp Pattberg.Global Governance as a Perspective on World Politics[J].Global Governance,2006,12(2):185-203.
[16] James N.Rosenau.Patterneo Chaos in Global Life: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the Two Worlds of Global Politics[J].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88,9(4):327-364.
[17] 詹姆斯·罗西瑙.全球新秩序中的治理[C]∥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曹荣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8] Bas Arts.Non-State Actors in Global Governance[R].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the 2003ECPR Joint Sessions.Edinburgh,Scotland,March 28April 2,2003.
[19]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M].武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20]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导言[C]∥约瑟夫·奈,约翰·唐纳胡.全球化世界的治理.王勇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21] Daniel Feakes.Global Civil Society and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Weapons[C]∥Mary Kaldor,Helmut Anheier and Marlies Glasius.Global Civil Society 2003.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87-117;Richard Rice.Reversing the Gun Sights: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Targets Land Mines[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8,52(3):613-644.
[22] 叶江,殷翔.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权力观之比较分析[J].国际政治研究,2008,(1):131-142.
[23] Lester M.Salamon.The Ris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J].Foreign Affairs,1994,73(4):109-122.
[24] Jessica T.Mathews.Power shift[J].Foreign Affairs,1997,76(1):50-66.
[25] Neil Stammers.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Challenge to Power[C]∥Martin Shaw.Politics and Globalisation:Knowledge,Ethics and Agency.London:Routledge,1999.
[26] Richard A.Higgott,Geoffrey R.D.Underhill and Andreas Bieler.Introduction:Globalisation and Non-State Actors[C]∥Richard A.Higgott,Geoffrey R.D.Underhill and Andreas Bieler.Non-State Actors and Authority in the Global System.London:Routledge,2000.
[27] Kenneth Waltz.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J].PS: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s,1999,32(4):693-700.
[28] 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杨宇光,杨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9] Susan Strange.Wake Up,Krasner!The World Has Changed[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conomy,1994,1(2):209-219.
[30] 詹姆斯·罗西瑙.面向本体论的全球治理[C]∥俞可平.全球化:全球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1] 玛格丽特·E·凯克,凯瑟琳·辛金克.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M].韩召颖,孙英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2] 梁守德.新世纪的国际政治[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1:104-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