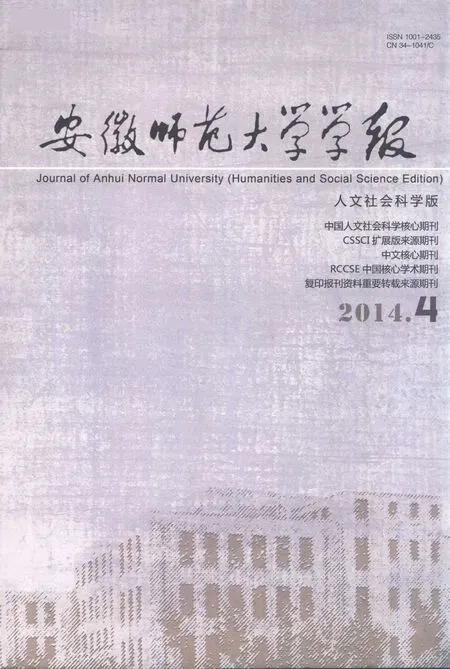中国文学起源问题重议——从甲骨文与中国文字起源发生说起*
木 斋,祖秋阳
(吉林大学 文学院,长春130012)
一、中国文学起源传统说法的反思及新的理论体系构建
关于中国文学的缘起,有两种近乎定论的权威说法和写法:一是就文学体裁而言,几乎都是说诗歌先于散文,这种说法似乎主要与文学艺术源于劳动的理论有关;二是就文学题材而言,在文学史的写作中,往往又是以神话为开篇。
其中文学起源诗歌说,诗歌源于劳动说、源于民间说,具有双向的理论来源。一方面,来自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如 《淮南子·道应训》云“今夫举大木者,前呼 ‘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可视为后来 “杭育”说的先声;又如班固、何休出于儒家民本思想编造,朱熹光大张扬之诗三百 “采诗”说、民歌说等,皆为胡适以来民间说之宗祖。另一方面,源于俄苏意识形态以及更为上溯的以普列汉诺夫、恩格斯为代表的劳动创造人理论。而这些舶来品又同华夏民族长期以来儒家出于民本思想的需要所产生的采诗说、汉乐府民间说等说法相互呼应,相互之间循环论证。
将神话视为中国文学的起源,则是中国文学史写作的惯例——在理论上诗歌是中国文学最早的体裁,在文学史实际的写作中,往往是以散文体裁写成的神话为开篇,如 “神话的起源正如诗歌的起源,是文学最早的源头”①林庚 《中国文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如袁行霈本 《中国文学史》等,莫不如是。等。诗歌起源和神话起源这两种说法看似有别,实则同本同源,都源于一个多世纪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劳工神圣、民间创造这同一个意识形态思潮。在中国学者中,鲁迅最早借助现代的 “神话”观念讲述中国文学史的起源,其 《中国文学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云:“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鲁迅之后,叙述中国文学的源头一自神话,已成为一种中国现代学术的新传统而为众多学者所接受。[1]39
如上所述,这两种说法,几乎都主要发端于一个多世纪以来新兴的意识形态观念,当然,也和中国本土原有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民本思想异曲同工。但这两种说法,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圆通的悖论:既然诗歌为文学的起源,就不应该是以神话为起源。迄今为止所见到的中国最早的文献史料,罕见中国上古以诗歌体裁写作神话,因为中国文字的特点以及上古时代甲骨文、金文的书写形式和传播方式,从根本上制约了神话文学的写作,华夏民族上古时代渐次形成的广义上的儒家文化,则更从文化层面制约了神话文学的写作、接受与传播。尧舜禹汤文武的儒家道统(无论尧舜禹是否可信,其作为一种道统则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标识了华夏民族在自身民族文化的起源发生阶段,就基本奠定了以人为本而非以神为本,以现世为本而非以冥界为本的民族文化特征。这一民族文化特质,必定衍生出重视现世的人伦关系,重视记载历史等等。宗庙祭祀,祈祷神灵,都是为了现世的存在。中国文学的起源发生,必定也应该主要以上述方面作为主要的书写内容。而这些内容本身,决定着中国文学在起源发生时期,理应是散文的而非诗歌的,理应是写实的,而非想象的,理应是记载现世日常必须的应用文字、记载重要的政治文诰,记载对于祖宗神灵的祈祷等。这些理应是起源发生时期主要的书写内容。当下文学史以神话作为开端,主要是采用 《山海经》 《淮南子》等后来之文献,是以写作题材所显示的所谓远古内容替代了写作时间,是以想象替代了中国文学史起源发生的时间次序。其中少量认为出自 《诗经》雅颂关于禹的部分,出自 《尚书·百刑》(成于西周)的上帝、蚩尤故事,楚辞 《天问》等中的后裔故事[1]43,这些都不能说明中国文学最早的题材是神话故事。
总之,不论是诗歌早于散文之说,还是神话为中国文学之起源的说法,都主要是来自于意识形态的臆断,这是一个时代集体的误区。以之到历史文献中去验测,必定归之于推断,并无实在之根据。笔者认为,中国文学就文学体裁而言,最早起源于散文,即由甲骨文记载的应用性散文,随后才是诗歌的产生。诗歌的产生和两大文学艺术文化类型密切相关,即与音乐和散文有关。两者之间,应该是先与散文有关,诗的因素是从甲骨文的反复记录和书写中萌生的,以后到周公制礼作乐的时代,音乐的音律节奏引导了这种原本从散文文体中孕育出来的诗歌雏形,从而成为了中国最早的诗歌。无论是甲骨文还是礼乐制度,皆为帝王宫廷文化的重要组成,与所谓下层民众并无关系。因此,无论是最早由甲骨文记载的应用体散文,随后一些的政令性散文、记载历史的散文 《尚书》,还是与西周礼乐制度密切相关的 《诗经》,都同样是贵族政治制度的产物。
笔者的这一观点,其含义主要有:(1)就中国文学的起源的时间而言,笔者断代在商周之际,甲骨文肇始于武丁时期,因此,即便是广义的以甲骨文作为载体的中国文学的起源,不能早于武丁之前;而由文字的创造到文学的创造,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的起源,由宽泛概念的文学到狭义的文学的出现,一直到西周初期周公制礼作乐之际,才真正出现。换言之,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发端于周公时代,是礼乐制度的产物,周公本人即为其中的创造者、始作俑者。(2)如前所述,散文早于诗歌,中国诗歌的起源,来源于礼乐制度的需要,中国诗歌之产生里程,概略而言,先以散文体裁写出祭祀祖先的文字,然后配乐以合于礼仪,音乐的节奏音律导引了后来祭祀文字的写法,诗歌体裁遂由散文体裁中借助音乐的载体蜕变而出,从而有了诗歌这种形式。(3)以上是从文学的视角立论,若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而言,则凸现了周公礼乐制度的历史性变革的伟大地位,再向前追溯,则武丁时代的文字的创造和甲骨文的发端,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地位。(4)再进一步作追问性质的思考和研究,则中国文字的产生,也需要给予深一步的研究。以笔者所见,武丁时代的甲骨文,正是中国文字的真正意义上的产生。
这些观点,构成了一个中国文学起源产生的新的理论体系,其中包括中国散文的起源发生历程、中国诗歌的起源发生历程、中国文字的起源发生历程、《诗经》的写作历程、甲骨文化、青铜文化向竹帛文化载体演变历程等诸多问题的重新认知。几大问题之间盘根错节,相互印证,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文学的起源发生史,需要系列篇章将诸多问题逐一论证,此篇为其首篇,着重论证文学的界说、文字的界说等基础性问题。
二、中国文学的界说
笔者所阐发的这一认知,可以先从任意其他学者的相关论证中辨析与阐发。笔者随举手头正有的材料。如柳存仁认为:“观乎商代铜器之刻词多仅记名字、称号、年月,或某人作之子孙永宝之陈词,而周代铜器之记载已渐能达情表意,文从字顺。”“其后殷周民族之畛域渐泯,文化混合而产生更大之进步。此时期已达成熟之农业社会,生活既较前复杂,而文字之表现亦见典整丰长,有时且用韵律。”[2]17
此段文字,可以归纳几点含义:(1)中国文学的发端,就现有的文献记载,大抵在商周之际,也就是柳先生所说 “渔猎社会向农业社会之过渡”之际。柳先生从现有的商周之际的青铜器文字的变化上,已经看出了商、周之间正是从滥觞阶段转型为江河阶段本身。(2)有关中国文学的缘起,就柳先生具体论述而言,理应是文早于诗,诗源于文。虽则如此,但中国文学之诗歌早于散文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一种近乎定型的观念。即便是柳存仁先生随后也同样论述:“远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文学史发源之程序,其韵文之发展,必先于散文者若干年,此为各国文学史之通例。在吾国最早者为 《诗》三百篇,希腊则有著名之史诗,印度则有古梵文之歌唱,均为韵文写成……韵文之中,复以诗歌一体为最先。盖诗歌产生于原始人类生活之真实素描,即为自然感发之歌唱,故其所藉以倾吐哀乐心感之节奏韵律,亦无不归反之于自然。且诗歌多伴音乐歌舞而俱成,而乐舞又咸为举动中节之表现……”[2]22
上述之理由,并不能说明诗早于文:其一,诗三百的写作时间,基本为开始于周公时代的作品,殷商时代的甲骨文文献,远远早于诗三百的产生时间;诗三百之前的诗歌作品,可能会有,但迄今为止,尚未出现能证明早于周公时代的原创文献,因此,都不能确认为早于散文之作。其二,“诗歌产生于原始人类生活之真实素描,即为自然感发之歌唱,故其所藉以倾吐哀乐心感之节奏韵律,亦无不归反之于自然”的理论,也不能成为诗早于文的内证根据。从情理上来说,功利的、功用的、实用的早于审美的,这才应该是合于人类社会文化包括文学在内的基本起源发生发展规律。
西方的文学起源发生历程不在本文探讨之内,就中国文学的起源发生历程而言,就现有的文献史料而言,无疑应该是应用性的、政治性的、记载历史的文字在先。在经历漫长岁月的应用文字、政令文字、历史记载文字的过程中,先民们在这种大量的文字书写的经验基础之上,无意地、有意地发现了在文字书写中较为整齐的句式,以及句式之间的声韵节奏,不仅仅能带给接受者某种快感,而且能在这种富含诗意的书写方式中,起到容易记诵、容易传播,并能得到阅读的快感。于是,在漫长的散文体裁的书写过程中,发现了诗歌的文学样式。这应该是中国文学的起源发生历程之梗概。
先秦诗三百,虽然名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但对诗三百的阐发史,却始终遵循着汉儒说诗的轨迹,将其视为人伦教化的教材。换言之,就其内在的功用而言,并非是审美的、愉悦的、人性的、情感的产物和存在,而是如同散文体裁最早产生时代的应用的、政治的、历史记载的载体。此则为诗文之间唐前交互影响史之概要。在汉魏以后的发生发展的历程中,一直到六朝之际的文笔之辨,实际上,一直是诗体从原本产生之际对文体的依赖、比较中逐渐实现尊体的历程。
这样一说,就要涉及到文学的界说。或说是中国文学的界说。因为,反对者可以说,你所说的这种应用的、政治的、历史的文字,不一定是文学。概括而言,文学有狭义、广义之不同,狭义而言,文学为诉之于审美、情感的语言艺术,广义而言,钱基博的界说最为精准:“则述作之总称也。”[3]3就中国文学史的演变历程而言,乃先为广义,逐渐走向狭义之文学。文的本意来自于织,《易·系辞传》曰: “文相织,故曰文。”《说文·文部》曰:“文错画,象交文。”演变成为 “文者,会集众采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意,如文绣然”(《释名·释言语》),“所谓文者,盖复杂而有组织,美丽而适娱悦者也”[3]3。如同“文”字本身有演变过程引申之义,文学在中国历史文化之中也经历着由广义而狭义,由 “述作”而 “美丽而适娱悦者”的演变历程。仍以柳存仁的界说为基础进行讨论:柳先生例举 《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之语,而后说:
文学为 《诗》、《书》、《礼》、《乐》,同于典籍文献……迨及两汉,更以文学泛指一切学术而言……诵经书者众,当时即美之为 “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魏晋之后,有倡言文学应自有其特殊之范畴,而与玄、儒、史分称“四科”者,自宋文帝始。其前,则范晔 《后汉书·文苑传》赞、陆机 《文赋》已肇其端。其后,则梁昭明太子萧统尝举 “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者……西文之释 “文学”,最早盖源于拉丁语之“Litera”,衍变而成 “Literature”,实含有文字、文法及文学等三种意义。西人著述中对 “文学”所下之定义,亦有广义、狭义之不同,而采用狭义者较多。如美国韩德氏 (Hunt)于其所著《文学原理及其问题》中,阐述其个人对文学之解为:“文学为思想之文字表现,藉想象、感情与趣味为之媒介,使人易于理解及发生兴味。”……综合其定义中所列举之文学要素,则想象、情绪、思想、形式四者,不可缺一。[2]4-5
以此来衡量中国文学之发轫,其进入到狭义文学的认知,亦为一个长期渐进的历程。先秦时代,则文学为 《诗》《书》《礼》《乐》,同于典籍文献;迨及两汉,更以文学泛指一切学术而言。诗三百之所以列为儒家经典之首,其原因并非由于其为 “诗”,为文学之一种,具有文学的想象、情绪、思想、形式,而是由于其更为典型具有兴观群怨的人伦教化功能,是更好的政治教化教材,它使政治凭藉着文学的翅膀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所谓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它的立足点在于教化,在于对儒家思想的传播,而非审美的愉悦。在这一点上来说,诗三百与其说是“诗”,毋宁说是当时最为优美的文,是诗化的散文,是散文化的诗。一直到齐梁时代,才有了狭义文学的认知。当然,这是就理论的层面而言的,就文学创作的实践来说,早在建安时代,准确的说,是从建安十六年开始的时代,发生了五言诗的游宴诗写作运动。游宴诗写作,成为了将诗歌从儒家人伦教化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契机,成为文学自觉的摇篮,成为中国文学从政治化、散文化向审美化、诗歌化转型的枢纽。
尽管如此,就中国文学的起源发生运动而言,则应该是在先秦两汉时代完成的。既然在起源发生时期,华夏民族对于文学的理解,尚在文学为诗书礼乐,同于典籍文献的阶段,则当下我们研究中国文学的起源发生,自当同此标准,一切典籍文献,一切由文字而形成文章者,即均可化入到广义的文学大范畴之中。这也就是一向所说的先秦时代文史哲不分的历史文化现象之所由来,之所存在。
三、甲骨文与中国文字之起源
笔者以为,对于中国文字、文章、文学的起源,自然应该以现有的文献史料作为依据,而不能脱离这些文献进行想象判断。甲骨文不仅仅是华夏民族语言最早的文字,而且是当下所能见到的中国最早历史文献,①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商周帝王凡事都要用龟甲 (以龟腹甲为常见)或兽骨 (以牛肩胛骨为常见)进行占卜,然后把占卜的有关事情 (如占卜时间、占卜者、占问内容、视兆结果、验证情况等)刻在甲骨上,并作为档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 (可参见甲骨档案)。甲骨文献中还有少数记事刻辞。殷商有三大特色,即信史、饮酒及敬鬼神;也因为如此,这些决定渔捞、征伐、农业诸多事情的龟甲,才能在后世重见天日,成为研究中国文字重要的资料。同时也是最早的华夏民族的散文。
甲骨文,指刻于商周甲骨之文。当下出土的主要为安阳殷墟以及西周初期周原的甲骨文。一向所说的从夏代开始有文字,或是更早的黄帝时代仓颉造字,都仅仅是一种传说,并无实证。陈梦家对此论证甚为详切:认为 “仓”是 “商”的声同相假,商契就是仓颉:《尔雅》《释鸟》“仓庚商庚”, 《夏小正》 “仓庚者商庚也”,可证“仓”“商”声同相假,而古音 “颉”和 “契”又非常相近。因为汉字为商人所造,而契不仅仅是商的古王,更因为契字的本意是契刻——最早的文字是契刻于甲骨上的,因此,才有仓颉造字之说。但这一附会,它帮助我们解说:龟甲上的文字是最早的文字,发明文字的地方是契的封地,发明文字的人仓颉实在就是契。总之,最早的文字是商人契于龟甲的卜辞。[4]此论是否准确,验之以甲骨文的实际情况,便可得知。
1933年,董作宾发表了 《甲骨文断代例》,在十项标准之下,提出了甲骨文的五个时期:1.盘庚、小辛、小乙、武丁 (二世四王);2.祖庚、祖甲 (一世二王);3.廪辛、康丁 (一世三王);4.武乙、文丁 (二世二王);5.帝乙、帝辛 (二世二王)。[5]以五期断代来看殷商甲骨文的实际情况,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在商代之前,中国尚未进入到以文字时代,甚至在第一期之前,尚未进入到书写文献的时代。在早、中商时期既发现刻划符号,又发现文字。在郑州商城出土的大口尊、盆、豆等陶器上,经常发现刻划符号。一般一器一个符号,个别的刻有相同的两个符号,或者两个符号的合文,已经发现的刻符有30多种。[6]关于这些符号的意义,有学者认为是 “陶器容量的符号”[7]。其中,“在大口尊口沿所刻有的有些图像,则很可能是象形文字”,“商代早中期的文字资料,还见于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在该遗址的70多件陶器上,发现了文字和符号。” (参见原书图57、58)[8]其中止、刀、矢、戈等字,与殷墟甲骨文相似。从这些文字与符号来看,河北藁城台西出土的4处刻划符号和河北藁城所出土的文字,显然有刻划符号和文字的不同。虽然这些刻划符号 “与殷墟甲骨文属于同一个系统”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4-425页。,但明显属于华夏文字的早期雏形形态,河北藁城的4处刻划尚还属于图画形态。
河北藁城台西与郑州商城出土文物,两者皆被视为是早中商文化的产物,但却显示出来由图画文字向表意文字转型的痕迹,可以充分说明在殷商之前尚未进入到文字时代,而在没有其它商代早中期甲骨文出现的情况下,又可说明郑州商城出土的这片刻字甲骨,比较接近于当下出土的殷墟甲骨文。“大多数学者认为夏代应当有文字,但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只在陶器上发现数十种符号。其形体大多属于几何符号,也有象形符号。”[5]迄今为止发现的考古材料,正说明了夏代仅有刻划符号,尚属于图画阶段和几何符号阶段,商代早期的情况,也仍然在夏代的这种刻字符号阶段之中。从当下所能见到的第一时期的甲骨文,虽为二世四王,实则主要是武丁时代的作品。笔者前文的判断,认为发生于武丁时代的甲骨文文献,基本上就是中国文字的发生期,同时,也是中国最早文献的发生期以及中国文学的起源期。不仅仅根据前文所征引的出土文物的对比,同时,也根据如下的方面得出判断:
(一)甲骨文文字,尚还处于文字发明的探索时期
这其中包括一字多样写法,如 “舌”字,根据董作宾所掌握的甲骨文字,就有12种之多,除了前1、2种无异 (前两种也有不同,2种多一枝杈),其余3-12体,两旁均有小异,示舌上有水、舌下有口、舌在口中等,至于金文中所掌握的 (参见 《董作宾先生文集》,艺文印书馆印行)。即便是最为基本的天干地支,其写法在董作宾为殷商甲骨文的五个分期之中也有变化。其中既有相对稳定的写法,如甲,写成+,乙,则与后来的乙字近似,但在武丁时期,方向尚未确定。类似情况还有 “己”字,开口方向一直在变化,在武丁时期两个方向皆有,并一直延续到文丁时期,到帝乙、帝辛时期方才定型为左开口,如同现在的己字。丙字、丁字大同小异,丙字在帝辛时期略有变化,戊字在武丁时期原本与甲骨文的 “又”字相似,一直到第五期才开始看出后来 “戊”字的形态。癸字则一直到帝辛时期的写法,仍与后来文字的 “癸”字不似。还有合字现象等。
甲骨文除了作为文字方面的这些特点,说明其时中国的文字尚在早期雏形形态之外,由当下甲骨文所形成的文献,其本身同样属于雏形形态。甲骨文文献刻写的目的,是对占卜情况的简单记录,也是对商王朝的史的最原始记录,文献篇幅短小,尚未具备后来之所谓文章写作的意识和形态。同时,甲骨文在书写形式上,也还处于非常原始的状态,一片甲骨上,或是从左向右,或是从右向左。如 《殷墟文字乙编》第6385片。从右往左为:贞:有疾自,隹又它?右面文字从左向右:贞:有疾自,不隹又它?自,“鼻”之初文,《说文·四上》:“自,鼻也。象鼻形。”隹,语气词,经籍通作 “唯”。它, “蛇”之初文。《说文·十三下》:“它,虫也……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蛇,‘它,或从虫。’”此处与有灾祸意近。该辞句意:贞人问:鼻子有疾病,是否有灾祸?
当然,在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原始记录中,逐渐也会出现某些文学的因素。譬如,叙事文学的因素,如《甲骨文合集》第14002片正面:
甲申卜, 贞:“帚好冥, ?”王 曰:“其隹丁冥, ;其隹庚冥,引吉。三旬有一日甲寅冥,不 ,隹女。”
甲申卜, 贞:“帚好冥,不其 ?”三旬有一日甲寅冥,允不 ,隹女。
全辞意为:甲申日占卜,贞人 问:妇好将要分娩,是生男的么?王察看卜兆后判断说:如果在丁日分娩,就生男的;如果在庚日分娩,就永远吉利。结果过了三十又一天,在甲寅日分娩了,不是男的,而是女的。甲申日占卜,贞人 问:妇好将要分娩,不会生男的吧?结果过了三十又一天,在甲寅日分娩了,果然不是男的,是女的。这是一组对贞卜辞,第一条卜辞的叙辞、命辞、占辞、验辞齐全,第二条则省去了占辞。妇好是武丁之妻,也就是殷王武丁的后。这组卜辞记录武丁王后生育男女以及是否吉利的事情,显示了在殷商时代已经认为生男为吉,生女不吉的风俗。 (音确),为武丁时期贞人之一,冥,通 “娩”,甲骨文原文写法为 ,为腹中有子之子宫形象; ,通嘉 (参见郭沫若 《殷契粹编》);其、隹皆为语气词。这一片卜辞记述妇好生子的占卜,可以视为后来叙事文学的雏形,由贞人和殷王卜辞的记录,形成了事件发生过程的完整记录。
(二)重复构成诗歌因素
其中或有重复,成为一种重复美,如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卜辞通纂》第375片)占卜者和刻写甲骨者,不一定为了诗意的韵律节奏,而仅仅是面对四个方向占卜是否有雨的自然记录,但却自然形成了每句只变换一下方位的重复节奏美。与后来 《江南可采莲》“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有异曲同工之美。有些是对占卜正反定否的自然记录,偶然出现诗歌因素,如 “自今辛至于来辛又大雨?自今辛至于来辛亡大雨?”(《甲骨文合集》第30048片)虽为甲骨文刻字文献,仍为文言文系统,这就保持了两句之间的对仗之美,尝试比较白话语和原文的不同:从这一个辛日到下一个辛日有大雨么?从这一个辛日到下一个辛日没有大雨么?这一点,也正解释了中国文言文的由来,同时见证了中国文言文自其起源发生之日起的演变历程。
(三)句式构成的文学因素
在殷墟甲骨文前数期中,主要刻写人为占卜者,也就是贞人,因此,甲骨文文献所载,也多为占卜者的口吻和视角记录下的殷商史实,其中也可以看到以后六经时代书写文字的印痕,如:“壬子卜,争贞,我其乍邑,帝弗 ,若?三月。”①《殷墟文字丙编》,第147片。其中乍,为 “作”字的初文,“左”字需要造字,去除 “工”字,为左字的初文。“我其乍邑”四字,《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两者之间,后者将原先单一出现的四字一句,而为两个四字句,遂由散文而为诗。此与两周散文笔法并无太大区别。或说是两周散文的基本元素并无二致。
四、文字的界说与文学的起源
关于甲骨文在中国文学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既不能高估其地位,因为,不论是中国的文字还是文学,甲骨文均为开辟鸿蒙、从无到有、筚路蓝缕的历史阶段,但也不能低估其历史作用和地位。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起源发生,很多人虽然谈及甲骨金文,但仍然从神话和诗歌的起源谈起,这就无视了甲骨文文献的存在,放着最为可信的最早的文字、文献记载而不研究,反而以后人所作的神话和传说中的所谓上古诗歌作为文学的起源,这是不对的。甲骨文文献所显示出来的文学因素,既是粗糙的、无序的、胚胎的,但又是极为宝贵的、自然的、美妙的,它们在应用的、功利的、历史的记载中,放射出了文学审美的异彩,播种了后来文学的、诗歌的种子。
有关中国文字的开始,自古至今,争论甚大,有学者认为夏代开始就有文字,也有学者认为更早,要往前推到图画文字,譬如前文所引的出土文物中的以脚印代表 “止”字等,也有学者更进一步上溯到上古结绳记事,为中国文字之起源发端。之所以争辩不清,主要是争论双方不是用同一个界说标准:文字有广义狭义之不同,有起源与发生开端之不同,如果说是广义的起源,则结绳记事有关,图画文字有关,刻划符号有关,周易占卜有关,但这些均非文字本身,而是广义的文字起源。
作为狭义的文字,需要先行确定其界说范围,方能指认其产生时间。以 《辞源》对 “文字”界说为例,主要有两个义项:语言的书写符号;连缀而成的文章。①《辞源》第1357页,“文字”条。但这两个义项,似乎都还不能作为我们想要追究文字发生点这一使命的权衡标准,前者过宽,如前文所引商代早中期的四个画图文字,以脚印作为 “止”字,虽然是典型的画图表意,但也似乎可以视为一种语言的书写符号,更何况以河流的正反走向代表 “逆”,则初步具表意的特质,再更进一步,“目”“五”两字,均已经和后来的文字极为相似。但这些单独出现的表意符号,无论怎样接近后来文字的雏形形态,它们均非我们所要寻求的用诸多字来表达完整含义这样人类特有的功能。后者过窄,因为文章也可以有狭义广义之分,广义而言,一切表达出人类思想的连缀文字皆可以称之为 “文章”,狭义而言,文章在规模上较大,在表达思想上较为复杂,在应用场合上较为正式、庄重。譬如我们常用 “庙堂文章”和宋元之后的 “小品”相对,来指认同样是散文体的不同样式和阶段。同此,我们平日三言两语的日记文字和便条文字,一般来说,我们也不称其为 “文章”,但它们确乎为 “文字”。同此,甲骨文文字,我们也不便称其为文章,但它们确乎为文字、文献。
因此,笔者尝试为 “文字”重新界说:所谓文字,简单来说,就是 “连缀字以成文”。文的含义较文章更为广义,这里,“文”或是文学的界说,可以重回 “则述作之总称也”[3]3的表述。文字可以独立的表达一个完整的思想,而前举的四个单独的字 (如果将图画文字也称之为字的话),并没有连缀以成为文,这就还没有达到文字的发生发展阶段。
采用笔者的这一界说,重新来审视殷商何时开始产生甲骨文的问题,也就会有了新的认知。从以上对武丁之前,盘庚之后的甲骨卜辞的综述来看,虽然从提出五期分期说的董作宾,就开始尝试为之寻找证据,将第一期放宽到 “武丁及其以前 (盘庚、小辛、小乙)”,但这仅仅是为自己的学说留有余地,并无实证;以后,胡厚宣又在《甲骨续存》中,尝试指认某些甲骨卜辞为盘庚小辛小乙之物,但也仅仅是 “疑皆当”而无实证。以后的出土文物,似乎为这一难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线索,但终究尚未得到真正早于武丁的甲骨文。
以笔者的推测来看,一个重大文化现象、文学现象的产生,必定要有着从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哲学、文艺、语言文字,到文学等多学科的重大历史变革作为背景方能得以发生飞跃性的突破,从而成为一个新时代的里程碑。正如以后周公制礼作乐的革命,发生了中国诗歌的飞跃,从而产生诗三百以及中国诗歌;曹操邺城铜雀台起,清商乐兴起,才有了五言诗体形式的飞跃,从而奠定了中国诗歌美学的发展方向和诗歌史历程。武丁时代,也一定会有类似的文化变革发生,譬如已经被学者所论述的,至少从武丁时代开始,殷商之间开始发生的军事冲突。屈原《离骚》记载的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为我们描述了武丁时代圣君贤相的历史图景。此外,占卜制度的确立,贞人群体占卜记录历史的确立,政治、宗教等的需要,可能会极大地刺激了文字记载的需要,从而发生了中国文字、文献、文学凿空鸿蒙从无到有的历程。换言之,当下其它地区所出土的甲骨残字,一鳞半爪,均只能是中国文字史、文献史、文学史江河发轫之前的涓涓溪流而非江河本身;武丁时代之前之于文字的暗中摸索历程,似应为渐变的历程,武丁时代,则为质变的飞跃。
在讨论基本完成了武丁时代殷墟甲骨文之后,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于周原甲骨文的讨论。至今有字甲骨共发现300多片,其中周原一地就出土300片左右。西周甲骨的文字一般都比较少,而且,字迹纤小,“在没有争议的较为典型的西周卜辞中 (无论是在周原,还是在几千里外的邢台),其刻辞行款几乎都毫无例外地都是自右向左。”[9]相对比殷墟甲骨卜辞,可以明显地看到,殷墟甲骨卜辞的书写次序,并无一定,从左到右,从右到左,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无不具备。这可能与殷商甲骨卜辞的记录,基本都是以甲骨为书写材料有关,而西周很有可能在文王时代即已经开始有竹简书写,而竹简书写最大的特点,是可以采用绳等物将其编为策。如果当时已经习惯编在其左,掀动方便,则势必要由右向左书写,方能阅读方便。当然,不排除也会有从左向右的书写次序。但不论如何,西周时代的甲骨文,已经开始有了书写次序的规范意识。
曹玮编著 《周原甲骨文》一书的图片[10],均为从右向左,从上向下。《周原甲骨文》一书为收集周原甲骨最为全面的一书,可知周原甲骨基本为接近西周之后开始的 《尚书》等的书写习惯。图片中的文字,涉及周方伯等的字样,应为西周早期,近于文王时代的文字。其书写刻画的痕迹非常纤细,疑其之地原本惯于竹简刻写,与甲骨采用不同的刻画工具。甲骨贵重于竹简,也有可能,就是王室用甲骨而非王室则用竹简。至于周原甲骨字迹纤小是否与竹简的书写习惯有关,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但也有例外,采用自左向右的书写次序,如来自陈全方摹本的周原甲骨文①均出自陈全方摹本,原载 《四川大学学报》第10辑 《古文字研究论文集》,第381页。:同样出现周方伯,但文字的表达,似乎更为接近成熟。在刻写风格上,同样纤细。有学者探究了周原甲骨文中“王”字的演变②王宇信等 《商周甲骨文》,第222页。,尝试比较殷墟甲骨文中的“王”字,显然,周原甲骨更为接近后来的写法,或说是基本完成了 “王”字的定型。这一点,几乎是具有典型意义概括意义的。中国文字,在西周初期,一方面通过在甲骨刻写载体内部的变革演变,渐次接近定型,一方面,随着西周新时代的开始,也渐次完成了由甲骨文字向青铜器金文书写的变革和定型,以及当下尚未能有出土文物证明,却在情理之中的竹帛载体以及竹帛书写文字形式的变革和定型。同此,伴随着文字书写载体的变革和日趋稳定,书写文字、文章变革飞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 赵敏俐,谭家键.中国古代文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
[2] 吴梅,柳存仁,等.中国大文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3]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3.
[4] 陈梦家.中国文字学[M].北京:中华书局,2011:11-12.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29.
[6] 裴明相.郑州商代陶文试释[C]∥河洛文明论文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7] 安金槐.商代粮食的器量[J].农业考古,1984,(2).
[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90-99.
[9] 王宇信.周原甲骨卜辞行款的再认识和邢台西周卜辞的行款走向[J].华夏考古,1995,(2).
[10] 曹玮.周原甲骨文[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