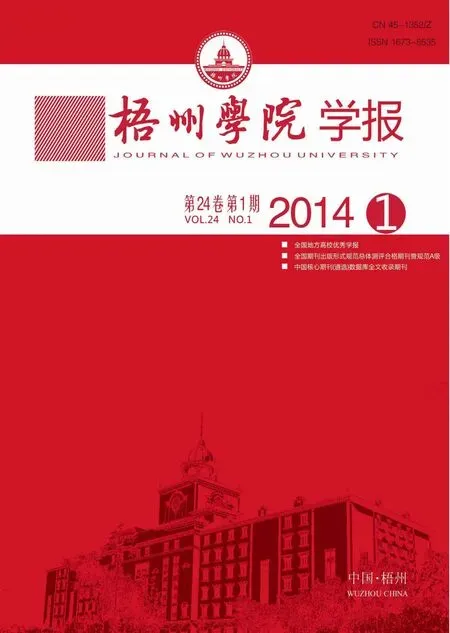“十七年文学”中的爱情模式建构分析
——以赵树理《三里湾》为例
戴彬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 541006)
“十七年文学”中的爱情模式建构分析
——以赵树理《三里湾》为例
戴彬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 541006)
“十七年文学”时期,特定的时代政治背景也催生了独特的爱情建构模式,该文试图以十七年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代表作《三里湾》为例,深入分析这种特定政治环境对爱情的产生及发展所发挥的影响,以及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
十七年文学;爱情模式;《三里湾》;赵树理
“十七年文学”时期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革命历史题材、农村题材和工业题材等三大类。其中农村题材小说因为近距离地再现了当时农村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体现出反映现实生活同步性方面的独特优势,成就最为引人注目。而特定的时代政治背景也在文学创作中催生了独特的爱情建构模式,《三里湾》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1955年发表的《三里湾》写的是太行山区的三里湾成立了初级农业合作社,但是围绕着秋收、扩社、整党、开渠等事件,各阶层农民表现了不同的态度。小说将农村的社会改革和日常的家庭矛盾、爱情纠葛结合在一起描绘,展现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农村生活画卷。小说的整个进程前紧后松,在急速的情节推进中让王玉生、范灵芝等6个年青人各自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在这些爱情的叙述建构中,一方面反映了作家本人的叙述习惯和政治取向,也映衬出特定政治环境所给予的影响。
一、政治立场和运动对爱情发展的影响
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主题的《三里湾》,我们始终可以看到一条或隐或显的依附于合作化运动的爱情线索,它对合作化主题起到了重要的衬托作用,与合作化运动相互依附,共同推进小说的故事发展。其中最典型的依附于合作化运动的爱情线索就是范灵芝爱情观念的前后变化。在合作化运动中,范灵芝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爱情观念,将政治立场和对合作化运动的态度作为衡量爱人的尺度,而不再以有无文化为标杆。在这样的爱情想法转变过程中,政治运动和政治立场并非是一个陪衬的角色,而是扮演着催生和推动的角色,并对爱情发展形成制约。
1.政治立场和运动对爱情发展的催生和推动
范灵芝读过书,担任村里扫盲学校的教员,一开始她喜欢的是同样读过书也担任教员的马有翼,因为“她总以为一个上过学的人比一个没有上过学的人在各方面都要强一点。”[1]93而王玉生没有读过书,因此并没有进入她的视线。对王玉生看法的改变要从一天夜里,她去旗杆院修改表格,结果发现王玉生“怕扰乱别人睡觉”而到这里研究改装水车,这初步改变了她对王玉生的看法,觉得“他真是个了不起的聪明人,要不是有个‘没文化’的缺点,简直可以做自己的爱人了。”[1]123作为青年团员,范灵芝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坚决给父亲范登高“治病”,并最终让他加入了生产合作社。而马有翼却处处受制于落后家庭,甚至到了连团的会议都不敢参加的地步,还处处为自己的懦弱找借口。这样范灵芝便开始从内心渐渐接纳了王玉生。
范灵芝对王玉生和马有翼的认识是依附于他们对待“入不入社”的思想以及实际表现而不断变化的,也是相同步的。可见,在《三里湾》中男女的相识相恋都是与合作化运动紧密相连的,合作化运动成为他们的“红娘”,男女双方的认识了解不再需要第三者充当媒介,而是单一地在认同合作化事业的基础上自由恋爱,共同劳动、开会、斗争封建势力、秋收、扩社、整党、开渠等都是双方增强了解对方的途径,并成为影响他们爱情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
并非在范灵芝做出了爱情选择之后,这个故事就结束了,这也是为什么爱情线索相对于政治线索而言是个副线的重要原因。因为在小说中,范灵芝本想与同是中学生的马有翼谈恋爱,认为读过书、有文化,多少都要比没读过书要强,但是由于有翼总是受自己封建家庭的局限,不要说和聪明积极的玉生比,就是和另一个任劳任怨的积极分子王满喜比有时也差一些。范灵芝几次将有翼和玉生放在一起比较,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终毅然决定将绣球抛给了志同道合的合作社积极分子王玉生。所以,最后当马有翼得知范灵芝和玉生将要结婚的消息后,也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同封建家庭进行彻底的斗争,并最终使得马家变糊涂为光荣,在解决了农业合作化开渠的问题的同时也赢得了王玉梅的爱情。这就透露出作家在这篇小说中的主要旨意,就是政治正确对爱情的影响,也可以表述为“爱情,只有建筑在对共同事业的关心、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对劳动的热爱的基础上,才是有价值的、美丽的、值得歌颂的。”[2]
2.政治立场和运动对爱情发展的规约和限制
合作化创造的大集体生产环境,在提高了农民的组织观念的同时,也通过组织学习活动或劳动竞赛让“年轻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自由地、不需要介绍人谈恋爱,因为集体生活为他们提供了在一起生活并互相了解的机会。”[3]但政治立场在促使爱情开花结果的同时,也严厉地制约着爱情的发展和走向。合作化运动要求人们摒弃旧有的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走向共同发展的道路,随着运动在农村的开展,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两条道路和两种思想的冲突和斗争,同样的,男女双方在“合作社”和“家庭”孰重孰轻的关系上也产生了明显的分歧,这样,当男女双方在道路选择上出现了不一致的时候,他们的婚姻和爱情也就走向了尽头。
《三里湾》中王玉生和袁小俊的爱情悲剧就是最好的说明。王玉生是青年团员,能做些别人做不来的巧活,人们都叫他“小万宝全”。专门管理合作社里的技术活,发明的活柳篱笆挡沙法保护了互助组里的地,得了县里的特等劳模奖状。小俊和玉生初结婚的时候,也不闹什么气,但他们的爱情后来还是坏在了岳母“能不够”的手上,“能不够”满脑子的自发思想,处处阻碍合作化运动,最终导致了袁小俊和王玉生的爱情悲剧。“能不够”认为:玉生更是个‘家懒外头勤’,每天试验这个、发明那个,又当着民兵班长,每逢收复、收秋、过年、过节就在外边住宿,根本不是个管家的人。认为玉生弄的那些是没要紧的闲事,因而挑唆小俊和玉生离婚。因为反对合作化而不惜牺牲了女儿的幸福。从侧面也反映出了两条道路斗争的艰巨性。
而当范灵芝纠正过来自己的爱情观念后,毅然选择了王玉生。王玉生与范灵芝都是参与合作化运动的积极分子,两人志同道合。玉生的再婚也有力地显示了合作化运动对爱情的规约性,将不符合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合作化的爱情拆散,通过规约使其回归正确的方向。
二、特定爱情模式产生的弊端
通过分析,我们看到了政治运动和政治立场对爱情发展的深刻影响。在小说中,在爱情最初萌芽的时候,原本是“劳模”王玉生配袁小俊,范灵芝倾慕马有翼,王玉梅也爱马有翼,马有翼则在两人之间徘徊,在袁小俊因为抵触合作化运动而离婚后,王满喜更是直言不会“收破烂”要袁小俊。而当合作社进行到扩社的关键时期时,作者给大家来了一个突然转变,“没有文化”的王玉生进入了中学生范灵芝的视野,马有翼在关键时刻,“被革命”快速表明选择了王玉梅,就连直言不会“收破烂”的王满喜也接受了袁小俊。在短短的两三章里,作者突然解决了从开始就一直缠绕在这6个年青人之间的情感问题,整个过程前紧后松,显得非常不自然,给人一种刻意安排,勉强为之的感觉,那么一直遵循着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表现农村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现实问题的赵树理,为什么会在小说结尾处将这6个年青人的爱情问题解决得这么草率呢?这也就是我们在研究赵树理时,经常面对的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历来的文学批评家在探索赵树理的文学成就时,都会遇到这样的困惑: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给予赵树理的‘地位’和‘意义’却很难在文学框架内找到有力支撑。原因正在于这‘地位’和‘意义’本来就是政治运作的结果。”[4]
三、特定爱情模式产生的缘由
因为政治话语成为小说的内在主线,成为小说故事发展的动力和原因,也对爱情叙述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损害,这种损害造成的结果就是爱情发展的失真。另外,“合作化运动”是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是《三里湾》中的故事背景和叙事线索,但对爱情叙述造成损害的并非仅仅是外在政治运动的主导,当然还有作家本人写作风格的主持以及作家思想的限制。
1.政治话语主导下的叙述错位
《三里湾》采取的是第三人称叙事,叙事者和人物的距离较远,有旁观的理性的意味,站在全知的视角对人物的爱情做出理性的干预,对符合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爱情加以褒奖,而不符合的则给予约束,从而消解了爱情主人公情感表达的主体性。赵树理在写《三里湾》的时候也承认是为了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该不该扩社的问题,为了使小说走向符合规范而采取的全知视角对爱情模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三里湾》中叙述人虽然无处不在,但是基本上还是较为隐蔽的。
而为了达到政治话语主导的效果,叙述者甚至直接跳出来指出范灵芝爱情观里错误的地方,文中是这样写的:
有翼这个人,在范灵芝看来是要也要不得,扔也扔不得的,因此常和他取个不即不离的关系,可是一想到最后该怎么样就很苦恼。她这种苦恼是从她一种错误思想生出来的。她总以为一个上过学的人比一个没有上过学的人在各方面都要强一点。例如她在刚才开过的支委会上,听说有翼下午给菊英作证时候是被满喜逼了一下才说了实话,便痛恨有翼不争气。有翼在那时候的表现确实可恨,不过范灵芝恨的是“一个中学生怎么连满喜也不如?”其实满喜除了文化不如有翼,在别的方面比有翼强得多,有些地方连范灵芝自己也不见得赶得上。不是说应该强迫范灵芝不要爱有翼而去爱满喜,可是根据有翼上过中学就认为事事都该比满喜在上,要叫满喜知道的话,一定认为是一种污辱——因为村里人对满喜的评价要比对有翼高得多。范灵芝根据她自己那种错误的想法来找爱人,便把文化放在第一位[1]93。
这种叙述上的错误和跳跃,是因为作家本人“创作的功利性,决定了创作中太强的主观表现意识和动机观念的传递意识,表现于叙事过程中,往往形成作者与叙述者的合二为一,由作者代替叙述者来观察形象体系,决定审美的距离、角度和视野,从而形成了一种作家主观焦点叙事的特征。”[5]
2.政治话语主导下的失真描写
“赵树理写乡村,省略了许多本不应该省略的东西。这种省略都可归结为一种语言的省略”[6],这种省略造成的一个显著问题就是故事情节的不适当跳跃,使爱情发展不自然。比如,小说两次描写到玉生和范灵芝的爱情都显得非常突兀。
范灵芝内心的情感天平一直都是倾向马有翼的,可是到了第二十七章下决心的时候,却突然发生了转变,范灵芝彻底放弃了马有翼。在凌晨四点二十分鼓起勇气主动去找玉生并直截了当地问玉生:“你觉着我这个人怎么样?你爱我不?以前没有考虑过,现在请你考虑一下好不好!”玉生说:“我的老师!只要你不嫌我没有文化,我还有什么考虑的呢?”玉生伸出了双手,范灵芝把自己双手递过去让他握住,两个人四个眼睛对着看,都觉着事情发展得有点突然[1]139。
其实最令人感觉不真实的还属王满喜和袁小俊的结婚。袁小俊和玉生结婚后变得泼辣、刁钻,闹得玉生一家不得安宁,分家后又和玉生两人很难相处下去,便离了婚,即使后来她决定改,但在小说中,也只看见她后悔的眼泪,并未看出她究竟改了多少。而王满喜人称“一阵风”是个直爽的性子,第三十二章接线中在黄大年老婆开始给他介绍小俊的时候,甚至说了一句:“我又不是收破烂的!”[1]169而到了第三十四章国庆前夕的时候两人居然就决定要结婚了。这里给读者的感觉是作者宁愿让读者感觉到突然和不真实也一定要把这6个年轻人凑成3对。
3.创作者自身的政治立场参与
赵树理是“文学史上唯一一个放弃高雅选择而立志为农民写作的小说家”[4],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怀着文摊理想的赵树理与解放区大众化通俗化文学的迫切需要刚好不期而遇。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赵树理这样安排《三里湾》中的爱情模式,也与自己一贯的艺术感觉有关。
他写作《三里湾》的目的在于对农村合作化问题的思考,是因为下乡工作时感到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农业合作化应不应该扩大,对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和对扩大农业社有抵触的人,应该怎样批判[7]。但是,解放区特殊的历史环境不允许过多地提出问题,赵树理的《三里湾》表面上看起来是“歌德”的,其实,从侧面批判了农村隐藏着的问题。《三里湾》的叙事焦点就是“问题”。从“问题”切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广阔社会生活,通过“家庭”在这场变革中的矛盾和变化及其与社会的互动,讲述三里湾村的农业合作社。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而家庭则是社会中最基本的单位,赵树理选择将家庭和问题联合起来的角度自然是很合适的。《三里湾》将合作化运动带给农村的“新”与“变”落到了实处。封建家庭马家的解体,怕老婆的袁天成革命,范灵芝、王玉梅和袁小俊的爱情婚姻关系变化是小说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是最富有生活气息的部分。
问题的解决成了《三里湾》的关键部分。为了解决问题,对于错误的思想开党内会议,做出批评与自我检讨,关于家庭内部的矛盾,当不符合主流政治的爱情模式出现时,都会在无形中对其进行约束以及纠正。为了解决问题,追求大团圆的结局,作者让这6个年青人在最后都找到了一条优化组合的路,配与了一个最为合适的对象。因此,这样解决3对年青人的爱情关系,也可以看做是艺术为政治做出牺牲与让步,而这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则是创作者本人的政治立场和态度。
[1]赵树理.三里湾[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了之.爱情有没有条件[J].文艺报,1957年3月号.
[3]高默波.书写历史:高家村[J].读书,2001(1).
[4]陈非.乡村文学的殉道者:赵树理创作行为的道德意义与历史功用[J].学术论坛,2008(11).
[5]刘克宽.阐释与重构——当代十七年文学沉思[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154.
[6]王彬彬.赵树理语言追求之得失[J].文学评论,2011(4).
[7]赵树理.谈谈花鼓戏:三里湾.[M]//赵树理文集:第4卷.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
I247.5
A
1673-8535(2014)01-0059-04
戴彬(1991-),女,江西:南昌人,广西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诗。
(责任编辑:覃华巧)
2013-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