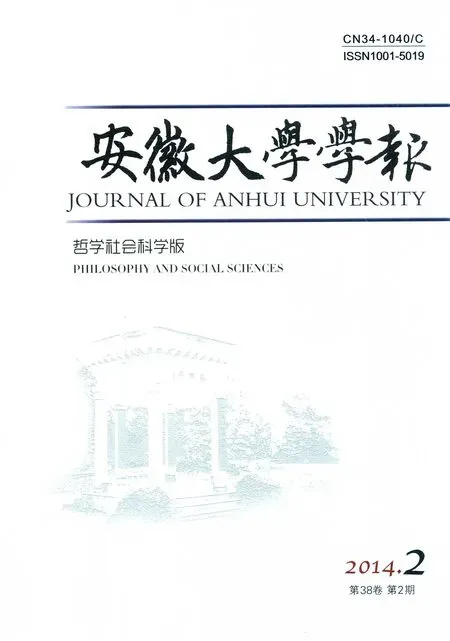1915—1937年中国报刊史探索的题旨情境及其书写
王天根
近代落后国家面临列强步步紧逼的语境,涉及政治格局与社会秩序的调整,传媒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就近代传媒史研究而言,尤要关注媒介系统及其在社会变迁中的生存样态,从中把握报刊的社会定位。从报业史研究本身看,不能仅拘泥于揭示报刊办刊时间、地点、人物等,将一部活生生的报业史变成报业名词解释或大事年表的汇编,而要探索报业兴亡盛衰的轨迹及其规律。近代报刊史学成果中,丁守和等集中全国专家编写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是标志性成果,部分参与者后来回忆称虽然编写时间紧,也存在一些问题,但目前为止仍有参考价值,至少可作工具书使用。而其后的报刊史乃至新闻史探索多倾向提供一堆知识,属有选择性的历史记忆,学术营养的层次性则有待分类或清理。当下若要在1915—1937年报刊史探索上有所突破,首先要超越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呈现的社会进化论模式、曾虚白《中国新闻史》序论倡导的社会有机体论模式,及部分报刊史论著呈现的阶级斗争模式。近年来的一些成果,包括笔者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探索》,从舆论建构层面讨论政治动员,过多精力集中在讨论媒介的主观能动性。当然,不论优劣如何,这些成果都是后来者再出发的起跑线。下文结合1915—1937年救亡图存的社会语境及报刊的政治趋向作探讨。
一、1915—1937 年中国报刊史的题旨情境
1915—1937年中国报刊史的题旨情境分析,首先涉及历史分期及分期的政治标准。目前中国报刊史学若以1915年袁世凯称帝及其历史反复为重要分界线,此前研究成果可谓丰厚,而1915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这一时段,学界虽有部分论著涉及大革命时期报刊及社会通讯,但系统研究及学理体系建构还有待拓展。学理探索涉及研究对象的定义及逻辑分类。以报与刊等为核心的近代社会通讯系统之间的关联本身属动态系统的重要构成。
近代报刊向国人呈现社会变革的纹理,亦展示媒介生态。传媒生态分析既涉及媒介也包括媒介环境,核心是舆论及其导向。报刊中的新闻及其基础上的时评可谓舆论呈现的重要形式。报刊连续报道及评论而形成持续的舆论方向感,则构成时代潮流。可见,书写报刊史,既要把握整体轮廓,又要注意细节刻画。探究近代报刊的题旨情境,既要纵向剖析诸多报刊新陈代谢的轨迹,又须从横向层面讨论近代报刊理论的中西交融互释。
(一)媒介历史纵向变迁呈现的趋向及历史记忆的逻辑起点
欧战与“五四”作为政治事件,其后续影响在报刊上有充分的呈现、展示。这既涉及国民革命的价值取向,也离不开反殖民主义的舆论氛围。后来者借助报刊史学的书写有选择地进行历史记忆,常有历史诠释之旨趣。
1.近代媒介环境变迁:通讯系统变动而形成的多元性及地域传播的不平衡性。
中国近代报刊史学离不开救亡图存压力下社会结构及其功能变迁的分析。近代社会性质复杂,既存有封建性的经济结构,也有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趋势,与此对应的就是西学东渐,诸如社会主义思想进入中国且社会主义运动逐步成为潮流等。这些对近代报刊舆论的新陈代谢皆有影响。
近代主流性报刊虽传布资讯,但更多的属言论担当,往往在社会框架的稳定与否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就社会框架而言,与封建制度相联系的是农耕社会呈现的结构性特征。这种结构性力量正如学人指出的:“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①[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8页。将这种建构性的结构主义用于分析中国传统社会框架无疑是合适的,但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着结构性的转型,特别是经济因素的变动对通讯系统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一,近代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及其变动趋向,与社会通讯系统呈现多元性特征有着内在的关联。近代中国面临西学东渐,本土传统的典章制度及其文化精神受多重经济因素变动的影响。就多重经济因素而言,西方资本、民族资本、官僚资本及封建性地主经济等在近代中国多元共存。多元经济在通讯系统的产业类型上亦有表现:既有外资支配下的报刊,也有官办的电话、电报或官督商办的电报局等传媒企业。就文化教育传承的空间结构而言,既有传统意义上书院式师徒传授,又有近代意义上大学的教学传播,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简言之,近代多种形式的传播及传播环境反映了通讯系统的多元性。
其二,近代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与大众传播在地理空间上呈现不平衡性亦有内在关联。近代中国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悬殊,被动的约开商埠与主动的自开商埠多在沿海沿江,城镇性质往往亦随之变化,多由封建的政治、军事统治中心演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重心及知识分子汇聚的文化中心。就文化传承而言,近代知识分子区别于科举制度下的传统读书人。科举在皇权为核心的“家天下”为背景的科层流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意味着科层流动另辟蹊径。一些知识分子通过留学而非私塾成为科学家。即便仍与经、史、子、集关联,但在西方经院哲学训练下的知识分子的言论报国有别于旧式文人的“道德文章”,他们可能成为哲学家、历史学家,等等。而城镇结构变迁中报刊、电报、电话等近代传播的发达,为图书馆、报馆、学校等提供了良好的资讯或技术等方面的支持。新的通讯业务提供了迅疾的资讯,同时亦塑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为新型都市的生长提供了传媒支撑。相比之下,广袤的内陆地区封建经济结构依然牢固。与经济水平大致同步的教育亦是如此,书院制的师徒传承关系依旧存在;受复制设备的限制,书稿的手工传抄仍大面积存在。诸如此类,使得近代意义上的社会通讯在内陆腹地举步维艰。可见,近代中国在空间上呈现地域性经济鸿沟,而报刊在地理上呈现的差异无疑是传播意义上的另类“知识沟”。与此对应,沿海与腹地在思想乃至社会开放程度上存在巨大落差。由此而论,我们一定要关注区域性报刊与区域社会的关联,尤其要探索区域性报刊是加强还是冲淡了区域特色。大体看来,面对近代救亡图存压力,区域性报刊也多有全国性目光。问题是,地方意识与全国视野两者如何进行视域融合,这往往是分析报刊等大众传媒冲击下,区域特色是彰显还是弱化的关键。这些分析同样适用于近代所谓的京派、海派文化比较及其与报刊传播关系的探讨。
2.作为媒介事件的欧战与“五四”及其影响:中国近代报刊史解释的逻辑起点。
1915至1937年,中国社会秩序的调适与传播建构相互整合。分析传播与社会之关系重构,须从时空层面区分社会类型。近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在时间与空间上皆有种种差异,探究差异原委可有多重视角。当下所谓媒介化社会,主要是从传播对社会的塑造层面着眼的。具体而言,传播参与社会型塑,并在社会建构及现代性的转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上的繁荣或衰落也无形中为传播提供现实的场景,这种场景或有利于传媒或不利于传媒的生存。就传统社会而言,王朝更迭频仍,但绝大多数王朝内部权、术、势等政治运作机制差不多,即权力架构呈现金字塔型,塔尖是君主,其下是官僚机构,基层是芸芸众生。与此对应,绝大多数王朝通讯系统的结构在传播的逻辑层次上亦呈现由上至下的趋势,以宫门钞、上谕、章奏为资讯内容的京报或邸报,也秉承君主为核心的王朝意志无形中进行上传下达。京报或邸报与王朝的权力架构,多属形式与内容之间的映射。由此而论,京报或邸报是绝大多数王朝权力外在的话语呈现形式而已。可见,政治与权力的话语表述及传媒呈现,往往有相对的一致性。体制内报刊的话语系统之旨趣,无外乎是统治者权力表述的工具。传统社会如此,近代亦如此。问题是,研究者在勾勒历史脉络的过程中如何把握历史分期的关节点。回溯历史,欧战与“五四”及其后续影响,是1915至1937年中国社会政治变动及其报刊呈现的重要风向标。从诸如《晨报》《大公报》《时事新报》《申报》等报刊上大致可窥探政治事件与媒介事件互动之一斑。
欧战爆发于1914年,其后续影响尤在1919年之后。欧战造成民族心理创伤及其历史遗产的清理显然有个过程。欧战一度被研究系核心人物梁启超等描绘成世界范围内工业文明的破产,与安福系密切关联的严复亦认为欧战是西方科学主导人类文明的毁灭。这些看法在研究系乃至进步党的《晨报》、安福系的《公言报》等诸多报刊上有充分展示。
欧战在思想上给欧美及国人带来了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以及自由主义,也促动了政论性报刊及报学研究的发展。正如戈公振所称,“研究报学之热度,则在欧战后始高。如美国哥仑比亚(Columbia)、威斯康新(Wisconsin)等大学,夙为研究报学之最高学府,而欧战以后研究最力者,则德国是也”。政治舆论动员及报学研究对同盟国、协约国而言皆是如此,“欧战或谓之宣传战也,或谓之报纸战,盖大战之勃发,对于报纸方面最先注意者,英国是也。在英国,以称为报王之北岩爵士(Lord Northcliffe)为宣传之领袖,其下有宣传最力之二大通信社:一为英国之路透(Reuter),一为法国之哈瓦斯(Havas),此专对外宣传者。若对于国内之宣传,则为北岩所有之《伦敦时报》(Times)与《每日邮报》(Daily Mail)等。德国睹此情形,为之惊愕异常。但德国之大陆电报通信社及其所属之宫廷派保守派同人,对于报学素未容心;虽报纸之利用,为铁血宰相毕士麦(Bismark)所深悉而曾行之,但终不知爱好与尊重。故报纸之进步,当然为之阻碍。迨欧战勃发,英法二国利用二大通信社,巧为对外宣传,至是而大陆亦踵行之,然已落后一步矣。盖英国有海底电线,长四十五万开罗,而德国仅有三万五千开罗。且通信社之内部组织,亦优劣迥殊。号称报王之北岩又聚精会神以赴之,德人视之,实有逊色。故宣传政策,谓由欧战而开一新纪元也无不可”。即欧战开辟了人类政治宣传的历史新纪元,亦为报学研究提供了素材,“德人既于欧战中得宣传失败之经验,故革命之际,同时知研究报学之价值。对于报学有兴味者,始有研究报学之组织。其后各大学均添设报学科。今柏林诸大学之报学科,又比较更为完美,且有报学专门学校。加之法科、文科、商科各分科大学内均将报学列为必修科,其意即社会之任何方面,对于报学应有正当之理解,然后对于社会之发达方有正当之引导也”①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第209页、210页。。相比之下,欧战前夕的中国属袁世凯执政,与之相伴的是癸丑报灾。失去舆论监督的权力愈发狂妄,袁世凯一度帝制自为,随后是皇权专制的复辟与破产。大体而言,袁世凯病逝即开启了北洋军阀统治,但由于记者有新闻采访权等,一些报刊培养了一大批名记者。报人报国,意为欧战后中国在世界的定位而积极献言献策,此成中国报刊史上一大人文景观。
其次,“五四”及其背景新文化运动,意味着现代性的中国亦须从文化上重建。这需要思想启蒙,报刊作为舆论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文化运动初从思想启蒙上倡导民主与科学,很快转向,进发到社会主义等政治理论宣传。此从《新青年》转变的历史轨迹中可窥一斑。而欧战的历史遗产也直接影响中国,巴黎和会议决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由此引发1919年5月4日学生大游行,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广为散发,学生在天安门集会并通过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这两份政治宣言分别刊登在5月5日《晨报》及5月6日《时报》上,再次引发传播意义上的政治动员。
作为政治事件的五四运动进入报刊后又变成传媒事件,报刊在政治鼓动中有其议程及框架。是年5月6日《晨报》第六版“评论”刊发“涵庐”(高一涵)的《市民运动的研究》,对两天之前的五四运动的性质与意义作了初步定位,他评点“五四运动”:“说一句老实话,这完全是市民的运动,并不单是学生运动,这件事顺着世界新潮流而起,很不可轻易看过,说他们是‘五分钟的热心’。”将五四运动诠释成市民运动,显系其解读的框架。5月9日《晨报》第六版刊发顾兆熊来稿《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他首先从“社会的生活与社会的秩序”层面分析:“此次示威运动中之关于警律及民法之各问题,皆当以上称之原则评判之。”其次从“道德之根本问题”层面分析。在作者看来,道德有主动、被动之分,主动的道德产生于“决斗”:“经一次决斗,人类之文明即增进一步。有决斗之决心曰‘勇’,故‘勇’之在伦理,占最高位置之一焉。”“以道德之本体论则‘强行我之所信’为‘主动的道德’,凡以胶固之形式羁束自由之理性者皆为‘被动的道德’。”“‘被动的道德’之所以有价值正以统属于‘主动的道德’故,不然则无宗旨、无意识而‘温良恭俭让’‘爱和平’‘守秩序’等等不过怯懦怠惰之装饰耳,然吾观于学生示威之举足知吾国青年中‘主动的道德’之复生。”再次,从“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方面阐述:“惟有阐明‘主动的道德’之根本的性质,且认清‘被动的道德’之有限的价值,使全社会中之人皆本其良心之所信决斗,决斗之结果,乃正如吾人之所期。”五四学生运动涉及方方面面,报刊对其呈现亦是如此。5月14日《晨报》第三版刊发“涵庐”的《再论学生事件和国家法律问题》,云:“若论正义拿什么作标准?我老实同你说,凡不卖国,不受贿,不受骗,不怕强力,都可算是正义,卖国不卖国,就是正义的标准。”总体看来,“五四”之后,舆论精英倡导学生走向民间,走向基层,并与劳工大众相结合。此涉及学生政治运动的社会定位。诸如此类,京沪报刊有充分的展示。
纵观1915至1937年报刊的变迁,可以说以政论报为主流的报刊其新陈代谢始终要面对欧战、“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这两个原点,并有所借鉴与反思。这两个原点内外关联,对后来者之借鉴既是颠覆性的也是原创性的。可以说近代报刊的新陈代谢就是两个原点彼此交叉的逻辑演化。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历史变迁对国人及报界影响的深刻性,是二战远远不及的。因巴黎和会没有很好地化解重绘世界地图等矛盾,二战不过继承一战的历史遗产而已。就人类文明断裂的程度而言,一战造成的后果是颠覆性的、划时代的,打开承载学人论政的近代报刊即可见。所谓新闻及中国新闻纸,自“欧战以后,经过巴黎、华盛顿诸会议,始稍明了世界大势,而时见有系统之记载。年来因教育实业之发展,社会新闻已大改观,如教育、商务之各有专栏是。然因军事扰攘,仍不免偏重于政治方面也”①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84页。。大体言之,一代报人或学人论政的逻辑起点往往就是如何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留给人类的历史遗产。
1915至1937年中国报刊时评以政论为代表,属典型的学人论政。此涉及学人、报人与报刊在政治、学术中的两难抉择。政坛乱象丛生,但22年的历史时光不仅仅是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关系,而是后来者继续从欧战及“五四”等新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不过,学人和报人更多的是回到欧战造成所谓西方文明的破产与中国新文化崛起的语境之中。西方科技文明破产与中国新文化崛起在报刊上形成质疑与对话,这是学理底蕴。而时评或因报人、学人论政的视角有差异,但两个原点在报刊史的长河中引发的反省显然有逻辑上的关联。
以欧战与“五四”为界,近代中国可谓前后两期,显经历史断裂。这种断裂多指告别过去的姿态与心态,毛泽东所论“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可谓从历史连续性层面诠释了断裂的历史纹理。建构与解构并存的1915年至1937年中国政治革命,史学探索趋向多个层面解读。其时报刊面对新旧思潮冲突与论战的语境。这一语境涉及欧战后世界版图的重新分割,其碎片化加剧,各种“主义”兴起。一战期间及其后的中国仍面临内忧外患,内忧外患涉及对内、对外关系。欧战对中国舆论精英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是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屠杀的武器无疑属科学进步的结晶,由此而来的“科学的破产”对舆论界代表梁启超等赴欧实地考察者来说是不言而喻的结论。面对欧战后残破的世界版图,竞争论、互助论等各种学说兴起,且百家争鸣。这些对既有战胜国兼有被殖民者身份的中国及其报刊舆论而言,无疑意味着多重学理的参照与多条道路的选择。
(二)横向意义上会通与近代报刊理论中西交融互释的特点
近代所谓资产阶级舆论精英办报常有其模式,早期多标榜同人办报的价值取向。从社会圈子及其身份认同来看,近代舆论精英大体可分为欧美留学派、留日派与本土知识分子圈。有留英背景的严复早年即折服于斯宾塞的“科学化”的社会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钟情于改良哲学的严复译介这些理论对早期的革命者汪精卫、胡汉民等亦产生深远影响,这些影响不仅表现在政治理论上,也表现在报刊理论上。另一方面,斯宾塞的社会教育思想传播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受到实验主义哲学先驱杜威的质疑。这些又间接对中国舆论界、思想界产生影响。总体而论,中国早期社会重构思想离不开社会进化论所倡导的生存斗争哲学的指引。生存斗争哲学的影响正如1919年杜威在北大演讲所称:“社会、政治的哲学不是凭空发生的,是在社会、政治纷乱不定的时候——病的时候,然后有医社会病、政治病的学说”,“社会、政治所以纷扰不安的原因,起于偏重一种人群的利益、兴趣,把别种人群的利益、兴趣都压下去;结果一种人群独占优胜,那被压下的不平起来,便与优胜的发生冲突”。乱世中易有“百家争鸣”,自然有各种各样的思想信仰,“一国的思想信仰,大致相同,固然是很好的事;但在这个变迁的时代,一致的趋势只可说是将来逐渐发展的结果,决不能硬求一致的。何以是逐渐发展的结果呢?只要让大家自由发挥思想,不合的逐渐淘汰,将来自能趋于大致相同的地步”①杜威著、胡适口译:《杜威五大讲演》,第2版,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0页、15页、83页。。这些言论大致可看出社会进化论为核心的社会功能哲学的影子。杜威在中国的演讲在思想界有着深远影响。舆论精英胡适等一生皆受业师杜威哲学的熏陶,胡适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验主义,不仅是为了改良社会,也是他主持报刊的学理基础。与胡适对应的是李大钊等先后从日本、苏俄引进马克思主义,并与胡适等展开论战。这场论战不仅关系政治变革的道路,也涉及报刊传播的理论创新。上述是主脉,下文对细节将有所揭示。
1.斯宾塞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报刊理论的影响。
近代“社会革命”及“政治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及其舆论精英胡汉民、汪精卫等受严译社会进化论的影响是显然的。早期革命派将报刊与“合群”联系在一起。大体而论,早期革命派的合群思想多源自严译《天演论》,亦与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社会进化论关联。1905年10月20日,孙中山撰写《民报》发刊词,称:“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吾于《民报》之出世觇之。”可见,孙中山认为革命领袖的天职是利用舆论引导民众。孙中山称“此群之历史既与彼群殊,则所以掖而进之之阶级,不无后先进止之别。由之不贰,此所以为舆论之母也。”⑤《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9页、288页。1911年12月31日,孙中山为《民立报》题词“戮力同心”,英文题词为:“Unity”is our watch word①《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81页。。强调在革命历程中报刊为核心的社会通讯系统应鼓吹民众团结,即“合群”思想。回过头来看,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与社会有机体论共同支撑起早期社会学的理论基石。斯宾塞社会学在世界广为流传,早期革命派人物马君武、汪精卫等注意到社会有机体论也在情理之中,特别是胡汉民。早期的革命派从社会意识层面进行社会分层,有所谓“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等社会有机体感觉的类型区分。早期革命者自视为社会中间阶层。所谓“中间”当然处在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中间阶层的政治宣传有向上、向下两个方向。即他们认为,“先知先觉者”要利用报刊舆论,对“后知后觉者”要采取引导的方式,对“不知不觉者”则要采取思想灌输的方式。
2.杜威实验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报刊理论的影响。
斯宾塞社会功能哲学传播到美国及经严复等译介传播到中国后,亦被胡适等自由主义者结合中国传统哲学加以诠释。胡适称在上海求学时,读过严译《自由论》和《天演论》,“严氏所译赫胥黎的论著,于一八九八年就出版,并立即得到智识阶级的接受。有钱的人拿钱出来翻印新版以广流传(当时并没有版权),因为有人以达尔文的言论,尤其是它在社会上与政治上的运用,对于一个感受惰性与濡滞日久的民族,乃是一个合宜的刺激”。胡适还谈道:“我对于达尔文与斯宾塞两氏进化假说的一些知识,很容易的与几个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自然学说联了起来。”②胡适:《我的信仰》,《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附录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59页。另一方面,斯宾塞“这个系统本身也正好与早期达尔文主义者的科学概念非常合拍,因此在所有英语国家,甚至较少范围内在欧洲大陆都得到广泛传播”③[英]索利:《英国哲学史》,段德智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4~275页。。相比之下,斯宾塞的社会功能哲学传播到美国,且与实用主义相结合,对培养了宋子文、张奚若、蒋梦麟、孙科、胡适等知名中国留学生的哥伦比亚大学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蒋梦麟谈及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我在哥大学到如何以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现象,而且体会到科学研究的精神。我在哥大遇到许多诲人不倦的教授,我从他们得到许多启示,他们的教导更使我终生铭感。我想在这里特别提一笔其中一位后来与北京大学发生密切关系的教授。他就是约翰·杜威博士(Dr.John Dewey 1859—1952)。他是胡适博士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业师,后来又曾在北京大学担任过两年的客座教授。他的著作、演讲以及在华期间与我国思想界的交往,曾经对我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发生重大的影响。他的实验哲学与中国人讲求实际的心理不谋而合。但是他警告我们说:‘一件事若过于注重实用,就反为不切实用。’”④蒋梦麟:《西潮·新潮》,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92页。杜威正是在斯宾塞的“教育为社会做准备”的学理基础上批判性地提出“教育即生活”。胡适受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他自云:“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我对实验主义作了一番有系统的阅读和研究之后,我决定转学哥大去向杜威学习哲学。”1915年秋至1917年夏季,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部就读,“这几年正是哥大在学术界,尤其是哲学方面,声望最高的时候。杜威那时也是他一生中最多产的时期。……当时哥大的哲学系实是美国各大学里最好的哲学系之一。”⑤唐德刚整理、翻译:《胡适口述自传》,第2版,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98页、91页。而蒋廷黻则有另一番境遇,他说:“当我一九一九年夏入哥大时,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认为我应该专攻新闻。我想如果我能成为中国报界大亨,我就能左右中国政治。我曾阅读英美两国许多报纸。也曾阅读许多对美国舆论具有广大影响力的主笔们所写的社论。我梦想在自己国家政坛上,能扮演一个像他们那样的角色。为此,我进了新闻学院。但我在新闻学院读书期间,有一年夏季,突然感到新闻人员对一国政治的理解仅是表面的,无法深入,所以他们只能随波逐流,迎合时代。我认为:为了左右政治,就必须懂得政治,欲想懂得政治,就必须专攻政治科学。因此,乃于一九一九年秋放弃新闻专修政治。但是不久我又觉得,政治也有它的限度。首先,政治科学讲的是抽象理论和计划。我相信伟大的政治家绝不会固守任何固定的原则。因为政治科学中所讲的政治,是理论的而非实际的。那么我要从那里去获得真正实际的政治知识呢?我的结论是:欲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方面下手。我已经由新闻转政治,现在我又从政治转攻历史。”⑥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76~77页。从蒋廷黻、胡适等后来的著述及主持的《独立评论》等刊物来看,他们显然受到政治哲学、社会功能哲学的影响。
杜威受胡适与蒋梦麟等邀请,自1919年5月1日来到中国,并目睹了五四学生运动。9月20日始,杜威在北大演讲《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称:“倘有人问我用什么方法可以使社会将来有条理、秩序的进化?我的答案是:利用正当的有功效的舆论机关,就是采集、研究、记载、判断、解说、传播,都是正确的。舆论能够做到如此,在社会进化上自占一个重要地位。……民治的国家,宣传事业的机关是很重要的。”①杜威著、胡适口译:《杜威五大讲演》,第2版,第78页。杜威的这些思想经过胡适口译后在诸多报刊上传播,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
杜威的实验主义学理多被视作欧美传播学思想的重要源头,而作为舆论精英的胡适,其传播思想显然受杜威实验主义及欧美自由主义的影响。胡适归国后筹办的诸多报刊,可谓世界范围内新闻专业主义洪流的一部分。这从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1938—1942)参加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Robert M.Hutchins)主持的新闻自由委员会(The Commis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这一举措中可窥见一斑。该会发表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报告。这一新闻传播学经典文献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当下,正如美国学人布莱文斯教授在《哈钦斯委员会走过50年:再现于今日公共与公民新闻事业的主题》一文中所称:“哈钦斯把一群中产阶级趣味的技术官僚论者和文化卫士会聚一堂,来决定一个自由新闻界的‘不可剥夺的’和‘自然的’权利这样的自由至上主义范式是否需要调整。”该报告正如布莱文斯教授评价的那样,“如果对哈钦斯委员会的中产阶级趣味的兴衰总结出持久的教益,那就应了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断言:第一位原理针对的是特定的时间、地点以及最重要的环境。当哈钦斯委员会在20世纪40年代进行思考时,维多利亚式的民主化理想的残余被消费主义包容了。”②[美]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展江、王征、王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3页、143页。用胡适业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去评价美国舆论界倡导的新闻专业主义,颇为精当。而用杜威的实用主义来衡量与评价胡适等的报学思想,亦当中的。
3.苏俄列宁主义对中国报刊的影响及近代报刊理论分野。
就近代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是时代潮流、世界潮流。马克思主义思潮乃至潮流在近代中国的成功显然与媒介系统的舆论动员密切相关,而报刊无疑是鼓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平台。“五四”前后的报刊上百种,组成了媒介系统,鼓吹马克思主义是整个媒介系统的反应。关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源流中的共产国际、日本社会思潮中的共产主义因素,无疑显示了报刊预流之精神,也展示了近代报刊的世界目光。
缺陷分析时需要计算一些分析指标,使分析结果得到定量描述,以便进行直观地对比。度量分析指标能够为定量分析缺陷提供基础。对软件产品发布后缺陷分析而言,分析指标主要包括:
就新文化运动中的《晨报》《新青年》等报刊而言,社会主义思潮是伴随着欧战中德国、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而起的。而中国“五四”前后舆论精英面对的不仅仅是欧战后世界地图的重绘,还涉及袁世凯病逝后社会秩序的重构乃至民族精神重建的种种设想。近代知识分子改造社会过程中对西方的审视及对近代民族精神的重构,与西方政治语境对中国的影响密切关联。就知识分子而言,自由主义者胡适、蒋廷黻等与社会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等,在由思想启蒙转向谈论政治后有诸多分歧。1919年下半年胡适与李大钊等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胡适倡导解决中国社会的出路要从问题出发,其学理依据来自杜威哲学。在胡适看来,“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都放在脑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③唐德刚整理、翻译:《胡适口述自传》,第2版,第206~207页。。李大钊等予以反驳,诸多报刊投入论战。
与封建的结构论及资本主义的功能论相比,社会主义者多强调民众思想启蒙要从社会底层做起,中国社会变革要从下至上。与资产阶级同人办报的学理相比,社会主义者多强调舆论宣传高度一致,党报强调阶级性、组织性与战斗性。当然事情有另外一面,正如杜威在北大演讲所称:“激烈思想传播所以如此迅速,其原因不在思想本身,而在思想以外的情境。例如最近俄国过激派传播这样迅速,我们可以断定,许多小百姓绝不见得了解他们领袖人物列宁的主义原理;其原因不在他的思想本身,而在俄国人的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屋住。”④杜威著、胡适口译:《杜威五大讲演》,第2版,第82页。杜威在北京的演说当然有针对中国所谓过激派政治传播之用意。但李大钊、陈独秀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强调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统治,以重建的精神进行革命。对待报刊舆论,他们强调要以民众为中心,且认为党报是党的喉舌。相比较而言,胡适等知识分子显然占据了主流的话语,而近代早些时候无产者无疑处在文化资源与社会资源的下游,他们作为民众群体的代表,无疑与社会草根阶层有更多的联系,这从报刊筹办上也可窥见一斑,他们的论著更多地反映了社会底层的风貌。我们考察抗战前的学人论政,“学人”既应包括胡适等社会精英,也应包括中下阶层的文化群体。两个层面合起来考察,就有可能较清晰地反映整体性的社会风貌。
简言之,近代西学东渐,思想与潮流交融的思潮风起云涌,其呈现的脉络无疑与展示的载体或平台有着密切的关联。就空间而言,从报刊史的角度揭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很有必要,若没有看到树与森林的关系,而把近代中国看作另外一种树,可能属误读。这种思路之下的报刊史书写有所偏向是显然的。对国人而言,民初面临政治转型,其时政论性报刊无疑亦是近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承载着重构政治意识形态的重任,对社会架构有重大影响。1915—1937年报刊史探索涉及国家与社会的理论分析框架,其间国家、社会重建中媒介议程与政治议程的互动关系密切,我们应当注意。
二、国家—政党—社会语境下报刊史的书写
近代报刊史学区别现当代报刊史学,主要是媒介环境不一样。制约媒介环境的重要因素是社会制度,其核心动力是政治时局的变迁。
近代媒介生态的变动显然离不开政治语境的考量。在欧战所谓科技文明破产与新文化重构的语境中探讨中国的出路,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构中讨论政党—国家的架构,近代报刊的学理路径大抵如此。即:从维新舆论与革命舆论的较量、国家与社会关系重建的视野出发,论述欧战语境下中国社会重组与报刊舆论的互动、报刊改革与京沪新思潮的互动、报刊与知识精英言路的聚合及分野,等等。近代报刊与报人乃至学者、政治家的关系复杂多变。近代特别是抗战前报刊的新陈代谢等历史变迁也反映了文人论政到学人论政的进程。
就政治语境而言,辛亥革命后,民国肇建。民国政治呈现政党—国家的框架,在国民党政治独裁的语境中则简称“党国体系”,国家机构多由执政党掌控,属典型的以党治国,故有“党国”之谓。近代党国体系既涉学理探索,更有政治语境。这显然有别于皇权专制下的金字塔型权力结构,这一政治语境对媒介生态的变动有相当影响。
就1915—1937年政治语境与媒介生态的关系而言,政党—国家架构与报刊的党化密切关联。1924年国民党改组在学理上确立的党国体系首要面对欧战冲击下的社会重心的寻找及社会秩序的调整等,报刊舆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时报刊政治宣传除了革命主题外,还涉及实业建设。救亡图存语境中革命与建设,属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星期评论》《建设》等反映了孙中山等为首的革命党人继续革命语境下建设之努力。随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政治舞台上形成了可与国民党对话的政治力量。总体而言,除社会主义、三民主义之外,还存有自由主义,这些“主义”都有自己的报刊作发言平台或舆论阵地。媒介与政治渐趋连体。
近代报刊类型已趋复杂,而母报、子报等纵横交错的诸多关系已形成生态系统的重要链条。报刊为谁服务,则不仅涉及媒介资本,尤关联意识形态。就报刊传播而言,国民党报刊是个系统,国民党统治下的党国架构既有独裁之旨趣,也意味着国家与社会之间有其他政治派系存在的可能性,尤其是其时中共领导下的报刊舆论,有反独裁趋向。就共产党的报刊系统而言,也有多个层次,党的刊物、共青团的刊物、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解放日报》等、在国统区的《新华日报》等等。他们面对的政治对象、面对的读者毕竟不一样,政治宣传策略显然有异。而诸如《独立评论》《新月》等,既非国民党也非共产党的刊物,实属存在于中心与边缘的中间力量。这些刊物不能仅以革命或反革命去区分。1927年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很长一段时间国民党刊物因执政党等政治优势,实际上处在政治宣传的核心地位;共产党则有个成长、壮大的过程,其领导下的报刊也随中共成长及发展由边缘走向主流。当然,共产党、国民党及其时的一些政党组织有其政治信仰,这些对其麾下的报刊显然有影响。以近代报刊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新青年》为例,可以看出其由同人期刊转向政党期刊的一些痕迹。国共关系涉及近代多重矛盾冲突、社会力量博弈的过程,各自的刊物显然也存在着分野与斗争。诸如国民党刊物内部,也有各种政治派系利益的不同,同一刊物的经理与主笔的看法有时也未必一致。总体而言,这些刊物代表社会舆论网络的建立,成为国民党或共产党等政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近代报刊史所以要关注党国体系有其原委。作为政党喉舌的报刊在党国政治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1927—1937年的党国体系实是近代中国社会乃至国家运转中新型的政治系统,区别于皇权之下的朋党政治。所谓近代中国党国体系有多方面的政治话语表述,它源自西方学理,借鉴欧美包括苏俄的党国系统。当然,早期中国的政党发展有个流变过程,首先是孙中山等领导的同盟会,后由宋教仁根据议会选举的需要将其改造成国民党;随着军阀政治的展开,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进步党进而改组,形成研究系;与研究系相对的是徐树铮、王揖唐等为核心的安福系,还有交通系等。研究系、安福系、交通系都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利益集团,属政党的雏形,都有自己的政治喉舌,如研究系下的《晨报》《时事新报》等。这些报刊在政治利益的角逐上显然要捍卫自己的政治利益。由此看来,须比较政党或军政利益集团在建国问题上的共通及分歧,从而提升看问题的逻辑参差性,可能更有利于分析近代中国什么是真正的社会发展,及政论性报刊在话语表述上有何立场。
1915—1937年间报刊史书写,涉及国家—社会重构语境下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及两者的合作与分裂。这是无法避免的。前者说不清,中间地带就难以揭示清楚。伴随着中国学院派知识分子的舆论诉求,以论政为主旨的专业化期刊应运而生。《独立评论》是近代留学欧美的中国知识分子学术沙龙发展到新阶段的伴生品,也为学人论政提供舆论平台。《独立评论》等刊物不但报道资讯,更重要的是成就学人论政的言说方式:近代报刊改变大众传媒下文人生活姿态甚至是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报刊有见之不见,也有不见社会所应见之功能。从这个层面来看,报刊往往被视作开拓眼界的利器,也可以成为有意识遮挡社会阴暗面的遮羞布。这往往与媒介议题设置功能密切相关。特别是近代学人探讨民主或独裁的话题,可谓众声喧哗。1934年底的汪蒋通电可以说是民主与独裁讨论的分水岭。民主或专制之论争由福建事变引发,前期的论争基本上是以胡适、蒋廷黻为核心在唱对台戏,这又与两人所依附的汪精卫、蒋介石等政治权势密不可分。后虽有一些文章陆续助阵,但基本上是为胡适、蒋廷黻的观点作注脚。后期的论争显示抗战后的文化精英在现实的政治操作与理想的政治制度追求上艰难抉择这一特有的媒介场景。无论汪、蒋合流还是分裂,只要外敌仍存在,国内政治秩序的规范化没有解决,学理的纷争就不可避免,而办刊经费相对独立的《独立评论》《大公报》等仍会为学人论政提供舆论交锋的平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独立评论》《大公报》等报刊政治建构功能急剧嬗变,涉及社会内在的结构与传媒外在的表述形式,两者或较一致,也可能矛盾。面对所谓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民主,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有不同的看法,其中包括胡适的民主论,也包括蒋廷黻的独裁论(实为开明专制论),但其核心成分是自由主义。胡适、蒋廷黻等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办报或主导舆论,多强调与社会上层的联系,往往远离民众。其时自由主义者与三民主义者在舆论场域上商兑既有交汇也有距离,罗隆基致胡适的信函提及中国其时三种思想鼎足而立:(1)共产;(2)《新月》派;(3)三民主义。思想在报刊上有投影,1915年至1937年报刊分为党报(国民党党报、共产党党报为主体)、民间报刊(中间地带的报刊),多少能说明一些问题。
就报刊史乃至新闻史书写的史学史而言,相比较台湾曾虚白的《中国新闻史》是站在其时国民党及其统治下的台湾政治立场来看问题,大陆方汉奇等主持的新闻史吸收了曾氏等在史料及其分析上的长处,但整体上以共产党的报业为主要线索,其他往往作社会背景交代。笔者以为,1915—1937年报刊史应尽量客观公正地看待共产党、国民党的政治立场分歧。即便是探讨国民党的报业,也不能局限于报刊的创刊或终刊的时间、地点等等,也要看到国民党的政治传播涉及党校、宣传部及其外围政治氛围等,也离不开中共领导人的一些论述。由此而论,研究国民党报刊史,研读《毛泽东选集》之类是十分必要的,因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任过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等等。至于国民党统治下的意识形态如何渗透到报刊,宣传部门及宣传人物在起什么作用,研究者必须注意。何况这些涉及史学研究中的知人论世。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与中产阶级的兴起也有密切关系,传媒可能是中产阶级政治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这在西方世界较为普遍,在近代中国的具体情况则需深入发掘史料。探究中产阶级的报刊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自由主义与中产阶级的关联。近代意义的报刊有了共产党、国民党为核心的政治磁场,党化甚至党报的意识更加明显了。面对诸多政论报刊,研究者思考问题要有比较意识。突出的问题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何以在国统区那么受欢迎?这里涉及党报为什么也能办得好看或耐读。总体而言,报刊政治宣传的成功与否,涉及社会结构、行动、话语等。报刊从话语层面唤醒革命尚涉及概念史、舆论史,而党化的报刊又是如何以革命话语的方式呼应的?诸如此类,说明研究需要细化。
简言之,近代中国经历了由皇权专制走向君主立宪,再走向民主共和等政治范式的转变。现代报人、学者、传媒与国家、社会的角色认同的关系极其复杂,作为文人存在的报人与作为政客的报人对现实的政治变革的认同肯定不同,这会影响到报刊内容的选择。在国家—社会的框架中,报刊是偏向国家或意识形态,还是偏向从底层进行社会秩序的重建?中国社会通讯系统是如何变化的?此类问题涉及舆论转向与报刊的政治功能开掘及两者的关联。分析近代报刊的政治功能乃至党化趋向,离不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调适。其时,“国家”多与现代性相伴而生,而“社会”与传统性密切关联,两者不仅有过紧张与对峙,也有断裂乃至错位。传媒在两者关系的弥合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我们在近代报刊史书写中应有所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