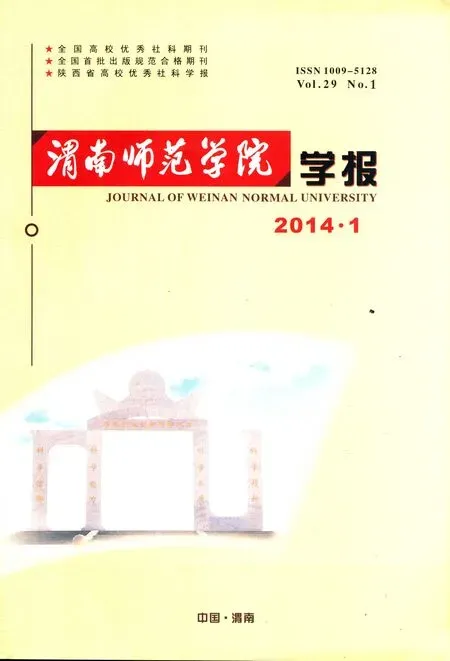曹植《洛神赋》之美学特征的多维考察
刘伟安
(昭通学院中文系,云南 昭通657000)
《洛神赋》是曹植脍炙人口的名篇。在这篇赋里,曹植建构了一个人神相恋的故事,荡气回肠,哀感顽艳。前人和当代学者们已经从各个角度对《洛神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围绕其主旨意蕴和艺术成就两个方面而进行。关于《洛神赋》的主旨,历来有“感甄说”和“寄心君王说”两种观点,并且这两种观点千百年来一直互相辩驳,争论不休。出于对有关《洛神赋》主旨的上述两种传统观点的质疑,当代学者们还不断另立新说,使得其主旨更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以说,关于《洛神赋》的主旨前人和当代学者们已经探讨得很多,但似乎始终未能得出一个学术界公认的结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恐怕这种状况还将持续,因此本文不打算参与这一探讨。而关于《洛神赋》的艺术成就,前人和当代学者们也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在探讨《洛神赋》之艺术成就的同时,前人和当代学者们自然不会遗漏对其美学特征的分析。毕竟一部文学作品的美学成就是其艺术成就的一个不可分割甚至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洛神赋》也不例外,因此学者们对其美学特征也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探讨乃顺理成章之事。不过虽然学者们对于《洛神赋》之美学特征的探讨已经相当细致而深入,但从多维角度综合而全面地探讨其美学特征的相关研究尚不多见。笔者认为,对于《洛神赋》这样一篇令古往今来无数读者们为之倾倒且对后世的赋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杰出作品,仅从单维的角度探讨其美学特征显然不够,片面地突出其某一方面的美学特征而忽视其他方面的美学特征尤非所宜,因为此类做法无法真正揭示其巨大而持久的艺术魅力的来源,也无法说明它何以能对后世赋创作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因而从多维角度对其美学特征予以综合而全面的探讨实有必要。而从多维的角度来看,《洛神赋》至少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美学特征。
一、词采之美
与其父曹操以及其兄曹丕不同,曹植在从事文学创作时是非常自觉地追求词采之华美的。而《洛神赋》又集中体现了曹植赋所具有的词采华美的特点。比如在作品中洛神芳容乍现,作者即以大量的笔墨对于其绝代风华予以了生动优美的描绘,如: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象应图。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
在这段引文中曹植从或远或近等不同的视角,并以一连串形象、新颖、优美、绚丽的比喻和衬托,对洛神初现时的容颜、体态、神情、服饰以及举止予以了生动的描绘和细致的刻画,让人感受到洛神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端庄,那样的高洁,那样的妩媚,那样的芬芳,又是那样的飘逸。在对洛神进行描写和刻画的过程中,作者还采取了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动静结合的方式,使得其形象更加光彩照人,栩栩如生。不过洛神虽然高贵华美,却又芳泽无加,铅华弗御,其天生丽质完全可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形容之。对于洛神充满美感的绚丽描述充分显示了曹植赋词采华茂的特点。又如:
尔乃众灵杂遝,命俦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扬轻袿之猗靡兮,翳修袖以延伫。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
洛神与众仙人在山隅里戏清流,翔神渚,采明珠,拾翠羽,五彩缤纷,几乎有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感。尤其作品中关于洛神“体迅飞凫”“凌波微步”以及“动无常则,进止难期”的一系列动态描写,使得洛神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德国文艺批评家莱辛曾指出:“诗想在描绘物体美时能和艺术争胜,还可用另外一种方法,那就是化美为媚。媚就是在动态中的美,因此,媚由诗人去写,要比画家去写较适宜。……‘媚’比起‘美’来,所产生的效果更强烈。”[1]326我国当代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在分析《诗经·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时对最后两句极为赞赏,指出:“寥寥八字,便把一个美人的姿态神韵,很生动地渲染出来。这种分别就全在前五句只历数物体属性,而后两句则化静为动,所写的不是静止的‘美’而是流动的‘媚’。”[2]135《洛神赋》中的这一段动态描写也有此种化美为媚的效果,使得前文关于洛神的静态描绘生动化了,因而更显现了洛神风姿绰约且飘忽若神的灵动之美。
上面所引两段文字想象瑰美,辞藻华丽,讲求对仗、排偶、音律,语言整饬、凝炼、生动、优美,渲染出了洛神动静结合的绝世之美,充分显示了曹植惊人的文学才华,也充分显示了《洛神赋》华丽的词采之美。后代无数作家在描绘女性之美时都从《洛神赋》中获得了灵感,比如从清代伟大作家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五回中关于警幻仙姑出场时的形象描写,即可看出《洛神赋》的影响。
二、距离之美
瑞土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美学家爱德华·布洛于20世纪初提出了心理距离说。他认为心理距离有别于时间距离与空间距离,它“是通过把客体及其吸引力与人的本身分离开来而获得的,也是通过使客体摆脱了人本身的实际需要与目的而取得的”[3]96。“距离要求被视为‘审美知觉’的主要特征之一”,因为距离的存在能使人超越现实的功利的需要而产生纯粹的美感,没有距离则美与美感均难以成立。
事实也的确如此,许多原本美的事物由于我们平常总是近距离接触,习焉不察,感受不到它们的美,只有拉开一定的时间或空间距离,我们往往才能排除外界利害得失的干扰而对其产生较为纯粹的审美观照。在《洛神赋》中,作者与洛神之间恰好保持了一定的空间距离。比如在序言中,作者交代了写作此赋的原由:“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而在赋的正文一开始,作者就写到自己邂逅洛神的背景:“余从京域,言归东藩,背伊阙,越轘辕,经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倾,车殆马烦。尔乃税驾乎蘅皋,秣驷乎芝田,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于是精移神骇,忽焉思散。”在这样一种人困马乏、精神恍惚的状态下,曹植“俯则未察,仰以殊观。睹一丽人,于岩之畔”,巧遇洛神。于是他问御者:“尔有觌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而御者则回答:“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则君王所见也,无乃是乎?其状若何?臣愿闻之。”这种构思,赋予了作品一种距离之美。
而在随后的叙述中,这种距离之美一直被保持了下来。正如常言说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类天生就是一种具有感性欲望的动物,而对于青年男性来说,最具有吸引力的美当莫过于异性之美,正如孔子感叹的:“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古往今来表达对于女性之美的倾慕的文艺作品可谓多矣!面对美丽、端庄、高洁、妩媚、芬芳、飘逸的洛神,曹植不由得不倾慕,不由得不动心:“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众所周知,曹植本非等闲之辈,而是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青年才子,这种青年才子自然也是女性所倾慕的对象,何况他对洛神又是那么一往情深,因而洛神被其真情所感动,对其心生爱慕之情也就自然而然了:“嗟佳人之信修,羌习礼而明诗。抗琼珶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凡是有过恋爱经验的人都知道,相互猜疑在男女恋爱中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处于热恋中的青年男女常常一方面如醉如痴,感到无比幸福,另一方面则又一遍复一遍地问自己:“对方真的钟情于我吗?”恋人们之间的山盟海誓,最主要的目的大概也就是为了消除双方的猜疑。但即便有了山盟海誓,恋爱双方彼此的猜疑也未必就能消除,恋爱者依然会一次又一次地想方设法互相试探以求证“对方是否真的钟情于我”这一问题的答案,并常常因此自寻烦恼。《洛神赋》的作者曹植也是如此,由于对于洛神太过爱慕,反而对其“指潜渊而为期”的誓言产生了怀疑,“执眷眷之欵实兮,惧斯灵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在此情况下,“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可见,作者曹植的怀疑对于洛神之精神的打击极为沉重,激发了其内心巨大的情感波澜,并且内心的情感波澜外显为了“将飞而未翔”的动作和“哀厉而弥长”的悲吟。这也难怪,爱情作为世界上最美好的感情,是容不下一粒沙子的,越是专一执着的爱情越是如此。对于一个执着的恋爱者来说,最大的打击莫过于所爱恋对象对自己的爱情的怀疑。而洛神的激烈反应消除了曹植的怀疑,增进了对她的的信任。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于是人神之间便无可避免地产生了一段缠绵悱恻的恋情。但遗憾的是,不管曹植和洛神之间的恋情多么缠绵悱恻,心心相印,二者之间却始终存在一种无法逾越的人神距离。而这种距离又增加了洛神之美,使得其更像神而不是世间的凡俗女子。
三、礼义之美
人类具有自然属性,因而具有生命激情和本能欲望,并且生命激情和本能欲望是人之为人的前提,不容轻易否定。但人类毕竟是一种理性动物,故不能一切都顺应自己的生命激情和本能欲望,而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对它们加以约束。而要约束人类的生命激情和本能欲望,可用的手段有很多,礼就是其中的一种。具体到中华民族,礼自古以来就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而中华民族对于礼的尊崇主要当归因于儒家的影响。儒家自古就崇尚礼,比如孔子就一再倡导“立于礼”(《论语·泰伯》),“克己复礼”(《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论语·颜渊》)。对于人类的情感,儒家也主张“发乎情,而止乎礼义”(《诗大序》)。进入近代以来曾有人批评儒家所尊崇的礼是维护等级秩序的工具,是束缚人性的枷锁,是吃人的恶魔,应当彻底否定并抛弃。但我们认为,儒家的礼教在历史上或许确实产生过一些流弊,但其积极意义也是不容轻易抹杀的。以爱情而论,儒家先哲从未否定过这种人类最美好之情感的正当性,在孔子整理编辑的《诗经》中就有大量真挚优美的爱情诗,但儒家先哲也鄙夷那种“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孟子·滕文公下》)的背礼行为。这种鄙夷确实有其道理。如果仅仅是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而放纵生命激情和本能欲望,那么恋情就降格为了动物性的肉欲。无数世俗的青年男女就是如此,他们往往因控制不住自己的肉欲而最终将恋情变成了苟合,因而也就丧失了爱情所本来具有的美学意义。
从《洛神赋》的叙述可以看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恋情虽然真挚缠绵,却并没有逾越人神之间的界限。换言之,这一场人神之恋遵循了“发乎情,而止乎礼义”的儒家模式。或许在现实中这种模式是不完满的,有缺憾的,但在艺术中却具有高度的美学意义。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把《洛神赋》与在此之前以及同时代的其他辞赋家们所写的同类题材的赋做一番比较。在曹植之前以及同时代也不乏描写人神之恋的赋,如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以及杨修、陈琳、王粲的《神女赋》,等等。这些赋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人神之间“嘉今夜之幸遇,获帷尝乎期同。情沸踊而思进,彼严厉而静恭。微讽说而宣谕,色欢怿而我从”(杨修《神女赋》),“顺乾坤以成性,夫何若而有辞”(陈琳《神女赋》),得以共享鱼水之欢。在这类赋中,人神之间的肉体欲望倒是满足了,但其美学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因为我们感受不到其中的女神比世间的娼妓高出多少。另一类则描写人神之恋的赋倒是提到了几句礼义大防之类的话,诸如“怀贞亮之清兮,卒与我而相难”“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宋玉《神女赋》),“心交战而贞胜,乃回意而自绝”(王粲《神女赋》)。但赋中的这些话往往类似于概念化的套语,难免给人以言不由衷之感,因而其效果也不过是劝百讽一而已。而《洛神赋》则没有如前代以及汉末魏晋时代许多同类的赋一样,进行露骨的性爱描写或粗俗的性爱暗示。如果在《洛神赋》中,曹植果真与洛神得以共偕鱼水之欢,则洛神留给世人的形象即使不是淫乱,其高贵性也至少会在读者的心中有所降低。与此同时,在《洛神赋》中,作者也没有如前代以及汉末魏晋时代许多同类的赋一样,在结尾部分模式化地勉强附上几句礼义大防之类冠冕堂皇的话,而是道出了内心的礼与欲的挣扎,这就避免了自我和洛神形象显得虚伪做作,因而更为真实。尽管在作品中主要是因人神道殊而使得作者曹植和洛神之间不得不以礼自持,但其道德意义依然不可低估。如果说作品中人神之间的自主恋爱象征了人性的觉醒,那么最终的以礼自持则象征了道德意识的升华。可见,正是“发乎情,而止乎礼义”的悲剧性结局,使得《洛神赋》所描绘的人神之恋净化了,升华了,美学意蕴也更丰厚了,因而大大提高了作品的艺术品位。
四、哀怨之美
人间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人的一切愿望,一切追求都要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并不是所有的愿望都能满足,也不是所有的追求都有结果。人的恋情也是如此,古往今来的痴情男女可谓多矣!虽然彼此相恋且“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痴情男女从来都不乏其人,但并非普天下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之《蒹葭》中,追求者即怅惘地吟咏道:“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古往今来不知多少有情人由于种种原因而劳燕分飞,也不知多少有情人由于种种原因而生离死别。曹植与洛神之恋情的结局就是如此。在作者曹植笔下,他与洛神的恋情是无比纯洁,无比执着,无比忠贞,无比缠绵的。但可悲的是,曹植深爱的并非世俗的凡间女子,而是一位美丽、高洁的女神。虽然洛神对于曹植也是情意绵绵,但“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她只能眼泪纷飞,献上美丽珍贵的江南明珰以表情意,且留下“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的誓言,杳然而去。“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洛神倩影一逝,从此芳踪难觅。
纵然自己对于美丽、高洁的洛神情有独钟,洛神也对自己心怀眷恋,但人神道殊,洛神可望而不可即,曹植也最终只能让自己的恋情发乎情而止乎礼义,只能在无限的怅惘中眼看着洛神美丽身影的离去。“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遗情想像,顾望怀愁。冀灵体之复形,御轻舟而上泝。浮长川而忘反,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可是无论曹植如何望眼欲穿,洛神的芳影再也没有显现。他只能“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可见,这一段人神之恋无论多么纯洁,多么执着,多么忠贞,多么缠绵,却注定无法成就,最终只能是一个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悲剧,整个赋也因此笼罩上了一层哀怨的氛围。正如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所说:“我并不主张‘欢悦’不能与‘美’结合,但我的确认为‘欢悦’是‘美’的装饰品中最庸俗的一种,而‘忧郁’却似乎是‘美’的灿烂出色的伴侣。我几乎不能想象……任何一种美会没有‘不幸’在其中。”[4]225在曹植之前以及同时代描写人神之恋的赋如宋玉、王粲的《神女赋》中,作者未必没有人神未接的憾恨,但由于人神未接的结局揭示得似乎过于突兀简短,且对于这一结局带给作者的心理体验未予描述或即使有所描述也着墨不多,因而其憾恨所带来的美学效果戛然而止。在《洛神赋》中,由于人神之恋的悲剧性结局,且作者将这种悲剧性结局带给自己的心灵体验做了大量的渲染,这就使得《洛神赋》有一种无与伦比且缠绵不尽的哀怨之美蕴含在其中。可见,《洛神赋》中的人神之恋虽然留下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永久憾恨和哀怨,但在这种憾恨和哀怨中洛神的形象也就更为美丽,更为高贵,更为圣洁,更让人神往了。
五、结语
钟嵘在《诗品》中称曹植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其实,这一评价不但可用之于曹植之诗,亦可用之于曹植之赋。在曹植众多的赋中,千百年来人们又公认《洛神赋》的美学成就最高。而通过上文对《洛神赋》之美学特征的多维考察,笔者认为该赋至少具有上述四个方面的美学特征:词采之美、距离之美、礼义之美、哀怨之美。当然,《洛神赋》的美学特征不止上述四个方面,比如从后人提出了关于其主旨的种种不同观点且均言之成理,就足以证明它还具有一种象征之美,一种阐释空间巨大的意蕴之美。此外,《洛神赋》或许还有其他更多的美学特征有待更深入的揭示。正是上述四重以及其他更多的美学特征使得《洛神赋》既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又荡气回肠,哀感顽艳,其艺术成就远远超过了战国时代的宋玉以及汉末魏晋时代的其他辞赋作家们创作的人神相恋之赋,因而古往今来的无数读者无不为其巨大的艺术魅力而倾倒,且后代的赋创作也深受其影响也就绝非偶然了。
[1][德]莱辛.拉奥孔[M]//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名著选编(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2]朱光潜.诗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3][瑞士]布洛.作为一个艺术因素与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M]//美学译文(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4][法]波德莱尔.随笔[M]//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