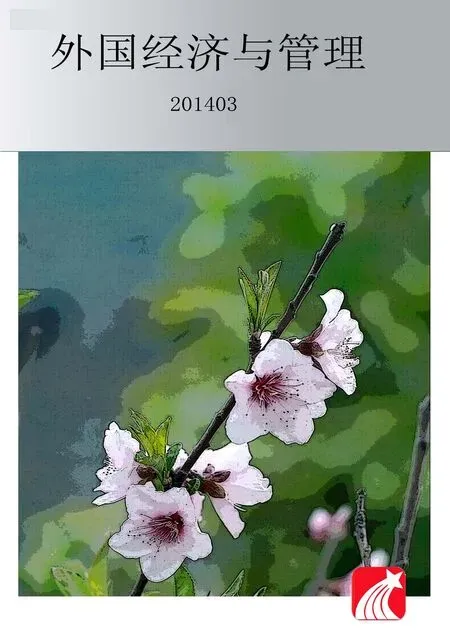职场管理的新领域
——职场友谊研究述评
张晓舟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361005)
一、引 言
通常,人们将一天中三分之一的时间贡献给工作。在工作中,由于必要的接触与联系,或者是因为分享相同的兴趣、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同事间不可避免会产生友谊,即职场友谊(workplace friendship)。作为正式任务目标与非正式人际关系两者交互影响的生成物,职场友谊在职场人际关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学者们对于职场友谊的关注与认同可以追溯到梅奥提出的“社会人”假设。梅奥基于霍桑实验,指出“组织中的‘社会人’不仅要求通过劳动获得收入,而且作为人,他们还需要得到友谊、安定和归属感……”20世纪70年代,以Hackman为代表的心理学家开始关注友谊机会这一工作特征要素,然而即便如此,工作中的友谊对于个人和组织的影响作用也并未受到重视。直至进入新千年,职场中的友谊现象及其影响效应才再次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职场友谊在组织管理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在Gallup在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中,30%的受访者称在工作中拥有好友,其中超过一半的人感觉自己对工作充满激情并且与组织有深厚的联系;而那些在工作中没有好友的人,只有10%会有这样的感受。此外,在那些声称自己在工作中有好友的人中,75%的人预计将在所在组织至少待一年,而对于那些在工作中没有好友的人,该比例仅为51%。可见,职场友谊的建立与维系对于员工自身的满意度和幸福感的提升以及组织认同意识的增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概而言之,作为友谊的一种特殊形态,职场友谊因社会性情感寄托而发,职场化色彩更加浓厚,突出表现为职场友谊的发展环境和质量与个人行为及组织相关结果息息相关。目前,虽然学术研究者,尤其是组织行为学者、心理学者和组织管理者,对职场友谊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是相比正式的组织关系(如上下级关系),有关职场友谊这样的非正式组织关系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相对缺乏,未来的研究需不断巩固和加强,以便为充分发挥职场友谊在促进高质量工作与生活方面的积极作用提供参考。
二、职场友谊的定义
个人作为社会网络的一个结点,与他人存在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关系产生于人际交往,而职场友谊正是人际关系在职场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是人们在工作中形成的一种非正式的亲密联系,是友谊在工作中的具体体现。由于学术界对“友谊”的理解存在差异,因此在相关研究中职场友谊这一概念也变得相对模糊。
一些学者从职场友谊的特征与表现出发对其加以定义。如Berman等(2002)认为职场友谊表现为包括相互信任、承诺、喜爱、分享利益和价值观在内的非排他性自愿职场联系。这一经典定义被之后的相关研究广泛引用。台湾学者梁金龙(2006)认为职场友谊是指个人对组织内人际关系友好程度的感受,这种人际关系应富含相互的承诺、信赖,以及工作和生活等方面可分享的价值观与乐趣,并且具有能够提供相当的社会支持的效果。部分学者从职场友谊的来源角度对其进行解析。如Morrison和Nolan(2007)认为,如果两个人感觉彼此非常了解,认为他们能发展为好朋友,那么他们即使不在同一场所工作,也不会只把对方当作同事(而是会建立起比同事更亲密的关系)。后来,Morrison(2009)又指出,职场友谊是在正式工作联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密切的伙伴关系。其中,“工作联系”可以从具体的工作接触和处在同一工作场所来理解。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如Sias、Smith和Avdeyeva(2003)从职场友谊的功能和作用的角度来加以理解,指出职场友谊能够提供情绪支撑、内在报酬,能够增进信息的传播与接收,甚至还能提供晋升机会。综上所述,必要的工作联系以及相似的地位、价值观、兴趣乃至教育背景都可能使职场中的两个人建立深厚的友谊。友谊不仅指友好的关系,友好的关系只是友谊发展的初级阶段。
工作中产生的友谊蕴含亲密与情感,支持与帮助,平等与互惠,真实与尊重,参与与分享;它依赖于彼此间的情感投入,同时双方在平等的地位上互惠互利,分享工作或生活信息,以信任和合作为基础。这些特征表明:一方面,职场友谊不同于职场中的其他关系,如雇佣关系、同事关系、师徒关系等。职场友谊更具有自愿性,追求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个人与社会情感利益,更为复杂;而相对来说,雇佣关系、同事关系等是基于组织中与工作相关的利益而存在的客观现实,是一种必要的联系,情感上的投入相对较少。另一方面,职场友谊也不等同于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一般友谊。职场友谊由工作联系演化而来,它的存在和发展可以说是团队工作的必然结果。同时,影响和巩固职场友谊的因素也和一般友谊大不相同。当然,相对于生活中的友谊而言,职场友谊还具有“表层化”特征和“两面性”特质,这都归根于友谊参与者同时具备情感寄托的真实性与投入动机的功利性。
此外,还要注意的是,拥有职场友谊和在友好的气氛中工作存在较大区别。职场友谊内在地包含个人主动而深层次的情感投入与收获,主观性较强,甚至蕴含工具性期望;而良好的工作氛围是从工作环境的层面所努力营造的积极氛围,与每一位员工及其表现息息相关。管理者和学者都认为组织中和谐友好的氛围很重要,但是,关于职场友谊的利弊,他们则有不同的看法。
综上所述,虽然学术界对于何谓职场友谊尚未达成统一认识,甚至在关系程度认定上存在一些分歧(例如部分学者认为其等同于伙伴关系,而部分学者则认为其不限于此),但是在职场友谊的特征以及研究意义上都找到了共同点,这为继续深入研究职场友谊这一新领域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视角。
三、职场友谊的构成及测量
测量职场友谊首先要对职场友谊的构成有清楚的认识。明确职场友谊的构成,并据其设计出科学合理的量表,是深入研究职场友谊相关问题的基础。回顾职场友谊构成研究的发展演化,有三篇文献在职场友谊构成研究中具有关键性意义。首先,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Hackman和Lawler(1971)为代表的学者在参考Turner和Lawrence(1965)关于工作特征维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六个工作特征维度,并首次将“友谊机会”(friendship opportunity)纳入工作特征维度之中(其余五个维度分别是工作多样性、自主性、完整性、反馈性以及合作性,其中前四个维度为核心要素)。Hackman和Lawler(1971)将友谊机会定义为“一项工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员工在工作中同其他员工进行交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员工在工作中与其他员工建立非正式人际关系”。他们运用职位描述和调查问卷等研究方法测量了友谊机会这一维度,并在此基础上证实“包含合作性与友谊机会的人际关系维度与工作满意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在职场友谊研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Riordan和Griffeth(1995)在进行其模型建构与检验时直接沿用了这一概念,并且发现友谊机会与工作满意度、工作投入、组织承诺和离职意向之间存在一定相关关系。然而,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职场友谊相关研究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Hackman(1971)、Riordan(1995)以及 Griffeth(1995)等的研究仅涉及友谊机会,而没有涉及在存在友谊机会的条件下,职场友谊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或强度。直到20世纪末,学者们才开始将研究视角转向职场友谊的强度和质量,并认为持续的组织绩效与个人行为与人际关系的质量密切相关。为此,Winstead、Montg和Pilkington(1995)提出了友谊质量(quality of friendship)这一概念,并将其应用于职场友谊与工作满意度之间关系的探讨,从而将职场友谊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到2000年,Nielsen等人批判地继承了上述研究成果,并结合Hackman(1971)的工作特征理论构建了基于友谊机会和友谊强度(prevalence of friendship)两个维度的职场友谊量表。其中,友谊机会是指“组织中存在可以让员工与其同事建立友谊的机会”,友谊强度则与“职场中同事间友谊的质量”相关。每个维度都由相对应的六个指标来测量。该量表由于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近年来被广泛使用(Song,2005和2008;Lin,2008;Morrison,2009;Lin,2010;Teimouri和 Hamid,2011)。职场友谊构成的发展与完善奠定了目前学术界对职场友谊的认识和讨论框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综上,在对职场友谊概念进行深度剖析的基础上,学者们就这一抽象概念的构成要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可以说,最初有关职场友谊构成的研究结论是友谊研究与工作特征维度研究相结合的产物,包括从友谊量表中筛选出测量职场友谊的指标,以及从工作特征维度中抽离出与友谊相关的“友谊机会”要素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测量的信度与效度,但也割裂了职场友谊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此后,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友谊强度”概念的引入弥补了上述缺陷。然而,在Nielsen等(2000)之后,关于职场友谊构成的研究一直没有取得大的突破,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职场友谊研究的理论基础比较薄弱。当前的研究侧重于运用量表去分析实际问题,而忽略了量表本身的准确性与科学性。
四、职场友谊的影响因素
众多研究表明,多种因素会影响工作中友谊关系的确立以及友谊的质量与强度,进而影响职场友谊与个人行为和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正如Francis和Sandberg(2000)所言,在不同的情境下,职场友谊可能对员工离职产生负向或正向影响,进而改善或者损害组织绩效。
建立友谊是一种个人选择行为,且多依赖于个人情感动机,因此,职场友谊首先与个体因素相关。影响职场友谊的个体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人口统计学相关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任职期限等。有关这些因素的考察结果并不十分一致,在通常情况下,年龄和任职期限与职场友谊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效果则不确定。考虑到实际意义,相关研究通常将上述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以判断在控制人口统计学相关因素的情况下,其他因素对职场友谊的影响结果。但即便如此,针对人口统计学相关因素的研究近年来仍经常出现。例如,Morrison(2009)研究认为,在职场中,女性往往将同事间的友谊当作必不可少的情感支撑,以满足其情感需求,而男性则更以利益为导向。这种差异使得不同性别员工对友谊机会和友谊普遍性的感受不同,从而使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和组织认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Morrison(2009)在其针对445人的调查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相对于女性而言,职场友谊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对于男性更为密切,而职场友谊与离职倾向的显著负向关系则只存在于女性被调查者中。因此,女性更有可能依据工作提供的社交机会(友谊机会)多少来决定是离职还是留职。第二,个体特征(例如性格、兴趣爱好等)及自我表露。早在20世纪70年代,社会渗透性理论就被用来解释人际关系尤其是友谊等亲密关系的形成。自我表露的强度会影响友谊的广度和深度,Rubin和Shenker(1976)指出,愿意自我表露的人比较容易获得他人的信赖。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多的自我表露对于职场友谊的形成和维护是有益的。第三,人际相似性。职场友谊的建立与维系主要源于高度的人际相似性。早在1985年,Brehm就指出拥有相似兴趣和感知的人容易建立个人友谊。这里的人际相似性既包括实质的相似性又包括感知的相似性,涉及价值观、兴趣、利益等多个方面。这些相似性能够提升人与人之间的吸引力,继而促进职场友谊的产生与发展。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相似性愈强,互动质量就愈高。但是,既有文献对该方面的定量分析还存在严重不足,现有研究的重点已经逐渐由个人心理层面转至组织层面。
除个体因素外,组织环境和工作情境也是影响职场友谊的重要方面,具体涉及工作特征、组织结构与层级、组织文化、领导者态度等诸多因素。首先,Hackman(1971)在工作特征分析中明确指出,工作通常能够对员工的行为与态度产生极大影响。工作特征影响着友谊机会,进而同员工差异交互影响着员工的行为与满意度。一些研究结论证实,依赖同事间协作的工作(而非技术型岗位),由于离不开员工之间的互动,因此更容易增进员工间友谊,这在医疗、教育等服务型行业表现得最为显著。其次,同事间的友谊由组织中的正式关系发展而来,因此,与正式关系密切相关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层级也会影响职场友谊的产生与发展。Krackhardt和Stern(1988)的研究表明,正式的组织结构会对工作中非正式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作用。在组织层级和职场友谊的关系问题上,学者们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Madison(1980)认为,职位较高的员工由于享有更高的权力,不需要与人竞争,因此职场友谊境况较佳。而Mao(2006)则指出,职位层级与职场友谊负相关。他认为组织层级是理解职场友谊的一个重要视角,且职位较高的员工更关注整个组织的利益,容易忽略他人的观点,因此相对于底层员工,会较少发展职场友谊。换言之,组织层级是发展职场友谊的一种现实障碍。再次,Mao(2006)在分析讨论中还强调了组织文化与人际关系密切相关,他认为组织层级与职场友谊的具体关系还受到组织文化的影响,若组织文化倾向于将员工看作是工作伙伴而非雇员,那么组织的氛围就有利于职场友谊的建立。此后,Song(2008)通过对韩国和美国两个国家地方政府雇员的比较研究,不仅发现文化差异对职场友谊存在显著影响,而且还进一步证实那些鼓励同事或上下级交流的规章制度有助于增加员工建立友谊的机会。同理,与组织文化密切相关的组织政治知觉同样会影响职场友谊。组织政治知觉是组织行为学领域的重要概念。资源的有限性使得以自利为导向的政治行为得以产生,而组织政治知觉就是对组织中这种行为的一种认知评价。一些学者认为,组织中较强政治知觉的存在会减少人际互动,进而导致职场友谊的减少。但是,Yen等(2009)则认为,组织政治知觉越强烈,环境越不确定,组织成员就越需要得到他人的支持与帮助,这会促进职场友谊的发展。他们的实证研究的确证实,二者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可见,学者们的激烈争论能够不断丰富和完善职场友谊的研究框架。
总之,从现有研究来看,有关个体因素对职场友谊影响的结论趋于稳定,相关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因素以及更为复杂的个体特质、个人感知等。相关研究在强调个体差异性的同时,也注重相似性探究。当然,个人因素研究也并非尽善尽美。笔者认为,职场友谊参与者建立职场友谊的动机是一个深层次影响因素,最简单的区分在于是否掺杂利益动机。考虑到职场友谊特有的工具性和利益性特征,初始动机应该是影响友谊建立与维系的重要基础,不过上述观点还有待验证。就组织因素而言,相关研究较为全面,涉及宏观组织文化和微观工作结构等多个层次,甚至涉及领导者的领导风格。需要注意的是,现有的职场友谊前因变量研究缺乏对同一研究对象的动态追踪,特别是缺乏对相关变量发生变化的前后对比研究。此外,前因变量中的组织因素相关研究揭示了职场友谊存在环境的复杂性,说明多重因素会相互交织干扰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五、职场友谊的影响结果
友谊是人们双向交往中的一种亲密情感,其作用不言而喻。同理,职场友谊对于个人成长和组织发展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为此大量研究都围绕职场友谊与其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职场友谊与工作态度、工作满意度、离职意向、组织承诺等变量的关系方面。此外,职场友谊的消极影响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只是相关实证研究比较缺乏。下面分别从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对有关职场友谊影响结果的研究进行梳理。
(一)个体层面
从个体层面来看,职场友谊可以促进同事之间的相互交流,增进彼此了解,促进兴趣与价值观的共享,并使员工彼此给予支持与信任。在满足个体情感性需求的同时,职场友谊也有助于个体获得朋友的帮助和更广泛的资源,从而促进个体工作任务的完成。Kram和Isabella(1985)对同事友谊的功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他们认为工作中的友谊可以促进个体的职业发展。而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建立职场友谊已经成为释放压力的一种策略性反应,特别是对于职场中的女性而言,当她们感到工作充满压力,或者对工作产生了负面情绪时,她们往往会在工作中结交更多的朋友。
随着职场友谊研究的深入,职场友谊的消极影响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职场友谊在发挥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往往伴随着流言蜚语、骚扰、裙带关系、偏袒等问题。Teimouri和Hamid(2011)在其研究中总结道,“职场友谊产生的上述消极影响会降低个体对组织的忠诚度,同时也会对组织绩效产生不利影响”。Morrison和Nolan(2007)通过研究列举了职场友谊涉及的矛盾问题,从而从侧面揭示了职场友谊给组织中的个体带来的困扰。
如上所述,职场友谊对个体的影响存在正面和负面之分。国外学者往往从职场友谊的正面效应展开研究,认为职场友谊能够让参与者在高压的工作中找到情感寄托与平衡点,并提高个人绩效。相对于国外学术界对职场友谊的乐观态度,国内学者对职场友谊的探讨则体现了较多的负面感情色彩,多以消极观点为主。正是不同认识的冲突交融,才使得职场友谊及其影响结果研究能够在短期内得到极大的丰富。
(二)组织层面
人际关系构成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同理,在职场人际关系网中,个体作为网络结点,其与他人的互动必然依托于组织背景,也必然会对组织绩效以及组织相关结果产生影响。
综合各类文献,有关职场友谊与其结果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更多地表现在组织层面而非个体层面。Nielsen(2002)在综合Riodan(1995)和 Winstead(1995)等人的研究成果后,运用自己开发的量表研究证实,职场友谊和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后来又得到Berman等(2002)、Morrison(2004)以及Song(2008)的支持。Ellinwood(2001)和Song(2008)等学者同时发现,职场友谊能够改善员工的工作态度。由于工作满意度直接影响离职率,因此可以推知职场友谊也与离职率相关。Riodan和Griffeth(1995)以及Nielsen等(2000)的研究证实,职场友谊的存在可以降低离职意向和缺勤率,这是因为职场友谊能够增进友谊参与者的归属感,并使参与一方对另一方产生自愿性义务感。此外,组织公民行为作为一个结果变量,同样受职场友谊的影响。组织公民行为属于个体自发实施的有益于组织的行为,包括利他行为。台湾学者陈建佑(2011)分析称,“当朋友需要帮助时,不管是否能够获得回馈,个体都会主动帮忙”。这就说明,职场友谊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陈建佑通过其基于286人的调查研究证实,二者的确正相关,即职场友谊越深厚,个体越可能实施组织公民行为。
在诸多关系中,职场友谊与组织承诺之间的关系最为复杂。组织承诺源于员工对组织的整体评价,较高的组织承诺意味着较高的忠诚度和认同感。组织承诺可以细分为情感承诺(affective commitment)、持续承诺(continuance commitment)和规范承诺(normative commitment)三个不同的维度。其中,情感承诺是指员工对组织的情感投入;持续承诺是员工因考虑到离开组织的机会成本而对组织产生的承诺;规范承诺即因社会责任意识而产生的关于继续留在组织的义务感。Teimouri和Hamid(2011)的实证研究表明,友谊机会能够促进持续承诺和规范承诺,同时,友谊普遍性与组织承诺的三个维度也都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综合而言,众多研究成果表明职场友谊可以改善员工的工作态度,提高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并且对组织承诺、组织公民行为等工作相关结果存在正向影响(Krackhardt和Stern,1988;Riordan和Griffeth,1995;Winstead,1995;Berman等,2002;Morrison,2004;Song,2005和2008),而对矿工缺勤和离职意向存在负向影响(Krackhardt和Stern,1988;Riordan和 Griffeth,1995;Morrison,2004)。职场友谊能够促进伙伴间的交流与协作,有助于共同任务的完成,因此职场友谊往往能够推动组织绩效的提升。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也对职场友谊能否长期存在以及职场友谊的作用提出了质疑。Song和Olshfski(2008)对职场友谊研究五十多年的发展所经历的各种争议进行了简要描述,指出除积极影响外,职场友谊也可能助长裙带关系、偏袒等不正之风,并且容易成为滋生流言蜚语或办公室恋情的土壤。从长远看,这会降低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度,进而对组织绩效产生不良影响。Morrison和Nolan(2007)也认为,职场友谊会分散员工的精力,从而降低工作效率。从现实角度而言,实务界的管理者对职场友谊的建立和维系仍持谨慎态度,尤其是上下级之间的友谊。
综观职场友谊影响结果相关研究,现有研究存在几个显著特征:第一,个体层面相关研究多为定性研究,而组织层面相关研究多为定量研究;第二,研究选取的角度多为管理者角度而非友谊参与者个人角度,且研究目的趋向于组织目标的实现;第三,在测量中对职场友谊的考察并不充分,表现在仅运用职场友谊的一个维度进行检验,而非全面考量这一概念;第四,结论的普适性有待验证。
六、研究不足与展望
2000年,Nielsen等人在借鉴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包括Hackman、Riordan和Griffeth等学者),开发了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职场友谊量表,职场友谊也因此重新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这一现象引起了部分管理者和实践家的关注,为实现新时期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创新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然而,综观现有文献,不得不承认目前有关职场友谊的讨论仍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与局限,这也为未来对职场友谊相关问题更深入的探讨埋下了伏笔。
第一,对职场友谊的理解和认识不统一。由于研究对象与视角的差别,学者们对职场友谊概念的理解缺乏统一的标准,一些学者在谈及职场友谊时,往往将其与友好的工作氛围混为一谈,从而在研究伊始就陷入认识误区。而且学术界与实务界在对职场友谊问题的认识上存在较大出入。学术界更强调职场友谊对员工行为和组织绩效的积极作用,而实务界更关注职场友谊的现实功能和作用,对待职场友谊的态度相对谨慎。此外,由于忽视了对概念构成的研究,现有研究多直接借用Nielsen的量表,虽然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但是并未充分考虑不同情境下职场友谊的特有结构。
因此,未来的研究有必要准确界定职场友谊的概念与构成。首先,未来的研究可以将职场友谊置于社会网络的大背景中,明确职场友谊这一特殊社会关系的具体特征。应通过一系列标准将职场友谊与组织正式关系、办公室恋情等进行严格区分,确定职场友谊的具体边界。其次,未来的研究不应局限于既有量表的应用,而应在夯实理论基础的同时另辟蹊径,补充和细化职场友谊的内涵与结构。这就需要结合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从多种研究视角出发,构建系统性理论模型。最后,职场友谊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应当让管理实践者参与其中,例如可以让实践者就量表指标的确定和筛选提供参考意见。
在清晰界定职场友谊概念和结构的基础上,后续研究还可以围绕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之间的具体关联展开探讨。作为组织中的一种关系形式,职场友谊与组织中的正式关系是相互影响的。应该说,职场中非正式的社交网络是正式组织安排的一种映射。正式的组织设计如果有利于营造能够促进员工交流的工作环境,组织成员就更有可能成为朋友。然而,组织关系错综复杂,角色冲突普遍存在。因此,职场友谊与组织正式关系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交互模式,应当受到学者们的足够重视。
第二,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当前职场友谊研究的重心已经由个体心理层面转向组织结构层面,然而这一转变也导致了现有研究对职场友谊参与者动机和心理的忽视。职场友谊的建立与存在离不开作为友谊感知主体的人,同时友谊关系只有作用于人才会对组织绩效产生影响。因此,笔者认为未来的研究要兼顾个人和组织两个层面。未来有关职场友谊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的研究应更关注人的主体因素,尤其是友谊参与者的自觉意识,包括动机、情绪劳动、工作倦怠等。
第三,有关职场友谊功能的研究有待拓展和深化。一方面,现有研究的广度有待拓展。受积极组织行为学的影响,现有研究仍局限于一种思维框架,即认为可持续的组织绩效以及个人发展依赖于职场中的积极关系,因此现有研究的内容多局限于探讨职场友谊对组织承诺、绩效、满意度的正向作用和对离职意向的负向作用,而弱化甚至忽略了职场友谊的脆弱性以及消极影响。例如,个别行业以及特殊岗位并不适合发展职场友谊,譬如保密机构。现有研究在这方面的探讨并不充分。另一方面,现有研究的深度还有待提高。正如Nielsen等(2000)所言,目前的研究存在因果关系不明的弊端,有时无法对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严格区分。就像Winstead(1995)在其研究中所指出的,尽管职场友谊的质量是工作满意度的前因变量,但是工作满意度同样也可能影响职场友谊的性质。
第四,当前实证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于某一类组织,因此研究结论缺乏普遍适用性。现有研究针对同一问题的研究结论有时差异较大,且对差异性缺乏必要的解释,研究结论的推广因此受到限制。因此,未来的研究在调查对象上应涵盖多种组织,应探讨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组织中的职场友谊现象及其与组织相关结果的关系,从而提高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和普适性。
第五,现有研究仅基于某一时点对调查者就职场友谊进行测量,并不具有持续性。而在职场中,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会改变组织行为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职场友谊具有动态性,因此,未来的研究应体现职场友谊的纵向变化,重视对职场友谊的动态考察,即通过纵向追踪样本数据来更加深入地分析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与职场友谊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发挥职场友谊在提高个体工作与生活质量方面的积极作用,进而为改善组织经营管理提供启示。
此外,目前我国除台湾地区外,有关职场友谊的研究还很少。能够搜索到的有关职场友谊的文献也主要从管理者经验的角度讨论工作中是否需要友谊以及友谊带来的负担与维系友谊的建议,多为指导性的,严格意义上称不上研究。国外学者反而更加关注我国职场的人际关系现状。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笔者试图对国内外有关职场友谊的学术研究进行全面的梳理,呈现既有研究的成果与重点,并尝试对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分析和判断,但这对于丰富我国的职场友谊研究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未来国内学者有必要加强职场友谊研究。同时也要注意,在研究中要充分考虑我国特有的组织文化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合理地判断国外的研究成果在我国的适用性,并展开本土化研究。
[1]Berman E M,West J P and Richter Jr M N.Workplace relations:Friendship patterns and consequences[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2,62(2):217-230.
[2]Francis D H and Sandberg W R.Friendship within entrepreneurial teams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team and venture performance[J].Theory and Practice,2000,25(2):5-25.
[3]Hackman J R and Lawler E E.Employee reactions to job characteristics[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Monograph,1971,55(3):259-286.
[4]Krackhardt D and Stern R N.Informal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al crises:An experimental simulation[J].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1988,51(2):123-140.
[5]Kram K E and Isabella L A.Mentoring alternatives:The role of peer relationships in career development[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85,28(1):110-132.
[6]Lin C T.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position,job attributes,and workplace friendship:Taiwan and China[J].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in China,2010,5(1):55-68.
[7]Morrison R and Nolan T.Too much of a good thing?Difficulties with workplace friendships[J].Business Review,2007,9(2):33-41.
[8]Morrison R.Are women tending and befriending in the workplace?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place friendships and organizational outcome[J].Sex Roles,2009,60(1-2):1-13.
[9]Nielsen I K,Jex S M and Adams G A.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scores on a two-dimensional Workplace Friendship Scale[J].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2000,60(4):628-643.
[10]Riordan C M and Griffeth R W.The opportunity for friendship in the workplace:An underexplored construct[J].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1995,10(2):141-154.
[11]Sias S and Avdeyeva T.Sex and sex-composition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peer workplace friendship development[J].Communication studies,2003,54(3):331-340.
[12]Song S H and Olshfski D.Friends at work:A comparative study of work attitudes in Seoul City Government and New Jersey State Government[J].Administration &Society,2008,40(2):147-169.
[13]Teimouri M and Hamid I B A.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place friendship and organization commitment[R].Aceh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2011.
[14]Winstead B A,Montg M J and Pilkington C.The quality of friendships at work and job satisfaction[J].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1995,12(2):199-215.
[15]Yen W W,Chen S C and Yen S.The impact of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on workplace friendship[J].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2009,3(10):548-554.
[16]陈建佑.从关怀和交易观点探讨职场友谊与组织公民行为之关系[J].人文暨社会科学期刊,2011,(2):1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