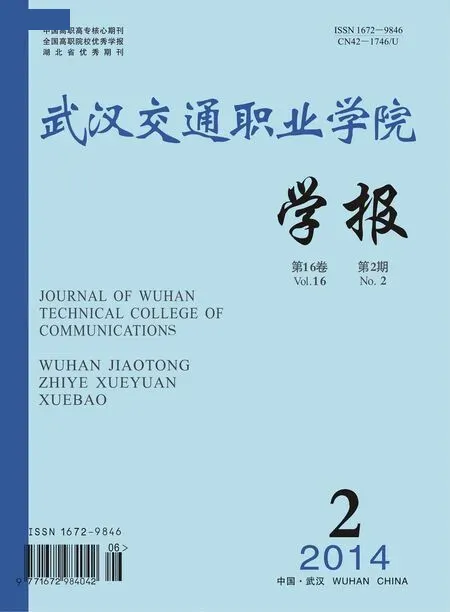中国当代版画民族性的思考*
梁 华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湖北 十堰 442000)
从定义上说,“艺术的民族性就是表现民族的本质特点所形成的艺术上的特殊性。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艺术的民族性最重要、最基本的内涵在于是否表达了民族精神,是否用民族精神去观察客观事物。民族精神是民族艺术性的核心和灵魂。”[1]而作为中国当代版画艺术,在当代文化语境的影响下,能否一如既往地坚持民族的文化传统,如何在当今中西文化交流频繁的环境下保持独特的艺术本质,是版画家在探索中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当代版画语言的民族性探索
上个世纪30年代初,新兴木刻的兴起,模仿西方的版画语言和创作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在零起步阶段,一批中国版画家为中国当代版画的成长奠定基础。但是,拿来主义的欧化风格慢慢不适应战火纷飞的中国环境,需要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富有战斗精神的版画作品来宣传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这种需要要求版画家创作的版画作品符合时代的审美特征,既通俗易懂又富有战斗性。值得高兴的是,版画家在探索中意识到这个问题,及时调整了创作方向,纷纷把目光转向中国民间各种艺术样式研究。作为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版画队伍,在汲取民族、民间艺术营养的基础上,注重中国人的审美追求,在形式上加强线的运用,把黑白、刀法等版画语言更好地与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如果说在民族化的进程中,解放区版画是急转弯的话,那么,国统区的版画则是缓慢而循序渐进的”。[2]在不断的探索中,某些版画家艺术风格的形成,标志着民族版画逐渐走向成熟。在题材上,有的版画家取材静物、风景;有的版画家取材苦难的农民形象,如被剥削的工人、英勇抗战的军人。在创作手法上,有的版画家注重黑白的光影效果,如李桦作品《怒潮》;有的版画家借鉴民间艺术的线刻手法,如古元《拥护咱们老百姓的军队》;有的版画家强调线与面结合的装饰性,如陈烟桥作品《剥玉米》,等。这种挖掘和借鉴的手段使新兴木刻在逐渐摆脱欧化的影响中形成了本民族的艺术风格,不论在解放区还是国统区,版画的表现语言都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
1949年后,随着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全国上下都投入到新社会的建设大潮中,版画艺术在探索民族性的道路上又面临新的问题。在革命战争年代,版画的创作模式是单一性的,解放后,版画家深入到广大的农村、工厂,创作题材聚焦于农民、工人,如:李桦的《征服黄河》、黄新波的《年轻人》、董其中的《送春肥》等,这些作品贴近现实生活。新版种的兴起丰富了木刻语言的表现力,如水印木刻和套色木刻在这时期也发展起来。水印木刻是最富民族特色的版种,画面中既有中国画的韵味又有版画简洁、概括的语言,有鲜明的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如李平凡的作品《我们要和平》、黄永玉的作品《阿诗玛》等,突出了水印木刻的装饰性和趣味性。
具有地方特色的版画群体的出现,对于繁荣地方版画和促进中国版画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四川版画群和北大荒版画群。四川版画家充分利用四川的特殊位置,寻找最有民族性的创作元素。李少言《老街新貌》表现出新社会的妇女走出家门,投身到生产劳动中去,表现了城市居民生活的巨大变化。牛文《欢乐的藏族儿童》通过巧妙的构图,把藏族小朋友手拉手唱歌跳舞的欢快情景表现出来,这种民族性的探索是画家深入体验生活的表现。李焕明《初踏黄金路》勘称此时期的佳作:暖黄色的主色调,S线的构图,将丰收的喜悦心情跃然画上,画中鲜明的主题、生动的人物塑造,把我们带进版画艺术的殿堂。吴凡《蒲公英》采用水印的印制方法,把一个小女孩吹蒲公英的常见动作提升到诗一样的意境,画面清新淡雅,传递出对生活的赞美。北大荒版画群是在十万军民奋战广袤的荒原中诞生的。二十世纪50—70年代,军人、农民、工人、大学生进驻北大荒,把沉睡千年的黑土地开垦出来,变成北大仓。与此同时,也诞生了一批以北大荒为创作题材的版画家,在全国同行中产生了深刻影响。大多数版画家以北大荒的自然风光和工作场面为刻画对象,用木版套色的方法“表现出北大荒浓烈的色彩及与大自然搏斗的英雄气概和热烈气氛,采用辽阔的构图,以再现北大荒的自然环境及创业场面的博大气象”。[3]其中最著名的代表画家就是晁楣,作品《北方九月》表现出密密麻麻的成熟高粱,隐约可见正在收割的农民和远处田野上繁忙的收割机。作品追求浓烈的火红色,大胆使用原色和响亮的色彩,构成红色的主色调和宏大的场面。
我们总结如下:30年代新兴木刻的诞生使中国当代版画从无到有,从模仿到为中国民族版画的形成奠定基础。40年代以解放区木刻为代表的民族风格形成,对各种表现形式的尝试,尤其强调线的运用,带有年画的装饰性。到文化大革命前,随着江苏水印版画的兴起,这种特有的版画表现形式既有版画的印痕味,又有中国画的韵味。至此,民族版画形式的探索逐渐完善。可以说,中国版画的研究和创作始终未离开中华民族这块土壤。
二、版画民族性与多元化格局的构建
改革开放后,在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影响下,中国的文艺出现一轮借鉴高潮。同样,画家大胆借鉴西方现代派的绘画风格,打破了原来单一的创作模式,使绘画创作向多元化格局转变,如“85美术运动”。绘画观念的更新打开了一扇色彩缤纷的艺术世界之门,写实的、表现的、抽象的、抒情的都拿过来画,令人眼花缭乱。艺术多元化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版画的民族性在现代艺术浪潮中迷失了方向,丢失了最根本的东西,模仿西方现代艺术的风格成为许多版画工作者的工作常态,老一辈版画家在新兴木刻时期建立起来的民族性版画在现代艺术的浪潮中湮灭,值得我们深思。中国版画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带着这样的疑问,一批版画家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去阐述了对中国当代版画发展的看法。
(一)坚守版画民族性不动摇
任何艺术都离不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作品无不烙印着本民族的历史痕迹、艺术特征等。埃及的金字塔、古希腊的雕刻、欧洲的油画、中国的国画等,都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艺术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典范,是独一无二的。鲁迅扶植和倡导的新兴木刻版画是民族性版画最有代表性的象征,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民族版画追求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着力展示中国历史的进程和民族气派。
版画的民族性要求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体现民族精神,其题材应与社会、民族、时代生活联系在一起,并凸显出重大题材,弘扬民族历史的主旋律。这类版画多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追求思想与内容的高度统一,激发人的精神斗志,催人奋发向上,在雅俗共赏中得到美的享受。我国老一辈版画家李桦、古元、彦涵、力群、王琦、黄新波等,他们的作品多数属于民族性的画法。在80年代的版画家中,如董克俊汲取中国民间艺术的创作经验使作品趋向平面性、充满原始的野性意味;江碧波的版画以我国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采用装饰性的手法表现出民族少女的婀娜多姿;谭权书以组合的方式,以线为手段表现出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
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借助一定的创作手段把艺术形象完美地呈现出来。因此,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创作之基,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如果一味地模仿和抄袭别人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到头来丢掉的却是我们的文化精髓。
(二)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汲取西方现代艺术的有益成分
民族性版画也不是固步自封的,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吸收和借鉴外国的版画艺术,才逐渐发展壮大的。国门打开,交流日益频繁,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蜂拥而至,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国内相对稳定的艺术形态。有的版画家在创作观念、创作技法上学习西方,按照版画的国际通用标准如印刷、尺寸、签名等一系列的规定进行创作,改变了他们原来的创作风貌。
在新的历史时期,老中青版画家以开放的姿态去表现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不再局限于主题性或叙述性的题材。如老版画家彦涵是一位不墨守成规的人,一生都在寻找版画的创新点,在作品《山村的节日》中刻画各种不规则的图形,通过一条曲折的黑线穿插在画面中,犹如康定斯基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组成一首跳跃不定的乐曲。王华祥作品《贵州人系列》以近距离的手法创作一批套色木刻,采用传统的手法却又有新突破,这种超视区的图式恰当地表现出故乡人的朴实厚道。贺昆作品《秋歌·发白的土地》表现出云南地域民族风俗特色,充满一种原始的、野性的味道。
(三)创作观念的改变是根本改变
受西方现代艺术的最大影响还是在创作观念上。观念的转变使版画家打开了视野,写实的、抽象的、表现的艺术形态都可以运用在创作上。版画创作不是局限于某一种固定的表现模式,而是强调视觉和精神对当代民族版画形成的强大创作力量。康宁介入版画形式的探索是比较早的,在作品中加入了他的个性符号来组合,减弱了黑白的对比色调,以大面积的灰度铺满画面,如作品《女人与马》,变形的马头和夸张的女性人体组成不协调的视觉。张广慧打破了传统的套色木刻方法,取消了主副版的套印,以通版叠印、多层次印刷的方法使画面产生一种硬边印痕的效果。如作品《北渚洗发》,“在对传统楚文化的眷恋和不断自省的现实中表达,因此画面人物图式多为平静肃穆的情氛”。[4]张敏杰将地域文化和乡土文化相结合,以原始主义的农民舞蹈图式转化为符号性的象征意义,体现出一种生命的原始活力,这种观念就是乡土的人文主义,如作品《城墙上下的舞蹈系列》。
三、当代民族版画从符号回归到精神本体
可以说,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民族性版画在学习、模仿、汲取、突变中走过来,彻底改变了版画原有的面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版画与国际间的交流已经处在一个无缝联接的平台上,国内的版画家到国外去办展览,西方大师的作品也频繁在国内展出,这种交流对促进和提高中国版画的创作水平意义重大。与此同时,经过激变后版画家的创作心态慢慢趋向平和,版画家作为个体通过版画语言“在现实中去寻求艺术的意义,去触及社会问题,思索文化问题等等,版画需要通过本体语言的建构和边缘的摸索去表现当代人的精神”。[5]
(一)版画民族性的当代意识
在互联网、信息化的时代,版画跟其他艺术一样,也受到极大的冲击和影响。一方面,对新语言、新技术、新形式的诉求,对纯精神、纯技术的追求,削弱了版画的功利性、主题性,促进了画家主体意识的增强,这种审美取向建立在当代意识的基础上。另一方面,版画越是当代性、越是国际性,更突显出民族性的重要,具有民族精神和特征的版画才能在国际上显示出本民族的优秀文化。
新时期版画家迷恋版画纯粹的技术性,注重精湛刻印技艺传递出的版画细腻或粗犷印痕之美,强调视觉带来的愉悦享受。因此,对制作性、技术性、借助媒体的介入在探索上都有突破性进展。在各个版种的领域,都涌现出一批代表性的版画家。陈琦在水印木刻中对线精准的把握,对水与色的精确计算,把印刷技术推进到一个新的境地。郝平的《古瓶》系列以精巧的线刻技法印刷出古瓶的高雅格调。徐冰的《天书》以惊人的毅力,耗费两年时间刻出自编的汉字,强化了雕刻技术的艺术性。
新生代版画家缺少对社会、历史的责任感,借用新媒体的新技术,不管作品有没有思想深度或精神内涵,只管把作品表现出来,重形式或重技法。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对纯化版画语言,建构我国版画的当代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建设性的意义。
(二)本体的回归
任何艺术都有自身发展规律和艺术特性。艺术作品的本质就是审美,给人带来视觉上、心灵上和精神上的美感享受。如果让艺术承担过多艺术以外的负荷,就不利于艺术自身价值的显现。在革命战争年代,新兴木刻承担了战斗宣传的任务,承载的社会责任感胜过木刻本身的艺术性,我们不得不承认艺术作品的思想深度比纯粹的艺术本身更有说服力。文革时期的艺术作品为政治宣传服务,红、光、亮的绘画模式更是偏离了艺术创作规律,带有唯心主义和迷信色彩。改革开放后,版画家在探索中意识到版画本身的特征才是重要的,对纯视觉、纯技术和纯精神追求回归到版画的本体上来。
总的来说,当代版画要以民族的文化为根基,抛开文化基础,艺术形式就变成了空洞的东西,纯视觉和纯技术就是毫无意义的技法堆砌。版画本体的回归是建立在民族的根基上,又以开放的胸怀容纳世界优秀的文化。不管强调哪一方面,内容和形式都是完美结合的,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民族性是中国当代版画区别于其他国家版画的要点,也是一面镜子,不管艺术形式怎么改变,这面镜子不能丢。当代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各国、各民族都在模仿、吸收和借鉴中提升自己,保持创作的独立性和包容性。这一趋势有助于中国版画在世界艺术之林中绽放异彩。
[1]王宏建.艺术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256.
[2][3]齐凤阁.中国现代版画史[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0:121,189.
[4]张广慧.木版画工作室[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1999:33.
[5]李桂金.版画艺术教程[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79.